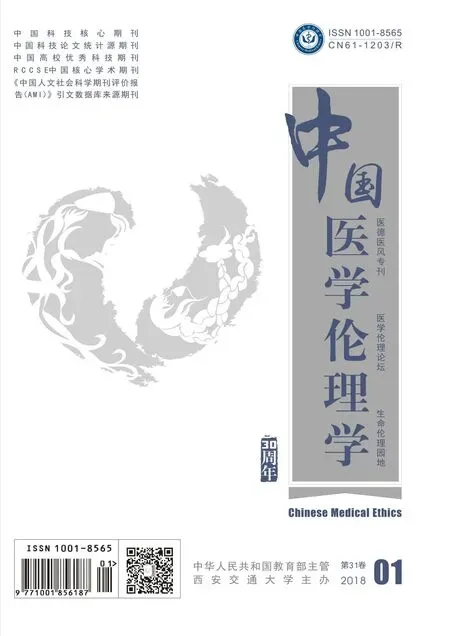“换头术”之论
引导教师:张新庆
(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北京100730,zxqclx@qq.com)
1 导言
“换头”问题近来吵得沸沸扬扬。意大利神经外科专家赛吉尔·卡纳维罗(Sergio Canavero)在2013年宣布了一项“天堂计划”,称已在技术上实现了人类“换头”的可能性。他的论文发表后仅仅一个月,患有先天性霍夫曼肌肉萎缩症的俄罗斯计算机科学家瓦列里·斯皮里多诺夫(Valery Spiridonov)就成为“天堂计划”的首位志愿者。在2017年11月,哈尔滨医科大学任晓平教授率领的医疗团队称合作完成世界首例异体头身重建术,一般称“换头术”。一石激起千层浪。
2 医学生的困惑:该不该允许“换头术”?
北京协和医院2017级研究生田苡箫:第一次看到这个话题时,我毫不犹豫地想:当然应该开展了。理由是,对科学的探索应该是无止境的。如果这项技术成功,意味着实现永生的可能性,意味着我们可能揭开物质和灵魂的面纱。只这两项意义就足以让人神往沉迷。
再三思考后,我犹豫了。且不说“换头术”成功之后可能带来的各种伦理问题、法律难题,单是从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到能够熟练实施这一技术还有多远的距离,中间要花费多少人力物力财力,需要多少实验动物和实验者,就足以成为一大难题了。
我曾试过从利弊两个方面分析“换头术”是否应该开展,但是无果。因为,没有一条理由可以做到一票通过或否决,也无法量化这些理由进行权衡评分。
我把这个问题转化成了几个小问题:从现在的技术水平到能熟练实施“换头术”还有多远?具体有哪些技术难题?成熟的“换头术”可能会带来哪些伦理问题?可有解决办法?“换头术”实施成功,最理想的效果是什么?能否具有解决如此严重的神经损伤的修复和免疫排斥反应的技术?有没有替代的治疗方法,比如将神经干细胞的再生作为治疗截瘫的方向?成熟的“换头术”真的可以延长人类平均寿命吗?如果现在成熟的“换头技术”就在我手中,我会不会把它推广?还是把它“雪藏”?推广之后引发的问题,我是否有把握处理?这样看来,我们如何看待“换头术”探索的这一过程才是现阶段我们亟待要面对的问题。
“成熟的‘换头术’真的可以延长人类平均寿命吗?”这个问题带有玄幻色彩,但我想,我的回答是“不会”。因为,“换头术”带来的一系列伦理、法律问题,是我解决不了的。我认为,一项技术对科学的发展有益,不一定对人类的现状也有益。或许现在时机尚不成熟,还不是开展“换头术”研究的时候。事物的发展是所有条件俱备之后的结果,水到渠成。如果真的有一天,技术成熟,“换头术”登上了人类历史的舞台,这个时候,解决一系列伦理问题就是必须的和迫切的。现在,我们可以尽可能全面地找出其中的伦理难题,未雨绸缪。
3 导入案例
田苡箫同学提出的问题也是相当多医学生共同面对的伦理困惑。为了便于同学们学会识别“换头术”中的伦理难题,掌握伦理分析论证的基本方法,进而培养伦理决策能力,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技术哲学课堂上,任课教师设计出如下一个案例,并提出若干棘手的伦理问题。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的一年级硕士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解答。
假如患者甲患有霍夫曼肌肉萎缩症,他的肌肉和神经已经严重退化,唯有开展头部移植手术才有可能延长生命。医生称自己有能力也愿意尝试着实施换头术。某一位终末期患者在生前预嘱中同意捐赠自己的躯体。由此,医生向自己所在的三甲教学医院提出希望开展换头术的申请。换头术都涉及哪些伦理问题?人类社会该不该允许在人体上实施换头术呢?
问题一:该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在审查过程中,需要重点考虑哪些因素?
教师:首先,换头术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其次,该手术的潜在风险与受益;第三,医院和医生是否具备实施换头术的资质;第四,患者及家属以及躯体捐赠者的家属是否真正做到了知情同意。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换头术是否存在可接受的风险-受益比。假如动物实验结果显示,换头术符合基本的科学原理,伦理委员会审查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换头术是否存在不可接受的风险。那么,换头术到底有哪些医疗风险呢?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王硕:不言而喻,换头会给甲带来躯体的伤害,瘫痪或者死亡。此外,术后可能对患者及其家属造成心理伤害,产生怪异的心理,让患者产生自我认知障碍、自我怀疑:我到底是谁?我是不是一个怪物?我和我的躯体是一个组合体,还是同一个个体?我所使用的躯体之前的个体是不是正在与我一同存活?手术后发现达不到自己的预期效果,久而久之现实与想象的落差都会对患者产生一定的心理伤害。此外,换头术还会对患者的家属造成心理伤害,如果一个男性患者换了一个女性的躯体,那么他的父母、妻子和子女如何能够坦然面对这种换头术?可以说,换头术对家庭角色产生的影响很难接受,这也是家庭伦理风险吧。
教师:假如“换头术”给患者甲或人类社会带来的仅仅是不可接受的医疗风险,而没有医疗收益的话,负责任的医疗机构是不会批准“换头术”的,负责任的医生也不会主动尝试“换头术”。既然“换头术”被炒得沸沸扬扬,一定意味着它有某种潜在的医疗收益吧。
首都儿科研究所郭秋瑶:无论手术成功或失败,人类都能从中获取大量宝贵的经验,有助于神经再生、免疫排斥反应、大脑低温保存及缺血再灌注损伤预防问题的解决。假如换头成功,患者的生命得以延续,生活质量提高,受到病痛的折磨减少,精神状态好转,就可以减轻社会的负担。患者家属方面受益,家庭的完整性得以维持,两个家庭的老人及子女的抚养义务可以由该个体承担,生活幸福感提升。但是相比之下,“换头术”的风险要高于其受益,应当等到该技术更加成熟一些再普及,但具体情况还是要尊重患者及家属对风险和受益考量后的选择。
教师:在医学史上多数革新性医疗技术在首次应用到病人身上时,首例受试者均可能存在较高的乃至似乎不可接受的医疗风险,但有时医学进步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在临床上实施换头术前至少需要下列条件:建立在牢靠的科学原理之上,严格动物实验和临床前研究,要具备技术上的可行性,医生/研究者和医疗机构具有资质,伦理委员会要在科学技术方面和伦理方面严格审查。
问题二:除了上述的风险受益分析外,换头术还需要遵循知情同意原则。那么,换头术会引发哪些知情同意问题呢?
教师:具体而言,患者的父母及配偶需要参与其中,但这些直系亲属在知情同意过程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假如父母尤其是配偶坚决不同意,从内心无法接受这种激进的手术方式,那么,伦理委员会能否据此而不批准这项手术呢?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刘琨、杨孟可:患者不能作为手术决策的主体,还应取得家人和社会的同意。原因如下:第一,家庭成员需要承担手术失败后带来的打击和伤害以及社会舆论压力,因此,他们也有权利参与决策;第二,手术后生物学意义上“性别”界定是一个难题,配偶及子女如何称呼他/她,他们能否接受这个事实;手术后个体的社会福利保障是否会保留和延续;第三,换头术带来了社会恐慌,社会公众也有权利参与决策;一旦换头术政策开放,可能会导致该技术的滥用;或者被不法分子利用,例如改变外貌形态特征,从而逃避法律的制裁;最后如果是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换头应得到社会的普遍接受和同意。
老师:在临床上面对较高风险的手术,医生通常会开展术前谈话,充分告知风险与受益,让患者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但是“换头术”作为一种颠覆性疗法不应遵照按照传统的临床伦理常规,而是要实施最为严格的知情同意,不仅需要患者本人同意,还要直系亲属(父母和配偶)的同意和签字。
问题三:除了伦理问题外,“换头术”还引发了诸多棘手的哲学问题。例如,甲的头与供体乙的躯体连接后,新形成的这个人又是谁,甲或乙,还是一个新人?
北京协和医院朱晨:换头后的这个人是供头者和捐赠躯体者的结合体。从哲学上讲,人是意识和物质的统一体。一个“人”的同一性存在于与意识相同系统的身体中。经历“换头术”后,从躯体上看,尽管甲还保有自己的头,但已经没有了原来的身体,所以他已经不是当年的自己了;从意识上看,虽然甲主要保留的是自己的思维体系,但是有研究表明,身体中的肠道菌群、体液环境以及激素水平等均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的思维方式,所以他的思维既不同于原来的自己也不同于后来的躯体,而是二者的结合体。综上所述,最后形成的这个人,是来源于二者新个体。
同理可得,若换上一位女性身体后,对于个人来说,他是既不同于这个男性也不同于这个女性的新个体。对于他生出的孩子而言,孩子不是他的生理学后代,而是属于那个女性身体的。因为从生理上来说,因为他身体中的大部分细胞是XX染色体,且具有女性生殖系统的功能,他将来生出的孩子的染色体来源于女性身体的卵子,所以他生出的孩子不是他的生理学后代,而是属于那个身体的女性原有者。
教师:同学们讨论的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关于换头后的身份认定问题,或人格同一性问题。
问题四:换头术会不会引发其他类型的问题呢?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王硕:首先,当富人和穷人都需要接受这个手术来保命的时候,富人就更有能力拿出金钱来手术,这就造成了社会稀缺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其次,如果患者成功地接受了换头术,那么患者的身份如何界定?他的身份信息怎样确认?如果患者今后出现了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是常规出入境,又当如何论断?这些都会给社会管理带来一定的社会管理难题
教师总结:
经过上述对换头术伦理问题的课堂讨论,或许不少同学会从上述伦理论证中得出如下结论:只要存在可接受的风险-受益比,又获得真正的知情同意,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就不应该禁止换头术。这种带有浓厚效用论色彩的观点不一定会得到其他道德理论(如:德性论、道义论)的认同。一种观点认为,人生价值不能简单还原成“寿命延长”或“痛苦减轻”等生理性指标,人的生命有其尊严。假如换头术损害了人的德性、高贵、尊严,就不应当尝试这一技术,也没有必要去计算风险与受益了,哪怕其长期的功利好处较大也不行。这就是伦理学学者在换头术论证中应该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