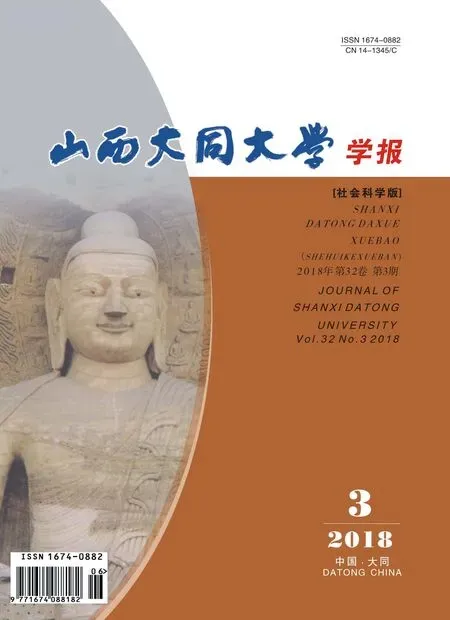刘逢禄《诗经》文体观研究
孙 娟,陈良中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 401331)
刘逢禄(1776-1829),字申受,亦字申甫,又号思误居士,江苏武进人。他作为清代常州学派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在清代经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其文学思想亦值得我们深入探究,他认为文体学上“黄初《典论》、挚虞《流别》约而未详,任昉《缘起》、刘勰《雕龙》辨而弗著”,[1](P172)在《八代文苑叙录》中指出,韵文之赋、乐府、诗、颂、符命、赞、箴、铭、连珠、碑识、哀诔和散文之序皆源于《诗经》,并对这12种文体之流变做了系统梳理,有助于认识《诗经》在后世文章学和文体学方面的影响。他由“《诗》分四始,《书》标七观”展开,在承袭魏晋“文笔之辨”观念的基础上将所述文体分为两大类:“主于用韵之文,从古诗发源”,“不用韵之文,从《尚书》发源”。梳理刘氏的文体观,不仅能发现文体序次内在的规律,也可以发掘其复古返本的治学精神,进而理解其今文经学变革的意义。
一、文体的序次及其与《诗经》的渊源
刘逢禄将发源于《诗经》的“用韵之文”依次排列为赋、乐府、诗、颂、符命、赞、箴、铭、连珠、碑识、哀诔,这并非随意拼接而成,而是依据各文体与《诗经》间的亲疏近远等内在逻辑进行排序的,前五为直接发源,后六为间接源于《诗经》。今以赋、颂、赞三种文体为例来揭示刘逢禄对文体间内在逻辑的认识。
(一)《诗》与赋 刘逢禄在梳理源于“古诗”的韵文时,将赋列于首位,认为赋与《诗经》关系最近,并论及了赋的源头、定义、流变及品类:
赋者,其原出于古诗,传曰:“不歌而颂谓之赋。”《汉志》题《骚经》为屈赋,今据以为首,荀卿之制异出同原,兼比兴之文,专赋篇之目,翱翔屈宋,宫商潜应矣。枚叔《七发》原于《招魂》,对问沿袭至广,昭明所刊无遗憾焉。吊哀之文亦出《楚词》,刘彦和云:“华过韵缓,化而为赋。”贾、马、潘、陆全乎赋矣。叙赋第一:曰骚、曰七、曰赋、曰颂、曰辞、曰吊文、曰哀文,凡七品,皆赋也。[1](P173)
首先,刘逢禄明确赋体源自以《诗经》为代表的“古诗”;其次,引《汉书·艺文志》说明赋与诗的区别在于“不歌而颂”;其三,刘逢禄所提及的作家以两汉三国为主,这潜含着个人的取舍倾向;最后,简述赋体的发展演变:由先秦之屈赋、荀赋、宋玉,到汉代辞赋家枚乘的《七发》,其后才有严格意义上的赋体,等等。此外,提及吊文、哀文也源自《楚词》。刘逢禄将赋体详分为七品,明确骚、七、赋、颂、辞、吊文、哀文皆属此类文体。
为何刘逢禄说赋“原出于古诗”呢?自刘歆《七略》将诗赋划为一个独立门类以来,具“讽谕之义”且“辨丽可喜”能悦人耳目的赋,作为一种独立文体,常被人与“诗”并提,比如曹丕《典论·论文》就有“诗赋欲丽”等论述。“赋”与“诗”的并提,彰显了两者的紧密关系,但究竟是何种关联呢?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有精彩论述:“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2](P134)体何物,又写何志呢?《毛诗注疏》明确其旨在于“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其言通正、变,兼美、刺”。[3](P11)刘勰又说:“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2](P134)《毛诗注疏》解释说:“升高能赋者,谓升高有所见,能为诗赋其形状,铺陈其事势也。”[3](P200)刘勰认为“赋之原始,即取六义之赋推衍而成”,[2](P137)即所谓“赋自诗出”,简单而形象地反映出诗赋的源流关系。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云:“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指,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庄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4](P288)可见,刘勰与挚虞都确认了“赋为古诗之流”这一命题。故而,刘逢禄将赋列于其首是根据亲疏远近的逻辑关系排列的。
刘逢禄弱化了赋体名称与《诗经》“六义”间的关系,而更强调艺术形式上的渊源,强调赋体与“古诗”相比,有“不歌而颂”的特征,说明赋只诵读而不入乐歌唱。刘氏又强调赋与吊文、哀文间的区别,即“华过韵缓”。《文章缘起》举贾谊《吊屈原赋》说明吊文“大抵仿佛《楚骚》,而切要恻怆似稍不同”,否则“华过韵缓,化而为赋”,其能逃乎夺伦之讥哉,可知赋之“华过韵缓”与吊之“切要恻怆”相对应,吊必须志哀,而赋体华辞更盛且韵律节奏更为缓慢绵长。
(二)赋与颂 刘逢禄认为“颂与赋同原”。在他看来,“颂”与“赋”一样皆出于《诗》之“六义”,都是直接发源于《诗经》的文体:
颂与赋同原,成康之没,厥声亦寝。三闾比类细物,启《洞箫》《长笛》之始;上蔡谀辞褒过,作扬雄、班固之诵。今以王马归赋,扬班领颂,志变古焉,次诗。[1](P173)
第一,刘逢禄为何说赋、颂同原呢?因为赋、颂皆出自《诗经》的“六义”,故而同源于《诗经》。第二,刘逢禄强调,颂和《诗》一道,随王迹之熄而厥声亦寝。第三,区分赋、颂为“王马归赋,扬班领颂”,并且强调“志变古”。变古为何意?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序》有云:“颂之名,实出于《诗》。若商之《那》、周之《清庙》诸什,皆以告神为颂体之正。至如《鲁颂》之《駉》《駜》等篇,则当时用以祝颂僖公,为颂之变。”[5](P205)他以祀成汤之《那》、祀文王之《清庙》和多美僖公之《鲁颂》为例说明颂有正变两体。刘师培也认为“颂之最古者,推《商颂》五篇,其词率皆祭礼祖宗所用。即《周颂》三十余篇,非祭祀天地神祇,即为祭宗庙之文,是知告于神明,乃颂之正宗也。逮及《鲁颂》,多美僖公,不皆祭神之词,是颂体之渐变。两汉以降,但美盛德,兼及品物,非必告神之乐章矣。”[6](P222-223)由于颂体有“志变古”这一问题,故而颂的序次稍远。
《孟子·万章》“颂其诗”中颂诗即诵诗,“诵与赋二者音调虽异,而大体可通,故或称颂,或称赋,其实一也”,[2](P161)但刘逢禄更注意区分赋、颂之异,他以王褒、马融“归赋”,扬雄、班固“领颂”。此外,刘逢禄还举屈原的“比类细物”与李斯的“谀辞褒过”来略论赋颂的同异:赋“比类寓意,又覃及细物”,[2](P157)颂则言辞谄媚、文过饰非。
(三)颂与赞 颂、赞二体的关系十分密切,因为赞之为体“发源虽远,而致用盖寡,大抵所归,其颂家之细条”。[2](P159)但刘逢禄更强调两者之间的差异,认为“赞者原于夫子赞《易》,《彖》《象》《文言》《杂卦》,皆有韵之文也。史家参以论颂志体,失其本矣。”他推赞之起源,以孔子作《十翼》为最古。认为赞旨在佐助其文,而非褒美之意。“逮及后世,以赞为赞美之义,遂与古训相乖。”[5](P210)就形式而言,赞为有韵之文,而论则无韵。“皆有韵之文”,说明赞体的独特性:“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辞。”[2](P159)刘逢禄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阐述赞体,意在复古。由于赞只是与颂有关联,并非是直接发源于《诗经》的文体,故而刘逢禄将其排列在序次靠后的位置。
由上述所及之诗与赋、赋与颂、颂与赞可见,刘逢禄所述文体虽皆源于《诗经》,但他强调区分其同中之异,将源于《诗经》的韵文按由近到远的逻辑排列,以反映各文体与《诗经》的渊源由亲到疏。刘逢禄将乐府、诗、符命的源头分别追溯到“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取三百五篇”,“三王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乐》亦亡”,“《玄鸟》《思文》”,故而这三种文体与上述赋、颂一样直接发源于《诗经》;而“箴、铭之体皆出三代”,“连珠兆于韩非,引于扬班”,“秦焚诗书,专尚名法,李斯刻石,法家之诗书也”,“哀诔原于古天子南郊定谥”,所以箴、铭、连珠、碑识、哀诔与上述之赞一样,是间接源于《诗经》的韵文。此外,刘逢禄虽将序作为“不用韵之文”归入“从《尚书》发源者”,但仍旧不忘说明《诗经》对序这一文体的意义:“序者出于夫子序《易》《诗》《书》。”
二、文体评价标准受《诗》教熏染
刘逢禄在条述发源于《诗经》的文体时,以《诗》教——“温柔敦厚”作为评价的终极标准。《礼记·经解》记载,孔子曾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7](P1254-1255)其中“温柔”以辞气言,“敦厚”以性情言。《礼记大全》阐明“教者,上所以勉下;经者,所以助成其教也。《诗》之规刺嘉美,要使人归于善而已,仁之事也”。“温柔”谓颜色温润、情性和柔,“敦厚”谓脾气温和、性情忠厚。可见,《诗》教的旨归不过是教人仁善而已,而“温柔敦厚”在《八代文苑叙录》中具体呈现为辞气的追求纯雅和性情的谨守本分。简言之,刘逢禄把经学的价值尺度作为文学的评判标准,强调文章导人向善的功能与效用。
(一)辞气:讲求纯雅 刘逢禄文体观中受“温柔”影响的评价标准,今略疏释一二,以为明证:
昔夫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今取其雅者次于赋。
自汉以后,皆郑卫之音也。意不戾古,情不越礼,君子犹有取尔,次乐府。[1](P173)
首先,刘逢禄明确了乐府的选择标准,即“取其雅者”。这一准则,不少文论家都曾有类似讨论。如刘勰“夫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先王慎焉,务塞淫滥。敷训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故知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声,瞽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好乐无荒,晋风所以称远;伊其相谑,郑国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观辞不直听声而已”,“赞曰:八音摛文,树辞为体。讴吟垧野,金石云陛。韶响难追,郑声易启。岂惟观乐,于焉识礼”。[2](P100-113)再如吴讷“《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故其辞亦多纯雅。”可见乐府一体辞意要雅正,若“哀怨不及中和”则“无复雅句矣”,“今之学者,深沉之思不讲,而讲为粗疏鲁莽之语;中和之节不谐,而益为寂寥简短之音。此其心术之所行,气数之所至”。[5](P31-75)乐府之“雅”,即要求辞气的中正平和。
其次,刘逢禄选诗要求“意不戾古,情不越礼”,即要求辞义与情意不能淫伤,亦符合上述雅正之旨。故而,刘逢禄的评价标准在辞气要求雅正。而外在的辞气是与内在的性情密不可分的。正如刘勰所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2](P65)辞气与性情是密切相关的。
(二)性情:谨守本分 刘逢禄的“温柔”标准体现于辞气的雅正,“敦厚”标准表现在坚守本份及“九能之士”的人生追求方面。以箴、铭为例:
箴诵于官,其制未改;铭题于器,迁转多方。刘彦和云: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令德。九能之士,作器能铭。扬雄、李尤稍存古制,至如钟鼎不韵,全成碑文,又无取焉,次赞。[1](P173)
刘逢禄在论述箴、铭时强调恢复三代之“古制”。箴应似《诗经》中《庭燎》《沔水》等篇,因为“箴是规讽之文,须有警诫切劘之意”,吕祖谦认为“凡作箴,须用‘官箴王阙’之意”,陆机《文赋》说“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李善解说“博约,谓事博文约也。铭以题勒示后,故博约温润;箴以讥刺得失,故顿挫清壮”,而萧统《文选序》也说“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而铭则“名其器物以自警”,虽也有颂德之义,但与箴一样皆主于警戒。姚鼐《古文辞类纂·序》云:“箴铭类者,三代以来有其体矣。圣贤所以自戒警之义,其辞尤质而意尤深。若张子作《西铭》。”[5](P188-202)可见,刘逢禄借申明箴、铭警戒的古义来强调“古制”,意在坚守文体发源之初的旨义,即坚持发掘圣人的微言大义以坚守圣人之心。
刘逢禄借“九能之士”阐明文章引人守本向圣的教化功能。所谓“九能之士”是:“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3](P199-200)作为坚守本义的凭借,刘逢禄将“九能之士”作为学者应有的人生追求。他认为“哀诔原于古天子南郊定谥,内史执策,太史读诔,卿大夫赐谥,小史读诔,鲁庄始诔及谥,厥后体传而文颂,失其本矣。叙述先世,亦诗人之则也。曰诔、曰哀策文,凡二品,次碑识。”刘逢禄为何说“失其本”?“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暧乎若可觌;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此其旨也。”[2](P213-214)所以诔之本义是颂美德行,而非郑玄所谓“累列生时行迹”。[5](P270)刘逢禄提出的“九能”和谨守本分,实质上都是要求不断挖掘圣人微言大义,复古以阐明并坚守圣人之心。
刘逢禄的评价标准受到《诗》教“温柔敦厚”的影响,表现为辞气上的雅正和性情上的守本,以及“九能之士”的理想人格追求。若前者为“文”,则后者为“质”,故而刘逢禄的文论观是坚持文质并重的。
三、余论
先秦时文章混沌未分,而后世体分派别,衍生出了许多体式,于是区判文体、考镜源流成为历代学者的自觉。不少学者都注意到《诗经》对后世文体的重要影响,如刘勰《文心雕龙·宗经》有所谓“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黄佐《六艺流别》“凡《诗》之流五,其别二十有一”;章学诚《文史通义》“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且“战国之文,既源于六艺,又谓多出于《诗》教”等,但论述过简而不够充分。刘逢禄丰富了这一命题的内容,并在其中融入了自己的价值判断与选择,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可供参考的文体源流演变图。在《八代文苑叙录》的论述中,不仅有“温柔敦厚”的《诗》教影响,还可看出刘逢禄崇汉复古的学术倾向,以及其文体观的疏失与价值。由此可以发掘常州学派的特色,并进而管窥时代思潮的论争。
(一)复古返本的治学宗旨 刘逢禄文章辨体的目的及讨论文章功能的意图,实质上是由其今文经学“反本开新”的治学旨趣所决定的。讨论刘氏经学思想观照下“复古”“崇汉”的文体学倾向,可以将还未详细讨论过的符命、连珠、碑识三种文体列出,作为例证略加论述:首先,刘逢禄论符命“原于《玄鸟》《思文》,变于李斯刻石。相如蔚为称首,绝笔兹文;扬班事非镌石,亦乖韵体。邯郸以下盖无讥焉”,[1](P173)举李斯、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作为代表人物,而其中后三位皆为两汉时期的名家。其次,论及连珠时说“兆于韩非,引于扬班,言近旨远,假物连类,亦箴铭遗意也”,[1](P173)再次将“扬班”作为这一文体流变过程中的关键代表。而后,在论述碑识时,将“新莽”作为与“上古”相对应的一个关键节点,此后用“后之作者”一带而过。由此可窥见刘逢禄在文体条述时的一条重要规律,即所述大多截止于东汉,汉以后则一笔带过,且除文体的发源时期外,他所关注和推崇的作家(如扬雄、班固等)大多集中在汉代。而刘勰、吴讷等人则通常会历数各时期的代表。在刘逢禄与其他文论家的对比之下,可以推测出刘逢禄所举典范的选择聚焦于汉代是自有一番深意的。
此外,在赞、颂二体的合离中,也能反映这一问题。尽管真德秀认为“赞、颂体式相似”,姚永朴也认为“此二者大体相同,故《古文辞类纂》合为一类。必欲求其别,则颂义自是宏大,凡命题之重者宜用之;赞义则较狭,凡题之稍轻者用之。此其不同处也”。[5](P214-215)刘勰亦将颂、赞合为一题,认为“发源虽远,而致用盖寡,大抵所归,其颂家之细条乎!”[2](P159)但刘逢禄却将二者分述(甚至在二者中插入另一文体——符命),其原因大概是由于“赞之一体,三代时本与颂殊途,至东汉以后,界囿渐泯。考其起源,实不相谋。赞之训诂,一明也,二助也。本义惟此而已。文之主赞明者,当推孔子作《十翼》以赞《周易》为最古。乃知赞者,盖将一书之旨为文,融会贯通以明之者也。”[5](P216)由于赞的古义本就与颂有别,故而刘逢禄在《八代文苑叙录》中将二者区分开来。
由上述两例可见刘逢禄的复古返本思想,魏源评其“由故训声音以进于东汉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1](P2)刘逢禄的学术趣旨在于刊落名物训诂而求“微言大义”,[8](P133)求“圣人之统纪”。知乎此,便可在宏观上理解刘逢禄的文章学思想。正所谓“《诗》三百篇,皆可以播管弦、荐宗庙”。[5](P10)在他看来,不仅《诗经》本身如此,源于《诗经》的其他文体也应具此功效,这是经学思想对文学观念的观照,也展现出刘逢禄“宗经”与“尊体”的思想。
(二)得失参半的文体观念 刘逢禄的文体学思想中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问题:其一,将天下文章根据“文笔之辨”分两类,未免失之过疏。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中所述“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9](P959)将文章分源于五经,比刘逢禄所分韵文源自《诗经》、散文源于《尚书》,更为细化。其二,文、笔之分下属的各文体是否各得其所,存在争议。如上述之哀诔与箴铭,刘逢禄皆划入《诗经》,而在颜之推看来则分源自《礼记》与《春秋》,此类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考证。其三,论述中存在交叉现象,文体划分不甚分明。例如颂和铭,分别与赋和碑识相牵涉等等。
有学者认为:“清代今文经学到了刘逢禄,对儒家各经有了比较全面的阐述,也有了较为系统的理论。”[10](P9)在文体学方面也是如此。刘逢禄文体观的价值可总结为四点:首先,他系统地梳理了源于“古诗”的“用韵之文”,有助于深入理解《诗经》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其次,刘逢禄文体论中“温柔敦厚”的《诗》教影响,对今天的创作实践有一定借鉴意义;其三,其“求圣人统纪”、阐微言大义的治学宗旨,在一定层面上对当代学术研究有启示意义;最后,有助于管窥刘逢禄所选定的40卷《八代文苑》,[11](P128-129)以及20卷《绝妙好词》、40卷《唐诗选》以及4卷《辞雅》的面貌。
[1](清)刘逢禄等撰.刘礼部集[A].续修四库全书(第1501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明)梅鼎祚编.西晋文纪[A].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98册)[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5](明)吴讷著,凌郁之疏证.文章辨体序题疏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6]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7](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5.
[8]黄开国主撰.清代今文经学新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9](北齐)颜之推著.颜氏家训[A].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8册)[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0]汤志钧.清代经今文学的复兴:庄存与和经今文[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11]张广庆.武进刘逢禄年谱[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7.
[12]洪湛侯.诗经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