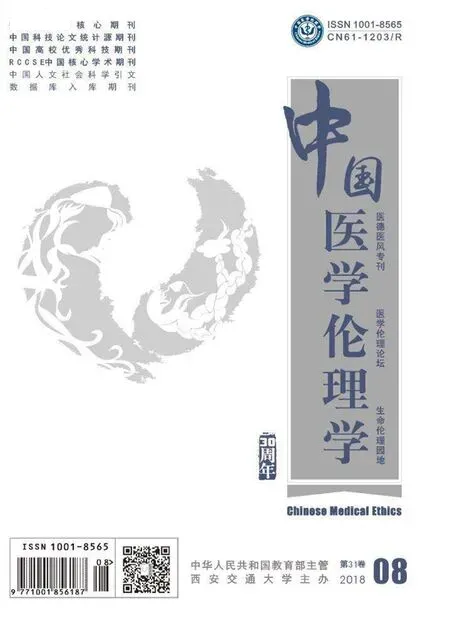人类“头移植”的伦理学探析*
张 迪,刘 欢
(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北京 100730,zhangdi87@outlook.com)
1 案例回顾
2017年11月17日,英国《每日邮报》一篇名为《富有争议的科学家宣称,世界第一例头移植手术成功》的文章激起了全球有关“异体头身重建”的争论,并被误读为中国已实施第一例活体“头移植”[1-2]。必须指出的是,该报道中卡纳维罗宣称的“成功”是在人类尸体上实现的。为避免歧义,本文将使用人类头身接合术(Cephalosomatic anastomosis,CSA)[3]代替“头移植”。
尸体CSA手术由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医生团队与卡纳维罗在中国共同完成。该手术共使用两具尸体,其中一具尸体D被诊断为脑死亡并将其作为身体捐献者,另一具尸体R则作为头部捐献者。他们分别对D和R的颈部进行切割,将R的头部连接到D的躯体之上,并对脊髓、神经、血管进行了重新连接,尸体手术共花费了18个小时[3]。卡纳维罗在媒体上的发言及两人发表的论文中都提及下一步将在拥有心跳的脑死亡器官捐献者与一位合适的活体患者身上完整复制这一“排练”(rehearsal)[3]。
无论是活体或尸体CSA,均受到科学和伦理学的双重质疑[4]。本文结合上述案例,对其面临的伦理学问题进行探索性分析,讨论是否应允许开展尸体CSA研究?是否应允许实施活体CSA?
2 尸体头身连接术的伦理学问题
对于尸体CSA,涉及两个重要的伦理问题:尸体的获取是否获得了逝者生前或其家属有效的知情同意?尸体及其器官作为稀缺资源应如何分配?
2.1 有效的知情同意
关于尸体移植,据已发表的论文来看,研究者获得了脑死亡患者(D)家属的书面知情同意,明确将遗体用于该次研究,而头部捐献者生前是否给出了明确的知情同意并未提及。此外,研究者称该研究获得了有关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并指出该研究获得了有关基金和部门的资助[3]。
患者或其家属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并不意味着研究获得了有效的知情同意,而伦理委员会批准研究实施不等于研究能得到伦理学辩护。由于笔者不清楚知情同意书的细节及伦理委员会的审查细节,在此只对知情同意和审查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论述。首先是知情同意问题,一个有效的知情同意应当包含四个要素,信息的告知、信息的理解、同意的能力和自愿的同意。
第一,捐献者本人在生前是否被告知死后遗体可能被用于研究,以及是否会用于富有争议的CSA研究?此外,其研究成果是否会发布在媒体上,以及如何保护死者及其家属的隐私等?如果患者本人生前未表达其意愿,以上信息是否已告知其家属?
通常遗体捐献时知情同意只提及未来将用于教学或/和科研,不会说明具体用途,其原因包括这些行为不会对死者本人造成伤害,包括对其死后名誉的伤害,并且也不会伤害到死者家属。但如果尸体的用途可能对死者或其家属造成名誉上的伤害,或家属的隐私有被暴露风险且因此对家属的心理和精神产生伤害,则应当明确尸体的具体用途,无论是用于教学、研究或其他目的。
此外,在获取知情同意时研究人员或医务人员是否将足够的信息传递给患者家属?我国目前推行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政策中,患者或其家属(在患者未明确拒绝捐献的前提下)可以选择捐献器官用于移植手术以挽救其他患者。他们可在遗体捐献用于研究和捐献器官救治真实患者之间进行选择,而不是仅提供给他们一种选项。如果家属未获知这些信息而做出捐献遗体用于研究的决定,该知情同意应当被视为无效。
第二,患者生前或死后家属是否具有理解这些信息的能力,以及研究人员在表达这些信息时是否使用了患者或其家属能够理解的语言?如果使用专业性的语言,例如“我们会使用电击和PEG对遗体的血管、神经、脊髓进行连接融合”,而非“我们会对遗体头部进行切割,并将其通过手术将其连接到另一具尸体的去头躯体之上”,患者或家属很难理解遗体具体被如何使用,即如果他们所作出的决定是基于对关键信息的不理解甚至是误解,则该知情同意应被视为无效。
第三,同意的能力指个体是否具有作出自主判断的能力。如患者不具有,例如患者处于脑死亡状态,则决定由其家属做出代理同意。代理同意应当符合患者的最佳利益,且在不违背患者的意愿的同时,遵守法律和伦理原则。
第四,自愿的同意。无论遗体捐献或器官捐献,我国现行法律和伦理学原则都要求自愿无偿。这要求捐赠者本人或其家属在做出决定时是自愿的,未受到胁迫、引诱或其他外部压力变相胁迫其捐献。例如,在家属作出同意捐献的决定前,告知家属如果他们同意捐献则会减免患者入院治疗期间的医疗费,甚至给予患者家属一定金额的经济补偿,这可能会对患者家属构成引诱或变相胁迫,使其作出非自愿决定。
以上四点是研究人员在获取知情同意以及伦理委员会审查时都应注意的关键因素。如果本次尸体移植研究未满足这些伦理学要求,即使患者或其家属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也应被视为无效。
2.2 稀缺医疗资源分配
人类遗体和器官,目前仍旧是稀缺的医疗资源。此次尸体CSA手术,其中躯体捐献人D为脑死亡后捐献,对于D而言,如果家属同意捐献器官用于其他器官衰竭患者进行器官移植,极有可能救治数位濒临死亡的患者。但本次研究中,D的遗体连同其器官被家属捐赠用于尸体CSA研究,如果从效用论出发进行分析,将器官捐献给数个活生生等待移植的患者,或整个遗体捐献用于尸体CSA研究,显然前者的效用要远大于后者。当然人们可能会反驳,尸体CSA研究可能会获得重大医学突破,有助于脊髓损伤患者的治疗。但就目前的科学证据来看,这些技术还十分不成熟,相关实验应首先在动物身上开展,而不是在技术仍处于初级阶段时便使用十分珍贵和稀缺的人体器官资源用于动物实验可替代的研究。因此,尸体CSA研究本身是否应当开展值得商榷。
如果将本次研究作为器官捐献进行讨论的话,根据我国现有法规和政策[5],尸体器官捐献应遵循自愿无偿原则,不应指定捐献。因此研究人员使用本可以救治多名患者的器官,去开展目前看似并无很高科学价值的CSA尸体研究,在伦理学上不但有失公正和效用,更不合规,甚至是违法的[5]。
3 活体“头移植”的伦理学问题
对于活体CSA,我们主要围绕以下四个问题展开分析:风险/受益、患者自主性、稀缺资源公正分配、同一性问题。
3.1 风险/受益
对于活体CSA当下是否应当开展,一个重要的伦理学问题便是风险/受益比。
首先是手术目前存在的风险及可能带来的伤害。目前该手术仍存在如下问题尚未解决:①未实现良好的脊髓功能恢复;②如何维持切割后等待移植的头部血流供应;③移植排斥反应如何及应对策略不详;④术后存活时间极短,以分钟、小时或天为单位计算(无证据表明移植后可长期存活);⑤移植后对患者心理上可能造成巨大伤害[6]。
如果说此类手术的适应证为瘫痪的患者,他们的期望是通过手术改善生活质量,可以支配躯体活动,使躯体具有感知力等[7]。但是,就目前的科学证据而言,手术无法修复脊髓功能[8-9],对这些患者而言,在脊髓修复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前提下,实施手术意味着不但要花费巨大的经济成本,并且瘫痪状态不会改善。此外,手术可能会出现严重并发症且移植排斥反应仍未得到妥善解决,即使服用现有抗排斥反应药物,其用量可能将远超现有器官移植的使用量,是否能够控制排斥反应暂不考虑,而患者可能难以耐受其药物副作用[10]。瘫痪患者不但无法得到治愈或治疗,甚至可能会死在手术台上,即使手术后存活,其生活质量也会远低于术前状态。
一些人认为CSA的适应证还包括除脑部疾病以外的任何危及生命的疾病,例如癌症、严重肢体残疾、严重免疫系统疾病等。但即使我们不争论这些适应证是否合理,就目前该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而言,其风险均远远大于受益。对于这些患者而言,如果不做该手术,他们的生存周期会远远大于接受手术的长度,且生活质量也未必较手术后差,更何况患者如果死亡,又何谈生活质量和生命的存在与否。
两位研究者将CSA与心脏移植进行对比,认为心脏移植在当时也备受争议,但最终被人们所接受。但是,CSA不同于心脏移植,就风险/受益分析而言,心脏衰竭的患者如果不进行心脏移植,患者的生存周期将十分短暂,即他们的医疗紧急度极高,并且即使因心脏移植失败而死亡,他们在生命长度上的损失小于CSA。目前,无论是瘫痪患者还是癌症或其他所谓的符合CSA适应证,甚至希望“延长寿命”的人,首先其医疗紧急度普遍没有心脏移植高,这意味着即使这些人不进行CSA,他们仍可以存活很长时间,并且这个长度要远远大于进行手术后的生命长度。因为以目前的技术考量,患者在术中死亡或术后数小时或数天内死亡的概率极大,且死前的这段时间患者处于疼痛、痛苦或无意识状态,而这对于患者的伤害和风险要远远大于其可能获得的微乎其微的受益。
有学者指出,CSA将使患者体验到严重头身不一致性,并导致患者精神错乱甚至死亡[10]。例如难以适应一具完整的不同的躯体。此类情况在人脸移植后有报道出现,包括身份认同的混乱[11]。
CSA对患者心理身份认知的影响可能与其他移植存在显著差异。
第一,移植百分比的巨大不同。与心、肝、肾等脏器的移植不同的是,CSA患者接受的是除头部以外的一整具躯体。例如之前躯体捐献者的行动,如犯罪、流产或舞蹈等,可能会引发患者对于责任和身体所有权的困惑[12]。
第二,根据目前的动物实验来看,CSA的存活期以分钟、小时或数天来计算,因此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断如果现在开展活体CSA手术,严重失败的可能性极高,并将最终导致患者死亡。患者及其家属是否能够从心理上承受这一极低生存率的事实需要被慎重考虑。
第三,即使患者术后存活,但脊髓并未成功连接,患者将面对(继续)终身瘫痪的现实及一系列生活质量和心理问题。
一些学者认为,即使手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已经达到科学共同体的认可,但在开展临床实验(这里使用“实验”而非“试验”,其中重要原因在于该研究的风险极高但受益概率低,提示研究人员和受试者研究的风险)之前,必须妥善解决这些手术所带来的心理问题[13-14]。
应先开展动物实验解决上述重要科学问题后,再考虑是否应当开展人类活体实验[1,8-9,15-16]。从现有证据看,当前CSA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极低,活体实验将对个体造成极大伤害,从风险/受益分析可以得出当前不应开展任何活体CSA手术,这也是《纽伦堡法典》及《赫尔辛基宣言》等国际伦理学准则所要求的[17-18]。
3.2 自主性
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生物医学研究,获得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是必要的。但对于目前的CSA手术而言,获得有效的知情同意几乎是不可能的[14]。目前并不存在某个确定的科研计划,且基于确凿及令人信服的实验数据,故患者无法认识到CSA的真实风险。此外,对于那些所谓符合手术适应证的患者(主要为高位截瘫严重脊髓损伤者,但不排除其他危重疾病患者),他们清楚地知道目前无法被治愈,故他们可能会不顾一切地寻求任何治愈方法,并对那些未经验证和缺乏科学证据支持的研究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而这种绝望可能使个体暴露在CSA实验巨大的已知和未知风险之中。
由一个绝望或濒死患者做出的关于手术实验的同意并不符合研究伦理(除非这一实验是其唯一提升生活质量和生存的希望,但就目前的科学证据而言,CSA手术并不满足这一条件),它既不会使受试者恢复脊髓功能,也无法延长患者生命,且有极大的可能降低患者生活质量和生命长度。当前开展这类活体实验是对脆弱患者的剥削[6],伦理审查委员会应拒绝批准研究。
3.3 分配公正问题
在本次事件中,躯体的供者(D)为脑死亡患者,即他的大脑功能已经不可逆的丧失,而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殊规定性就在于其具有意识经验能力,而这种能力的物质基础在于脑部功能,对于D而言大脑功能的丧失意味着他作为人已经死亡了。对于脑死亡患者而言,其心脏、肺脏、肾脏、胰腺等器官仍处于活性状态,这些器官如果用于器官移植手术可以救治数位濒临死亡的患者。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都会在征得患者本人和/或其家属同意的前提下,摘取器官用于救治其他器官衰竭的患者。
如果将这些器官连同该患者的躯体用于活体CSA手术,这意味着脑死亡者体内的众多器官只用于救治一位患者,与救治多位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相比,从效用论出发显然后者更佳。此外,如果考虑医疗紧急度优先原则[19],脊髓损伤患者的紧急度要小于不接受器官移植会在数月或数年内死亡的患者,就目前的器官移植水平而言,后者接受移植的成功率远远大于前者CSA的成功率,后者在生命质量和预期寿命上都会有质的提升。
因此,就目前CSA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而言,将捐献器官用于器官移植手术而非CSA更符合公正原则。
3.4 同一性
CSA涉及伦理学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人的同一性。是什么因素使得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个人仍旧是同一个人,是心理上对于自我认知的连贯性?还是贮存在头脑中的记忆?CSA是否会改变个体的同一性?
如果我们将A的头换到已被判定脑死亡的B的躯体之上,这一个体是否还是A?还是B?或者成为某一新的个体C?通常我们认为人的特殊规定性在于意识经验能力,而这些都直接受大脑支配,故默认情况下我们可认为移植手术后的患者应是A,而非B。但是,如果有科学证据表明,A移植到B的躯体之上后同一性发生巨大改变,如在换脸手术后可能出现的身份认同问题,我们必须思考是否应当允许此类手术。
这类似于20世纪各国对克隆人的讨论,克隆在技术上的成熟度要远超CSA,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禁止生殖性克隆[20],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同一性”问题,这一新个体的生存意义何在?就目前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极低的前提下,无论同一性是否发生改变,活体实验都无法得到伦理学辩护。
就目前的技术安全性和有效性而言,笔者认为不应允许开展人类活体CSA临床研究和应用。即使该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获得可靠科学证据支持,在开展研究前必须对其中存在的伦理学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在获得伦理学论证的基础之上考量是否应当开展研究。最后,为减少和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应加强伦理委员会的能力建设,保护患者和受试者健康福祉的同时,避免使国外科学家将中国视为具有巨大伦理争议之技术的“实验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