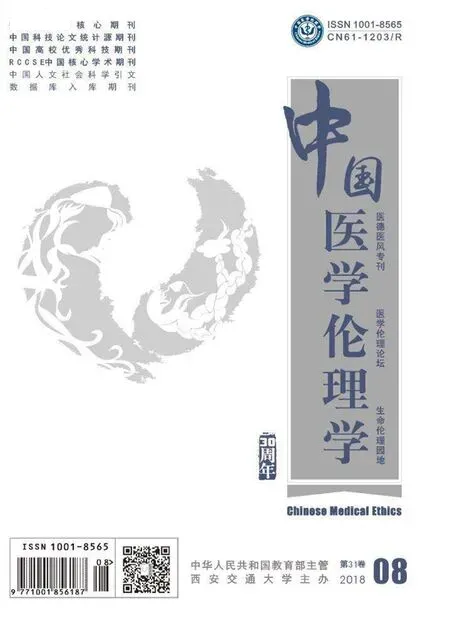耕耘好我们的风水宝地
——加强对传统文化中生命伦理智慧的发掘与提炼*
郭照江
(空军军医大学,陕西 西安 710032,guozhaojiang@aliyun.com)
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伟大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它是中华文明的精华,也是古朴智慧的宝库。作为生命伦理学工作者,应怀着使命感和紧迫感,自觉耕耘好这片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努力发掘与提炼古朴的生命伦理智慧。这对构建中国特色生命伦理学,促进世界生命伦理学的健康发展,将发挥古为今用、中西互补的独到作用。
1 从北京国际医德研讨会说起
1.1 一次富有特色的研讨会
1993年11月,中华医学会与国际合作与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了一场富有特色的国际医德研讨会。由会议主办方选定论文作者,指定交流选题;实名邀请赴会,控制总体规模。境外成员包括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士等国的36名学者,我国应邀参会和当地与会学者共计百人左右;会议将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置于同一框架之下交流研讨。
1.2 笔者的交流论文与会议共识
笔者在大会发言的题目是《我国儒家文化与传统医德》。文中主要阐释了三个方面的内容:我国古代儒家文化及其深远影响;我国传统医德的历史发展及其基本要点;儒家文化对现代医德建设具有的启迪与可能发挥的作用。论文突出强调:儒学问世之后,其伦理道德观念对历代医务工作者均有深刻影响,对我国传统医德的发展发挥了主导作用[1]。
会议取得的重要共识之一,是强调东西方文化交融互补是发展生命伦理学的必由之路。
1.3 该论文在国内外陆续发表
《我国儒家文化与传统医德》一文中文版刊载于《中国医学伦理学》1994年第1期。同年5月杂志编辑部致函笔者,对该论文作了客观、公正和全面的评价,并给予了鼓励赞扬。
论文的英文版于1995年8月在英国《医学伦理学》杂志全文发表[2],引起国外学者关注,有知名学者在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中引用该文,并被SCI收录。20余位国际知名学者来函交流,希望赠予该文抽印本,或开展、商讨、邀请学术交流。临终关怀开创者桑德斯博士(Cicely Saunders)专门来函咨询儒家文化对于人的生与死持何观点?基于当时的认识程度,笔者只能回复: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1.4 对自身学术生涯影响巨大
上述经历不仅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促进了自身学术观点的升华。当今,生命伦理学的发展离不开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大背景;深化生命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是开展比较研究;推进生命伦理学实际应用的要害在于向“本土化”转变;生命伦理学的生命力在实践中;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生命伦理学必将成为一门举世关注的“显学”。上述认识长期在笔者的脑海里萦绕,陆续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研究。例如,关于从规范伦理学到境遇伦理学的研究,关于生命伦理学研究的文化、学术和技术氛围的研究,关于生命伦理学的文化解读研究等。2008年,为祝贺《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创刊20周年,笔者专门撰写《生命伦理学在实践中》一文。在培养研究生时,指导他们开展中美、中英等比较研究,围绕具有我国、我军特色的选题进行系列研究。
2 生命伦理学呼唤跨文化研究
2.1 生命伦理学的理论根基
传统认识习惯于将生命伦理学视为“舶来品”,甚至存在将生命伦理学思想渊源归结为基督教伦理学的误解。此类看法只是基于现代生命伦理学发端于美国这一客观事实,顺水推舟引出的简单认识,这对生命伦理学的健康发展和广泛应用是相当不利的。
一是历史脉络较短浅。美国独立的历史,至今不过242年。试图在这样短的历史进程中寻求生命伦理学诞生的时代背景和直接动因是可以的;但是在与整个人类文明史相对接的时候,二百多年所能提供的文化积淀显然是过于短浅了。
二是文化支撑力薄弱。在人类伦理文化的发展史上,东西方文明均有着巨大贡献,这对生命伦理学而言,足以形成巨大的文化支撑力;仅就欧洲伦理学史而言,经历了远古、中古、近代和现代四个历史时期的漫长发展,涌现出不胜枚举的著名学者和重要著作,积淀了既丰富多彩又深刻宝贵的伦理文化遗产,这是“美国伦理学”远远无法比拟的。
三是普遍接受性有限。据估算基督教信仰者约占全球总人口的25%左右,换句话说,非基督教信仰者相当于信仰者的三倍。而具有宗教色彩的文化往往具有排他性,上述1∶3的数量关系,客观地反映了将生命伦理学植根于基督教伦理学不可能被世人普遍接受。
四是发展驱动力不足。受上述诸方面所制约,生命伦理学难以避免“先天不足、后天受限”的局限性;它在自己的文化圈内部可以畅通无阻,但离开特定的背景文化,它就会遭遇重重阻力,使其发展驱动力随着地域的拓展而衰减,形象地说就是其发展过程中难以逾越“文化屏障”的问题。
上述情况已经引起许多知名学者的高度重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美国著名生命伦理学家恩格尔哈特教授(H.T.Engelhardt)。他认为“美国伦理学”有基督教宗教观念世俗化移植的浓郁气息。这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一种被拥有其他宗教信仰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普世伦理,美国的生命伦理学同样如此,“特定的西方基督教背景建构了目前世俗道德情感和直觉 ”[3]。
2.2 生命伦理学研究的视野
诸多中外有识之士均强调要跨越不同文化、融入自身文化、联系本国国情以促进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教育与实践。恩格尔哈特教授堪称典范,许多中外知名学者也用不同的语言阐释类似观点。
德国著名学者萨斯教授(H.M.Sass)曾经在原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举办系列演讲。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生命伦理学”一讲中,他强调指出:“如果我们能让所有的文化传统都有计划地进行医学伦理学的教育和回顾,并且这些教育和回顾均基于自身文化遗产,而非从其他传统舶来的法则,那将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4]萨斯教授突出强调的是“基于自身文化遗产”,开展医学伦理学的教育与回顾,就是要突破“舶来的法则”。具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西方学者也认为“舶来的法则”是行不通的,这同我们的认识是不谋而合的。
许志伟教授曾经指出:北美生命伦理学重视个人利益而轻视集体责任。生命伦理学关注的问题,大多是建立在私人经济及私人权益的考虑上的。强调个人自主权的首要生命伦理学原则也体现了这种趋势:偏向个人利益而轻视群体及社会的责任,尤其是忽视了对社会贫困阶层、处于社会边缘、受社会歧视与偏见的人群的责任[5]。他揭示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的价值观念,甚至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群,对于北美生命伦理学亲和力存在显著差异的社会根源。换句话说,拘泥于北美的既定观念,生命伦理学不可能走向世界。
徐宗良教授在其著作中主张: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可能要从两个方面去加强:一方面,静下心来对浩瀚的文献资料进行分析和整理,从中理出若干关键的理论思考点,进而对其作深刻的反思;另一方面,要深入实践之中,对目前生命科学的研究、高新技术的应用和人体试验等引人瞩目的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伦理、法律等问题进行研究,并尽可能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6]。他提出“文献整理分析和理论反思”与萨斯教授所说的“回顾”有相似之处;他提出的“深入实践之中”则击中了生命伦理学永远离不开实践支撑这一要害之处。笔者在西安、南京等地的学术会议中,曾同邱仁宗教授等学长,交流过生命伦理学不是“象牙之塔”,其生命力在实践中;应注重对其进行文化解读和跨文化研究等观点和认识,并得到他们的肯定与赞同。
3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块风水宝地
3.1 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地位
纵看历史,横览中外。我们为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和独特地位深感自豪。华夏文明源远流长、积淀厚重、内容丰富,是汇集了56个民族集体智慧的宝贵文化遗产;它经过五千余年的漫长发展而长盛不衰,与某些文明古国中道衰落,文化式微,淡忘母语,变成外来语国家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享有举世公认的历史地位;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古代文明智慧的宝库,它博大精深、瑰宝无限,既是炎黄子孙世代承袭的文化基因和心智血缘,也是有待我们精心耕耘的风水宝地和当仁不让的“责任田”;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世界和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我们对那些厚彼薄此论调的险恶用心和文化断层潜在的危险后果需保持清醒的头脑,本着客观自觉的心态和开放包容的胸怀,通过积极传承和科学扬弃,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
3.2 儒家文化充满生命伦理智慧
笔者早期的论文中提到“儒学问世之后,其伦理道德观念对历代医务工作者均有深刻影响。”[1]在此笔者想延伸上述观念,讨论儒家文化中古朴的生命伦理智慧亟待深入发掘。
3.2.1 彰显仁者爱人的人生态度。
仁者爱人是孔子的一贯主张,也彰显其人生根本态度,贯穿于其一系列言论和行动。有个叫季路的弟子向孔子请教“如何事鬼”“敢问死”等问题,遭到孔子教训:“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态度很不客气,答复非常果断,可以感知孔子优先关注人生的理念。这同“子不语怪、力、乱、神”,尊重自然力量和现实人生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当孔府马厩失火焚毁,孔子退朝归来时,首先问询伤到人没有,而不问马匹损失。体现了人命至重、远胜财产的价值取向。后来,有注家将孔子的上述言论重新断句,改读为“伤人乎?否。问马”。这一更新的版本拓展了“仁者”先人后马、由人及物的宽广境界,有发展生命伦理智慧的蕴意。《论语》中有“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记载,反映了孔子以身作则,反对滥捕滥杀野生动物的愚蛮做法,倡导和实施有节制地、合理利用和保护生物资源的古朴生态理念,这是其生命伦理智慧的重要内容之一。孔子不是医师,也不负责管理饮食卫生,但却能够结合自己的认识与实践,提出注重饮食卫生,防止病从口入的“十不食”准则:鱼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沽酒市脯,不食。如今,公共卫生已经是生命伦理学关注的重要领域之一,联想到两千五百多年之前,孔子就倡导“十不食”,关注饮食卫生,维护生命健康,显示了其生命伦理智慧达到很高水准,具有重要的先导和启迪意义。《论语》中还有“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不恒其德,或承之辱”的记载。 译成白话文就是说:孔子对生命的守卫者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认为“没有高尚职业道德的人,将会辱没医业的崇高精神”。 他采用警示的句式,来彰显对医师职业道德的高度重视,这在我国古朴生命伦理智慧中具有开创的意义。无怪乎历朝历代的传统医学名家大师皆遵循孔子教诲,强调医者仁心,折射出儒家古朴生命伦理智慧对古代医德建设的重要指导意义。
3.2.2 儒家生命伦理智慧的精髓。
首先,孔子突出强调的“仁”,紧紧围绕着人、人生、生命的主线。《吕氏春秋》中曾有圣人“深虑天下者,莫贵于生”的一般性概括。我国现代学者也一致认为:孔子视为核心理念的“仁”,蕴含着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爱护生命、发展生命的深刻内涵。 更为直白地讲:“孔子的仁道也就是生道,仁就是生的意思。”[7]304上述思想在儒家文化中是一脉相承的。何怀宏教授指出“孟子所倡导仁政也是以‘生生’为根据的”,宋儒对于把孔子的仁解释为生道有着特殊的贡献[7]307。
其次,儒家文化对生命伦理智慧持开放的、发展的态度:从敬畏生命到珍爱生命;体现由人及物,推而广之;进而由社会到自然界……体现视野逐步开阔。邱仁宗教授指出:行“仁”的方法是由近及远。“孝”“悌”是“仁”之本,然后推广至其他亲属、朋友、邻居、社区其他成员、陌生人、动物、植物……由于儒医提出“医本仁术”,使得儒家学说与医学伦理学直接联系起来。“仁”是一种美德、一种情感,也是一种伦理要求。儒家伦理学这些观点对于生命伦理学具有重要意义[8]。一以贯之地倡导维护生命、增进健康的有益实践。
4 清代文献中的伦理案例辨析
就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而言,无论是“经史子集”,还是历代文献资料,均可能蕴含生命伦理智慧。我们在阅读古代文献时,如能格外留心古朴生命伦理智慧的隐匿线索,就会不断有新的发现。笔者曾信手翻阅清代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惊奇发现作者以传奇笔法记载了一些堪称古代生命伦理个案的奇闻轶事,也述及前人对生命伦理敏感问题的争论与思辨,这些古朴生命伦理智慧的亮点,实属笔者读书生活中始料未及的收获。
4.1 关于“堕胎权益”之辩
一则题为《医戗二命》的作品讲道:“一夜,有老媪持金钏一对,就买堕胎药。医者大骇,峻拒之。次夕,又添持珠花两枝来。医者益骇,力挥去。越半载余,忽梦为冥司所拘,……”[9]67当初托老媪持重金求购堕胎药遭拒的年轻女子,在阎罗殿状告医者犯了“杀人罪”。接下来双方的控辩陈词,堪称一场古朴而精彩的“堕胎之争”。医者申诉:卖药让你堕胎,等于杀人渔利,违背了药以活人的准则。你因奸情败露而死,与我无关。女子批驳:我乞药时,孕未成型,堕胎之后我可不死,打掉的只是一团无知血块,而挽救的却是我这条待尽之命。得不到药,不能不产,导致新生儿被扼杀,我也被逼自缢身亡。你不仅没有成全我一条命,反而戕害了两条命。不是你的罪过,那是谁的罪过?上述质问已经牵动着医者是愚循礼教、死搬条文、脱离尘世,还是结合境遇、权衡利弊、择善行之的道德实践原则;更触及孕女是否具有终止妊娠、堕胎自保的正当权益等重要生命伦理议题。纪昀先生不仅为我们展示了清朝的生命伦理案例,而且展开了抨击腐儒医风和封建礼教的伦理辨析,堪称一位同情堕胎的开明人士。
4.2 关于“亲子鉴定”之辩
另一篇题为《滴血验子记》的笔记,讲述了“晋人以资产托其弟”,背井离乡赴外地经商,并在他乡娶亲生子。十多年后,其妻病亡,携其子落叶归根。其弟恐兄讨还资产,凭空诬陷侄儿是抱养的异姓,不能介入其兄家业。兄弟二人为此诉讼公堂,衙门依古法采集血样进行“亲子鉴定”,结果血样相合,判定亲生。其弟因诬陷罪遭笞刑,败诉后终日耿耿于怀。为了推翻官府的判决,他遂采集自家儿子血样私下作亲子鉴定,发现父子血样“果不和”。他据此提起上诉,认为县令方法不当,断案失准。面对这场“上诉”闹剧,众乡里仗义执言:该弟媳作风放荡,其子乃该妇与他人苟合所生。官府遂将妇人、奸夫拘捕过堂,二人当庭招供、低头认罪,貌似复杂的亲子悬疑迎刃而解。“弟愧不自容,竟出妇逐子,窜身逃去,资产反尽归其兄。”[9]86-87在这篇“滴血验子”伸张正义的伦理故事结尾,纪昀也指出该方法不够严谨,操作中或存猫腻,尚不足以成为审判定罪的铁证。作者既非刑吏,又非法医,更不是伦理学工作者。但是,其翔实记载和客观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印证前人生命伦理智慧的鲜活材料。
4.3 关于“婚前体检”之辩
《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一位焦姓女子已经受聘待嫁闺中。有土豪劣绅图谋夺其为妾,处心积虑地散布流言蜚语,极其恶毒地诋毁女子名节。其翁婿一方应声中招,执意悔约退婚。女方之父告于官府,要求伸张正义,维系婚约。由于策划者挖的“坑”已经足够深了,不仅编织了所谓“确凿证据”,而且雇佣不肖之徒谎称该女情人。女儿见事凶险危急,主动请邻家老妇率自己直奔翁婿之家,登堂拜见未来的婆婆,坦荡陈词:“女非妇比,贞不贞有明证也。儿与其献丑于官媒,仍为所诬,不如献丑于母前。”遂阖户弛服,请姑验。讼立解。作者点评说:此女“更越礼矣,然危急存亡之时,有不得不如是者。讲学家动以一死责人,非通论也。”[9]112作者不仅精心描述了面临危情险境,将自己的圣洁之躯交给未来婆婆,主动要求“婚前体检”这一伦理个案。肯定了女方临危不惧、大智大勇和超越封建礼教的生命伦理抉择,抨击了某些迂腐的理学家误导女性不惜一死、以证清白的陈腐论调。可以看出纪昀先生的生命伦理观念是进步的、明智的、务实的,而且很有一点拥戴境遇伦理学的情怀。
审视上述案例,可以发现同两千多年前以“仁学”为核心的古朴生命伦理智慧相比,后人们的生命伦理智慧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甚至在敏感领域有了突破性的进步,愈来愈直面生命伦理学的现实课题。
5 加强对生命伦理智慧的研究
5.1 加强生命伦理智慧研究的意义
加强生命伦理智慧的研究具有诸多方面的意义。
首先,它事关增强文化自信。作为生命伦理学工作者,我们应该怀着坚定的文化自信从事专业学术研究。我们有义务考证清楚:在古代中国,我们的祖先们有哪些古朴的相关认识;我们有责任向国际学术同仁推介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命伦理智慧,为东西方文化交融做出应有贡献;我们应该更多地发出中国声音,不断提升在当代生命伦理学领域的话语权。
其次,关于古朴生命伦理智慧的发掘整理是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研究领域,不仅国内学者应该勇于担当,而且应欢迎外国学者和留学生参与共同研究。对内我们可以视之为推进生命伦理学本土化进程和促进构建中国特色生命伦理学学科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外我们可以视之为进一步夯实生命伦理学理论基础的重要课题之一。通过各国学者分工合作,为生命伦理学的成长打牢多元文化基础,丰富其文化内涵,助其更加根深叶茂,更加充满活力。
第三,此类研究有利于突破生命伦理学遇到的文化屏障。借助文化多样性的探索、交融和共识,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同,增强其在不同民族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人群中的通用性,使之更为有效地造福人类。
第四,通过古朴生命伦理学的源头活水和古为今用的正确途径,促进现代生命伦理学的普及推广,可以引导人们更加重视生命伦理学,更加自觉地应用相关的理论、原则、法规、准则,为生命科学与医学的研究保驾护航,进而为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正确的伦理导向。
5.2 促进生命伦理智慧研究的建议
就政府层面而言,应该对相关研究工作给予足够重视和有力扶持。主管部门应该担负认识引导和政策扶持的职责。如今,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有能力、有远见、有襟怀面向世界,设立相关基金,大力资助有中国特色的生命伦理学研究。
就相关学会、机构、院校和交流平台而言,应该将此类研究工作纳入视野,列入规划,用心组织,持久建设。
当然,归根结底需要学术同仁自觉担当,履行学术使命,发挥自身优势,耐得住寂寞,脚踏实地开展团队化、课题化、系列化的研究。
总之,笔者坚信在这个充满生机的时代,对上述充满希望和潜力的学术领域,展开
坚持不懈的研究探索,通过日积月累,薪火相传的共同努力,必然会取得具有重大影响并获国际同行高度认同的系列崭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