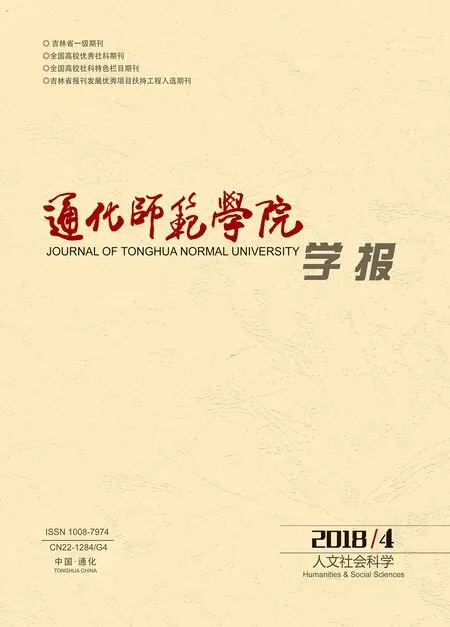中国画中线的艺术特性与审美规律
黄欣凤
中国画是有着民族艺术特色和审美习惯的艺术,其以线为主要造型手段,自我国古代就已经体现出特殊的审美意味,加之所使用的毛笔的特殊性,使线条中赋予了刚柔、情感、疾徐、畅涩、节奏、韵律及抽象美等因素,是西方绘画所不能企及的。中国画中的线之所以能够达到自由、灵活多变、抒情写意、传神写照的审美体验,要归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阴阳相生”“物我为一”的哲学思想基础,往往以“散观”世界的方式,游心于天地之间,“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捕捉自然山川和生命之美,构造诗、书、画、印相融于一体的画面。“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粹,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1]44中国画中线的语言实则超越了客观物象简单再现的层面,而是融入了画家主观思想,更注重传神、写意,是一种有文化铺垫并倾向于意向性表现的艺术。在塑造形象方面,线自古就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从形态、节奏、气韵等方面展现出其所特有的意象美和内涵,而“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须八法通”,“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临抚石鼓琅琊笔,戏为幽兰一写真”等,更点出了中国画中线艺术的书写性内涵,“骨法用笔”成为线表现的一个重要因素,书画之间往往“书中有画,画中有书”,使中国画的线成为一中有体量的艺术,在历代画家辛勤的探索下,形成了自身的审美法则,并蕴涵了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的精髓。
一、线的艺术特性
(一)线是客观生活的提炼和升华
线是画家观察和体验生活后,所提炼和抽象出来的艺术造型表现形式。然而,线虽源于客观自然,又并非是客观生活的再现,从立意、构思到选取艺术形象等,都是画家经过反复推敲和挖掘后的结果,正所谓“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形象的取舍是要服务于主观意愿的,人格化的创造,成为中国画着意表现的内容,即使是看上去真切的工笔画艺术形象,实则也是画家超越客观物象归纳和提炼出来的主观造型,为了“传神写照”,往往多方观察、速写,“搜尽奇峰打草稿”。
线的表现性语言也不等同于写生。当自然物象比较繁琐、杂乱的时候,就必须去简化和概括,选取最具有特征和有利于提升画面的形象,增强艺术表现力和典型性;有时对于简单、平常的物象,又需要仔细去挖掘能够体现艺术美的元素,达到丰富的艺术效果。此外,不同的对象可能还要分别对待,如需要“立骨”、显骨之处,线可能就得方、硬;而有时需要圆柔、饱满的地方,就需要削弱骨气的传达,线条可能会细而柔美;有时可能需要科学分析、理性真实的表达对象,而有时又需要夸张和改变,模糊客观理性成分,介于“似与不似之间”。因此,中国画中线艺术的表现是审美取舍的结果,是客观生活的提炼和升华,以截取最具魅力和艺术性的线造型,构建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并达到生动、传神的目的。
(二)线是情感与个性的体现
线条是表现画家情感与个性的重要因素,且能“不施丹青而光彩动人”,以线性表现为主的中国画作品更突出了这一点,不借助任何辅助色彩,纯以线的丰富多变来表现神韵和传递感情。如果把线条简单地认为是轮廓的框形,那就把线的语言简单化了,那样,所描绘出来的线也会缺乏“生气”而不够鲜活。然每个人对线描又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一般洒脱奔放的线给人以活泼畅快之感,刚劲健挺的线有阳刚之美,飘逸流动的线又如烟云般曼妙,等等,中国画中的线总是如诗般的传递着个人的情感,是情感与理想相融合的产物,也是人们个性、文化、修养和气质的写照。
历代画家作品中的线条各有情感和特性,如东晋顾恺之的线条“紧劲连绵,循环超乎”,如“春蚕吐丝”、行云流水般悠缓自然而高古,流露出魏晋文人士大夫追慕仙姿、超脱自然、旷达的风度;唐代吴道子因本性“好酒使气”,性格豪迈,他的线条遒劲有力、雄健奔放而富有变化,营造出“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艺术效果;而同时代张萱、周昉的人物画“衣纹劲简”、流丽,线条匀细而流美,体现出唐代贵族仕女所特有的精致、华贵和丰腴之态;宋代李公麟的线描简洁优雅少有顿挫,连贯流利,加之“扫去粉黛”纯以线描作为表现手法,作品朴素、古雅而超逸,体现了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审美和韵致;而明末陈洪绶的人物画造型善用夸张变异的手法,线条古劲清圆或顿挫盘屈,奇纵怪异而沉着,于古拙中见清俊,朴质旷达又缜密,体现了不同于前人的品格、气度和趣味。近代吴昌硕作品中的线则老辣苍劲,纵横恣意,笔力熊强能“抗鼎”,气势恢宏,等等。
总之,中国画中的线虽无声,却如诗如歌如舞般,优雅动人,以直观的语言倾吐着一切,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画的线是画家的审美、情感与个性的完美契合和表现。
(三)线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直观反映
“以线写形”,更反映着中国古代“阴阳相生相克”“物我为一”的哲学思想基础,即使是一花一叶,一草一木,一举一动往往都是人类对宇宙精神、生命和自我世界的解读与表现,特别是表现性比较强的线,能够达到自由挥洒、抒情写意的审美体验,并衍生出富有节奏和生趣的线,可以说,中国画中的线正是在传递和塑造宇宙生生不息的天趣之美和人类主观精神的中和之美。
首先,以意“取象”,追求“物我交融”“天人合一”的意象造型。明代王履就谈到“画虽壮形,主乎意”,线的提取虽以客观物象为参照和依据,却又非客观物象的写真模仿,往往舍去了光影、体积、明暗等因素。即使是现代工笔也不完全受解剖、比例及空间透视等科学条理的约束,仍以散点透视为主,随画家个人的意愿自由地选择和利用形象,可以移花接木、东挪西借,可以夸张变形、托物言志,用郑燮的话说,即“手中之竹不是胸中之竹,胸中之竹不是眼中之竹”,心、脑、眼、手之间所提炼出来的“形”,是揉入了作者对客观物象神质的认识、理解和有感而发的意象性符号,并在有意为之中取得“偶然得之的无意境界”。因此,以意“取象”,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是中国画线描的表现性和艺术性典型性所在,也是成为主客观高度统一的最高艺术准则。
其次,“阴阳相生”“计白当黑”的空间组合。“一阴一阳谓之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无相生”[2]23,中国画的艺术审美思想正是古代哲学观念映射下的产物,如以道学、儒学、禅学等为思想结构,“识度闲放”,“观物取象”,在冥冥宇宙中寻求大道,无欲无念、无喜无忧,五蕴皆空。具体表现在画面中的物象形体与空间上,便是以虚代实、以实写虚,“计白当黑”,求世间素净空灵之境界,突出的是虚实相生、“知白守黑”等的辩证统一思想。因此,中国画中的线,并不是简单的组织和罗列,是通过人与客观物象的联系,根据主题融入主观思想、自然灵性以及画理与技法等的浓缩和升华,以“简于象而非简于意”为原则,在清净淡薄中达到笔简情溢、墨简趣足、宁静致远的审美精神,创造寓情于“虚”的审美妙趣,体现的是特定的精神境界,讲究气脉、开合,并与印章、题款、诗意等综合构成画面,追求“道法自然”“气韵生动”的艺术神韵效果。
最后,“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艺术追求原则。以老庄为根基的玄学,注重探究宇宙生存之奥秘,通过激赏人的才情、个性、气质和风度,追求人的精神内涵,除了要表现客观物象之神外,更注重传达作者之神,并把“畅神”“怡情”等作为人们发挥的主要题材和导向。如东晋顾恺之主张绘画“以形写神”,提出“传神写照”“迁想妙得”的艺术理念;宋代苏轼提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认为以形作为艺术表现的水准是如同儿童般的认知;北宋沈括强调“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3]40;元代倪赞形容自己作画是“逸笔草草不求形似”;清代石涛则有“不似之似似也”,同时代的查礼亦有:“不像之像有神,不到之到有意”[4]等等。可以看出,中国画不把形似作为追求的目标,往往以造化为师,又以牺牲物象的某些形似为处理手法,缘物寄情而绘制画面,形神之间的关系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既体现着外在的、表象的、具象的、可视的内容,又表达着内在的、本质的、抽象的、隐含的内容;形无神不活,神无形不存,只有做到形神兼备、“物我为一”的状态才是最绝妙的艺术作品。
上述可以看出,线既是中国画造型艺术最主要的表达方式,又由于特定的民族审美习惯和文化思想基础,以及画家个性、情感、修养等的参与,使中国画的线自由度更大,主观性更强,追求的是“神似”“意真”“情真”的精神境界,微妙、丰富而多样,体现的是东方艺术所特有的线性美。
二、线的审美规律和要求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遵循一定的规律和法度,线描亦如此,不同的线条组织、空间、层次和走势,所带给人的感受是不同的,在黑白的世界里通过对物象的形、神和质感的把握,绘制出合理、动人的构成关系、韵律和节奏感,从而达到生动、传神的目的,广泛流传的“十八描”便是线描最好的艺术表现形式实例。而线条艺术表现的具体法则体现在一系列对立而又统一的关系里,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形状上有长短、粗细、起伏、方圆、曲直、轻重、刚柔等对比
中国画的线条长短粗细、方圆曲直等形态各异,而不同形态的线又体现着不同的质感和视觉效应,如飘逸洒脱、奔放自如的线给人以活泼和动感;娴静、流美的线给人以安宁和静气;刚劲有力、粗犷的线条则体现出熊强、厚重之感;虚无缥缈、简洁的线给人以空灵感;阴柔凝重的线给人以沉郁感;沉着、温润的线又给人以典雅端庄的感觉。在线的表现中,或方或圆、或轻或重、或粗或细、或曲或直等,都要随物象的不同而择取。
此外,线形态的这些对比因素既对立又统一,既矛盾又相辅相成,相互穿插并作用于画面中的,不能孤立的去看待。如一味方线,容易使画面缺乏圆融和生趣,显的呆板;一味圆线又会造成柔弱、力感不强的现象;有直无曲的线组合会使画面显得直白、简单,有曲无直又使画面过于迂回而不畅通,以及杂乱无章、轻重无度、过粗过细的线,都无法产生合理的画面美感和气势,并失去统一感。
只有依照画面所需进行把握、组织和安排,能够长短有序、虚实明朗、轻重有别的线,才合乎法度、合乎画面,产生一团和气,带来自然、舒畅之美感。
(二)用笔上有快慢、虚实、张弛、顿挫、顺逆、提按之分
用笔是线描艺术的一个重要环节,南齐谢赫所提到的“六法论”就将“骨法用笔”位于第二的,并称赞笔力好的作品“一点一拂,动笔皆奇”,[5]35对于笔力差的作品评为“笔迹轻赢”。唐代张严远在《历代名画记》里也说:“夫像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5]61这都是对用笔功力的强调和要求。中国画中的线又与书法紧密结合,所谓“书画同源”,“一波三折”“无垂不缩”“无往不收”等,其笔法是相通的,在“指实掌虚”的握管中,中侧锋兼用,勾勒写形,并讲究平、圆、留、重、变。这一方面要求的是画家对用笔力度的把握和控制。另一方面要求的是画家对时间和速度的权衡。即:用笔稳健、力度适中,“如锥画沙”谓之“平”;用笔圆润浑厚、流畅并富有弹性,“如折钗股”谓之“圆”;笔力沉着、不浮不飘,“如屋漏痕”谓之“留”;用笔极其富力感,力透纸背,似“高山坠石”谓之“重”;而用笔方式多样、技巧丰富,又不墨守成规,谓之变。所有这些,在主观意趣和审美个性的共同作用下,线描有了快慢、顺逆、“虚入实出”“实入虚出”、收笔回锋等多种变化后,线条便增添了鲜活的生命力,或轻盈或凝重,或浑厚或飘逸,或运动或平静,赋予了线以强烈的节奏感、动势和生趣,丰富而有体量。
(三)用墨上的干湿、浓淡、枯润变化
除了用笔外,用墨也是中国画非常重视之处,所谓墨分“五色”“六彩”,笔与墨共同组合,构成中国画特有的形式内核。墨的使用要恰当才产生奇特之韵,墨色太淡,容易使笔弱而被隐含或覆盖,表现力不强。墨色太深,色与墨无法相融,使画面生硬,不能融为一体。因此,墨在水的参与下,线所呈现的的层次和质感是多样的,需要合理的发挥和应用,才能起到更好的作用。如焦干的墨,较易体现枯涩与沧桑感;饱和湿润的墨,易显现华姿秀美之态;清透湿润的墨,体现的是虚静淡薄之美。具体运用上来说,如粗枝、土墙等,一般选用较干的墨,以使其达到粗糙皴裂的视觉感;花朵、纱衣、孩童与少女的皮肤等,一般用润、淡的墨,以体现纤细、圆润、流畅、轻盈之感;头发和深色物一般以重墨居多;而对于相同的物品处于远近不同的位置时,可能前面的线条精细而墨浓,后面的线条虚淡而墨浅。还有一种情况,同样湿度的墨,速度慢时墨色可能饱和、流畅,速度快时墨色可能会较干。当然,具体的线描处理方法还要以不同的结构和空间来设定,往往于实处流畅有力,于虚处涩涩而轻。总之,一幅线描作品,墨色要有轻重对比,或以浓破淡,或以淡破浓,色墨层次相间相存,能利用恰当,线条也就会有丰富的表现力。
(四)构图与布局上有主次、疏密、阴阳、交错、气势连贯等的审美
仅仅做到一条线的起伏飘扬、流畅、合乎法度是不够的,线与线之间,在勾勒、穿插中,还须注意起承转和、首尾相呼,通幅连贯、阴阳相生,才能使线不孤立。画面主要的物象较为考究,轮廓清晰,刻画精细、醒目;次要的相对含蓄、模糊,轻描淡写,起到陪衬作业。分出主次,不喧宾夺主,才能更好地烘托和提升画面,加强前后、虚实、层次的对比,并有一种体积感。而线条疏密的不同安排和搭配,也是画面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疏密、穿插得当,会让画面纵横交错、聚散有别,紧凑中又有舒朗,开阔中又不单调,正所谓“密不容针,疏可走马”,繁简得当,有理有度,才能助长和提升画面表现物象的生势和生机。
一幅完整的线性作品还要注意“布势”、整体和局部、宾与主的关系。布势的因素既包括自然、生机、生趣的自然生命之势,又关乎艺术表现手法、节奏、韵律、气脉、开合、情感的流露等主观表现之势。布势中线的提取首先要参照的便是生命之势,如春意盎然、生机勃勃之势;盛夏朴茂、炎暑之势;山势雄伟高大之势;云水湖畔平远之势等,取其势态而传之。其次,布势还关乎画面本身所追求之势,是倾向于萧疏简远还是表达富丽妖娆之势,是挺拔崇高还是平和秀美之势,是狂放粗野还是娴静雅致之势等,成为作画所要把握的一个主体之势。而画面中的笔、墨、水、色以及留白、款识、章印等都是组合画面气势的重要因素。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法无定法,势无定格,所谓“取势”“写势”,即是取情、取景、取材,只要各种因素巧妙搭配,能够表现各情态下的画面之势,在流动与穿插中生生不息,通幅气势连贯、完整而成韵成美,充满宇宙生命精神的大势之美,便是抓住了画面主体之势。
线作为中国画的造型基础,在中国哲学思想的指引下,以“散观”世界的摄取形象之法,游心于天地之间,既师法自然,又着重表现着画家主观的思想情志;既“传移模写”,又强调“似与不似之间”;既“写形”,又以留白、款识、章印的组合来构成画面。可以说,缘物寄情、抒写心性、“畅神”“写意”成为中国画中线艺术表现的一大特性。而用线即是用笔、用墨功夫的体现,“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笔锋下决出生活”,[6]53“神采生于用笔”,[6]51其长短、粗细、快慢、虚实、顿挫、干湿、浓淡、疏密等都透漏出特有的审美规律和法度要求,也正是这些神采各异、微妙变化、丰富多样的线的特性,构成了中国画艺术的生机与活力,富有独到的神韵感,呈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生生不息,以及“物我为一”的宇宙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