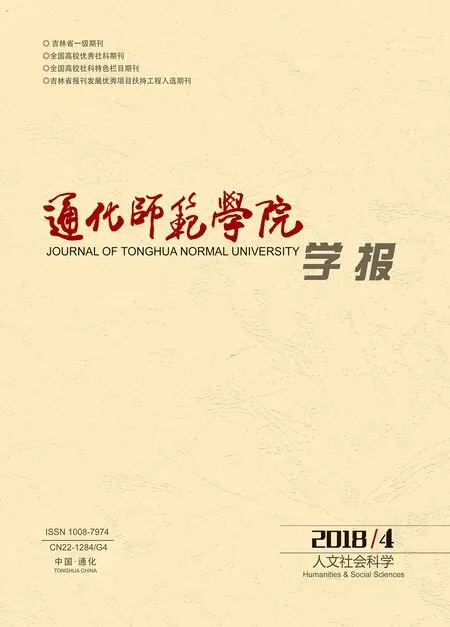论文学翻译的语境顺应
——以《细雪》的中译本和韩译本为例
金成花
语境顺应论是由比利时语用学家耶夫·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提出的语用学理论,它认为语言的使用就是不断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这种选择不仅包括语音符号、词、句、段、篇章等语言形式的各个层次和方面,而且包括语言策略,涉及面很广。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作出各种不同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三个特性: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变异性是指语言具有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它限定选择的可能范围;商讨性指语言使用者在选择语言时不是按机械方式,也不是按严格的形式——功能关系,而是高度灵活和策略性地进行;顺应性是指能够让语言使用者在一系列范围不定的选择项中进行可协商的语言选择,从而满足交际需要。语言的三个特性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根据语言的顺应性特征,对交际过程的描写和解释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语境关系的顺应、语言结构的顺应、顺应的动态过程以及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恰当的、成功的交流既是语言顺应环境,或者环境顺应语言,或者两者相互顺应的过程,也是顺应的结果。语境顺应论把语言环境即语境,分为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其中交际语境包括三个方面:心理世界、社交世界、物理世界。
翻译活动实质上也是一种对语言不断进行选择的过程。它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是双语转换活动中多层次的、更为复杂的语言选择过程,是译者对原文作者以及译文读者不断进行动态顺应的过程。译者要深刻理解原文作者的意图,准确理解原文的意思,必须顺应原语的语境。与此同时,译者要想将自己所理解的原文信息以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满足译文读者的阅读要求,就必须顺应目的语的语境。语境顺应论提出于上世纪80年代,而在我国开始以语境顺应理论研究翻译活动始于本世纪初,既有翻译理论研究、翻译实践研究,也不乏翻译教学的研究。但是基于语境顺应论的翻译研究,无论是理论研究、实践研究还是翻译教学研究,基本都以英汉互译为研究对象,几乎没有涉及其他小语种。本文将尝试依据语境顺应理论对日本唯美派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代表作《细雪》的两个中文译本——周逸之版(1985年)、储元熹版(2007年)译本和韩国송태욱(宋泰旭)的韩文译本(2007年)进行比较,探讨其翻译的正误。作品主要描写了太平洋战争前夕大阪富商莳冈家风格迥异的四姐妹——鹤子、幸子、雪子、妙子各自的人生故事,由于内容涉及很多日本传统文化,而且使用了大量的日本关西方言,因此准确理解和翻译《细雪》具有一定难度,中、韩文译本都存在一些翻译不恰当之处,适于我们在语境顺应论的指导下加以研究改正。以下将把周逸之版译本简称为周的译本,将储元熹版译本简称为储的译本,将송태욱(宋泰旭)的译本简称为韩文译本。
一、翻译要顺应语言语境
余高峰(2011)指出“语言语境,亦称上下文语境,这里指的是语篇自身的结构衔接及逻辑连贯”。在翻译中对语言语境的顺应,指译者必须首先正确、清晰地理解原文的语言语境,并在重构译文时保证词语译得正确,指代清楚,逻辑明晰,并注重段与段之间句子安排得当,保证段与段之间的连接及全文的流畅。请看下面例文:——「実は本日は、その爛柯亭へ御案内申したかったのでございますが、生憎彼方が塞がっておりまして――」そう云って未亡人は、それまで手持ち無沙汰にしていた幸子達の方へこなしながら、「――蒔岡さんの方々をお泊めしますのに、彼方を使っているものでございますから、――」「本当に此処のお座敷も結構でございますが」と、幸子はようよう会話の仲間入りをさせてもらって「――彼方は離れ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せいか、実に閑静な、ええお座敷でございますわ…」(谷崎润一郎《细雪·下》P38)——这是原著中描写雪子第四次相亲场面的一组对话,由于出场人物较多,会话使用的又都是敬语,尤其是多处使用了指示代词,所以对外国读者而言,理解起来有点难度。译者要创作出最佳译文就必须先弄清每句话的发言者是谁,正确理解敬语的含义,尤其要理清句中指示词的指代关系。上文中的“此処”在日语里是近称场所代词,相当于汉语的“这里”;“彼方(あちら)”是远称代词,当用于指代场所时,相当于汉语的“那里、那边”。因此,此处的“彼方”指代的应该是前一天晚上幸子她们就寝时使用的烂柯亭,“此処のお座敷”指代的应该是相亲时正在使用的房间。为此,储的译本和韩文译本分别将此处的“此処のお座敷”译为“这个客厅”“이쪽방(这个房间)”。但是,周的译本却把“本当に此処のお座敷も結構でございますが”译为“真的,那栋别屋可真不错呢”,“此処のお座敷”成了“那棟别屋”,用来指代烂柯亭,显然是个误译,不符合日语语法规则。一字之差不仅导致指代关系混乱,没有表达出幸子所要表达的这个房间不错,那个烂柯亭更好的意思,而且更是没能突显出和内向、不善交际的雪子不同,幸子处事周到、圆滑的性格特点。
二、翻译要顺应社交语境
社交语境指的是社交场合、社会环境和机构对社交双方的言语行为所规定的原则和准则,包括社会和文化规范。社交语境的顺应也就是说交际者为实现交际目的所作出的语言选择必须符合社会交际规范和文化习惯。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必须在正确理解原文社交世界的基础上,顺应译文读者的社交世界。下面我们看几组因为违背有关亲属称谓规则而产生的误译。众所周知“中国有着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国人自古就重视以家庭为中心的血缘关系,宗法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核心内容,它包括:父权,夫权,长幼尊卑有序,遵守孝道伦理,重男轻女,重视家庭外部众多亲属关系等。所以汉语的亲属称谓系统复杂而精确”(才洪侠、李筱平2005)。我们的近邻韩国在亲属关系称谓上与我国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其亲属称谓系统甚至比我国更加复杂而精确。但是同属亚洲文化的日本,亲属称谓却非常简单,无处不体现着欧美文化的影子。
在《细雪》原著中,主人公幸子的女儿悦子只把幸子的姐姐鹤子叫作“伯母さん(姨妈)”,而分别称呼幸子的两个妹妹雪子和妙子为“姉ちゃん(姐姐)”和“こいちゃん(日本大阪一带用来昵称家里最小女儿的称谓词,相当于汉语的老丫头、小妹等)”。这是因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日本人在称呼别人时,会尽量采用小于实际年龄的称谓词,以满足人们希望年轻的心理,这已成为日本交际规则之一。但是与日本不同,虽然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近年来在中国和韩国也有人喜欢在言语交际中对对方使用小于实际年龄的称谓词,以迎合人们希望年轻的心理,但是在家族成员之间依然非常重视长幼尊卑,“辈分”观念根深蒂固,没有摆脱自古以来形成的传统文化的约束。正如孔子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辈分”也是“名分”之一,要保持家族秩序的稳定,必须要严格遵守“辈分”之约。这一点,不仅从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称呼中,从韩国电视剧当中也能领略一二。如,韩国热播电视剧《家门的荣光》中的河珠贞是河氏家族领养的弃婴,在辈分上是河氏家族的掌门人河万纪会长的妹妹,但是年龄上却比河万纪会长的长子河惜灏社长小13岁。在剧中河惜灏社长始终尊称河珠贞为“고모님(姑姑大人)”,而且使用敬语。因此,应该说两个中文译本分别把悦子称呼“雪子”和“妙子”的“お姉ちゃん”“こいちゃん”译为“二姨”“小姨”或“阿姨”“细姨”的翻译方法,顺应了中国读者的社交语境。同时,也不得不说韩文译本将称呼雪子的“姉ちゃん(姐姐)”直译为“언니(姐姐)”、将称呼妙子的“こいちゃん”直译为“막내언니(小姐姐)”的译法,只实现了形式上的对等,没有很好地顺应韩文译本读者的社交语境。笔者认为韩文译本应将悦子称呼“雪子”和“妙子”的“お姉ちゃん”和“こいちゃん”分别译为“둘째이모(二姨)”和“막내이모(小姨)”,并称鹤子为“큰이모(大姨)”。
类似这种由于社会规则及习惯的不同所导致的亲属称谓的误译在《细雪》中、韩译本中还有多处。如在原著上册第22回中有这样一段话:「鶴子が帰って行ってから数日過ぎて、いよいよ出発の日が二三日後にさし迫った頃、亡くなった父の妹に当たる人で、『富永の叔母ちゃん』と呼ばれている老女が、或る日ひょっこり訪ねて来た」(谷崎润一郎《细雪·上》P172)。其中“叔母ちゃん”,虽然使用“叔母”两字,但不仅指叔母,还具有姑妈(고모)、姨妈(이모)、伯母(큰어머니)、舅母(외숙모)等含义。此处的“富永の叔母ちゃん”,因为前文有交代此人是鹤子四姐妹爸爸的妹妹,所以中文的两个译本根据汉语的称谓习惯都将此译为“富永姑母”。但是韩文译本却直取“叔母”两字,将此译成了“도미나가숙모(富永叔母)”,显然是不符合韩语的亲属称谓规则,应译为“도미나가고모(富永姑母)”。由于违背汉语亲属称谓细分原则而导致误译现象的还有一例,就是关于日语“兄さん”的翻译。“兄さん”相当于汉语的“哥哥、姐夫”,韩语的“형(哥哥、男称)、오빠(哥哥、女称),형부(姐夫)”。因此储的译本和韩文译本分别将原著中册第23回鹤子写给幸子的信中指代鹤子丈夫辰雄的“兄さん”译为“你姐夫”“네형부(你姐夫)”。但是,周的译本却将此译为“你哥哥”,显然是不符合汉语亲属称谓习惯,属于误译。
三、翻译要顺应心理语境
心理语境包括交际者的情绪、愿望等认知和情感方面的因素。在翻译活动中,心理语境的顺应指译者应在正确了解原文作者心理意图的基础上,创作出适合译文读者心理语境的译文来,否则再华美的译文也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根据这一翻译原则,笔者认为中文的两个译本对上册第24回中的“支那事変”(谷崎润一郎《细雪·上》P196)一词的翻译忽视了中国读者的心理感情,没有顺应中国读者的心理语境。我们知道在日本“支那事変”有两种含义,一指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另指“中日战争”,在原著中也可理解为这两种意思。中文的两个译本都直接挪用了原文的“支那事变”,只是储的译本对“支那事变”加了注解,解释为“指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我们知道“支那”一词,自明治维新以来已成为对中国的蔑称,曾留学日本的我国著名作家郁达夫在其小说《沉沦》中写到“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贱贼’还难听……”(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郁达夫文集》第一卷P46,47),可见这是一个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称呼。而且,日本称中日战争为“事变”具有企图掩盖侵略战争真相之意图,一直不为中国人民所接受。为此,中文译本应该顺应中国读者的心理语境,将“支那事変”翻译为“中日战争”或“卢沟桥事变”或“七七事变”。与中文译本不同,韩文译本对此处理得比较得当,不仅将“支那事変”准确地翻译为“중일전쟁(中日战争)”,而且加以注释:“일본은<지나사변>이라고하는데원문에도그렇게표기되어있다.일본이<전쟁>이라는말을붙이지않고선전포고도안한것은중국의항일운동을진압하고유리한중일관계를수립하는데전투의목적이있었고미국등제삼국에서군수물자를수입하기어려워지는상황을꺼려서였다(日本称中日战争为“支那事变”,原著中也是这样表达的。称其为‘事变’而不用‘战争’二字,并且不宣而战的目的是为了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建立有利于日本的中日关系,同时也是因为担心一旦宣战,难于从美国等第三国家购买到军事武器。)”这不仅有利于韩文译本读者正确了解历史事实,识破日本人称中日战争为“支那事变”的不良用心,而且也顺应了韩文译本读者憎恨日本侵略者的心理语境。
四、翻译要顺应物理世界语境
物理世界主要指的是时间和空间的指称关系。其中时间包括事件的时间、说话的时间和指称的时间;空间包括绝对的空间、说话人的空间、指称空间以及交际双方在物理世界中所处的位置等。因为各种语言交际都发生在交际者的物理空间之内,所以物理空间的顺应是交际活动顺利进行的最基本的保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顺应原文、原文作者及译文读者等三方的物理世界,所以物理空间的顺应显得更加困难。
原作上册第29回使用了一个不为中国人所熟知的一个词——“節季”(谷崎润一郎《细雪·上》P247)。这是一个用来指称时间的名词,是一个多义词,既有“季节之末、年末”之意,也有“结账期”之意。后者是日本的一个商业用语,多指商店等在中元节(农历7月15日)和年末清算外账的时期。周的译本将此译为“年底”,储的译本将此译为“清明节”。根据小说的上下文推理,含有“節季”这个词的句子所描述的情节应该发生在当年4月3日的前几天。因为在原著中,在此句前有写到雪子于3月3日,即西历的女儿节那天回到幸子家,在此句后又写到雪子来幸子家已快有一个月,幸子规劝雪子该回东京的大姐家了,于是雪子说要在4月3日农历的女儿节①日本的女儿节一般是在西历的3月3日,但是在日本关西地区通常要在农历的3月3日过女儿节,所以要比关东地区晚一个月,也就是4月3日过女儿节,关于这一点原著中有说明。本文为了便于说明,分别使用了西历的女儿节和农历的女儿节两种说法。过后回去。由此看来,周的译文“年底”,在时间上与原文完全不符,属于误译。而储译本中的“清明节”,按照中国人通常在4月4日或4月5日过清明节的习俗,应该说翻译得不够准确。这种时间上的误译使译文失去逻辑性,导致读者不能正确解读译文。再看韩文译本,它将“節季”灵活翻译为“외상결제일(赊账结算日)”。既然是4月3日前期,那它就不会是中元节或年末时的结账期,而是平时的一次结账期,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韩文译本对“節季”一词的翻译顺应了原文的时间语境,是准确的翻译。另外,笔者认为也可以将此处的“節季”译为“3月末的一个结账日”。根据小说的上下文情节,此处的“節季”应该是在3月末、4月初这个期间。因为日本的财政年度采取跨历年制,从当年4月1日至下一年的3月31日为一年度,3月末应该是日本人清算一年旧账的时候,而且在中国人的时间观念里,月末一般是结账期,所以这样翻译,既顺应原文的时间语境,也顺应中国人的时间概念。
语言顺应论认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语言的使用是一个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任何语言在使用过程中都要对语境做出动态顺应。通过分析研究以上的翻译实例,笔者深感译者要进行成功的翻译,达到良好的翻译效果,也要遵循这一原则,积极地顺应原文及译语的各种语境——语言语境、社交语境、心理语境、物理世界语境等。语境顺应论对翻译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既为我们提供了翻译活动所要遵循的规则,也为我们提供了评价翻译质量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