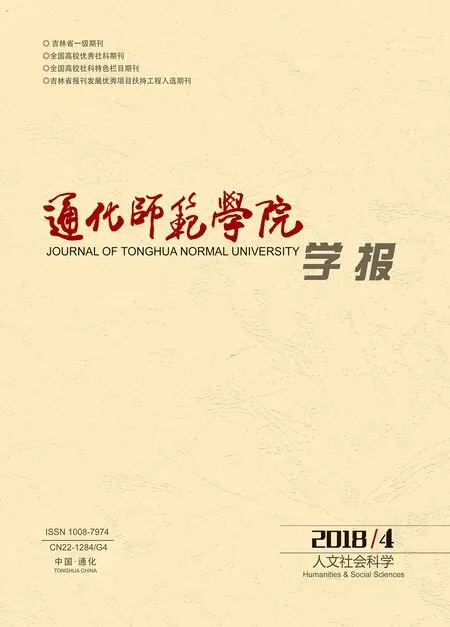艾伦·布坎南对马克思正义观的解读
田佳琦
一、重新构建了马克思正义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思路
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关于马克思与正义理论的探究是西方分析哲学家重要的研究方向。尤其是在资本主义与正义的争论上,主要呈现出两种立场,一个是以伍德为首的主张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指出资本主义是非正义的,所以他主张私有制的剥削是正义的。而与其观点尖锐对立的另一方是以胡萨米为代表的主张用无产阶级的正义规范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正义性。
马克思是不赞成正义的,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本人对正义和权利是持有批判态度的,而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指责并非来源于某些正义的观念,也就是说不应该秉持正义的概念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所以,伍德从历史科学的角度出发,断定正义并不是一个革命性的概念,因此,得出资本主义的剥削是正义的结论。伍德指出,正义按照黑格尔的理解应该是一种解释性质的法权概念,也是社会中的最高的理性标准。黑格尔高扬政治国家却贬低市民社会,认为正义国家是高于市民社会的,也是市民社会不可能赶超或逾越的绝对性的存在,因此是支配并主导着市民社会。但马克思与其相对立,认为现存的市民社会是法和国家存在的先决条件。据此,伍德总结说,马克思的正义制度在社会生活中只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在评价社会合理性中并不起重要的作用。
资本主义的剥削是正义的,看似匪夷所思,但伍德论证的观点却是有理有据的。伍德指出,首先,正义取决于一定条件下的生产方式,所以,唯有与其生产方式相适合的方式就是正义的,就比方说剥削这种形式是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生产方式相一致的,由此可以推断出资本主义的剥削是正义的;同理,与生产方式不适合或者是相违背的就是非正义的。其次,“掠夺”“抢劫”和“强迫”也并非就意味着不正义。伍德认为,马克思把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比喻成“掠夺”和“抢劫”,但是这并不是指生活中具体的真实的抢夺东西。而是马克思借以映射资本家不仅抢劫而且强迫工人,虽然这种强迫的剥削带有非正义的色彩,但是在伍德看来,这种强迫却被自愿的契约所掩饰,所以这种剥削也并非不是正义的。最后,伍德说,马克思的正义不是一个变革性的口号。因为,在马克思看来,革命政治只是由社会中特定的具体的生产方式或者是行动准则构成的。也就意味着,如果把新的生产方式取代旧的生产方式叫作革命的政治的话,那么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也将不比旧的生产方式更自由、更正义、更高级,因为,无论新与旧都只是自己生产方式上的正义形式,所以正义并不是一个革命性的概念。
马克思支持正义一方,他们主张把资本主义看作是非正义的制度来批判,也就是认为剥削是一种非正义的现实存在。所以,马克思在作出剥削是正义的这一道德评价时,往往采用的是反讽的写作手法。基于这一点,胡萨米一派反驳伍德没有理会到马克思的讽刺意义。胡萨米、科恩一派驳斥了伍德主张的资本主义剥削是正义的看法。胡萨米说,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剥削叙述成“偷盗”“偷窃”“攫取”等含义时,他使用了更加确切的表达,就是这种掠夺是不正义的,是不公正的。对此,科恩曾用过贴切的语言描述了剥削是不公正的,他说:“一般来说,偷就是错误地获取权利上属于他人的东西,因此,他就是做了不正义的事。一种制度‘建立在盗窃的基础上’,就是建立在不正义上。”[1]194
在胡萨米看来,正义是有两重决定性的因素,它不单单只是伍德所强调的某种生产方式下所固有的正义原则。同理根据马克思的道德观,上层建筑都有两重的决定因素,即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和它们所在阶层的集团利益。道德观随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随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对一个规范的解释,必须从决定它的两个因素去说明。这也是胡萨米批评伍德只看到了生产方式这一因素,从而产生了与生产方式不相适应的便是非正义的错误结论。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统治阶级会形成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和分配原则,并且把有利于自己的利益的分配方式看作是正义的。在马克思看来,这样一种分配方试显然不是自然产生的,也不是普遍存在的,它是在既定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因而也是可以被超越的。所以,胡萨米说用共产主义的正义尺度去评判私有制的分配原则也应是正当的。
从总体来看,关于马克思正义观的争论,无论是反对一方还是赞成一方,他们的理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伍德一派认识到了生产方式对正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能够说明剥削就是永远正义的。与伍德相悖的胡萨米一派准确地看到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基于两重要素,可是却没能把正义观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理论立场。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分析马克思主义中的双方在这场论战中,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致命性的根本缺陷,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偏离。因而,他们的正义理论往往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遗失了科学性。因此,布坎南就致力于提出一个既基于马克思文本的事实又能达到扬双方理论之长避双方理论之短的双重目的的解说方式。可以说,布坎南的阐述是相当富有创造性的,也是颇有见地的,他不但归纳、概括以及融合了两方的理论观点,并以其缜密的逻辑阐发了他本人独特的认识和看法。布坎南关于马克思批判正义论思想的解读被佩弗称作是重新理解马克思与正义理论无法绕过的学术成就,高度赞扬了布坎南所作的努力。甚至曾经被布坎南所批判的艾伦·伍德也评价说,它算得上是用通俗的、可理解的方式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与道德理论结合起来的著作。
我们知道黑格尔是通过他预设的客观理性或者说是绝对精神的支配下来探索人类的社会史的。正如黑格尔指出:“正义思想、正义概念一下子就得到了承认,非正义的旧支柱不能对它作任何抵抗,因此正义思想现在就成了宪法的基础,今后一切都必须以此为根据。”[2]719但是这在马克思的理解中,单纯地凭借法权手段是无法完成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批判和否定的。所以,马克思首先是对黑格尔的法权框架的本身进行了批判,按照布坎南的解读,马克思也就开启了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法权的独特的评价视角。布坎南对马克思的这一超越性的批判,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与有力的论证。布坎南进一步指出,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制度,并非是由于这个私有制的法权框架自身有问题。而在于,一个社会若是必须要以法权为根基,并在此根基之上,去期望完成人类自由的话,那么可以说,这便是存在缺陷的社会。就像布坎南说的,法权框架之所以会存在就是因为它对应的本身就是一个不完美的社会。所以,要想真正地推翻或者批判资本主义,就必定要超越私有制的法权框架。按照布坎南的理解,也正是因为这样,马克思才预设并规划了一个不存在法权的理想社会的宏图,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可以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说成是,希望建立一个无需法权存在环境的社会。所以,在这里布坎南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一个超越法权概念的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评判的视角。布坎南肯定了马克思关于黑格尔法权概念进行激进式地否定与超越。
从此,马克思告别了抽象的唯心的法哲学的论证思路,转而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路径。也就是说并不是为了追求某种“正义”才去批判或废除某种社会制度,而是只有从人自身切实的利益出发,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实践的革命中,进而提出了用人类的解放来替代政治上的解放这一重要的科学论断。所以,在布坎南眼中,废除资本主义这一制度,它并非是局限在“正义”的法权概念,而是一个具体历史的革命的实践行动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坎南认为马克思是一个实至名归的唯物论者,因为他从具体的生产方式以及生产力的辩证运动中去探求一个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或者说,决定社会发展趋势的是生产方式为主的经济基础,而并非是人们思想观念中的“正义”与“自由”。
总之,在马克思思想的早期,尽管深受黑格尔理性思维的影响,试图从抽象的理性角度去追寻合乎正义概念的国家,但是在完成这一唯物史观的转变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黑格尔的法权立场。同时,他坚决抵制把正义、公平等看作是墨守成规的、远居于现实社会之上的普遍价值的预设,却力图在实际生活中的经济领域着手,并以此在变革中去实现人类社会的自由与发展。所以,从整体来看,布坎南的解读思路是符合马克思本意的,因为他看到了最为关键的一点,也就是费尔巴哈利用“爱”的宗教以及蒲鲁东企图用“道德”来批判资本主义的方式,这与马克思所强调的批判方式有着天壤之别。马克思极力反对他们利用唯心主义套路式的法则去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问题,对于马克思而言,他们的批判方式似乎都显得软弱无力,根本无法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更谈不上从根本上彻底地消灭资本主义。因此,马克思力图从人们生活相关的物质利益着手,并采取暴力武装这一激进的批判方式,只有这样才会实现从根本上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也是布坎南本人在理解马克思正义问题的一个重要的立足点,同时也是他之所以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一种超法权的评价视角的一个根本原因。
二、首次提出了非法权的共产主义评价视角
通常所说的法权,是指对社会的解释或者批判要以“正义”和“权利”的概念为依据,也就是说当一个社会用正义或非正义、维护权利或侵犯权利,这样的概念来架构一个社会的根本评价时,它就给予了法权作为一种基本的批判标准的权力。所以,法权之所以产生,其实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确立或者规范一个社会的价值理想。就像布坎南指出伍德等人解读的正义观点,认为他们依旧是在法权框架内的这种思维方式的理解,布坎南称他们最多也就只是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的“内在批判”。而在布坎南看来,只有马克思才真正地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的“外在批判”,也就是马克思凭借一种非法权本身的崭新的评价视角,以此在根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这种评价视角毫无疑问就是共产主义。布坎南阐释了“内在批判”和“外在批判”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他说内在批判主要是指依然用法权形式下的批判方式,也即是在保留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对其制度本身的且不消除法权关系的一个内部的批判。而外在批判就是与内在批判相对立的另一种批判方式,比如像马克思式的批判,就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法权问题的前提进行的批判,正是由于这个制度的前提本身是存在问题的,所以要想从根本上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就必须从这个“前提”批判开始,而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寻求出路。所以,把谋求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捍卫私有制度的内在批判不同的方式,即从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个前提条件开始着手的批判,布坎南称之为外在批判。
可以说,布坎南阐述的这一外在批判的观点,在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上是十分深刻的。正如布坎南认为西方学者关于类本质的“抛弃说”是对马克思思想连续性的遗忘。因为他们的观点并非是成立的,在布坎南看来,马克思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的评价视角并不是对类本质学说的抛弃。相反的是,“马克思把共产主义描述为人类本质的实现,是试图提出一个‘社会的’、‘历史的’、‘非唯心主义’的概念”。[3]27所以说,在他眼中,马克思的这一外在批判,与以往的所谓的“外在批判”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以往的所谓的“外在批判”无非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态度,也就是用一个更高级的正义概念或者是理论去批判另一个相对于低级的正义概念而已,它们仍然没有突破法权的框架,所以,充其量也就是一种理论上的“外在批判”。而布坎南称马克思的外在批判之所以是一种激进的、革命的批判是因为他从根本上突破了法权的正义观念。此外,布坎南对马克思评价视角的理解与体会,同时又赋有新意地提出了一个新的表述,即“普罗透斯般的核心概念”。[3]35他认为这种“普罗透斯”的概念是更加具体的,是实实在在地从人们生活中的实际需要出发的。因而可以说,马克思是在本质上推翻了正义概念的法权视角,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中实现了共产主义超法权的评价视角。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布坎南第一次清晰地阐述了共产主义这一非法权的概念,可以说这是对理论界的一次大胆的挑战。他摆脱了黑格尔式的法权概念下的解释原则,这更是马克思一直所期望的。所以,布坎南的这一新解对于理论界重新认识和解读共产主义更为深层的本质内涵有着深刻的意义。
所以,从整体来看,布坎南的解读思路是符合马克思本意的,因为他看到了最为关键的一点,也就是与黑格尔法权概念在性质上有着根本不同的共产主义是一个“非法权”的评价视角。也即是说,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不在于它本身实现了更高一级的正义和权利,而在于它是一个无阶级、无国家概念的人类理想的生存形态,因而也就无“正义和权利环境”的,所以自然也是无法权的社会,因此要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优越。这也是布坎南解读马克思正义问题的一个重要的立足点。因此,布坎南关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评价视角的转变,这一独特的解读,不仅开创了我们研究社会正义问题的崭新范式,而且对于我们今后深入学习马克思正义思想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方法。
三、重新阐释了剥削概念的三重内涵
布坎南对马克思的剥削概念进行了三重内涵的分解,不仅是为了从更深层次中去扩展剥削方式中所体现的共产主义评价视角,更是针对那些马克思剥削概念的反对声音,在理论上为马克思作了有力的支持与辩护。布坎南把剥削的内涵主要划分为,“雇佣劳动的剥削”“跨历史的剥削”和“一般的剥削”这三重含义。在布坎南看来,大多数人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只是停留在了第一个层面,也就是只局限于雇佣劳动中的剥削概念,这样的理解是不全面也是不深刻的。布坎南分别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对剥削概念进行多层次和多角度的详尽的解读,进而概括出第二个和第三个层面的剥削,即跨历史的剥削和一般的剥削两个概念。可以说,布坎南对剥削内涵的重新划分,不仅让剥削问题又重新回到了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而且为我们进一步理解马克思非法权的共产主义评价视角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布坎南所指的跨历史性剥削概念的提出,表示着马克思所研究的剥削,是贯穿于人类历史中的剥削问题,而不单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剥削。所以,就会有人来追问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社会是否有剥削的问题,进而来反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批判。这非常明显,是人们抨击马克思剥削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维度,所以在反对者看来,马克思对剥削的批判已经是过时的了,根本没有必要存在了。可是,布坎南却指出,这正是跨历史性剥削概念的一个对比性认识中的关键的切入点。因为,在布坎南看来,马克思即便也指出在以往的社会历史中也存在剥削的概念,可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削的程度相比,可真所谓“小巫见大巫”了。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然把剥削的概念上升为一种人与人之间带有某种特殊意义的社会关系了,因此,布坎南才强调为什么说马克思并没有过多地在意或者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社会形态中的剥削问题,而是着重地针对和批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剥削问题。
所以,基于布坎南的理解,剥削的问题并不是法权问题,而是生产方式的问题。但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剥削又不单单是生产劳动中的雇佣剥削,还具有一般、普遍的剥削意义。尤其是布坎南没有局限于法权框架下的解释原则来理解剥削,也就是剥削不是分配领域的问题,而是跳出了法权框架,从生产领域来解决剥削问题。在布坎南看来,正是因为生产决定分配,生产第一性,分配是生产过程中的派生,是第二性。所以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剥削问题的批判,不能仅依据私有制中的法权手段,而是要从生产领域中,从根本上彻底地铲除决定剥削产生的生产方式,所以这也就是布坎南所说的共产主义超法权评价视角落实到了具体的生产方式领域中对剥削问题的解决与运用。
在布坎南眼中对资本主义剥削问题批判的共产主义是一个非法权框架的评价视角,并且在这一视角中所有的一般剥削的问题都不再是问题,这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剥削问题的最高级的批判。这也正是马克思为什么要诉诸于在经济领域中通过最现实的途径去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性批判的关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唯有在生产领域中首先完成了经济的解放,才有可能实现政治上的解放、进而实现人类的解放。所以,实现人类的解放,这并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空想,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付诸于具体的现实的实践行动,一个循序渐进地过程。因此,马克思的人类解放不是不要正义,而是在现实的行动和革命的实践活动中,从根本上真正地超越了正义,超越了乌托邦。可以说,布坎南的这一理解也是符合马克思本意的。他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钻研,采用了逻辑分析的解读方法,从三重剥削概念的提出,从理论到实践上的建构,一直到共产主义人类解放,都充分地论证了马克思的观点,也即是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个更高级的法权代替另一个相对低级的法权的社会。可以说,布坎南所得出的这个结论是非常重要的,他的理解也是非常深刻的。他不仅基于文本的理解呈现了马克思的本来意图,更彰显了马克思本人对理想主义社会的一种价值祈盼与诉求,更对我们深入地开展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