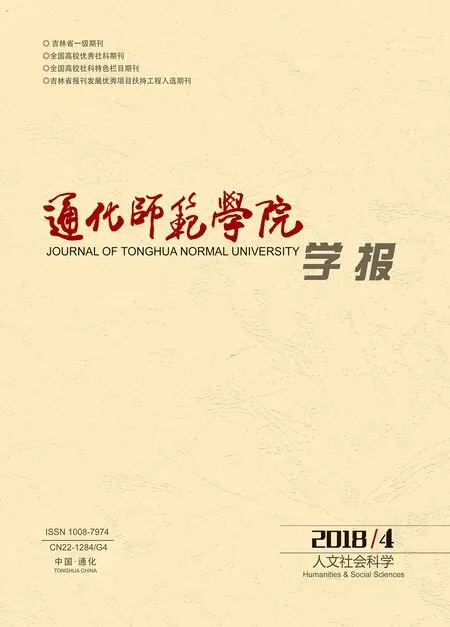侨民宗教:哈尔滨东正教的特殊存在模式
史 书
作为基督宗教三大派别之一的东正教,纵观其传入中国的历史,与其他两派(天主教和新教)差异非常明显。从17世纪末东正教开始进入中国,直到鸦片战争,东正教在华的主要服务对象一直仅限于北京的阿尔巴津人及其后代。可以说是阿尔巴津人把东正教带进中国的。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俄天津条约》以及《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北京传教士团才真正得以行使其传教的使命,开始积极地向中国人传教,并将大量的东正教经典翻译成汉文。到了1900年,中国信徒增至500人[1]307。义和团运动之后,东正教又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高峰期,北京传教士团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地都分别设立了分部。到1916年,领洗东正教的中国籍信徒已经达到5587人[1]309。十月革命后,俄国爆发内战,在华东正教人数突然猛增。上海、天津和新疆等地的教徒人数最多时分别增加到了2万、5千和1万人左右[1]316-323。不过,这些突增的东正教徒并非中国人,而是来自俄国的侨民。特别是东北一隅的哈尔滨地区①指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东铁路沿线及周边由俄罗斯人经营的地区,这一区域被俄罗斯人称为满洲或北满。,以其庞大的侨民团体(30万人[2])成立了独立主教区,形成了北京传教士团之外在华东正教的另一个中心,并成为侨民宗教的典型代表。
事实上,“侨民宗教”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侨民宗教”不乏其例。“唐朝的所谓‘三夷教’(景教、祆教和摩尼教)构成中国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3]140。甚至可以说,除了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以外,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新教在一定时期都属于侨民宗教[4]233。
一、从哈尔滨东正教的源起看其侨民宗教属性
哈尔滨的东正教是因为俄侨的涌入而兴起的。俄罗斯人进入哈尔滨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98年中东铁路的修建开始;第二阶段则是俄国内战①笔者根据哈尔滨俄侨在法律地位上的不同将俄国内战作为哈尔滨俄侨发展史的分界线。因为,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内战爆发。20世纪20年代流亡难民开始大量涌入哈尔滨地区。因此,俄侨在哈尔滨的历史不能单纯地以十月革命为界线,应该以十月革命之后的整个俄国内战为一个大的分界点。之后。
第一阶段的俄罗斯人进入哈尔滨地区是源于沙皇向中国东北地区的扩张策略。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顺利在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俄罗斯以保护中国免受日本对东北的侵扰为借口,攫取了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的权利,包括对铁路附近领土的经营权和使用权。
这一时期来到哈尔滨的俄罗斯人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中东铁路局的员工和家属,他们包括修建铁路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其他的相关工作人员;第二部分是俄罗斯商民。在沙皇“黄色俄罗斯”政策的刺激下,大量看到铁路沿线巨大商机的俄罗斯商人、手工业者以及农民纷纷涌入哈尔滨地区;第三部分则是俄罗斯军人(包括退役军人)②其中一部分属于中东铁路的护路队;另一部分则是以镇压义和团为由向满洲地区派驻的军队和参加日俄战争的军队以及之后留下的退役军人。参见:Петров В.: Город на Cунгари, Вашингтон: Рус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1984,C.11。。这些俄罗斯军民迅速在哈尔滨和铁路沿线建起了许多俄侨村镇。东正教则是为了保证这些俄罗斯军民的宗教生活而进入这片土地的。
1898年,这是哈尔滨东正教发展的起点,哈尔滨最早的教堂被设立在一座简陋的草棚里,后迁至铁路工棚,并命名为圣尼古拉教堂③座落在白毛将军霍尔瓦特将军庄园(今哈尔滨市香坊区卫生街)的附近。。第一位主持宗教事务的是护路队的随军司祭亚历山大·茹拉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Журавский)神父,其主要服务对象是中东铁路护路队军人以及第一批勘测技术工程师和建筑人员。随着哈尔滨城市建设的不断扩大,俄罗斯居民也在迅速增长,为了维持这些不断涌入的俄罗斯人的宗教生活,在哈尔滨以及中东铁路沿线接连修建了一批新教堂④包括圣尼古拉大教堂(后来的主教座堂),军人教堂—伊维尔教堂,由军人教堂转变为教民教堂的索菲亚教堂,商学院附属教堂,还有另一座也是由军人教堂转变而来的马家沟的阿列克谢耶夫教堂,以及新墓地教堂——圣母安息教堂。还有北京传教团分会教堂——圣母领 报 教 堂 等 等 。 参 见 :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Храмы в Cеверной Маньчжурии, Харбин: Казанско-Богородицкий мужской монастырь,1931,C.1-17。。这些教堂都是因中东铁路局、护路队,以及俄罗斯商民的需要而建。正如当年东正教教会史学家苏马罗科夫(Е.Cумароков)所写的那样:“北满的教堂是随着俄罗斯居民数量的增长,在他们特别集中的地方修建起来的。”[2]这也印证了东正教在哈尔滨兴起的原因并不是为了向中国人传教,而是为了服务自己的侨民。这一点与北京传教士团初来中国的动机相似(为了保护阿尔巴津人的精神生活)。这是在华东正教与基督宗教的其他两派不一样的地方。
这一阶段来到哈尔滨的俄罗斯人享有较高的法律地位。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们并不等同于异国他乡的侨民。因为他们将自己视为哈尔滨的“主人”,是俄罗斯“属地”上的“沙皇子民”。他们享有治外法权,不受中国政府与法律的管辖及制约。在哈尔滨,俄罗斯人有自己的政府(铁路局)和法庭,还有自己的军队和学校。学校也是根据俄罗斯的教学体制而建。对于当时的俄罗斯人来说,哈尔滨除了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国,其他的一切,从城市外貌到内部生活均属于俄罗斯的[5]8-9。所以到现在,有一些俄罗斯人仍然习惯称哈 尔 滨 为“русский город(俄罗斯的 城市)”。关于这一点,从当时的俄罗斯人学习汉语的态度就可以看出。当时的俄罗斯人并不积极学习当地语言(中文或满语)。在仅有的四所学校里,只有商业学校教授中文,而且中文并不属于第一外语,第一外语基本上是拉丁语、德语、法语和英语等西语。反倒是为他们工作的中国人需要积极学习俄语,以便于和他们交流。[5]17这便是早期哈尔滨的俄罗斯人所享有的法律地位以及身份定位。
第二阶段来到哈尔滨的俄罗斯人,是源于十月革命之后爆发的俄国内战。这一时期,哈尔滨俄侨人数的规模迅速壮大,因为内战导致大量俄罗斯难民逃入中国东北地区。曾经是俄罗斯扩张目标的哈尔滨地区,此时却成为俄罗斯白俄政权和逃亡者的避难所。与第一阶段的俄侨不同,俄国内战之后,哈尔滨的俄罗斯人正式成为了流落在异国他乡的“侨民”,甚至是无国籍的流民。到1926年,他们逐渐失去了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一切“沙皇子民”的待遇。他们必须遵守当地政府的管辖,并受制于不断更替的政权,还会受到中苏关系的影响。尽管如此,哈尔滨的俄罗斯人仍然是哈尔滨地区经济领域和文化生活的主导力量。这是因为前二十年俄罗斯人在哈尔滨已经奠定的社会基础,以及当时中国局势的不稳定因素。大量白俄难民的融入,反而刺激了哈尔滨地区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其中,一批裹挟在难民里的东正教神职人员和修女的进入,带动了哈尔滨东正教的发展。此时的东正教会已成为流亡俄侨最重要的精神凝聚场。在这些避难的神职人员当中不乏一批高级僧侣:他们包括图尔盖和奥伦堡的大主教梅弗季(哈尔滨教区的主管主教)、大主教梅列基、大主教涅斯托尔,以及后来的苻拉迪沃斯托克教区主管主教米哈伊尔等[6]290-294。这些东正教神职人员带领着哈尔滨的俄侨迅速建起了一批新教堂。哈尔滨教堂总数的三分之二几乎都是这一时期修建的,并以这些教堂为中心形成了许多堂区。几年之内哈尔滨地区的东正教徒就迅速增加到了近30万人。一时间成为了当时东正教在华人数最多的地区,也造就了东正教在华发展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哈尔滨的东正教是因俄罗斯侨民的涌入而兴起,又因俄侨团体的壮大而兴盛。从原初的那一时刻起,哈尔滨的东正教会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任务就是服务来自俄罗斯的侨民。后来,哈尔滨的神职人员和信徒人数迅速增长,这些人几乎也都是俄罗斯人,中国东正教徒凤毛麟角。并最终成立了独立的教区。1956年后,哈尔滨东正教的侨民宗教属性与居住于哈尔滨的俄罗斯族的民族宗教属性①关于中国东正教与中国俄罗斯族的关系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国东正教具有一定的“民族宗教”属性。参见王帅:《新疆东正教的现状与思考》,载于石衡潭、李栋材主编,《东正教研究》(第1辑),民族出版社,2017,第282-285页。有一定的重合交叉,但侨民宗教的特点直到今天一直存在。
二、从教会的隶属关系及其使命看哈尔滨东正教的侨民宗教属性
自从1898年第一座教堂建立开始,哈尔滨东正教会的隶属问题就曾历经多次调整。在东正教进入哈尔滨的前两年(1898—1900年),俄罗斯圣主教公会决定:与后贝加尔湖相邻的北满的东正教居民由后贝加尔湖主教管辖。到了1902年,在北京传教士团的请愿下,俄圣主教公会将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东北地区的神职人员划归北京传教士团管辖。期间,当中东铁路正式交付使用后,中东铁路局又将满洲地区的神职人员纳入铁路局宗教事务科的人员管理范围。但是整体的教会事务,仍归北京传教士团管理。到了1907年8月,俄罗斯圣主教公会颁布谕令正式取消北京传教士团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管辖权,并将哈尔滨及中国东北地区的东正教事务划归俄罗斯境内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教区管辖。这样的调整,表面上是因为区域管理的便利,实际上,体现了当时的俄罗斯政府希望将中国满洲地区的东正教事务视为其国内教区事务的意图。还在1902年,当北京传教士团请愿收管哈尔滨地区的东正教事务时,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А.Н.Куропаткин)将军曾经向圣主教公会提议:应该“只将中国境内俄罗斯军队已经撤离地区的神职人员划归北京传教士团管理,而其他由俄罗斯军队所占领地区的神职人员则应该纳入附近属于俄政府管辖的教区管理”[7]。这样的建议在1907年得以实现,哈尔滨的东正教事务正式纳入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教区管辖,并服从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滨海地区大主教耶夫谢维(Евсевий)。相比之下,同样在中国地界内的北京传教士团则是俄罗斯东正教的驻外教区,属于东正教的涉外事务。两者相比,这一时期的哈尔滨东正教,已经体现出了明显的“侨民宗教”特性。
俄国内战爆发后,哈尔滨的东正教团体不承认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服从塞尔维亚的“国外临时主教公会”的管辖,并在国外主教公会的支持下,于1922年成立了独立的主教区。当时独立的哈尔滨教区从行政关系上与北京传教士团属于平行关系。由于在1907年以前,哈尔滨地区的东正教事务曾经接受过北京传教士团的管辖。因此当哈尔滨决定成立独立教区的时候,北京传教士团提出了抗议,因为传教士团团长认为中国境内的所有俄罗斯东正教会都应该统一在北京传教士团的领导下。其实,哈尔滨之所以成立独立教区,与哈尔滨东正教会特殊的历史背景不无关系。哈尔滨东正教会建立之初是为了配合中东铁路的修建以及俄罗斯向中国东北扩张策略的实施。因此,从一开始,哈尔滨的东正教就与进入哈尔滨的俄罗斯人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哈尔滨东正教在教团的规模、水平、素质①由于俄罗斯内战导致大量俄罗斯的高级僧侣(大主教、大司祭等)进入哈尔滨,因此哈尔滨有条件建立水平较高的教团。,以及教徒的人数规模(近30万)和教民的宗教素养②哈尔滨的东正教会是由俄罗斯侨民组成,俄罗斯人自幼熟知东正教教义与传统,是成熟而虔诚的信徒。因此,对为他们提供宗教服务的神职人员的素质要求与针对其他民族的非教徒进行传教的传教士是有所不同的。上都与北京传教士团的规模不相上下,甚至超越了北京。因此,其建立独立教区是有一定道理的。
另外,由于哈尔滨的东正教从一开始就是因侨民而兴起,因此哈尔滨教区的使命与北京传教士团的使命在形式上也不完全一样。两个教会团体在功能属性上存在一定的差别。北京传教士团就像其名称一样,其首要任务应该是向非教徒传播东正教,吸纳非教徒成为东正教徒。其主要的传播对象应该以中国人为主。正如18世纪彼得大帝向中国派遣第一届传教士团时,就已经明确指出的那样:“使中国和西伯利亚民众从罪恶的崇拜偶像、不信基督的黑暗中走向东正教信仰的光明,使他们认知圣洁的上帝”[8]26。虽然,历史上由于清政府“禁教”以及中俄外交关系等各种原因,传教士团有很长一段时间并不传教,且主要从事外交以及情报方面的事务。但是,一旦机会成熟,传教士团就会发挥其向非教徒传播宗教的功能和使命。特别是在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允许俄罗斯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之后,北京传教士团的活动逐渐集中在了其本质工作上——向中国人传教。
哈尔滨教区则完全不同。哈尔滨教区从一开始的定位就是“教民教会”,无论是从哈尔滨东正教教徒的国籍来看,还是从哈尔滨教徒的人数规模来看,教区的存在都是在为自己的教民服务。它的主要功能是带领本教区的东正教徒进行有序的宗教生活。他们的服务对象是教区内虔诚的东正教徒,也就是俄罗斯侨民。教区的主要宗旨就是如何让流亡在异国他乡的东正教徒能够继续正常的宗教生活,并让他们的信仰获得维持以及能在下一代得到传承。作为“一个没有政权,没有领土的民族,这些侨民以最纯粹的形式团结在精神生活中。”[9]118当时哈尔滨教区内的俄罗斯东正教徒,包括神职人员大多数都是因为俄罗斯内战逃亡而来。与那些身负传教任务的传教士不一样,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在异乡团结自己的教民共同生存下来,等待内战结束之后,重返家园。这样一来,无论是从教区的服务对象,还是从教区本身的功能属性来看,哈尔滨教区都带有侨民宗教的属性。当然,在俄国内战爆发以前的哈尔滨东正教会所服务的对象也是仅针对那时的“沙俄子民”。因此,无论是在哈尔滨教区成立之前,还是成立之后,哈尔滨的东正教都属于“教民教会”。
关于哈尔滨东正教会与北京传教士团在使命上的区别问题,体现在两个教区划界问题的争论上(1926年)[7]。当时,隶属于北京传教士团的教堂被教会内部称为“传教士团教堂(миссийские церкви)”,而哈尔滨教区管辖内的教堂则被称为“教民教堂(приходские церкви)”。在哈尔滨教区的地界内有两座教堂并不隶属于哈尔滨教区主教管辖,而是直接受北京传教士团主教领导,被称为“传教士团教堂”,分别是满洲里的圣英诺肯提乙教堂和哈尔滨的圣母领报教堂。这两座教堂被认为“首先是为了满足传教士在中国人中间传播基督信仰真理的目的”[7]。哈尔滨教区的边界划定委员会曾经提出:“需要考虑到传教士教堂的性质。按道理,这些教堂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在非东正教徒的中国人中间进行传教,而实际上它们都是‘教民教堂’。如果这些教堂的存在首先被解释为为了满足教民的需要,那么无论是教堂还是神职人员都完全不合格……当然,不能说在传教士团教堂里有任何禁止举行教民圣事的规定,不过,有个先决条件,那就是缴纳教区所有税务,还有就是将这两座教堂的教民与附近的哈尔滨教区的教民隔离”[7]。从两个教区之间在行政界线之间的划分上可以看出,即使当时北京传教士团也在履行救助俄侨难民宗教生活的职责,但对于哈尔滨教区来说,北京传教士团在其职能上和水平上与他们是有区别的。这也更加印证了哈尔滨教区的定位是“教民教会”,其唯一使命是服务在华的俄罗斯侨民。
三、从神职人员的来源上看哈尔滨东正教的侨民宗教属性
神职人员是教会存在的基础,人们可以从神职人员的民族、毕业学校、与按立人的关系等方面,判断东正教的属性问题。在哈尔滨东正教120年的历史上,曾产生过6位主教级的神职人员,但没有一位是中国人。在培养神职人员的问题上,哈尔滨教区曾经在1927年开设了牧养神学培训班,此后在1937年升级为哈尔滨圣弗拉基米尔学院的神学系①哈尔滨的圣弗拉基米尔学院一共开设过三个系,但另外两个系不久分别停办,只剩下神学系,从这个角度上说,圣弗拉基米尔学院就是一个神学院。,提供高等神学教育。另外在1938年还开办了一所专业的神品学校,属于中等教育。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在教民中间培养教会神职的接班人,甚至希望他们将来有一天能够回到俄罗斯重振东正教的事业:“这些受过教育的神父能够有助于当地的宗教生活,特别是能为俄罗斯作出贡献,准备好通过传播福音来与无神主义做斗争,并把十字架重新放回东正教教堂。”[10]从这些未来神父被赋予的使命来看,其培养对象必然是以俄侨为主。这一点可以从第一届和第二届毕业生名单中发现[11]10。当时有很多从俄罗斯流亡而来的只具备中等神学教育的神职人员,最后都是在哈尔滨完成的高等神学教育。
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哈尔滨教区有过培养中国籍神父的计划。在现有的哈尔滨教区的历届神职人员名单[11]10中并未发现中国籍人员②虽然,在神学院教师的名单中有一名叫伊万·亚历山大洛维奇·吉姆波(И.А.Тимбо)的中国籍东正教徒(Троицкая C.C.: Харбинская Епархия, Брисбен:Издание«Жемчужина»,2005,C.10.),他主要教授中文和日文课程,还曾经将《金口圣约翰礼仪》翻译成中文(Cумароков Е.Н.:Харбинская епархия в прошлом и настоящем //Хлеб Небесный,1942,№5,C.37),在《亚太地区和北美地区的俄罗斯侨民名典》中也简短地提到过吉姆波是哈尔滨的一名教师,主要从事语言学方面的研 究(Хисамутдинов А.А.:Российская эмиграция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и Южной Америке,Био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Владивосток:Дальневост.ун-та,2001 C.303.)。除此之外便没有任何其他的信息。唯一出现过中国学生名字的是由教会建立的音乐培训班(Cумароков Е.Н.:Харбинская епархия в прошлом и настоящем // Хлеб Небесный,1942,№6,C.32),但音乐培训班并不是培养神职人员的地方。而50年代哈尔滨所出现的第一批中国籍神父则全部是由北京传教士团开办的神品学校培养出来的。。而哈尔滨教区的历届神职人员几乎全部由俄罗斯人组成③在哈尔滨教区成立之初,教区委员会就要面对大量无教职教士的生存问题。因此,在教士比教职多的背景下,不可能产生培养其他民族为神职的需要。即使到了30年代,哈尔滨开始出现神职人员后继无人的危机时,面对大量成熟的俄罗斯教民,培养自己的神职人员则是当务之急。。中国籍神父则是50年代之后才出现的④20世纪50年代,基督宗教各派的外籍神职人员相继离去,中国三自教会相继成立,东正教也面临中国化的需要。北京传教士团出现了首位中国籍主教杜润臣,并随之将以前培养的一批中国籍教士祝圣为神父。详见Православие в Китае,М.:Отдел внешних церковных связей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патриархата,2010,C.148-173。。这是由于当时的哈尔滨教区已经严重萎缩。大量俄侨的撤离,也导致了众多神职人员的离开①哈尔滨教区的最后一任主管主教尼康德尔(епископ Никандр)于1956年离开哈尔滨回到苏联。。此时一批中国籍神职人员②当时哈尔滨的俄罗斯籍神父都纷纷撤离之后,逐渐由中国籍神父接管几个主要教堂,其中王玉林是圣索菲亚教堂的最后一位神父、何海林是圣母领报教堂(哈尔滨的北京传教士团分会)的最后一位神父、朱世朴是哈尔滨圣母帡幪教堂的最后一位神父。这些神父基本上都是在北京接受神学培训的,并由北京传教士团主教为其举行的按手礼。参见Православие в Китае,М.:Отдел внешних церковных связей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патриархата,2010,C.148-173。替补了哈尔滨的神职空缺,他们全部由北京传教士团培养并委派,这也是哈尔滨东正教的最后一批神父。正是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哈尔滨教区从最初的那一刻起就以服务俄侨为宗旨和使命,历史也没有机会让他们思考培养中国籍神职的问题。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哈尔滨东正教的神职人员仍然需要俄罗斯教会培养。
新中国建立之后,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在中国的外籍传教士和神职人员都陆续撤离,留下的则是大批已经成熟的中国籍神职人员和中国教徒,于是有了本土化的三自教会。东正教却因太过依赖俄罗斯政治和侨民,因此本土化问题困难重重。无论是在俄国内战前,还是新中国成立前,哈尔滨东正教最重要的载体是侨民,哈尔滨的东正教会始终没有被赋予过传教的使命。从中东铁路的修建,到俄国内战后的难民,其宗旨都是为了维持与传承俄罗斯侨民的精神信仰。
四、从文化慈善事业看哈尔滨东正教的侨民宗教属性
哈尔滨东正教会的宗教教育与文化生活针对的主要对象也是俄罗斯的侨民。为了满足哈尔滨俄侨的精神文化生活,哈尔滨教区开设了图书馆,从各方收集了大量神学以及各类经典书籍。不过图书馆的藏书基本上是俄文书籍,主要针对俄侨开放。同时,哈尔滨教区还创办了教会报刊和杂志,如《天赐食粮》(Хлеб Небесный)、《领袖》(Кормчий)、《善良的牧师》(Добрый Пастырь)等。当时宗教书籍的出版发行主要由伊维尔兄弟会来承担,而印刷厂则设立在喀山圣母男修道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在哈尔滨出版印刷的期刊和书籍几乎③目前只发现了一本由И.А.Тимбо出版的《金口圣约翰弥撒》(Литургии св.Иоанна Златоустого)的中文翻译 ;参 见 :Cумароков Е.Н.:Харбинская епархия в прошлом и настоящем // Хлеб Небесный,1942,№5,C.37。都是俄文版的。其读者范围除了哈尔滨地区的俄侨,还延伸到了其他国家地区的俄侨。显然这些文化事业的受众主要是俄罗斯侨民,而非当地的中国人。这亦说明哈尔滨教区并没有将传教当成其主要任务。因为将教义经典翻译成当地文字是传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用自己的文字出版书刊往往是侨民社团的一贯行为。
为了让东正教信仰能够在下一代人当中得以传承,哈尔滨教区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宗教教育体制。“满洲教堂的使命不仅是满足宗教需要,它们同时还是教育的摇篮”[2]。哈尔滨教区的宗教教育主要是以在各类学校开设神学课,由教会分派神职人员去教授的方式进行。教会负责向各教学机构提供宗教教育资源[7]。根据1933年的记载④此时哈尔滨的俄罗斯学校已经分化为两类,一类属于苏联公民(承认苏联政府,持有苏联护照),在这一类学校不开设神学课;另一类则属于俄罗斯侨民(不承认苏联政府),在这一类学校就开设神学课。,在哈尔滨仍有25所学校和3所幼儿园在教授神学课[7]。这些学校都是俄罗斯侨民学校。这些俄罗斯人从出生就受洗入教,接受神学教育,是他们从俄国沿袭而来的传统。正因如此,20世纪20年代,当时的东省特别行政区规定“宗教课程不能成为必修课”⑤应该是在1924年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后。东省特别行政区曾要求所有学校里的“宗教课程不能成为必修课”。这一政策主要是为了抵制西方教会学校强制中国学生接受宗教教育。不过,哈尔滨教区内的宗教教育则完全属于另一种情况。,这一政策对于哈尔滨的很多俄罗斯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哈尔滨教区委员会组织家长委员会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抗议,在递交到东省特别行政区长官张焕相手中的抗议书中强调:“俄罗斯民族学校若没有神学课是不可思议的,没有神学课,就没有俄罗斯学校……我们请求将神教课保留为必修课”[7]。哈尔滨俄侨学校开设的神学课主要授课对象是自小就接受宗教教育的俄罗斯学生,其宗旨是为了在自己侨民的后代中传承他们的精神信仰。
除了教育事业,哈尔滨教区的慈善事业在建立之初也主要是为了救助在华的俄侨难民。其中还涉及救助从俄罗斯逃亡而来没有教职的东正教教士。哈尔滨教区成立之时,受命管理教区的大主教梅弗季本人就是逃亡而来。教区设立各种慈善机构,其中包括伊维尔兄弟会建立的孤儿院“俄罗斯之家”[6]292、伊维尔教堂开设的谢拉菲姆免费食堂和四个分散在哈尔滨各区的福利院,贫困教士救济所、教士遗孤救济所、养老院、以及专门救助慢性病人的慈心院(由涅斯托尔大主教创办)[6]302等等。这些慈善机构建立的初衷都是为了收容来自俄罗斯的难民。
虽然并不排除哈尔滨东正教会所创办的文化教育事业和慈善事业曾惠及中国人。但这些事业的建立初衷却是为了救助俄侨。相比之下,天主教与新教的传教士在中国建立的文化教育事业和慈善事业主要针对的却是中国人。这也是哈尔滨东正教具有侨民宗教属性的一种体现。
哈尔滨的东正教因侨民的涌入而辉煌,也是因侨民的撤离而衰落。虽然俄国内战爆发后,不仅哈尔滨教区,包括以北京传教士团为中心的其他各地区的东正教会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了救助流亡俄侨的生活上。但是,哈尔滨东正教侨民宗教的特征却是最典型和最具代表性的。无论是中东铁路的修建,还是俄国内战后的难民潮,哈尔滨的东正教会一直面对的是不同时期涌入的俄侨,保证他们的宗教生活是哈尔滨东正教的重要(在当时也是唯一的)使命。哈尔滨和北京分别形成了东正教在华的两个中心。东正教在这两个中心的发展分别体现了东正教在华发展的两大特点:对世俗政权的极度附庸,以及对俄罗斯侨民的依赖。正是因为东正教对世俗政权的极度依赖,才导致其官僚化做派和缺乏自主发展意识。大批流亡俄侨的涌入,才是其在华发展高峰期的原因,这种依赖世俗政权和本国侨民的发展模式在宗教传播的道路上,必然会因政局的改变和侨民的撤离而受到严重的影响。像哈尔滨教区这样曾经如此庞大而高度系统化的教会组织,却因为俄罗斯的政治动乱和中国的政治变革导致不同时期俄侨教民的相继撤离,最后只剩下一批博物馆式的教堂遗址和寥寥无几的教徒。而对侨民的依赖还会阻碍东正教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并形成一定的保守主义。因此,当俄罗斯神职人员和侨民撤离之后,东正教却因为没有及时与中国文化有效融合而面临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