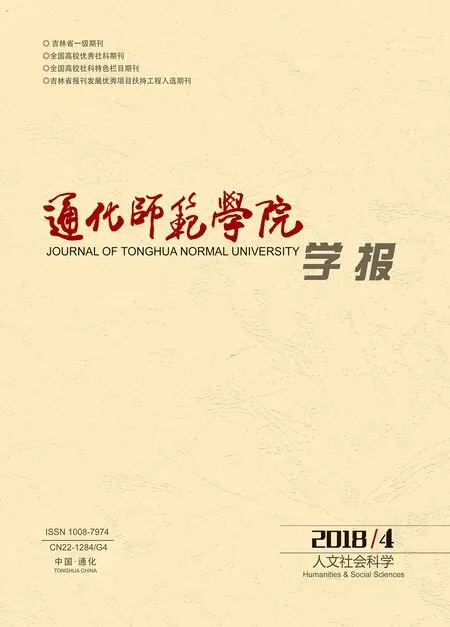论俄罗斯东正教在中国发展缓慢的原因及启示
王志军
东正教是基督宗教的三大宗派之一,分散广泛。近现代以来,“东正教在中国的开端乃是与俄罗斯东正教联系在一起”[1]75。俄罗斯东正教在中国已经存在了三个世纪,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京传教士团[2]。毋庸置疑,东正教在中国的传播缓慢,对中国人的直接影响甚微,探究其背后的原因,学者们也是见仁见智,下面我们将从中国学者和俄罗斯教会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中国学者对于东正教在华发展缓慢原因的探讨
对于这一问题,国内的学者主要通过中俄近代侵略与反侵略的关系史、俄国在中国的侨民史进行反思。
第一种观点,以张绥先生为代表。张先生认为,东正教在中国发展缓慢的原因,主要是其传教对象和传教主体出现了严重问题,导致东正教不能同中国传统文化有效结合。张先生在《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一书中,这样评述道:“任何一个宗教要想在中国汉族地区流传,假如不考虑汉文化的特点,不能主动地吸收汉文化的因素,是很难取得汉文化的容纳的。”[3]304因此,他认为,对于东正教没有在中国取得重大进展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两个具体方面:一是,关于传教对象的选择出现偏差,如“由于俄罗斯正教传道团,一直不注重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发展信徒、培养神职人员,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东正教也一直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这应该说是俄罗斯正教难以在中国居民中有较大发展的主要原因。”[3]242在张先生眼中,“不能使中国知识界从文化的角度感到兴趣,这就使俄罗斯正教在中国的传播失去了一个最有效的‘中介’层次。而那些到俄罗斯正教传道团所办工场谋生的中国百姓,大多数又是为了‘糊口’而信仰东正教的。……当他们一旦脱离这些工场以后,其中绝大部分人就认为已同教会脱离了关系”[3]305。二是,东正教神职人员数量严重不足。张先生认为,之所以出现中国籍居民皈依东正教人数不多的情况,不可忽视的是“从事传教活动的人员太少。”[3]241这也使得俄罗斯东正教成为不能为汉文化所容纳的“侨民教会性质”[3]305。
第二种观点,以乐峰先生为代表。乐先生的这种观点,代表了中国国内20世纪末期对此问题的主流意见。乐峰先生运用大量的俄文史料,力图证明沙俄在中国近3百年的传教历史,就是他们利用东正教侵华的历史,是无恶不作的罪恶史。原因如下:一是东正教的传教活动与沙皇的侵华活动密切结合;二是东正教传教活动与沙俄的军事、贸易、外交密切相配合;三是东正教传教士是一群打着传教幌子从事间谍活动的“文化特务”;四是东正教传教活动披着“慈善”的外衣干着罪恶的勾当。正是如此,“传教士”并不是真正传教,而是披着宗教的外衣从事间谍特务活动,搜集中国情报,为沙俄的侵略政策服务。所以,沙俄政府利用东正教的这种侵略活动,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必然被中国人民所唾弃[4]。
第三种观点,以台湾著名俄国问题专家明骥先生和北京的佟洵先生为代表,他们认为,此问题的症结应该归结于东正教与政治因素纠缠得过于密切。明先生在《中俄关系史》一书中,对东正教来华的起源、发展、目的,以及传教绩效不显著的原因作了分析。他认为,俄国东正教会(北京传教士团)在华传教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与其他西方教派相比,其政治色彩更加浓厚……他们在助长帝俄攫取中国领土及其他权益的策略固然成功,但此种作为,都构成了中俄两国长期不能和睦相处的因素。”[5]338也就是说,在明先生的眼中,沙皇俄国在中国的侵略越成功,那么,东正教的传教事业就会越失败。佟洵先生认为,东正教传入中国后,总是过多地和政治纠缠在一起。过多地借助政治势力来谋求宗教的发展,其结果则损害了东正教长期发展的潜能;东正教所代表的俄罗斯民族利益同中华民族利益的冲突是东正教在中国难以发展的一个更本质的原因。因而,造成了中国人对东正教的拒斥心理[6]。同此相似,有学者认为,俄罗斯在经济、文化上的弱势很难与另两位基督宗教的同族兄弟(天主教与基督宗教)所依赖的西方列强匹敌,也使得东正教传教士很难自觉和有意识地去扮演先进文化传播者的角色,从而影响了东正教的传播[7]。
第四种观点,以高崖教授为代表。高先生认为,东正教的传入多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强行殖民,是以刺刀和枪炮为后盾的,这就使中国人对东正教“敬而远之”。人们看到、听到的不是耶稣舍己为人的崇高人道主义关怀,而是许多烧杀、抢劫、奸淫妇女的兽性事件。这些流血事件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迹,自然也就对侵略者的宗教“恨屋及乌”了。近代中国政治、经济落后,造成文化上的不平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原来的那种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俄人教徒心中仍然强烈地存在,他们把华人看作是低下的民族,不配为上帝的选民[8]。加之语言、民族习惯方面的障碍,大多数俄国人不与中国人交往,因此哈尔滨及周边地区信教的中国人很少①高崖先生在此文中引用了如下数据:据1953年的调查,尚志、牡丹江、阿城、东宁、穆棱,共有东正教徒2289人,全为苏联国籍,无一华人。参见高崖:《黑龙江东正教钩沉》,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1期。相关数据,亦可参见,黑龙江省外事办公室:《黑龙江省志·外事志》(讨论稿),1991,第143页注释①。。
第五种观点,以唐晓峰先生为代表。唐先生通过对于现代中国东正教徒(集中于东北、新疆、内蒙古、北京地区)的广泛接触,从传播学的4个主要要素出发,为人们提供了如何看待东正教在中国的传播处于劣势的另一种视角。在唐先生眼中,东正教在中国存在与发展的危机表现:宗教传播主体(谁来传)、宗教传播内容(传什么)、宗教传播媒介(怎么传)、宗教传播对象(传给谁)软弱乏力。一是宗教传播主体乏力。东正教信徒个体、神职及其组织的规模和数量“十分有限且薄弱,有限的信徒及组织无任何外宣的动力,甚至连子女都很少再坚持这种信仰”,可以“给予信仰指导的神职人员在短期之内又无法得到更新,造成其在传播主体上的危机”[9]221。二是传播内容匮乏。虽然“东正教神学较天主教及新教神学具有更强的保守性、稳定性,反对神学进步和革新,但即使如此,这些‘稳定’且易于把握的神学主题离中国的东正教信徒仍十分遥远。”[9]222三是传播渠道有限。中国的东正教会缺乏介绍自己教义知识的印刷品。信徒数量有限、传教热情不高、缺乏神职人员以及有限的教堂数量之间“形成一种负面互动”[9]224。四是传播对象流失。由于历史的原因,“光从宗教受体的层面来讲,如果将东正教潜在受体仅仅局限于数量不过一万多人的俄罗斯族,或者扩大为所有华俄后裔,这种趋向对于东正教在中国的发展来说,无疑是故步自封之举”[9]225。唐先生的这种观点,像是以上几种观点的综合体,较具有系统性。
第六种观点很有意思,它强调了东正教在华传播的“特殊性”,尤其是北京传教士团的特殊性,此种观点以肖玉秋先生为代表。在肖先生的眼中,之所以说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特殊,就是“因为它在缘起与沿革、构成与换班、给养与经费、组织与管理、使命与职能等许多方面都具有与西方来华传教士完全不同的特征。这种特殊性的产生与中俄两国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东正教的实质以及中俄两国的社会变迁都有密切的联系”[10]。肖先生的这种观点新颖之处在于,其着眼点没有局限于教会自身,而是从中俄两国的国家交往中寻找症结。
二、俄罗斯教会对于东正教在华历史经验的反思
俄罗斯东正教内部神职人员对于东正教在华历史的思考,源远流长。一方面,他们注意到,东正教在华的传播无法与同属基督宗教的天主教与新教相提并论[11]5。另一方面,他们也强调,20世纪的中国东正教的历史,在客观上存在特殊性,留给俄罗斯东正教发展的机会并不多。主要代表观点如下:
第一,俄国东正教驻北京第8届传教士团团长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Cофуроний,1814年去世)在其所撰写的文章《未名札记》,指出东正教同天主教和新教相比,东正教未能在中国扎根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同中国文化很好地相融,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点:一是东正教的神职人员方面存在一定问题,例如,在中国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的思想意识中,“中国化”没有受到重视,不像西方天主教传教士那样,为了便于同中国人交往,很快就穿上中国的服装;俄国传教士不熟悉中国的风俗传统,绝大多数神职人员不熟悉中国语言,难以开展传教活动;传教士团内部真正懂宗教有学问的人不多,因而在传教方面收效甚微;传教士内部混乱,人员屡犯教规,给中国人的印象极坏,在中国人中间传教没有市场;他们没有在中国开办更多的宗教学校,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因而难以扩大影响。二是东正教没有像新教和天主教一样,拥有较充足的资金支持和广泛开展社会服务活动来吸引中国人。沙俄政府拨给传教士团的经费有限,因而俄国传教士团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发展传教事业;东正教没有像天主教、新教那样,在中国广泛建立慈善机构(如兴办医院,孤儿院等)吸引中国人。三是东正教传教士在使用圣经方面没有与儒家经典相结合,不像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利用儒家思想论证基督宗教教义,以便适合中国士大夫和统治者的胃口[12]。
第二,1933年,哈尔滨教区主教涅斯托尔在设在南斯拉夫的俄罗斯东正教海外主教团公开演讲时,曾经提到他拜访过的哈尔滨市附近阿城城里的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团,感慨良多,他说:“我们先拜访了天主教北京传教士团,那里正在用汉语举行圣母安息日的礼拜仪式。中国天主教徒依照新历于当天庆祝圣母安息日。举着圣母像的十字架游行由年轻的中国司铎主持。那些在天主教北京传教士团学校受教育的中国小孩们令人很感动,他们严格遵守纪律,很好地参与着教会活动。离开天主教北京传教士团,我们来到由斯堪的纳维亚传教士组建的长老宗北京传教士团。该北京传教士团设有药店、医院和学校。学校分为男校、女校和专司《圣经》学习的主日学校。其中一个传教士是女医生,她告诉我们,就在我们来之前,她接连给4个中国人做完大手术。我们一行人参观了运营良好的诊所和医院,看望了所有病人,他们中有中国人和满洲人,有男有女。他们都得到了传教士们细心的关怀和呵护。这些外国北京传教士团真令人羡慕,他们拥有大量的资金,能够完成许多工作”。[13]23-24在这段话中,涅斯托尔通过具体的事例,将哈尔滨地区的俄罗斯东正教在与其他基督宗教相比较时的困境,明显地揭示了出来,这种困境的主要方面就是东正教在开办学校、资金和传教手段方面的缺乏。
无独有偶,中国俄罗斯传教士团主教维克托尔在1949年给莫斯科和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谢一世的报告中,提出了恢复在中国人中进行传教的问题,重点提及资金问题:“在制定具体和详细的经济发展计划时,维克托尔认为,将讲究实用主义的中国人吸引到东正教中来‘最为有效的方法应该是要让他们同传教团中的俄罗斯和中国教民在耕地上、菜园里、花园里和商业性企业等领域有事务上的联系。’”[14]148但是,这些计划却遭到了阿列克谢一世的指责。
第三,2010年,在由莫斯科宗主教区对外教会联络局出版的《东正教在中国》一书中,俄罗斯教会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问题所给予的回答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并不认为俄罗斯东正教与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相比,自己在中国传播失败(这种观点与上面的肖玉秋先生的观点有些类似):“俄罗斯传教团的主要任务,是使人数不多的在华俄侨后代保留东正教信仰。在这一点上他们同欧洲传教士有着本质的不同。非东正教的传教者劝说中国人接受一种对他们来说全新的基督教信仰,同时还要求他们放弃从先辈们那里代代相传的‘迷信’思想。而东正教的任务,则是教导阿尔巴津的后代必须保存好自己先辈留存下来的信仰,不让自己的教徒融入中国人的信仰。这个区别使俄罗斯教团的神甫避免了为证明基督教的优势而对中国传统进行侮辱性的批评,东正教神职人员免于与维护中国宗教支柱的清廷产生冲突。”[14]42他们还强调,如果“考虑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由俄罗斯革命、难民外逃和母教会的困难,则应该承认的是,俄罗斯东正教是不可能有机会在更早的时期内着手解决建设中国正教会这个迫切任务的。”[14]154另一个方面,书中也会偶尔提及东正教在中国的困难。例如,在康熙当年恩赐给阿尔巴津人中国罪犯的遗孀当妻妾这件事情上,就被认为“差不多可以说是我国哥萨克士兵道德崩溃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些多神教的淫乱女性严重破坏了哥萨克士兵家庭生活的和谐”[14]20。
第四,在В.В.谢里瓦诺斯基所主编《东正教在中国》一书中,他以时间为线索,分别叙述了各个时间中国东正教发展的特点,也列举了不利于东正教传播的因素,具体来说:19世纪上半期,由于内部的政治压力和文化因素,宗教身份与国家身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中国东正教的发展遭遇到严峻的社会政治困境。如,中国当局对受洗的国民采取施压的政策;新加入东正教的商人会因合伙人的告密,失去了个人在公司里的资本股份和份额;新入教的工人面临更大的困境,不仅中国人对他们持有敌意,而且俄罗斯工程队也不会录用皈依了东正教的中国泥水匠或者木匠,这些人可能成为真正的被社会抛弃的人[15]19-20。20世纪初是东正教的复兴时期,传教人数和信徒数量都明显增加;俄罗斯内战急剧改变了中国东正教传教团的性质,使其转向俄罗斯流亡人群[15]43;20世纪50—60年代,作者将中华正教会组建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国内政治环境恶化和中国东正教会高级神职人员的野心勃勃[15]48。
三、中国东正教兴衰的关键在于教会与世俗政权的关系
以上中俄学者对东正教在华历史的检讨反省,在我们眼中,都是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丰富借鉴与启示的。这里,我们只是着重强调,东正教对世俗政权的依附性特征,对于中国东正教历史进程有着重大影响。我们的观点是,俄罗斯东正教在中国传播的快慢、兴衰,最关键、最重要,同时,也是非常容易被人遗忘的,是它对于俄罗斯世俗政权高度的依附性,以及这种依附性所产生的影响。宗教问题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作为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它总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问题交织在一起。对于俄罗斯东正教而言,从其传入俄罗斯之日开始,它就与俄罗斯国家政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各教派的特点,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16]141正因如此,当英美等国“连跟两广总督直接进行联系的权利都得不到的时候,俄国人却享有在北京派驻使节的特权”,并且“使俄国外交在中国,也像在欧洲一样,能够产生一种决不仅限于纯粹外交事务的影响。”[17]698换言之,与其他两派基督宗教相比,东正教与世俗国家政权相结合的特点更加突出、更加鲜明,更加具有本质属性。有很多时候,当人们考察俄国传教团在中俄关系的历史作用时,往往看到在其背后的政治目的,但是,我们对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却探究得不够。东正教是“在拜占庭帝国皇权统治下产生的。在东正教的教阶制度中,拜占庭皇帝被视为‘上帝选民’的代表、神在人间的代表和教会的最高领袖。拜占庭皇帝拥有极大的权力,有权任免教会牧首,有权诠释教义和制定教规,有权管理教会生活等。如果教会不听从皇帝的旨意,教会的活动就要受到限制,甚至打击和迫害。就是说,教会必须绝对听命于皇帝,完全依附于世俗政权。”[18]318俄罗斯东正教的历史召示我们,东正教会就像农奴般地依附于国家一样,依附于沙俄世俗政权,甚至作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
从历史上看,与欧美新教来华传教士不同,十月革命前的“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尽管也有传教及为沙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动机,但由于其基本上是由俄国政府直接派出,直接由沙皇的谕旨或训令掌控,其来华动机带有更强烈的国家功利性,即几乎是完全按照沙皇的战略,为沙俄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19]。20世纪上半期是东正教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恰恰在这一重要时刻,俄国十月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发展轨迹,也决定了此后半个多世纪东正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自从“一九一七年十月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直到一九八八年俄罗斯基督教庆祝千年历史,苏联的正教会一直在围城的状态下生存。”[20]147面对巨大的灾难,一向依附于政府的东正教受到了严重削弱[20]148-151,教士们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对中国人进行传教活动①此外,当地中国人中流传的各种宗教观念,已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势力,深深地浸染了中国人民的心灵。例如,萨满教的“大神”、“黄仙”(黄鼠郎精)、“狐仙”(狐狸精)、“屈死阴魂”等。还有,各种民间信仰的土地神、龙王爷、灶王爷、门神、财神等。这些中国民间传统习俗对外来的东正教自然地产生了排斥作用,不是短期可以改变的。参见高崖:《黑龙江东正教钩沉》,世界宗教研究,1995,(1)。。同时,中国的俄罗斯东正教会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其性质也产生急剧改变:“主要是帮助俄罗斯难民,这也导致了中国东正教徒的不满”[11]3,号称俄罗斯的亚特兰蒂斯的哈尔滨教会“传教作用微乎其微”。在这些俄罗斯的移民中,“上帝所确立下的会福音的任务并没有建立起来,而且政治意味深厚的移民团体将教会与各种政治联盟拉近,没有人关心非基督徒的皈依事宜。”[11]43-44也可以说,就东正教整体而言,沙皇之后的新政权对传教事业带来了重大负面影响[21]627。加之,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大量俄侨撤离中国;50年代中期中俄关系恶化;中国十年文化大革命接踵而至,使得本就非常虚弱的东正教会,雪上加霜,根本无法度过此等严酷考验②即使一些神甫和信徒转入地下,但是,这种活动也是非常稀少,并且是没有组织性的。。这也是为什么同样面临母会的危机,日本与韩国的东正教会能够生存发展③日本的东正教会由圣尼古拉(Kassatkin,1836-1912)创立,他在1868年为第一个皈依者洗礼,日本的第一位神甫是在1875年被授圣职。现在日本有一位东正教主教,40位神甫,25000名信徒。韩国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也是由俄罗斯人建立的,时间在1898年,在20世纪最后的15年得到复兴。韩国现在有主教1名,教区数超过5个,还有一所神学院和一所修道院。参见韦尔:《东正教会导论》,田原译,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13,第191-192页。,中国大陆的东正教一直在生存与死亡的边缘徘徊的重要原因。从这个视角出发,宗教问题是小问题,而政治问题则是大问题。中国境内的俄罗斯东正教的发展史莫不如此:北京教团在中俄两国有关系的最初150年中,一直是俄罗斯在中国的唯一官方代表机构。随后的150年,政治因素也一直是主导其发展的主要方面;黑龙江地区东正教的产生的历史根源是中俄关系问题,决定现在黑龙江地区东正教发展的是中俄关系问题,整个中国俄罗斯东正教的情况与此类似。从这个视角出发,“资金问题”是表面问题,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它只是政治与教会关系的附属品、衍生物。换言之,俄罗斯东正教在中国的失败,乃是“它过分关注于为世俗政权服务”[22]。当然,中国的东正教会“始终具有‘侨民教会’的特征”[23]133、东正教自身保守性、深奥难懂的斯拉夫文等,也是阻碍其在俄罗斯之外其他地区传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