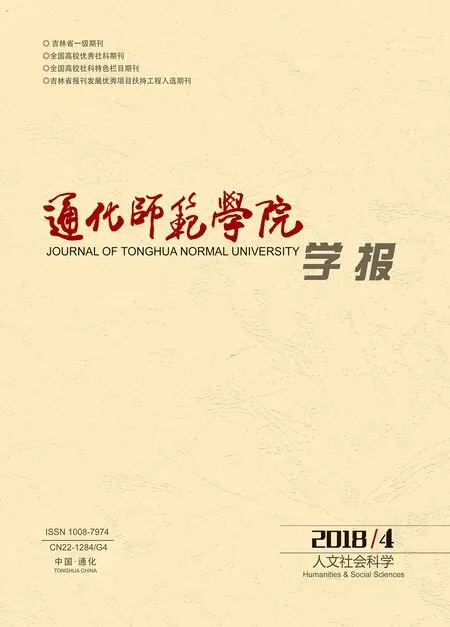独立与依附的文化向度
——论扬州刺绣与绘画的关系
杜晓禹,赵 芳,顾 浩
扬州传统的刺绣图式有其独特的艺术语言,与绘画没有直接的关系,可谓是游离于绘画作品之外。尽管刺绣与绘画在一定形式上有着相似之处,但其本质上的独立性是不容忽视的。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变迁,工艺技术的辗转流变,以及传统刺绣市场格局的缩小,扬州刺绣开始逐渐走向艺术欣赏品的道路,用针线将绘画演绎成刺绣作品,使之依附于绘画的存在。诸多工艺美术品与扬州刺绣有着相似的命运,用工艺重现绘画,已经成为当代工艺美术作品创作的主要手段之一。
那么,工艺美术与绘画关系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变化模式?其本质又是什么?
一、与民俗伴生的独立——传统扬绣图式
扬州刺绣①《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中收录扬州刺绣的定义为扬州刺绣:简称“扬绣”,与苏绣同出一源,是扬州著名的传统工艺品。素以劈丝精细、针法缜密、色彩丰富、表现力强著称,以绣制仿古山水、花卉、翎毛、人物、亭台楼阁等最擅长。作品采用点彩、乱针、发绣等不同技法,再现了古代中国画的笔墨气势的深浅、浓淡、虚实、远近的关系,绣品精丽、工整、细洁。扬州刺绣现除生产欣赏陈列品外,还采用手绣、机绣生产大量日用品,如绣童装、枕套、被面、帐沿、靠垫等,产品畅销国内外。参见:吴山主编.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江苏美术出版社,1999.12第852页属于苏绣一脉,它包括扬州地区和其下辖地区——宝应县境内的刺绣。新中国建立之前,扬州与宝应境内各乡镇女子出嫁时,都将刺绣品作为嫁妆的一部分。刺绣技艺在全境流行,与民俗伴生的吉祥程式化图式最为多见,为艺人们专为刺绣所创,具有形式原创性。
现存于扬州市汉墓博物馆的一件汉代刺绣碎片年代最为久远,此碎片于1980年出土于扬州市高邮天山的西汉广陵王刘胥夫人墓,其针迹清晰、色泽靓丽,纹样是用辫子股针法绣成的云纹、兽纹和变形的长寿纹。还有一件是现存于宝应博物馆的明代刺绣官服,官服的主人为明代江苏宝应人仲本,卒于嘉靖十五年(1536),于20世纪80年代宝应县泾河乡仲氏家族墓地出土。此次发掘出的刺绣官服实物距今四百多年,刺绣补子①补子,是以金线和彩丝绣成的表示官位品级的标徽。方形,钉饰在衣服上。参见:田自秉、吴淑生、田青主编.中国纹样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1第368页构图饱满华丽,针脚流畅精美。整个补子单纯地利用针脚的纹理将画面中动物兽和祥云的造型表现得精湛绝伦。通过补子的丝线色彩观察,整个画面仅采用一种颜色的丝线绣制,此种情况下是难以利用色彩的对比来彰显其图案的特征的,但刺绣者依靠自身深厚的绣工,用整齐的针脚排列成清晰的线状肌理来表现动物兽的轮廓、身上的回纹装饰及祥云的流动感,当时刺绣者的独运匠心在此可见一斑。
扬州传统刺绣与其他手工艺一样,起初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萌芽,被绣制在衣服、门帘、帐沿、荷包等生活品上,有着自身独特的语言图式。吕品田在《中国民间美术观念》中提到:“农业生产经验的积累和氏族宗法血缘传统的延续,使中国的实用理性特别发达,以至整个中国文化带有鲜明的实用性格。”[1]99扬州传统刺绣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的主要功能是实用性。刺绣衣服、荷包、鞋履、结婚喜被、鸳鸯枕等这些生活中的用品,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实用价值,每件物品上被绣着不同的图案,各司其生活中的职责。
清代吴炽昌《客窗闲话初集·张惠仙寄外诗记》中有这么一段话:“问:女年几何,曰:二十岁矣。问:近习何事,曰:刺绣耳。”[2]90刺绣几乎成为民间女子的唯一要务。刺绣艺术的社会环境与传授方法普遍是母女传授,大户人家的小姐有绣娘、针线老妈子相伴,传习刺绣技艺。以前学习刺绣,要先学剪纸花样,然后将纸样贴在绣布上,依据形状选择彩色丝线进行配色,最后进行绣制。人生的大好青春似乎全寄托在刺绣上。[3]4由此可见,刺绣是继承男耕女织的传统,在刺绣中寄托女性情思的一种方式。
扬州传统刺绣日用品除了普遍的实用性及帮助女子消遣时光、托寄情思的功用之外,它的装饰图案也有着一定的祈祥祝福功用。民间有“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之说,扬州传统刺绣的图饰都是吉祥寓意主题,这些具备象征意义的刺绣图案与其作为日用品的功能性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民间美术的创作观念中往往伴随着主体人的祈福、禳灾、避邪心理。扬州留存下来的民国时期的刺绣日用品大多表达了民间百姓的祈福心理,有服饰绣、婚嫁绣、得子绣、祝寿绣等种类。
扬州传统刺绣的实用、继承传统以及表达祈福心理的功能,使得各种图式都携带着各自的功能性、寓意性与符号性。
扬州“阮元家庙”②阮元家庙,坐落在扬州市毓贤街8号,占地9000平方米,现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阮元(1964-1849),字伯元,号芸台,别号雷塘庵主,晚号颐性老人,占籍仪征,实为邗江公道人。阮元从乾隆五十四年为进士,到道光年间共从政五十年,逐渐晋为太傅,谥号文达,《清史稿·阮元传》有“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之美誉。参见:阮元家庙文化景点的《阮元简介》《阮元家庙简介》。卧室内陈列着的清代民间刺绣品、扬州博物馆收藏的部分刺绣品以及宝应县文化馆收藏的床头挂件、门帘、绣花鞋等作品,相较四百年前的刺绣补子在色彩上有了明显的突破,此时已不是单纯地利用针脚肌理来处理画面,更多的是利用色彩的对比来表现造型特征。
过去在扬州,少女常常为自己的亲人亲手纳制绣花鞋垫,把对亲人的关切和思念一针一线地纳入鞋垫之中,伴随着亲人们远走四方,可谓是针针融心血,线线叠思念。这些鞋垫常绣有“福海无边”“事事如意”“莲花童子”等意味的图案花纹。鞋垫图样的花色繁多,风格各异,设计精美,在具有传统韵味的同时,又有着现代气息。
现存于宝应文化馆的传统刺绣鞋样上,绣着朵朵荷花与一只吉祥鸟,显而易见是双女鞋。图中的荷花含苞待放,寓意着少女亭亭玉立的形象;吉祥鸟的绣工极其精细,尤其是羽毛部分,用红、蓝、紫三种色彩搭配绣出鸟的羽毛形态;鞋头中央绣着一朵花瓣颜色各异的五瓣花,鞋头两边点缀着两只对称的蝴蝶,两只鞋的图案整体为内对称造型。刺绣者往往针对物件的形状及大小,采用“适形造型”方法,以确保饱满、对称、均衡等美的要求。[4]25宝应传统刺绣也是围绕这种造型规律将图案与物件融为一体。保存于扬州博物馆的两双绣花鞋,浅蓝色的那一双,鞋身缠绕着含苞待放的荷花,与宝应文化馆藏的荷花绣花鞋不同的是,此鞋的荷花图案较小,颜色较素雅,应该是一位少女的鞋。另一双藏蓝色的,鞋头左右绣有“卍(万)字不断头”的内对称图案,有“吉祥万德之所集”的寓意。从颜色与花纹来看,相较绣荷花的鞋少了几分活泼,但更显得沉稳,鞋主人应是一位中年女性。
门帘边沿的图式有“凤穿牡丹”“鹤鹿同春”“富贵有余”三种;床上帐沿的图式有“凤穿牡丹”“富贵有余”“富贵花开”“富贵成双”“鹭鸶绕莲”“四季平安”“麒麟送子”七种。旧时,卧室内的床靠着墙面放置,床的一侧与两面墙体形成一个长方体式的半开式空间,内部放置便桶,供居住人方便时使用,外面在墙面与床之间搭一门帘遮掩,门帘顶端挂置与门帘同宽的帐沿,在这里,为了区分床上帐沿,暂且称此种装饰绣品为“门帘边沿”。
“凤穿牡丹”图式的刺绣帐沿的正中央都是一支盛开的牡丹造型。牡丹,花姿典雅雍容、端正大方,是吉兆的标志。它富丽庄重的艺术美感,蕴含了吉祥意义,是富贵的象征。围绕帐沿中心的牡丹花是两只凤鸟与之缠绕的牡丹花茎,凤鸟皆为彩色,有的在牡丹花左右两侧面朝面对称呈现,有的一上一下,在静态的画面中呈现出围绕牡丹起舞的动态美感;有的背对背,但头部是互相对望的的姿态。凤被誉为鸟中之王,丹、凤结合,象征着美好、光明和幸福。也正因此寓意的美好,“凤穿牡丹”图式被采用得最为频繁。
门帘边沿与帐沿“富贵有余”的图式都是由牡丹花与两条鱼组成,同“凤穿牡丹”中牡丹的位置相同,都在帐沿正中。两条鱼与两只凤鸟一般头与头相对,但这种图式不同在于,双鱼不再安排在花的左右,而是牡丹的下端。鱼纹图饰源于新石器时期的彩陶纹样,在漫长的四五千年中,于民间广为流传。闻一多先生在《说鱼》中谈到:“在中国的传统图案艺术中,鱼具有生殖繁盛,多子多孙的祝福含义。”[5]66“鱼”与“余”二音相谐,牡丹花的花枝蔓延在整个帐沿的形状,下端的两只鱼在水中游动,因此构成“富贵有余”的吉祥寓意图。
在帐沿为“富贵成双”的图式中,牡丹依旧在画面的正中央,鸳鸯的位置与“富贵有余”中鱼的位置相同。也许是因为鱼与鸳鸯喜居水中,刺绣者故将此放在牡丹花下端,而不是在空中的左右或上下的位置。与“富贵有余”中鱼的头对头所不同的是,鸳鸯身姿一前一后,相互追逐着。两幅绣品中的鸳鸯皆被安排在画面偏右的位置,有着黄金比例①黄金分割是指,将整体一分为二,较大部分与整体部分的比值等于较小部分与较大部分的比值,其比值约为0.618。这个比例被公认为是最能引起美感的比例,因此被称为黄金分割。的构图形式。画面中鸳鸯的神态自然,你侬我侬的神态细节表达得淋漓尽致,鸳鸯象征着婚姻,象征着爱情,鸳鸯成双出现,与牡丹合在一起,构成了“富贵成双”的寓意。
帐沿“富贵花开”图式及以上三种图式皆以牡丹花为主体,“富贵花开”与以上三种绣品图式的不同在于,画面中仅有牡丹花造型,不再利用“凤”“鱼”“鸳鸯”等吉祥物共同装饰,而是只有一支牡丹呈现在帐沿正中,构成“富贵花开”的寓意图。
在“鹭鸶绕莲”的帐沿图式中,两只鹭鸶嬉戏在莲花的花茎间,鹭鸶一左一右,一上一下,整体构图和谐饱满,色彩鲜艳,刺绣者改变了物体的固有色,利用色差较大的蓝白色来烘托出鹭鸶与莲花的造型特征。鹭鸶与莲花皆有纯洁的象征,寓意着造物者对生活美好的希冀。以上帐沿的刺绣图式均是单一的平绣,用色彩的对比突出物象的外形和特征。
帐沿“四季平安”图式中,对图案的绣法采用的是镂空法,瓶子与“平”谐音,有“平安”之意,画面右上方有两只飞舞的蝴蝶,“彩蝶双飞”是婚嫁用品的常选图案。瓶中插满鲜花,又有“蝶恋花、花恋蝶”的寓意效果。瓶中的几枝鲜花并不是具体的哪一种花,更像是刺绣者随心随感绣出的“心中花”的图案。民间美术的创作者们往往强调用“心眼”去感知、洞察、觉悟世界。[1]105
刺绣门帘边沿的“鹤鹿同春”图式,是由一只五彩吉祥鸟、一只梅花鹿和春天里几种种欣欣向荣的植物构成,此件绣品又名“六合同春”,“鹿”与“六”谐音,“鹤”与“合”谐音,“六合”指代天地四方,“六合同春”则有祈盼天下同春之意。在这里,鹤的外形已经与吉祥鸟、凤凰等别的鸟的外形同化,与帐沿“凤穿牡丹”中的凤鸟外形极其相似。
刺绣帐沿“麒麟送子”图式中,画面中心为“麒麟送子图”,左右两侧又有两只对称的凤鸟。麒麟送子,是中国民间祈子的风俗,流行于全国各地,其传说由来已久。晋王嘉《拾遗记》中记载,在孔子诞生之前,有麒麟吐玉书于其家院,此典故成为“麒麟送子”的来源。在民间,人们认为麒麟是仁义之兽,有吉祥之兆。
床上悬挂之物除了帐沿之外,还有求子团头与彩色的飘带,在帐沿上悬挂着“求子莲花”刺绣作品。画面中的花心上坐着一女童,上有莲蓬,下有莲藕,藕是荷花的根,藕断丝连,四边为花瓣,每个花瓣再绣花,上有银扣下有须带,求子的目的十分明显。在扬州邗江一带将此称为团头,是床帐上悬挂之物。其形式有莲花型、莲藕型、石榴如意型和莲花莲蓬型,可视为一种求子绣的装饰挂件的衍生。扬州地区的求子团头共8件,整体外型有葫芦型、莲花型、倒莲花型、莲藕型、燕子型。葫芦藤蔓绵延滋生,象征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闻一多先生说葫芦是“造人的工具”,寓意人类繁衍、子孙昌盛之意。
床帐上悬挂着的绣帐飘带,其图式多为莲荷造型,上有并头莲,下有并头藕,根深叶茂共一家,有“莲荷同根”“并蒂连心”之说。“莲藕”谐音“联偶”,寓意连续不绝,繁荣兴旺,合聚团圆的景象。尹文、许星明在其所编著的《江南民间刺绣》中有:“川叶脉串花,下有莲花者,寓意如意连连;刺绣龙凤图案者,下有莲花,寓意龙凤相连。”[3]17另外还有两种特殊的飘带,一种绣着龙盘旋在屋顶,寓意大吉大利,出门见喜;另一种绣着百吉图,曲直相交模拟绳线编结而成的百吉图像,为“百事吉祥”的象征,整体环绕盘曲连接成形,无头无尾,无终无止,又称盘长。
综上,扬州传统刺绣主要为生活日用品刺绣,其针法单一,几乎全为平绣;利用色彩对比营造物体的造型特点,图式普遍为与其实用性相关的传统吉祥图案,并且重复利用荷花、莲藕主题,偶尔出现有鱼、女童、石榴、百吉图、鸳鸯、鹭鸶、蝴蝶等吉祥物。程式化图式与绘画关系无染。
二、对于艺术欣赏品的依附——当代画绣的绘画性
绘画作品可作绣稿之用,早在宋代中国画绣就已形成一种风气。崇宁年间(1102—1106),宋徽宗在皇家画院设绣画专科,绣工们在宋徽宗的推崇和嘉奖之下,采用名人书画为绣稿,极力追摹画作。绣工们与书画家配合,使绣品达到无施不巧的程度,因此又有“画绣”之称[6]12。孙佩兰在《吴地苏绣》中也提到:“无论从历史上‘摹画’的传统,还是‘绣画同理’来看,绘画作品是可以作为绣稿来源之一的。”[7]57张謇于《雪宧绣谱》中也有记录:“绣于美术连及书画”(《考工记》:“画缋之事。”贾《疏》:“凡绣亦须画乃刺之,故画绣二工共职)[8]143,他认为刺绣这门艺术与绘画密不可分。
乱针绣的创始人杨守玉既擅长传统刺绣的针法技巧,又精熟西洋画的笔触色彩,于是才创造出了有别于传统的针法。她融绣理画理为于一炉,越传统针法之规,将西洋画中的笔触与色彩运用到刺绣作品中,一改传统刺绣“密接其针,排比其线”的方法,以水粉画“小女孩”“老头像”为绣稿创作了一些作品,用特有的线条组织使绣品面目一新,脱颖而出,轰动了当时整个正则女专,得到了艺术家吕凤子的推崇,当即取名“杨绣”①以杨守玉的姓命名。,在杨守玉的一再谦虚推辞下,遂名“乱针绣”或“正则绣”。[9]2乱针绣是借鉴了西洋画的笔触色彩演变而来,所以相应的更擅长表现将油画、摄影和素描等作为底稿的作品。
绣绘相通自古就有记载,以名作为底稿绣制刺绣作品,是刺绣艺人用刺绣工具对绘画作品的“再创作”的过程,并不是单纯地复制。
首先,从刺绣的技艺而言,如何用刺绣技艺将原作还原,可谓是一种再创作。在绣画之前,需要对原作品进行缜密地解读,思考用何种针法能够还原原作,使名作不失真。如何用刺绣的语言同样表现出物体的质感,具体用何种针法,或者哪几种针法交叉使用才能够达到最佳效果,这些都是刺绣艺人进行再创作时,通过实践才能知晓的。艺人们在绣制运针的过程中,第一针的结尾蓄势着第二针的开始,一针与一针完美无瑕的衔接就是一种节奏。运针的节奏造就了刺绣艺术的生命力,它的那种互相牵绊、互相依存的统一性和规律性构成了一种生命的形式。
其次,是在刺绣过程中,对原画不足的地方进行修改调整,也是一种再创作。不是任何一幅绘画作品都可以用刺绣形式表现的。在选择绘画作品时,有特别的讲究:一方面,需要观察绘画作品是否适合用刺绣的语言表达,能否用刺绣的形式将绘画作品表现得接近或者不亚于原作;另一方面,需要考虑到刺绣语言能否通过绘画作品发挥到极致。绘画作品可以用各种绘画材料将色彩、笔触、肌理等表现到位,但使用刺绣材料就需要另当别论,有时需要改变原作中的色彩和笔触,有时有使用刺绣工具也表达得不太完美的地方。
再次,在绣画过程中,如何将丝光效果表达出来,也是一种再创作的过程。利用丝线的反光原理,将刺绣与绘画作品区别开来,最终表现出刺绣的独特语言,使得刺绣作品远观似画,近看胜似绘画。
基于以上几点,从绣制之前的选择绘画作品到绣制过程中的修改调整,都是刺绣艺人将自我的主观情感融汇于已形成经典的名作之中的证明。借用吕品田对民间美术创作中的符号解释,可以这样理解:我们不能单纯地将扬州刺绣名作当作是一种复制行为,它是一种再创作的过程,是在创造主体的内在需要的驱动下,通过有目的的选择和观念的利用,存在于社会化意义系统中,蕴含自我观念情感的另一种物化表现形式。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审美趋向也在日益变化。扬州刺绣便有别于一般传统刺绣图式,将绘画作品以刺绣的形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至于何种题材,则受地域文化、人文情怀的影响。扬州刺绣受扬州八怪文人精神影响较大,而扬州宝应地区的刺绣则更多的受到了常州乱针绣的渲染。为了彰显扬州地方文化特色,在传承传统刺绣的基础上,当代扬州刺绣作品主要以宋元及清代工笔山水、写意花鸟画、扬州八怪的作品以及近现代名家名画为底稿。[10]目前绘制的绣稿主要是吴晓平工作室所用的画册《扬州画派书画集—李鳝》《南宋四家画集》《任伯年精品集》《中国近现代及当代书画》《刘旦宅画集》《袁江袁耀画集》《扬州八怪书画精选》等。在受到扬州地域文化与人文精神的影响下,目前扬州刺绣以“仿古山水秀”和“水墨写意绣”为主,所绣作品灵秀古雅,笔墨神韵俱佳,宛若原作。
扬州的地域分支宝应县境内的刺绣在传统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了常州乱针绣的优势,创造出一种具有创新性的刺绣风格。宝应刺绣善表现写实油画及风景画,题材较广泛,包括人物肖像绣、写实风景绣、名家画绣等,使扬州刺绣更加丰富,更具魅力。
无论是扬州地区的中国画绣还是宝应地区的油画绣,二者皆追求绣画的意境,既表现出画面本身的艺术性,又展现出刺绣本体的工艺性。刺绣作品风格异彩纷呈,在一针一线的工具运用中,将艺人们的创造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使得扬州刺绣作品具备了“不是绘画,胜似绘画”的艺术效果,同时赢得了“针画”的美誉。
扬州刺绣以绘画作品入绣,取材多样,将画理与绣理融为一体,追求绣画意境,集新意与技艺于一身。扬州刺绣在向艺术欣赏品发展的过程中,刺绣工艺对绘画作品产生了一种依附的联系。刺绣者在临摹绘画作品的同时,为了使刺绣在绘画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系统,在工艺方面进行了改革创新,这种创新甚至是一种对刺绣本身针法的再创造。
三、刺绣之于绘画关系的文化向度价值判断
扬州刺绣属于四大名绣之一“苏绣”一脉,经历了服饰绣、宫廷绣、风俗绣到艺术绣的发展过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传承和发展,博采众家,不断创新,完整地保存了乡土手工艺的变迁风貌。当代扬州刺绣以扬州八怪等文人书画为底本进行绣制,包含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反映出时代的风貌和当地民众的审美取向,是苏中地区人群生产生活的一部分,是历史上民间百姓认可、欣赏、喜爱的文化精华,也是乡土艺术的活化石,更是民众审美发展的历史见证。扬州的地域分支宝应地区的刺绣在传统的平绣基础上沿袭了常州乱针绣的技艺,使得宝应刺绣工艺在顺应时代潮流的趋势下,不断融合创新,寻得了独属于宝应的立足之地。因这种工艺手法主要集中在鲁垛地区,故世称“鲁垛乱针绣”。
扬州刺绣从以传统的日用品绣为主旋律,发展到当下以艺术欣赏品绣为主题,每种趋势下刺绣与绘画之间都存在着不同的关系。每一个时期皆有着平民风俗类、贵族宫廷类和艺术欣赏品类等刺绣作品。本文中所谓的某一时期的传统日用品绣或艺术欣赏品绣,并非是草率地将同一时期的其他刺绣种类排除在外,而是形容当时刺绣种类流行的一个大趋势。
向绘画靠拢不仅是刺绣工艺存在的一种特性,也是其他工艺尚有的一种共性。由于刺绣的半立体式趋向于绘画平面的造型,因此相较其他工艺,刺绣倾向绘画的痕迹更显著,其他工艺器物如陶瓷、木雕、牙雕、剪纸等则更倾向于三维立体空间。在器物上作画的手法,只是在原有造型基础上进行适型改变,其本质未变,其本身的表现手法也并未因引画入物产生弱化。刺绣便不同了,由于它的特殊性,导致它成为“胜似绘画”的欣赏陈列品,因此用“仿”“代”等手法来体现刺绣工艺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双面性。当代扬州刺绣在模仿绘画作品的过程中,为达到刺绣作品更接近原作的目的,针法需要不断地变化调整,在这种艺术的“再创作”过程中,针法得到了丰富,绣法技艺也相应地得到了提升。扬州刺绣依附于绘画的光阴岁月中,传统刺绣工艺的原生性已经被逐渐磨灭殆尽,变成一种刺绣工艺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新型刺绣,弱化了扬州刺绣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因素——状态上的原生度、信息上的承载度、时间上的跨越度等。
2014年扬州刺绣作为绣画这一类的艺术欣赏品,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①国务院关于公布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12/03/content_9286.htm。扬州刺绣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绣制绘画作品,至今只有五十多年的时间,远不足百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中有明文规定:时间跨度不足百年者,不能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1]10也就意味着必须有悠久的历史沉淀,才能冠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号,但此时的扬州画绣已经有别于传统刺绣图式,对传统刺绣图式的传承和延续已经所剩无几,其对传统美术的信息承载度也被弱化了许多。扬州画绣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传统的原生性。
当代扬州刺绣与绘画关系密切,失去了传统的“本真性”。以此个案微观视角的探讨,发现其他相关工艺如剪纸、木雕、雕版印刷等也都遭受了同样的境遇,它们在时代的洪流汹涌中退却了传统工艺的色彩,逐渐依附于绘画形式。纵观当今工艺美术现状,在活态传承中原汁原味的成分还剩几分?现如今有多少工艺的“本真性”在逐渐流失后,仍然作为一种次生文化或者新型文化而继续存在,甚至被当作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保护着。在这种情形下,是否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健康发展,传统工艺美术的现代转型是否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相悖,在这里,答案是否定的。
吕品田先生也认为:“全面转向审美方面的中国民间美术,是适应现代文化要求而重建其美学形式的现代形态。”[1]410当社会更倾向于开放的、多元的文化品格时,很多工艺原有的优点往往可能蜕变为致命的弊端。尤其是当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美术意欲适应社会环境而重新发展时,它就无可避免地面临着文化定位转变的问题。这样下去,若在工艺上固守所谓“文化本真性”就显得不合时宜。[12]
基于此,扬州刺绣绣画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虽没有完全传承其本真性,但面对社会的发展,这种改变并不会与保护其本真性相悖。纵观扬州刺绣的发展,它与绘画作品之间存在着一种“波状发展”的规律,存在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活态变化关系。任何一个时期,刺绣与绘画之间都是紧密交织的,但并不是偏指同一时期所有的刺绣作品与绘画之间的关系只存在着这种状态。清末民国时期的传统刺绣便极具独立性,是独立于绘画形式而存在的,它呈现的是一种“分”的大趋势。当代扬州刺绣完全依附于绘画作品,是一种“合”的状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业内人士已经发现这种“合”的状态存有一定的问题,刺绣需要有自身特有的形式语言,不能一味地对绘画作品进行“再创作”。部分刺绣艺人已经意识到创新的重要性,将会逐渐避开绘画作品,去绣制独特的刺绣图式。由此推测未来扬州刺绣与绘画作品之间的关系将会逐渐脱离“合”的模式,走向“分”的状态,扬州刺绣必将在不久的将来独立于绘画作品并得到新的延续。
四、结语
如今社会的发展与从前任何时期相比都显得更加地迅速、开放和多元,传统工艺的变迁在这种大环境下也呈现出灵活性、多样性和可逆性①可逆性是指工艺作为某种文化系统的发展,在不断变迁的过程中,既不封闭,也不单向,而是基于普遍的文化适应性原则,呈现独立与交叉发展的双重特质。的特点。从本质上说,传统工艺的变迁是手艺人们“为了更好地利用他们所能获取的一切有效资源,不断地整合手工技术总成,使工艺作为产品的隐性‘非物质’来适应民间美术的生存[12]15。”扬州传统刺绣功能的变化,导致了市场格局的缩小,正是基于此,促使当代刺绣向着艺术欣赏品的方向发展,从而依附于绘画而存在,这种关系的变迁是社会变革、工艺流变的必然结果。扬州与宝应刺绣的绣师们在传统刺绣工艺的血液上融入了新的针法、新的工艺,带来了创新的活力。同时不断地对工艺进行自我调整和优化,改善了其生存发展的形势,构建了有益于自身的生存环境,延续了扬州刺绣的生命力。正如其他传统手工艺一样,扬州刺绣一直处于发展之中,并且处于某种不断“活化传统”的状态,这既是农耕时代手工艺在21世纪得以延续的必由之路,也是传统乡土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球化之际得以华丽转身的文化自觉。
此个案代表了农耕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工艺美术行业诸多品类共同的发展轨迹。
1.当代扬州刺绣向绘画靠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首先,扬州刺绣的传统功能性在逐年弱化,与此同时,社会又不断催生出新的需求,伴随着现代文化的高度渗透,三者之间矛盾愈加白热化。20世纪社会变革,直接引发了刺绣传统民俗功能的衰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社会审美的演化,使得刺绣走向艺术欣赏品的道路。其次,刺绣从业者身份的转变,即从以生活刺绣为目的的全女性技术业余化,向商业生产性欣赏的技术职业谋生化方向演进。20世纪50年代,由于我国发展大工业的需要,传统工艺被作为原始资本积累。[13]1261959年扬州绣品厂的建立彰显了地方文化特色,在传统刺绣的基础上,刺绣作品主要以古代山水画、花鸟画以及扬州八怪作品为底稿。再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提出,给予了扬州刺绣模仿绘画满血复活的机会。2003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走上全面、整体的保护阶段。[14]3自20世纪50年代末,扬州开始绣制绘画作品,至今仅数十年,远不足遗产所必须的百年历史,[11]10值得强调的一点是,2014年扬州刺绣是作为绣画的艺术欣赏品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类扩展名目,②国务院关于公布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12/03/content_9286.htm也就是说刺绣绣画造就了扬州刺绣当代的地位及荣耀。
2.当代刺绣依附于绘画,实质是一种工艺的异化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仿”是低级者对高级者的一种模拟或敬意,绝少有高级者向低级者模仿。工艺美术对于绘画的“仿”十分常见,而绘画却鲜有“仿”工艺者。仿制方式有四:一是图式简单抄袭,即忽视“仿”过程的再创造,而仅仅为了达到视觉上的相似度,在文化价值上通常不如原作;二是部分仿制,即在图式或者技术上参考原品,但有进行某些方面的技术改进,与原品有明显差异;三是浅表仿制,深度再创造,即在对原品全然消化的基础上,注入新的原创性理念,使得仿制品转化为另一种超越原品的新产品;四是挪用式仿制,即刻意地将对象元素在新作品中进行错位,经加工而生成具有独立意义的作品。扬州刺绣绣画便是属于对绘画的再创造形式。
3.当代扬州刺绣依附于绘画并彰显其绘画性,这一点在模仿绘画的过程中有利也有弊
在整个流程中,原初图像中最为珍贵的创造性被最大程度地淡化了,再创作过程中形成的工艺技术,同时篡改了艺术本体所稀缺的独立性,使得技术和艺术在模仿的过程中变得交织错乱。并且刻意地追求细致化的技术探索,使得手工技艺的原生美出现异化的现象,亦促使技艺本身变得更加脆弱化和小众化。这种从自身独立逐渐转化为依附于绘画的文化向度,一旦被纳入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针对“本真性”命题也将引出更多值得探讨的新问题。各种工艺美术在顺应时代洪流的同时,与绘画之间所体现出的独立与依附的分合关系该如何处理?尤其是在申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的势头上,如何权衡文化“本真性”变更的利弊关系,需要民间美术保护工作者加以斟酌,为其健康良性的发展作出正确的文化判断。
扬州刺绣与绘画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独立亦或是依附,都仍需创造力来稳固,艺术创造才是保持扬州刺绣未来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扬州刺绣本是工艺性在先,装饰性在后,现今将视觉享受作为目的,变成装饰性在先,工艺为其次,工艺越来越向美化的方向靠近,但传统工艺不能成为纯欣赏的东西。当代扬州刺绣在依附绘画之后,缺乏创造性这一问题迟早会使它枯竭殆尽。柳宗悦在《工艺文化》中一再强调,美术是看的,工艺是用的,美术抛离了生活,单纯谈美的意义就不大了。[15]3美术的苏醒便是向工艺性靠拢,只有深入群众,美的价值才能找到归宿。唯有在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中融入工艺需求,扬州刺绣才能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