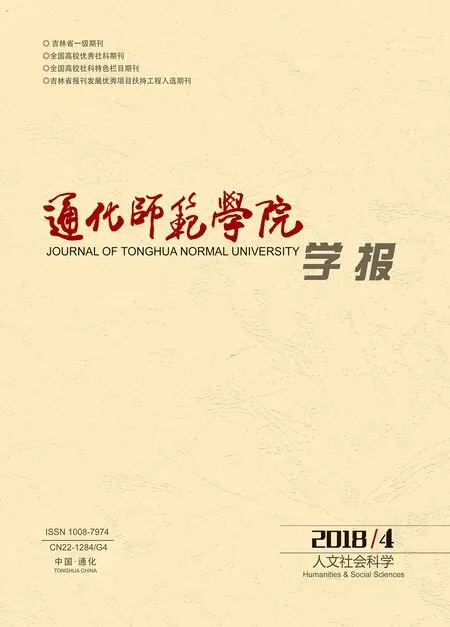论满族说部传承人文化特质
邵丽坤
满族说部基本是泱泱大篇的文本,尤其最初凭借口耳相传的方式在族众中流传,所以需要传承人具备一些与讲述普通民间故事不同的能力特质,以保证其得以传承下来。经过比较分析,满族说部传承人具备的能力大体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惊人的记忆力及较强的讲述能力
具备超常的记忆力也是民间故事传承人普遍具有的一项能力。以《满族三老人故事集》中提及的几位故事讲述人为例,李马氏七十年前听过的戏,佟凤乙十三岁时候听过的萨满跳神歌,李成明五十年前听过的抗日义勇军歌,至今都能一字不漏地演唱下来,可见三位故事家超常的记忆能力。与满族说部相比,民间故事一般都篇幅短小、精炼,但是对说部的传承人来说,传讲大部头的著作更需要良好的记忆力。通过满族说部几个有代表性的传承人田野考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马亚川(1928—2002),黑龙江省双城市人,原属马富费氏满族镶黄旗,祖籍辽宁省岫岩县,小学文化,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他在本村当过文书;土改减租减息中干过武工队员;在韩甸区政府任过基层干部;当过公安及供销社的公会主席。马亚川主要以传承几个系列的女真故事为主,即:族源的神话传说、萨满神话传说、金始祖阿骨打征辽传奇及清代帝王传说。其中,满族说部故事主要有《女真谱评》《女真传奇》《阿骨打的传说》《女真萨满神话》等。尤其是《女真谱评》,从九天女与函普经过一段神奇的经历结为夫妻,被完颜族人尊为始祖起,历述了德帝乌鲁、世祖劾里钵以及太祖阿骨打各个时期的传说。而且,《女真谱评》实际上不仅仅包括整个完颜部各个时期的历史传说及故事,还包括了后金及清初的历史。这是因为清太宗皇太极于天聪九年在给父亲努尔哈赤修《太祖武皇帝实录》时候,下旨禁本族称诸申(即女真),只可以称满洲,把女真族改为满族。但是在金源故地不少满族人仍称女真,所以《女真谱评》的内容实际上包括女真起源、完颜崛起、大金兴亡、后金风云、清朝盛衰等整个发展史。
在史籍中,关于这些人物的记载仅寥寥数言,而《女真谱评》却以完整故事的形式,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完颜部发展的历史画卷,堪称女真族的无韵史诗。已经出版的《女真谱评》,分为上、下两册,可谓篇幅宏大,远远不是普通的民间故事所能及的,所以需要传承人首先具有较强的记忆力。满族说部故事《女真谱评》的重要传承人马亚川先生,传承《女真谱评》的故事,起因于曾经得到过外祖父赵焕的一个手抄本,当初是清末由本屯的一个秀才傅延华用墨笔缮写在黄表纸上。马亚川幼年时候读过这个珍本,所以一直记得里面的诸多细节,还有一些可被确认为早经消失了的古女真语词的记录。不仅能记得多年前的词汇及故事,马亚川时隔三十年,还能流利地讲出当年在职工大会发言的内容,而且分毫不差。
对于其令人叹服的博闻强记的能力,马名超先生曾经对其做过测试。比如两人在交谈时候正在说女真旧话或帝王传说,在兴头的时候,可是马名超先生故意让他讲段“瞎话儿”,如果不是肚囊宽的故事家,非得“打奔儿”不可。马亚川却毫不迟疑地讲了一则环扣紧密的民间故事《教的曲子唱不得》,还把傻子学话中出现的一连串“包袱”,甩得利利落落、酣酣畅畅,连半个崩挂掉字的漏洞都抠不出来。[1]如果讲述者没有超强的记忆力和对故事的谙熟,是无论如何达不到脱口而出的。
满族说部传承人傅英仁先生、穆晔骏先生都具有博闻强记的能力,使得说部故事在他们这一代较为顺利地得以传承。
满族说部植根于满族“讲古”的沃土,而且“讲古”的习俗可以追溯到金代,依靠传讲口口相传的故事,传讲人不但是“讲古”的创作者,也是口碑文学的传承人。尤其在女真没有文字时期,只能用口耳相传或者刻木为号的方式记录历史。也在这样的方式中,练就了一批博闻强记的人。史书记载,女真贵族阿离合懑:“为人聪敏辨给,凡一闻见,终身不忘。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属时事并能默记……见人旧未尝识,闻其父祖名,即能道其部族世次所出。或积年旧事,偶因他及之,人或遗忘,辄一一辨析言之,有质疑者皆释其意义。世祖尝称其强记,人不可及也。”[2]1684通过这条史料,可以判断,阿离合懑就是讲述各部族故事的优秀传承人,具有超群的记忆力,而且也具备极佳的讲述能力,令人叹服。
对于民间故事而言,很多情况下,大量的民间故事就掌握在这些“见识多,说话巧的讲手的个人手里,这些讲手就是民间故事讲述家,在学术上又称为民间故事传承人。他们从前人口中听来大量故事,过目不忘,不断积累、贮存,又不断在群众中传遍、发挥、创作。他们在村落里从来就不是无名氏,恰是被群众用俗语授以各种称号的故事家……”[3]3
满族说部传承人很多也是讲故事的能手,被周围的人们倍加推崇,受到大家喜爱。傅英仁先生的三爷傅永利(1868—1940),黑龙江宁古塔人,满族名字叫色隆阿,终年72岁,也是位满族说部故事的传承人。傅永利从小就不识字,但是会很多技能,比如编织、木工、泥瓦匠、看风水、厨师、说书等,样样都精通。他不但记忆力强、口才好,而且天文地理、风土人情、历史传说、萨满故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每到闲暇的时候,就四处听故事,四处讲故事。大家听他讲的故事都有云山雾罩般的感觉,又因其在家中排行老三,所以大家称他为“傅三云”。他每次讲起故事来,都口若悬河,娓娓动听,又通俗流畅,有时候甚至达到大家追着他到处听故事的情景。傅英利经常讲的满族说部故事是《老将军八十一件事》《红罗女》《东海窝集传》等,当地的民众十分爱听。
傅英仁的祖母傅梅氏是“梅何乐哈拉”说部的传承人,也是一位众人知晓的讲故事能手。年轻时嫁给傅英仁的祖父后,就把家传的说部带到傅家。梅何乐是蛇的意思,原住在镜泊湖,他们都崇信蛇,所以这个家族始终祭祀蛇神。受祖辈的影响,傅梅氏爱讲故事,一讲起来就没完没了,而且几天都不会重复,是宁安西半城有名的“故事妈妈”。她讲的故事如同行云流水一般,悦耳动听,让人越听越着迷,有时候听众连吃饭都顾不上。
这种惊人的记忆力及讲述能力,在锡伯族故事家何钧佑①何钧佑:(1924—2012),锡伯族人。祖籍是吉林省扶余县人,后定居在沈阳市于洪区马三家街道东甸子村。身上,有同样的体现。何钧佑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父亲及祖父都在盛京的得胜营做过官,讲古论今是锡伯族固有的传统,家族人也都喜欢听故事、讲故事。何钧佑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从小就爱听故事、爱讲故事,尤其是与鲜卑族有关的历史故事。据何钧佑回忆,“孩提时代,祖父很疼爱他这个孙子,白天在盛京衙门当差,晚上茶余饭后,常常把何钧佑抱在膝上,给他讲鲜卑祖先的故事,仅一部《喜利妈妈西征传奇》,祖父就断断续续讲了一年之久。在祖父讲故事的时代,锡伯族已经开始使用汉语,祖父讲起鲜卑祖先的故事时是两种语言并用,且讲唱结合。讲的部分混杂着使用汉语与锡伯语,交代故事情节进展;唱的部分仍然沿袭使用鲜卑语,用以抒发感情。令何钧佑遗憾的是,自己年幼时往往痴迷故事情节的进展,对祖父讲述中唱的内容既听不懂,也不感兴趣,常常催促祖父尽快往下讲,以致这些作品中用锡伯语演唱的内容都没有承继下来。而这些古老的‘郭尔敏朱伯’②郭尔敏朱伯:郭尔敏,系指长长的意思,朱伯:系指故事。传承到何钧佑父亲这一代时,便已基本上全部使用汉语讲述了,且不再有演唱的形式,但故事中仍保存有大量的锡伯族词语。何钧佑基本上因袭了父亲的讲述风格,因而这些散发着浓郁的北方民族特色与渔猎生计特色的锡伯族词语得以保存下来。”[4]何钧佑先生靠着惊人的记忆力和讲述能力传承下了《喜利妈妈西征英雄传奇》《黄柯氏神医传奇》《勃合大神传奇》《海尔堪大神传奇》《石刀石锥历险记》《吾初勒西漫游记》《擅石槐统一鲜卑》7部锡伯族长篇故事的采录整理;出版发行了《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上、下)。[5]“何钧佑锡伯族民间故事以锡伯族部落时代的生产、生活活动和英雄传奇为题材,故事内容丰富,既有展现锡伯族英雄人物的传奇故事,又有歌颂爱情的神话故事,还有反映锡伯族风土人情的千姿百态的故事。何钧佑锡伯族民间故事与我国其他地区流行的锡伯族民间故事有很大不同。我国新疆等地流传的锡伯族民间故事多以短篇叙事为主,幻想色彩较强,而何钧佑锡伯族民间故事则带有明显的‘史诗性质’。如《喜利妈妈传奇》《黄柯与神袋子》《慈势得本救母》等,在叙事中贯穿了锡伯族的民族发展历史,折射出锡伯族部落时代的生存状态、生活环境、精神信仰、日常生产和生活习俗等。”[6]
二、较强的创作能力
除了具有博闻强记的能力,讲述创作能力是说部传承人需要具备的另一个特质。同样的一个故事,不同的讲述者会形成不同的风格。实际上,原封不动的传承是不可能存在的。讲述能力也是传承人再创作能力的体现,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例如上述提到的《满族三老人故事集》中的三位民间故事讲述者,他们“不满足于单一地把他们从前辈那里继承下来的艺术财富转述出来,而是经过自己的融会贯通,加工润色,使得原来的故事更加完美。同时又将自己广泛的阅历、切身的遭遇,渗透进去,使得故事增加了更丰富的内容,更强烈的感情色彩,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7]
创作能力,主要是指在故事结构大体不变的情况下,有的追求细节,比如对一个具体的物件,每个故事家都会有不同的描绘;有的体现在对情节的渲染上,来追求讲述故事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创作能力在满族说部传承人身上体现得也较为普遍和明显。也许有人会说,对于满族说部如此宏大的篇幅,有的甚至达到百万字,难道都是传承下来的吗?满族说部与民间故事的区别不就是讲究“原汁原味”,少加改动吗?对于这个问题,满族说部国家级传承人赵东升①依据文化部2017年12月28日公布的“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单,赵东升名列其中。给予了较好的回答:“满族说部,有的故事传承数代,最多有十代之久历经数百年,应该承认,每传一代,就会有一次改动,文盲型的越传越少,因为他记住多少传讲多少,有的传了几代就传没了。而知识型的会越来越多,因为他还有个加工升华的过程,能把简单的故事情节系统化、形象化,并且记录成文本、加工创造,这也是保证说部长久流传的一个有效手段。所谓的原汁原味,那就是在传承、加工、发展过程中,原来的故事情节不变、人物属性不变、语言风格不变,地域特色不变和宗旨不变,再一个就是族内传承方式不变,因为有些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只能在族内传承,外人是不知道的。”[8]事实上,人世间所有的一切都不能一成不变的传承,这样的理解也是片面的。所以,较大篇幅的满族说部在知识型传承人手里,经过加工和升华,越传越多,这是传承人创作能力的一个体现。赵东升先生的家族是乌拉纳喇氏,也是明末清初“扈伦四部”之一的乌拉部的后裔,为乌拉国王布占泰第十一代孙。清入关前,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诸部,乌拉国灭亡,家族的人也各处逃散,隐姓埋名避居于乡下,在生活较为艰难的情况下,却传下了大量的与本家族相关的轶闻故事,当时称为“乌勒本”,后来经过历代的传承,演变为说部故事。到了赵东升先生这一代,他利用业余时间整理满族说部,而且多方寻找扈伦四部的后裔,并亲自考察其历史遗迹。按照先人提供的线索,足迹不但遍布东北三省的相关各市县,还踏访了北京、河北、甘肃等地,访谈一些知情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为丰富、补充其家传的说部故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赵东升家传的说部《碧血龙江传》中,有不少歌谣。《碧血龙江传》是赵东升的祖父崇禄先生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自编自讲的说部故事。崇禄的经历带有传奇色彩,一生见多识广,多才多艺,不但精通满汉文字,对俄语、日语、朝语等懂得一些。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北京,沙俄出兵18万人,占领了东三省。这种情况下,盛京、吉林不占而降。黑龙江则在寿山将军的主持下,瑷珲副都统凤翔首当其冲,最后抗战失败,二人均殉难,但是他们的民族气节与不畏强暴的精神却鼓舞了后代人。当时,崇禄先生就在瑷珲前线凤翔的军中,他不但目睹了整个事件的过程,还搜集到了一些军中的轶闻故事,后来撰写成为《碧血龙江传》,四处传讲。赵东升先生将其整理成满族说部故事出版,在讲述的开篇就是当年流行在黑龙江清军中的一支歌曲,它来源于瑷珲地区的民间歌谣:
瑷珲的山岭啊,布满了硝烟;
黑龙江的水哟,碧波流丹。
哪里有啊,我们的父母;
何处是啊,我们的家园。
俄罗斯匪徒啊,杀人又放火;
大清国的黎民啊,生灵涂炭。
何年何月啊,赶跑那敌寇;
哪朝哪代啊,收复我河山![9]1
笔者就其中插写的歌谣,访谈过赵东升先生,他说他专程去当地采录过,收获不少。有的歌谣不太完整,赵东升先生本人根据歌曲或歌谣的风格和特点又合理地进行了补充,加入到说部中,起到良好的作用。此外,赵先生还谈及,《碧血龙江传》的开篇本来没有这首歌谣,在一个学者的提醒下,他后加上去的。因为开篇就进入正文显得有些突兀,加入当地流行过的歌谣,就让读者有了不一样的感受。②笔者根据在赵东升先生家中的访谈录音整理而成。因为歌谣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由此引出一段悲壮的历史。
另一位比较著名的满族说部传承人穆晔骏先生,也是著名的满语研究专家,其先祖为恰喀拉人。恰喀拉人世居锡霍特山,是东海女真的一支。穆晔骏先生是恰喀拉最大氏族之一穆尔察氏族的直系后裔。他承袭了恰喀拉人的血统和文化基因,比较熟悉恰喀拉人的生活及习俗,其传承的满族说部《恰喀拉人的故事》,不但反映了恰喀拉人生活和历史,而且穆晔骏也把自己积累的深厚的文化知识,融入到说部中,使得说部既有趣味性又有知识性。不仅仅是故事的简单复述,这其中包括了传承人创作的过程。
三、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
普通民间故事的讲述者与传承人,大多是地处偏远地区的农村老太和农村老汉,其生活的环境较为封闭,基本没受过教育,识字的人寥寥无几,而且大多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也恰恰是这样的环境,得以保存了相当一部分民间故事。与讲述普通民间故事的传承人不同,满族说部在传承的过程中,文化精英在其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他们不但使得说部得到丰富与发展,也为其更广泛的流传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满族说部传承人具备较高的的文化素养,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富育光先生曾对此现象作出过解释:“满族长篇传统说部虽为数十万甚或近百万言泱泱巨篇,绝非文化愚氓者所能为。它集多种条件和因素而凝生,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事实如此,考满族说部的创始者,虽有荷马史诗型人士,更有满汉齐通的大家、朝廷的学士、编修、将军。他们博古通今,甚或通达阿尔泰语系诸民族语言、风俗,本身都是才智多能者。使满族说部独具一格,具有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学科价值,令各方人士百听不厌,爱不释手。满族诸姓望族还不惜银两,延请国学和汉学名师,意在满族说部的延续和传承。民国已降,满族有些姓氏家藏说部失传或传留日少,亦因痛缺文化人士。”[10]近世以来,满族说部的传承人如刘显之、傅英仁、关墨卿、马亚川、富希陆等诸位满族人士,都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而且其中几位还满汉齐通。此外,时至今日,居住在黑龙江省孙吴县四季屯的何世环老人,时至今日还会用满语讲唱《尼山萨满》,她的父亲就是一位满汉齐通的人物,曾做过瑷珲下马场村的小学校长,何世环跟随父亲学习过满汉文,再加上幼时成长的环境,周围讲满语的人较多,所以迄今为止还记得较多的满语,吸引许多研究者去访问、采录。可见,满族说部传承人大多是具备较高文化知识的文化传承人和民族知情人,也正因此,满族说部能较好地保留并传承下来,时至今日还能大放异彩。这一点,在当代传承人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满族说部传承人大多具有知识型传承人的特质,之所以强调这一点,这也是与普通民间故事传承人的最主要区别。
赵东升先生曾跟笔者讲过,家族的历史不仅仅在他们这一支传讲,也在别的支系传讲,但是能不能传下去,跟传承人的文化水平还是有关的。在文化高的族人中传承,就能越传越丰富、完整,在文化低的族人中传承,可能无法传承下去,家族故事就传没了。赵东升先生除了继承祖上传承下来的中医医术,他从小就对本族的历史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从少年时期就一直关注家族的历史。经过业余时间的刻苦钻研,赵东升先生后来成为比较有名的地方史专家。欣逢盛世,赵先生把家族的历史整理成说部故事,业已出版了《乌拉秘史》《扈伦传奇》和《碧血龙江传》。通过笔者与赵先生的接触,他一直强调,说部讲述家族史的真实性,绝对不是虚构的,要确有其事。就连其中佐证一些历史事件的材料也不是空穴来风,一定要审慎地处理和引用。赵先生曾提供给笔者一份《碧血龙江传》中引用的史料汇编,正如他在关于《碧血龙江传》主要史料选辑说明写的那样,“《碧血龙江传》是说部故事,不是历史课本,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知情者和当事人以其亲见亲闻,自编自讲的历史传说故事,其中免不了虚实相间,真假融汇,褒贬失当之处。但总体来讲,还是原有所本,历史事件、人物活动,还是真实的。讲述者并没有采用官方公布的史料去改变自己的观点,而是以自己对所经历的事件的认知,以愤慨和惋惜的心情控诉列强,特别是沙皇俄国的暴行,以及对舍身报国的满汉八旗优秀儿女的颂扬,主旋律是积极向上的……该故事反映了自己对历史事件的认识。为了配合阅读《碧血龙江传》所展示的历史事件,便于缕清庚子事件的来龙去脉,在浩如烟海的中外史料文献中,我们选编了部分当时中外公开发表的著述,作为研究《碧血龙江传》所反映的历史事实参考之用,也将会对庚子事变的历史的了解有所裨益。”①赵东升先生提供的《关于〈碧血龙江传〉主要史料选辑说明》(未刊稿)。史料选辑共分为三部分,即中国史料、外国史料和中外专著。仔细研读赵先生整理的选辑目录,的确可以看出,作为家族历史传承人兼整理者及研究者的多重身份,赵东升在说部中引用的文献都是经过细心的筛选和斟酌,审慎引用的。这需要整理者的判断力与深厚的功底。在说部中,有一段关于慈禧西逃,途经怀来县,怀来县令不但要做好接驾的准备,还要筹办皇室和随行军兵们的生活供给。县令为其准备一份膳食谱单,盖有延庆州的大印。此处的谱单,是整理者引用日本吉田良太郎《西巡回鸾始末记》中的一段史料,文献来源不但可靠,而且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一个行将没落的帝国的执政者,最后的奢靡生活。
这仅仅是整理者引用文献的一个侧面,但是可以看出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与知识底蕴,对传承说部的重要性,这是普通的民间故事讲述者不具备的能力。也恰恰是这些较高文化素质的传承人,能将满族说部充实、完整地一代代传承下去。
不仅仅是赵东升先生,富育光先生作为“满族说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备受关注。因其学者及研究者等多重身份,富育光先生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时候,不是十分顺畅。他说:“我不敢苟同将学者与民族文化传承人对立或分开的观点,纵观古今中外、古往今来,这种类型的例证不胜枚举。学者或艺术家与民族文化继承人和传承人双层职能合二为一者,往往是一个民族或集群在一定社会的特殊环境和条件下形成的,是社会发展中很必然很普遍的现象,何足为奇。原胎文化由原胎民族后裔的文化人士参与抢救与承袭,更易守其纯真性。这种现象,恰说明文化承袭事业的普及和深化,乃民族文化之幸事。”[11]锡伯族长篇故事讲述家何钧佑先生也是一位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传承人,他曾留学过日本,在苏联也工作过,还曾阅读了大量的关于东北史的文献和一些资料,以及神话传说故事,此外还学过绘画。在已出版的何钧佑讲述的锡伯族故事《喜利妈妈西征英雄传奇》中,就经常地带有插图,这些插图都是何钧佑老人自己亲自绘画的,图文并茂的形式更能传达讲述者要表达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