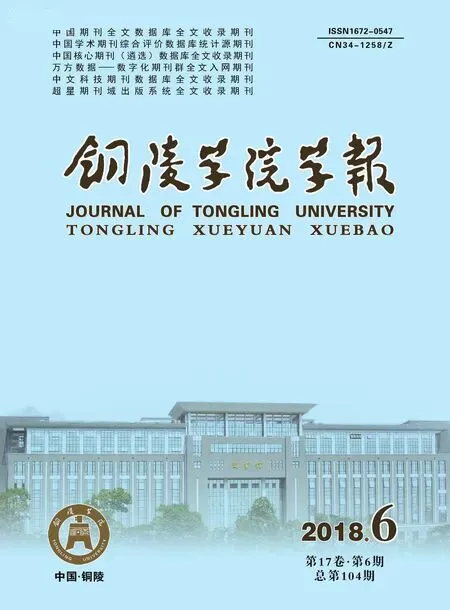教育人种志:徽州本土音乐课程建设的方法论意义
史一丰 田雅丽
(1.黄山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2.安徽大学,安徽 合肥 230601)
当人类学研究的视野寻遍非西方小规模社会之时,人类学研究的思维开始发生转向。对已有西方小规模社会研究的反思成为当下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尤其是在多元文化交织的今天,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观照已经涉及文学、经济、医学、教育、艺术等多门学科。当人类学与这些学科交缘后,拓宽了这些学科已有的研究视阈,并将阐释人类文化各个方面作为贯穿研究的主要线索。以教育人类学为例,原本研究教育教学规律和现象的教育学研究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引下,研究的触角逐步深入教育教学现象的背后,阐释教育的文化背景,强调用教育教学的手段对人类文化进行“深描”。研究方法也从先前单一的理论研究转变为以田野调查为主要手段的实证型研究。作为教育人类学研究的实证型研究,人类学将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与整体分析的方法带入了教育学研究,并以文本书写的方式予以呈现,这种被誉称教育人种志的方法为本土课程的建设提供资料积累、研究者文化体验和整体地方文化分析等手段。因而,在地域文化浓厚的徽州地区建设本土音乐课程需要体现教育人种志的方法论意义。
一、人种志与教育人种志
人种志也称民族志,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追溯其源头,现有记载是由狄阿斯 (D·Dias)认为该词最初由坎普尔(Camp)于1807年提出,其基本含义是对民族的记录和描述(Description),即人类学家将自己作为研究工具,深入某一原始民族或异域文化,经过长期的资料收集过程,最后完成对该民族或文化的详尽描述。[1]人种志方法研究既有个案研究的模式,又不失对整体文化的把握。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使其实施的主要方式。人种志方法研究是对研究对象的微观考察,获得的是对研究对象整体性文化的系统阐述,因而,人种志方法研究又被认为是“关于特定社会或社会群体的有意义的行为之详尽描述,或产生这种描述的方法论系统”。[2]人种志方法被沿用200余年来,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法宝。随着人类学研究的不断演进,出现了诸多例如艺术人类学、教育人类学、饮食人类学等文化人类学分支研究,人种志(民族志)研究同样是此类研究不可或缺的获取一手资料的手段,是实证研究的核心方法。
教育人种志是教育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是人种志在教育教学研究领域内的运用。自教育教学研究涉及文化研究伊始,教育人种志逐渐成为研究的工具。它既是衡量教育人类学家研究水准的砝码,也是教育人类学及教育人类学家成长的必经之路。[3]人类文化的形成和行为习得离不开教育,通过教育的方式对人类思想和行为上进行洗礼,是人类文化形成的一个方面,也是体现地域文化特征和不同国家、地区人类文明的手段。教育人种志对跨文化的教育研究和异域文化研究,且在倡导实证研究上是其特征和精髓。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提出的“地方性知识”理论是地域文化总的精神实质的囊括,也是体现地域文化方方面面的一个体系。在现代文明浪潮中,“地方性知识”本质的保持需要依靠教育的传承功能来实现其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因此,建构教育人类学的体系,做好人类文化传承与教育教学内在研究,是当前教育传承地方文化的重要方面。也就是说,注重从田野研究的立场出发,以人种志方法为标志,深入学校之中开展研究,形成独特的教育研究成果。[4]因而,通过教育人类学研究,用教育人种志方法深入徽州本土文化开展从宏观到微观的研究,汲取徽州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音乐文化的优质土壤,做好本土音乐课程体系建设,是体现教育人类学学科特征和教育传承徽州音乐文化的特点,且在教育教学体系内做好不同音乐文化的对比研究和整体性研究,同样需要教育人种志方法的指引。
二、徽州本土音乐课程建设的方法论诉求
本土音乐课程又称地方性音乐课程,即将当地具有代表性的民间音乐以课程建设、教材编撰、专业教师培养以及相配套的教学辅助活动、兴趣小组活动等的一个教育教学体系。这其中的教学辅助活动可以将民间艺人请入课堂言传身教;可以将专业教师拜民间艺人为师,在“田野”中接受民间艺人的口传心授式的传承;也可以将上述两者相结合,制定专业教师的本土音乐课程教学的进修制度等。兴趣小组活动可以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由教师带队、组长负责,利用周末的时间深入田野,感受民间音乐的乡土性,感知民间音乐从本体到内涵的独特艺术魅力,这一活动中小学生实施时间不宜过长。而高校专业学生可以利用假期一段时间或者通过“三下乡”的形式予以开展。总体目的是让学生在课堂内外以不同的教和学的方式从音乐本体到音乐内涵认知民间音乐,从外在到内涵感受民间音乐的地域气息。作用在于从形而上的角度来看,在年轻一代思想上树立对民间音乐的尊重感和对本土音乐文化认知的自发性;从实际行动来看,可以使民间音乐的保护、传播和传承的工作从年轻一代抓起,从教育的途径来实践对民间音乐保护工作,且做到深入人心,最终实现对本土音乐文化的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世上没有适合一切文化的教育,教育必须满足所属文化的需求。[5]传承,是教育最基本的文化功能。[6]因而,在地域文化浓厚的徽州地区通过建设徽州本土音乐课程,处理好文化与教育的关系,实践教育传承文化的功能,是非遗之后以徽州民歌为代表的徽州民间音乐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途径。
实现本土音乐课程建设的体系的架构,需要采攫本土音乐元素,因而,本土音乐课程建设是一项既涉及教育学理论研究又与文化人类学、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相关的教育教学改革工程。教育学理论研究可以从宏观上对本土音乐课程建设进行教育教学视阈内理论指导和理论规范,文化人类学和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研究是本土音乐课程内容的主要来源和目的指向。所以,在教育教学理论框架内,以实证研究为依据,是建设本土音乐课程的基本思路。其中,实证研究是人类学及其各分支学科研究的主要方法,教育人类学研究的实证研究离不开教育人种志方法的运用。本土音乐课程建设和实施一直以来以传承人类乡土文化为目标,故而始终置于接受教育人类学研究的视野。参与艺人的传承全过程的观察、对艺人的深度访谈;比较不同本土音乐种类间传承的方式的异同点和其它地区相同音乐种类的关系;探寻现有传承路径的优缺点;思考当下文化背景下教育传承文化的新模式等都是需要依靠教育人种志的具体方法来得以实现。以徽州本土音乐课程建设为例,课程建设的主导者需要带领相关团队深入徽州的田野,与民间艺人同吃住,参与他们的生活和音乐传承活动中,以异文化身份从局内、局外两个角度和所持文化的远近距离不同来看待艺人的传承活动和徽州民间音乐的本体与现状,并且将所见、所得撰写人种志(民族志)报告,作为徽州本土音乐课程建设的核心内容。同时,课程建设团队还需要爬梳、整理、归类已有徽州民间音乐的原始材料和相关教育教学的理论资料,为徽州本土音乐课程建设作理论铺垫。另外,邀请民间艺人进入课堂,合理设计学校音乐课堂传承徽州本土音乐的课程及教学步骤是教育人种志教学个案研究的方法,不论是教育教学理论的梳理和运用,还是徽州本土音乐多种类的搜集、整理和文本撰写,以及本土音乐课程教学个案研究,因而,教育人种志(民族志)方法能满足本土音乐课程建设在方法论上的诉求。
三、徽州本土音乐课程建设中教育人种志研究的实践反思
斯平德勒认为,教育人种志的研究特点注定了只能实行个案或有限场合作必要研究。[7]而教育人种志对研究者来说,教育人种志研究的关键是在理论积累的基础上,养成对研究对象的敏感性,形成透视特定现象的敏锐意识,而不是简单迎合田野调查的外在形式。[8]所以开展教育人种志研究,对所要研究对象已有研究成果及相关文献的梳理是研究的理论基础,这一基础的构筑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时间研究的积累;在这基础之上,还需要对进行教育人种志研究的参与者对研究对象的选择要带有“职业敏感性”,并在田野调查研究上注重展开的广度和深度。同时,还需要放弃自我,参与被研究者的行为之中,近距离的感知被研究对象的文化经验。教育人种志方法遵循这样一条主要原则:研究者应将先入为见、“自我文化”的衡量标准、模式、图式、类型等搁置在一边,在“离我远去”的状态下,从日常生活的普遍功能视角来考虑课堂教学行为。[9]这一原则对徽州本土音乐课程建设来说,需要重点考虑课程建设的初衷,强调课程建设在文化传承和地方社会发展上的积极意义。即对徽州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作用,以及徽州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通过对歙县新安学校《徽州民歌教唱课》和黄山学院音乐学专业《徽州民间音乐采风》课程的观摩,我们可以发现,基础教育阶段的徽州本土音乐课程建设注重识记和学生的积极参与,高校的此类课程更注重理论层面的教学和少量的实践;新安学校的《徽州民歌教唱课》开设的目的在于让在校的小学生重拾歙县方言,并从音乐的角度来感知徽州传统文化;黄山学院《徽州民间音乐采风》课程需要达到从理论到实践的认知与理解。虽然两者参与对象年龄和学历层面不同,但是在促进徽州文化传承的意义上具有一致性。其次,前者的优势在于传承人亲自教学。学生面对的是原汁原味的徽州民间音乐,而黄山学院《徽州民间音乐采风》课程宏观理论性较强,教师多从民族音乐学通论上来指导学生如何进行徽州田野的工作,并获得自己所要的学习和研究目的。总体上间接知识较多,直接经验较少。两者共同的缺陷在于多以局外人身份进行体验的交流;课程内容较为单一;田野调查学生参与度不高;对研究对象的考察程度不够深入等。从教育人种志研究的归属和特征来看,它本身就是教育教学研究领域内新的研究范式。它(新的研究范式)注重整体和定性的信息以及理解的方法,否认研究过程中的价值中立而倡导价值互动关系,主张通过全面整体的理解,把握蕴含于教育现象种的深刻意义和价值。[10]所以,我们在谈论教育人种志对徽州本土音乐课程建设的方法论意义的时候,需要把握教育人种志特征到意义的指导。把握徽州传统文化的整体观,摆好研究中不同文化身份间互为主体性地位,处理好主客位间不同研究视角的切换,以及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对本文化远近经验的感知,努力做好徽州本土音乐课程体系建设的全面性、客观性,能充分体现徽州地域文化特色,发挥好学校教育传承地方文化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