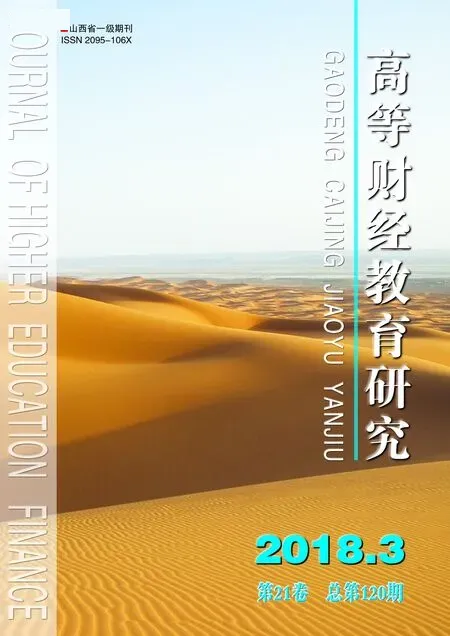劳动力流动的理论演变与最新研究进展
李 莉
(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山西太原030006;山西财经大学学报编辑部,山西太原030006)
劳动力作为基本的生产要素,其变动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劳动力流动与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经济增长紧密相连。我国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开放政策的实施使外资大量涌入沿海地区,劳动力需求旺盛,收入预期的增加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然而,随着劳动力大量流出农村、流入城市,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从城市而言,出现了城市拥挤、环境污染等问题。同时,由于户籍制度的约束,以及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福利待遇,使得劳动力在城市并不能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待遇,出现了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从乡村而言,随着劳动力的流失,出现了乡村凋敝、留守儿童等问题,导致劳动力流动的宏观经济效应难以完全体现。然而近些年,随着供给侧改革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制度约束的放松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劳动力的流动可能出现了一些变化,面临的选择更加多样化,可以选择外出打工,也可以留在农村成为职业农民,还可以在附近城镇从事非农产业但选择居住在农村。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关的理论研究层出不穷。这里我们主要针对劳动力流动的理论发展进行梳理,并就国内最新的研究进展进行总结与分析。
一、劳动力流动的理论演变
自工业革命以来,劳动力流动就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对于劳动力流动的理论发展,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再到中观的历程,成果丰富。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1]研究了二元结构下劳动力流动的情形,认为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在于地区之间经济收入的差距。之后,托达罗(Todaro,1969)[2]进一步认为,劳动力在做出是否迁移的决策时,关注的不是城乡现实的经济差距,而是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之后,随着现实中出现了新的现象与新的变化,人们认为仅根据区域收入差距考虑是否迁移,决策因素过于单一,于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新的理论应运而生了。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劳动力的迁移或流动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虽然在迁移过程中需要一定的支出,但人们期望通过迁移能够得到更好的工作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力迁移是权衡成本与收益后的一种投资决策,由此形成了人力资本理论。斯加斯塔德(Sjaastad,1962)[3]沿袭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引进成本-收益法,认为劳动力迁移是一种长期投资,是否迁移以及迁移到何地是在迁移者比较了所有可能目的地(包括现住地)净收益之后的权衡结果。人力资本理论将劳动力迁移从宏观视角转向了微观领域,更加关注对劳动力这一微观主体进行分析,研究了教育、培训对迁移决策的影响,从而对劳动力迁移的选择性给出了更加可信的解释。但是,该理论并没有考虑人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性,也忽略了家庭对劳动者迁移决策的影响。
在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比较低,社会保障并不完善,家庭成员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是普遍现象,劳动力迁移往往是整个家庭做出的策略。为此,斯塔克(Stark,1985)[4]提出了新劳动迁移经济学,将家庭因素纳入分析框架。斯塔克认为,劳动力流动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整个家庭的集体决策。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较低,社会保障不完善,家庭是家庭成员预防风险、提高收益最基本的保障,因此,家庭因素在劳动力流动中的作用,在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
社会网络理论则弥补了已有研究只局限于宏观总量、微观个体的视角,从中观的视角出发开辟了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研究层面。马西(Massey,1990)认为潜在的迁移者与已迁移的亲朋好友(包括城市亲戚)之间的联系是劳动力迁移的重要影响因素。这种亲朋好友构成的社会网络降低了劳动力流动的成本与风险,促进了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流动。波提斯(Portes,1995)认为劳动力流动网络是将迁移者与被迁移者联系在一个具有互惠责任和义务的网络中,该网络系统可以促使劳动力流动进入目的地。
近些年兴起的新经济地理学则在基本假设上不同于以往理论,其将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纳入了分析框架中。在新经济地理框架下,市场潜能对劳动力流动具有显著影响。对此,Crozet(2004)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构建了劳动力迁移决策的结构方程,检验了市场规模对于五个欧盟国家(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结果发现,在这五个国家的劳动力转移中市场潜能均具有显著作用。
二、国内最新研究进展
从对国外的理论梳理可以看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多种多样,既包括宏观层面的经济因素、制度因素等,也包括微观方面的个体特征,还包括中观方面的社会网络因素。国内对于劳动力流动规模、趋势的探讨起步较早,但应用经典理论研究劳动力流动动因最早是由陈吉元[5]在1993年开始的,他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扩展为农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城市部门的三元经济结构,认为发展农村工业部门能够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之后,中央政策研究室农村组(1994)[6]分析认为,日益增长的农村就业压力、发达地区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是上世纪90年代初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主要原因。高国力(1995)[7]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流动机制更加符合托达罗的理论模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劳动力找到工作的概率是其进行迁移决策时主要考虑的因素。
我国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在最初的研究中,考虑的因素较为单一,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此后,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同时我国自身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曾经的城乡分割政策引发的二元结构、户籍与土地制度的约束、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人情社会的传统文化特征等,使劳动力流动在方向、速度、规模等方面逐渐呈现出复杂性。近期的相关研究则基于这种复杂性,研究的侧重点不再单一,而是呈现出多层面、多角度的融合。
(一)宏观层面的因素更加丰富
1.制度的约束。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劳动力流动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蔡昉(2001)[8]对劳动迁移的过程及其制度性障碍进行了研究,认为政府的政策与规制以及诸如户籍制度在内的制度约束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柳建平(2011)[9]研究了土地制度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作用,认为土地制度变革能够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但与此同时,由于对土地潜在价值的预期不断升高,因此增加了劳动力放弃土地的难度,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郑子青(2014)[10]研究认为,虽然目前的土地制度对劳动力流动仍有约束作用,但其依然促进了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统计结果具有正相关性。傅晨、任辉(2014)[11]研究认为,在农民分化背景下,土地所发挥的功能有所不同,因而对土地的诉求不同,土地制度的改革也要与时俱进。张晓敏、张秉云、刘燕、吕世辰(2017)[12]研究了北京、山东、山西等地农地流转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认为农地流转与劳动力转移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劳动力的有序转移是土地流转的前提和条件,农地流转则为劳动力转移提供了资本支持。
此外,户籍制度由于自身的约束作用以及与福利保障相挂钩,因而也备受关注。张正河(2016)[13]从人口要素流动门槛变迁的角度,在制度实施的背景目标、举措效果和制度弱化后引发的新问题三个方面,对户籍制度的变迁过程进行分析,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在放宽人口要素流动门槛的同时,也提高了大型城市的准入门槛,并提出公共服务要分类配置、适度整合,解决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或将成为户籍制度改革的新方向。
综上可知,户籍制度的放松有利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但需要公共服务相匹配。土地制度的改革一方面促进了劳动力流动,另一方面由于其预期价值上升,因而对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也可能产生阻碍作用。
2.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城乡公共服务水平的非均等化也是导致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原因。蔡秀云、李 雪、汤寅昊(2012)[14]认为目前中国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跟不上城市化发展速度。夏怡然、陆铭(2015)[15]研究了公共服务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认为公共服务会稳定地影响长期的劳动力流动,劳动力会流向公共服务水平更高的地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有利于人口空间分布的均匀化。徐超(2015)[16]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教育扩展由于降低了劳动力获取信息的能力以及迁移成本,因此提高了劳动力的流动性。总体来看,研究大多认为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利于人口分布的均匀化。
3.技术的进步。赵德昭、许和连(2012)[17]发现,从全国层面来看,FDI和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正相关,但就各地区而言,作用效果还存在显著差异。宁光杰和林子亮(2014)[18]、杨蕙馨和李春梅(2013)[19]认为信息技术应用提高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王子敏(2017)[20]研究发现,互联网所导致的技能偏向降低了流动劳动力的就业概率,但提升了其就业的稳定性。就目前收集到的文献来看,对技术进步引发的劳动力流动,研究还有所不足。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降低了人们收集信息的成本,在很多方面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如消费习惯、教育资源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这些因素就会显著影响到劳动力的流动,有可能流入城市,也可能回流农村。此外,新能源技术的发展使某些产业分布趋于分散化,这也会影响到劳动力的流动方向与规模。
4.交通设施的改善。马伟、王亚华、刘生龙(2012)[21]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促进了人口迁移,改善了要素的自由配置。宋晓丽、李坤望(2015)[22]分析显示,铁路提速对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的促进作用仅在长期显著,其对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减少了劳动力的出行风险,缩短了交通时间,并且使远距离通勤成为可能。工作与生活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工作的地方在城市,生活的地方在城市近郊或邻近的乡村,交通设施的改善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劳动力的流动具有了更多的选择性。
5.市场规模与集聚的外部性。新经济地理学中,认为市场规模的扩大增加了商品种类,使人们具有更多的选择性。同时商品种类的增加加剧了市场竞争,导致商品价格下降,从而增加了人们的实际工资,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入。朱妍等(2010)[23]在新经济地理框架下,利用市场潜能函数研究了劳动力流动的区位选择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此后,王永培和晏维龙(2013)[24]、敖成军等(2015)[25]的研究均证实了市场规模对我国的劳动力流动具有显著影响。
(二)多层面因素相融合
实际上,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并且在不同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其一,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相结合。蔡昉、都阳、王美艳(2003)[26]认为劳动力做出的迁移决策是权衡预期收益与迁移成本之后的结果。基于劳动力迁移决策模型,可以发现,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有很多,除了预期的收入差距外,还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因素、制度因素、社会关系网络等。程名望、史清华、徐剑侠(2006)[27]基于推拉理论分析发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城镇工业技术的进步等所表现出的拉力作用更为显著。同时发现,教育、性别、家庭收入水平、区位等因素也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具有明显影响。程名望、史清华(2010)[28]通过建立计量模型研究了农民个体特征及其家庭特征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结果发现,男性、非农户口、身体健康的农民流动的意愿更强,而受过农业技术培训或有技术职称的劳动力流动的意愿较弱,“家庭收入来源”等家庭特征变量对劳动力流动影响较大,从而表明,个体特征与家庭特征对劳动力转移有重要影响。雷超超(2013)[29]认为,除了非农部门更高的生产率之外,居民现实消费的非位似偏好,是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赵峰、星晓川、李惠璇(2015)[30]分析认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主要分为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宏观层面的经济政策、制度改革以及微观个体及其家庭的收益权衡,相互交织,共同驱动着劳动力的流动。其二,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心里因素相结合。陆铭(2011)[31]认为,要在制度约束和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解释中国的特殊现象,分析社会互动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一是分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二是分析社会网络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何军(2011)[32]则从经济、社会、心理三方面构建了农民工社会融入程度指标体系,并考虑到了农民工的内部分化与异质性。
可以看出,一方面,劳动力作为基本的生产要素,具有明显的经济属性,其变动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劳动力又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其一举一动受社会因素、心里因素牵制。因此,研究劳动力流动的文章纷繁复杂,角度多,层次差距较大。原因在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面对不同的主题,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三、小结
通过简要梳理文献可知,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除了城乡收入差距外,户籍与土地制度、公共服务水平、技术进步、交通状况等在现阶段都具有稳定作用。个人特征更多地决定了流动意愿与流动能力,密切的社会网络能够降低劳动力流动的成本与风险。影响因素的多层次性以及交互性,使最新研究成果更加多样,结论愈加丰富。同时,劳动力的流动与产业结构变动相互影响,更与城乡关系演进密切相连。本文仅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梳理,对于其所产生的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未有涉及,而这也是研究劳动力流动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需要做进一步的梳理与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