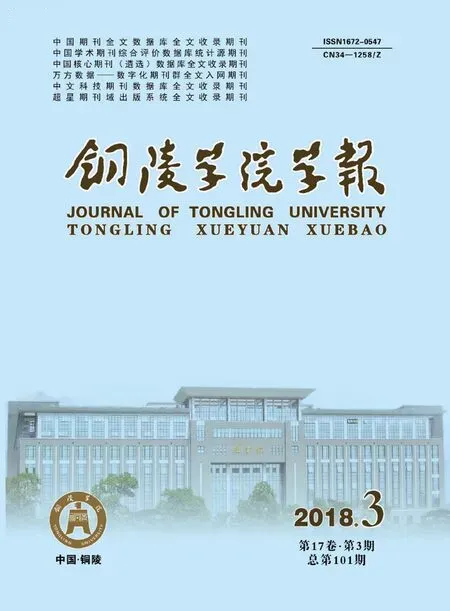生命美学语境中的《牡丹亭》艺术内涵透视
李劲松 罗可曼
(合肥师范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书而非也,虽其言出自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之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之于孔子者乎。”[1]这是王阳明《答罗整庵少宰书》中一段话,其中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观念,已经隐含了对普世性“理”的质疑和对个体性价值的尊重,“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2]这里的“成己”指的是主体自我造就成独立人格。这种以心性与理性之争为旨趣而独树一帜的思潮在明代个性化的土壤中孕育滋长开来,就戏剧的发展路径来看,宋元戏剧中的“情”、“个性”在历经数百年之后又一次在明代的戏曲土壤和适宜的环境中潜滋暗长、深化和升华,深化表现为戏剧表现手法的多元化而彰显生命的不同面向,升华则反映在主旨思想的情感化倾向,二者结合起来歌颂生命之品性。所谓生命化美学倾向,即明代戏剧主题的生命情感化、戏剧表现手法的生命化描摹、戏剧人物语言追求“真我”的个性化表达。下面笔者就带领我们走入《牡丹亭》的戏剧时空,展现独特的生命化艺术内涵。
一、以“情感”为发端,潜滋生命之动态
“情感”二字是中国古代戏剧创作的一条主线,从唐代的参军戏到宋代鼓子词,从金元杂剧到明清的戏曲,无不体现情感之种种面向、状描情感之形态,个中情味或豪迈或幽怨、或喜悦或悲悯,均构成一幅幅市井百态图,使人荡气回肠、掩卷长叹。在这条线索的另一端——明代戏剧,由于成化、弘治时期,伴随着人情心性的觉醒,崇尚自由之个性和人生乐趣成为文艺思潮之主流,并将对恪守仁义礼信的程朱理学、台阁文风构成前所未有的强大冲击,戏剧家的主体意识在作品中得到高扬,恰逢明中后期的“土木之变”、“夺门之变”等政坛的跌宕起伏、腥风血雨,使得迂腐守旧、苟合取容之政风被谅直骨鲠之气所涤荡,迷恋程朱、醉心功名之文风也被明心悟性、追求自我的自为拔振的豪放精神所取代,而这种敢于冲破思想牢笼、努力寻求真我、彰显生命自觉的时代精神作为大写的“个性”张扬在明代的戏剧创作之中。
诚如明史学家们所论证,明代的文化格局发生了根本性转向,从创作主体看,文人从依附贵族转向倾慕平民,或准确地说,从附贵族之骥尾转向借平民以自重,文人自我意识的高涨和主体精神的张扬,促成了不可抑制的文化权力下移的趋势,以文人为主角的社会文化模式正逐渐取代了以贵族为主角的社会文化模式。[3]在汤显祖的《牡丹亭》中、在王实甫的《西厢记》里,柳梦梅与张君瑞都是一介书生,都是文人主角的社会文化模式在戏剧创作里的转向。而这种转向是在陈腐的宗教礼法与鲜活的生命张扬之间的生死搏斗而呈现出来的,是在文人生命主体意识觉醒所产生出的情欲与钳制个性、封杀思想的程朱理学捍卫的宗法制度之间的鱼死网破而绽放出来的生命火花。诚如杜丽娘在《寻梦》一出中唱到:“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4]这里的恋、愿、怨都是作者极力渲染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与宗法等级制度之间抗争的血泪故事,同时也寄寓了诗人的深切关怀,贯注了诗人的生命激情和人生体验。因此后人评价道“《牡丹亭》是一首青春的诗、一首生命的诗。”[5]笔者要说,这是在文弱书生不堪宗法礼教之精神压迫,而求诸于史事,放任自己的生命意识游历、掀起情感之事的生命旅程的真实写照。阅读此类作品,总能给读者带来对生命的体认和对生命本体的褒扬。
明代以来以文人为主角的社会文化模式的转向实质上是文人生命主体意识觉醒所产生的情感欲望与钳制生命、封杀个性的程朱理学所捍卫的宗法制度之间展开的较量过程中而绽放出来的对生命体认与否的转向。
汤显祖,临川人(今江西),字艺仍,号若士,年少成名,才华横溢,但性情耿介,得罪了当朝权臣张居正,遭报复。后中进士,任南京礼部祭司主事。因为上书,触怒明神宗,被贬为广东徐闻典史,终弃官回临川老家,著书《牡丹亭》。从汤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文人士大夫,且是性情刚直不为名利所累的读书人,其才华横溢却屡遭排挤,仕途的坎坷为其人生增添了无穷的感触,而这些对生命品相的真实感悟则又为其创作提供了宝贵的人生体验,在屡次的迁徙中,汤显祖不与官场聚首,却同许多戏剧行当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据《作紫阑戏衣二首》所记载,汤显祖同许多宜黄腔演员交往密切,甚至在戏院经营之人的安排下,汤显祖亲自粉末登场参与自己编创的戏曲排练[6]。从典籍记载中可以得知,汤显祖的真情实感和文人底蕴以及亲自参与艺术演出的体验都是其能驾驭《牡丹亭》的秘诀。后人也就能从《牡丹亭》的一曲一辞中体味到来自宗法礼教封冻下涌动的生命情感,才能体会到【北尾】中那句唱腔“牡丹梦影双描画,南枝挨暖北枝花,做鬼有情谁似咱?”[7]所传递出的向死而生的悲壮与酸涩。也不禁让我们想起《西厢记》结尾处:“愿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一句唱,两出剧作都是文人主角的情感主题,但却能各美其美、各领风骚,其中的缘由要等到读者仔细品读汤显祖的一连串亲历之事后,更确切地说,等到我们能以生命为参照系,跨越时空随剧作家生命轨迹的离合聚首而悲欢动容之时才能真正体悟。文人为主角去影射生存时空的权利角逐和情感冲突是明代戏剧创作的一大特色,而剧作家的“行当”出身,则更为其创作增添了专业特色和真实的生命底色。
二、离奇的情节设计,描绘生命色彩之烂漫
所谓“本色”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是明代戏曲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对于“本色”的确切含义,戏剧史论界众说纷纭,不一而衷,这里就借用当代中国古典戏剧研究学者谭帆的观点作为本文对“本色”的诠释,且谭帆先生之“本色说”已经得到古典戏剧界认同,他认为本色:一是指明代戏曲语言的平民性,即通俗易懂性,二是指明代戏曲内在的“曲”的个性和特征。前者从具体的戏曲语言呈现来立论,后者则从抽象本体特征来概述,二者在汤显祖笔下,以离奇荒诞的情节编织出色彩烂漫的生命水粉画,即情节设计的非常规化要表达出明代戏曲内涵独特的生命个性。反过来说,明代戏曲中鲜明的生命母题就是通过剧作家们巧妙的情节设计、人物造型来展现的。
先看情节设计之妙,明代戏剧根于宋元之南戏和金元之杂剧,在长期舞台实践中,形成了以唱南曲为主的长篇戏曲形式——“传奇剧”。作为案头的传奇剧本,从曲之韵律到文之内容,均较前有了大的突破。从明代茅暎的《题〈牡丹亭记〉》对传奇剧的见解中,可见“传奇”二字的艺术内涵:“第曰传奇者,事不奇幻不传,辞不奇艳不传。其间情之所在,自有而无,自无而有,不瑰奇愕眙者亦不传。”[8]
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道出了牡丹亭离奇的情节构架:“天下女子有情,宁有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9]
这是何等离奇之故事情节,这样的故事情节设计和构思为何能历经千年而不衰,被人经久吟唱呢?原因之一,恐怕在于“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10]
即今人看来颇为奇幻的死而复生的情节,实际上是死去的年轻女子通过其幽灵一度与世间男子交媾的故事,如此情节设计可以枯骨得以生肉从而再生信仰。[11]这种信仰以生命不息,追求不已,生命有涯而追求无涯的方式反抗着当时理学对人性、对生命的桎梏。
再看人物造型之工:汤显祖在《牡丹亭》对杜丽娘形象的塑造是煞费一般苦心的,先是“烘云托月”式的出场渲染,借名儒杜宝之口为女主人公的上场作好铺垫:
[老旦]也长向花阴课女工。[外]女工一事,想女儿精巧过人。随后拔云见日,丽娘一上场,拳手投足尽显大家闺秀的风范,[见介]爹娘万福!……[旦跪介]今日春光明媚,爹娘宽坐后堂,女孩儿敢进三爵之觞,少效千春之祝。[12]
这一席话语向观众展现出一位孝敬父母、精巧聪慧的大家闺秀的女主人形象。
陈最良,一个从生理上到心理上都深受科举制度毒害的酸腐书生,对他的安排,汤显祖是精心设计的,就是要通过陈最良这个腐儒,一个深谙宗法礼仪却又暗藏一颗善心的迂腐知识分子,他的言行、举止体现出道德沦丧的社会与个人情感之间的角逐,字里行间展示出对科举制度的讽刺与挖苦。我们看腐儒陈最良的登场,先是一段客观的人物刻画:
【双劝酒】[末扮老儒上]灯窗苦吟,寒酸撒吞。科场苦禁,蹉跎直恁!可怜辜负看书心。吼儿病年来迸侵。
然后一连串“七个小算盘”的心理活动刻画,使得一位腐儒形象活脱脱呈现在观众面前:
作日听见本府杜太守,有个小姐,要请先生。好些奔竞的钻去。他可为甚的?乡邦好说话,一也;通实节,二也;撞太岁,三也;穿他门子管家,改窜文卷,四也;别处吹嘘进身,五也;下头官儿怕他,六也;家里骗人,七也;为此七事,没了头要去。[13]
这一出的人物内心活动的刻画,着实有趣传神,为今后戏剧情节的推进营造了氛围,丝毫不露斧凿之痕迹。而对男主人公柳梦梅的出场,作者似乎并未多施笔墨,而是以杜丽娘的梦境为纽带,梦中对话的描写为观众呈现出一个“窈窕淑女、梦寐以求”的君子、书生形象:
【山桃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儿闭寻遍。在幽闺自怜。……[生]转过这芍药阑前,紧靠着湖山石边。[旦低问]秀才,去怎的?[生低答]和你把领扣松,衣带宽,袖梢儿揾着牙儿苫也,则待你忍耐温存一晌眠。……[14]
“游园·惊梦”是明代戏剧舞台上常演不衰的经典剧目,也是传奇剧本中之珍宝,从“梦”起笔、由“梦”入境、以“梦”收尾,杜丽娘的命运由此而发生彻底改变。一连串精巧的情节设计,一个个生动灵活的人物造型,彰显了汤显祖的“意、趣、神、色”这四大创作理念。也正是由于明代戏剧作家的匠心独运,使得明代戏剧演绎出异常丰富的时空转换、非同一般的舞台艺术镜像。无怪明代戏曲论者王思任叹道:“杜丽娘之妖也,柳梦梅之痴也,老妇人之软也,杜安抚之古执也,陈最良之雾也,春香之贼也,无不从筋节窍髓,以探其七情生动之微也。”[15]诸如此类的超越生死追求爱情的明代戏剧、传奇,尽管情节之奇幻、人物之奇异,仍令人觉得真实可信,实质乃情感的力量所驱动,正如张岱说的:“情的调和”[16],在戏曲表演中,剧作家融入了个人的强烈情感和生命体验,使剧中角色得以起死回生,富有生机活力、性格千面、感人至深。
三、营造个性:人物语言追求真我之表达
每一位剧作之人都是在传统基础上开拓创新,并在继承中又呈现自身个性和独创性而又构成传统的一部分,供后人临摹学习。因此,考察明代戏剧,尤其是传奇剧,应该把他们放入戏曲发展的历时性语境中,考察其继承与拓新,方能还其一个客观性评价。犹若明之戏剧之于宋之南戏,传承中带有革新,尤其戏曲语言为最,南戏的剧本多出自民间艺人,大多质木而无文采,后来文人参与表创,但又雕镂过甚,多带斧凿之痕,而失去戏曲艺术本体特征,这可以从汤显祖等人的早期戏曲里找到痕迹,仆人说话也是四六文的对句,但到《牡丹亭》一剧的创作时,汤显祖已经找到“雅”与“俗”之间的张合之“度”,在人物塑造、唱腔设计时深得“浅深、浓淡、雅俗”变化张合之三味,如《劝农》一出中,写到公人、农夫、牧童、采桑妇、采茶女的唱辞时,语言与身份更加相称:
【前腔】【生、末扮父老上】白发年来公事寡,听儿童笑语喧哗。太守巡游,春风满马,敢借着这务农宣化?……
【生、末】……官也清、吏也清,村民无事到公庭,农歌三两声……。
【前腔】【旦、老旦采桑上】那桑阴下,柳篓儿搓,顺手腰身翦一下丫。呀,什么官员在此?俺罗敷自有家,便秋胡怎认他,提金下马?……[合]官里醉流霞,风前笑插花,采桑人俊煞。……[17]
像这样朴实的生活语言为观众编织了一幅 “桃花源”美景,画中公人、农夫、牧童、采桑妇、采茶女的形象通过对其言语、神态的准确刻画而传递出生动、清新的艺术氛围,这与汤显祖本人的经历和独特的艺术天赋是密切相关的,汤显祖曾经在浙江遂昌担任过地方官,且政绩颇佳,这里的杜太守就有着作者的影子,此为“真我”,所见之人、所闻之音,皆为其真实生活的一个场景,但要使这些真情实感能升华、折射出人间世俗之情,且还需要作者具备一颗涌动生命活力的体悟之心,此为“真我”之表达。在脍炙人口的【惊梦】、【寻梦】中,尽管受到严格的曲律限制,但剧作家极富生命活力的描画,为观众展现的画垣、春景如同身临其境一般,在春光烂漫中品味着杜丽娘对爱情的渴望。
【懒画眉】最撩人春色是今年。少甚么低就高来粉画垣,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悬。(绊介)哎,睡荼藶抓住裙衩线,恰便是花人心好处牵。
【尾犯序】心喜转心焦,喜的明妆俨雅,仙珮飘飖。则怕呵,把俺年深色浅,当了金屋藏娇。虚劳,寄春容教谁泪落,做真真无人唤叫。……[旦]这一幅行乐图,向行家裱去。……[18]
这一出“写真”定格了女主人公的美妙青春、俏丽姿容。可又是徒劳的,因为金屋藏媚娇、深闺锁花容,无人得见。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剧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少时神悟、聪明过人,颇为众里邻人所褒赏。当时的权丞张居正欲使其子与汤交往,学汤所长,加强其政治资本,但被显祖断然拒绝。后又有丞相申时行,垂青于其,欲拉拢汤显祖。显祖亦不为所动。结果显祖屡遭排挤与陷害,纵有一身经天济世之才、却无施展才华之机,一生仕途多舛,壮志终不能酬。古人以“诗言志”,然显祖何尝不是把一腔难酬之志付与《牡丹亭》一剧,剧中杜丽娘、柳梦梅不正是作者的影子在戏文中的投射吗?官场的倾轧如宗法之禁锢情窦,杜丽娘、柳梦梅用生命为屏障坚守情之忠贞,显祖则是以剧文为堡垒捍卫人格之不屈、生命之尊严。
“还生命以尊严”或许是汤显祖所处时代的知识分子面对宗法制度、程朱理学钳制个性、扼杀生命情感的现状时发出的呐喊。初始一声破云呼,万众齐唱霞光来。“生命”在汤显祖天才妙笔的描画下呈现出种种面向,或妖媚或痴迷、或软弱或懵懂、或轩昂或隐晦……。汤正是用如此灵动可爱的生命镜像为我们描绘了一出真戏、真情,这些凝聚着作者“真我”生命印记的情感片段共同演绎出一幅美仑美幻的、且生命之气息波澜壮阔的戏剧——《牡丹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