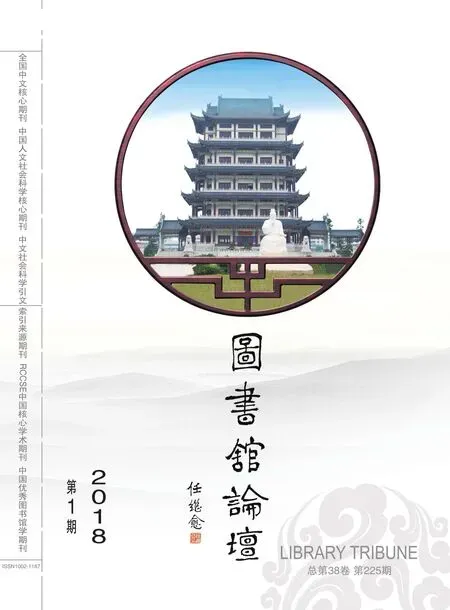当代图书馆新公共文化外交功能的培育路径与实施策略
栾 娟,熊 伟
当代图书馆新公共文化外交功能的培育路径与实施策略
栾 娟,熊 伟
在全球化背景下,代表全民外交趋势的新公共外交成为很多国家全球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作为公共文化空间和公共知识交流体系的当代图书馆具有培育独特公共文化外交功能的理论依据,为各国新公共外交提供了新型长效载体。当代图书馆新公共文化外交功能培育的基本路径包括创建“大开放”传播平台、开展“请进来”活动和实施“走出去”项目。各类图书馆可从实际出发,稳妥选择实施内联量力推进、外联合力推进和创新巧力推进等工作策略。
图书馆功能 新公共文化外交 公共文化空间 公共知识交流体系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全球化进程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再到文化领域的不断拓展,各国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公共外交的重要性骤然提高,很多国家把强调全民参与、面向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新公共外交提升为全球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近年我国拓展公共外交,在开放接纳国外先进文化输入的同时,大力推进中华优秀文化向国外输出。图书馆本身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较大规模社会化的信息与知识交流的产物,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有机体。为了持续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环境和更好地实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图书馆新的社会功能逐步在原有系列社会功能的基础上继续生成与表现出来,特别是通过持续发生自身服务空间的当代转向,不断为自身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历史机遇。由于国际范围内的社会舆论、观念和信息等因素对一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与日俱增,作为特定社会教育机构的图书馆在拓展国际视野的追求下,在辅助性支持相关政府外交活动的基础上,开始自觉主动参与到非政府性的国际文化交流与信息传播活动之中,逐步生成了作为非政府组织主体的民间对外交往与交流功能,进而拓展生成了强调话语影响、有效辅济政府外交的新公共外交功能[1-2],丰富着国家的整体外交内涵。20世纪初期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重视发挥图书馆的新公共外交功能,相关理论与实践引起了图书馆界的关注[3],上海图书馆[4]与广州图书馆创新践行[5]。在上述时代背景下和薄弱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图书馆新公共文化外交功能的培育路径与实施策略,对促进我国图书馆重视开拓并切实发挥好新公共文化外交功能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1 当代图书馆新公共文化外交功能生成的理论依据
《中国公共外交发展报告(2015)》对新公共外交的界定是“一国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各方从各种角度向外国公众表达本国国情,说明本国政策,解释外国对本国的不解之处,并同时在国际交流中了解对方的有关观点,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形象,改善外国公众对本国的态度,进而影响外国政府对本国的政策”,其核心观念是最大可能地调动和发挥普通民众的参与,“在公共外交的行为中,政府是主导,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和社会精英是中坚,广大公众是基础”[6]。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图书馆可以成为新公共文化外交的主体,并以其具备的独特属性而发挥重要的作用。
1.1 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当代图书馆为新公共文化外交提供了新型长效载体
长期以来,图书馆作为文献中心或信息中心为社会主要提供资源服务。因此,在人们的传统认识中,图书馆空间主要是一种建筑空间或物理空间。受后现代主义“空间转向”思潮影响,国际图书馆界提出了“作为场所与空间的图书馆”“作为第三空间的图书馆”的新命题,并给出了信息共享空间、知识共享空间、社会创新空间、社会公共空间、学习交流空间、知识生活空间、休闲娱乐空间等多元化阐释[7]。概言之,当代图书馆服务正在发生从“资源服务”向“空间服务”的转移,即服务重心由“以资源为中心”向“以用户为中心”转移[8],其服务领域也由“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转移,凸显了其公共性的基本属性,正在加快构建其深刻影响公共权力、公共事务和公共领域等方面“公共性谱系”[9]。当代图书馆空间已经逐步演变为一种“公共文化空间”,具有高度开放性、公共空间性和社会交互性等基本特征。这就使得当代图书馆开始具备独特社会文化组织主体地位,为强调国际间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新公共文化外交提供了交流场所或空间方面的新型长效载体。
1.2 作为公共知识交流体系的当代图书馆为新公共文化外交提供了先行基础保障
图书馆究竟是如何面向社会大众提供公共服务的?20世纪以来,我国图书馆学术界先后从“社会交流”视角提出一系列理论解释。早期代表性的学说有周文俊提出的“文献交流论”、倪波等提出的“文献信息交流论”和宓浩等提出的“知识交流论”。近年来,梁灿兴在辨识客观知识的交流类型,即客观知识交流(包含心灵对话、交流、交互和流通等含义)、公开知识交流、公共知识交流与私域知识交流,特别是分析公共交流特性基础上,提出“新知识交流论”[10],强调图书馆是私域交流与公共交流连接的枢纽,不仅支持私域知识交流,而且以提供公共场所发起公共话题等方式支持公共知识交流[11]。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公共领域的发生顺序是文学公共领域——公共文化领域——公共舆论领域——公共政治领域[12]。总的来说,图书馆所支持的公共知识交流基本上是按照此发生顺序影响特定社会公共领域的形成及其拓展的。较之传统公共外交,新公共外交的“新”主要体现在[13-14]:(1)新公共外交是软实力视野下的全民外交,强调行为主体多元化,生成了垂直化和网络化并存的实施结构,并且更多聚焦非政府行为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和职能。(2)关注以WEB2.0为代表的社会媒体活跃所引发的海量信息生成及其对公共外交专业工作人员带来的严峻挑战,依托网络和传统媒体,倾听、反馈和引导网络舆论,势必要通过“独白”和“对话”同时进行。(3)强调公共外交与国内公共事务相一致原则,淡化传统公共外交信息传递内外有别的传统套路。(4)关注对公共外交实施效果的考察,认为很有必要建立专职跨部门协调机构,明晰权力与职责划分,统筹安排以有效利用各部门资源并形成发展合力[15]。由于新公共外交的核心目标是通过改变外国对本国的现有认知,促进国家整体或相关具体利益的实现,而外国人士和本国人士对一个国家认知总是通过其全方位接受的跨文化信息濡化构建而成。当代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是非常重要的文化传播类非政府组织,从可以大力支持外国人士获取本国知识和信息,以及支持本国人士获取外国知识与信息双向交流意义上说,为新公共外交提供了一种基于客观知识的公共交流路径。值得注意的是,在深度全球化过程中,全球化、国际化、现代性的因素与区域化、本土化、历史性的因素之间的各类矛盾也随之产生,其中既有各种现实复杂利益的纠葛,也有来自价值观差异的尖锐冲突。这正是在政府外交之外,强调人人均可参与面向他国公众维护本身国家形象、国际间互信、增进政治经济相关利益和社会认同建构的新公共外交走上历史舞台的根本原因。图书馆所支持的公共知识交流对于新公共外交的独特深层意义还在于,可以依托其由知识载体存取层、知识内容解释层、知识应用转化层和智慧思想启迪层构成的专业资源支持体系,为国际交流的参与双方提供了一种常态化的基于丰富客观知识或信息的跨文化沟通平台,有利于双方在系统地观照彼此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差异基础上求同存异,逐步营造起理解、善意和趋同的互信机制,在取得某些社会共识的基础上开启对话与合作。由于文化外交是公共外交的最早形式,“新公共外交的中心是信息与观点的流通”,强调公共文化交流与沟通的图书馆的公共文化外交在当代新公共外交体系中可以处于一种先导性和基础性的类型地位。
2 当代图书馆新公共文化外交功能培育的基本路径
2.1 “大开放”文化传播平台建设与推进路径
在现代化城市深化发展过程中,作为典型公共文化空间的公共图书馆正在成为一个城市高度开放化的信息、知识与社交的综合传播平台,其日常服务对象不仅包括本国的常住居民,还包括外国在本地的永久居民或流动人士,面临着内在驱动促进城市政治经济社会的建设与发展的时代任务。其中,如何善待在本地工作外国人士,不仅是一个涉外活动中的政治问题,而且是一个“情感留人”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柔性感化”的人道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大中型公共图书馆应该高度重视并积极承担起自己的新公共文化外交责任,并使之成为一个国家的城市新公共外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在互联网环境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当代图书馆日益成为全球化信息与知识网络中的公共枢纽与服务平台之一,直接面向国内外用户提供信息与知识链接入口,是一个国家的网络公共外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面临着如何具体做好基于网络的国家对外形象传播与塑造的任务。此外,在新媒体特别是自媒体勃兴环境下,当代图书馆正在更加深入广泛地应用新媒体与自媒体,是一个国家的媒体公共外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6],面临着如何创造性进行相关国内外新闻报道与促进形成必要的公共舆论。例如:上海图书馆开通了“上海之窗”项目的中英文官方网站及微博,把“上海之窗”项目与中外图书馆之间馆际互借、国际文献交换工作、编目国际化、网络全球化等其他国际交流业务紧密结合起来,还与境外单位联手开展专题学术活动,开展馆员交流和研修以提高专业人员队伍的业务水平。近年来,上海图书馆正在依托分布在52个国家70个城市中的“上海国际友好城市”平台,与更多境外合作伙伴积极互动,努力把“上海之窗”开设到更多海外读者中去,继续联手打造“上海之窗”文化品牌,着力形成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全球合作与交流模式[4]。综上,加快创建具有国际化视野的、由实体场所平台和网络虚拟平台构成的“大开放”传播平台,是培育当代图书馆新公共文化外交功能的根基所在,且是一种相对独立自主开展新公共外交的基本途径。
2.2 “请进来”公共文化外交活动策划与实施路径
在较长时期,并非各国各种类型的图书馆都具备策划与实施“走出去”公共文化外交项目合适条件。但是,所有类型图书馆都可以依托现有条件在本土适当策划与实施针对外国目标群体或个体的“请进来”的公共文化外交活动。这是因为,以社会包容性著称的各类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本身就是很多国家的各类群体或个体经常光顾的场所,即使在异国他乡的光临仍会使参观访问者感到特别熟悉与亲切。更为重要的是,凡是较为合格的公共图书馆在一定程度上应是浓缩本地特色风土人情的“文化地标”,而较为合格的大学图书馆在一定程度上应是集中展示本校办学状态的“学术中心”,可谓是外国人士较为迅捷获得“区域印象”或“单元印象”的合适窗口单位之一。目前看来,适合当代图书馆本土化策划与实施“请进来”活动途径主要有4个方面:(1)积极承担外国政府要员或民间友好代表团的到馆外事参观访问任务,如上海图书馆和广州图书馆作为“城市客厅”均经常性接待过很多高级别的外国政要,并通过国际化的新闻传播方式,显著提升了国内外民众的关注与好评。(2)积极承担外国科技、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工作团体或个体的到馆参观访问任务,一方面可以开阔本馆工作人员的国际视野,提升人员的外事工作素养;另一方面也可以对外展示本区域或本单位的良好社会形象,增加更多的对外合作交流项目的机会。(3)积极策划与实施针对在本地工作或学习的外籍人士的多元文化信息服务项目,如设置专题书库或书架;专门活动区或主题活动区等,热心帮助他们尽快克服跨文化交流障碍或解决一些工作学习上方面的实际困难,特别是可以考虑组织若干具有民族或民俗特色的文化娱乐活动,在促进“民心相通”方面有所作为。(4)加快城市公共图书馆空间再造步伐,积极建设更多的“联合办公室”,支持在本市工作的国际友人与国内合作伙伴开展相关业务活动。
2.3 “走出去”公共文化外交项目策划与实施路径
根据英美发达国家开展公共外交的经验与做法[3][13],当代图书馆公共外交功能的培育还需要依托一系列“走出去”的对外交流项目,并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执行相应的公共外交战略和策略。目前看,当代图书馆可以从自身条件出发的“走出去”项目策划与实施路径主要有两个方面:(1)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积极实施具有官方背景或民间背景的相对独立的海外图书馆项目、图书捐赠项目、信息交流项目和教育与文化交流项目。主要实施主体包括国家图书馆、基础条件较好的大学图书馆或大中型公共图书馆等,主要实施对象是作为该国“民意风向标”的知识分子阶层和精英人士。其中,在“海外图书馆”设立方式上,既可以在外国本土直接设立实体图书馆,如美国和法国历史上曾在海外设立了数量较大的实体图书馆,或依托文化研究院或书院设立附属图书馆,如韩国在海外设立的文化院建有相应的图书馆,也可以依托在国外本土的文化交流中心设立虚拟图书馆,如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设有叶利钦总统图书馆虚拟分馆,还可以在作为合作伙伴的外国图书馆实施合作发展项目或品牌,如上海图书馆在国外开展的一系列合作项目或活动品牌[4]。(2)在本国特定时期公共外交战略规划或统一部署下,依托图书馆界积极实施该国信息、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国际交流项目。例如,强调建立“一膊之距”文化管理体制的英国长期聚焦文化外交,高度重视具有官方背景的文化协会作用,把海外语言教学工作作为政治、经济与军事外交之外的第四类中外交形式,推进以流行时尚为传播主元素重塑国家形象,确立了关于英国的国际核心形象并着力完善执行体系,为了配合国家反恐战略而致力于国际互信与认同建构。其中,英国文化委员会非常重视在海外建立图书馆与资料中心来输出英语图书和信息,并依托这些图书馆与资料中心建立网络化的信息共享平台,开展全面的信息咨询服务,吸引大量的英语爱好者在此学习交流[13]。
3 当代图书馆组织开展公共文化外交的主要策略
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公共外交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主要的公共外交理论导向分别有实践导向、效果导向和整合导向,已概括出来的实践模式有基础冷战模式、非政府组织模式和国内公共关系模式等,也有政府与非政府行为体合作模式和非政府行为体独立担当模式,还有“四个阶段”模式(问题发酵和病毒式传播阶段、主动出击阶段、反应阶段和议题衰退及新议题发酵阶段)以及“上下级组织协同创新外交”模式等,并且强调公共外交要淡化意识形态喊话色彩、重视倾听他国公众心声、提升公共外交实践者专业素质、重视非政府行为体参与公共外交的资质考查和尽快建立公共外交项目评估指标体系。这些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探索都需要当代图书馆充分学习、借鉴与反思。今后在具体组织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方面,我们既要充分看到图书馆独特的知识资源优势,同时也要看到其明显的社会资源劣势;既反对“大有作为”的过度乐观,也反对“无所作为”的过度悲观,主要应该坚持围绕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有所作为”的中肯基调。更重要的是,务必深刻认识到图书馆具体类型的多样性、地域条件的差异性和综合实力的差距性等实际情况,尤其是深刻认识到从本国启动到连接影响他国公众面临诸多繁复操作环节与诸多现实障碍,既鼓励条件好的图书馆先行一步示范,也允许条件差的图书馆做后进跟踪效法,逐步实现图书馆界公共外交的“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当代各类图书馆在培育公共文化外交意识和明确公共外交路径的基础上,应当从自己实际出发,坚持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稳妥选择合适的实施策略。
3.1 内联量力推进:分类定位,分步实施,分工合作
当代各级各类图书馆积极推进公共外交时,首先必须坚持内部联合与分工合作这两个基本工作原则。从基本类型上看,当代图书馆大体可以区分为国家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科学图书馆和专门图书馆等。在角色定位方面,整体实力最强的国家图书馆,以及省级或较大地市级公共图书馆毫无疑问应发挥本国本行业的公共文化外交平台的设立者,更是总体设计师、倡导者和培训者的作用,充分发挥好龙头示范或领军整合作用,其他层级的公共图书馆特别是基层公共图书馆更适合以区域参与者或区域自主者的角色积极贡献自身的力量。大学图书馆、科学图书馆和专门图书馆应在自主或参与其开展传统外事活动的基础上继续开拓提升,可根据自身整体实力发展状况,分别确定为领域参与者或领域自主者或领域引领者的角色,求真务实地做好相应领域公共文化外交的资源统筹、战略规划与年度计划。在实施步骤方面,由于绝大多数图书馆在目前都面临着对公共文化外交的认识深化、经验积累和资源筹备等问题,也必然有一个跟踪学习与探索实践的过程,因此很有必要由易到难和由内而外,大体上可以按照“大开放”路径—“请进来”“走出去”进行分步实施。具体来说,很有必要按照“活动策划”—“项目策划”—“品牌策划”的递进层次进行分步实施。在资源整合方面,由于绝大多数图书馆尚缺乏公认的行业国际影响力、较高的专业公信力、稳定可靠的公共外交渠道和较为充分的经费保障等,其公共外交活动、项目和品牌建设策划环节迫切需要各级政府的宏观规划与指导,特别是政府外事部门和相关公共外交协会的引领与支持,而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也需要相关企事业单位的密切配合。
3.2 外联合力推进:借船出海,借地扎根,借机实施
较之“大开放”平台开放和“请进来”,只有认真策划与积极实施可持续发展的“走出去”公共文化外交项目才是当代图书馆真正具备公共外交能力的基本标志。根据国内外著名图书馆的先行成功经验,有一定实力的各类图书馆要实现“走出去”,客观上需要很好选择外联合作基础上的某个单一策略或系列策略组合:首先是“借船出海”策略,即依托或纳入本国的某个国际科学文化交流计划项目或“国际友好城市”等外交平台,实现与其他国家特定组织或公众的具体对接。上海图书馆依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提供资助“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在56个国家和地区的95家境外图书馆设计并组织实施“上海之窗”对外文化交流项目。这是绝大多数大中型图书馆重点要考虑的首选办法。其次是“借地生根”策略,即依托作为公共外交项目合作伙伴的其他国家特定文化组织的场所或空间展开相关业务活动。上海图书馆通过向境外图书馆及藏书机构等捐赠图书的形式,架起文化交流和中外友谊的桥梁。再次是以项目本身为平台相继策划实施相关双向公共外交活动。最后,在深化与外交项目合作伙伴业务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双向互动的公共外交项目实施长效机制。上海图书馆的“上海之窗”项目秉持“互通有无,相得益彰”的方针,接纳了一些境外机构开展讲座、展览、文艺表演、中国传统文化体验等一系列读者互动活动,推广中文学习,为传播中国文化注入了活力。
3.3 创新巧力推进:创新方式,创造内容,创意设计
所有国家的公共外交都必然要在全球新公共外交的宏观语境下进行,这就对当代图书馆的新公共文化外交活动提出了创新方式、创造内容和创意设计的时代任务。目前看来,值得当代图书馆今后重点关注的创新思路和实践举措有6个方面[6]:(1)创造性地依托国家外事部门或公共外交部门策划实施的国际教育、文化和信息项目,与本国在他国设立的文化中心、文化书院、文化学院等组织机构合作创办附属图书馆及研讨、论坛、展览和征文等相关服务项目,其中,依托我国在各国设立的“孔子学院”拓展实施具有图书馆特色的新公共外交项目是一种非常便捷有效的思路。(2)深度融入本地城市公共外交体系,借助本地城市搭建的各类公共外交渠道或项目平台,积极开展涉及科技、教育、文化等合作领域的“大开放”“请进来”和“走出去”等多种形式的新公共文化外交活动或长期项目。(3)重视公众话题设置,积极策划与实施具有本地图书馆特色、侧重传播国家文化形象与促进公众跨文化传播的网络公共文化外交项目或活动,特别是积极策划与实施好具有较强互动性和社交性的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公共文化外交项目或活动,其中应办好图书馆内部连续出版物,定期更新并发布图书馆对外形象宣传片,重点做好数字化视觉传播、双语化传播甚至母语化公共传播的内容策展工作。(4)国家相关智库开展以资政研究资料交换为先导、以资政研究报告交流为核心内容的新公共文化外交活动,力争在重大外交政策问题上通过影响外国智库进而影响外国政府、媒体及普通民众。(5)要针对国外特定社会团体、社会群体(如侨民群体)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关键个体(如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名人),着眼于充分发挥好侨民群体的双向桥梁和纽带作用,策划与实施若干强调双向交流的微型新公共文化外交活动或项目。(6)积极向本国相关企业提供相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信息咨询服务,帮助相关文化传播企业“走出去”开拓国家市场并有效配合其开展相应的新公共文化外交活动。
4 总结与讨论
深度全球化特别是其核心主题的文化转向为当代图书馆拓展生成新公共文化外交功能提供了时代背景,作为公共文化空间和公共知识交流体系的独特存在方式则为当代图书馆拓展生成新公共文化外交功能提供了本体依据。然而,当代图书馆新公共文化外交功能的真正形成,尚有待各类图书馆紧密围绕“文化强国建设”这个中心,大力服务国家“新公共外交”这个大局,辨识明确该功能的基本培育路径,稳妥选择合适实施策略,采取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才能做出自己应有社会贡献。目前看来,多数图书馆全面培育并发挥该功能的诸多条件尚不成熟,但是,作为当代图书馆服务功能拓展的一个新发展趋势,的确值得业界密切关注和积极探索。
[1] 高飞.公共外交的界定形成条件及其作用[J].外交评论,2005(2):105-112.
[2] 李志永.公共外交相关概念辨析.外交评论[J],2009(2):57-65.
[3]常贝贝.冷战时期的美国图书馆——文化外交工具的历史考察[J].图书馆论坛,2015(5):119-124.
[4]蔡莉,沈虹,沈丽云,等.上海图书馆的公共外交实践与探索[J].图书馆杂志,2013(9):27-33.
[5] 潘拥军.试论图书馆与公共外交[J].图书馆论坛,2012(4):62-66.
[6] 赵启正,雷蔚真.中国公共外交发展报告(2015)[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7]段小虎,张梅,熊伟.重构图书馆空间的认知体系[J].图书与情报,2013(5):35-38.
[8]熊伟.2015年陕西省图书情报界中青年学术年会成果简报[J].科技文献信息管理,2016(1):62-64.
[9]梁灿兴.试论图书馆的公共性谱系[J].高校图书馆学报,2013(2):27-31.
[10]梁灿兴.新知识交流论(上):基于客观知识的交流类型辨识[J].图书馆,2013(4):1-3.
[11]梁灿兴.新知识交流论(下):图书馆是私域交流与公共交流连接的枢纽[J].图书馆,2014(2):1-3.
[12]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87-205.
[13]钟新,何娟.英国:从文化外交到公共外交的演进[J].国际新闻界,2010(7):19-26.
[14]钟新.新公共外交:软实力视野下的全民外交[J].现代传播,2011(8):51-55.
[15]郑华.新公共外交内涵对中国公共外交的启示[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4):143-153.
New Public Cultural Diplomacy Function of Contemporary Library:Cultivation Approaches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LUAN Juan,XIONG Wei
New public diplomacy which represents the universal diplomatic trend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in importanc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It become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global strategies in many countries.Modern library,as a public space for cultural and knowledge exchange,provides not only the new long-term carrier and fundamental support,but also a unique theoretical basis for new public cultural diplomacy.There are several basic approaches to cultivate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of modern library,for instance, the establishment of“opening-up”communication platform,“coming in”and“going out”programs.Based on its own actual situation,libraries of all kinds could choose the appropriate implementation strategy,like internal promotion,external cooperation and innovative reform,etc.
library function;new public cultural diplomacy;public cultural space;public knowledge exchange system
格式 栾娟,熊伟.当代图书馆新公共文化外交功能的培育路径与实施策略[J].图书馆论坛,2018(1):62-67,85.
栾娟,博士,长安大学图书馆馆员;熊伟,研究馆员,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图书文献与信息传播研究所常务所长。
2017-07-27
刘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