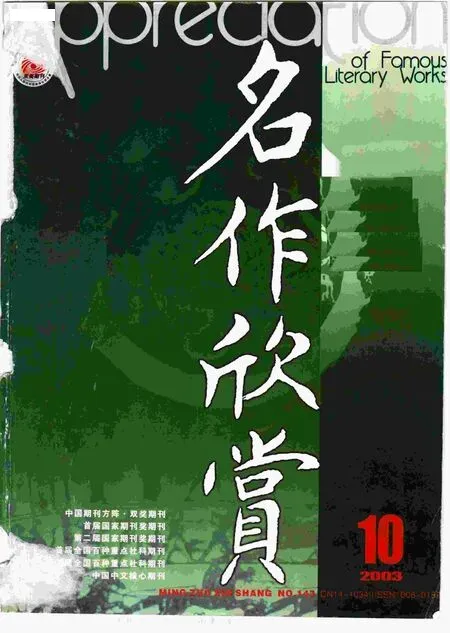陈冠中:我们这一代香港人
北京 赵稀方
作 者: 赵稀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代室主任,“20世纪海内外中文文学”重点学科负责人。著有《小说香港》《后殖民理论》《翻译现代性——晚清到五四的翻译研究》《历史与理论》等。
一
陈冠中是西西笔下的“我城”一代,他们都生在大陆,长在香港,在香港受的教育,因此认同香港,与他们的父辈拉开距离。20世纪70年代他们开始写作的时候,首次用作品表达出自己对于香港的认同感。不过,陈冠中虽然在70年代就开始写作,然而正式大量生产小说,却是“九七”之后的事情,因而他已经不单单表示认同,而是可以隔着二十年的历史重新反思他们这一代香港人。
在殖民地受教育,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腾飞中长大的新一代港人,具有鲜明的香港性特征。用陈冠中的话来说,他们这一代属于“什么都没发生的一代”。这里的“什么都没发生”主要指政治的空缺,即与大陆、台湾同一代比较,他们并无政治意识形态的负担,或者更简单地说,是没有历史,没有理想。
这一代港人是天生的经济理性人,并且在刚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就幸运地碰上香港的经济繁荣,“我们从小知道用最小的投资得到最优化的回报,而回报的量化,在学校是分数,在社会是钱。这成了我们的习性”。“我们是受过教育的一代,可训练性高,能做点事,讲点工作伦理。”①可以作为这一代港人代表的,是陈冠中的小说《什么都没有发生》中的男主人公张得志。张得志先是在非洲的一家公司,后来又到加拿大的一家公司,后来又去了印尼,中国台湾以至中国大陆。他有钱,但不是老板,只是为老板服务。创业家需要承担投资的风险,他没有这个勇气,却可以凭自己的技术拿稳定的高薪,这就是专业经理人。专业经理人正是香港的特产,“我们都是二把手。香港盛产我们这样的人,构成香港的比较优势”。
按照小说的看法,商人、生意人古已有之,专业经理人反倒是现代的产物。“我们会讲英文,会写字,懂得看资产负债表,可以在电脑上写营运计划,理解什么是内部回报率。我们看合约时会去看细文。”“我们用理性去帮公司达成目标:赚钱,占有市场,建立品牌,合并收购,上市,不管是用什么手段。”②专业经理人的特征是高度理性经济人,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他们为世界各地的公司服务,但目的只是赚钱,“我们不会被一些非理性的感情、喜恶、价值、对错、好坏所牵制”。在各个方面,他们都处理得干净利落,甚至于在性、感情等私人领域,也同样是如此。
《什么都没发生》(1999)的开头,张得志在超市遇见一位胸脯很丰满的女子和她的同伴私自夹带货品,被管理人员发现,幸而张得志及时出手替她们付账才得以解围。这种“侠义”行为,让他搭上了这个名叫沈英洁的女子。张得志平时解决性问题的方式,是叫小姐,付钱买性服务,钱货两清。这次却有点喜欢这个叫沈英洁的女子,第一次做爱,让他很有满足感:“她造爱时候的中国良家妇女动作和广州口音叫声,令我感到分外挑逗。”不过,完了之后,张得志却急于划清界限。冲动过去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立刻以专业的态度评估这种行为的后果。一方面喜欢、追求这个女人,另一方面却事后撇清,拒绝牵连。专业经理人的冷静和自私,尽显于此。
来自大陆的沈英洁却陷入了爱情,一次做爱之后,她对着张得志的耳朵说:“我爱你。”这句话却让张得志十分警惕:“我没有表示,本来礼貌上我应该说些话回应,但我没有,我的沉默应足够让英洁知道我不认为要把爱扯进来。”他最恐惧的,就是感情上的负担。并且,他对于沈英洁的激情也因为重复而消退了。他很快就假借出船为理由,离开了沈英洁,刻意没有留下任何地址。
当然,张得志并不是那种占便宜、耍无赖的人,专业经理人的特征是把一切就视为交换,公平交易。因此,他帮沈英洁付了半年房租,买了一点家具和衣服,经过精心计算两不相欠之后,他才离开。事实上,他并没有真正离开,而搬到了香港的另一个地方。这种难免被世人看作“负心”的行为,张得志却很满意:“我很满意自己对待英洁的态度。这次经验,证明我有坚定不移的意志,完全有能力掌控自己的感情。这是我十几年来努力的结果。我不会用感情去枷锁别人,自己也不会为情困。”
不过,一生以两不相欠、干净利落为目标的张得志,最终却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抱憾死去。张得志认为,他离开以后,沈英洁会有另外的男人。没想到十年后回到香港,他发现沈英洁居然把他所付的半年房租还给了他妹妹,并且还为他生了一个孩子,叫沈张。听到这个消息,他的第一反应仍是撇清责任:“我们不是订好了游戏规则吗?本来我愿意用套,她坚持说由她来避孕,这是我们的默契。如果她没有遵守,追究责任应是在她,不在我。”“我也不可不必操心,两年之间,她有能力把三万元还我,大概环境已不错了。”③不过,张得志的内心终究不安,他设计资助沈张去美国念书。然而,计划尚未落实,便死在枪弹之下。小说的开头,写张得志的弥留之际,为自己未能干干净净地死亡而不得安宁。
二
提到陈冠中,港人首先想起的是他在1976年创办的刊物《号外》。陈冠中从美国留学回来,看到香港严肃通俗两分,左右政治对立,没有中间灰色地带,于是想把他在美国看到的流行刊物如The Village Voice等带到香港来。《号外》一方面既讲哲学,谈马克思列宁主义,另一方面又讲disco,讲服装,讲明星,被称为香港正宗的雅皮士文化刊物。
雅皮士(Yuppies)是young urban professional的缩写,这个词在20世纪80年代诞生于美国,指的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住在大城市,有专业性工作而且生活很富裕的年轻人。他们去高档的餐厅,喝上等的酒,穿名牌的衣服,用顶级的化妆品,开豪华的轿车。张得志正属于这一类,我们在小说中看到,他受过高等教育,懂英文,服装都是名牌,藏有七百瓶法国红酒,穿行于世界各地,与各等上层人物打交道。不过,陈冠中却认为将《号外》称为雅皮士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它给《号外》带来了大量的广告收入,他更强调《号外》的波希米亚性质,如此就少了贵族气,而多了叛逆、边缘、颓废的味道。
读一读陈冠中写于当时(1978)的小说《太阳膏的梦》(《香港三部曲》之一),我们就会看到香港专业经理人的另一端——波希米亚精神。《太阳膏的梦》的主角宋家聪出身豪门,但厌倦上流社会精神。他有两个成功的兄长和三个成功的妹妹,在这种情况下,宋家聪愿意扮演败家子,“我还未能全面地与他们所代表的东西背道而驰,我只能证明我不及家族其他成员能干,头脑不如他们敏锐,态度不似他们踏实。更不用说,我的干劲分是负数。暂时,我只能证明我的不同。”在波士顿的时候,他喜欢在高速公路上开着1973年红色火鸟揸车。他的揸车,“不是为了表现自己的社会地位,高尚口味,男子气概”,相反,“我希望的是单独一个人,默默无声,不惹人注目。我揸车只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无能”。回到香港,无法再揸车了,他改成整天在浅水湾沙滩上晒太阳。他知道浅水湾有六个浮台、三个瞭望台、一百四十个垃圾桶,他熟悉太阳膏、肤色、名模、汽车牌子、修理游艇等,但在别人看来,这些都是无用的知识。
宋家聪看起来有点像是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像法国存在主义文学中的叛逆者,但他只是香港的产物,是对于香港专业经理人精神的背叛。他不想过于精明能干,把人生变成一场精心设计:“我不急于由A赶到B,我停滞不前以便好好欣赏路上的风光。”宋家聪明白,如果他表现得较有朝气,家族一定会逼他去观塘当制衣厂经理,或去旺角当酒楼董事。他害怕的是陷入他们的那套逻辑中去:“在成就趋向与快乐趋向,在商品规律与人文规律,在为将来而耕耘与为现在而生活之间,我要后者。我看穿了,家族那套逻辑的背后假设了多少人性的牺牲。”④宋家聪在小说中的结局是,在波士顿,他驾车撞大树自杀。
《太阳膏的梦》开头直接以“我”(宋家聪)的口吻叙述,表达他的对抗情绪,然而到了小说的结尾,却意外出现了另一个叙述者:“以上,就是我的亡友宋家聪了。”这个叙述者最后对于宋家聪的一生进行点评总结。这个叙述者看起来是一个正常的香港专业经理人,他对于宋家聪的行为不以为然,明确表达自己的选择是与社会妥协,并且满意自己的表现:“至于我,我的选择很简单:妥协。现在我是一个表现优良的银行行政人员。”
也斯在评论《太阳膏的梦》的时候,认为这个结尾表达了对于宋家聪的疏离,认为这种人无法适应现代社会。⑤这大概是一种“香港式”的读解,事实上这一结尾所展示的,是从波西米亚角度对于现代香港人的嘲弄和反讽。宋家聪的确是难以存活于香港的,因此到了《香港三部曲》之二《什么都没发生》,这最后一段的“我”就演变成了张得志,那里已经完全是他们专业经理人的世界了。
波西米亚为Bohemian的音译,原指流浪的吉卜赛人和颓废派的艺术家文化人,他们不受一般社会习俗的约束,与主流社会取向格格不入而自我放逐。陈冠中的波西米亚倒也不完全是这样。《号外》也谈政治——从香港到大陆——但是它不是理论的批判,而是戏拟、嘲弄,并且把它变成话题。《号外》虽然高品位,但并不排斥商业文化,它捧明星,谈服装等,既迎合又引导消费者。它既迎合又批判,既市场又精英,既通俗又严肃,是一种“四不像”,也即“杂种”。这样一种杂种文化,正是陈冠中近年来对于香港文化的新探索。自从日本竹内好提出“作为方法的亚洲”、沟口雄山提出“作为方法的中国”之后,近年来忽然流行将地域作为方法,陈冠中也不免俗,首次提出“香港作为方法”的说法。香港作为方法,其主要内容就是“杂种”。⑥
①陈冠中:《我这一代香港人》,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第7—8页。
②③陈冠中:《什么都没发生》,《香港三部曲》,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第15—153页,第15—153页。
④陈冠中:《太阳膏的梦》,《香港三部曲》,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第2—14页。
⑤也斯:《陈冠中写小说》,《香港三部曲——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第 vii-xvi。
⑥在《我这一代香港人》中,陈冠中收录了两篇《香港作为方法》的文章,可参阅。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