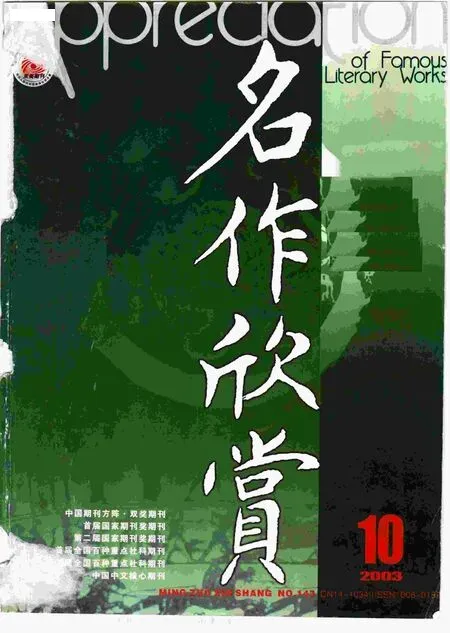陈国球:文学作为对抗黑暗之光
香港 许建业
作 者: 许建业,香港教育大学文学及文化学系博士,香港城市大学专上学院语文及传意学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批评、明清诗学等,著有《伪托文化底下题李攀龙编〈唐诗选〉的文本生成与诗学意义——以〈唐诗选玉〉及〈唐诗训解〉为考察对象》与《旧题李攀龙〈唐诗选〉的早期版本及接受现象》等。
镜花水月
“请坐,这位是语文学院的陈国球院长……”秘书小姐向我介绍道。陈老师坐在小圆桌子对面,和蔼地微笑着,眼镜与光交叠,透出智慧。第一次见陈老师,并不是入学申请,而是求职面试。时维2009年,老师和我碰巧都踏入人生另一页。那年年初,老师应聘从香港科技大学到香港教育学院(现正名为 “香港教育大学”)担任语文学院(现为 “人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讲座教授,主要工作是改革学院教研情况,以让学校符合正名“大学”的要求。夏天,刚刚本科毕业的我报读研究生失败,却幸运地赶上老师主持的研究项目招聘助理。于是,我这颗快要跌出学术之路的石子,由老师伸手捡拾回去。
研究项目是关于明代唐诗选本研究,我负责整理古籍和研究文献。顺理成章,往后随老师念博,论文题目也本乎此。明代诗学研究本身是老师进入学术界的试金石,硕士论文探讨晚明胡应麟的诗歌理论,博士论文承此广及明代复古派对唐诗学的传承。前者深刻而细致的思考和论述,以及擘画理论框架的书写方式,让人耳目一新;后者对明代复古派(格调派)研究也起了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我的研究兴趣是明清诗学,故在本科毕业前常翻看这两部专著。指导本科毕业论文的张少康老师得知我跟随陈老师工作,也替我高兴,还叮嘱道:“陈教授是古典诗学研究的专家,做学问很认真,眼界又很开阔,你要好好跟他学习。”
事实上,陈老师的学问兴趣不囿于古典诗学。他年轻时大量啃读“五四”作品,又受老师启发徜徉古典诗词的世界。特别爱诗歌,也耽迷于能帮助体味文学的理论和批评,1986年老师出版第一本论文集《镜花水月》,主要篇章都与文学理论批评有关。在他的思考之中,文学没有恒定的准则,而是如镜花水月般游移难测,论文集自序中便打比方道:“文学理论想探明何者为水中月,何者为镜中花;也关心水是清还是浑,镜是明还是昏。文学批评要知道水如何映月,镜如何照花;更追问水月是否宛然,镜花是否烂然。如何审视文学这面镜子,如何辨明水中镜外的二重世界,一直是我思索的问题。”老师跟我们畅谈文学话题,常提醒我们不要轻下判断,而要着意思考各种话语之间的上下牵系与彼此对应。但肯定的是,透过镜子我们可以发现别有天地,窥探古人诗心,还可以照见周折起伏的文学长河。亦因此,其思路便由文学批评趟开文学历史,从明代的胡应麟到布拉格的伏迪契卡,以西方铜鉴反照中国风景,开启了日后有关文学史书写的研究。
文学批评的视野向度,还由尺寸纸墨飞往加国的学术殿堂。前年我快要完成博士学位,与陈老师商量毕业后申请国外博士后的可能,于是他细述了当年在多伦多大学的游学经历。老师跟我说,到外国进修不应单纯求取履历的亮丽,而是真的能扩阔学术的眼界,让思考提升到另一个层次,选择导师必须慎重。当年老师钻研明代复古派的同时,还接触了不少西方理论如接受美学和结构主义等,尤其关注捷克布拉格学派。博士毕业后到香港浸会大学工作,获得当时系主任的信赖。期间更获得出国机会,知道布拉格学派学者Lubom í r Doležel教授在多伦多大学任教,便争取到那边求学。当时多伦多是文学理论专家的重镇,云集各国名师,除闻道于Lubom í r Doležel教授之余,也能沉浸在学者间的热烈论辩之中,这段游历着实让老师眼界大开。
一群热爱学问的人围在一起认真讨论,是陈老师时刻向往的情景。老师担任学院院长期间,在校内另外成立了“中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集合资源力量来处理大小研究项目和学术活动。他特别嘱我在研究中心协助组织一个恒常活动,那就是读书会。老师常分享自己的大学时光:香港大学是个风气自由的地方,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学习。老师当时跟不同专业爱好如历史、哲学等的同学定期读书,讨论问题。同一个文本,能从相异的立场、视野和知识范畴等碰撞想法,刺激思考,对于老师来说是十分美好的读书经验。后来,老师在台湾学界甚为活跃,并间中参与黄景进、柯庆明、颜昆阳、龚鹏程、蔡英俊诸位教授在台湾“清华大学”月涵堂举行的读书会。这些学者(包括陈老师)的不少研究成果,都是大家在月涵堂的清风朗月之下细心研磨、互相砥砺而来的。这亦是台湾地区学术界至今仍然传颂的佳话(老师称之为 “月涵堂神话”)。后来台湾政治大学的廖栋梁教授和曾守正教授继承此论学之风,举办名为 “百年论学”的公开论坛,定期邀请学者分享研究心得,与会者积极讨论,可谓每月之盛会(惜此论坛已于2016年停办)。陈老师既欣羡彼方学术交流之频繁,相得益彰;同时感叹香港各院校中文系甚少往来,基本上对彼此的研究发展都不大关心,不甚了解。老师希望在香港都能推动这种论学氛围,故亦有定期读书会之思。
老师曾总结,问学时主要受罗忼烈、黄兆杰、陈炳良等不同风格传统的教授影响,又与台湾地区学友交流互进,这些都是学术路途上的重要印迹。老师也涉猎西方文学理论,关心的始终是中国文学、香港文学。但这不是单纯的借鉴或撷取,用以映照或套用到中国的文学处境。事实上,老师是从更高的立足点投进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的视野。世界各地的文学文化当然特异,但他相信,文学反映人类的情感和思维,不论何时何地,彼此心灵都总有联系之处。老师希望把握这些共通的特质与规律,启发中国文学、香港文学的研究出路,并在世界文学的版图里安放适切的位置。
黑暗之光
2011年,我正式成为陈老师的学生。陈老师对博士生要求颇为严格,例如不建议研究生匆匆毕业,因为人文学科需要时间浸淫。台湾的博士生起码得熬过六七年才毕业,已是常态,香港的一般只消三四年便完成学位了。有一位老师跟他讨论,认为香港就业艰难,若拖延太久,也不容易。其实,老师十分关心和体谅学生的境况,能力所及会尽力帮忙的。而他更着紧的是,学生在毕业后的路途上如何走远,在学术圈中是否成熟以独自应付各种挑战。当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完结后,老师还特别训勉我说:“为学与做人,不完全等同,但一定有关联。放开心胸,多从不同角度思考,才能做比较合宜的判断。”至今,仍然感激老师这份对我这个不肖弟子的焦心。
除了把握年月积储知识、扎实根柢,老师更希望博士论文题目具有比较宏大的格局,且能开辟出新的渠道。老师本身便是从明代复古派诗论中,探析出独特的文学史和知识系统的建构意识,基于此再上下求索,便陆续编著《文学史》(与陈平原合编)、《中国文学史的省思》《文学史的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以至《文学如何成为知识?》等书。由单篇论文到规划成书,从清末的中国与现代的香港,各种应对和追问,自有其脉络与历程。张晖师兄曾指老师的学问是 “一以贯之”的思路,老师回应道: “起码是不彷徨的。”(《文学的力量:陈国球教授访谈录》)事实上,这条清醒的进路与老师的生命感怀和问题意识息息相关。2007年,老师出版第二本文学评论结集《情迷家国》,文章既是二十多年来对于“家”对于“国”,关乎“时”关乎“史”的一些“不得已、不能已的情怀”,实际也透露了研究重心转向“抒情传统”论的消息。“抒情传统”论近年颇受争议,但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影响不少台湾学人。其论奠基于留美汉学家陈世骧和高友工,起初是从世界文学的视野来反思和定位中国文学的本质。如陈老师所说,它不只在传统文化伤春悲秋的层次,反而是一种论述方式,虽不能用来解释中国文学的所有现象,但亦给予我们一些重新思考和诠释文学传统的角度和力量。其实,陈老师很早已接触陈世骧和高友工的文章,后来研究文学史时,便以此回溯书写者的生命焦虑与心灵踪迹。于是,林庚之诗歌情结、司马长风之文化怀想,他们书写文学史的情调和怀抱,皆成为老师从纸背后仔细审辩的音声。
前年夏天,我到北京出席一个研讨会。会上一位年轻学者与我边走边聊,突然提出“为何喜欢上研究古典文学”这样一个问题。他认为,大陆学者根于家国,潜心古典文学文化乃顺理成章,而他更以此为抱负;那么香港的学人研究古典文学背后会有什么怀抱?当时我反应不过来,后来又想到,老师或许也曾遇到这样的问题,他会怎样回应呢?事实上,老师常常追问,文学之于今日社会有何意义?文学研究除生产知识以外,还可以体现出更多的精神价值和人文关怀吗?应如何实践文学的所谓“大用”或“无用之用”,而不仅仅是堂皇的说辞?
老师曾直言,他研究现当代学者,特别着力追踪他们的习思培养与生命焦虑。对于抒情传统论述的投入,当不少研究以此回溯古典文学发展的各种周折时,老师却别有怀想,将眼睛移到提出这些论述的学人身上。老师之所以孜孜于陈世骧学问进路的爬抉,应是从中找到了某种私淑与契合。老师曾如此描写道:“事实上,陈世骧对中国抒情传统的体会,本就是从 ‘文学’与 ‘历史社会’、‘诗’与 ‘史’等的辩证思考而来。在他的人生旅程以至学术经历中,充满历史转角带来的感喟。……国族文化认同的起伏变化以及时世推移,种种悲怀莫遣,可能尽压在陈世骧庄严肃穆的文章纸背之下。”(《抒情中国论》)当然,彼此历史时空不可同日而语,然视陈世骧之若此,老师家国之叹亦几近是。也许,最令人潸然兴叹的是陈世骧英译陆机《文赋》时用上的标题: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文学作为对抗黑暗之光)。老师在不同场合都引用和强调这句话。对于老师而言,那点幽光既是心灵的安顿,也是坚持文学研究的信念。
事实上,那点幽光也可化作长衢燃灯,一传千百,赓续照远。佛家有所谓传灯,法师传法于徒,如灯传照。倬玮师兄和我曾私下讨论,陈门众子弟之中,老师的传灯者暂时独张晖师兄一人而已。晖师兄学术成绩卓异,年轻时已为学界肯定。但老师更为欣赏的是晖师兄的敦厚性格,以及 “把生命和生活经验相联系,和他完全投入的学术相连接”的态度,老师认为这样才能成为大学问家。坚守一方而精研细究的专家确是不易,但更难得的是做大学问,即将自身学问结合生命寻思和人文关怀的胸襟。老师和晖师兄都肯定,晖师兄是要做大学问的,在北京社科院燃起学问之光,将能照得更亮更远。(《怀人》)谁想到,天风暴殄,灭殁孤灯?
镜本无像
香港流行一个术语,叫作“少睡精英”。没想到我踏入社会工作不久就遇到一位,他就是陈老师。跟随老师当研究助理的一段日子里,中间收到他凌晨三四时寄来的电邮,但八时上班时间,却又看到他匆匆走进办公室,再拿着文件疾步往校长室开会。有时候,我整理资料几近午夜,正焦躁地赶尾班车,竟又瞥见老师穿着拖鞋在打印房转来转去。后来与老师闲聊,大概掌握他的作息时间分配。担任院长一职,加上带领改革学院,老师的行政事务特别烦琐,几乎占去白天所有时光。但他始终不忘研究,于是夜里勤勉地读书属文。曾试过赶稿子直到几道晨光撩动窗帘,但伸个腰,便又换上西装前往学校的会议。在这行政、学术两不忘的八年里,老师将自己的能量燃烧得更加旺盛。行政方面,让学院改革成功,协助学校正式正名为“大学”;学术方面,除主办几次工作坊和国际研讨会外,更先后完成抒情传统论述的整理和编纂(包括先后出版《抒情中国论》、与王德威教授合编的《抒情之现代性》),以及担任总主编,联合十多位香港学者出版《香港文学大系》(1949年之前)。
一位学院的高级主管曾问我:“陈院长的行政工作十分认真严谨,大小事情都准备充分,我们都十分欣赏。我不是学术中人,反而很好奇,他在学术界是很有影响力的吗?”这事我一直没告诉老师,恐怕老师听后亦啼笑皆非。他从不要求学术专业以外的人理解自己,但因为行政能力而对自己专业的事有兴趣,这亦肯定是意想不到的。其实,老师担任院长期间的私人秘书也曾提过这个疑问,但更多的是对老师的薄责:“他又接受一份学报的评审工作了!下星期还有排山倒海的会议,为什么就不懂得拒绝?”老师评审学报论文绝不含糊马虎,是否推荐刊登,都必定详细说明,以事理服人。而且,这也是观察不同范畴的发展的好机会,更应认真看待。后来,那位秘书似乎也被老师感染,跟我借《李白选集》来读,因为老师曾和她分享过李白作品的一些有趣地方。老师的克己和热忱往往是我们同门之间的话题,既由衷钦佩,也担心他累坏身体。在我印象中,老师担任院长初期不常生病,但一病便需住院或在家休养。后来真的把身子拖垮了,病痛倍多,也不得不推辞一些讲座或研讨会的邀请。不过,对比身体的疲惫,这几年精神上的各种焦虑和伤悲,更是难熬。
2013年先是与老师深有交谊的梁秉钧教授(笔名“也斯”)患癌离世;不数月,老师十分看重和怜惜的张晖师兄竟也因病而早夭了。晖师兄出事前不久,我们师生还愉快地在电邮讨论晖师兄快要访港,师门可以再好好聚旧。没想到几天后噩耗传来,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震撼,老师更是哀痛无比,连夜从台湾回港拿回乡证,再转往北京奔丧。
我最迟进师门,对晖师兄的印象只来自老师和其他师兄姐的零星描画,因为专业相近,便先找他的《诗史》(后来修订出版《中国“诗史”传统》)来读,心中一直叹服不已。直到2012年5月,才与晖师兄见面,当时他作为嘉宾学者到香港教育学院演讲,讲座后第二天我们师生数人一起游览龙跃头文物径,再到附近的蓬瀛仙馆品尝斋点。晖师兄谈吐极儒雅,总是微笑,且耐心地听着我一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老师就一个学术用语的翻译认真地询问晖师兄的意见,晖师兄思索一会儿便为老师下了决定。从二人的眼神可以感受到那份相知相得的温热。后来老师嘱我翻读《王阳明集》的《教条示龙场诸生》,读到“责善”篇“谏师之道,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耳”一段,我觉得晖师兄的学养和真诚,肯定已做到“责善”,已做到“谏师之道”。晖师兄不单是老师托以传续的星灯,也是一面朗润厚重的镜子。老师的镜子,不仅多面向地照见文学世界,也用来鉴明自身的得失。前些年老师探讨朱自清,特别细读其日记,放在心头好几次和我们分享的,是朱自清对于课堂准备的焦虑以及教学成效的反思检讨。朱自清苛求诸己的态度,与老师有某种迢远的接通。老师新近出版的散文集《香港·文学:影与响》,最后一章题曰“镜本无像”,主要辑录几篇关于老师学问的讨论和评价,以此作为“鉴照反思之资”。老师没有说明起题原因,这让我玄想不断。可能在老师看来,天下真有“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境界,自证自悟,何用鉴照?不过,他既以镜子探视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各种形相;亦十分明白,别人会同样拿着镜子对着自己的学问与言行上下打量。映示人前,不代表愈加刻意经营形象,而是更须明白所谓度己量人,会因点面之不同,形影之深浅,而难得全象。所以,为学做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同时换个角度看,既要理解别人的遭际处境,也要虚怀听取意见,检讨自身可以发挥的力量和意义。作家可以孤芳自赏,但学者绝不能遗世独立。正是因为“镜本无像”,才应该更加珍视别人的鉴照以及自我的省思。
2017 年初,老师尊敬的Lubom í r Doležel教授也溘然长逝了。哀伤之余,也忧心其对文学的深思能否沾溉后人。老师张看世间道,反顾林中路,四野萧散苍茫,影影绰绰。多少年来,在一道道文与字、家与国、教育与研究的风景中彳亍前进,但是,擎灯掌镜,幽人谁之?人文天柱,复伫何时?
唯在老师心怀间的文学抒情,始终烛光荧荧,镜影澄澄。他不忘等待,灯的故事;依然相信,文学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