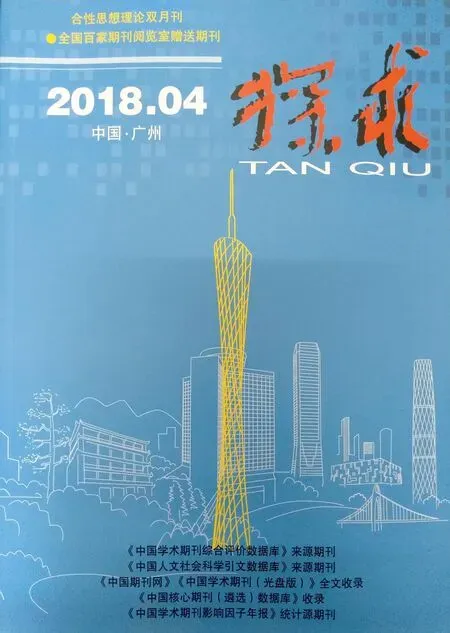毛泽东中西文化观探析
□亓娇
思想的产生往往缘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在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中不断建构的过程。毛泽东在走出韶山冲之前,无论是童蒙教育还是私塾教育,均以传统经典的学习为主,因此毛泽东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并试图从其中寻找复兴之道。走出韶山冲之后,随着资产阶级救亡图存运动的开展,西学激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兴趣并开始系统地学习西方文化,尤其是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更是进入了思想的迸发期,力求在诸多思想流派中糅合出适合中国发展的文化形态。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诸多政治实践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毛泽东坚定的思想指导,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更加科学、系统的中西文化观。虽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实践经验促使毛泽东作出了不同的文化选择,但他始终担负着同一个文化使命,就是复兴中华文化,以文化的复兴促进民族的崛起。
一、以辩证思维反思中西文化的独特品质
毛泽东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一直是理性的、辩证的,一方面充分认识和反思中西文化的不足;另一方面肯定了中西文化的独特品质,及其对世界文明的意义和价值。在反思批判的同时,肯定中西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是毛泽东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前提。
早在《讲堂录》中,毛泽东就曾以中医和西医为例进行比较,认为同为医道的中医和西医,各有所长。中医讲究气脉,西医讲究实验,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各有偏重。除此之外,毛泽东还指出了中西文化在思维方式与精神倾向上的差别,认为中国文化偏重“汉字”研究,西方文化则偏重科学研究。对汉字的过分研究,极易务虚,而侧重科学研究,则有利于适用于实践。另外,毛泽东还从学术的角度指出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他指出中国文化的创造注重师承关系,重门户,而西方文化则注重个性,注重独创。综观西方现代学术,大多数为个人所创造或构建,注重个性的彰显。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门户之争、派别之争,这种门派关系的约束,极大地限制了学术的自由发展。因此,毛泽东倡议:“著书之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振笔疾书,知有著书,而不知有他事,知有自我,而不知有他人。”[1](P247)在近代,虽然传统文化已经难以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纷纷掀起了学习西方文化的热潮,但毛泽东始终认为西方文化并非尽善尽美,与中国文化一样需要加以改造和变革。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写信给黎锦熙激烈批判传统思想的信中,也曾谈到:“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部分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他的好友张昆弟在同年9月16日的日记中做了如下记载:“毛君云: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2](P91)可见,无论是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毛泽东的态度都是极为理性的,这促使他在之后的文化选择和文化创造实践中,力求从现实需要和可行性出发,实现中西文化的融合。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曾指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共同构成了世界文明,而就东方文明来说,则就是中国文明。这成为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基本看法,而且贯穿一生。正是基于这一观点,无论青年时期的毛泽东还是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的毛泽东,都不曾对传统文化采取妄自菲薄的态度,一直将传统文化视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宝贵的精神遗产。正如特里尔所言,“不能撇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特点来解释毛的品格。”[3](P518)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可谓持久而深刻,无论其哲学思想还是治国方略、军事战术等,都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与创新。
二、以历史主义深耕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坚持历史主义是毛泽东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他一再强调要看到文化发展的历史性,不能一味地割裂文化发展的延续性,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极富优秀遗产和革命传统的文化古国。对于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能片面地轻视甚至抛弃,而应该予以总结和继承。没有旧的文化基础,就不会产生新的文化萌芽,更不会有新文化的发展和壮大,所以应该坚决抵制以今非古的态度,坚决反对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1939年1月17日,毛泽东在给何干之的信中,写道:“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4](P136),建议何干之对历史资料进行选择和编纂以促进党内对历史文化的学习。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提出,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是构建和发展新文化的必要条件。延安整风期间,针对党员缺乏中国历史与现状的研究,言必称希腊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必须要树立起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即既要了解外国,也要了解中国;既要研究外国革命史,也要研究中国革命史;既要立足于中国的现状,也要立足于中国的历史。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一直贯穿于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之中,并成为毛泽东从事文化研究和文化实践的基本方法。之后无论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是《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毛泽东一直强调学习和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对于构建新文化的重要性。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面临的中国国情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如果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不能脱离中国的历史和传统。1938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应当总结并继承传统文化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5](P533)
继承传统文化,就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深耕传统文化的创造力,延续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传统文化继承和创新方面,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以《实践论》与《矛盾论》为例,这两篇著作可以说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经典之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基本形成的标志。毛泽东通过这两篇著作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也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关系和辩证思维方式。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扬弃了传统的知行观,在实践的基础上解决了古典哲学中的知行关系问题,提出了“实践出真知”的观点,并揭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则用“天不变道也不变”来概括形而上学,用“相反相成”来概括了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等等,这实际上是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重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特刊》上曾题词“推陈出新”。这不仅是对中国平剧发展的指导性建议,而且是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要实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就必须以历史的观点来看待文化形态的形成与发展。肯定历史意义,发掘当代价值,这是借鉴和吸收传统文化的意义所在,也是进行新文化创造的必要条件。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作品创造,必须要借鉴和吸收一切优秀文化遗产中的有益部分。
总之,毛泽东在文化改革和文化建设实践中,并没有一味地否定传统文化,而是以历史的、辩证的态度来看待传统文化,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呈现了独特的中国风格,另一方面,以科学的理论改造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成为新文化建构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实现了“古为今用”的文化旨归。
三、以创新精神实现“洋为中用”的文化融合
“洋为中用”是毛泽东主张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的目的和意义。毛泽东认为,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借鉴首先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理论在一个社会中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这个社会的需要,这对文化而言同样如此。
1917年,毛泽东在给萧子升《一切入一》写的序言中曾言:“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1](P22)毛泽东认为,对西方文化应采取比较、借鉴的态度。针对当时的留洋热潮,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指出,虽然留过洋的人不在少数,但大多数人仍然是“糊涂”的,与其糊里糊涂地出洋留学,不如先吃透中国传统文化,弄清中国的国情。如果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缺乏了解,那么留洋也是一无所获,是盲目的。只有了解了中国的实际才能有选择地、有针对性地学习和利用西方文化,对中西方文化进行比较。
在如何吸收和运用西方文化的问题上,毛泽东则运用辩证法,从中西文化关系中存在的共性和个性展开了论述。毛泽东对“中体西用”中的“体”和“用”作了新的阐释。在他看来,中学与西学之间不是“体”与“用”的关系,“学”指的是基本理论。因此,中外是一致的,不分中西,但它们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具有各自不同的民族特点和风格。这就从哲学上指明了“华夷之辨”、“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等文化观点的形而上学性质。“华夷之辨”是片面地强调了中西文化的差别,而抹煞了二者的共同之处;“全盘西化”则与之相反,抹煞了中西文化所蕴含的民族特点;“中体西用”则是把中西文化的关系纳入到了体用、道器的关系之中。虽然这些主张各有特点,但都忽略了中西文化关系中的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这正是毛泽东在中西文化关系中所着重强调的。在毛泽东看来,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包含着共同规律与特殊规律的关系。而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全盘西化”与党内盛行的“全盘西化”,都是忽略了中国的民族特点,没有明确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因此,毛泽东认为应该以西方的一般科学原理来研究中国的问题,一般原理是中国和西方国家共同的,只是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民族特点。将一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则是为了创造和发展新的民族文化。不过,将西方文化融入到中国的新文化建设中并非简单的文化嫁接或移植,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在这个融合的过程中,民族的文化形式中可以混合一些西方的东西,可以存在一些不中不西的东西。“洋为中用”就是要在中国自己的文化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方文化中有用的部分,最终使中国的优秀文化与西方的优秀文化相融合,创造出既有别于西方,又能超越古代文化的现代新文化。但是,向西方学习并不意味着要“洋化”,而是以本民族的文化为主,以西方文化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就以音乐为例进行了说明。他提出,隋唐时期的九部乐、十部乐,大多是西域音乐,也有高丽、印度传来的外国音乐。但是,演奏外国音乐并没有让我们民族的音乐消亡,而是得到了继续发展。对于外国音乐,我们可以消化它,然后吸收它的长处。这不仅是毛泽东对音乐的态度,也体现了他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可以说,以辩证的、科学的态度来学习和运用西方文化,不仅不会损害中国文化的民族性,而且可以使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与世界性有效地统一起来,使我们的民族文化以更加辉煌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这既是我们批判地继承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指导,也是克服和抵制一切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
综上,毛泽东的中西文化观是在实践中形成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的科学理论,它之所以在今天仍然具有研究价值和借鉴意义,关键在于其思想的科学性与实践性。首先,这种科学性和实践性源于毛泽东独特的知识结构和实践经验。无论是其所处时代背景还是中西文化观的形成与发展,都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中西两大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以及在现代性之维下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超越。其次,毛泽东的中西文化观之所以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是因为他一生都致力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和改造,他的中西文化观是立足于中国社会实际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的文化理论。因此,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当代中国,必然能够成为指导中国文化发展的科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