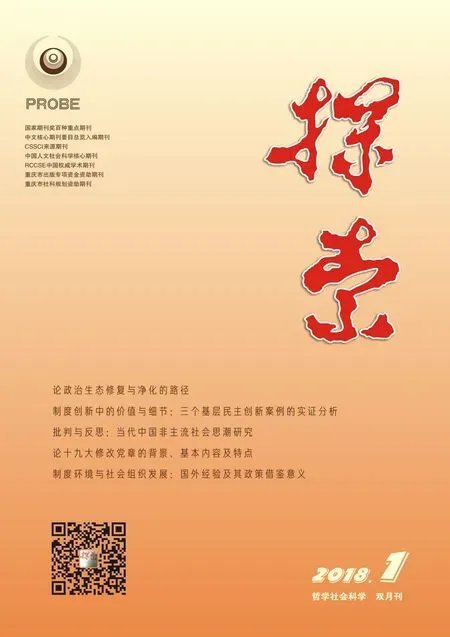大数据与民主实践的新范式
徐圣龙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互联网交往特别是移动终端的飞速发展,大数据开始从概念进入实践、从萌芽步入成长。根据麦肯锡在2011年发布的报告《大数据:下一个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前沿》,大数据被描述为这样一个数据集合——它已经超出既有软件工具获取、存储、管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范围[1]。当然,这一定义还只是停留于大数据的典型特征描述,但它无疑预示着生产能力和生产交往重组的必要性。正如戴维德·博利埃指出的,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和发展,产生了数不胜数的新的信息流、乃至信息的海洋……当这些数据库系统相互之间互联互通,以及数据分析软件设备和技术的更新使得更大规模数据分析成为可能,至此,一种新的‘知识基础设施’产生了,即‘大数据’时代的形成”[2]1。因此,大数据的关键在于提供一种全新的“知识基础设施”,而不是局限于作为既有生产能力和生产交往的附属物。这一点是理解大数据本质以及大数据区别于互联网经济的核心所在。面对大数据的冲击,既有生产能力和交往形式都开启了转型的趋势。根据《大数据图景2017》统计,在被调研的915家大数据公司中,涉及业务领域72个,其中,占比最高的是“安全领域”(共计36家,占比3.9%),占比最低的是“办公自动化支持”(共计3家,占比0.3%)[3]。在我国,大数据的发展也呈现快速成长趋势,据《中国大数据发展调查报告(2017年)》统计,“2016年中国大数据核心产业的市场规模约为168亿元,较2015年增速达45%”,“预计到2020年中国大数据市场规模将达到578亿元”,另外,大数据的应用主要集中于“营销分析、客户分析和内部运营管理”三个领域[4]5-8。可见,大数据的发展既广泛影响各个行业领域,同时也在重塑既有产业链条,孕育着全新的生产方式。
那么,在大数据冲击既有生产能力和生产交往的同时,政治交往层面是否也受到影响,特别是将大数据应用于政治过程中,是否会改变既有的政治交往实践?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因此,在承认大数据重塑生产能力和生产交往的基础上,基于物质生产能力和交往对于政治交往的影响,笔者尝试以政治民主实践为分析对象,探究大数据发展对于民主政治实践的影响。尤其是随着大数据逐步进入政治生活和政治系统之中,既有的民主政治实践是否会进行重组,是否会形成全新的民主实践形式。另外,假定全新的民主实践范式成为可能,在既有的条件下,大数据与民主的结合是否更好地实现民主、达致民主目标,抑或如某些学者所指责的——大数据会加剧不平等并威胁民主[5]。不管如何,大数据对于生产能力和交往的改变已经逐步成为事实,对于政治交往实践的重塑在不远的将来也将成为事实。因此,探究大数据对于民主政治实践的影响不过是迎来政治交往变迁的前奏,最终,需要做的是为大数据的发展营造有利的条件、破除各种障碍因素、避免潜在风险,积极推动大数据生产和交往以及大数据背景下政治交往和实践的向前发展。
1 大数据与民主实践新范式的生长
民主实践新范式的生长条件主要来源于网络民主的实践准备,但是又不局限于此。一方面,网络民主拓展了民主政治的空间和载体,通过互联网媒介这一新兴的形式,将现实政治中的民主活动在网络空间加以呈现,这为民主政治的多样化实践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未来的民主实践范式将延续民主政治的网络呈现,并通过将民主政治系列实践以数字化的方式加以存储、收集、整理和分析,优化民主进程,重塑民主实践。
1.1 网络民主的前期准备
生产改变交往,技术改变政治。马克思曾指出:“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其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6]498这里,技术构成“物质条件”的重要组成,而政治交往方式则是上层建筑的关键部分。其中,“物质条件”对上层建筑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换言之,技术变迁改变并影响着政治交往的方式。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方式发生着明显的改变,这种改变无疑包括政治交往在内。由此,开启了网络民主研究之先河。不管是肯定互联网对民主政治的正向作用,还是批评互联网民主政治中存在的各种负面效应,二者都必须承认,互联网改变民主实践已经成为一个事实。
不过,在既有的网络民主研究中,大多将互联网界定为民主媒介,即互联网依附于现实政治中的民主实践,并不能因此得出民主实践的新范式。网络民主并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和范畴而加以研究。比如,有学者将网络民主界定为“参与主体借助网络技术,以直接参与为主要形式,以高度互动为主要特征,以网络空间为载体,培育、强化和完善民主的过程”,并强调“网络民主不是独立的民主形态,而是媒介与民主新的结合形态,它的突出特性就是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对话的广场’和‘互动空间’,重现了‘广场政治’的某些要素,丰富和拓展了民主的内涵”[7]。由此可见,虚拟空间的网络民主一方面拓展了现实民主政治的时间和空间,增加了民主形式和载体的多样性;另一方面,网络民主在根本上不过是现实民主政治在网络层面的影像表达,它并没有超出现实民主实践的范畴,更没有确立民主实践的新范式。即使如此,网络民主还是将现实政治生活中民主实践的部分内容、环节以数字化的方式加以呈现,比如网络投票的统计、政治观点的表达、情感属性的分布等。这为后续民主实践系列活动的网络化、数字化转向提供了前期准备,也是全新民主实践范式得以运转的重要条件。
1.2 民主实践新范式的初步呈现
严格来说,互联网从产生开始,即构成了“物质条件”的重要组成,只是在互联网发展的初期,这一物质条件只能附属于既有的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民主实践的方式仍然延续现实政治中的民主逻辑,很难形成全新的民主实践范式。网络民主只是民主政治的“翻版”,改变仅限于内容更为丰富、形式更为活泼、载体更为多样。但是,大数据的出现正在改变这一依附状况。
首先,大数据脱胎于网络技术的发展并不断成长为独立的生产方式。大数据正在重塑既有各个行业领域、全部产业链的生产和交往活动,它为我们带来的不是一个内容更为丰富、内涵更为拓展的工业时代,而是一个重塑工业生产和交往方式之后的全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各个行业和领域的物质生产活动需要并可以通过“iGDP”加以衡量。其次,在大数据重塑生产和交往的同时,人类社会的政治活动也在发生相应的转型,民主交往不再局限于拓展形式和载体,而是要确立全新的民主实践范式。网络民主只是将现实政治中民主活动的部分内容、部分环节进行数字化处理和表达。但是,大数据会将民主实践系列活动进行数字化收集、存储、管理和分析,这一民主实践新范式的可能性正是建立在大数据对于整个社会生产和交往活动改变的基础之上。
正因为我们的生产交往活动是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之上,那么,民主实践就必须进行重塑,而这一重塑就是再造一个全新的民主实践范式。比如,在民主参与过程中,不能再局限于既有的上传下达、下情上传、投票选举等传统方式。一方面,原有的参与方式和参与渠道需要进行数字化改造,这在网络民主实践中已经部分完成;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除了传统的结构化参与方式之外,要更为重视非结构化方式的参与和表达,这是一种更为直观、直接的参与形式。例如,在某一问题上的态度或征集有关某一政策的建议,决策部门与公众的互动除了结构化的官方表达、征集意见、投票选择之外,还要重点分析有关这一问题或政策的非结构化参与,包括转发、评论、表情、视频等方面,并将其列为民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这一参与更为直接、直观,覆盖面广,更能反映社会公众的价值观念和选择偏好,它是公共活动有效性和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不管是结构化参与的数字处理,还是非结构化的数字处理,民主参与明显被重新定义——它不是现实民主政治为主、网络民主为辅,而是产生全新的民主实践范式。
2 大数据对既有民主议程的重塑
大数据对于民主实践的重塑覆盖民主活动的全过程。不同于网络民主仅对民主形式和载体的丰富与拓展,大数据实现了民主过程和民主结果的重新定义。在民主过程方面,大数据可以有效解决民主参与的两类难题:一是民主参与的不充分问题;二是民主不参与问题,即政治冷漠问题。在民主结果方面,大数据能够有效完成民主选择并重新定义一致性:一是有效避免民主选择困境;二是充分化解公意与众意的潜在冲突;三是避免少数意见被掩盖并建立相应的补偿机制。在此基础上,大数据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既有民主交往的全新民主实践范式。
2.1 大数据对民主参与充分性的重新定义
民主过程有两个层面的内涵。第一,民主是一个循序发展的渐进过程。比如,查尔斯·蒂利认为,“民主是一个现代的现象”,以法国为例,“在1789年之前,法国的政权从未接近民主的范围”,而“诸如1848年的广泛的革命和普法战争的惨败等政治冲击在加速法国民主化中起了不成比例的作用”[8]27-36。可见,政治民主在近代以来经历了从无到有的生长过程,民主的实现也需要由不充分到充分的过渡阶段。基于此,有学者提出,发展民主需要充分考虑民主生长的环境,强调“需要根据目的的不同而分别设定不同的路径,而不会试图依靠一套完备的政治制度和规则以不变应万变”,“民主是一个践行的过程,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民主是点滴式渐进的”[9]。在民主发展过程观念的引导下,民主在很多时候都是不充分的。不管是对于先发国家的民主发展还是对于转型国家的民主建设,民主参与考虑到制度的容纳性和有效性,并不允许所有社会成员立刻参与到民主过程之中。这就是民主参与的不充分问题。
第二,民主过程也指民主运行的过程。特别是随着选举民主流行开来以后,民主过程就意味着选举过程,选举过程强调公民参与投票。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过程导向的民主不仅仅关心决策过程或选举过程,而且更为强调“个体作为自由和独立的参与者,参与公共事务”,同时,过程导向的民主并没有忽视社会公共产品分配平等与公正这一总的目标,它只是不以牺牲差异性和多样性来达成公共目标[10]。但是,即使以公共产品分配平等与公正为目标约束,其目标实现多数时候仍然是建立在票决参与基础之上的。伴随着选举民主的发展,充分民主面临着另外一个难题,即政治不参与问题,也称之为政治冷漠。政治不参与的形成原因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民主参与机会和条件充分的背景下,政治不参与不利于民主目标的实现,也在不断侵蚀着民主实践的合法性基础。因此,解决民主不参与问题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那么,大数据如何有效应对民主参与的两类难题并重新定义民主过程?
对于第一类问题即民主参与不充分的问题,在现有的民主过程中,受制于结构和制度的容纳性限制,难以为社会中所有公民提供充分参与和表达的机会与条件。并且,在网络民主的背景下,即使所有社会成员得以充分参与和表达,在前大数据时代,也无法提供收集、存储、管理和分析这些数据的软硬件设施。正因为如此,不充分的民主、比例代表制、票决形式、网络民主补充形式等才成为民主参与的主要形式。大数据的出现,使得全员参与和表达成为可能。以现下流行的Hadoop为例,在数据存储和分析方面,HDFS和MapReduce分别实现了海量数据的存储和分析,比如MapReduce通过并行运行的方式,可以有效处理大规模数据集,这对于任何层面的民主参与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它真正实现了民主的充分参与、参与的充分有效,既可以避免民主参与受制于结构和制度的容纳性不足,也可以改变网络民主条件下充分参与不能有效存储和分析的难题。
对于第二类问题即民主不参与的问题,关键在于改变既有民主参与的结构化模式。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政治生活作为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公民不通过这种方式参与进来,那么,必然要通过其他路径参与进来。换言之,既有民主参与的结构化模式确实存在普遍的政治不参与和政治冷漠问题,但是这不能推导出公民的政治不参与。相反,在结构化参与模式之外,特别是伴随着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发展,公民政治参与开始呈现出普遍的半结构化、非结构化特征。网络民主之所以不能产生全新的民主实践范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网络民主附属于现实政治中的结构化民主参与模式,而忽略了越来越普遍的半结构化、非结构化参与渠道。大数据的出现,一方面在软硬件等方面提供了处理各类海量数据的技术支撑;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大数据将重新定义民主参与模式。在大数据条件下,民主参与在既有的结构化参与模式之外,半结构化参与、非结构化参与将越来越普遍,并被纳入到民主参与的组成部分之中。比如,在通常意义上的票决参与之外,公民(也是网民)可以通过转发、评论、文字、图片、动画、视频等多种形式和渠道,表达相应的政治态度和选择偏好,而这类态度和偏好同样构成民主参与的组成部分,是民主结果形成的必要参照。大数据的优势正是在于分析这类半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11]5,它们与结构化数据共同组成民主参与和表达的全部内容。
因此,大数据提供了民主充分参与及有效分析的技术条件,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定义民主参与的模式,即民主参与既包括结构化参与模式,也涵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参与模式,它们共同组成民主参与的内容和民主合法性的基础。
2.2 大数据对民主结果一致性的重新定义
民主结果,又称结果导向的民主,其强调“整体意志和利益协调”[10],即民主结果的一致性。在既有的民主实践过程中,民主结果与民主过程很多时候是被割裂开来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多数学者担心过分强调民主结果的一致性必然会损害民主过程中的独立性和多样性。比如朱莉·莫斯托夫就认为,一致决定有助于结果导向的民主的实现,但是,在民主活动中,它很多时候都演变为一种强制。因此,民主应该建立在允许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民主过程基础之上,并尽可能达成一致性目标。当然,在过程民主与结果民主相结合的过程中,还需要解决个体的平等性和独立性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关系层面[10]。可是,一方面,民主过程与民主结果的割裂并不符合民主的完整内涵;另一方面,即使承认过程与结果的分立,在达成民主结果一致性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难题。
第一,基于个体选择偏好和差异性的民主过程,并不一定能够达成一致的民主结果。这是典型的民主选择困境。比如,阿罗假定在民主条件下,在涉及许多人不同意志的集体选择中“个人选择和社会选择的协调性”[12]4是否存在值得怀疑。在此基础上,阿罗提出了著名的不可能性定理,即甲、乙、丙三人面对方案 A、B、C,出现了{{A>B>C},{B>C>A},{C>A>B}}的选择偏好排序,而这一选择偏好正是建立在民主过程中的独立性和多样性基础上,却无法完成民主结果输出,更不要说一致性的民主结果。换言之,在现实的民主实践过程中,完全可能存在无法达成民主结果的情境,这使得民主实践呈现极为尴尬的一面。
第二,在民主过程通向民主结果的路径中,存在多数选择或公众选择与公共利益相背离的情况,即众意与公意的潜在矛盾。卢梭曾明确提出了众意与公意的区分,“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13]35,这意味着民主过程的多数意志完全有可能不符合公共意志,反而可能是个别意志对于公共意志的侵占。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卢梭提出的基本设想是,“人民能够充分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公民彼此之间又没有任何勾结;那么从大量的小分歧中总可以产生公意”[13]36。可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这一充分了解情况并基于理性的讨论是很难实现的。即使信息充分,也很难避免政治派系、政治煽动等对于多数意志的控制和引导,这意味着在票决民主过程中,民主结果有可能背离民主本身。
第三,在民主结果方面,遵循多数原则的民主一致性结果容易掩盖少数意见,并且少数意见有时候是无法纳入民主议程的,特别是在结构化民主参与模式中,这导致各类冲破既有民主实践的参与形式和表达方式。首先,民主议程中需要呈现少数意见;其次,在少数意见呈现与多数结果的关系处理上,应该做到不以牺牲少数意见为代价。正如托克维尔在分析美国民主时所指出的,“我最担心于美国的,并不在于它推行极端的民主,而在于它反对暴政的措施太少”[14]290。这里,“暴政”指的就是多数结果,而作为少数,如果缺乏必要的保护措施,很可能成为多数结果的牺牲品。因此,衡量民主结果一致性的关键标准,不在于整体一致性,而在于遵循公意的前提下,是否存在避免少数意见被掩盖乃至被牺牲的制度设计。可是,这与民主的完整内涵还有不少差距,少数意见除了不能被掩盖和不被牺牲之外,更应该体现于民主议程之中,并协调好与一致性民主结果的关系。
既有民主实践在民主结果方面的三类难题,既有可能割裂民主过程与民主结果的紧密联系,也有可能造成民主结果输出的困难,同时还存在多数意志与公共意志的背离、多数结果与少数意见的冲突等。那么,大数据的出现如何应对民主结果方面的三类难题,并重新定义民主结果的一致性?
对于第一类问题即建立在选择偏好基础上的民主过程无法输出民主结果,这是一类小概率事件但却又是可能发生的民主受阻。个体选择与社会选择如何协调一致,并达成相应的民主结果,大数据主要通过趋势预测来避免这一民主选择困境。首先,在假定公共利益无根本冲突的基础上,通过备选方案置于公共空间并加以充分讨论,搜集、分析社会成员对于不同方案的态度、立场和意见,并预测可能出现的选择僵局。在此基础上,修正方案内容或调整备选方案数量,以期输出民主结果。大数据从其产生开始,即以预测作为其核心功能设定[15]16,通过非结构化数据的搜集、处理和分析,可以预判事物的发展趋势和可能结果。这意味着,在大数据条件下,民主选择并不是从结构化的投票选择开始,而是从投票之前的方案设定就已经开始了民主选择过程。个体选择与社会选择的关系在民主运行过程中,还需要加入个体与选择对象互动这一变量关系,即个体选择(个体→←对象)→社会选择。当出现类似的投票悖论时,大数据可以预判选择僵局,自动调整或修正备选方案,以完成民主结果输出。
对于第二类问题即公意与众意的潜在冲突难题,这可能导致民主结果的多数决定背离公共利益。这类问题的产生,主要在于既有民主选择过程的二分逻辑。卢梭已明确指出,公意的达成离不开个体的参与,个体参与实现公意离不开充分的情况了解和讨论。但是,在现有的民主选举过程中,民主选择基本都以“是/否”“支持/反对”这一“非此即彼”的形式加以呈现,公民缺乏充分了解情况、特别是充分讨论的机会和条件,即使公民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在前大数据时代也无法实现全部意见的搜集、存储、整理和分析,并将“是/否”“支持/反对”的内涵充分展开,比如是否一揽子肯定、肯定什么、肯定的依据是什么,等等,这都是实现公意凝练的必要基础。大数据的优势正是在于可以充分展开“是/否”“支持/反对”的丰富内涵,比如,通过数据挖掘的方式发现“是”与{a1,b1,c1…}之间的关系、“否”与{a2,b2,c2…}之间的关系。这时,公意形成就不再是简单的“是/否”二元选择,而是“是”“否”的合理性讨论,最后的选择结果也是基于这种合理性的非结构化分析。在此基础上,众意不再是简单地通过投票做出取舍或“数人头”,而是个体充分参与、讨论并凝练公意的过程。
对于第三类问题即少数意见被掩盖的问题,民主结果一般很难是全体一致的结果,它必然存在个体性和多样性,大数据所定义的民主结果并不否认这一点,它只是在更好地达成这一点上做出相应的安排。在既有民主实践中,多数原则是衡量民主结果的关键指标,不管是绝对多数还是相对多数。但是,很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少数意见被掩盖,甚至被牺牲。在无法保证全体一致的情况下,一方面,充分吸纳个体参与、讨论,并逐步形成民主结果;另一方面,作为民主结果的必要组成,少数意见呈现于民主议程之中。大数据提供了“捕捉”少数意见的技术条件,并清晰展示少数意见的关联性因素。在输出民主结果中,少数意见并不是可以被自动忽略,甚至被牺牲的部分;相反,少数意见会被纳入民主议程。当民主结果与少数意见存在冲突时,需要以少数意见的关联性因素为基础,做出相应的补偿性机制安排。民主结果与少数意见之所以可以共存于民主议程之中,前提在于个体之间在公共利益上的根本一致。大数据分析的结果输出,既输出一致性结果,也输出少数意见,并且,少数意见是可以被感知并被理解的。
因此,大数据保证了民主结果的输出,并充分挖掘个体选择的关联性因素,在此基础上,形成民主的公意结果。这一公意由个体的充分参与、讨论凝练而来,它并不否定少数意见的存在,并将少数意见纳入民主议程。大数据分析的结果是承认公意与理解少数的结合体,这里,民主结果一致性的内涵得到重新定义。
3 民主实践新范式的发展障碍和潜在风险
大数据条件下的民主实践新范式,产生于物质条件改变所带来的政治交往方式变迁。大数据有助于化解既有民主政治实践中所存在的系列困难,并重新定义民主议程。不过,作为一种独立的民主范式,其发展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在推动全新民主实践范式发展的过程中,它还面临着一系列的障碍因素和潜在风险。这类障碍因素的破解和风险的化解,是民主实践新范式成长、成熟、完善的必要步骤。
3.1 大数据发展不充分制约民主实践新范式的成长
全新民主实践范式的发展离不开大数据的进步,这意味着生产和生活中的一切观念、偏好、行动等,都可以通过数据或符号加以表达。伴随着数据处理软硬件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数据互联互通的实现,民主实践新范式才真正成为可能。但是,目前中国的大数据发展还存在两方面的不足,这些不足严重制约了民主实践新范式的有效成长。
第一,大数据应用的不足容易造成民主实践新范式的数据准备不充分。大数据条件下,全新的民主实践范式依赖于民主全过程的数据存储、收集、整理和分析,这意味着需要充分的互联网化,并有效地将公民的行为、偏好、价值、观念等转化为可供处理的数据或符号。但是,在我国,网络发展目前还存在不充分和不平衡的问题,这将直接制约民主实践过程中的数据准备工作。一方面,我国的互联网普及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根据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10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16]。不过,相比发达国家70%左右的网络普及率,我国只有部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达到了相应水平,比如北京、上海等。另一方面,我国的互联网发展还存在较为严重的不平衡问题,包括城乡不平衡和地区不平衡。比如,在城乡差距方面,农村互联网普及率截至2016年6月为31.7%,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超过农村地区35.6个百分点,城乡差距仍然较大[16]。再如,在地区差距方面,只有10个省(直辖市)的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除了四川省和重庆市外,其他8个省(直辖市)都属东部地区,移动宽带普及率方面,有12个省(直辖市)的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多为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东部地区[17]。这一系列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直接影响了大数据条件下民主实践过程中的数据准备工作。离开了充分数据,民主实践新范式将缺少实践的前提性条件。
第二,数据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的不足容易导致民主实践新范式的数据准备割裂,无法有效展开后续的民主实践。大数据条件下,充分数据除了民主全过程的数据搜集、存储、管理和分析之外,还需要尽量避免数据之间的割裂。换言之,对于不同层面的民主实践而言,它需要确保民主范围内的数据共享和数据之间的互联互通。否则,割裂的数据将直接导致后续民主实践无法有效展开。但是,在我国目前还存在着普遍的“信息孤岛”现象,从技术层面到利益层面,信息孤岛问题的破解是民主实践新范式得以成长的必要条件。比如,在技术层面上,不同部门的数据储存在不同地方,格式也不一样,这就使得数据整合起来出现困难;在利益层面上,由于政府部门之间、企业之间、政府和企业间信息不对称、法律制度不健全、缺乏公共平台和共享渠道等多重因素,导致大量政府数据存在“不愿公开、不敢公开、不能公开、不会公开”的问题,人为制造数据隔阂和信息孤岛[18]。大数据条件下的民主实践必然涉及不同主体,如政府、公民、社会组织、企业,也要求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商,民主范围内的数据割裂必然造成民主实践的困难。有效解决信息孤岛问题,实现民主范围内数据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是推动大数据条件下民主发展的必要环节。
3.2 大数据公共平台建设不足影响民主实践新范式的有效展开
民主实践新范式得以可能,除了大数据自身充分发展之外,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那就是民主实践大数据平台的支撑。公民的政治参与以及民主结果的输出,最终都需要接入公共数据平台并处于严格的监督之下。不管是政府主导建设的民主实践数据平台,还是第三方组织或机构承担的大数据平台建设,都存在相应的法律边界和伦理边界,以使民主实践的大数据平台服务于公共利益。
目前,在我国,大数据的公共平台建设主要由政府承担。但是,政府在发展公共性大数据平台应用中,还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这对于推动大数据条件下民主实践的有效展开造成了障碍。
一是政府大数据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侧重于重点领域和重要部门,缺乏统一的大数据公共平台,尤其缺乏针对民主实践的大数据平台建设。根据2015年《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现有的大数据公共平台主要集中在“社会治理新模式”“经济运行新机制”“民生服务新体系”“创新驱动新格局”和“产业发展新生态”五个方面。对于民主实践的公共数据平台建设,零散分布于社会治理新模式和民生服务新体系建设之中,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民主实践新范式的有效展开,以公共的大数据平台为载体,并且针对不同的民主范围和民主领域,还需要有针对性的大数据平台。在大数据条件下,从民主实践的前期准备,到民主过程的充分参与,再到民主结果的有效输出,涉及的系列数据处理都离不开公共数据平台的支撑。因此,积极推动围绕民主实践的公共数据平台建设,充分吸纳多方力量的参与,保证民主实践新范式的有效展开,这就显得必要和迫切。
二是围绕公共数据平台的法律制度建设存在不足,尤其是服务于公共目标的数据搜集、存储、管理和分析规范建设,包括制度规范和伦理约束。对于民主实践的大数据平台而言,关键在于厘清民主实践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大数据条件下,民主实践围绕公民活动展开。虽然大数据平台在具体运行过程中,会有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主体等参与其中,但是,大数据公共平台最终是服务于公民民主生活的,不受其他因素干扰。面对政府权力和市场力量的优势地位,公民民主权利如何在公共数据平台中得到保证,这就需要相应的制度规范和伦理约束,从而明晰公民、政府以及市场之间的关系。同时,这也是保证公民民主活动在大数据条件下有序展开的制度条件。但是,在我国,目前还缺乏涉及公共数据平台的完整法规制度及伦理共识,这经常造成政府权力、市场力量以及第三方组织的干预和介入,从而影响到公共性的实现。对于民主实践新范式而言,离开了制度保障和伦理约束的公共数据平台,自然无法保证公民民主活动的公共性,更无法有效展开大数据条件下的民主实践优势。因此,在民主实践的公共大数据平台之外,还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制度规范和伦理约束。
3.3 大数据条件下民主实践过程中的控制权风险及其规避
民主实践的控制权问题,主要涉及公民的自主性。在实现大数据充分发展以及确保大数据平台公共性的条件下,需要处理好大数据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大数据是服务于公民民主交往,而不是反过来控制民主交往。
目前,对于大数据控制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府权力集中和政治操控,包括满足于私人利益。比如,有学者提出“被设计的社会”和“被设计的公民”等概念,其认为,“在‘驱动’的名义下,政府会倾向于通过‘驱动’实现公民更健康、更友好的行为表现——这不过是现代形式的家长制”,“保姆式政府不仅关心我们做什么,而且关心我们做出所谓正确的事情”[19],大数据使得这种政治控制在更大范围内、更深层次得以实现。因此,在未来,完全有可能出现一个“数据之王”,它不通过民主参与的过程就可以实现更有效的大众管理[19]。可见,这与民主实践的公意目标完全相悖。不过,笔者认为,通过制度规范和伦理规范,限制市场资本的参与、规范政府权力的运行,基本可以确保民主实践大数据平台的公共性,服务于民主的公意目标,避免所谓“数据之王”的出现。
只是,在解决了市场资本和政府权力对于民主实践新范式的潜在威胁之后,要想真正化解民主控制权的风险,根本在于解决公民的自主性问题,即大数据条件下公民的民主能力建设。民主实践的控制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外部威胁,如政府集权和操控、市场资本干预等;二是内部威胁,即公民民主权利实现的能力匮乏。如果公民缺乏大数据条件下相应的民主能力,那么,即使不存在外部威胁,也无法保证民主实践的有效性,更无法保证民主实践的控制权。因此,培育公民在大数据条件下相应的民主能力,对于发展民主实践的新范式不可或缺。这里,可以借鉴一些学者提出的富有启发性的建议,主要针对公民在大数据条件下民主能力的学习和培养,包括“不断实现信息系统运转的去中心化;支持信息的自我决定和参与;为了获得更大信任必须提高透明度;减少信息扭曲和污染;提供用户控制的信息过滤器;支持社会和经济多样性;提高互用性和合作性机会;提供数字助手和协调工具;支持集体智慧;通过数字能力和数字启蒙,推进公民在数字世界的负责任行为”等[19]。其中,公民在“数字世界”中的“数字能力”构成自主性的关键,它也是民主实践新范式规避控制权风险的重要保障。
4 结语
大数据对于生产能力和交往方式的改变,在政治层面直接表现为民主实践范式的转换,即民主实践新范式开始生长。区别于现实政治中的民主实践及其网络民主的补充形式,大数据对民主的过程和结果都将重新定义。在民主过程方面,区别于既有的结构化参与模式,通过大数据技术,使得结构化参与、半结构化参与和非结构化参与成为可能,并行之有效,民主参与的充分性得以体现。在民主结果方面,可以避免民主结果输出困境,同时将民主选择及其关联性要素纳入民主过程,由众意到公意的民主结果输出得以可能。基于此,大数据将重塑既有的民主政治实践,确立全新的民主实践范式。
不过,对于民主实践新范式的怀疑从其产生开始就一直紧随其后。特别是在大数据促进民主实践范式转换方面,不少学者担心大数据不仅不会带来全新的民主实践范式,不会造成民主更好地实现,相反,其可能加剧不平等并威胁到现有的民主交往。比如,凯茜·奥尼尔(Cathy O’Neil)就提出了“数学杀伤性武器”概念,其认为,数字及数学模型在宣扬高效和公平的同时,“会扭曲教育、推高债务、鼓励监禁、处处牺牲穷人、并破坏民主”[5]175,特别是大数据与数学模型的结合,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不平等、威胁民主。这类观点有其合理性,但是,不平等的加剧和民主的削弱并不是大数据引起的。相反,大数据在解决既有民主实践的系列难题方面,提供了诸多可能并可能重新定义民主。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主作为一种公共活动,是以公共利益作为目标约束的,现实社会中的利益分化和对立必然导致民主失灵。因此,解决利益分化和利益对立才是民主有效展开的基础性条件,而大数据条件下民主实践的新范式正是需要建立在此基础上,并实现对民主的重新定义。
[1]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Big Data: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EB/OL].(2011-06).http://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digital-mckinsey/our-insights/big-data-the-next-frontier-for-innovation.
[2]BOLLIER D.The Promise and Peril of Big Data[M].Washington,DC:The Aspen Institute,2010.
[3]TURCK M.Firing on All Cylinders:The 2017 Big Data Landscape[EB/OL].(2017-04-05).http://mattturck.com/bigdata2017/.
[4]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大数据发展调查报告(2017年)[R].北京: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17.
[5]O’NEIL C.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How Big Data Increases Inequality and Threatens Democracy[M].New York:Crowns Publishers,2016.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郭小安.网络民主的概念界定及辨析[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9(3):24-31.
[8]查尔斯·蒂利.民主[M].魏洪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9]程同顺,张国军.民主的回归——从选举民主到过程民主[J].探索,2012(1):53-59.
[10]MOSTOV J.Karl Marx as Democratic Theorist[J].Polity,1989(2):195-212.
[11]汤姆·怀特.Hadoop权威指南[M].周敏奇,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12]肯尼思·阿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M].陈志武,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13]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4]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5]维克多·迈尔-舍恩伯格,等.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盛杨燕,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
[16]CNNIC.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6-08-03).http://www.cnnic.net.cn/gywm/xwzx/rdxw/2016/201608/t20160803_54389.htm.
[17]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宽带普及率已达60%左右地区分化很大[EB/OL].(2016-08-12).http://money.163.com/16/0812/15/BU9EDTSJ00253B0H.html.
[18]大数据观察.大数据信息孤岛、技术不足、人才缺失问题亟须解决[EB/OL].(2017-07-11).http://www.sohu.com/a/156161536_398736.
[19]HELBING D,etc.Will Democracy Survive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EB/OL].(2017-02-25).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will-democracy-survive-big-data-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