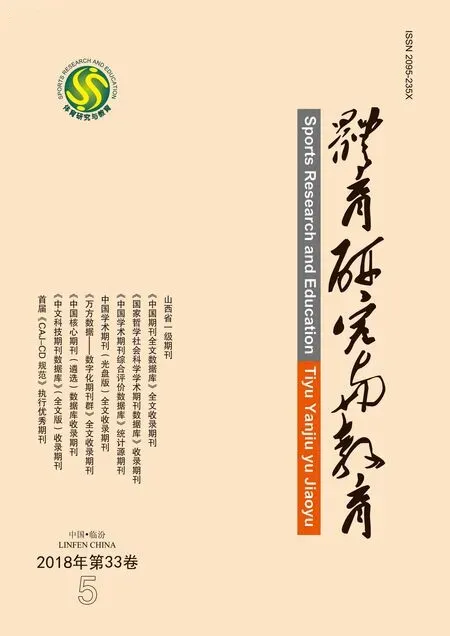民俗体育的学术史回顾
——兼论晋地民俗体育治学的发展及走向
王若光,张 凯,彭 欣,梁雅婷,逯文莉
1 民俗体育的学术肇始
古时虽无体育概念、科学研究范式也尚未形成,但有关民俗体育项目整理、拾遗或考录的传统古已有之,相关文章著述确已形成。宋代调露子所撰的《角力记》[1]即是有关民俗体育的一篇专学文章。文章字量非甚,但对我国古代摔跤运动的称谓、流源、纪事、杂说趣闻等作了细致的叙述;宋代李清照的《马戏图谱》[2]明代佚名的《丸经》[3]《蹴鞠谱》[4]等著述均专注具体活动进行了详细的文字记录。文本为我们展示了古人参与某类体育活动的考究,如场地、器械、行为、规则等方面的问题。古代文本中均作了细致入微的描述。此外,对参与体育活动的道德规范性的论述更是事无巨细,民俗体育参与的道德教化功能彰显无疑。明代学人杨嗣昌的《武陵竞渡略》亦是民俗体育的考录之作。作者以个人旨趣为导向,将目光瞄向武陵地区盛行的竞渡习俗。作者不仅引经据典地讨论了竞渡的起源问题,而且还通过个人长期的参与性观察极为细致地描述了武陵地区竞渡的组织、机制、流程、规模、规则、训练、技术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注意到当时竞渡在民间常常出现的社会负面问题,如竞渡有可能引发地方民众寻衅滋事、集体斗殴的社会风险,以及官方主流常采用的治理措施,并在此事实基础上提出了充满人文关怀的民俗体育治理观点:“杀其力,存其戏”。[5]体育活动本为古代士林之边鄙,文献非甚。他们的留存为民国学术开创及当代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文本。
1926年我国著名民俗学家江绍原先生在《晨报副刊》上刊发《端午竞渡的本意》一文。江绍原在《端午竞渡的本意》中对《武陵竞渡略》作评价时认为:“作者没有学术的眼光”,误导了我们对竞渡习俗本意的认识。[6]但笔者看来杨嗣昌的现代学术价值更甚,拿杨、江二人的原版文本比照,发现《武陵竞渡略》并没有误导竞渡习俗本意的嫌疑,而是江绍原“误解”了杨嗣昌。这一点也再次被现代民俗文献学学者所证明。[7]目前,学界有关“龙舟竞渡”专题的学术成果对《武陵竞渡略》进行有效深入剖析及消化吸收者不多见,其中许多具有学术价值的信息未予以重视,仅有学者江绍原以《武陵竞渡略》为主要分析文本,可以算得上近代以来民俗体育个案研究的开创性学术作品。近年来,张勃[8]、王若光[9]等也开始分别从民俗及竞技的视角关注《武陵竞渡略》的学术意义。1947年闻一多在《中兴周刊》与《文学杂志》分别发表《端午的历史教育》[10]及《端午考》[11]两篇文章。闻一多从民族或国家层面探究端午竞渡习俗的文化价值,提出龙图腾为中华民族共同凝聚的族徽象征,竞渡的本意虽不是拯觅屈原,但这种纪念屈原所体现的爱国情感是值得肯定的,具有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如果说江绍原的个案研究是历史实证主义经典,那么闻一多的研究则是历史价值主义的典范。两位学者的研究虽时隔仅21年,但二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差异甚大。从研究的方法上看江绍原与闻一多的研究虽受到过正统的学术训练,但研究层次仍停留在以典籍文献为主的个案研究,仍然沿袭着民俗研究的“一重立证法”的方法论思想,某种意义上尚未超越明代杨嗣昌的“书写”策略。
鉴于民国期间,内忧外患,特别在1930年代后期,民国体育学科尚处在发展初期。绝大多数体育学人多将学术旨趣集中在体育教育范围之内,涉及武术研究较多,如唐豪、张之江、褚民谊等学人的武术相关著述多达数十部,其中不乏提倡“国术救国”的教育理念,亦不乏教授拳术技法之作。而对于处于民间种类繁多的民俗体育事象研究尚未形成有序且具规模的研究脉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的王健吾、金铁盦在1935年所作的《毽子谱》[12]和《风筝谱》[13]。作者在“民族积弱”“倡体育普及”的社会背景下专注体育品类中微小却极易普及之项目,对毽子与风筝运动作了细致的源流考据、习俗分析、功能辩证等讨论,并且针对广大民众服务,将毽子与风筝的制作方法及运动技法问题予以了详细的描述。
质言之,古代民俗体育文本的留存为我们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字史料,值得学界广泛重视。民国的相关研究是基于古代典籍文献而开创了本土体育的学术先河,奠定了当代民俗体育学术发展的基础。
2 民俗体育的学术暂裂及成熟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大背景下,民间体育研究非但未被学人重视,反而被社会各个层面多冠以迷信、旧俗的标签所遗弃。经历了短暂的30年集体化时期,直至1980年代,国家“文化热”兴起,体育学科研究再度多元化。一批体育史研究方向的学者逐渐开始对民间、民俗及民族传统体育进行系统的探讨与梳理。
1990年中国体育史学会编写的《中国古代体育史》是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立以来的首部系统性著作。该作品将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形态、历史流变及时代特征等做出了全局性探讨。其中对于我国具有典范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如养生、武艺、蹴鞠、舞蹈、角抵、击鞠、捶丸等,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并且对同一项目结合不同时代背景特征做了进一步的细致探讨。[14]1997年,翁士勋主编了《二十五史体育史料汇编》(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5]著作将权威的二十五史作为史料资源,对散见于其中的体育材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虽然该著作在个别条目归类、体例统一、选录标准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在总体上却将权威文本中有关的体育材料分门别类、梳理得当,为后续体育文史类研究者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除此之外,上世纪末还有不少有关中国传统体育整理的学术成果问世,如任海的《中国古代体育史》、[16]崔乐泉的《中国古代体育文物图录》等。[17]以上时期的学术论著总体来说是基于古籍文献材料所进行的史学探讨。在研究范围及视野上相对宏观,大多涉及体育思想、制度、项目三大领域构成,尚需进一步将体育作为人的生活整体考察,对底层、地方和民间的关注较少,尤其是反映民众日常体育生活及相关活动的内容尚未进入学术视野,诸如婚俗、节庆、仪式、神话、传说等深刻的研究相对较少。
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逐渐带动了我国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民间、民俗等传统体育项目也受到了官方与学者们的双重重视。随后学界对其进行的学术研究开始转向微观史、多元视角、田野考录等特征的研究范式。
3 新世纪民俗体育研究的方法变革与视域多元
3.1 民俗体育研究的方法变革
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有关民俗体育的研究开始呈现出研究方法论的变革。崔乐泉专注中国古代体育史的研究,尝试将考古实物“数据”纳入到立证的材料范畴,突破了既往本土体育研究的“一重立证法”的方法论层次。“考古学在相当的程度上把原始人类体育的意识(物化形态)和体育行为的基本线索提供出来了。它从一定角度印证了作为一种文化特质的创造过程的文化形态,印证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原始人类体育形态的基本景观,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原始时代体育形态的初步的理论和技术方法”;[18]“在考古学资料分析的基础上,除了首先注重考古学的一系列理论和方法的应用外,更要把体育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实证材料,把原始人活动的精神图景和民族学材料,把个体发生的逻辑意义、群体发生的历史意义和历史文献的描述结合起来。这正是从理论的高度总结原始时代体育文化发生、发展及其演化规律与现象的最重要的方法论”。[19]同时,崔乐泉采用考古实物与文献材料相结合的“二重立证法”策略,对我国捶丸、蹴鞠、六博、射箭、巫舞等文化事项进行了一系列的学术探讨,在学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学术成果体系,为民俗体育的研究开创了新的方法论研究范式。
2004年,李志清提出了对少数民族体育研究的田野调查路径,认为关注民间传统体育个案进行“专题性研究”,采用“小题大做、以小窥大”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的实证性研究方法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少数民族体育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20]2005年李志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践行田野作业研究方法,对桂北侗族地区的抢花炮习俗进行了扎实的实地研究。该研究对古老的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活动在现代社会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如理性化、世俗化、组织化、规范化以及媒体的利用、妇女的参与等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民族特色的强调、功能的扩展则是民间文化在现代化与全球化中的生存策略。这些变化都是文化主体自觉的文化改造过程,反映了民族文化的生存能力和适应性以及仪式性,体现了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现代价值。”[21,22]
如果说“侗族抢花炮”的研究尚属个别学者的初步尝试与努力探索阶段,那么,以胡小明为首的“黔东南独木龙舟”研究的开始则标志着体育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形成。2008年,胡小明组织的华南师范大学体育人类学研究团队,赴贵州清水江与巴拉河流域开始了当地独木龙舟习俗的田野实证性研究。他们通过对黔东南地区清水江与巴拉河流域“独木龙舟文化圈”的田野调查,印证了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法的适恰性。同时,也展示了体育人类学的个案研究方法是体育界对保护文化遗产采集科学数据的有效手段。“黔东南独木龙舟的田野调查,不仅是展示体育人类学的实证研究范例,显现研究各原始运动形态获取第一手真实资料的有效途径,还是运用文化人类学进行具体深入的解释和分析,通过理论建设为倡导生态体育和保护文化遗产提供更完善的思路。”[23,24]
人类学田野作业研究范式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体育文化研究的实证性、增加了学术探讨的立证维度,亦提高了对某一问题或某一文化现象的纵深性理解。如博士学位论文中,张基振《文化视野中民间体育的保护、传承与发展——以潍坊风筝为表述对象的实证研究》(2007)、杨建设《我国传统节日体育现状与发展研究》(2007)、孟纹波《彝族火把节研究——以石林彝族撒尼族群为个案》(2012)、覃琮《“标志性文化”生成的民族志——以滨阳的舞炮龙为个案》(2011)等,他们田野调查的平均耗时在三个月以上。在众多研究成果中“田野调查”运用的方式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基于“个案”的田野,如《文化视野中民间体育的保护、传承与发展——以潍坊风筝为表述对象的实证研究》,将田野工作瞄向潍坊地区的风筝运动。“风筝”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作为民间体育,不同地区的风筝运动所具有的文化特征互有差异,若以抽象概念出发,研究所得出的理论知识亦是抽象宏观的共性特征,无法深入到具体文化的内部,探究其深层意义。张基振的博士论文采取了“个案”田野作业的研究策略,所得出的理论知识与“地方”契合且深入到文化的内在机理,可对该地区的风筝发展提供有效的地方性理论。另一种是基于“多案”的田野调查研究,如《我国传统节日体育现状与发展研究》,将田野工作瞄向了湖南地区的龙舟竞渡、山东淄博的蹴鞠、内蒙古那达慕等多个“个案”。标准的文化人类学田野作业本应针对“个案研究”,目前流行的“多点民族志”研究亦是针对同一研究对象而开展的。一项研究时间相对固定,这也决定了田野调查工作时间的最大范畴。在田野工作时间相对不变的情况下,“多案研究”对事实的认识深度必然会随着“案数”增加而有所“损失”。如《我国传统节日体育现状与发展研究》,其田野工作的努力非常值得推崇。研究者为进入“田野”获取一手资料几乎跑遍中国版图,特别在议论“龙舟竞渡”部分时充分体现了作者的田野成绩,那种研究者“在场”、充满鲜活情感的文化真实再现,自然地流露于字里行间,深度访谈的研究魅力也显现得淋漓尽致;但在涉及其他体育事象时其“田野气息”明显不及“竞渡”部分。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更无法同时踏入两条河流。田野调查即是要走进文化的真实,而面对概念(如传统节日体育),它是跨节日体系、跨地区、跨文化的众多真实的抽象。一项研究中的“田野调查”本无法兼顾如此众多的“跨越”。
概而言之,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民俗体育研究经历了方法或方法论的革新。无论以崔乐泉为代表的考古学方向还是以李志清、胡小明为代表的田野作业,这两种学术路径均在民俗体育研究的方法论上有所突破,即在传统“一重立证”的研究基础上完成了“二重立证”的方法论“升级”。庆幸的是,双方关注的立证资源亦不相同:一是考古实物;二是田野活态文化。就如上两方面的学术贡献来推测,对学界的后续影响还远不如此。顺着立证资源维度深化的逻辑思考,我们会发现方法论进一步革新的可能,“三重立证法”的研究范式已呼之欲出了。
3.2 民俗体育研究的视域多元
随着研究范式的革新,研究视域的地域走向也会随之由以往宏观的“中华文化圈”视野转向相对具体的具有地方特征的区域性体育文化研究视野。近些年来,区域性民俗传统体育研究成果逐渐丰富。白晋湘、万义等学者围绕湖南湘西少数民族体育的研究,主要从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维护的立场入手,对具有典型性的民间传统体育事象进行了实证性研究,并提出了一些与地方文化背景相互契合的民间体育文化保护理论。[25,26,27]王俊奇等人针对江西民间、民俗体育,以古籍善本等为数据来源,对江西区域民间体育进行了细致的理论梳理。陈康则在国内极富影响力的敦煌学基础上,利用敦煌学资料去挖掘民间体育的新材料。所谓的“敦煌体育”是指在敦煌莫高窟壁画、雕塑及藏经洞文献和敦煌及其周边地区考古发现的体育遗物和遗迹。该研究将敦煌体育的内容分为角斗、射术、剑术、徒手格斗、相扑、武舞、围棋、气功等,并在体育内容的基础上还深入探讨了相关体育器械、场地、规则等方面的内容。[28]结合敦煌学、考古学、体育史学的综合研究一方面体现了研究方法论的创新,另一方面还为我们带来一个新的研究视域。有关汉文化区域民间体育的研究则以付玉坤为代表的“山东民俗体育”研究。他们在其研究成果中对山东省范围内的民俗、民间体育进行了一般的梳理与统计,并基于专项的田野调查,完成了山东民俗体育“发展现状”“存在问题”与“发展展望”等多个方面的文化保护的研究工作。[29]
视域的多元还体现在民俗体育分析框架的走向方面。新世纪以来,体育人文学科领域始终与相关学科保持着适恰的张力,不少体育学者努力汲取其他学科优秀的理论观念、分析概念以及新的研究范式,取“他山之石”来解决体育领域的学术问题。就民俗体育而言,在学科性质上与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性质相关联。不少学者开始进一步尝试运用其他学科极具分析力的分析框架来聚焦民俗体育研究。冯强、涂传飞等在民俗体育的研究中汲取文化人类学的经典理论贡献,尝试运用马塞尔·莫斯的“礼物交换理论”来分析民俗体育中的社会互动关系,[30]以及借鉴格尔茨的深度描绘的文化观分析涂村舞龙习俗的文化变迁。[31]王若光则运用皮尔斯的文化符号学“三位一体”的基本分析框架探讨了中国岁时民俗体育的文化符号问题,提出了民俗体育生成的逻辑起点为“民众求保安生的生活理想”。[32]
李志清将涂尔干仪式理论引入民俗体育,较早地运用国家-社会互动的分析框架探讨“抢花炮”之于国家、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了国家政治生活及国家社会互动关系是通过诸如“抢花炮”一类的民俗体育实践而实现的观点。[19]刘素林、行龙从社会史的角度,对山西万荣集体化时期的一支“海鸥”女子锻炼队进行了微观史的分析,探讨了集体体制下新式体育嵌入农业生产、融入乡土生活,重塑女性形象和社会角色的运行机制。[33]杨海晨、万义等学者从不同的田野个案入手,分析了近现代以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如何与国家力量发生关联,并从“国家符号”与“女性参与”的不同切入点展示了国家社会关系在田野个案中是如何互动、变迁及呈现的。[34,35]以上研究已基本形成了借助社会学、人类学经典理论框架探讨微观体育“国家社会”互动的视角与分析范式,为当前研究中国本土体育的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维度的方法论思考。
3.3 民俗体育研究问题的精细化
研究材料的出新与视角的多元,自然也会影响学术研究问题的走向。相对既往解决民俗体育是什么、有什么价值意义等一般性问题导向来说,新世纪以降,有关民俗体育的研究问题进一步向精细化方向发展。王若光通过历史典籍的梳理对端午竞渡习俗何时使用龙舟、为什么要使用龙舟的问题进行了基本解决。他将龙舟使用的大致时期“确定”在唐代、将龙舟的使用与传统文化中体现时间意义的爻辞“飞龙在天”予以关联。[8]对民俗体育的深入研究必然也会对体育学科内固有的学术问题进行重新审视。王若光在对竞渡习俗的历史细节具备了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回应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学者提出的“中国体育未能成熟”的全称命题,以竞渡为单个反例的研究策略证伪了“中国体育未能成熟”的全称命题,提出中国历史上确乎已经出现了可与西方媲美的“标准化体育”。[36]胡小明的研究团队,在滇西进行田野作业中发现“东巴跳”与东巴文字之间的关联性问题,提出了学科辐射性较强的研究问题,即“身体运动与原始文化(文字)形成之间存在着文化关联”。[37]研究团队在问题的引导下创造性地采用了“从身体动作到图画文字”再“从图画文字到身体动作”的身体动作分析法的“双向实证”技术路线,为研究原生态的身体运动对古文字形成的作用开拓出科学的新路径。[33]杨海晨与万义等学者则密切关注社会人类学理论前沿,在探索地方民俗的过程中,发现了民俗体育中的“国家符号互动”与“女性参与”的变奏现象,将母学科中的传统问题意识带入民俗体育的个案研究,提出了更为切合自身学术探讨的研究问题:如杨海晨认为黑泥屯演武会的文化变迁是一个“国家—社会”关系走向“相互在场”的过程;[38]万义则认为苗鼓习俗女性参与的历史系工具理性的社会行动,向价值理性的社会行动发展会成为地方民俗体育保护与传承的应然走向。[39]近十年来的学术成果中,一系列研究问题的提出及解决成为了后续研究的问题导向,提示着后续研究中学者们对研究问题的精细化把握与多元化关照。
学生本身的相似性度量,给定训练集 Dtr,sp为训练样本中的学生标识号,sq为待分类样本中的学生标识号,则学生自身的相似度为:
问题意识是学术品质的核心命脉,但是在具体的研究中过分强调问题意识也有可能为研究带来一定的风险。王若光在《民俗体育研究:方法、价值及现代性问题》中针对这种学术现象以文化人类学界著名的学术公案,玛格丽特与弗里曼有关萨摩亚研究截然不同的结果,为分析案例提出:“问题意识”的强调虽然是学术品质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特别是对于民俗体育个案倾向的研究类型来说,问题的提出不应该是“想当然”的提前预设,“过分强调问题”则有可能导致研究者对客观且不符合问题导向的现实证据视而不见,最终导致研究的无效。[40]问题意识应该是一个在研究数据获取、分析中“自然涌现”的过程。研究者面对现实呈现的真实数据进行分类、比较、归纳、总结后所形成的“问题意识”才应该是研究所需的真问题。
4 晋地民俗体育研究的现状与发展方向
4.1 晋地民俗体育研究的现状
有关山西省域内民俗体育的研究,近年来初见端倪,如李建英等学者关注的河东地域民间、民俗体育文化研究;[41]王铁新对山西民俗体育项目的梳理等。[42]但囿于该领域的学术积淀时间尚短,目前尚未出现一项较为系统、全面的整理山西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事象的研究成果。而建立在整理民间传统体育之上的相关保护研究也在相当程度上流于宏观抽象的“概念性研究”。所谓的“概念性研究”主要是指,有关保护研究主要还集中在“非遗保护”的一般概念探讨层次,并且具有“针对性”的保护研究也并没有针对具体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特征、区域内文化保护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开展探讨,因而所得出的保护对策、建议、观点、理论等仍然是极度宏观抽象的。虽然这样的研究路径并没有什么错误可言,但这样的保护理论却又严重缺乏与文化事实之间的契合,文化保护的真正意义值得商榷。
从既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一方面,部分学者对民俗体育的个案进行了研究,如对忻州挠羊赛、襄汾跑鼓车文化事象的关注;其中最具有学术代表性的成果为孟林盛、李建英的《民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研究:以山西忻州挠羊赛为视角》。他们以山西忻州挠羊赛为个案,通过追溯其发展历史及目前文化保护的现状,对民间体育非物质文化在法律保护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原因分析,并提出了“完善各位阶的法律规范”“树立公法与私法协调保护的理念”等文化保护的对策建议。[43]此外,襄汾跑鼓车文化由于其自身独特的身体竞技性、团队合作性及完整的文化仪式传统谱系及近年来成功跻身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体宣传效应,引起中国体育研究者的关注,目前已有众多论文成果问世。如,王兴一[44]对尉村跑鼓车习俗的历史起源、形式、文化价值等做了初步探讨;暴丽霞、冯强[45],尉福生[46],刘浏[47],李博文[40]等人亦分别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对跑鼓车项目做了研究。通过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目前有关跑鼓车的研究成果均属于表浅、粗线条的“浅度描绘”。无论在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基础理论储备方面均有待进一步提高。在硕士学位论文研究中,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硕士范静的论文《节庆中的仪式展演——晋南襄汾县跑鼓车及其文化内涵研究》对尉村跑鼓车习俗研究比较细致。她先后9次深入田野考察,以表演理论为指导,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探究跑鼓车的文化内涵,分别对跑鼓车习俗的文化渊源、仪式及技艺、文化内涵等方面做了细致的研究。[47]只是范静的研究主要在于对民俗仪式文化的关照,而对该习俗特有的体育意义相对忽略;并且在研究中的历史时代划分方面略显逊色,对鼓车习俗之于社会民众的文化意义阐释方面尚未达到格尔茨“深度描绘”的水平。此项研究对后续的研究者再次进入田野进行研究有着引导式的作用。它将该习俗的一般特征、形式、规模、环境等问题已探讨的比较细致,对后续研究的理论检验,提供启发性信息方面有着不错的学术贡献。
另一方面,学者们从民俗体育的普查、文化价值、文化特色等视角对民俗体育进行了一定的归纳研究或整理。王铁新运用文献资料及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山西晋南地区社火民俗体育事象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该研究涉及临汾、运城整个区域的众多县市,共梳理出了参与程度高的项目,如锣鼓、秧歌、高跷、竹马、旱船、舞狮、舞龙等,以及近年来有可能消失的项目,如转灯、麒麟舞、人熊舞、蛤蚌舞、甩杆等30余项。[40]该研究是近年来对山西民间体育事象整理最为全面的一项成果,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不少指引信息。李建英的《河东体育文化研究》,[39]在研究视域方面准确地将“河东”这一既有历史流源又有学术传统的文化区域概念纳入研究;并以河东文化为背景,将河东地区几种最具地方特色的民俗体育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形成与发展特征及文化内涵进行调查、梳理与研究。从历史文化的视角,诠释其发展的历程以及存在的问题,为河东体育文化的发展提出了“整合创新、可持续发展”“借助传媒、学校结合”“建立研究团队、开展学术交流”“政府调控,健全传承保护政策”“文化建设规范化和产业化”等理论支撑,对河东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扬具有一定的“顶层”指导意义。
4.2 晋地民俗体育治学的发展方向
自1926年民俗学家江绍原发表《端午竞渡的本意》以来,继之闻一多,王健吾、金铁盦等一批学者的众多研究均瞄向了民俗、民间传统体育事象,为民俗体育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具有里程碑式的《中国古代体育史》(1990)、《二十五史体育史料汇编》(1997)等十余部学界极具影响的传统体育著作的理论架构,以及21世纪以来倪依克、肖焕禹、崔乐泉、万建中、李志清、胡小明等人对民俗体育研究的专学形成,已续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在新近的研究中崔乐泉、王俊奇等继之深化探索民俗体育的史学方法,开创了“考古实物”证据材料的研究立证维度;胡小明、李志清、杨海晨、万义等学者则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及方法引介到该研究领域,突破了文献考证的单一材料来源,增加了“活态民俗”另一证据材料的研究维度,开创了以田野作业为主的研究范式。晋地民俗体育的学术努力已随着国内发展的前沿趋势起步升温。经既有学者们的学术贡献提示,省域内可资探讨的学术资源丰富、厚重。就当前山西区域内有关民俗体育文化整理及文化保护研究的现状,综合来看,至少应在新材料、新视角、新问题三个方面做出学术尝试,需跟进国内前沿的学术主流脉络与发展趋势。
首先,民俗体育的学术讨论我们可以从证据来源方面多下功夫。文献证据方面要努力突破二手文献的引证,将数据来源描向古代典籍中的地方志、诗歌、族谱、契约、档案、碑刻文字等,山西地上文物位居全国之首,留存在古建筑上的壁画、文物、砖雕石刻等文化信息丰富,如广胜寺水神庙的壁画捶丸图。此类数据的收集整理及分析定会夯实晋地民俗体育研究的材料基础。与文献证据、考古实物相配合使用的数据来源还有田野作业中收集的口述材料、活态民俗信息。如果我们能在一项研究中将文献材料、考古实物以及活态民俗三者有机结合的共同使用即可达到“三重立证”的学术水准。
其次,在新视角方面,需进一步加强微观层面的研究,描向纵深研究的学术趋势。既有的宏观研究已不在少数,然而缺乏中观层次及以下的微观研究极有可能造成研究体系的不完整。按照常规学理,宏观的研究必须有中观及微观研究来予以支撑方有意义;另外微观的研究可以真正细致入微地解决实际问题。这既是学理使然亦是彰显应用价值、实践意义的必经之路。与之同时我们还需关照、借鉴其他学科视角的更新突破,如以山西大学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他们在探讨山西社会史问题时聚焦到了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水资源,提出“水利社会”概念。这一概念是基于“山西水资源匮乏的历史现实”而提出的。学者们从类型学的视角切入,分别从“泉域社会”“流域社会”“洪灌社会”的类型对山西地方社会进行研究。这一视角更新的思路值得我们学习;在研究的时代视角方面,溯源的研究固然重要,但相对晚近的研究往往更具有现实意义,如民国时期、集体化时期、改革卅年时期等均已是当今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体育学界的研究热点。晋地民俗体育的研究也应针对不同的历史片段深入做文章。
最后,学术之所以会延续终究还要归结到新问题的提出。就山西民俗体育而言,她作为一个区域的类型,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民俗体育的异同本就是我们亟待解决的学术问题。但由于我们目前的研究深度尚未与全国水平同步,这一基本问题还不可能明确地得以解决。据笔者长期的田野感悟来看,晋地民俗体育所内蕴的学术问题远不止既有研究成果所呈现的那些常规问题,如民俗体育与社会变迁的步调在具体的时空情境下会有地方特色,与我们惯常认为的常规历史时段并不完全吻合;决定民俗体育的原因机制也并不只是我们一般认同的“祈报昭格”。而在“祈报昭格”的外衣下还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机制需要我们去阐释;官方与民间对待民俗体育的态度亦不始终如一,针对聚焦在民俗体育之内的国家社会关系的探究或许更有利于我们认清民俗体育保护的核心;当前国家“非遗”政策、“留住乡愁”“创造性转换”等顶层设计对地方民俗的存续无疑有巨大的利好优势,但在深层领域、实践层面是否具有局限性,如何将“国家要素”适恰地融入“地方知识”。这些问题的讨论均需我们在治学中深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