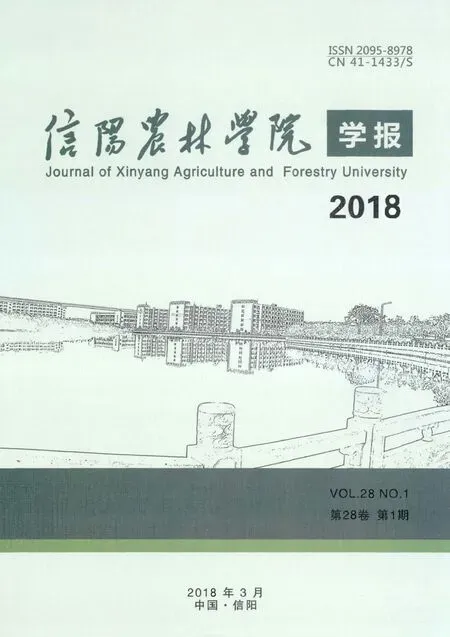解读《月亮与六便士》的象征性意义
陈 洁
(莆田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莆田 351100)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但在之后漫长的岁月中,英国小说评论家并没有给毛姆太高的评价。他们普遍认为毛姆与同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家——普鲁斯特、乔伊斯等人不同,认为毛姆并不擅长运用抽象的意识流写法创作作品,还有许多人认为他的作品太过一目了然,缺乏深度,甚至有评论家称他的作品“没有艾略特对家乡的崇拜仪式感情,又无法同劳伦斯那样的预言式写法相较量”[1]。但是,毛姆的作品具有极强的故事性,没有太过晦涩的语言和隐藏含义,使那些没有文学基础的人也能很容易读懂;另外,由于其作品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具有一定的艺术魅力,所以喜欢毛姆小说的人并不在少数,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够成为英国文学史上“雅俗共赏”作家的原因所在。《月亮与六便士》以法国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为素材,描述了主人公查尔斯·斯特里克兰——一名性情有些呆板的证券经纪人在不惑之年抛弃了自己稳定的收入和美满的家庭,开始迷恋绘画,对艺术进行不懈追求的传奇经历。这本书运用象征性的艺术手法,表现作品的中心思想、作者的情感态度以及想要表达的抽象哲理,使用深入浅出、寓意深远的构思方式完成作者内心深处隐藏情感的表达[2]。《月亮与六便士》这篇小说的题目就是象征手法的典型表现,在作者对故事人物、周遭环境和社会风貌的逐步刻画下,毛姆关于“月亮”和“六便士”的象征意义也逐渐在人们眼前展开。
1 “月亮”与“六便士”——理想与现实
斯特里克兰作为中产阶级的一员,有着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享受着社会赋予的各种权利和美满的家庭。但是在平静生活的背后,是他那颗不安分又为了理想而猛烈跳动的心脏。斯特里克兰的画家梦想自幼扎根在心中,迫于父亲“艺术赚不了钱”观念的压力只得按照家庭的意愿从事证券经纪人的工作。人生到达四十岁时理应按照原有的生活轨迹继续走下去,生活的平静经受不起梦想的折腾,但是斯特里克兰说:“我觉得,大多数人这样度过平庸的一生好像缺点什么。我承认这种生活的社会价值,我也看到了它井然有序的幸福,但是在我的血液里却有一种强烈愿望,渴望一种更加狂妄不羁的旅途,我的心渴望一种更加惊险的生活。”他甚至还认为:“一个人要是跌进水里,他游泳游得好不好是无关紧要的,反正他得挣扎出去,不然就得淹死。”对现实生活的不情愿与对理想生活的向往让他认为自己是个溺水者,要挣扎着爬出现实沼泽的羁绊。对“月亮”的追求使他放弃了手中“六便士”能为他带来的社会地位和悠闲的生活。他住在巴黎下等街道的一个永远散发着浊气和霉味的旅馆里,穿着破旧的衣服,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生活,但是他却在这里找到了自己内心的闲适。他神态自在,对生活毫不在乎的状态反而给予了他画画的灵感,他获得了心灵和身体上的暂时自由。在这段日子中,迪尔克·施特勒夫非常看好他的绘画天赋,在他生病时不管妻子的劝阻把他接到家里,让妻子帮忙照顾他。但是斯特里克兰丝毫没有感激之情,而是在不断地嘲笑他,甚至霸占了施特勒夫的房子和妻子,害得施特勒夫家破人亡。这种毫无怜悯的恶魔心理,毫无道义和责任的行为让人们对斯特里克兰的印象大打折扣。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又亲手烧毁了自己一生的画作,烧烬了自己执着、疯狂的一生。这个行为既神秘又耐人寻味,也依旧不容于世。斯特里克兰的灵魂似乎只为艺术梦想而燃烧,梦想的召唤、人格的狂躁、灵魂的躁动把他推上了一条不容于世的追梦之路。
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过:“理想是人生的指路灯,有理想,人生的小船就不会迷失航向。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但是,现实生活中理想和现实永远是一对矛盾体。有许多人为了实现理想,不得不放弃已有的生活和正常的工作,或者是为了现实的生活放弃自己的理想。因为要想实现理想,必须切合实际,这样才能保证现实生活中的努力是为了理想而进行的。面对理想和现实,绝大多数人都会进行反复比量和思考,理想来自于现实却又高于现实;现实中的物质基础恰恰是支撑理想实现的必需品,这两者永远是辩证统一的关系[3]。在《月亮与六便士》中,毛姆就把主人公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的矛盾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文中的斯特里克兰并没有像普通人一样尽量兼顾理想和现实,而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理想的怀抱中,他完全忽略了现实中的种种问题,甚至完全否定了现实,他认为除了绘画本身,其它都是没有意义的,生活中的种种便利都是他追逐梦想道路上的绊脚石。证券经纪人本来可以带给他正常的退休生活、美满的家庭以及较为富足的晚年,顺利地过完这一生,但是斯特里克兰并不屑于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充实而又幸福”的一生,毅然决然地抛弃了所有,转身投入到未知的艺术前程中。作者在描绘这一过程时,将“月亮”和“六便士”的象征意义运用得合情合理,“月亮”来源于“六便士”的平凡生活,要追求“月亮”就必须有“六便士”的物质基础。小说中斯特里克兰在疯狂追求自己“月亮”的同时也离不开“六便士”的支撑,就像理想离不开现实物质的支持,理想来源于现实却又高于现实。
2 “月亮”与“六便士”——真爱与虚情
西方国家的人们认为,月亮代表着纯洁。月亮时圆时缺的线条变化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少女的身姿,月亮皎白的光亮也象征着纯洁的感情。“月亮”与“六便士”间的第二层象征意义,则表现为爱情和虚情的对比。
斯特里克兰夫人体态丰润,面容姣好,是一个可以把家里打扫得井井有条的合格家庭主妇,也是一个能够照顾好孩子的称职家庭主妇,但她却不是一个能获得丈夫喜爱的妻子。斯特里克兰太太较为虚伪、好面子。她曾经温柔评价她的丈夫为“平庸,并不妄想自己是天才的人”,但是事情的发展却证明了斯特里克兰夫人根本就不了解自己的丈夫。在斯特里克兰为了追逐梦想去法国后,她却以为丈夫有了外遇。纵使内心极度不满,她还是在第一时间向周围邻居宣称即使丈夫为了外遇抛弃他们,她也不会选择离婚。多年后丈夫离世,面对评论家的采访,为了面子,她仍然暗示自己同丈夫的关系非常好。她非常看重社会的评价,她同斯特里克兰的婚姻更像是为了虚荣心而达成的婚姻事实,所以尽管她能够将一切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这种“六便士”的婚姻还是被斯特里克兰认为是逐梦路上的绊脚石,所以斯特里克兰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毫不留恋地抛弃了妻子。布兰奇·施特勒夫在迪尔克·施特勒夫将斯特里克兰接回家中养病之后,对斯特里克兰的感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布兰奇在斯特里克兰身上发现了自己生活中一直缺少的激情。但是斯特里克兰对她的占有则出于目的性,同爱情无关。斯特里克兰将这两个女人视为“圈套”,他对她们没有爱情,只有“六便士”般的利用,但他却对爱塔另眼相看,将这个年轻的土著女孩当作自己的“月亮”。他认为他同爱塔之间的爱情符合他对纯洁爱情的定义。当时爱塔只有十七岁,有自己的地产和房子,不要求爱情的仪式,愿意付出自己的全部为斯特里克兰而不要求回报。她的这种付出让斯特里克兰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塔希提岛的自然风光给了斯特里克兰创作的灵感,家庭环境给了他足够的创作自由[4]。斯特里克兰说:“她为我做饭,照顾孩子,让我独处,却能够帮我做我要她做的事情。”甚至在斯特里克兰患上麻风病后,依然坚定地表示不会离开他,这让抛妻弃子、占有友妻却不觉羞愧,对感情毫无知觉的斯特里克兰触动了心肠。斯特里克兰同爱塔的感情无关金钱,无关目的,像月亮般纯洁,没有丝毫杂质。
3 “月亮”与“六便士”——塔希提岛与欧洲社会
小说中的“月亮”还象征着一片神圣的净土——塔希提岛。开始追求梦想的斯特里克兰生活在欧洲大陆上,这是一个物欲横流、追名逐利的地方,同斯特里克兰追求的梦想之国有着天壤之别。塔希提岛则是一个纯净浪漫的地方,在那里斯特里克兰可以放松心情,画自己想画的任何事物。这两个地点的对比正是“月亮”和“六便士”的第三层象征含义。
塔希提岛是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向风群岛中的最大岛屿,这里是斯特里克兰实现理想的最佳场所,在这座岛上他的梦想第一次完整地呈现。斯特里克兰第一次在打工的轮船上看到这座岛时就产生了一种自然的亲近感,这种亲近感甚至让他产生了一种曾经在这里居住过的错觉,于是他便留了下来。塔希提小岛是一个远离文明世界的岛屿,这里物产丰富、民风淳朴,岛民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河流环绕着房屋,树上挂满了果子,斯特里克兰居所周围围绕着河流以及椰子树、芒果树、遍山的橘子树。同欧洲社会相比,塔希提小岛就是一个远离文明社会的世外桃源。当地人的生活方式感染了斯特里克兰,他也开始只穿一件围裙,头发蓬乱,赤脚行走,晚上钓鱼,白天作画。在他的画作中,土著人成为了他的模特,他画他们的生活,画他们的劳作,创作内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斯特里克兰如此喜欢塔希提岛,以至于他仅存的几幅画作都是关于这个小岛的。塔希提小岛有限的土地和悠闲的生活安抚了他躁动的灵魂,他的梦想找到了扎根的土地,他夜以继日地作画,不断地将创作的汗水挥洒在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5]。在创作之余,他也会同心爱的爱塔坐在凉台上,一边抽烟一边悠闲地望着天空。在这种毫无压力的状态下,他创作出许多震惊世界的作品,人们评价他的作品“表现出一种原始并且野性的东西,这些画作让人战栗,好像这些画作根本不属于人世间”。
斯特里克兰在塔希提岛上的遭遇同欧洲大陆完全不同。当时的欧洲大陆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物质生产的快速发展使人们的价值观倾向于以金钱为基础,利用金钱划分社会地位。同时,新世纪的到来也使人们心中的孤独感倍增,战火开始蔓延。在十九世纪,人们认为健康的生活方式离不开对社会条例和既定社会规则的遵守、驯服。所以,斯特里克兰放弃原有的幸福生活转而抛弃一切去追求绘画梦想,这一想法根本无法被当时的人们所理解。斯特里克兰的邻居、同事、合伙人都不敢相信这样一个看似呆板的人居然会如此痴迷于画画,他的所有价值观同当时的社会现状都格格不入。这一情况在他到巴黎之后也没有好转,巴黎的人们也不能理解他异于常人的做法和由此产生的荒诞感。斯特里克兰在受功利支配的欧洲现实环境中根本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他的精神失去支撑,艺术创作失去灵感,只有内心关于艺术的向往在支配着他不断前进。为了生存,为了继续追逐梦想,他只能逃离欧洲。塔希提岛的环境则不同于欧洲,当地的人们并不厌恶斯特里克兰的“疯狂”想法,反而对他格外怜悯和包容。在塔希提岛上,他的独特行径不再被异样的眼光审视和判断,斯特里克兰可以自在地做他想做的事情。对当时的斯特里克兰来说,塔希提岛就是他的纯净圣地。
[1] 骆谋贝,陈兵.传统土壤上开出的现代之花——论《月亮与六便士》现代主义叙事技巧[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111-119.
[2] 李 瑞. 真的自由了吗?——从萨特存在主义来解读《月亮和六便士》[J].语文学刊,2010(3):40-41.
[3] 顾 弘.理想和现实的冲突——解读毛姆《月亮和六便士》的主题[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2):38-41.
[4] 鲁 苓.追寻自我的旅程——读《月亮和六便士》[J].外国文学研究,1999(1):75-78.
[5] [英]威廉·萨摩赛特·毛姆.月亮与六便士[M].傅惟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