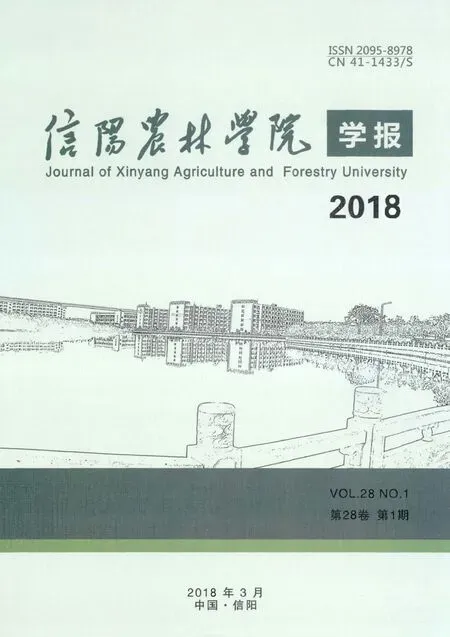斯坦纳阐释学观照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以傅雷《高老头》为例
丁 珊
(安庆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自20 世纪70 年代“文化转向”后,翻译研究的侧重点从语言学角度向文化角度迁移,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并高度重视译者主体性,译者的地位大大提高。许钧认为: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一种自觉的人格意识及其在翻译过程中的一种创造意识。这种主体意识的存在与否,强与弱,直接影响着整个翻译过程,并影响着翻译的最终结果,即译文的价值。……所谓‘翻译主体性’……是指翻译的主体及其体现在译作中的艺术人格自觉,其核心是翻译主体的审美要求和审美创造力。”[1]
傅雷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生平译介了大量法国文学作品,其“重神似而不重形似”的理论也引起了广泛关注,译作《高老头》堪称傅雷后期翻译的经典作品之一,本文旨在探讨傅雷先生在翻译活动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从乔治·斯坦纳阐释学翻译四步骤论的视角入手,以求为这一经典译作的研究增添新的视角。
1 乔治·斯坦纳的翻译观解读
在“阐释的运作”(The Hermeneutic Motion)中,斯坦纳阐述了翻译活动的本质,他从阐释学的视角入手,运用阐释运作的“四步骤”理论来解析翻译活动——信任(trust) 、侵入(aggression) 、吸收(import)和补偿(compensation) 。我们逐一来分析。首先,译者要对原文或者作者产生认同,认同作品的影响及意义,“所有的理解,以及作为翻译的对理解的外在描述,都起始于信任行为”[2]312。 其次,作者以自己本身的学识、个人经历、世界观来理解原文,挖掘原文的含义,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所难免。斯坦纳认为:“是海德格尔让我们认识到理解、认知和解释是一种密集紧凑、无法避免的攻击行为。”[2]313接下来,译者要将原作的内容和思想译介给目的语读者,但是在“吸收”的过程中,源语和目的语都有所变化,在忠实的翻译原则下,为了平衡源语和目的语的变化,弥补意义的流失,就要进行“补偿”。也就是说,译者要发挥其主体性,保持原有的平衡,补偿在翻译过程中遗失的部分。译者在不同的生活和成长环境中形成了极具个人特点的思维模式和语言能力,进而完成了信赖和入侵这两个步骤,接下来译者根据自己的理解,用个人风格明显的语言将源语移入目的语,同时以自己的翻译经验来权衡翻译技巧和翻译策略。然而,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不平衡,最后需要译者做出补偿,这时译者自身的学识、习惯及其翻译动机无时无刻不对翻译产生影响。因此可以说,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理论完整地阐述了译者主体性在翻译活动中的运作。
2 斯坦纳阐释观在傅雷译作《高老头》中的体现
译者主体性是“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3]。傅雷从对巴尔扎克作品的选择到翻译过程中语言的处理,都展现了其个人的人文品格、文学修养和艺术审美。
2.1 信任
“首先是初始的信赖,一种信任的投入,以过去的经验为保证。”[2]314在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限制和影响下,译者对源文本甚至作者产生认同,建立起信赖,开始尝试理解原作,挖掘其含义,才能称之为开始翻译。傅雷为何选择巴尔扎克的作品作为自己的翻译对象呢?众所周知,傅雷前期的翻译多数为罗曼·罗兰的作品,其中《约翰·克利斯朵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傅雷后期为何选择巴尔扎克的作品来翻译呢?
首先,傅雷对翻译巴尔扎克的作品很有信心:“我的经验,译巴尔扎克,虽不注意原作的风格,结果仍与巴尔扎克面目相去不远。只要笔锋常带情感,文章有气势,就可说尽了一大半巴氏的文体能事。”[4]其次,傅雷认为国内更需要巴尔扎克的作品,1954年傅雷在信件中表示,“大概以后每年至少要译一部巴尔扎克,人文决定合起来冠以《巴尔扎克选集》的总名,种数不拘,由我定。我想把最好的译过来,大概在十余种。”[5]
2.2 侵入
信赖之后,就是 “侵入”。在斯坦纳的观点中,这第二个步骤是无法避免的攻击行为,因为译者总是会受到其所身处的社会、文化及某些个人因素的干扰,因此,主体性的发挥会受到各方面的限制。但译者的 “侵入”却是积极有效的,可以促使目的语读者的视域更接近原作者的视域,从而让原作更容易被目的语读者理解和接受,甚至可以增强原作的生命力,在目的语环境中获得第二次生命。
傅雷1919年入周浦镇小学,1920年考入上海南洋附小四年级,1921年转至上海徐汇公学(天主教会学校),后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中。1927年冬,傅雷赴法留学,他同时在巴黎大学和卢佛美史学校听课,专攻文学、美术理论、艺术批评。留法期间,曾游历比利时、瑞士、意大利。1931年秋返回祖国,被聘在上海美专讲美术史和法文。因此,傅雷对天主教以及中国传统的道教、佛教都很了解,在翻译的过程中处理这一类问题得心应手。例如对Dieu的处理,将Dieu les a créés pour être l’un à l’autre.译为“天生一对,地造一双”[6]349,再比如将Par le sacré nom de Dieu...,译为“皇天在上,……”[6]391。原句中的Dieu本意为“上帝”,今天的读者对此并不陌生,然而在建国初期国民受教育程度偏低、国际交流甚少的国情下,为了使译文通俗易懂,傅雷采用了同化的翻译策略,用目的语中的文化意象来表现,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点,傅雷在将巴尔扎克的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的过程中,考虑到读者的接受程度,对原文作出了适当调整。首先表现为一些称呼的翻译,例如femme de chambre,《法汉大辞典》给出的解释为“贴身女佣”,并没有在年龄上做出规定,女佣也可能是青年妇女,但是傅雷将其翻译为“老妈子”。对于这个处理,傅雷综合考虑了读者的接受能力、原文所要表达的意思以及地域文化差异。傅雷生长在上海地区,传统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自然选择了自己习惯的日常称呼。此外,傅雷在地名的翻译上也颇费心思, la rue de l’Arbtère et la rue Buffon 分别翻译成“箭弩街”和“布丰街”。虽然要考虑读音,但傅雷并没有完全采用音译法,而是参考中国读者的喜好,选择了大众接受程度较高,比较贴合传统习惯的名字。
2.3 吸收
“对原文意义及形式的引进和接纳,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也不是要把它们引进或吸纳到真空中去。”[2]314这里所谓的“真空”指没有障碍的语言环境,现实中并不存在。目的语本身已有的语言规则以及自身的文化环境,都为翻译设置了重重障碍。因此,译者不得不采取各种翻译策略来克服这些障碍,使译作能够为读者接受,这就是翻译的第三个步骤“吸收”。在“吸收”这一步骤中,常用的手段有两种——同化或者异化。无论选择那一种手段,译者都将主体性发挥到了极致,难免会使原文本或者译文失去原有特点。
众所周知,傅雷在翻译中喜欢使用四字成语,推崇纯粹的中文表达,并提出“重神似而不重形似”的理论。中法两种不同语系的语言,从形式到内容,都有着巨大差异,例如en lui montrant la profondeur de l’ab?me dans lequel il avait failli rouler,翻译为“一失足成千古恨”[6]372。原文是描写主人公内心活动,傅雷用成语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原文意思,且读者更容易接受。但这种归化的翻译策略,往往也有夸张的成分。
再比如Là surtout l’amour est essentiellement vantard, effronté, gaspilleur, charlatan et fastueux. 傅雷译为“巴黎的爱情尤其需要吹捧,无耻,浪费,哄骗,摆阔”[6]380-381。法语中的形容词后置在汉语中没有对应的语法规则,因此原文的形容词全部用名词替换,既符合读者的语言习惯,又表达出原文层层递进的感情色彩。
2.4 补偿
斯坦纳认为:“译者频繁地介入:他要么加入太多——填充资料,润色渲染,曲解附会;要么省略太多——草率行事,删减内容或截去棘手难译的部分”,而“真正的翻译总是寻求均等的补偿”[7]。傅雷采用的补偿方式是增加注释和内部补偿。
由于中法文化的差异,很多现象难以直接表述,傅雷不得不采用注释的方式,例如vin de Bordeaux. “来拿我的一瓶波尔多去。”①[6]342随着中法文化交流的推展和深入,现在的读者深知波尔多产葡萄酒,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国内读者对法国了解甚少,傅雷不得不加以注释:①波尔多为法国西部港口,盛产红葡萄酒,通常以此地名称呼红酒。[6]342
在源语文本中,只言片语即可表达的内容,为了使其更加丰满,译者往往加入自己的理解,以达到更好的接受效果。比如... Eh ! quoi, j’aurais travaillé pendant quarante ans de ma vie, j’aurais porté des sacs sur mon dos, j’aurais sué des averses, je me serai privé pendant toute ma vie pour vous ...
……嗳,怎么,我忙了四十年,背着面粉袋,冒着大风大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样样为了你们……[6]386
高老头这段台词中,傅雷将本意为“袋子,包”的sac翻译为“面粉袋”,虽然与原文稍有差异,但是联系高老头面粉商的身份,译文恰到好处。je me serai privé 这一个动词,为了刻画良苦用心的父亲形象,傅雷译为“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虽然与原文形式上相去甚远,但意思高度符合。这些都是译者对原文的补偿。
3 结语
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在尊重原作的前提下,将自身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以及审美创造融入翻译活动中,最终达到完善译作的目的。因此,译者主体性的发挥直接影响翻译的质量。本文从斯坦纳阐释学翻译的“四步骤”视角入手,发现译者的主体性贯穿了《高老头》翻译活动的始终,傅雷凭借其自身深厚的文学、文化功底和对文学艺术的热忱与追求,既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也兼顾了原文的自我约束,重塑了巴尔扎克的名篇《高老头》,使读者了解了原作的内容和风格,可谓法语翻译史上的经典之作。
[1] 许 钧. “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 [J]. 中国翻译, 2003( 1) : 6-11.
[2] STEINER, GEORGE.AfterBabel:aspectsoflanguageandtranslation[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3] 查明建,田雨. 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谈起 [J]. 中国翻译,2003(1):19-24.
[4] 金圣华. 傅雷与他的世界 [M]. 上海:三联书店,1997: 271.
[5] 傅雷. 傅雷文集·书信卷[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 162-165.
[6] 巴尔扎克著.欧也妮·葛朗台 高老头 [M]. 傅雷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1980.
[7] 谢天振. 当代国外翻译理论 [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