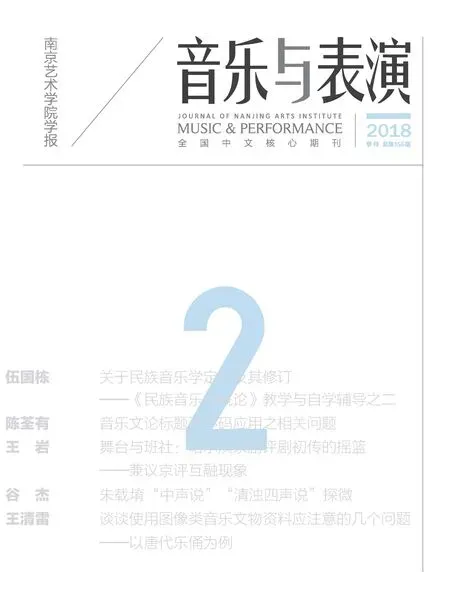从“失聪”到“失语”
—— 通过对现象学美学叙辞梳理而引发的思考
本文试图通过对现象学相关哲学美学叙辞进行一次音乐美学视域下的梳理,并由此对笔者一直以来以为音乐美学学科存在的一大罅隙进行边界缝合。罅隙即指面对音乐,我们所听(听“到”的)与所写(写下的)之间的巨大间隙。之所以诉诸于现象学哲学,是因为我在思考过程中,遇到了一般艺术学理论常有的边界,即当对“听音乐”还原到“对音乐的听”以及将“写音乐”还原到“对音乐的写”时,那本体论意义上的“听”本体和语言本质到底如何运作的疑问总是凸显在进一步书写中。因而,我企图从现象学的他山之石中获得解释某种学科悖论的钥匙。
罅隙来自悖论,语言终止时,艺术兴起。而中国古人也有类似的说法。毛亨《诗经·大序》里写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悖论引发悖谬,站在我所学之基点,试图远行却在起点就遭遇桎梏。既然音乐是兴于语言之后,那如何用语言来描绘语言之不能所及的地方;普通语言的边界是否可以由音乐美学的语言来突破,如果有一种音乐美学的方言,又该是何种语言……一系列困惑,我将其具象化为两个问题,即:音乐怎么听、美学怎么说。
虽然会被利奥塔支持者诟病我的部分初衷——打着现象学名义找寻元叙事——但我仍然觉得在一次以现象学哲学美学为基点的作业中,我的初步目的应该是找到音乐美学学科的元叙事存在的可能。其中包涵了音乐美学所听与所说,也许在作业后此种罅隙非但没有缝合反而愈加明显亦未可知,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来看,罅隙存在就有着一定的合法性。但元叙事还是要找寻,这也是一个悖谬。
就此作业,我拟定以胡塞尔——海德格尔——列维纳斯三人为主线,前承布伦塔诺,后至德里达,依照时间脉络与提出问题的巧合合适,将行文划分为两大部分,以对仗设问“音乐怎么听”以及“美学怎么说”。
一、“音乐”怎么听(或曰听什么):从布伦塔诺到胡塞尔
厄匹门尼德说,有一个克里特岛人说所有克里特岛人都说谎;欧几里得说,我这句话是谎话。
说谎者在说谎,这个引人入胜的莫比乌斯环先验地预示了存在于矛盾辩证逻辑外的智慧,在这里围绕原先的being的理解方式似乎遭遇了一种啼笑皆非的尴尬境地,身处一派模糊的边界,这种隐晦的延伸属于悖谬,微妙而令人感到陌生,像是“他者的智慧”,让人对世界有了新的认知。这种朦胧的诗意完全地凸显在现象学中,带括号的讲话、悬置、直观、还原……而这一隐晦的“折返希腊”途径,最终引向德里达对哲学死亡的宣判,这次末日审判的发端在胡塞尔,缘起自布伦塔诺。
“我”,主体,being;
我思,我在,我是;
形而上学作为第一哲学一直占据着西方哲学思想的主流地位,逻各斯中心之路作为第一次好的起航却也是一次桎梏之途。因而希腊人最终决定了第二次起航,努斯之路,仿佛预示了若干世纪后这场浩浩荡荡、破釜沉舟的现象学运动和带着镣铐跳舞的语言中心之路。从胡塞尔——或者再加上布伦塔诺——一直到利奥塔和德里达这些法国思想巨匠,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现象学运动中涉及了许多哲学家,为了方便研究,我简单将布伦塔诺和胡塞尔划分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意向性、直观、心的逻辑等提法,让感性的力量从隐到显,而其中“听”也显得敞亮起来。
(一)布伦塔诺:和谐悦耳的音乐是人倾听时产生的快乐
一般来说,现象学哲学运动的发端是由胡塞尔开启,在划分胡塞尔现象学形成时期时,通常会以《逻辑研究》(1900-1901)的撰写为开端。在此期间,胡塞尔创立了现象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探讨了大量笛卡尔经典命题中“我思”的部分。然而,在让出版商犹豫又一石激起千层浪的《逻辑研究》之前,还有《算术研究:心理和逻辑研究》(1891),探讨数学、逻辑和心理的若干问题。此期间他师从的正是弗兰兹·布伦塔诺。若是研究胡塞尔的整体学理思路,考量现象学作为一种学科以及一种方法如何应运而生,布伦塔诺的思想无疑是普罗米修斯手中偷盗来的火种。
弗朗兹·布伦塔诺 (Franz Brentano,1828-1971),奥地利哲学家,心理学家,意动心理学派的创始人。他生于莱茵河畔,逝于苏黎世,早期受教士训练,学习神学,后在柏林、慕尼黑和杜平根大学学习。1864年获杜平根大学博士学位,同时在符茨堡被任命为神父。后任符茨堡大学教师,专门讲授和撰写亚里士多德哲学(这一经历可以结合亚里士多德意向)。在与教会产生冲突后,辞去原先神职、教职,就任于维也纳大学任哲学系教授直至退休。也是在此期间,胡塞尔得以听他的讲课并由此立志于从事哲学事业。
胡塞尔1919年回忆恩师时撰写的名为《回忆布伦塔诺》一文中如是描绘:
“……当时我对哲学的兴趣高涨,并正在踌躇之中,我是否应以数学为人生职业抑或献身于哲学,此时布伦塔诺的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关于基本逻辑学的课上,他特别详细清晰地在创造性的新结构中论述了统一体的描述心理学,并深入考察了波尔查诺的‘无穷尽悖论’;他还论述了诸如‘ 直观的和非直观的’‘明晰的和不明晰的’‘清楚的和不清楚的’‘本真的和非本真的’‘具体的和抽象的’等表象的差异,在接下来的夏天里他还进行了如下尝试:从根本上探究一切存在于传统判断背后的、描述性的、在判断的内在本质中自我显现的阶段。”①原文选自Oskar Kraus编撰的《弗兰茨.布伦塔诺:了解他的生活与学说》一书(Oskar Kraus:„ Franz Brentano:Zur Kenntnis seines Lebens und seiner Lehre“,München , 1919)附录二第153-167页,中文部分由王俊翻译。从中不难看出布伦塔诺对胡塞尔巨大的影响。结合胡塞尔对布伦塔诺的评价以及布伦塔诺本身研究范畴核心的梳理:心理——物理世界的区分、意向性、本质直观、自我还原、想象表象、感知表象等,在本次作业中,我打算详细就布伦塔诺心理-哲学中意识、意向、意向性的问题进行展开讨论。
布伦塔诺是意动心理学的代表,这一学说和冯特的内容心理学分庭抗礼。从其著作《从经验立场出发的心理学》[1]中可以知晓,布伦塔诺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感觉、判断等思维内容,而是感觉、判断等思维活动,并且他为这种感觉、判断的思维活动过程起了专门术语,即“意动”(意识活动),意向的动作与意向的内容完全二元化各自存在。考据其思想渊源,这种具有动态指向性的定义与布伦塔诺另一个理论观点,即认为物理和心理现象有区分标准,并提出以“意向性的内存在”作为区分标志。这都与中世纪经院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
意向性一词来源于中世纪经院哲学。在《逻辑研究》第十节作为意象体验的行为具有的描述性中,胡塞尔如是说:“任何心理现象都可以通过这样一种东西得到描述”。[2]434此处的“这种东西”即是在说布伦塔诺的这种意动观念;而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中,它一般被描述为:一个对象的意向的(心灵的)内存在(Inexistenz)。此处的“意向”与之后布伦塔诺的“意向”有着一定的意义的区别。到了布伦塔诺处,这个命题则被发展为“与一个内容的关系,向一个客体(此处并非实在的东西)的朝向,或者内在的对象性”。这里意向性更多强调的是一种方向的趋势,一种动态。较之中世纪作为一种意识实存,布伦塔诺的“意向”概念中的指向性更为显现。这启发了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而回到经验哲学的历史维度上,结合上文中提及布伦塔诺对于亚里士多德思想的长期教学和研究,不难发现,前承的源头可以直接在亚氏《论灵魂》中找到。
亚里士多德在《灵魂论及其他》[3]中曾提及这样的观点,即“每种心理活动都有自己的对象。”布伦塔诺在提出意向性概念时也将内容与对象进行了关联。这仿佛是对亚里士多德上一句话的对偶。在《论灵魂》中,心理活动与心理活动对象有这样的朴素但具有意义的划分,并得到对象(内容)和动作不可分的强调,诸如:
光:视觉对象;
声:听觉对象;
亚里士多德前进到了这一步,将某种感性性质——或者我们可以成为某种物理现象——和这种感性性质的表像(即感觉)分开讨论,我们由而获得了两种层面上的意动和一种意向的指向。而布伦塔诺的关注重心除了此二者,还引入了心理学的情感,即爱憎,然后划分出三种意动关系:
表层意动;
判断意动;
爱憎意动;
又,旁及想象力和直觉经验,除了在亚里士多德提到的性质与性质表象二者,同时也将“对性质的表象”的活动本身视为关照对象。
回到音乐美学学科的出发点,联系到“听”这一感性性质,在布伦塔诺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片段:
1.关于“听”表象活动及想象力:
“……每一种呈现在感觉中和想象中的表象Vorstellung都是心理现象的一个实例;这里的表象不是指被表象的东西,而是指表象活动本身。这样,听一种声音,看一个有色对象,感到暖或冷,也包括类似状态的想象,都是我意指的心理现象的实例……另一方面,物理现象的实例则有:我所看到的一种颜色、一种形状和一种景观;我所听到的一种音乐和声音;我所感觉到的热、冷和气味;其中也包括在我的想象中对我显现的类似的意象。”[4]191
2.关于对音乐的听和由此产生的情感:和谐悦耳的音乐是人倾听时产生的快乐
“当一意外事件发生时,我们立即有了三种东西:首先是某种感性性质即某物理现象,其次是对这一性质的感觉(或者说对它的表象),然后有建立在这一表象上的情感。……情感所指向的对象并不总是某一外在对象,当我们倾听某一段和谐悦耳的乐曲时,我所感到的快乐并不是声音里包含的快乐,而是倾听它时所产生的快乐。确实,我们甚而可以说,这种快乐情感就是以某种方式指向它自身,……心理现象乃是唯一一种能被真正知觉到的现象。据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它们也是唯一一种既能意向地存在,又能实际地存在(actual existence)的现象。像只是、欢乐、欲望这类心理现象是实际存在的;而诸如颜色、声音、热这类物理现象则只可现象性地(phenomenally)和意向性地存在。”[4]206
(二)胡塞尔:听不能与对声音的听相分离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中都有曾表述过类似的观点,即世界是现象世界,人类理性无法达到事物本身。这话说得一点没错,也无奈预示了逻各斯智慧的局限。但幸亏我们还有第二次起航,好的起航。他说了一个词,到现在还有时暧昧难懂,trahscehdehtal,先验;又,结合康德对理性无法达到境遇的推论,感性显现。现象、物自体、理性,胡塞尔找到了一个精神拐点,气势汹汹地投身到现象的洪流,逆流而上,顺流而下。
这就好比理性患上了远视,当理性被穷极,顺延逻各斯途径,许多时候越是“拥有”了越多逻各斯之给予,越是离事物本身相去甚远。就像远视眼患者看事物一般,近则远,咫尺天涯,最无奈莫过于此。这不是辩证,是吊诡,所看和所看者有了错位。然后在这种悖谬中,现象学的生命力得以找到一个精神拐点,在错位中寻找定位。
康德说trahscehdehtal,胡塞尔也说trahscehdehtal,但康德意指的是先验,而胡塞尔更多的而是指一种超越论。王炳文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该词在胡塞尔行文的翻译中用到“超越论的”译文,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由胡塞尔开启的现象学的先天宿命。
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一个被称之为哲学家中的哲学家的著名德国哲学家、现象学家。1884年,他开始听弗兰兹·布伦塔诺(1883-1917)的课,并接受其建议前往哈勒大学学习哲学,成为卡尔·斯通普夫(1848-1936)的助手。此间(1891)撰写了第一部著作《算数哲学》(Philosophy of Arithmetic)。1900年,他发表《逻辑研究》卷一,并应邀于哥廷根大学、弗莱堡大学任教16年,影响了一批哲学家。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对师生关系莫过于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1889-1976)的传承和疏离。1933年后,因其犹太人血统,在海德格尔任校长后,禁止胡塞尔出入弗莱堡大学,并禁止进行学术活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聘请胡塞尔,但遭谢绝。1938年,胡塞尔死于胸膜炎。
结合我目前所要迫切解决的音乐美学临听问题,我主要学习了其现象学时期的研究,即以《逻辑研究》为主要读本,旁及《关于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哲学的观念》《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等著作。针对胡塞尔对笛卡尔“我思”的再反思、对布伦塔诺意向性的继承、现象学还原直观等来辅助我对学科问题的思辨。
阅读胡塞尔,艰难但不枯燥。这源自其写作方式:一种陌生的表述,仿佛是对他现象学理念的贯行。康德说世界是现象的世界,人类理性无法穷极事物本身。的确,那些前逻辑、那些前因果、那些意识界经验类的本质,都无法企及、无法解答。因而胡塞尔就采用一种描述的方式,直观还原、直接描述。而进一步,在对笛卡尔的批判和对布伦塔诺的继承上,他用“意向”、用“悬置”、用一种隐士般的姿态,倒着前行,超越“我思”,进行“返”思,返回反思的经验本身。
胡塞尔的现象学有两个动力源,对布伦塔诺的继承与对笛卡尔的批判。可以说布伦塔诺对意识的研究,对意向的提法结合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命题,给胡塞尔提供了剑走偏锋的精神之拐点,同时也是他晚期的精神之屏障。我们可以结合这两种动力源说起。
意识,德语写作bewusstsein,原意指“被知晓的存在”,意识之本性即意向性,在意识和世界的关系中,意识主体即相对应“我思”,而意识之主体性则对应于“我在”。胡塞尔投入了大量的工作在对“我思”的分析上,更关心的是“wie”-如何,而非“was”-什么,因而他得以预先避免了“我在”命题中隐含的许多危险。笛卡尔开启了一个二元,然后潘多拉的盒子打开就无法完全弥合,那些困扰就因二元而一直存有。胡塞尔在还原考量意识之前,先行使用“悬置”的方法。悬置,意味着无所谓前提对错的投射,这无疑是极其睿智的做法,因为如果不悬置这个二元,那就会一再面对近代哲学的壁垒,即主客体的隔绝。
“思”,物质,如果是用实体/概念的方式去理解,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在实质上只能是外在的关系。布伦塔诺依据心理学搭建了“意向性”的桥梁,胡塞尔在这里更近一步。
意识必定是对某物的意识。前人强调两端,而经过悬置后,我们不必急于前进或后退,在这个指向过程中就大有文章可做。也就是说,胡塞尔要说的,就是那个“对”某物之“对”。
“对”某物,这是意识之为意识的属性,我们可以在这里回想一下柏拉图说的洞穴比喻:不难理解,所意识到的内容在意识中的存在是与实际存在状况无涉的存在,既非实存又非虚无。因而,意向性真正的内在本质,是作为实存者的意识与作为实存者的意识之对方在意识自身中便能自行证明的关系,而非主张意识之外“必定”碰见某个与意识相关的东西。
由此推得,意识本身就其本性就是自身超越的存在,意识具有超越性,这种超越性也是意向性的重要属性。再进一步,意识一定是对某物的意识,因而意识就是有某物,意向性就是存在者在场的证明。对于意识本身也是如此。最终,这种意识之意向性引发了海德格尔此在之超越性,这是后话。
回到命题:“听不能与对声音的听相分离”,原句出自《逻辑研究》第二卷。
“布伦塔诺引入这种划界的原初方式……纳托普尔坚定地反对这种划界,但如果这位出色的研究者指责说:‘尽管我可以自为地或在与他意识内容的关系中考察声音,同时无需继续顾及它对一个自我而言的此在,但我不能自为地考察我的听,同时却不去想到声音’,那么我们在其中并不会发现有任何能使我们产生迷惑的地方。听不能与对声音的听相分离,就好像听在没有声音的情况下还可以是某种东西一样;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无需再区分一个双重的东西:被听的声音、感知客体,以及对声音的听、感知行为。纳托尔普对被听的声音所做的陈述肯定是正确的:‘它的为我的此在,这就是我对它的意识。意识只能在一个为我的内容的此在中被发现,如果有人除此之外还能以其他方式去发现意识,那么我是不会……去仿效他的。’但我觉得没这个‘一个为我的内容的此在’是一个可以并且需要进一步现象学分析的实事……”[2]447在尝试进行本质还原之前,笔者进行如下发问:
没有听见的听呢?
没有在听的听呢?
没有在听但听见的听呢?
…………
意识有一个自我极,在意识关照中的“听”也一样。或者说,意识中的具有艾多斯“听”是意识流(主体)的自身保持其为同一的极之一,是现象学还原后的剩余。因此,在现象学还原后,我们会得到意识的剩余,即意识自我极,而对听还原后,听的和意识流自身同一的极也仍旧存在。像一个蛰伏的动作,短跑运动员等着号令,悬停,等待在内时间意识中被构成。悬置的是“自然反应”,保持一种“近”的距离,但与“艾多斯”近就会看起来离“现象”远。悬置听,说着听不能与对声音的听相分离,实则必须将两端悬置,“听”和“声音”悬置起来,剩余的是个过程,是听的极。柏拉图说太阳的光芒太过耀眼,我们只有通过其散发出的阳光对物的照射才能感知到太阳,对于“听”也是一样。回答上文三个狡辩式的发问,现象学中的“听”和人耳的形而下听觉事实不同,更多的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明证。在指向中,两端的存在和存在者自明。或许,那便是隐德莱希(entelecheia)的一种体现。
二、美学如何说: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
以布伦塔诺为起点,胡塞尔为主导的现象学运动开启了一条面对现象世界的归隐之路。这有点像中国隐士得道后的智慧,采菊东篱下,才能悠然见南山。而对此中真意,则常常是得意忘言。这带有德意志诗意的归隐之路在海德格尔处开始寻找归隐后更进一步的家。因而他开始找路,就像胡塞尔文字中对于“流”的热衷,海德格尔找到语言希望能够通达存在的澄明,而因此开启了一条语言的流浪之路,也开启了近代现象学对传统形而上学、对罗格斯中心的“暴动”。
(一)海德格尔:将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
胡塞尔“超越”了康德,海德格尔“超越”了他。
在经历了胡塞尔大刀阔斧的本质还原和“悬置”后,我们离事物本身更近了,但那其中还有剩余。因为无论如何,胡塞尔用意向性的指向看还原后的世界,其关注点还是在世界本身,在个别的存在者上,而比起个体的存在者,存在者得以被意向关照的前提却被忽略了。从柏拉图开始,就忽略了的哲学剩余,被海德格尔不断折返希腊的途中找寻出来,那就是存在者存在这件事。
存在者存在,这是逻各斯光明未曾照耀的缝隙,连努斯之路也将它遗忘。存在,是指着天空的柏拉图和指着大地的亚里士多德都遗忘的脚下,是剩余的智慧。但有些隐晦的哲学家却开辟了一种新思维的敞亮,剑走偏锋的赫拉克利特以及隐藏了胡塞尔直观还原存在的海德格尔。
马丁·海德格尔,德国哲学家,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1911年,他决定放弃牧师的前程而专攻哲学, 跟随胡塞尔潜心研究现象学,后来创立了自己的哲学——存在主义。在《面向思的事情》①《面向思的事情》【德】马丁.海德格尔著,陈小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出版,收录了海德格尔晚年的三个演讲稿和一次讨论班的记录稿,该书名中所用的命题显然与胡塞尔的“面向事情本身”有一定联系。中,海德格尔指出胡塞尔的问题还是在于主体性,即便胡塞尔在研究后期,已经有了接近海德格尔dasein的提法,但不得不承认,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的确超越了一大步。但无论怎样,我们仍旧能够看到许多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之间隐蔽的联系。就笔者而言,我从意向中看到了存在的先现。
正如前文提及,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因而从这个指向,我们可以看到有某物。海德格尔进一步悬置,如果说意向性的得出是胡塞尔及之前现象学家们的一次两端悬置,那么海德格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两端进行悬置。意向就是有某物,向就是有。这个有,就是sein,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是、存在。
而海德格尔对赫拉克利特的解读也给与了我粗略分切的勇气。存在,是一个“向”。这里需要从四个词切入:sein存在、seiendes存在者、dasein此在、phusis解蔽(联系敞亮一词):
Sein,对应于英文中大写的Being,中文语境中有多重解释,常见的有:存在/是/有;
Seiendes:存在者;
Dasein:一般译为此在,但还有如张祥龙的“缘在”等译法在不同上下文中的替换也十分必要,有时候可以拆解成Da-sein来看,da相当于英语世界中的there,sein是being,就是being there的意思;
Phusis:海德格尔从解读赫拉克利特中重新拿来用的一个词汇,解释为“解蔽”,即解开遮蔽的过程,在海德格尔语境中有时即指存在,而从这个词我们还能联想到他的“敞亮”。
就海德格尔的存在论,阿兰·雷诺(Alain Renaut)曾将之比喻为斯芬克斯。斯芬克斯借着缪斯的智慧向人们提问,隐喻的话是答案自身的隐蔽。而一旦被回答出谜题,它就羞愤难当跳崖消亡。这种隐蔽的展开和展开的隐蔽,和海德格尔口中的存在有着某种惊人的类似。在《诗·语言·思》中,海德格尔如是说:存在即存在;存在是一个自身显现的过程。[5]但就好像我们不借助他物无法看到自己的眼睛一样,存在必须接触他物显现。而借助的就是特殊的存在者,人。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概括:
存在是现实性或在场,显现的是存在者,未显现的是显现自身的行为,也就是说存在自身。同时,显明了的是在场的存在者,隐藏的是使存在者显现的在场,完全被遗忘的是存在者在我们面前的涌现。进一步,可以这样定论,在海德格尔的语境中,存在是自行遮蔽着的解蔽。这和斯芬克斯简直像极了。
但笔者以为,我们宁可一直援用斯芬克斯这个美妙的隐喻而不是去试着归纳海德格尔语境中的存在是什么。是,存在,这个词太过危险。当我们说出一个词,就意味着没有利用这个词语的使用价值,也同时意味着不是。存在,在天性上拒绝着翻译的可能。但我们仍旧要去说话,那就需要用一种新的方式去说话。联系到另一个名词,dasein和《存在与时间》中关于ontology的论述,我们可以找到一种空置的说话方式:据说。而据说,就是此在。
海德格尔诟病我们将语言物化,语言不是语言。这是人类不愿被语言控制而试图占有语言的智慧。但还好我们有诗,有思。这里又暗合了他对胡塞尔的超越。意向性,这说着得有一个方向,但有些情绪譬如烦恼,有些情节譬如失眠,有些莫名的一见钟情,有些先天的排斥,这些无指向的显现,都可以用此在或缘在的称谓来理解。此在,此时存有、缘在,既远又近,能否碰见,全看缘分。即便不在场,但也可以在意向中缘在。
如果说存在者是通向存在的途径,那么此在或许是灵光一现间理解和表述存在的某些显现的途径。而最能通达存在的语言,应当是一种空置的方式说话,一种不在场的方式书写,这样语言才能成为存在的家。
(二)列维纳斯:书写即是死亡
列维纳斯开始了现象学的流浪。
现象学是描述客观世界的科学,换言之就是一场哲学语言的革命。语言被悬置、被架空、用陌生的方式说话、用不在场的方式说话。语言,和自己进行白刃战。在海德格尔的经典命题“语言是存在的家”中,我们找到了可以诗意栖居的凭证。然而列维纳斯却在马丁·布伯的对话中找到了一种新的他者的视角,而逐渐与终极的being渐行渐远。但在他那里,语言还未被完全放逐,却也为之后德里达对哲学已死的宣判打下基础。
列维纳斯,又译作莱维纳斯,1905年12月30日(此为俄国当时所用的儒略历,即公历1906年1月12日)生于立陶宛考那斯。他起初兴趣在古典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而后转向哲学。其哲学兴趣源自于就读犹太高中时所阅读的俄国文学,如普希金、陀斯妥也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列维纳斯重心转移之后,尤其对胡塞尔及柏格森的学说产生兴趣。1928年他转至弗莱堡大学跟随胡塞尔研习现象学。后来在胡塞尔的建议下,继续留在弗莱堡与胡塞尔指定的继承人海德格尔学习。于是列维纳斯成为最先关注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的法国知识分子。他者、陌生,他者的视角、陌生的语汇——这构成了列维纳斯颠沛流离的哲学语言:如果一定要说being,那么他宁可说dasein,这种小心翼翼的方式或许与他犹太人的身份有某种关联也未可知。
我们可以从狄德罗《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6]这一书的开场白中引入列维纳斯的语言途径:“他们是怎么碰见的?像所有人一样,萍水相逢。他们叫什么名字?这关你什么事?他们从哪里来的?从最近的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难道我们知道我们去什么地方吗?”这些话说了等于没说,答了等于没答,包含了一种语言中心之外的智慧,一种dasein的智慧。就好像狄德罗用的那个词,萍水相逢。列维纳斯对于主词的询问以及对于直接感受的界限包括对语言的解读,都可以从以上文字中得到澄明。
列维纳斯说:“谁的问题就在于发现主体,也就是发现存在与事物的连接中人的位置吗?或者说,就在于像柏拉图《斐多篇》所表达的那样,即这个‘谁’的问题就在于问‘他是谁’,‘他从哪儿来’?‘谁’这个问题是在存在(being)基础上提问的。问‘谁’可以回到问‘什么’,从问‘什么’再到所涉及的宾格……关于‘什么’的最高逻辑,是在被说的东西之中。这个被说的东西已经取消了‘谁’与‘什么’之间的差别。逻各斯就相当于被说的东西,逻各斯使‘谁’这个问题消失在‘什么’之问题当中……”[7]
“没有被说的说”,列维纳斯提到这个观念。在存在论意义上来看,文字是已经被时间化了的形而上学文字,语言被还原为being基础上的词语之间的关系,语言中的一切要素都是being衍生的结果,说话、写字、思考、心情……“书写即死亡”,终于,列维纳斯在《论布朗肖》中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们期待语言解释出背后的所说,我们相信说的背后一定有所说,我们觉得有人在说……列维纳斯要消解这种sein主权的说,因而他不说being,小心翼翼地说ilya,有。
传统理性总是用总体性压制差异性,对终极的sein抱有期待,列维纳斯却说trace,trace和“有”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一种找不到说话(者)和说话源泉、终止判断真假的方式说话。海德格尔说,天下雨了。这里真的没有人的什么事。我们看到,天上有月亮,诸如此种等,这些都是“有”,是“dasein”的变体,即不是存在也不是虚无,既不属于存在于虚无的序列,是一种“无我”之境,有点像禅宗里的“不空”和“真”,是一种真实又虚无的说话方式。
那么到底该怎么说,我们无需揭示一个穷极存在,我们要像他者一样面对此在,面对有。我们应当认知到语言的局限,摆脱习惯的名词性质的指称,话的本色,应是不透亮的,语言或者是说话,并非揭示被说,而是呼唤不断地到来的别的东西。一个词语总是在另一个词语之外,一句话总是在另一句话之外……语言不会也无需真正地在场,说话不算话不是“说”的失误而是“话”的本色。然后顺延这种说话方式,我们也把自己作为一种陌生的他者被唤醒,颠覆一种话语习惯实则是改变一种时间结构,人走出主体,不说being,但看到每个当下的“有”。
(三)德里达:语言,永不为人占有
伟大哲学家的背后往往都有个伟大的诗人。海德格尔有荷尔德林,德里达有保罗.策兰。列维纳斯开启了法国现象学的时代,开启了现象学哲学语言的流浪之路。但列维纳斯仍然栖居在语言中,德里达则真正的展开了流浪。对胡塞尔的批判分析、对海德格尔的批判继承、和列维纳斯的不断互动以及对保罗.策兰诗学的分析构成了德里达思想的大致内容。德里达说:“语言,永不为人所有。”
德里达(Derrida,1930—2004)全名雅克·德里达,当代法国哲学家、符号学家、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解构主义思潮创始人。德里达以其“去中心”观念,反对西方哲学史上自柏拉图以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认为文本(作品)是分延的,永远在撒播。
保罗策兰说:“所有事物都少于,它们之所是,所有(是)更多……”①原诗为保尔.科利而作,引自【法】列维纳斯《保罗.策兰:从存在到他者》,王立秋译“Paul Celan: From Being to the Other”),载《专名》(Proper Names; trans.Michael B.Smith,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96.),第40-46页,第174-176页。法国现象学一条脉络里,列维纳斯从他者中找到智慧,用一种不在场的方式说绕开being说“ilya”,有;利奥塔要摆脱元叙事,摆脱元语言,为个别存在者代言。然而这些在德里达看来都不够。他批评西方哲学一直没有摆脱逻各斯中心论或语言中心论,是一种在某种语言框架内的同语反复。海德格尔的语言中有“家”,列维纳斯颠沛流离,说着有这样的存在的分流,但实则离家出走的人也是有“家”的概念在。德里达要流浪,就要到那些语言都没有到达的地方去,这就得突破语言自身。如何突破,用现成的语言突破现成的语言。这种自我突破的边界,作为一个多语言者和犹太身份的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说:我们有习语。
被放逐的人或许没有家,但他们必须有自己。
德里达从未想要在语言中安身立命,正如他所说,语言,永不为人占有——这句话出自《争论中的主权》而这也是我此次想要详细说的文本——人无法占有语言,无法栖息也无法完全栖居,那该怎么办?正如他自己一样,他说:移居。不断的移居。而习语,则是移居的短暂停驻。就德里达看来,我们可以接近语言、达到语言,但却不能占有某种语言。在回忆保罗.策兰的诗学时,德里达如是说:“一个人永远不可能占有某种语言,只有一场对语言的白刃战……我们必须思考的是,当你在语言中寻找最符合语言习惯的最本质的东西时,却不能被占有……”,此外,在《单语的他者》一文中,也有类似提法:“是的,我只有一门语言,但它不是我的……”那我们如何让诗和思发生?如何在语言中留下踪迹?是否这样看来我们,就居无定所了。
德里达认为,我们在习语中不断地移居。习语抵抗翻译,因而附属于语言或身体时间的意指的独特性中。习语意味着专有之物,但绝对和所有物得区分看待。专有,指一种在语言中打上标签的做法(类似列维纳斯的“踪迹”),然后诗便能在标记语言的事件中发生,而在每一次标记中,我们不断移居。即便居无定所,但习语,仍是流浪者的避风港。
三、感性在二维中运作、理性在多维中表达
学科基点,也是学科的悖谬。罅隙让一切的近变成了远,但也让一切的“在”得以自然显现。就此回答两个设问并对大标题进行一次题解。
站在美学的学科基点,面对音响事实和音乐实事,我们该如何听?我们该如何说?此次现象学相关叙辞的梳理过程,也是笔者站在音乐美学学科基点尝试对“听”和“写”的一次尝试性还原。因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既消极又积极的念头,既光怪陆离,又似乎切实可行的想法。在试图弥合听和所听、写与所写、音乐美学与音乐、音响事实和音响(映象)实事之间的罅隙时,笔者产生出如下的尝试自我解答。
如何听:悬置听觉,在听-觉中美事实呈现;
如何说:解构语言,在语-言中美实事显现;
当我们尝试弥合罅隙时,我们便需要罅隙中的智慧。在面对音乐和语言时,我找到两个边界:听-觉、语-言。
(一)选择性是“失聪”,悬置听-觉:美事实呈现
听觉这个造词法,先天地具有现象学的特征。从听到觉,当拆解了熟悉的词,剩余的东西向我们展现,这时候,显现的是未曾显现的东西,是过程,一种指向,具有意向性的意味,又具有sein的分有,在过程中逐渐呈现。听觉,有听然后有觉,但听和听得所获的觉之间这层指向,在我看来是通达音乐美学观照下,美事实呈现的重要途径。我们该如何听?对仗现象学叙辞的断代,从布伦塔诺到胡塞尔,他们思维轨迹中那些开拓性的叙辞,尤其是意向性的提法,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新的“听”,对听的听。哲学诉诸于理性,让逻各斯在场回答问题;美学祈灵于感性,让逻各斯与努斯同时在场,借助理性让感觉在场。于是,在我看来,悬置听-觉的两端,回到“听”行为本身,在听中听,甚至可以让直觉在场,让理性从显到隐。在这里,“五音令人耳聋”有了新的解读,我们可以选择性的“失聪”,失去对表象之物和表象深究的趣味,还原到听,从一定层面对“听音乐”进行直观还原。
(二)回归性“失语”,解构语-言:美实事存在
语言,同样感谢这个词中的隐性和显性的双重意味——无论是索绪尔语言学意味的,还是海德格尔存在说意味的——这种并非单一物化存在的存在者给予我们更诗意地去结构美学语言的可能。而就我个人而言,但凡音乐美学,有着先天的悲壮,面对语言中止时音乐响起的悖论,面对语言需要达到语言所不能到达的彼岸,我们只能无限趋近而永远无法弥合罅隙。因为罅隙是美学生命力的源泉。但是否因此,面对这种边界我们果真无语?在我看来,回归性的“失语”,丢失掉不是语言的语言,回到语言本质力量中去,消解那些在场的描述性的言语、转而揭示某些在场的不在场,让语言自身去澄明某些在场的不在场,揭示某些存在的敞亮。如何找到语言的语言?在我看来,不表征且非模仿,用一种类似隐喻般的话语(有时候隐喻所带给我们的比直截了当的语言文字更多)来呼唤存在者在场。语言和音响,再怎样弥合也是两种存在者,一般语言面对音乐美实事的“存在”,难以完全敞亮。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弃绝从文字中外在置入存在者,如海德格尔引用史蒂芬诗歌中的偈语“词语破碎处,无物先现”。进一步,我进行命题续写:“词语破碎处,存在显现”,通过选择性的“失语”,我们可以在文字的行过程中得到美实事的同构,而最终达成,语-言,美实事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