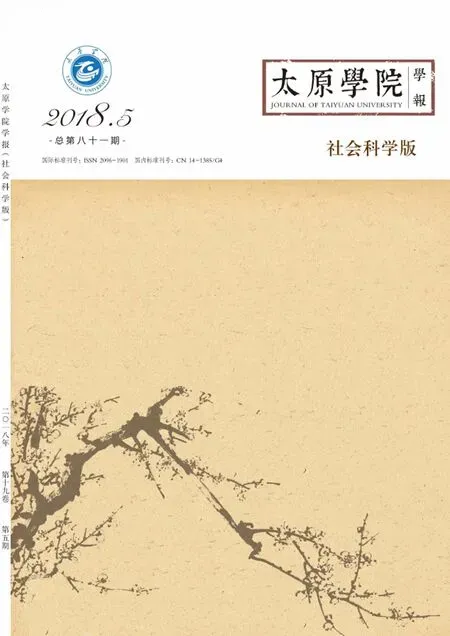隐匿的隐居叙事:赫尔曼·黑塞《德米安》中的社会型隐者形象分析
孟 国 锋
(班贝格大学 班贝格文学文化与媒体研究生院,德国 班贝格 D96047)
作为闻名世界的德语作家,赫尔曼·黑塞在其切入心灵的成长小说中娓娓道出人类生存的孤独状态。发表于1919年的小说《德米安》,正是一部从小主人公辛克莱的视角讲述其成长过程中经历内心彷徨与孤独的中篇叙事文本:在一次偶然的童年游戏中,辛克莱结识了一位年龄较大的同学德米安,并在他的辅导与帮助下,逃脱了小市民阶层的“思想道德壁垒”,走上了通向内心的个体化自由之路;德米安作为心灵导师的形象,在小说中自始至终保持着成熟完美状态,并且总是与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生活在特立独行的自我世界中;正是由于这种完美而孤独的人格特质,辛克莱从德米安的教导中受益匪浅,并且通过第一人称的视角暗示了德米安被隐匿的真实身份:身在城市社会群落中的隐居者——尽管小说中并无此类字眼出现。
在中国的传统隐士文化中,即有“大隐隐于世”的思想,指真正的隐居也可发生在所处人群社会的内置空间中,并不一定要逃离市井而身处荒野。黑塞笔下的德米安,正是这种社会型隐居者,他们往往有较高的学识与能力,然而并不过多参与世事,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在精神生活中。作为特例,辛克莱受到了德米安的成长指导,这种师徒制的教学模式也是德语文学成长小说中常出现的叙事类型,为揭开隐者的神秘面纱提供了契机;在更深层次上,德米安的特立独行也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社会精神空虚凝滞与无方向感的无声批判。
一、他者视角下的隐居者
小说《德米安》从形式上可以看作主人公辛克莱的自传,因此在文本中不仅出现其对自身经历的客观记录,更有对外部世界的主观体验与反思。“两极对立”作为黑塞常用的艺术准则,也能在此篇文本中找到踪迹,正如作为他者的辛克莱,在不断接近德米安的过程中,首先觉察到了德米安的行为模式与自身所处的学生群体并不相容,由此而产生了陌生与距离感:“在我们这群孩子中间,他显得成熟而生疏,更像一个成年人。他不受欢迎,因为他从来不和我们游戏,更不参与打架斗殴。也只有在他用坚定自信的声音对抗老师时,他才提起我们的兴趣。”[1]253在辛克莱的观察中,德米安与其他学生不仅在年龄上有差距,在性情禀赋上更不相同。尽管他身处学生小社群中,然而这个群体内的交友机制对他并无实际影响。他独立而成熟的性格也体现在他“反叛”的一面,即对掌管知识的老师作出质疑,对权威加以挑战,从而使自己在面对外在的教条与规矩时则保持独立意识。
作为社会型隐者,德米安主动与他人保持距离,其本身也没有参与社会融合的需求。孤独成为了德米安的本质标识,并且在辛克莱的记录中跃然纸上:“我看见他去上学,独自或是处在其他学生中间。他显得另类,孤独而安静,独立于任何人,生活在自己的空间与规则中。”[1]272在公众场域,德米安显得稳重沉静,甚至无法让人感受到他的心理状态与情绪波动;作为一个个体,他清楚地执行着“从自身意愿所出的生活规则,而不是出于对社会联结的需要”;[2]32抛开辛克莱自身的青春期叛逆冲动,德米安在一定程度上为他树立了独立人格的榜样,事实上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为后来的“人生辅导关系”做了叙事铺垫;他们之间的距离因此不再是隐居者与普罗大众之间永恒不变的陌生感,而是一种动态的不断接近、相互吸引的张力场。
在辛克莱的观念中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他父母所庇护的干净、明亮、安全的中产市民阶层社会,另一个是充满了不确定因素的“阴暗世界”——正如那个曾欺凌他的来自社会底层的克罗姆。出于对德米安的陌生感,辛克莱甚至一开始将他与克罗姆一起归类到“阴暗世界”中:“德米安绝不属于我们的世界,虽然他与克罗姆不一样,然而他们都是那个世界的人。他是一个拐骗者,将我和那个糟糕败坏的世界连接在一起!”[1]268在世俗的世界观中,市民们不自觉地将与自身不同的阶层或社会群组对立起来,这便直接影响了小主人公对德米安的道德评价。这种对立的心态尽管暂时遮蔽了德米安本身所具备的超越品质,然而正是存在两极对立的世界观有被超越和扬弃的可能性,辛克莱在德米安指导下所走上的独立成长道路才有了现实与叙事的动态演进。
在小主人公对德米安的“初级观察”中,因其视野尚处于人生未启蒙状态,也因受制于市民家庭伦理道德的规则限制,不能识破德米安作为其未来人生导师的身份,两者之间因此也存在着无形的距离。黑塞这种成长小说的开端叙事方式,正是对德语文学中一类隐居叙事模式的继承和发展:在中世纪骑士诗人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的宫廷叙事诗体小说《帕西法尔》(Parzifal,作于1200年左右)和巴洛克时期小说家格里美尔斯豪森的作品《痴儿西木传》(Der Abentheuerliche Simplicissimus Teutsch,作于1668年)中,年轻的主人公在探险的道路上偶遇一位年长的隐士时,一开始都表现为怀疑或抗拒,而后接受了隐居者的辅导教育,通过一段隐居生活促成了自身的成长,为后续的探险人生做下了铺垫;在《德米安》中,隐居的场所已经不再是原始的林野,教化的内容也不再是中古时期的宗教题材,而是整合成为处在现代化市民社会中的个体化独立精神教育。
二、扑朔迷离的谣言
在主人公辛克莱的记录中,不仅有他自身对德米安的观察感受,也有众人对这位神秘人物的种种猜测,特别是对于他宗教身份归属的议论,渐渐演变成为一种无法被证实的谣言:“学校里又有人在传,他其实是犹太人,或是异教徒,甚至他和他母亲共同皈依于某种神秘教派。我甚至听说,他和他母亲其实是情人关系。”[1]273尽管作为大众信息传播渠道的谣言扑朔迷离,甚至其表意也呈现出多样性与模棱两可,然而它还是能被受众广泛相信并继续被扩展传播,逐渐出现多个演变版本。作为社会型隐者,德米安很少与其他学生和其背后的家庭有所接触和交流,他的私人生活也很少与社会公共生活发生重合,例如他不去教堂参加共同礼拜活动;德米安与谣言传播者之间的鸿沟也从侧面渲染了隐居生活的神秘性,使得谣言成为大众讨论时各自发挥想象的空间;在小说中所构建的社会,尽管已具备工业化城市化的特征,在宗教生活中仍然遵循传统的基督教礼拜,教徒在面对不同生活方式和信仰行为时也表现出警觉与保守;德米安的特立独行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统一的市民意识形态与道德准则构成了威胁,因此众人在无意识中通过谣言对其身份进行贬损,甚至将他与其母亲附上乱伦之嫌,他们并未想要追寻谣言后的真相,而仅仅是利用谣言的匿名特征来维护公众的道德秩序。
辛克莱将谣言加入到自己的观察记录中,使德米安的隐士公众形象得以补充和扩展,尽管谣言在事实上充满了负面信息和主流社会的“异质排斥”。人们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中对谣言进行随意的评论和解读,从而使谣言本身的信息呈现不稳定性,从广义上更是体现了整个社会缺乏开放与自省的思想动力;在整篇小说中,德米安的父亲从未出场,这种缺少父亲的家庭结构,一方面使得谣言得以生成,另一方面恰恰暗示了德米安成熟圆满的人格,正是由于从小失去父亲而能获得机会及早历练所成;谣言中主要针对的宗教信仰问题,也是对之后两位主人公之间进行哲学宗教问题探讨所作的叙事预告——正是因为大众统一的信仰规则阻扰了个体意识的自由发展,才使得辛克莱需要德米安在诸如此类问题上给予解答。
三、神秘的“入定”仪式
真正而具象的隐士生活方式在事实上是更加隐匿和让人难以理解的。在辛克莱的记录中,德米安甚至能在公共课堂上悄无声息地进入“入定”状态,尽管身体还处在三维的时空中,然而思想意识像是离开了身体,而这种怪异的行为方式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他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没有呼吸,嘴唇像是木头或石块雕刻所成。脸色苍白,棕色的头发反而成了他身上最富有生机的部分。他的手放在桌上,静止得如同物件一般,也是苍白而毫无动弹。但他绝对不是憔悴无力,而是像有一个坚硬的躯壳包裹着隐秘而强健的生命。”[1]285德米安的“入定”状态并非通过药物或酒精等物质辅助得以实现,而是他将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自身的精神世界内,进而暂时遗忘了周围环境甚至自己的身体,而这种“出神”或“入定”现象,“能将人的主观感知暂时脱离已被安排和组织好了的日常生活,这样的方式便能在个体和文化层面获得神秘的超脱作用。”[3]9德米安通过练习这种反日常的行为,一方面将自身与外在的现实隔离,另一方面也是在辛克莱面前凸显这种行为的仪式性质。“入定”的行为使德米安作为隐士的生活状态极端化,即完全处在自我的精神世界中,他人无法进入;因他的这种行为直接发生在作为公共场所的大讲堂内,虽然并不影响他人听课,事实上构成了对制度化教学模式的挑战——正是在制度化的教育中使人受到了规则的训导,而在进入社会后只能按机械化的模式适应社会规则;德米安的“入定”状态在上下文中只引起了辛克莱的注意,一方面提示了两者之间逐渐发展的辅导与被辅导关系,即德米安演示了作为一个社会型隐者如何在众人包围下专注于自身,另一方面通过这种魔幻的仪式,也塑造了德米安的“魔法师”形象,使其身份在叙事层面具有多样性。
这样一种充满神秘主义的行为,在很多传统社会中具有其合法和积极的一面,然而在一个以知识理性为主导的工业社会中往往会受到质疑和贬低,因为它使人无法管控在有效的理性规范内,进而在一旦爆发扩散的情况下会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德米安的“入定”追溯到了一种远古的宗教仪式,本身具有非理性的隐秘色彩,必然无法被他所处的市民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甚至在一个以基督教为主的社会中,这种异教徒式的行为也无法取得合法性,更加强了其隐士的局外人身份;然而对于辛克莱来说,德米安通过其行为正是“将当下的现实问题化,将此过程的确认作为一种教学模式”[4]40呈现在小主人公面前,并且使其明白,走上个体化发展的道路必然是一条绝对孤独的道路,根本上只能独自完成;“入定”行为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也表明,除了按照大众的意愿生存,也还有更多的适合个体发展的道路,尽管它们显得古怪并有可能导向社会型隐居模式。
四、独行者的宣言
在不断的接近与交流中,辛克莱与德米安建立了深刻的友谊,并一同探讨了诸如“该隐的符号”“阿卜拉克萨斯神”“战争与命运”等问题。这些关乎个体命运的探讨使辛克莱一步步地摆脱了来自市民社会非此即彼的对立意识,逐渐形成了全面的生存论视角,而这一切也显示,他在观察与思考过程中本身所具有的自我分析能力,正是他能与德米安相遇并接受人生指导的前提所在。他不想再返回到“众人的理想生活”中,而是要追求符合自身命运的道路,甚至在一次内心独白中,他想要建立一个“独行者的联盟”:“我们的任务是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孤岛,用另一种方式去生活,也许这会是一种榜样。我明白,过多的团体生活使人失去了独处的机会,因此我不再渴望那种聚众的欢乐和节日的喜庆。”[1]348这种略带非理性色彩的宣言,首先是德米安作为社会型隐者所教育的结果,事实上是德米安的思想在辛克莱身上的映射和积淀。辛克莱脱离了市民道德伦理的制约,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和强大,认识到了通向内心自由之路的可贵,因此希望通过虚构一个独行者的空间,使诸如德米安一类的社会型隐士有容身之地;此处也暗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社会充斥了不稳定的政治和思想因素,社会改革艰难,有能力推行变革的人士只能作消极的斗争,正如此时的作家黑塞因提倡和平反对战争而在德国社会受到非议,只能隐入个人的小世界。
辛克莱在德米安的指导下所形成的“独行者宣言”,某种程度上也是黑塞对尼采“超人哲学”的一次文学解读。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开篇便是查拉图斯特拉经过十年的隐居生活,才创设了“超人思想”,并出山向世人传播,而德米安稳重圆融的人生哲学也是出于在孤独生活中的思索;“超人”的概念一般是指“自由、克服困境与重构价值,同时也带有魔咒般的对崇高和更高存在的期许”,[5]3而在德米安对辛克莱身份意识的教育中也包含了类似的意义;“超人哲学”期望推动知识分子“不断完善自身并构建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5]3而辛克莱走上的正是脱离原有的小市民思想层次进而发展自身命运的道路;尼采的“超人”和黑塞的德米安因此都具有普世的教育责任,特别是在思想意识和关乎人生存最本真的层面所进行的哲学教育,并且两者都衍生出强大而充满创新力量的人格化精神。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黑塞成长小说《德米安》中不同人物叙事视角的分析,特别是主人公辛克莱与其人生导师德米安之间张力关系的解读,揭示出小说叙事层面上被隐匿的社会型隐者形象以及因此所构成的人物互动结构:辛克莱通过自身作为他者的视角,觉察到德米安过着特立独行的生活,并与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不参与团体生活,而小主人公因自身所处的中产阶层视野所限,在初次相遇时并未真正识得他未来的人生导师;针对德米安宗教信仰的谣言一方面暗示了他作为社会型隐者的神秘性质,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市民社会思想意识和道德准则的保守和单一;德米安通过向辛克莱展示奥秘的“入定”行为,对当下的现实和机械化的教条规则提出了质疑,为生存的多种可能性提供了仪式化的范例;通过一系列的宗教哲学探讨,辛克莱终于领悟到了德米安作为独行者的生活真谛,从而坚定地踏上了寻求其自身命运的道路,也即是黑塞所称的“通向内心之路”。此外,正是由于此类社会型隐者在本文中被隐匿,使得叙事本身充满了“魔力”与范本效果,这样一种叙事美学既满足了现实的教育意义,又带有虚幻的色彩和追忆“古典隐居叙事”的倾向,从而在文本内在的层面上促进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美与当代中国年轻群体中对《德米安》的阅读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