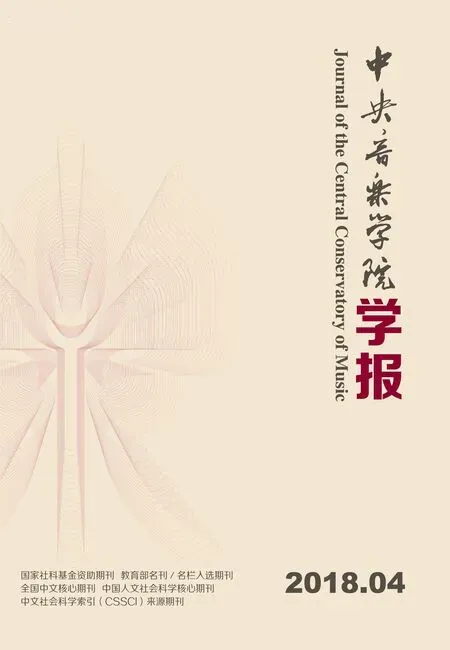勃拉姆斯对“新德意志乐派”的“抵抗”
——音乐史中“历史性”和“艺术性”矛盾的一个案例
沈雕龙
引言
1860年5月,勃拉姆斯(Johannes Bra ̄hms, 1833-1897)从汉堡前往汉诺威参加自己作品的演出,也顺道拜访了好友小提琴家约阿希姆(Joseph Joachim, 1831-1907)。两人闲聊的过程中,谈到了一篇柏辽兹近来所写的报刊专文《瓦格纳的音乐会:未来的音乐》(ConcertsdeRichardWagner.Lamusiquedel’avenir)。之后约阿希姆写信给朋友提到:“一篇柏辽兹的文章,让我最近和勃拉姆斯以及其他爱好艺术的朋友们好好地讨论了一下,那些‘新德意志’们用他们的作品和无所不用其极、伪君子、自吹自擂的宣传手法,对大家产生了有害的影响。……若再不对这些人提出抗议,我们就算不是真的懦弱,也似乎显得太没有原则了;这些虚荣妄为的人,把我们民族的音乐力量迄今创造出来的神圣和高级的一切,都当成是李斯特幻想出来的乱七八糟的杂草肥料。”[注]Johannes Joachim, Andereas Moser ed., Brief von und an Joseph Joachim, Bd.2, Berlin: Julius Bard, 1912, p.80.
让约阿希姆心生愤慨的历史背景,要追踪到19世纪50年代。那段时期,李斯特不断撰文宣称用文学与诗的精神来更新音乐,强调音乐的形式应该要来自于音乐之外的内容。李斯特能写又旁征博引,他借用了黑格尔的思考:诗为各种艺术中层次最高的美学观[注]黑格尔认为,“诗”(文字)虽然和音乐一样,藉由声响的媒介和时间性传播,但“诗”却超越了音乐声响的感官性,能够表达观念,呈现精神性的内容。请参考:薛富兴:《美学导读》,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第77—78页。黑格尔的想法,与19世纪初德国浪漫主义认为器乐以其无以名状的存在成为“艺术之中最浪漫”的理念,刚好相反。请参考:沈雕龙:《E.T.A.霍夫曼的贝多芬第五号交响曲乐评》,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研究》,2015年,第23期,第117—138页。和线性发展的历史哲学观[注]黑格尔认为,“历史所载述的种种沧桑变异,久已在一般上被特解为一种达到更完善,更完美的境界之进展”。〔德〕黑格尔:《历史哲学》,谢诒征译,台北:水牛出版社,第88页;“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之意识的进展(Forschritt)而已。”同前,第30页。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3, pp.32, 74;Richard Tarusk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vol.3, New York/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412-413.进行论述。在1855年他为柏辽兹的《哈洛德在意大利》辩解时写道:“黑格尔早就预料到,当真正能够理解并正确评价标题的人逐渐增多时,标题性定会成为器乐发展的主要源泉”,并认为“在器乐中的标题是一种诗意的解决之道,是一种时代发展进步(Fortschritten)的结果”。[注]Franz Liszt, “Berlioz und seine Harold-Symphonie”, Neue Zeitschrift für Musik, 43(4), 1855, p.49.按着这样的理念,李斯特发展出了交响诗这个新的音乐体裁,也引发了1850年代关于“未来音乐”(Zukunftsmusik)的争议。[注]Ulrich Tadday, “Tendenzen der Brahms-Kritik im 19.Jahrhundert”, in Wolfgang Sandberger ed.,Brahms-Handbuch, Stuttgart: Metzler, 2009, pp.112-125.
一、有争议的“未来音乐”
根据格奥尔格-戴林(Martin Georg-Dellin)的研究,“未来的音乐”(Musik der Zu ̄kunft)这一德语词汇,在1847年起就被用来形容肖邦、李斯特、柏辽兹等人的音乐;[注]Martin Georg-Dellin, Richard Wagner - Sein Leben - Sein Werk - Sein Jahrhundert, München: Piper, 1980, p.876.1849年在法语地区的报刊中也出现“音乐的未来以及未来的音乐”(L’avenirdelamusiqueetlamusiquedel’avenir)标题的文章,来描述李斯特等人的“魏玛集团”(Cénacle de Weimar);[注]Herbert Schneider,“Wagner, Berlioz und die Zukunftsmusik”, in Detlef Altenburg ed.,Liszt und die Neudeutsche Schule, Weimarer Liszt-Studien, im Auftrag der Franz-Liszt-Gesellschaft, Laaber: Laaber, 2006, pp.77-96.根据施耐德(Herbert Schneider)整理出的自19世纪中叶起德语和法语中关于“未来”(Zukunft/avenir)的乐评的表格,19世纪50年代的音乐报刊中开始有越来越多以“未来音乐”(Zukunftsmusik)为题的讨论;这些讨论中最常指涉的作曲家是瓦格纳、李斯特和柏辽兹,甚至偶有舒曼。[注]Herbert Schneider, “Wagner, Berlioz und die Zukunftsmusik”, in Detlef Altenburg ed., Liszt und die Neudeutsche Schule, Weimarer Liszt-Studien, im Auftrag der Franz-Liszt-Gesellschaft, Laaber: Laaber, 2006, pp.80-81.不过,前三个人虽然常被归为同一个阵营,他们不仅在擅长的乐种体裁、作曲原则和个人特色方面不甚相同,[注]请参考以下的分析:Gerd Rienäcker, “Wagner und die Neudeutsche Schule”, in Detlef Altenburg ed., Liszt und die Neudeutsche Schule, Weimarer Liszt-Studien, im Auftrag der Franz-Liszt-Gesellschaft, Laaber: Laaber 2006, pp.201-206.对彼此的认同,甚至对“未来”这词的想法,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注]请参考Beverly Jerold, “Zukunftsmusik/Music of the Future: A Moral Question”, Journal of Musicology Research, 36(4), 2017, pp.311-335;以及Herbert Schneider, “Wagner, Berlioz und die Zukunftsmusik”, in Detlef Altenburg ed., Liszt und die Neudeutsche Schule, Weimarer Liszt-Studien, im Auftrag der Franz-Liszt-Gesellschaft, Laaber: Laaber 2006。跟他们三人立场截然不同的舒曼,则是很明确地从维护音乐形式的立场上反对“未来音乐”的理念,他在1854年于信中私下对友人表示:
我无法认同李斯特和瓦格纳那种党同伐异式的狂热。您所认为的未来的音乐家,我认为是当下的音乐家,您认为的过去的音乐家(巴赫、亨德尔、贝多芬),在我眼里是最优秀的未来的音乐家。我绝不认为,最美丽的形式散发出的精神性美感,是一种已经过时的立场。瓦格纳有这些吗?李斯特杰出的贡献到底在哪里?也许还塞在桌上吧?他要召唤未来,难道是因为,他怕自己现在不被理解吗?[注]Briefe - Schumann-Briefdatenbank, https://sbd.schumann-portal.de/briefe.html?show=1088.舒曼的这位友人Richard Pohl同时也是李斯特的朋友。舒曼此信写于1854年2月6日;三个多月后的5月25日,舒曼收到了李斯特寄来的钢琴作品《b小调奏鸣曲》,封面上写着“献给舒曼”(An Robert Schumann),似乎有回敬舒曼先前信中“贡献还塞在桌上”说法的意味。无论如何,我们今人可以透过这些例子,见识到19世纪中的作曲家们,不仅在文字上交锋以坚持自己的论述,也积极用作品将自己的理念付诸实践。
与李斯特和瓦格纳等人代表的“未来”观相比,舒曼言下之意的“未来”,指的显然是传统中具有足以流传后世的“经典”性价值。[注]尤其自19世纪起,J.S.巴赫、亨德尔、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人,开始在不同的音乐体裁上被赋予这种“经典”(classic/klassisch)的地位。每个人的情况不尽相同,请参考:Hermann Danuser ed., Gattungen der Musik und ihre Klassiker, Laaber: Laaber, 1988.19世纪上半叶器乐领域能继承经典又能指引未来的作曲家,无疑是贝多芬。贝多芬的作品不但有形式上的美感,也有因打破形式而惹人联想的诗意,更有将纯器乐形式结合语言文字和人声尝试的《第九交响曲》[注]19世纪上半叶有关贝多芬音乐接受的文献中译本也请参考:沈雕龙:《E.T.A.霍夫曼的贝多芬第五号交响曲乐评》,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研究》,2015第23期,第122—137页;〔德〕舒曼:《柏辽兹的交响曲》,沈雕龙译,见沈雕龙:《柏辽兹执念的乐音实践》,台北: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第105—124页;〔德〕瓦格纳:《记1846年德勒斯登演出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罗基敏译,罗基敏、梅乐亘:《华格纳·指环·拜鲁特》,台北:高谈出版社,2006,第53—58页。。活跃于19世纪的那一整代作曲家遭遇的难题,就是在面对贝多芬留下来的各种经典作品时,要采取何种路径让自己的作品脱颖而出。如前所述,李斯特明确地抱持以文字内容来引导音乐形式的立场,除了自己发展出交响诗外,他在1847到1860年常驻魏玛担任宫廷乐队指挥期间,亦于重要的纪念场合演出符合他理想的其他作曲家之曲目,例如贝多芬的《合唱幻想曲》《第九交响曲》,舒曼的《浮士德》《曼弗雷德:三段式戏剧诗》,柏辽兹的数首戏剧交响曲。更具有影响力的是,李斯特在魏玛还聚集了一群自己的学生和崇拜者,这些人多为其时有影响力的指挥家、作曲家、演奏家、理论家,他们将李斯特的理念不断向外传播,就连执音乐评论牛耳的《新音乐杂志》(NeueZeits ̄chriftfürMusik),都变成李斯特自我标榜为代表进步与未来的发声筒,形成庞大的舆论势力。
二、“新德意志乐派”一词的诞生
舒曼在1844年为了专心创作而离开了《新音乐杂志》主编一职,该职位于是在1845年由布兰德尔(Franz Brendel, 1811-1868)接手。布兰德尔同时是一位音乐史家,[注]布兰德尔的音乐史专著,包括1848/1855年的《音乐史的基本特点》(Grundzüge der Geschichte der Musik)、1852年的《意大利、德国与法国的音乐史,从早期的基督教时代到当下》(Geschichte der Musik in Italien,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 von den ersten christlichen Zeiten bis auf die Gegenwart)、《当下的音乐和未来的总体艺术作品》(Die Musik der Gegenwart und die Gesammtkunstwerk der Zukunft),等等。他的音乐史观点深受黑格尔《历史哲学》(VorlesungenüberdiePhilosophiederGeschichte)中持续进步(Fortschritt)理论的影响,并以这种观念来看待其时的音乐发展,[注]细节的讨论也请参考:刘彦玲:《器乐曲的“两个事实”Franz Brendel的标题音乐美学》,《台大文史哲学报》,2013年,第78期,第165—208页。在论战中拥护的自然是声称代表“未来音乐”的李斯特和瓦格纳。1859年,布兰德尔广邀欧洲各地的音乐家,在莱比锡举行了庆祝《新音乐杂志》成立二十五周年的大会,会议的核心话题之一就是“未来音乐”,而在布商大厦举行的庆祝音乐会里,也是以李斯特的作品为主。布兰德尔在与会期间发表了一场演说《促进理解》(ZurAnbahnungeinerVerständigung),后来将讲稿发表于同年的《新音乐杂志》。文中,布兰德尔描述了舒曼创办《新音乐杂志》的意义和贝多芬的关系,以及后来出现的问题:
舒曼创办《新音乐杂志》的那个时代,贝多芬的晚期作品还是如同一本七印之书。[注]“七印之书”是《新约圣经》的《启示录》里提到的一种象征性概念;当七道神秘的封印被一一打开时,世界末日即会降临。“七印之书”在德语中是一句成语,意指艰涩难懂的事物。那时,大家急需在贝多芬的基础上,给予音乐继续发展的空间,提供一个方向,为精神性音乐找到一个出发点,而非停留在感官性的音乐。[注]Franz Brendel, “Zur Anbahnung einer Verständigung”, Neue Zeitschrift für Musik, 50(24), 1859, p.265.……舒曼开始了一个新时代,自此,艺术家也要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作品。……召开大会,是为了让意见分歧的大家能够有互相沟通的机会,……同时也是杂志的任务。[注]同注,p.266.……舒曼使得音乐家们纷纷开始撰文表达自己的意见,……越来越多的看法,却也造成无尽的误解和扭曲,让大家都看不清原来的出发点。[注]同注,p.267.
布兰德尔在文中指出这些争议的来源之一,就是“未来音乐”这个名词:
未来音乐这个名词,本身似乎是相当无所谓的,之所以变得越来越重要,是因为它成为党派之争的口号。我建议将这个名称取消。……请准许我建议大家采用一个新的名词:“新德意志乐派”(neudeutsche Schule/ neue deutsche Schule)。[注]同注,p.271.
布兰德尔为支持自己新创的名词,而陈述了他的音乐史观:
巴赫、亨德尔长期以来被称作“旧德意志乐派”(altdeutsche Schule),受意大利影响的维也纳大师们海顿、莫扎特,代表了“古典主义(Classicität)时代”,贝多芬则特别影响了北方的日耳曼人,开启了“新德意志乐派”。……我建议,将整个贝多芬之后的发展,都称作“新德意志乐派”。[注]同注,p.272.
对布兰德尔来说,站在这个音乐历史发展最前端的“新德意志乐派”代表人物,自然是瓦格纳、李斯特和柏辽兹。他对自己的历史发展观无比的自信,写道:
坚决反对我们,都完全是无效的、无理由的、错误的。我们的原则非常全面,也很客观,那些据称合理的反对,只不过是固执的人性弱点,是令人遗憾的行为。[注]Franz Brendel, “Zur Anbahnung einer Verständigung”, Neue Zeitschrift für Musik, 50(24), 1859, p.269.
姑且先不论李斯特、柏辽兹两人属不属于“德意志”民族血统或精神的这个明显争议,光是把“整个贝多芬之后的发展”,都归给瓦格纳、李斯特、柏辽兹和他们主要代表的“标题音乐”,并以此为“新”的进步路线,且以近乎霸道的语气表明自己的话语才符合历史哲学发展的逻辑性,这样的论调,势必在心理层面上伤害了所有不属于“新德意志乐派”的其他音乐家。布兰德尔一文的标题是《促进理解》,文中也不断强调要化解不同阵营间的误解和冲突,然而他讲出来的话,只是一味地呼吁异己顺从自己坚信的方向。意在化解误解和冲突的新名词“新德意志乐派”,明显地比“未来音乐”更有争议性,在往后只是进一步激化支持与反对阵营双方的对立。更何况,布兰德尔发表此言论的《新音乐杂志》,是由曾经反对以瓦格纳和李斯特来代表“未来的音乐家”的舒曼所创办的。
在这段后贝多芬时期,众人因找寻新的发展方向而导致争论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可以理解舒曼在停笔多年后,在1853年再度于《新音乐杂志》执笔为勃拉姆斯美言的《新道路》(NeueBahnen)一文,所代表的特殊的意义。同年10月,年方20的勃拉姆斯在约阿希姆的推荐下拜访了杜塞尔多夫的舒曼。舒曼对这位年轻作曲家的作品极为赞赏,认为他是“音乐的弥赛亚”。[注]据杜塞尔多夫的乐团首席贝克(Ruppert Becker,1830-1904)听舒曼亲口所述。Ute Bär, “Ruppert Becker, Notizen”, in Ingrid Bodsch, Gerd Nauhaus ed., Zwischen Poesie und Musik.Robert Schumann - früh und spät, Begleitbuch und Katalog zur Ausstellung, Frankfurt am Main: Stroemfeld, 2006, p.207.舒曼写到:“音乐中似乎有一股新的力量,正在宣告自己的来临。我怀着热忱,探寻着那些被选中而命定之人的道路……,有一个人一定会突然出现,此人是要被召来,以理想的方式,道出这个时代最高的表现力”。[注]Robert Schumann, “Neue Bahnen”, Neue Zeitschrift für Musik, 39(18), 1853, p.185.舒曼在那个“进步未来”与“传承经典”纠结对立的时代下,发现勃拉姆斯这股“新的力量”;然而,如此盛赞,对照另一个阵营挟带着强大舆论、众口铄金出的“未来音乐”,必然给勃拉姆斯不小的压力:那一个“未来”里,容不容得下舒曼对自己期待的“新道路”?
三、勃拉姆斯的“抵抗”
勃拉姆斯不是那种喜欢公开表达自己想法的作曲家。然而,布兰德尔在《促进理解》一文中,霸道地将贝多芬的继承权归给瓦格纳、李斯特、柏辽兹等人,并且以他们为唯一代表德意志音乐进步的新方向的论调,终于让勃拉姆斯忍无可忍。该文6月10日刊出,勃拉姆斯8月7日写信给约阿希姆,表示“忍不住想开始争辩,写一些反对李斯特等人的东西”。[注]Andreas Moser ed., Johannes Brahms im Briefwechsel mit Joseph Joachim, Bd.1, Berlin: Deutsche Brahms Gesellschaft, 1912, p.249.这两位朋友一直在筹划着怎么写比较好,可是他们写东西的计划似乎拖得很久。来年1860年5月5日,勃拉姆斯写信给约阿希姆:“我们进行的抵抗(Abwehr),绝不能让人想到瓦格纳。我们也必须要以同样的态度处理柏辽兹和弗朗茨(Franz)[注]整封信中,勃拉姆斯并未指明,此处到底是弗朗茨·布兰德尔还是弗朗茨·李斯特,抑或是其他信件中提过的弗朗茨·拉赫纳(Franz Lachner, 1803-1890)或是弗朗茨·符尔纳(Franz Wüllner, 1832-1902),这位“弗朗茨”尚待未来进一步从别的角度求证查明。此外必须一提的是,古往今来的书信往来里所使用的文字语言,常常并非正式完整的用语,甚或有主观和粗鄙的口气和形容。笔者认为,今人将这些第一手外语文献在论文中转译成中文作为“引文”呈现时,应尽可能地体现文字原来的历史和文化状态,以符合学术求真的精神。。大家真的要抵抗的,只有李斯特。”[注]Andreas Moser, Johannes Brahms im Briefwechsel mit Joseph Joachim, Bd.1, Berlin: Deutsche Brahms Gesellschaft,1912, pp.273-274.从相关的信件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勃拉姆斯所谓的“抵抗”,重点在于驳斥李斯特和布兰德尔所谓的“新德意志乐派”,并没有想与瓦格纳为敌。四天后9日的另一封信中,勃拉姆斯又写到:“如果只是要指出作品中的失误,我会指出瓦格纳、柏辽兹和所有相关的人的失误。我们写出来要反对的,就只能是李斯特的那种草率的态度。……我最希望的是,我们只提到李斯特的名字,这样大家就不会指责我们对瓦格纳固执和无情了。”[注]同注,p.279.同一封信里,勃拉姆斯也露出催促的语气“我们发表反对声明的事,现在真的变得很急了,再不出来的话,那些流言蜚语会造成极大的伤害,而且也会削弱这份声明的影响力。”[注]同注,p.280.
勃拉姆斯5月初的这几封提醒性质的信,显然来得太晚了。他和约阿希姆等人先前拟就的反对声明,已经在5月6日的《柏林音乐报:回声》(BerlinerMusik-ZeitungEcho)被公开出去了:
本地的音乐家之间,流传着一份勃拉姆斯、约阿希姆和格林(Grimm)先生的请愿书,他们在其中表达了对未来的音乐家及其阵营的反对,并且要求其他的艺术同行们一起签名认同。他们的声明如下:“这些签署名字的人,长久以来一直在关注某个阵营的宣传活动,还有该阵营的传声筒——布兰德尔的音乐杂志。该杂志持续地散播一种看法,就是‘一流的音乐家基本上都认同了杂志的方向,也承认领导者的作品和这个方向,都具有艺术的价值,也认为在北德进行过了一场有益于未来音乐的对决和争论’。在此签署名字的人认为有义务,要对这样的事实和态度进行抗议,并且至少从他们的角度发表声明,不承认布兰德尔的杂志所说出的种种原则,并且批判和谴责那些新德意志乐派的领导者和其学生的作品,这些作品有时能将所谓的原则付诸运用,有些只是勉强建立了一些越来越新,却劣质的理论,这些作品完全违反了音乐最根本的本质。J.勃拉姆斯、J.约阿希姆、J.格林、B.舒尔茨(Scholz)。”[注]Anonymous, Berliner Musik-Zeitung Echo, 10, 1860, p.142.
勃拉姆斯想针对的是李斯特,但是这样的措辞还是把瓦格纳扯进来了。[注]勃拉姆斯对瓦格纳的态度是越来越欣赏的:1862年勃拉姆斯在维也纳结识瓦格纳时,就帮过其音乐会做抄谱的工作,并仔细地研究了《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总谱;1870年专程去慕尼黑听瓦格纳的歌剧《莱茵的黄金》和《女武神》,也为对瓦格纳不公平的批评发声,甚至曾称赞瓦格纳的音乐为“伟大”(Gröβe)。Max Kalbeck ed., Johannes Brahms.Brief an Joseph Viktor Widmann, Ellen und Ferdinand Vetter, Adolf Schubring, Berlin: Verlag der deutschen Brahms Gesellschaft, 1915, p.88.此外,勃拉姆斯亦曾对汉斯立克(Eduard Hanslick, 1825—1904)称赞瓦格纳的大师性手法,尤其是管弦乐法。Gerd Rienäcker,Detlef Altenburg ed., Liszt und die Neudeutsche Schule, Weimarer Liszt-Studien, im Auftrag der Franz-Liszt-Gesellschaft, Laaber: Laaber 2006, p.201.前面提到的勃拉姆斯信中透露的着急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筹划得太久,尤其这份呼吁携手反对“新德意志乐派”的声明,还要求认同他们观点的音乐家们共同署名,在敌我阵营难分的情况下,支持“新德意志乐派”的人收到这样的联名要求,势必会将此事披露出去。[注]勃拉姆斯和约阿希姆收集到19位签署者。请参考Styra Avins ed., Brahms.Life and Letters, trans., Josef Eisinger, Styra Avi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gy Press, 1997, pp.749-750。此处转引自:Beverly Jerold, “Zukunftsmusik/Music of the Future: A Moral Question”, Journal of Musicology Research, 36(4), 2017, p.334.甚至,抢在《柏林音乐报:回声》发表的前两天5月4日,勃拉姆斯等人的“抵抗”行动早已被当成嘲讽的笑话,刊登在力挺“新德意志乐派”的《新音乐杂志》里:
公开的抗议
这些签署名字的人,期望也能有机会演奏第一小提琴[注]意指“领导众人的声音”。,而且抗议所有挡在他们路上的东西,特别是影响力越来越强的,被布兰德尔博士称作新德意志乐派的音乐方向。在摧毁了这些让签名者不舒服的东西之后,他们要为所有同样好心的人,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乏味又无聊的艺术的兄弟会。
同样受苦的灵魂们请一道入会吧!
消息音乐编辑部
(签署者:)J.小提琴家、汉斯·新道路、拖鞋人(Pantoffelmann)、张三(Packe)、李四、王五(Krethie und Plethi)[注]Anonymous, Neue Zeitschrift für Musik, 52(19), 1860, pp.169-170.
“J.小提琴家”,指的是约阿希姆,“新道路”无疑是勃拉姆斯,前缀的“汉斯”(Hans)是全名“约翰尼斯”(Johannes)的简化,也是德语里极为普遍通俗的名字,“汉斯·新道路”意在暗讽勃拉姆斯不过浪得“新”名,实为朵普通的明日黄花,加上后面那一串端不上台面的名字,这篇《公开的抗议》,显然意在恶意取笑勃拉姆斯一干人等,在进步的“未来音乐”/“新德意志乐派”时代里,还停留在落伍的观念中。勃拉姆斯等人的“抵抗”,在拖延、沟通不良和被抢先讥讽的一连串事件中,完全失去了反击力道,甚至变成“新德意志乐派”的笑柄。就像约阿希姆曾写信给勃拉姆斯说的:“李斯特阵营里的人太善于写了,总是埋伏着伺机而动,且太轻浮,太会诡辩。李斯特太懂得激起大家的热情,然后为己所用”[注]Andreas Moser ed., Johannes Brahms im Briefwechsel mit Joseph Joachim, Bremen: Europäischer Literaturverlag, 2014, p.186.。
勃拉姆斯不是操作媒体的能手,也不善于用文字替自己辩护。一同署名的舒尔茨(Berhard Scholz, 1835-1916)回忆到,希勒(Ferdinand Hiller, 1811-1885)在这次文字“抵抗”的挫败后,曾建议勃拉姆斯:“对此最好的回应,就是创作好的音乐”(Das beste Kampfmittel sei, gute Musik zu schaffen)。[注]Bernhard Scholz, Verklungene Weisen: Erinnerungen, Mainz: J.Scholz, 1911, p.142.于是,勃拉姆斯就像舒曼在《新道路》中说的那般,继续“创作于昏暗寂静中”,等待着,“每个时代中,相契的灵魂间都存在着一种秘密的盟约。只要艺术的真理越来越亮,同时欢喜与祝福遍地,这个属于你们共同的圈子就会越来越紧密”。[注]Robert Schumann, “Neue Bahnen”, Neue Zeitschrift für Musik, 39(18), 1853, p.186.
印证舒曼的话的最好例子,可以观察李斯特的学生、瓦格纳的拥护者,著名的钢琴家和指挥家汉斯·冯·比洛(Hans von Bülow, 1830-1894)对勃拉姆斯态度的转变。比洛在1853年11月读过舒曼的《新道路》后,以讽刺的口吻写信给李斯特:“不管是莫扎特勃拉姆斯还是舒曼勃拉姆斯,都不会妨碍我安稳地睡觉。我等着看他的表现。”[注]Hans-Joachim Hinrichsen ed., Hans von Bülow’s Letter to Johannes Brahms: A Research Edition, Cynthia Klohr trans., Lanham: Scarecrow, 2012, p.xi.三个月后的1854年1月,比洛在汉诺威亲自见到了勃拉姆斯,体验到勃拉姆斯本人的才气和其作品的优秀之处,原本的保留态度转变为对勃拉姆斯的全心接受,且在同年3月就登台演出了勃拉姆斯的《第一钢琴奏鸣曲》;[注]同注,p.xii.1856年,当一位朋友请比洛建议一些独特的钢琴作品时,他答到会“即刻先推荐鲁宾斯坦和勃拉姆斯这两位作曲家的任何作品,然后才是自己的”;[注]同注,p.xiii.1860年当勃拉姆斯等人发起对“新德意志乐派”的“抵抗”时,比洛深不以为然,甚至曾鼓动柏林的音乐家们不要签署这份声明;[注]同注,pp.xiii -xiv.比洛由此对勃拉姆斯产生的反感,直到两人于1866年11月再度不期而遇才化解,之后,比洛又继续演出勃拉姆斯的作品;[注]同注,pp.xiv - xv.1877年,比洛在接触了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后,惊奇地将此作喻为“贝多芬第十”,并将自己的赞誉于杂志《音乐界信号》(Signalefürdiemusi ̄kalischeWelt)中公诸于世[注]同注,p.55.。比洛的评价,对于成就勃拉姆作为“德意志”音乐代表性人物的地位,有着不可抹灭的贡献。
四、进步的概念与音乐作品,对当代的一点反思
勋伯格1947年的文章《进步的勃拉姆斯》,其实向我们证明了“未来的音乐”和“新德意志乐派”等源自19世纪中叶关于进步与传统的争论,依然存在于20世纪的上半叶:他点出,成长于19世纪后半叶的那一代作曲家如马勒和理查德·施特劳斯,所接受的音乐教育同时来自于勃拉姆斯代表的“传统”(traditional),和瓦格纳代表的“进步”(progressive)两种观念;而他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证明如勃拉姆斯这样的经典主义者(classicist)和学院派者(academician),也是一位音乐语汇的伟大创新者,事实上,是一位进步派”。[注]Arnold Schönberg, Brahms the Progressive, in: Style and Idea,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0, pp.52-101.的确,勋伯格能在和声的使用[注]同注,pp.57-59、形式的建构[注]同注,p.61.、乐句的散文化[注]同注,p.71.等方面,为我们指出勃拉姆斯与瓦格纳相比,具有同等、甚至更为进步的地方,然而,按照达尔豪斯(Carl Da ̄hlhaus, 1928-1989)的说法,勋伯格替勃拉姆斯的辩护,依然与音乐史书写的传统对立。[注]Carl Dahlhaus, Die Musik des 19.Jahrhunderts, Laaber: Laaber, 1980, p.211.
近来从达尔豪斯的《音乐史学原理》[注]Carl Dahlhaus, Grundlage der Musikgeschichte, Köln: Hans Gerig, 1977.英译本:Foundation of Music History, J.B.Robinson tra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中译本:《音乐史学原理》,杨燕迪译,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延伸出来的中文研究指出,[注]请参考:杨建章:《历史性和艺术性的两难:从Carl Dahlhaus的“结构音乐史”论历史书写的永恒困境》,《台大文史哲学报》,2004年,第61期,第25—52页;刘经树:《“作品”、结构史、人的历史——达尔豪斯的音乐史编纂学》,《音乐研究》,2007年,第2期,第63—81页;杨燕迪:《音乐史写作:艺术与历史的调解——对达尔豪斯《音乐史学原理》的深度书评》,《音乐艺术》,2007年,第1期,第6—11页;刘丹霓:《达尔豪斯音乐史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以19世纪音乐史研究为例》,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30—34页音乐史书写里,存在着历时叙事的“历史性”和审美自律的“艺术性”,两者间的矛盾与冲突。本文即呈现出一个这样的案例:纵使勃拉姆斯当时在新不新、进步不进步、未来不未来、德意志不德意志的创新与国族等概念之文字交锋上远远屈居下风,而后在音乐史的书写里也不能算是19世纪后半叶最前卫的进步派,他的音乐作品至今依然牢牢地深植于西方古典音乐的学习者、听众、音乐分析家、音乐史家的记忆和讨论里,也依然频繁地被演奏于舞台上。勃拉姆斯能超脱意识形态,凭借的不是文字和读者的力量,而是音乐和听众的力量。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在其《新的非了然性》(DieneueUnübersichtlich ̄keit, 1985)一书中指出:
那些当下本应能够毫无疑虑就当作典范的过去,已经变得黯然失色。现代(Die Morderne)无法再把其他时代当作榜样,建立起自己的指导原则。现代认识到只有自力更生——现代只能依靠自身建立起自己的规范性。[注]〔德〕哈贝马斯:《新的非了然性——福利国家的危机与乌托邦力量的穷竭》,曹卫东译,曹卫东:《赫尔默斯的口误(增订):曹卫东学术译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第82页。原文请见:Jürgen Habermas, Die neue Unübersichtlichkei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5, p.141。此处译文中的“典范”,原文为exemplarisch。
借用哈贝马斯的“新的非了然性”概念,达努泽(Hermann Danuser, 1946)指出,20世纪后叶变成一个指向未来和树立传统之典范业已难寻的时代。[注]达努泽在1988年讲这句话时所暗示的西方音乐发展背景,或许可以从一种比较宏观的“后现代”及其多元纷杂并陈的语境来思考:“后现代:物质、技巧与理性在70年代失去吸引力。进步与增长的信念动摇(68年的动荡),极端求新的压力也减退。前卫性的立场面临危机,大家转向寻求听众与沟通感(不再是五六十年代秘奥之学的态度)。在这个潮流下,主观的感受重新被肯定,然而经常不能免于对自我的过度强调”。Ulrich Michels, Atlas-Musik(Bd.2): Musikgeschichte vom Barock bis zur Gegenwart,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5, p.525.也请参考中译第二版:〔德〕米榭尔斯:《音乐图骥》,主编:杨建章、金立群、沈雕龙,台北:小雅出版社,2017,第525页。他又点出,面对这个情况,吾人依然可以用鲜活(lebendig)的方式对音乐文化的遗产进行反思,而音乐学的任务就是“透过对历史问题的研究,提供对当下更深层的理解”。[注]Hermann Danuser ed., Gattungen der Musik und ihre Klassiker, Laaber: Laaber, 1988, p.17.
笔者身为一位音乐史教学和研究的工作者,寻着达努泽的启发观察到,直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聆听着、演奏着、分析着欧美艺术音乐,探究其历史的发展脉络,并在自己的专业音乐创作中尝试各种西方与东方、现代与传统、当代与中国的元素融合,还追求个性化的展现,实实在在地吻合了当下历史发展趋势和美学概念中“进步”的一端。然而,另外一种常见的呼吁:让自己的作品成为“国际舞台常演曲目”,甚至让作品不只被音乐厅的听众聆听,其关键或许是“艺术性”是否还能在当下的区域性社会或全球化世界的“非了然”多元文化中,普遍地被认可和欣赏的问题。如果,还有这种可能性的话,本文不禁要问,了然地追随着“进步”的概念,是否其实也限制了创作其他“好的音乐”的潜力?
(本论文的构思和完成,要特别感谢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余志刚教授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