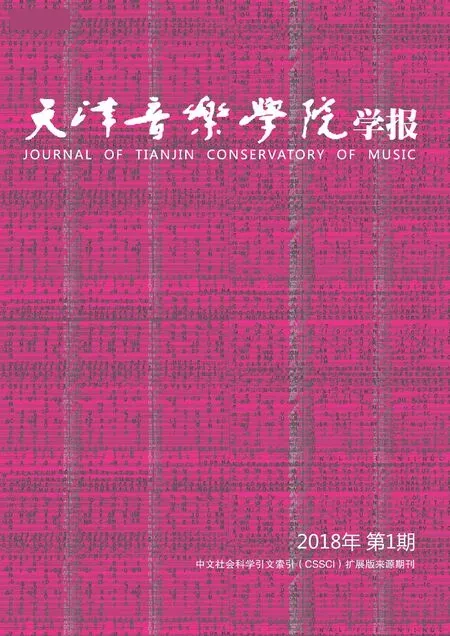朱权与明代前期音乐美学之雅俗精神
谭玉龙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结束了多年的战乱,国家安定、社会和谐,经济逐步恢复与发展。此时期,传统民间音乐艺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民歌、小曲、说唱、歌舞音乐以及戏曲音乐都各具规模,形成了民间音乐艺术异常兴盛的局面。这正如杨荫浏先生所言:“随着大量人口的流入城市,一方面农村民歌大量进入城市,另一方面,从民歌的基础上演变出来的城市小曲,也大量产生,渐渐得到艺人的加工,引起了文人的注意,适应着市民生活的需要,说唱和戏曲,在城市经济特别发达的地区达到空前的繁荣,而反对封建礼教、要求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市民思想也从中反映出来。”①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下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第746页。因此,明代音乐审美意识具有世俗化、大众化的特点,似乎毋庸置疑。可是,当我们细察明代心学转向之前的音乐审美意识时,却发现了与“世俗化”、“大众化”大异其趣的审美品质。具体来说,心学转向之前的明代音乐审美意识呈现出两大倾向:一是以儒家所倡导的雅正、平和为审美追求,要求音乐艺术具有维护统治、教化大众的功用;一是以道家、道教的清心寡欲、逍遥自然为审美旨趣,追求音乐艺术境界之美。而这两种审美倾向又集中体现在了“靖难之役”前、后朱权的音乐审美意识之中,故本文欲立足于朱权,探究明代心学转向之前的音乐雅俗审美意识。
一、“崇雅斥俗”:明代前期官方音乐审美意识
在明朝建立前夕,朱元璋发现由于多年战乱,国家民不聊生,伦理纲常、道德法度近乎泯灭,所以他对刘基、王炜说:“天下兵争,民物创残。……丧乱之后,法度纵弛,当在更张,使纪纲正而条目举。然必明礼义、正人心、厚风俗以为本也。”②《明太祖宝训》卷1,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第2-3页。因此,朱元璋在明朝开国以后将明礼义、正人心、厚风俗、立纲纪作为首要的任务。而历来以“修齐治平”为主要内容的儒家学说自然就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与倡导,从而形成了“以儒为宗”、“独尊理学”的政治政策与文化思潮。这种思潮渗透到了政治、文化、教育、艺术等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了明代心学转向以前主流的文化思潮。而明代音乐审美意识自然也会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与渗透,呈现出儒学化的态势。
太祖朱元璋认为,治道的关键在于教化民众,民俗的善恶就体现了教化的得失,故他说:“治道本于教化,民俗之善恶,即教化之得失也。”③《明太祖实录》卷203,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第3035页。而在儒家看来,礼乐正具有这种教化功用。正如《礼记·乐记》所云:“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④[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29页。因此,将儒学(程朱理学)当作行政的指导思想的明朝统治阶层十分重视礼乐的政教功用。虽然儒家认为音乐具有教化功能,但并非所有的音乐都具有这样的作用。因为只有那种平和、雅正的音乐才有利于社会和谐和道德教化,而与此相悖的郑声、俗乐则会让人们骄奢淫逸、危害国家和社会。孔子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阳货》)⑤[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第2525页。荀子也说:“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荀子·王制》)⑥[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59页。可见,儒家立足于音乐之教化功用而倡导一种“崇雅斥郑(俗)”的音乐审美观。
明代统治者在吸收儒家美学思想的基础上,重视礼乐的道德教化功能。朱元璋说:“礼以道敬,乐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为治。”⑦《明太祖实录》卷66,第1245页。而在他看来,元朝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元时古乐俱废,惟淫词艳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虏之声与正声相杂,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饰为舞队,谐戏殿廷,殊非所以导中和,崇治体也。”⑧《明太祖宝训》卷2,第141页。因此,朱元璋要求:“一切流俗喧譊淫亵之乐悉屏去之。”⑨《明太祖宝训》卷2,第141页。据《明史·乐志》记载,朱元璋在明朝建立之初就“立典乐官”,随即又“置雅乐,以供郊社之祭”,然后将元末明初音乐家冷谦招为协律郎,命他“考正四庙雅乐”、“校定音律及编钟、编磬等器”。⑩[清]张廷玉:《明史》第5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00页。明代宗朱祁钰也十分重视音乐的教化功用,他于景泰元年“请敇儒臣推演道德教化之意,君臣相与之乐,作为诗章,协以律吕”,以达“振励风教,备一代盛典”之目的。⑪[清]张廷玉:《明史》第5册,第1508页。质言之,朱元璋、朱祁镇等明代统治者所采取的正音律、去淫声的政策其目的其实是“锐志雅乐”、“欲还古音”⑫[清]张廷玉:《明史》第5册,第1499页。而排斥“喧譊淫亵之乐”,即通过音乐来教化百姓、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就体现出明王室在音乐的审美性和功能性之间,更重视功能性的一面。这与原始儒学、宋明理学对待音乐的观点相一致。
儒家美学所推崇的艺术,不仅对于人民大众来讲要具有教化功用,还要对统治者有谲谏的作用。这也就是《毛诗序》所说的“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⑬[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271页。。朱元璋非常赞同艺术的“谲谏”功能。洪武七年,他命令翰林院侍臣撰回銮乐时说:“古人诗歌辞曲,皆寓讽谏之意。后世乐章,惟闻颂美,无復古意。夫常闻讽谏,则使人惕然有警。若颂美之辞,使人闻之意殆,而自恃之心生。盖自恃者日骄,自警者日强。”⑭《明太祖宝训》卷4,第271页。因此,朱元璋从艺术之讽谏功能角度出发,倡导古乐而排斥今乐。另外,朱元璋“崇古抑今”是因为他意识到了古乐具有“和而正”的特点,而今乐则“淫以夸”,因此,古乐可以节制人民欲望而后世之乐则刺激、放纵人们的欲望。他说:“古乐之诗章,和而正;后世之歌词,淫以夸。古之律吕,协天地自然之气;后之律吕,出人为巧智之私。”⑮《明太祖实录》卷162,第2521页。质言之,朱元璋倡导古乐排斥今乐,是因为雅正、和谐之古乐有利于节制民欲,让人心保持平和,而淫逸、浮夸之今乐则让人放纵、骚动,危害社会安定。正是在明统治阶层的推动下,明代音乐审美以雅正、和谐为正统与主流。明初冷谦《琴声十六法》倡导“不轻不重”的“中和之音”(《轻》)⑯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第778页。也是这种音乐审美思潮的反映。因为冷谦认为:“和为五音之本,无过不及之谓也。”(《和》)⑰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第781页。所以,所谓“中和之音”就是一种符合儒家温柔敦厚、尽善尽美的雅正、和谐的音乐,这也是冷谦所倡导的琴乐之最高审美境界。
在明代“以儒为宗”、“独尊理学”的环境下,儒家的经典自然会得到了人们的重视。永乐年间,《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三部书的纂修完成,这让儒家经典正式以官方的形式确定下来。明成祖朱棣说:“厥初圣人未生,道在天地;圣人既生,道在圣人;圣人既往,道在六经。六经者,圣人为治之迹也。六经之道明,则天地圣人之心可见,而至治之功可成。六经之道不明,则人之心术不正,而邪说暴行侵寻蠹害。”(《御制性理大全序》)⑱周群、王玉琴校注:《四书大全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依此而论,儒家雅正的美学思想随着其经典的地位的确立而成为明代正统的审美观念。作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认为“经之所包,广大如斯”,儒家五经“各备文之众法”,因此“世之学文者其可不尊之以为法乎”(《白云稿序》)⑲[明]宋濂:《宋濂全集·銮坡前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94页。。《诗》、《书》、《礼》、《乐》(指《乐记》)、《易》是一切人文之源,所有从事文学之士都必须要以这五经为标准与楷模。从音乐美学角度看,《乐记》的地位在明初统治阶级尊“经”的政策之中得以提高。宋濂说:“《礼》之《檀弓》《乐记》,非论说之极精者欤?”(《白云稿序》)⑳[明]宋濂:《宋濂全集·銮坡前集》,第494页。可见,《乐记》被视为论说“极精”的经典。虽然宋濂在哲学上认为理在“心”,“心”即道、即太极,礼乐皆本于心。但是他仍然在《乐记》美学思想的影响下,重视礼乐在社会中的教化功用,他说:“说体莫辨乎《礼》,由吾心有天序也;导民莫过于《乐》,由吾心备人和也。”(《六经论》)㉑[明]宋濂:《宋濂全集·潜溪前集》,第72页。此外,他与《乐记》一样否定桑间濮上等淫靡之音,因此,他说:“桑间濮上,危弦促管,徒使五音繁会而淫靡过度者,非文也。”(《徐教授文集序》)㉒[明]宋濂:《宋濂全集·芝园后集》,第1351页。明成祖朱棣敕撰的《永乐琴书集成》中也蕴含着这种音乐审美意识。《永乐琴书集成·弹琴总诀》引刘向《琴说》云:“凡鼓琴有七例:一曰明道德;二曰感鬼神;三曰美风俗;四曰妙心察;五曰制声谓;六曰流文雅;七曰善传授。”㉓范煜梅:《历代琴学资料选》,四川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07页。这显然是《乐记》、《毛诗序》之音乐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强调音乐应具有道德内容,发挥政教作用,从而使国家安定、社会和谐。
要言之,明朝建立以后,统治者采取了“以儒为宗”、“独尊理学”的政治政策,将儒家学说定位官方哲学,赋予了儒学正统的地位。这种文化思潮影响着明代心学转向以前社会的方方面面,而音乐审美意识自然也包含其中。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明王室十分重视音乐的社会教化功用,而能起到教化民众、平和人心作用的音乐,只能是儒家所推崇的雅正、和谐之古乐。所以,明代前期音乐审美意识大体呈现出“崇雅斥俗”、“厚古非今”的特点,并将传统儒家所推崇的“雅乐古音”视为最高的审美理想。
二、“大雅正音”:朱权“崇儒尚雅”的音乐审美倾向
作为朱元璋的第十七个儿子,朱权自小在宫中就接受严格的儒学教育。宋濂、桂彦良等儒臣受朱元璋之命为太子、诸王传授儒学,所以朱权的学术思想自然受到明代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朱权在他的诗文中大赞周公、孔子等儒家圣贤,并且大力倡导儒家那套礼乐制度、文章典则等,如:“天无为而万物生,无争而万物成者,自然之道,非人力也。至若礼乐制度,文章典则,出乎人者也,必有所始。先圣制之于前,百王法之于后,开物成务,其功大矣。”(《原始秘书序》)㉔[明]朱权辑:《原始秘书》,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刻本。由此可见,朱权的学术思想在明代正统思想的影响下而具有“崇儒”的色彩。
这种“崇儒”的正统思想体现在朱权文艺美学思想之中就表现为“尚雅”。孔子曾删《诗》以倡雅正、和谐的审美风格,后之宋儒继承、发扬孔子之观念而追求至中至正之道,而朱权认为孔子和宋儒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一种“思无邪”的审美理想。他说:“孔子删《诗》以明教化,是使异端邪说不得以害正道,其功大矣。后濂洛诸儒而又发明其理,以开万世至中至正之道,而学者得其宗矣。……今得诗五百三十余篇皆得诗人之体,而其言无一字为浮屠之说,得儒者之正。……使后之作者不流于淫辞诐说,则亦可以思无邪矣。”(《〈颐安文选〉原序》)㉕[明]胡俨:《颐庵文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51-552页。我们暂且不论朱权对佛教的评价是否得当。朱权十分赞赏孔子删减《诗经》的做法以及宋儒发扬孔氏之理的行为,因为他们达到了排斥异端邪说、阐明至中至正之道的目的,实现了艺术的“思无邪”。而这种“思无邪”的创作标准正是“儒者之正”,即儒家美学之正道。朱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自己的雅正的审美观,即要求艺术必须“道性情、该物理、叙风化”(《〈颐安文选〉原序》)㉖[明]胡俨:《颐庵文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7册,第551页。。这也就是他对儒家美学之“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㉗[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270页。的继承与发扬。
儒家美学对“文”十分重视。孔子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㉘[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第1985页。,就说明“文”这种修饰对于艺术来说非常重要。朱权则更加形象地说:“有其诗而无其文,如舟之无水,不能以行远。”(《斗南老人集序》㉙[明]胡奎:《斗南老人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3册,第355页。“文”的基本含义是纹饰,也可用来指文字或典籍,后来在儒家那里指礼乐制度。㉚张毅:《儒家文艺美学——从原始儒家到现代新儒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申言之,“文”在儒家看来,就是人类从原始社会发展到文明社会的标志。“言之无文”、“有其诗而无其文”虽然指艺术需要一定的修饰,但其更深的内涵则是艺术需要符合“礼”的规范,否则就会“行之不远”。朱权还引用元代周德清的话说:“凡作乐府,古人云:‘有文章者谓之乐府,如无文饰者谓之俚歌,不可与乐府共论也。’”㉛[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卷上《古今群英乐府格势》,《涵芬楼秘笈》第9集,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第5页。可见,“文”、“文章”、“纹饰”在朱权的审美观念中成为划分雅与俗(“乐府”与“俚歌”)的标准。朱权重视艺术之“文”,其实就是要让艺术符合“礼”,从而达到雅正、和谐的审美标准。这也是其“崇儒尚雅”观念的具体体现。
儒家美学强调“礼”的规范作用,艺术必须要符合“礼”的标准。宋儒周敦颐说:“礼,理也;乐,和也。礼,阴也;乐,阳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通书·礼乐》)㉜[宋]周敦颐:《周濂溪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9页。这说明“礼”统摄着“乐”乃至所有艺术,因为“礼”已经成为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及其规律的“理”了。朱权在《古今群英乐府格势》中,对元代的马东篱、张小山、李寿卿以及明代的刘东生等乐府作者尤为推崇,并将他们放在了众人之前。我们本着一个人的审美批评通常与他的审美趣味和见解相一致的观点认为,朱权对马东篱等人的推崇一定意义上反映出了他个人的审美意识。朱权评价马东篱的词为“典雅清丽”㉝[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卷上《古今群英乐府格势》,《涵芬楼秘笈》第9集,第6页。、张小山的词“清而且丽、华而不艳”㉞[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卷上《古今群英乐府格势》,《涵芬楼秘笈》第9集,第6页。、李寿卿的词“雍容典雅”㉟[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卷上《古今群英乐府格势》,《涵芬楼秘笈》第9集,第7页。、刘东生的词“无谶翳尘俗之气”㊱[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卷上《古今群英乐府格势》,《涵芬楼秘笈》第9集,第15页。。他们的词具有共同的审美特点——“典雅”而无“尘俗之气”。而“典雅”与儒家美学所倡导的“礼”相一致。“礼”作为一种节制,要求审美创作“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㊲[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第2468页。,达到一种“温柔敦厚”(《礼记·经解》)㊳[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1609页。的审美效果。这也就是汉代扬雄倡导的“诗人之赋丽以则”(《法言·吾子》)㊴汪荣宝:《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9页。的审美标准。朱权所推崇的四位乐府作者,如张小山之词,正符合了儒家这种“温柔敦厚”的审美原则,因为他们的词“清而且丽,华而不艳”。所以,我们从朱权的审美批评中见出了一种“温柔敦厚”的雅正的审美态度。
由以上论述可知,朱权的雅正文艺美学思想植根于儒家学说之中。而他的音乐审美意识又植根于他的雅正文艺美学思想之中。因此,他排斥“郑卫之淫声”而弘扬“雅乐”。㊵[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卷上《词林须知》,《涵芬楼秘笈》第9集,第42页。朱权吸收我国古代的雅乐律制,用汉儒“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观念来解释“五音”,将五行、五德、五色、五方等与五音融为一炉:
宫:属土,性圆,为君。其色黄。在天符土星。于人曰信。分旺四季。
商:属金,性方,为臣。其色白。在天符金星。于人曰义。应秋之节。
角:属木,性直,为民。其色青。在天符木星。于人曰仁。应春之节。
徵:属火,性明,为士。其色赤。在天符火星。于人曰礼。应夏之节。
羽:属水,性闰,为物。其色黑。在天符水星。于人曰智。应冬之节。㊶[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卷上《音律宫调》,《涵芬楼秘笈》第9集,第40页。
朱权之“五音”说将音乐扩大到了整个社会乃至整个宇宙,使“整个宇宙也都仿佛音乐化了”㊷蒋孔阳:《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蒋孔阳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28页。。因此,他倡导雅正之乐,因为只有雅正的音乐才能保证五德、五常、五色、五行等相互和谐、平稳渐进。这也是他提出“得五音之正,故能感物化气”㊸[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卷上《音律宫调》,《涵芬楼秘笈》第9集,第41页。之说的缘由。而在所有的乐器中,“琴”被朱权视为最能代表“雅正”的乐器。这是因为:“琴之为物,圣人制之以正心术,导政事,和六气,调玉烛,实天地之灵器,太古之神物,乃中国圣人治世之音,君子养修之物,独缝掖黄冠之所宜。”(《神奇秘谱序》)㊹[明]朱权编纂:《臞仙神奇秘谱》上卷,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1956年据明刊本影印,第1页。可见,琴器、琴乐被朱权视为“天地之灵器”、“太古之神物”,其根本原因乃是琴乐是一种“治世之音”,琴器是一种“修养之物”,它具有“正心术,导政事,和六气,调玉烛”之功能。一言以蔽之,琴能让天地万物、国家社会保持安定、和谐的状态。朱权高扬“琴”,乃是他雅正音乐审美意识的具体体现。
朱权推崇雅正之音,是因为雅正之音有利于国家安定、社会和谐,同时,他还注意到了社会对音乐的反作用。他在《太和正音谱序》中说:明朝建立三十多年来的“礼乐之盛”、“声教之美”是因为明朝三十多年来的“天下之治”,另外,“近而侯甸郡邑,远而山林荒服,老幼瞆盲,讴歌鼓舞”都是为了“乐我皇明之治”。㊺[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序》,《涵芬楼秘笈》第9集,第1页。《礼记·乐记》认为音乐是产生于人心的,如“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㊻[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2527页。、“乐者,心之动也”㊼[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1536页。。朱权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夫礼乐虽出于人心,非人心之和,无以显礼乐之和;礼乐之和,自非太平之盛,无以致人心之和也。”㊽[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序》,《涵芬楼秘笈》第9集,第1页。其实,朱权并非认为社会环境可以直接作用于礼乐,而是需要“人心”作为中介。因为音乐是由人心之动而起的,而人之心又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他认为明代开国以来的社会和谐、国家安定造就了人心之和谐,而人心之和谐又创造了和谐之音乐。据此而言,朱权在儒家传统音乐美学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音乐与社会互为影响的学说,从而倡导雅正、和谐的音乐,因为雅正、和谐的音乐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国家的安定,同时雅正、和谐之音的出现也意味着国家、社会的安定、和谐。
如前文所述,朱权赞赏孔子删减《诗经》的行为,因为这使得艺术具有了“思无邪”的审美特点,从而彰显了儒家“至中至正之道”。因此,朱权仿照孔子删《诗》而删琴曲之“小雅”。他在《神奇秘谱·大雅》解题中说:
是曲者,周公之所作也。大概周建邦本,贵乎同姓,以天下为家,以家人治之。故不致于异类之倾覆,而能开八百六十七年之国,致使享国最为悠久而不坠。按《诗经》云:“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有大小之殊,先儒有正变之别。“正小雅”乃燕乡之乐;“正大雅”乃朝会之乐、受厘陈戒之辞。懽欣和悦,以尽群下之情;恭敬齐庄,以发先王之德。是以词气不同,音节亦异,致有“大雅”、“小雅”之别。予故删其“小雅”燕乡者而不用,独取其“大雅”正声之音而订正之。㊾[明]朱权编纂:《臞仙神奇秘谱》下卷,第12页。
一方面,朱权认为作为燕乡之乐的“小雅”不能入“正声”,因为他心目中的“正声之音”只有“大雅”。因为作为朝会之乐、受厘陈戒之辞的大雅之乐既是欢欣和悦的,又是庄重严肃的,它既能“尽群下之情”,又能“发先王之德”。也就是说,“大雅”之乐符合了孔子所说的“尽善尽美”(《论语·八佾》)㊿[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第2469页。、荀子所讲的“美善相乐”(《荀子·乐论》)[51][清]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82页。的标准。另一方面,朱权崇尚这种“大雅正声”其根本目的是维护朱明王朝的统治,是其“亲亲”思想的体现[52]姚品文:《宁王朱权》,西雅图艺术与人文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他所向往的“周建邦本,贵乎同姓,以天下为家,以家人治之。故不致于异类之倾覆,而能开八百六十七年之国,致使享国最为悠久而不坠”,也正是他推举大雅正音的缘由,因为他想通过这种雅正的音乐让朱明王朝千秋万世、永享太平。
简言之,朱权的音乐审美意识是其文艺美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他的文艺美学思想又与其“崇儒”的正统思想相一致。作为明王室成员之一的他,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倡导雅正的音乐审美意识而排斥郑声淫音。因为,“大雅正音”能维护王朝的统治、安定社会、和谐人心。这都体现出朱权具有的“崇儒尚雅”的音乐审美意识,而这种审美意识是在明代官方意识形态下所孕育出的。
三、“托志翀举”:朱权音乐审美之自由精神
朱权作为皇子,在音乐审美意识方面具有浓厚的儒家色彩,“隆雅崇雅”成为他音乐审美观的重要特点之一。但这并不能完全概括出朱权的音乐审美意识,因为在他的音乐审美意识之中还有道教的维度。据《国朝献征录·宁献王权》记载:“宁献王讳权,高黄帝十六子也。生而神姿朗秀,白皙、美须髯。慧心天悟。始能言,自称大明奇士。好学博古,诸书无所不窥。旁通老释,尤深于史。”[53][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宁献王》,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47页。朱权自小外貌出众,才华横溢,博览群书,同时“旁通老释”。此“老”并非指老子,而是指道教。清代查继佐《罪惟录·宁献王权传》称朱权:“性机警多能,尤好道术”,朱元璋还曾夸奖他“是儿有仙分”。[54][清]查继佐:《罪惟录·传三十六卷》卷四《宁献王权传》,上海涵芬楼影印吴兴刘氏嘉业堂藏手稿本。同时,净明忠孝道的典籍《净明宗教录》中还有《涵虚朱真人传》。据该传,朱权号涵虚、臞仙,具有净明忠孝道道士身份,著有《神隐》、《肘后奇方》等道教著作。[55][清]胡之玟:《净明宗教录》,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9-170页。
据姚品文女士研究,朱权一生“信奉道家,尊重儒家,排斥佛家”[56]姚品文:《宁王朱权》,第127页。。《明史·宁献王权传》记载,在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后,朱权被“改封南昌”,他迫于政治上的压力,为了保全自己,而“自是日韬晦,构精庐一区,鼓琴读书其间,终成祖世得无患”,到了仁宗时,他又“日与文学之士相往还,托志翀举,自号臞仙”。[57][清]张廷玉:《明史》第12册,第3592页。由此可知,“靖难之役”乃朱权人生之一大转折,亦是其学术思想的转折。“靖难”之后,朱权进入了其人生的“托志翀举”时期[58]姚品文:《宁王朱权》,第113页。,即由儒入道,追求长生不死、羽化成仙的归隐时期。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我国古代其他典籍中发现,朱权虽然好道归隐,但始终没有减弱其对音乐的兴趣,尤其是对古琴偏好。如《朱氏八支宗谱·宁献王事实》记载,在燕王朱棣即位后,将其改封至南昌,“王自是日韬晦,构精庐一区,读书鼓琴其间,终帝之世得无患”[59]朱兆藩等修:《朱氏八支宗谱》,盱眙务本堂刊本。。可见,“靖难”之后,“琴”始终伴随着朱权的归隐,成为其逍遥自然、修道成仙之生活的一部分。因此,“靖难之役”亦是朱权音乐审美意识由儒入道、由入世到出世的转折点。
卿希泰先生曾说:“道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而得名,相信人们经过一定修炼可以长生不死,得道成仙。道教以这种修道成仙思想为核心,神化老子及其关于‘道’的学说,尊老子为教主,奉为神明。”[60]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而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学者对“得道成仙”的不同理解,“得道成仙”又被赋予了不同称谓与描述。如隋代王通所说的“天隐”就是其中一例。王通《文中子·周公篇》曰:“至人天隐,其次地隐,其次名隐。”[61]王心湛:《文中子集解》,广益书局1936年版,第27页。《文中子·周公篇注》曰:“藏其天真,高莫窥测”乃天隐,“避地山林,高身全节”为地隐,而“名混市朝,心在世外”就是名隐。[62]同注。“能藏其天真”之“至人”就是“天隐”,这其实就是道人们追求的长生不死、羽化成仙的最高境界。而“地隐”只是远离尘俗、隐居山林,“名隐”则在尘世之中,保持一颗寡欲之心。朱权则说他的隐遁方式是不同于王通“三隐”的“神隐”,如其《神隐序》曰:
予之所避,则又不同矣。各有道焉。其所避也,以有患之躯,遁乎不死之域,使吾道与天地长存而不朽。故生于黄屋之中,而心在于白云之外;身列彤庭之上,而志不忘乎紫霞之想。泛然如浮云,飂然如长风。荡乎其无涯,扩乎其无迹。洋洋焉,愔愔焉,混混沦沦,而与道为一。若是者,身虽不能避地,而心能自洁,谓之神隐,不亦高乎?[63][明]朱权:《神隐》,《藏外道书》第18册,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309-310页。
可见,朱权之“神隐”有其独特之处。因为“黄屋”、“彤庭”都喻指皇宫。而“神隐”则可以出生在“黄屋之中”,生活在“彤庭之上”,但同时又要“心在于白云之外”、“志不忘乎紫霞之想”。总之,“神隐”就是“身虽不能避地,而心能自洁”,最终达到“与道为一”。这也就是一种在尘出尘、尘中修真的境界。另外,朱权诗文中的“达人”与“神隐”相通。他在《庄周梦蝶》解题说:“是以达道之士,小造化于形骸之外,以神驭气,游燕于广漠之墟,与天地俱化,与太虚同体。”[64][明]朱权编纂:《臞仙神奇秘谱》下卷,第30-31页。他在《神奇秘谱序》中言:“盖达人之志也,各出乎天性不同。于彼类不伍于流俗,不混于污浊;洁身于天壤,旷志于物外,扩乎与太虚同体,泠然洒于六合。”[65][明]朱权编纂:《臞仙神奇秘谱》上卷,第2页。由此而言,朱权之“达人”与“神隐”之人一样,具有超然物外、与道合一的品格,是一种“不伍于流俗、不混于污浊”的超凡脱俗之人。
“神仙”为道教之核心信仰,它既是道教的宗教追求,也是其人生追求,还是其审美追求。因此,道教美学是一种境界美学,它追求长生不死、羽化成仙的境界之美,即“道-美”、“仙-真”之境。所以,朱权之“神隐”、“达人”乃是其向往的最高的审美境界。而“琴”则对他实现“神隐”、“达人”的境界有巨大的帮助。
“琴”作为一种乐器,它本身就不是一种凡夫之器而是由圣人制作的,可以养人性、合造化。朱权说:“孰谓大道在天而人远,孰不知道之于人者尤近矣。且夫人生两间,禀乾坤之气,得阴阳之精,可以夺造化、抟阴阳。故圣人制琴以养性。”(《新刊太音大全集序》)[66]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北京古琴研究会编:《琴曲集成》第1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3页。他还说:“琴之为物,得天地之正音,可以感神明而合造化之妙。是以有道之士得之于心,应之于手,发乎丝桐,律为音声,以合神明之德。”(《新刊太音大全集序》)[67][明]朱权编纂:《臞仙神奇秘谱》上卷,第93页。在朱权看来,“琴”囊括了阴阳乾坤、造化神明,它似乎就是大道的体现。这正如台湾学者弘熹所言:“古琴本身构造就充满着传奇的象征色彩,包含天、地、人;年、月、日;山、水;龙、凤;北辰,五行,阴阳太极等,就像一个小宇宙。”[68]弘熹:《古琴揭密》,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古琴就是一个“小宇宙”,那么对于琴师来说,演奏古琴则可使人有旷达、雅适之意,最终使人与道冥合。朱权说:“矧琴,为娱性之乐”(《〈颐真〉解题》)[69][明]朱权编纂:《臞仙神奇秘谱》上卷,第46页。、“壁间有琴,可以乐吾之志”(《神隐下卷序》)[70][明]朱权:《神隐》,《藏外道书》第18册,第311页。。鼓琴不是为了外在的目的,如维护统治、安定社会等,也不是满足庸夫俗子所追求的感官享乐、欲望满足,而是为了娱性、乐志。娱性、乐志就是琴所带来的超越俗趣雅美的“雅适、旷达”[71][明]朱权:《赓和中峰诗韵·序》,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重刊本。之乐。这种乐只有有道之人才能获得,所以朱权说:“予之所以异于人者,乐人之所不乐,而独乐其所乐也。”(《壶天神隐记》)[72][明]朱权:《神隐》,《藏外道书》第18册,第274页。另外,鼓琴使人雅适、旷达之后,就通向了存在之域。朱权描述他自己鼓琴时的状态说:“于是乎予抱三尺之桐,神游于千古之上,回淳风于指下,发遐想于胸中,是以放浪形骸,怡悦性情,故不为世所隘,飘飘然出乎造化之外,俯八纮而游苍茫,吸元炁而饮沆瀣,纵神辔于太虚,弭璚节于天府,此则心与道契,气与神合者也,岂非道之在人为近者欤?”(《新刊太音大全集序》)[73][明]朱权编纂:《臞仙神奇秘谱》上卷,第93页。可见,朱权对音乐的看法已超越了“靖难之役”前那种指向世俗社会的功利性、工具性,而转向了自我、自然。鼓琴之时,即自我之心与大道冥合之时,自我生命与宇宙无间之时,道不离人,人道合一。鼓琴将人导向了道教追求的存在之域——神仙境界,也是朱权所讲的“神隐”、“达人”之境。
朱权不只是从琴器、琴乐以及鼓琴出发表达他超凡脱俗的音乐审美意识的。他还从音乐接受者角度,阐发了琴乐的境界之美。朱权一再强调《神游六合》、《阳春》、《白雪》等琴曲是庸人俗子无法欣赏的,所以这些琴曲总是“曲弥高而和弥寡”[74][明]朱权编纂:《臞仙神奇秘谱》上卷,第22页。。朱权认为,琴本身就是一个“小宇宙”,琴曲又指向了存在之域,鼓琴之人又是游于方外的清闲隐士。所以接受者也必须具备与之相应的境界,成为达人隐士、神仙中人,才能得以闻之。例如朱权说:《酒狂》一曲表达的是阮籍“叹道之不行,与时不合。故忘世虑于形骸之外,托兴于酗酒,以乐终身之志。其趣也若是,岂真嗜于酒耶。有道存焉,妙妙于其中,故不为俗子道,达者得之”[75][明]朱权编纂:《臞仙神奇秘谱》上卷,第35页。。可见,世俗之人认为此曲表达就是对酒的嗜好,而达人才真正能领悟此曲之中的“忘世虑于形骸之外”的超凡脱俗之志。因此,朱权倡导听琴者要培养一种“澹然与世两忘,不牵尘网,乃以大山为屏,清流为带,天地为之庐,草木为之衣,枕流漱石,徜徉其间”[76][明]朱权编纂:《臞仙神奇秘谱》中卷,第35页。的情怀,做到“拂却是非心,收拾圜中计”[77][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卷上《天上谣》,《涵芬楼秘笈》第九集,第93页。,这样才能成为一名“控鹤乘鸾”[78][明]朱权编纂:《臞仙神奇秘谱》上卷,第13页。之士,通过琴曲飞升到与道同化的太清之境。
香港学者张世彬曾说:“儒家以为音乐配合礼教,调节人情,而直接控制宗庙朝廷之乐;道家以为音乐当歌颂上古自然生活,描写理想境界,而潜伏于民间音乐。”[79]张世彬:《中国音乐史论述稿》,香港友联出版社1975年版,第456页。此说颇合“靖难”前、后之朱权音乐审美意识之不同。靖难之前,朱权“被服儒雅”[80][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宁献王》,第47页。,礼乐并举,将音乐视为一种政教工具,而靖难之后,却由入世转为出世,注重音乐的境界之美。他在《茶谱》中说:“话久情长,礼陈再三,遂出琴棋,陈笔砚。或庚歌,或鼓琴,或弈棋,寄情物外,与世相忘。”[81][明]朱权、[明]田艺衡:《茶谱煮泉小品》,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2页。如果说“靖难”以前,朱权持有一种礼乐刑政、政教纲常相统一的音乐审美意识的话,那么靖难之后,他却向往着琴棋书画、品茶行酒相融合的音乐审美情趣。前者指向了天下太平、社会和谐的入世精神,后者则通向了寄情物外、与世相忘的太古淳风。前者代表的是儒家雅正的音乐审美追求,后者则表现了道家、道教之超凡脱俗的境界之美。
由以上分析可知,“靖难之役”以后,朱权心中的道教审美情怀被完全点燃,他的音乐审美意识由儒而入道,由礼乐而转向琴曲,由乐教而归复自然。儒家的雅正之乐在此时已经不在是他追求的目标,他所要追求的是那种能体现超凡脱俗之境界的至音、大音。因为,这样的音乐有助于人达到“神隐”、“达人”的境界。
结 语
明朝开国以来,统治者采取“以儒为宗”、“独尊理学”的政治、文化政策,使得社会各个方面皆以儒学、理学为准则。此时期的音乐审美意识亦如此。如果将朱元璋、宋濂以及“靖难”之前的朱权等人的音乐审美意识视为“走路”的话,那么“靖难”之后的朱权以及明代前期全真教高道们的音乐审美意识则是“散步”。法国学者保罗·瓦莱里(Paul Valery)曾说:“走路象散文一样有一个确定的目标。这一行为的目标是我们所想达到的某个地方。……但每次达到目标后这些动作都被废除了,好像被动作的完成、被目的的大道所吸收了。”[82][法]保罗·瓦莱里:《诗与抽象思维:舞蹈与走路》,郑敏译,《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41-442页。可见,“走路”总是指向一个外在的目的,它本身是一种工具,伴随着外在目的的实现,作为工具的它的意义也逐渐消逝了。所以明代统治阶层礼乐并举,将音乐视为政治教化的工具,而倡导一种雅正、和谐的音乐审美观,其实就是一种指向外在于音乐艺术之目的的一种“走路”。而“散步”则是一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没有计划,没有系统”,但是“散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在路旁折到一枝鲜花,也可以在路上拾起别人弃之不顾而自己感到兴趣的燕石。无论鲜花或燕石,不必珍视,也不必丢掉,放在桌上可以做散步后的回念”。[83]宗白华:《美学的散步》,《宗白华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84-285页。可以说,“散步”超越了外在的目的、刻意的安排从而指向了人的存在本真,在任性逍遥之中获得那自由的乐趣。靖难之后的朱权就进入了这种“散步”的审美境界,他将音乐从尘世中拉出,音乐的目的不再指向社会、政治、道德等,而是转向了音乐本身境界之美的展现,以及助人达到自然逍遥、得道成仙的自由之境。对于朱权个人来讲,他具有儒道兼采的音乐审美意识。“靖难之役”是他音乐审美意识从“崇儒尚雅”转向追求“超凡脱俗”的转折点。但对于整个明代音乐审美意识来说,雅正、和谐的音乐审美观念虽然得到了明王室认同与推广,成为了当时的主流审美意识,但这并不能代表当时的整体审美风貌。因为,“靖难”后的朱权以及此时期的全真教高道在琴学上倡导的那种“无弦”之境[84][明]何道全:《随机应化录》,《道藏》第24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38页。,皆可说明除了“崇雅斥俗”、“崇儒尚雅”的主流音乐审美意识以外,在心学转向之前还存在一股既不同于儒家之“雅”,也不同于明代中叶以后市民审美趣味之“俗”的追求超凡脱俗、超越雅俗对立的音乐审美之潮。这也告诉我们,明代前期虽然统治阶层在思想领域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但是在音乐雅俗审美观乃至整个音乐审美观念方面,却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因此,明代前期音乐审美意识是整个明代音乐审美意识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不能只注重心学转向之后的音乐审美意识,而对心学转向之前的音乐审美意识置之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