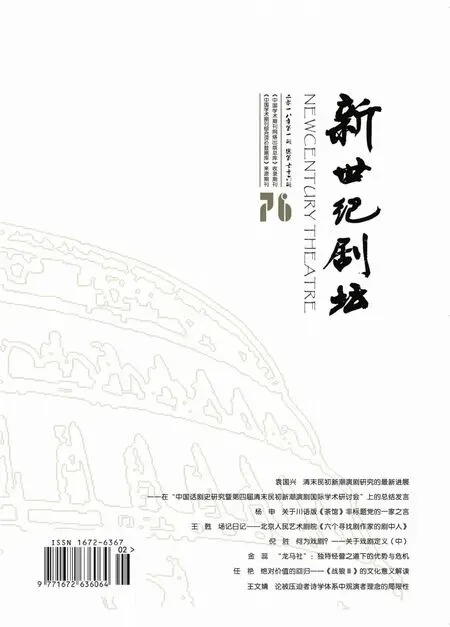论被压迫者诗学体系中观演者理念的局限性
观演者(spectator-actor)是巴西戏剧家奥古斯都·博奥于上世纪70年代在《被压迫者剧场》中提出的重要概念。在布莱希特体系的基础上,博奥再度提升了观众的主体地位,观众有权化身演员登台上演自己生活的戏,不再让角色代表其思考或行动。观演者的出现意味着传统观演关系中“第四堵墙”的彻底消亡,拓宽了戏剧的人际交流模式,使戏剧的社会功能得到极大提升。然而,“革命的预演”的火热理想背后,观演者理念是否真正脚踏坚实的土壤?一方面,观演者对于现实生活的摹仿基于个体的主观认知,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客观依据与普遍意义。另一方面,以文本的开放性、参与的民主化为特征的被压迫者戏剧本身具有不可控性。“革命的预演”或促使观演者形成丧失理智的共同体,反而演变成与博奥所谓的“亚里士多德悲剧压制系统”同质异构的产物。
2000年,英国学者戴维·戴维斯在《博奥是马克思主义者吗?》中指出,博奥并非遵循布莱希特的唯物辩证法,而是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对被压迫者进行着不切实际的改造,由此深化了我们对观演者理念局限性的思考。
一、观演者的培养机制
长久以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体系在剧场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博奥认为,在亚氏诗学体系统摄的剧场中,“观众采取一种被动的态度,把行动的权力委托给舞台上的角色人物。”[1]它利用了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在移情与净化的作用下,观众与主人公在情感上经历了从高度统一到相互疏离的过程,观众的个性被灌输的意识所替代,戏剧得以在潜移默化中达到规训教化的目的。到了20世纪20、30年代,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手段为演员与角色、观众与角色之间制造距离,观众的主体意识开始苏醒,幻觉剧场的麻醉作用被彻底祛除。但是,人们依然被禁锢在观众席间,行动的权力仍属于舞台上的角色。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既然戏剧可以作为压迫者的工具,那么也可以是反抗者的武器。沿着皮斯卡托、布莱希特的脚步,博奥的被压迫者剧场将观众的参与从思想层面扩展到行动层面,“被解放的观赏者,作为一个全人,踏出了行动的步伐”[3],冲破了戏剧与生活的界限。
博奥对观演者的培养实验在1973年8月进行,该实验是秘鲁整合性识字计划的一部分,面向当地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众。他注意到外部压迫给弱势群体的身体带来的改变:被禁止与地主直视的农民多年后与陌生人交谈时依然低垂着双眼,不同职业的人身体肌肉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博奥称其为“肌肉性异化现象”[4]。因此,恢复原初的身体,即重新激活身体的创造力便成为被压迫者诗学培养观演者的核心。
博奥通过四个阶段促进观众对身体的认知与开发,分别是了解身体、让身体具有表达性、戏剧作为语言以及戏剧作为论述。参与者被邀请来体验各种角色,仅限使用肢体语言进行交流,释放出长期压抑的“本我”力量,无形中他们已经在进行简单的戏剧性演出了。到了第三阶段,参与者逐渐开始利用身体语言进行戏剧创造。在同步编剧法的训练中,演员演出由民众提供剧情的短剧,戏剧在事件发展面临危机时暂停,这时参与者可以修正演员的动作或语言,演员则根据他们的建议演出相应的剧情。“这项行动不再以定论的方式呈现,不再将事情视为不可避免的命运……一切都可以被批判、被修正,一切都可能被改变。”[5]在“形象戏剧”中,博奥借助“活雕像”的形式让参与者再现某一印象深刻的生活片段,从现实形象、理想形象与转化形象三方面复盘,持有不同看法的参与者可以从中实现充分的交流。到了“论坛戏剧”这一模式(博奥后期“立法剧场”的雏形),参与者则完全“介入”到一场完整社会问题的演出,相较于同步编剧法训练,他们获得了将自己的观点转化为“行动”的权利,通过“革命的预演”综合分析各种行动的合理性,最终得出解决方案。第四阶段,博奥提出了一种前期具有周密的剧本安排,而有待演出现场随机因素填充剧情的戏剧形式,称其为“景象式戏剧”。其中,最典型的隐形戏剧指的是在自然环境下,面对非观众的群体发生的戏剧。这就要求演员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激发出戏剧最大的能量。
二、个体摹仿的主观性
作为布莱希特的追随者,博奥追求的是一种务实严肃的戏剧,强烈的社会政治诉求意味着他的实践甚至是牺牲艺术性的。纵观被压迫者诗学系统,从恢复观演者身体的表达性到“革命的预演”直到终极目标——实现真实的社会行动,“革命的预演”是支撑整个系统运转的枢纽。然而,正是在这里博奥背离了唯物主义,陷入了唯心主义,我们可以发现观演者理念在实践中的两个不合理性。
其一,观演者的摹仿建立在个体对压迫者的主观认知之上,本质上是观演者精神意志的显露。博奥曾这样描述观演者的表演机制,“被压迫者创造了关于他的真实的意象。接下来,他必须用这些意象的真实来表演。……如果用意象表演,他必须进行第二次推断,即从他的社会真实到他的世界的真实。为了改造第一世界(社会的),他在第二世界(美学的)中进行实践。”[6]
戴维·戴维斯一针见血地批判博奥的戏剧实质上是一种“意象戏剧”。他认为,“‘被压迫者的戏剧’演绎了这一错误观念,压迫者的形象是在被压迫者对于他们的感知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接着参与者们被要求,根据他们对一个总体上不准确的现实状况演绎的观察而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法或主意。一位主角也许会依据一个受压迫戏剧工作坊所提供的建议进行表演,结果也许会因为这个行动而遭致破坏。”[7]
从戏剧行动的角度来看,布莱希特与黑格尔的区别在于前者认为人是他所对应的社会力量及自身行为的客体,人物的行动受社会关系制约,而后者则认为人是绝对精神的主体,戏剧行动是人物精神意志外显的产物,被压迫者戏剧恰恰倾向于后者。在假定性的空间之下,观演者脱离社会关系的摹仿与理式隔了三层,“革命的预演”容易沦为观演者意志矛盾宣泄的空间。由此,我们认为,被压迫者戏剧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不能改善被压迫者的处境,“只能使观演者在自己虚构出来的世界中得到虚假的、暂时的满足。”[8]这无疑是相当危险的。
其二,在观演者与行动两者间关系的处理上,博奥的不干涉决定了被压迫者戏剧作为人的解放是一场伟大尝试,而作为“革命的预演”注定是一场缺乏方向的行动。博奥在“被压迫者诗学”一章开宗明义,“要了解这项被压迫者的诗学,必须将它的主要目的谨记在心:把人民——观赏者,剧场景象中的被动实体——转变为主体、转变为演员、转变为戏剧行为的改革者。”[9]博奥的重心始终放在促成观演者行动的实现上,而如何通过有效的行动达到反抗压迫的目的,博奥则鲜有提及。这似乎就可以解释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前后被压迫者诗学的内涵发生了重大转折。当我们试图全面了解压迫者剧场的演出内容时,会发现博奥对于“压迫”的认识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存在一定偏差。博奥早期主张通过戏剧改变现存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到了80年代末,受妻子精神分析学研究的影响,博奥从外在的压迫转向对个体内部压迫的关注。“革命的预演”开始将目光投注在家庭琐事的调解上,诸如妇女如何向背叛的丈夫复仇、家中该由谁照顾年迈的母亲等等。“压迫”外延的拓展意味着问题核心的转移,人类普遍性的反抗转化为个人意志的抗争。因此,与其说博奥是致力于改造社会的斗士,他更像是一个十足的人道主义者。
在论坛戏剧中,博奥充分尊重民主化的交流,不会对观演者的行动妄加评判,也不会对问题本身进行评估。他认为,如果有人表示赞同,那意味着在某些观演者之间产生了共鸣,但并不代表这种方法比其他方法高明。他强调,“这是一种共同学习的形式,和60年代的做法相比,戏剧家们好象是全知全能的,并且总是去教观众该如何去做。而在我们的戏剧形式中,我们会问观众,您觉得我们该怎么做,然后我们再共同完成这部戏。”[10]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彻底否认观演者的局限性,而是反复强调行动本身的意义所在。“即使他是在一个虚拟的状态下执行……在虚构的局限中,经验却是具体的。”[11]博奥的被压迫者诗学构建了一个不完整的体系,在充分提高人的主体性的同时,行动的导向被忽视了。经验往往不可靠,戏剧与生活亦无法等同。
三、群体行动的盲目性
“社会不同的方方面面只能被理解为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它们各自独立时不具备任何意义。将整体分解为‘最简单的单位’仅仅是一个初试,为的是把它们重组为‘由许多单位和关系构成的丰富的整体’。”[12]
群体是博奥戏剧实践中的重要概念,被压迫者戏剧中最突出的一点即在于充分给予观众入侵舞台的自由。强调观众对戏剧的介入与早期工人演剧运动有一定的关联,比如演出环境的嘈杂,演出内容与生活的贴近性,演出的业余性质等。谢克纳在《环境戏剧》中指出,参与“是把一个美学事件转变成一个社会事件——或者是把焦点从艺术幻觉转向剧院中所有人(如演员和观众)中间的、潜在的和实在的一致性。”[13]作为政治戏剧,参与可谓衡量被压迫者剧场实践成败的临界点。基于改造现实的渴望,群体的入侵使戏剧回归到原本的戏剧性的不确定性上来。
在博奥看来,传统的观演割裂的剧场是已完成的死寂剧场,他希冀着一种类似原始戏剧的新形式,“被压迫的人们重新恢复了原本属于他们的酒神颂歌般的剧场:人民自由自在地在户外高歌,戏剧成为狂欢节、成为人民自己的庆典。”[14]
“排演式戏剧”作为一种开放的戏剧形式具有不可控性。即使在(剧本)“已完成”的“隐形剧场”中,演员要想把控局面实际上也很难说。博奥试图利用群体效应达成预料以外的效果,与此同时却严重忽视了群体传播的盲目性。博奥曾批判亚里士多德悲剧压制系统将舞台与观众所处的世界并置,误导人们在真实的环境中做出不切实际的判断。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悲剧压制系统是创作者对观众实施的压迫,那么,博奥的被压迫者剧场则潜藏着观演者群体对个体压迫的危险。后者不仅仅是作用于心灵的压迫,更是一种立体化的感官震慑。“革命的预演”或促使观演者形成丧失理智的共同体,反而在行动层面陷入亚里士多德悲剧压制系统的另一极端。
普列汉诺夫曾以野牛舞的例子说明类比在原始思维中的意义。北美洲红种人跳野牛舞,一般在缺少食物的情况下进行,可以说,野牛舞作为功利活动与红种人的生存休戚相关。“他们企图通过模仿与希望出现的现象相似的动作,把这些现象召唤到现实生活中来。”[15]这与被压迫者剧场中观演者的心理机制似乎是相通的。“这些剧场形式的演练,创造了对于不健全事物的焦虑感,而且必须由真实行动才能得到满足。”[16]当亚氏的观众进入安稳的嗜眠状态,博奥的观演者则进入宣泄阶段,将潜在的怜悯与恐惧抛向现实,现实与预演之间的差距则会形成尖锐的矛盾。尼采认为,“当人由于根据律在其某个形态中似乎遭遇到例外、从而突然对现象的认识形式生出怀疑时,人就会感到无比恐惧。如果我们在这种恐惧之外还加上那种充满喜悦的陶醉……那么,我们就能洞察到狄奥尼索斯的本质。”[17]与此同时,在“沉默的螺旋”效应与亚氏移情作用的共同影响下,个体意志被碾碎,整体性得以加强。
那么,问题要归结为移情吗?在《关于共鸣在戏剧艺术中的任务》中,布莱希特极力反对移情在观众间滋生。他认为,“这种共鸣(一致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对于一定的历史阶级意味着一个大的进步,但越来越成为进一步发展表演艺术社会作用的障碍。”[18]科学时代的观众,他的情绪应该是由知识驱动的,出于无知而产生的情绪是毁灭性的。博奥在《被压迫者剧场》中并未彻底反对移情,相反,他提到,“好的移情作用不会阻挠(对行为理由)了解,相反的,它必须明确地了解(行为理由),以避免戏剧景象转变成某种情绪狂乱状态,也避免观众洗涤自己的社会罪恶。布莱希特所做的,基本上在于强调对行为理由的清楚了解(启蒙)。”[19]事实上,博奥的实践越过了布莱希特的思想启蒙阶段,因而,观演者的行动是带有盲目性的。
博奥的被压迫者诗学是随着社会环境变化而不断发展深化的理论体系。从《被压迫者剧场》到《立法剧场》《欲望的彩虹》,实现了从群体到个体、从社会到心理、从显在到内在的转变。尽管他的理论存在一定理想化倾向,在群体因素的把控上欠缺了合理的考量。不可置疑的是,作为20世纪左翼戏剧的一支重要力量,博奥对被压迫者群体的人道主义关怀使得他的大胆尝试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其观演者理念不仅修正了传统观演关系中演员与观众不对等的状况,使观众成为了有行动力的全人。同时,极大地激发了戏剧这门古老艺术的魅力与能量,使戏剧真正成为为民众所主宰的艺术形式。
注释:
[1][巴西]Augusto Boal. 被压迫者剧场[M].赖淑雅译.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48
[2]参看[德]卡·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6
[3]同[1]166
[4]同上175
[5]同上186-187
[6]转引自[英]戴维·戴维斯.伯奥是马克思主义者吗?[J].戏剧艺术,2000(5):16
[7]同上17
[8]陈世雄.现代欧美戏剧史(下)[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1161
[9]同[1]165
[10][巴西]奥古斯都·博奥.奥古斯都·博奥论戏剧——1995年1月27日在英国曼彻斯特绿屋的演讲[J].戏剧艺术,2004(2):23
[11]同[1],198
[12]同[6],20
[13][美]理查德·谢克纳.环境戏剧[M].曹路生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51
[14]周宁.西方戏剧理论史(下册)[M].福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1146
[15]陈世雄.戏剧思维[M].福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222-226
[16]同[1],198-199
[17][德]尼采.悲剧的诞生[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4
[18][德]贝·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M].丁扬忠等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175
[19]同[1],143
——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