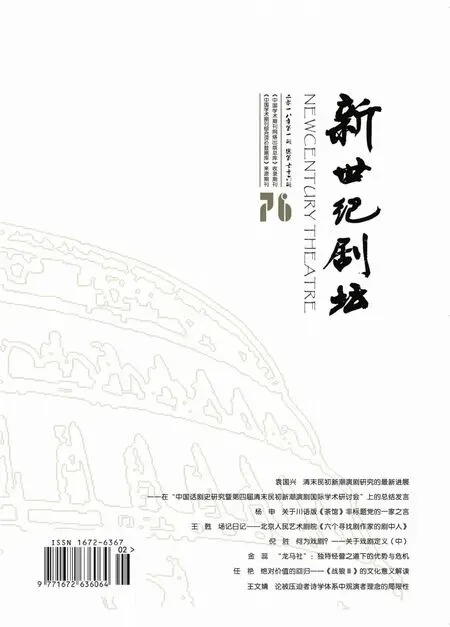关于川语版《茶馆》非标题党的一家之言
写这篇文字之前和之中,我的心里是有许多矛盾的。有的可说,有的不可说。
记得十余年前在彼得堡留学时,列夫·多金曾对我说,如果对一个戏不能明确自己是否喜欢,那么其他的评论是没有价值的。
我想他说的有道理。
然而川语版《茶馆》的出现,却让我对他这句话产生了犹豫。
因为我无法用单纯的喜欢或者不喜欢来评价这部戏,因为它所涵盖和产生的问题与思考,早已超过了戏本身的艺术范畴。
2006年我开始写评论,后自2010年起进入剧院做导演开始创作后,因各种原因而封笔不写,有时看了戏后觉得不吐不快,也只是偶尔在朋友圈内略有提及一些观剧感受。而川语版《茶馆》的出现,则首次让我忽然有了再写一篇文字的冲动,或者说是感受到了写评论的挑战感,就像是一个考核,既要真实地表达自我感受,又要考虑和联想到许多更深更广的问题。
当然,这篇文字真不算所谓的剧评,无论是相比于官方剧评家、戏剧专家,还是公众号剧评家等等,都有很多不足。我只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不争不吵。
我想,先用几句话来表达我个人最简单和直接的“真实与联想”:
首先,我对于李六乙导演可以将中国戏剧最“引以为傲”的经典作品予以新的排演,表示在精神层面上的最大敬意!
其次,无论是“茶馆”“茶棚”“茶广场”,都仅是舞台呈现方法,核心在于对原有剧本是否带来了新的解读与表达。而这些解读与表达对原剧本是延伸与拓宽,还是节选与侧重,则可供探讨。导演将自我艺术审美与价值观念赋予戏中,自然是对的,但却有是否处理合适、是否流畅与刻意之别。
再次,川语演绎北京故事,并非戏好戏差的本质问题。但不同语言所带来的不同演绎效果也确实不能忽略。
最后,一部戏本身的艺术讨论自然有必要,但更大的价值不仅是就戏论戏,更在于这部戏所产生的对戏剧发展的影响。
下面逐一聊聊以上感受的初衷。
一
世界戏剧范畴,其实并无中文“经典”这一直译之词。这仅是中国对于一些作品的“最高评价”。当然,这一词在近年间已经被用滥,甚至许多戏刚刚首演不久,便被冠以“经典”“新经典”等样式称号。当然,这大多是宣传噱头或者是定调儿需要。原先的“经典”意味着不可改动与不可复制,而现在的“经典”则仅仅是自我意淫的忽悠产物。与之相伴的,也是“大师”层出不穷,甚至组团结伴。于是之先生曾说“大师不能满街跑”,然而目前却早非如此,许多戏与人皆是,但与此文此戏无关,也就不一一列举了。
但如果必须谈到并且承认“经典”一词在中国戏剧中存在,那么《茶馆》应当是首当其冲的。尤其是戏剧人在面对世界戏剧自我鼓励的时候,《茶馆》则永远是最先与最后甚至唯一唯二的选择与举例。这就像是一块遮羞布,仿佛只要拿出,便可以掩盖中国戏剧艺术羸弱的现实。许多人总喜欢说《茶馆》在欧洲演出多么受欢迎,被洋人喝彩的事情以为佐证,但却忽略了这已经是数十年前的短暂“风光”。
我个人不否认《茶馆》的艺术造诣,也不止一次地观看该剧。直到今日,我依然认为,北京人艺的老版《茶馆》(焦菊隐版)是中国戏剧艺术性和民族性的最高峰。
然而冷静下来,把怀旧与自我标榜卸下之后,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果非说是经典,那么究竟是《茶馆》剧本经典,还是焦菊隐版《茶馆》的演出经典?从民族自豪感来说,我当然希望二者都是。但当我联想到诸如莎士比亚、契诃夫等剧作与相应演出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度与可塑性,却又对《茶馆》剧本没有了信心。
优秀的剧本,不受时间、空间、地域限制,可以通过各种形式来表达原有内容,甚至随着世界的发展与创作者的思维不断推进而产生新的解读与表达。从这个角度来讲,《茶馆》的原剧本是没有优势的。它受到了时代、环境、民族的制约,不可能完全带入到世界其他地方与文化的范畴中来生根发展(它的内容语境有很大限定,对于北京之外的地方排演,尚有难度,何况国外。下文会详细说),但北京人艺的老版《茶馆》演出却又是出色的,而这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老舍个人的文笔,而在于这部戏是由焦菊隐先生率领一批演员在排练场共同完成的。换句话说,真正的《茶馆》不是裁缝设计好给模特穿的,而是模特自行展示自身特点后再让裁缝量身定做的。这也正是为什么只有北京人艺老版《茶馆》深入人心并让人永远怀念,也正是为什么当年梁冠华等演员版的《茶馆》演出时,有很多人大呼“不如于是之版《茶馆》”的原因。同样的一个导演的同一版本,为何会产生如此说法?真是梁版的演员们自身水平不如于版的演员吗?恐怕也不见得。但之所以产生差异,是因为前者是“演得像”,后者是“他就是”的区别。前者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带着模仿痕迹的束缚发挥,而后者则是自由创作并让自己特点给人物进行了标准化塑形。
正因为北京人艺的老版《茶馆》的出色,加上近数十年中北京人艺的“茶馆垄断”(鲜有听闻其他剧院排演该话剧),让人们把剧本与演出等同,成为了中国戏剧最大的也是最后的“面子依靠”。然而从一部剧作来说,如果全国仅有一家剧院能够排演,那么这不是牛逼,而是悲剧。同样,一部戏如果数十年都按照一个样式去排演,那么不仅是悲剧,而且是停滞甚至倒退。当然,革新与发展需要勇气,更需要实力。因此为了未来的发展,需要允许争议甚至包容失败。这是历史进程的必然。观众可以怀念曾经的美好,但创作者却不应该在丰碑面前一味敬仰和回忆。毕竟,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创作者在离去,观众们也在离去。社会在变,人也在变。强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之世界戏剧地位,尚无法让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其导演版本的戏至今,为何不能将《茶馆》摆脱回忆而放眼未来呢?
当然,这是从创作精神的角度谈的,如果具体到艺术,那么自然会形成比较。无论是“今不如昔”还是“更胜从前”都是合理的观剧感受。因为每个观剧者的好恶不同、经历不同、目的也不同。从观众角度讲,这种差别无需争议,各持己见便可。但从创作者角度讲,则不应停留在历史的某一辉煌时刻,否则说好听了是敬畏,说难听了就是懒惰、怯懦与无能!
目前北京人艺的老版《茶馆》,想看被称为“最经典”的于是之版本,只能去看视频录像;想看“经典”版本的可以去首都剧场看梁冠华版本,但长此以往,下一个焦菊隐导演版本的继承者、或者说下一个王利发又会是谁呢?戏一成不变,仅仅是更换演员,那么当初说“梁冠华不如于是之”的人,会不会有一天再说“xxx不如梁冠华”呢?如此发展,那《茶馆》是不是就会成为一部“情景再现”的怀旧拷贝?等再过数十年之后,现在的许多人都已经离去,当年的历史环境已经真的成为书本上的介绍时,还会有人再关心和议论该剧版本“孰优孰劣”吗?我想,这不应该是“到时候再说”的问题吧?
所以,我说我对李六乙导演的创作勇气,表示最大的敬意。因为他在试图打破一些东西,让更多的剧院用“经典”之外的方式来表达。从目前的观剧效果来看,的确产生了两极分化的评价,但从戏剧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件“利远大于弊”的好事。
二
在李六乙版的《茶馆》之前,也曾出现过林兆华版的《茶馆》,从舞台设计上,林的版本被戏称为“茶棚版”。如延续这种戏称,那么李版也可以被叫做“广场版”。虽是幽默,但也直接反映了他们与焦菊隐导演版本在艺术呈现上的不同。
作为导演的二度创作,舞台呈现的风格是最能鲜明表达自己解读的手段,这一点从创作上是无可非议的。但重点并不在于简单的视听传达,更是在于导演是否能够通过舞台呈现来准确表达自己的思路,以及这一思路与原剧本之间的异同。

焦菊隐版《茶馆》

林兆华版《茶馆》

李六乙(川语)版《茶馆》

川语版《茶馆》
导演在表达时,对于原剧作无非三种可能:完整再现;内涵拓宽;截取所需。
这三种可能从原则上来说并无对错,仅是创作者态度与角度问题。但如果本着是否尊重原作的基础,那么可以衍生出“是否解构”“是否增删修改”“是否断章取义”等诸多手段。这些手段正是导演在二度创作时的工作,从原则上来看,也无对错之分,只有戏是否被观众接受的区别。
在观看李六乙版本《茶馆》时,我能明确看出导演表达的“野心”(非贬义),甚至在其中看到了许多“针砭时弊”“影射现实”的想法。当然,这仅是我个人感受。导演时而婉转时而直白地把自己的想法蕴藏在剧中,甚至不惜用一些看似“云山雾罩”的处理来保护自己的想法不被伤害。这不仅仅是艺术美学上的,更是解读以及时效上的。他所要的,就是让观众在“似明似不明”之间的思考与取舍。
这些表现,从我个人感觉来看,充分理解,但并不喜欢,当然这是艺术探讨。我认为许多呈现充满了刻意,甚至是没有价值,甚至是画蛇添足,甚至是故弄玄虚。我甚至能够感觉,导演是在想到几个要重点表现的段落之后,再将其他部分进行拼凑与合体,诸如第二幕远不如第一幕与第三幕的呈现与表达。第一幕是导演对于传统表达的“破”,第三幕则是导演对于自我解读的“放”。而第二幕就像是个鸡肋一样的过度,排则无味,弃之不敢。而群众歌队的运用手法并不新鲜,且在该剧中的审视作用颇为生硬,将间离变成了“我这是在处理”的灌输提醒(我早已对戏不多做讨论导演处理,仅为举例)。
《茶馆》剧作本身的东西,该表达的,焦菊隐版本已经表达得很完整和透彻了,因此在再现方面,李六乙版本的确无法超越,甚至更加简约,甚至并不动人。但可贵的是他选取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并且勇于尝试,也没有改动剧本。我想,这并非是简单的“致敬”,而是有些地方没法动,有的地方不能动,无论是艺术水平还是其他,而导演也正要以此来表达即使戴着镣铐跳舞也能展示自己的艺术。
很抱歉,对于艺术,我的话说得很不客气,但这就是我作为观众在艺术角度上的真实感受,而非同行。正如前文所说,原因我表示理解,但呈现结果并不认同。
三
看了和听到许多人说,关于川语和北京城背景的“不和谐”问题。我认为这不是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因为优秀的剧本真不在于用何种语言来演绎。但问题还是存在着,那就是“水土不服”,无论是观众接受上还是剧作展现上。
我是一个可以不用看字幕也能听得懂这部戏的川语的观众,因此在语言接受上没有问题,更不会产生“北京城怎么会有许多四川人这样生活”的观念。但是川语的运用,虽然产生了新的尝试,但却失去了北京话中的韵味,同时失去了老北京人特有的“精、气、神”。这些是这部剧作专门为北京背景北京文化所设置的,被其他方言取代后,所损失的并非艺术和表演所能弥补。

川语版《茶馆》
但我想,这一问题并不在于导演特意选择了川语,而是在于这个剧本本身更适合用北京话背景环境来展现,而不是像莎剧一样可以用任何语言驾驭。如上文所探讨,优秀的剧本不受限制,也可以被各种演绎。但问题是,这个剧本是否扛得住各种“造”(折腾的意思,此处非贬义)?结果恐怕是否定的。川语尚且如此,我更难以想象用英语、法语、俄语来演绎时会是什么效果。我也确信,川语版《茶馆》在川语地区的接受度一定会比在北京高。正如很多地方方言在别处时会有意外的喜剧效果,但在当地则被认为非常正常。此为地域与语言差异,实为正常。
川语的选择,并非不对。从戏剧的可能性与普及性来看,发展地方语言的戏剧是可行的,但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和具体戏来分析。单以《茶馆》原作来说,北京无疑是最适合其生存的土壤。
也有许多人说,那干嘛不做一个四川的《茶馆》,为什么不写四川当地的事儿?我想,那恐怕就不是《茶馆》了,而是另外一部戏。是否有人能写出同等水平的剧本且不论,对于《茶馆》革新与戏剧发展的意义来说,那就小得许多许多了。
四
对于这部川语版《茶馆》,我说了无法简单用“好戏和烂戏”作为评价定语。我不认同其中的一些舞台表现与内涵表达,但却能深刻感受到创作者的深意与此部戏对于戏剧发展的价值。
近六年没有写过正式的评论,我也已经走过了“就戏论好坏”的过程。想的更多的是一部戏对于戏剧未来的作用。我记得我与莫斯科艺术剧院博物馆管理员交流过,关于究竟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海鸥》出色,还是现在新排的《海鸥》出色的问题。管理员对我说,她并不喜欢新版的《海鸥》,但也明白斯坦尼的《海鸥》已经无法再适应这个时代的需求。(否则一直演斯坦尼的原版就好了,何必更新?)
管理员当时和我谈到一句话:一个新的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可能。
我想,一部戏的革新,对于观众来说,哪怕是一个新的感悟,就有可能产生新的人生价值;对于看戏的其他创作者来说,哪怕一个处理和一个解读让他觉得有道理,也许就能激发他自己的更出色的创作。戏,都有自己的优点与缺点,而重要的不是这部戏给这部戏带来什么,而是这部戏给未来其他的戏带来什么,给观众带来什么。焦菊隐版本的《茶馆》并非无懈可击,只是因为我们的艺术能力和思维不足,才无法找到其中的问题,因此我们宁愿把它奉为神。这当然不是焦版《茶馆》的问题,而是我们暂时没有能力去超越,包括导演、表演、舞美等等。但我想,没有能力去超越是水平问题,没有勇气去变革是态度问题。为了戏剧未来的发展,我们需要跳出旧有的美好回忆,减少“今不如昔”的感慨,因为那些都已经过去了。正如契诃夫写《万尼亚舅舅》中表达的“人生重要的是在路上”的话题,写《樱桃园》中所描绘的“不管你是否留恋,一切都将成为历史”的话题。这些都是人类永远需要探索的,而中国戏剧的发展也是一样。评判一部新的《茶馆》的优劣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这是否能够影响到我们对于中国传统作品的态度,能否影响到创作者敢于“踩着前人的艺术骸骨前进”的问题。正如我曾写过的一篇文章,关于俄罗斯的历代大师都是在背叛老师的基础上走向大师之路。需要尊重前人的成就,但更要去质疑和打破前人的艺术。这其中一定会有各种阻力(有的可以控制,有的不可以控制),一定会容易被扣上“歪曲经典”之名,一定会产生许多艺术并不成功的作品,一定会让许多观众一时或者永远不接受。但是必须要走这条路,必须要去坚持。
大师不是自封的,不是炒作的,不是继承的,而是用千千万万个艺术工作者成功或失败的戏剧作品积累产生的土壤,用智慧与勇气超越而孕育而生的。
最后回到川语版《茶馆》。作为观众,任何表达都是合理的。但从艺术发展角度来讲,如果单纯靠好坏来评价川语版《茶馆》,那么并不算负责。
因为该剧如果一片好评,则必会引来各种效仿,无论呈现水平高低,都可能变成打着“革新”旗号、“为革新而革新”,甚至是私人炫技的秀场;但如果一片差评,必然给未来排演传统作品带来压力,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这也正是我在写这篇文字时的矛盾与顾虑所在,虽然这仅是一家之言,也难以起到什么实质作用,但我需要面对的是我关于艺术、关于中国戏剧发展的态度。我不会做标题党,也无意去说某剧院未来该怎么排,一切该怎样就怎样。正如戏的结尾并不在演出结束,而应该在观众内心完成一样,此篇文字,仅供参考。
樱桃园再美,也终将成为那逝去的、亲切的怀恋;在路上,创作者和观众都在路上。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心要向往着未来,即使现在常是忧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