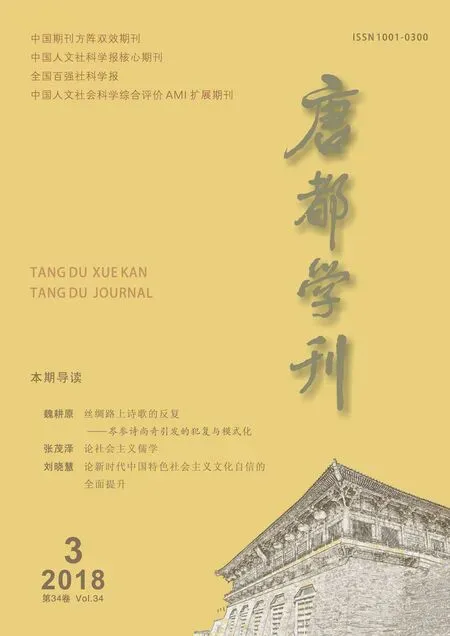论“孝”在二曲学中的逻辑线索
王文琦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20世纪初,当学者们把“启蒙、富强、民主、科学”的时代诉求投射到了明末清初的思想研究中时,李二曲的学术地位也就渐被新的“清初三大儒”所取代*“清初三大儒”原指李二曲、孙奇逢和黄宗羲,由全祖望提出(参见《二曲先生窆石文》,载于《李颙集》,李颙著,张波点校,西北大学出版社,第653页)。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三大儒”的新说法出现于20世纪初。。当代的二曲研究依然呈现为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倾向于“思想史”方面,从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到陈祖武的《清代学术源流》,代表着二曲思想研究在当代的奠基,过往取得的学术成果也主要集中于此。第二条线索则是在吸收前者成果的基础上,更偏向于“哲学”的诠释。近十余年来,林乐昌、孙萌、房秀丽等学者不约而同地把研究目光集中在二曲学核心概念“明体适用”的诠释上,即是明证。
二曲学崛起于理学“终结”、明清易代和西学传入的三叉之地,在过去很长时间内的传播与评价主要都是依靠“思想史”来完成的,二曲学“康济时艰”的独特价值,似乎也很适合在“思想史”中加以呈现和把握。然而,与其成绩并存之问题在于对二曲的研究往往也会因缺乏哲学的深度诠释而限于简单的传述。陈祖武就发现在《清史稿·李颙传》中,不仅漏记了二曲的学术宗旨,而且出现四个关于二曲学行记述的“重要疏漏”[1]116-120。笔者则认为,虽然在二曲晚年及其去世后,传誉其学的学者还是相当多的*例如现存《李颙集》中的二十三至二十六共4卷,皆为门人汇辑的李颙家史,篇幅不可谓不重。,二曲门弟子遍及大半个中国,他们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对二曲学的研究多有裨益。然而,《清史稿》的问题却非独存,追述到弟子、后学等所作的纪颂文章,一个明显的趋势反而应值得警惕:为了宣扬二曲学,学者们除了申述其“学术宗旨”外,对二曲的某些学行往往有意加以表彰,如:“孝”“拒应清廷之诏”和中晚年“闭门深居”等。毋庸讳言,如若对“孝”的诠释无法提升到本体论高度;若“拒应清廷之诏”仅变成一种名节之行;若“闭门深居”是一种无奈的避世选择,虽保全了二曲的气节,又有何益?为何对二曲的表彰还可能成为反向伤害,不得不引起后世研究者的重视。这也是现今二曲研究亟待提升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曲学始终具有“由本及末”的明显特点,其学展开有清晰的逻辑线索。能否准确揭示二曲之“用”背后的“体”、其“行为”背后的“实际”就成为能否准确诠释二曲学的关键所在。二曲对“孝”的讨论是上述问题中最有代表性的例证之一。正如他在三十余岁再提“经世致用”时,决然不同于弱冠之年所焚毁的“经世”之作,——虽同为“经世”,前后却有着天壤之别。二曲一生不仅以“孝”显名、闻人孝行即行表彰,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孝”发展出了一整套修身、治理的理论。本文拟以“孝”在二曲文集中所展现的深刻内涵为考察对象,梳理其在二曲学中的逻辑线索,并借此探索二曲研究进一步推进的可能方向。
一、“仁之本”与“行仁之本”——“孝”的本体论提升
李二曲早有孝名,母逝后又因襄城访父遗骸之举,大有以孝而名显天下之势,学者广为传赞。高攀龙的侄子高世泰就曾直言:“余闻二曲先生之孝也,关中人人颂之。”[1]277二曲本人则因不得尽孝于父母而终身抱憾,他常言:“李颙生为抱憾之人,死为抱憾之鬼”[1]158。论及其抱憾者何?则与其父为明王事而死和直接导致的母子困苦生活密切相关。二曲在《跋父手泽》中说:“痛子者父,痛父者谁耶?父仇不能报,父骨不能觅,有子如无,抱憾终天,死有余恸矣!”[1]220父逝后,其母彭氏于贫寒中守志,坚持督促二曲读书从学,后死于脾胃之病。故二曲有言:“服劳奉养,古人尚不以为孝,若并服老奉养而有遗憾,罪通于天矣!”[1]417。因而后来二曲将所闻孝行编著为《恶室录感》,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敬录所感,聊寄蓼莪之痛”[1]333。严酷的生活条件使二曲的成学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先严早岁没于王事,遗颙只身,别无次丁。先慈守寡鞠颙。是时,无一椽寸土之产,朝不谋夕,度日如年,饥寒坎,盖不啻出百死而得一生。迨颙成童,乡人悯其窭,甚或劝之给事县庭,或导之佣力于人,谓可以活母命,免沟壑。先慈咸拒谢弗从,朝夕惟督以认字诵书、修己砺行为务。颙所以不至失身他涂,堕落于小人禽兽之归,皆颙母之贤,有以成之也。孀居三十年,未尝一日温饱,坚忍不渝之操,闻者莫不叹异。生前,当道以“芳追孟母”表闾;没后,竖碑大书“贤母彭氏”表墓。[1]183
彭氏被评价“芳追孟母”并非揄扬之词,在母子最困苦的日子里,面对“乡人悯其窭,甚或劝之给事县庭,或导之佣力于人,谓可以活母命,免沟壑”,于情于理,这样的选择并不难理解,但是二曲母显然有更加深远的考虑,故“先慈咸拒谢弗从”,二曲则把上述选择定义为“失身”。
二曲的这段经历十分相似于《史记·淮阴侯列传》中韩信的年少经历:“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常从人寄食饮……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乃至受胯下之辱[2]1991-2007。显然,二曲母子的选择比起韩信之志,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因为在二曲行为背后是为了追求圣人之道,固有君子之行;而韩信的忍辱负重、发迹后的报恩则是出于一种利益的掂量:从“贫无以葬母”到为母修“万家之冢”,从一饭之恩到“赐千金”,从胯下之辱到“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比起韩信在在念念的名利之“量”,二曲母子的选择显然更关注于“质”。这也正是二曲母子在“慈”与“孝”上超出一般人的地方。
其实,从孔、曾、孟始而论“孝”起,“孝”就显然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礼”,而是与内在之“仁”有着密切联系,从“孝”到“仁”之间有一条清晰的逻辑线索。直到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二程兄弟那里,由“孝”而“仁”的这层本体论提升意义才被明确地揭示出来。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问:“‘孝悌为仁之本’,此是由孝悌可以至仁否?”
曰:“非也。谓行仁自孝悌始。盖孝悌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之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仁义礼智四者,几曾有孝悌来?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3]183
有子所言代表了孔、曾、孟的一致看法。在对比中,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的一脉相承和各有侧重清晰显现:孔子和有子把孝悌当“本”,把“不犯上作乱”当“末”,由“孝悌”入手来安顿政治生活的和平稳定;而二程兄弟的解释虽为创发,却无违于《论语》论“孝”的精神,主张不可止于“孝”之行,而需由“孝”上升到“性”、本体论的高度,“孝”的意义才会完整彰显。这两种思路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如果“孝”只流于外在的规范和形式,那么它显然无法与修身和社会治理建立必然的联系;只有把“孝”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它才可能直接与本体论的“仁”建立联系,此时的“孝”才会成为“仁”的具体表现,即工夫即本体。
返观二曲,李二曲之孝名孝行虽来自于真实的生活遭遇,为人赞赏,但是他能否超脱出“行孝”本身,把“孝”推至开来,提升至本体论的高度,使其从个人之行开发出普遍意义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或又言:“圣贤之道,不外孝悌。事亲从兄,莫非实学,舍此无学可言。”
曰:“能孝能悌,固是实学;然此能孝能悌之端,从何而发?满孝满悌之量,赖何而充?待父兄而可以言事言从,有时离父兄之侧,则将何若?有父兄而善从是学,无父无兄又将何若?”或无以对。先生曰:“圣贤之道,虽不外于孝悌,则知孝知悌,则必有其源。源濬则千流万派,时出无穷,万善犹裕,矧孝悌乎!故不待勉于孝,遇父自能孝;不待勉于弟,遇兄自能弟。存则或事或从,自然尽道;亡则立身行道,大孝显亲。随在是心,随在是学。‘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非‘春’,则安得‘万紫千红’;非‘识东风面’,又安知‘万紫千红’之‘总是春’也。”[1]75
二曲双亲早亡,只有在对“离父兄之侧,则将何若?”的追问中,才能把对孝悌的理解从“事亲从兄”的外在表现中超脱出来,才能循孝悌之“源流”,找到超乎“存”“亡”而“时出无穷”的“万善之源”。二曲借用诗句道明了“孝”与“万善之源”(仁)的关系:非“孝”,则安得“万物一体之仁”;非“识仁”,又安知“万物一体的境界”亦无非是“孝”的展开。
如果说“行仁之本”是二程兄弟所强调的:“用”必须要上升到“体”的高度,“用”乃为“真用”,为二曲所接受;那么“仁之本”的说法显然与先秦孔孟“由本及末”的“孝”的推致密切相关,亦为二曲所继承。无论是“仁之本”还是“行仁之本”的说法,无疑都是可以成立的,二曲并没有限于二程兄弟的理学解释,他确实有向先秦儒学复归的为学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二曲的确对先秦、宋明儒关于“孝”的理解有所总结与发展。
二、“孝以显亲为大”——从小孝到大孝的提升
李二曲对“孝”的理解往往能超出理学的诠释而直探本源,孝的根底确实来自对父母的爱敬之情。他说:“不思父母生我育我,顾我复我,昼夜劬劳,万苦千辛,未寒而思为制衣,未饥而思为储食,长成而为之授室,竭尽心力,恩同昊天!此亦父母务理学而然耶!”[1]158既然“孝”在最基础的层面是与父母的爱敬之情直接挂钩,那么“孝”的展开,亦首先应自“事亲”而始。
先生曰:“孝悌而不能为仁,只恐这个‘孝悌’还从名色上打点,未必是真孝真悌。若是真孝真悌的人,爱敬根于中,和顺达于外,一举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推之待人接物、居官莅事,不敢刻薄一人,不敢傲慢一事,岂不是为仁之本!故学者之患,只患孝悌不真。若孝悌既真,正不必患为仁之沮塞也。”[1]102
“爱敬”“和顺”、举手投足之间“不敢忘父母”,这些都是具体的“孝之行”。虽为“孝之行”,然二曲有意加上一层对“是否真孝真悌”的讨论,“孝之行”也就具有了更为深刻的意义。但说到底,这些毕竟属于“事亲”的范围,还不具有“为己之学”的自我意义,是养父母之“口体”,还不是养父母之“志”。于是,二曲进一步对孝展开讨论:
“事亲”不及曾子,是不孝其亲。“守身”不若曾子,亦非所以孝其亲。“养志”“养口体”,缺一非孝。若余则生而单寒,不惟缺于“养志”,并“口体”亦缺焉!无以为养,无论酒肉非所敢望;即谷食亦不能常得,致吾亲备极人世之艰危,未尝一日温饱。不孝之罪,上通于天矣![1]494-495
从“事亲”到“守身”,从“养口体”到“养志”,二曲对“孝”的讨论逐渐展现为由“小孝”至“大孝”的逻辑线索。
子有身而父母惟其疾之忧,子心已不堪自问,若不能自谨而或有以致疾,则不孝之罪,愈无以自解矣。故居恒须体父母之心,节饮食,寡嗜欲,慎起居,凡百自爱,必不使不谨不调,上贻亲忧。
父母所忧,不仅在饥寒劳役之失调,凡德不加进、业不加修、远正狎邪、交非其人、疏于检身、言行有疵,莫非是疾。知得是疾,谨得此身,始慰得父母,始不愧孝子。否则,纵身不夭札,而辱身失行,播恶遗臭,不几贻父母之大忧哉?”[1]416
孝以保身为本。身体发肤受于父母,不敢毁伤,故曾子“启手足”以免于毁伤为幸。然修身乃所以保身,手不举非义,足不蹈非礼,循礼尽道,方是不毁伤之实。平日战兢恪守,固是不毁伤,即不幸而遇大难、临大节,如伯奇孝己,伯邑考、申生死于孝,关龙逢、文天祥之身首异处……寸寸磔裂死于忠,亦是保身不毁伤。若舍修身而言不毁伤,则孔光、胡广、苏味道之模棱取容,禇渊、冯道及明末诸臣之临难苟免,亦可谓保身矣?亏体辱亲,其为毁伤,孰大于是!
保身全在修身,而修身须是存心。终日凛凛,战兢自持,察之念虑之微,验之事为之著,慎之又慎,无所容乎人欲之私,而务全其天理之正,如是则俯仰无怍,生顺而死安矣。[1]442
上述两段材料,前者主要是从“事亲”的外向视角转而为自我的“保身与修身”,后者则进一步强调了从“保身”到“修身”“存心”提升的必要性。能从“忧父母之疾”转而“体父母之心”,替父母照顾“己身”,固然已经比最基本的“行孝”于父母更为深刻,但“保身”毕竟保的只是实体之身,属于“气命”,有时甚至非人力所可必为。人生中有比“保身”更重要的“舍生取义”的情况存在,故而,人能做的乃在于“修身”以护“理命”,而不只是“苟且于保身”。“修身”的进一步要求则在于“存心”,通过“存心以修身”的不断努力,所能达到的境界则是“俯仰无怍,生顺而死安”。
李二曲论“孝”,显然不局限于“父慈子孝”的一般要求。如果相比起“修身与存心”的更高追求,那么“父慈子孝”的一般要求就只能勉强称为“小孝”了,后者才是“大孝”。但是李二曲对“大孝”所能达致的境界描述还远没有完全展示。这里我们先来看二曲论“孝”在“亲”与“己”之间的相互关系:
孝为百行之首,修身立德为尽孝之首。舜之大孝在“德为圣人”,故人子思孝其亲,不可不砥砺其德。“德为圣人”,则亲为圣人之亲;“德为贤人”,则亲为贤人之亲。若碌碌虚度,德业无闻,身为庸人,则亲为庸人之亲;甚至寡廉鲜耻,为小人匹夫之身,则亲为小人匹夫之亲。亏体辱亲,莫大乎是,纵日奉五鼎之养,亦总是大不孝。[1]405-406
他日道德如周、程、张、朱,事功如韩、范、富、欧,天德王道,一以贯之,为天地间第一流人物,庶几其尊甫大人望子之盛心,亦庶几声百立身行道、显亲扬名之大孝!岂非千古盛事?[1]187
“孝以显亲为大”常被二曲拿来作劝诫之辞、启发之机,以导人向善。诚然,对父母最大的“孝”乃在于自己“德为圣人”,显亲扬名。至此,原本是作为道德行为的“孝”,就被二曲完全转化成一套内在的修身理论。值得注意的是,“显亲”乃是一种名利之行,二曲以“显亲为大”来启人向善,本身就有着很强的现实引导性,此绝非二曲“好名”的证据。例如二曲曾说:“祖父之恶,非子孙之孝慈所能改,则知子孙之善,亦非祖父之不善所能掩。”[1]517显然,二曲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所谓的“显亲”亦只是一种带有理想性的人道追求,其实际效用却可以得到正面、积极的开发。
三、“孝”的推致——关于孝的“本体修养论”
“修身立德为尽孝之首”是孝与修身的关系,而“修身”在《大学》的“三纲八目”中,在孔孟之学的理论体系中,还远没有充分展开。“孝”的充分展开与最终落实乃在于它关乎“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治理大业。我们首先来沿着《大学》的纲领对二曲论“孝”进行考察:
治国平天下,必须纯一无伪、赤心未失之大人,率其固有之良,躬行孝悌仁慈,端治本于上,民孰无良,自感格蒸蒸,兴孝兴悌,不倍风动于下,上下协和,俗用丕变,孟子所谓“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者此也。此至德要道,于治国乎何有?
问:后世在上者,亦有孝悌仁慈之人,而俗不丕变,国不大治者,何也?曰:后世在上者,虽间有孝悌慈之人,未免从名色上打点。若果天性真孝、真悌、真慈,则爱敬根于中,和顺达于外,一举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推之待人接物,莅事临民,不敢刻薄一人,不敢傲慢一事,而国有不治者乎?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1]396-397
这段材料的重要性不止于关乎“孝”,它也是回答因何二曲一生严苛以律己,绝不轻受他人帮助,誓死不应清廷之召等行为背后的真实动因。传统“政治”的理论之基乃在于“先正己后正人”,己身不正则已然失去正人和从政的资本了。这也正是孟子所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的真实意涵。二曲的“爱惜名节”之行其实是出于对儒家政治观的准确践行。
弟子王心敬向二曲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后世不乏孝悌之人,因何不治?二曲的回答则十分深刻。他认为“虽间有孝悌慈之人,未免从名色上打点”,进而提出了“真孝、真悌、真慈”的拷问。这符合二曲一贯追求“体为真体,用为真用”的思路。笔者在另一习作《李二曲体用思想的反思与厘定》曾言:“不同于大多数学者对宋明理学体用思想的批叛态度,李二曲意识到,与其说宋明理学的体用架构是阻碍经世致用之学发展的绊脚石,毋宁说正是因为没有做到宋明儒所揭示的‘真体真用’才出现了‘体’的偏于理论思辨、‘做一场话说’和‘用’的无力、无为或肆意妄为。”二曲不同于同时代许多学者选择通过对传统“孝悌”观的质疑来寻找新的富有实效性的政治振兴之路,而是深刻挖掘“真孝真悌”的具体落实,肯定传统政治观的本末推致理论,在儒者的安身立命和康济时艰中找到平衡,返本以开新。而这一点,又恰恰是关学八百余年的传承中不断坚守的儒学正脉:
梁王以“制胜雪耻”为问,孟子答以“修其孝悌忠信”,“可使执挺以挞秦楚坚甲利兵”,不惟当时乍聆之以为迂,在后世骤读之,亦未有不以为迂者,然而非迂也。人心为制胜之本,人伦修明,忠义自奋,情所必然,无足疑者。天启初,边事告急,远迩震恐,冯少墟先生时为副院,慨然曰:“此学术不明之祸也!”于是限日率同志、士绅立会讲学,千言万语,总之不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及圣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六言”,当人心崩溃之余,赖此提撕,激发天下,当十万师。使天下晓然知有君臣父子之伦。三纲之道明,而樽俎之容,威于折冲,亦孟子“修孝悌忠信”,“以挞秦楚坚甲利兵”之意也。或曰:“此何时也,而犹讲学?”先生曰:“此何时也,而不可讲学?讲学者,正讲明其父子君臣之义,提醒其忠君爱国之心,正今日要紧第一着也。”或又谓:“方今兵饷不足,不讲兵饷而讲学,何也?”先生笑曰:“试看今日疆土之亡,果兵饷不足乎?抑人心不固乎?大家争先逃走,以百万兵饷,徒藉寇兵、赍盗粮,只是少此一点忠义之心耳!欲要提省此忠义之心,不知当操何术?可见,讲学诚今日御敌要着。”由先生斯说观之,益知孟子之言非迂,而人伦之修,在所不容缓矣![1]487
关学的长振不衰和重振宗风,都首先不能离开其对孔孟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无论是冯从吾还是李二曲,他们在这一点上都做得十分出色。面对理学“终结”、明清易代和西学传入的社会巨变,冯、李等关中大儒以“醇”儒之学,不仅能坚守两千年来的儒家真精神,又能应势而变、不闭目塞听,尝试构建“体用全学”等新的儒学形态以康济时艰,二曲学的独特价值亦由此而体现。
无论是“孝”的推致还是对“孝”进行“体与用”的诠释,“孝”几乎成为贯穿二曲一生之学的一条主线,由小孝到大孝的不断提升几乎包容了二曲之学的大部分内容。“孝”在二曲这里不仅仅是一种“修养”理论,更是关联着本体之仁、关联着“治国平天下”的完整政治理论。在一定意义上说,二曲的学术宗旨很难定位,与二曲学“由本及末”的显著特征有很大关系。二曲总能把所谓的各种“学术宗旨”落实在由道德修养进而获得实存体证的实践行为之中,这也正是“实修实证”之学的典型特点,“孝”“悔过自新”“明明德”“致良知”无一不可称为二曲从学的“下手宗旨”。“孝”显然已经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绝非普通的“孝言孝行”可以概括。
四、二曲诠释的新思路展望
“孝”本源于对父母的爱敬之情,二曲由感念父母对自己的“唯疾是忧”到主动地“事亲”“保身”以免除父母之忧。然“身之保”乃在于“气命”,不若以“修身”和“存心”护守己之“理命”,以“养志”超越对父母的“口体之养”,以道德修养进步上的“显亲扬名”鼓励行孝修身,进而通过“修身”将“孝”提升到“齐、治、平”更为广大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立本以达用。这构成了“孝”在二曲学中的逻辑线索。
如果说“孝”在二曲学的诠释中绝不可理解为一种简单的个人品格之行,那么同样的道理:二曲“拒应清廷之召”亦非一种简单的名节之行,它背后不仅有其父为明王事而死的刻意坚守之“孝”,更是二曲做人立世、誓不“失身”的“政治”(正己)之本。同理,二曲中晚年的“闭门深居”之行亦不当过度诠释,“闭门深居”的直接原因是二曲不想因名噪当世而陷于大量的应酬之中,更不想因名而“招祸”。深层的原因则与拒召一样,还需从其人、其学的独特坚守来加以正面解释。《纪略》和《年谱》等资料告诉我们,不仅顾炎武、杨愧庵等学者的到访获得二曲热烈欢迎,而且王心敬、惠灵嗣等弟子与之朝夕求学亦是常态,我们显然不能把“闭门深居”理解成二曲的一种避世隐逸之行。
二曲的孝行、孝名为学者所传颂显然是在情理之中,然而一方面若刻意显名扬高,往往无益于客观的研究。例如陈玉璂的《李母彭氏传》在“抉齿说”“尝粪说”[1]313-314等刻意描画上都帮了倒忙。另一方面,如果后世学者的诠释始终落在“思想史”的记述中,而不能对之加以哲学意义的说明,那么对二曲“孝”的表彰可能会流于人云亦云,反而无益于揭示二曲学的真实价值了。
哲学家和哲学思想的学术评价,根本上还取决于其本身的学说价值与后世研究者的准确诠释。过往研究已在“思想史”层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今的二曲研究呼吁一种“哲学定性研究”。作为明清之际的“三大儒”之一,李二曲的哲学思想还有很多深刻内涵尚待发掘。
参考文献:
[1] 陈祖武.清代学术源流[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 司马迁.史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 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