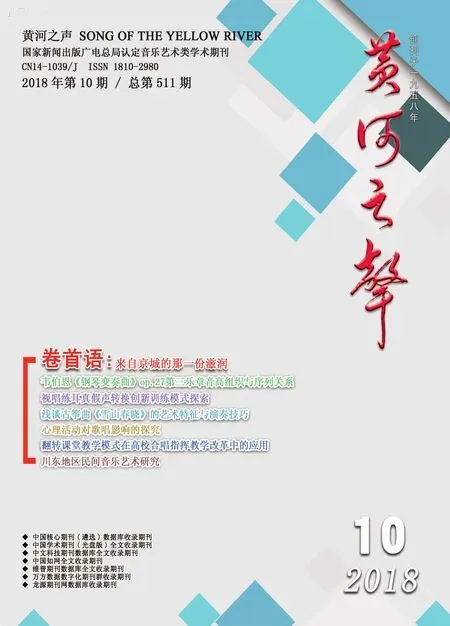“红”与“蓝”的交响
——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色彩”意象解读
何昱璋
(沈阳音乐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8)
一、序幕——点亮那吟诵着悲鸣的“红”
《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作品对于色彩的运用是十分考究也颇具写意的味道,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深蓝色和大红色两种色调。序幕起始,便用沉闷阴冷的灯光和音乐色彩写意的定下了整部作品贯穿始终的基调和格局。紧接着身着蓝色旗袍手拎大红灯笼的丫鬟们和着哀婉且凄美的京剧女声缓缓走上台来,深蓝色的旗袍裹挟着她们的身躯和深蓝色的夜幕浑为一体,整个气氛像被阴云笼罩,深宅大院禁锢和束缚着人性,给人深切的压迫感,鲜红的灯笼发出影影绰绰的红光并没有带给人一丝的温暖和明亮,反而好似魔鬼眼中夹带的血丝,令人瑟瑟发憷,在暗蓝色的夜幕下,这点点星火的反抗实在显得太过渺小微不足道,同时导演对于那个时代下女性命运的悲悯、同情和无奈通过这强烈的色彩压迫感和哀婉凄美的音乐色彩写意的勾勒出来,悲情的灯光色彩,悲情的音乐色彩,悲情的服装道具色彩,悲情的人物内心情感色彩结合的并不突兀恰到好处,共同营造出一种凄惨悲凉的气氛,无疑,一场悲剧即将在这深宅大院内上演,在这样的氛围中人物的色彩和命运也注定是凄惨悲凉的。
二、洞房花烛——遭受苦难的闺中之“红”
三太太身着暗红色的婚服缓缓地迈出轿门,满心忐忑的向四周张望,内心深处仍就无法接受自己要嫁入深宅大院的现实,看着穿在自己身上的婚服和如坟墓一般的婚轿,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怨怼上苍为何要这般折磨于她,这时凄美的主题音乐再次响起,此时此刻她内心的孤独、无助更与何人说。暗红而并非艳红的婚服色彩和胸口大大的喜字告诉观众喜事并不喜,这场婚礼对于她来说是如此的折磨煎熬,对于这样被捆绑的爱情她没有一丝向往,心中对真爱渴望的那份炙热早已黯淡无光,这样的红色禁裹着她让她喘不过气来。红与蓝的感官色彩,凄美的音乐色彩,无助无奈的内心情感色彩,共同将喜庆的气氛又一次拉到悲剧的基调上来。正当她苦求无门时,老爷身着黑色婚服斜挎着红绸绣球步入了婚房,这时锣鼓经响起伴着刺耳的二胡声提琴声,威胁感正慢慢地向她袭来,老爷每碰自己一下都觉得像万虫侵噬般浑身不自在,正要挣脱却又被老爷的红绸缠拌着一把搂在怀里,无论怎样反抗都逃不出老爷的手心,红绸本也是喜庆祥和之物,这里的运用却像皮鞭一般残酷,威吓着三太太,让这一抹红显得如此冰冷无情。紧接着导演运用皮影戏的光影表现手段,巧妙的将三太太惨遭蹂躏以及内心和身体上的挣扎反抗的激烈场面通过剪影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表现方式既委婉含蓄又能让观众仿佛置身其中,感觉自己就是这大院中的一个丫鬟一个下人在窗外偷觑,通过光影大小的对比变化塑造了老爷强悍而充满威势的人物性格,另一方面也放大了两人之间的对抗关系,让人对纤小柔弱的三太太遭受的束缚和苦难更加悲悯和同情,对老爷所代表的“深蓝色”般黑暗的封建礼教更加憎恶,同时音乐也随着反抗的逐渐激烈从低沉到紧张,老爷一边追赶,三太太一边躲逃,最后从光影追赶至到现实,在惊恐中一次次的冲破窗户纸,象征着其奋力想要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和枷锁,但最终仍就无法逃脱命运的手掌,紧接着大红色的红绸铺满整个舞台如泰山压顶般将她瘦弱的身躯淹没、遮盖,这时凄美的主题音乐再次响起,她缓缓地从冰冷的红色中爬出,探出头来,将红绸紧紧裹在身上,经历了身体上的蹂躏,她的内心已是一片死寂,没有了无助和恐惧,有那么一刻她会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恶心肮脏,但身在这个黑暗的深蓝的时代中,这是她这一抹红所无法选择的命运。
三、狱中受刑——叩问时代和人性的抗争之“红”
惨白的幕布下,三个定点光瞬间形成带着围栏的牢狱状,投影在暗黑色的地面给人以压迫感。三太太、武生、二太太在冰冷的狱室中分别起舞,表达了他们三人各自对命运和现实的抗争,对冲破牢笼和枷锁强烈的渴望,对自由和美好爱情的向往,但在这黑暗的封建礼教的社会现实中,在这重男轻女的时代枷锁里任何的反抗都是徒劳,同时也将三人内心对现实的无奈和无助借助这写意的光影色彩变化表现的更为真切。三太太和武生在感受到二太太对两人的告发行为虔诚的悔过后,经过内心情感的矛盾和激烈的挣扎,最后选择了原谅二太太给两人带来的命运的转折和不幸,当然他二人深切的懂得这种不幸也并非是由她而起,活在这个时代本身就是不幸的,同时他二人也知道二太太和自己本就是同一类人,都对爱情充满着渴望,对自由充满着无限的向往。最后,三人手拉着手并肩而行,欣然接受这命运的不公,共同面对这即将到来的死亡,他们从没有一刻像现在这般勇敢坚定。象征着封建礼教的黑衣武士手执刺眼而血腥的红色棍杖重重的击打着惨白色的幕布,第一杖下去打在武生身上,一道鲜红的伤口显现在观众的视野中,第二杖下去打在三太太身上,第三杖下去打在二太太身上,一次次的杖打,一道道在深蓝色笼罩下红的发黑的血印伴着凄美的主题音乐令观众感同身受,沉浸在残酷冰冷的气氛中,导演运用这样的表现形式,一方面放大了观众对于人物的真实感受,一道道惨红的血痕,一声声无情的击打声,打在三个人的身上也打在观众的心里,让观众更直观的从视觉和听觉上真听、真看、真感受,体会到三人被鞭杖时所遭受的磨难、煎熬和痛苦。另一方面,最后这段三人舞的编排也恰到好处令人印象深刻。虽然每次的杖打都万般痛苦,但三人始终手拉手互相扶持,谁也不抛弃谁,一次次的杖笞将三人无情的击垮分开,但她们却又忍受着疼痛艰难的爬起,紧紧地依傍在一起,无论怎样的杖打怎样的磨难,此时此刻都无法囚禁她们心中那一抹红,更无法束缚她们内心对自由爱情的向往和渴望,这是那个“深蓝色”封建礼教的旧社会下以三太太、二太太为代表的广大女性无声的抗争,每一声棍棒的“砰砰”击打也起到了一棍双冠的效果,不仅是对三人的杖打,同时更是对黑暗的旧社会对封建礼教的杖挞,每一杖都带着角色带着观众一起叩问着那个“深蓝色”的时代下对女性的不公和对人性的蔑视。
四、尾声——红海沁心,人生如戏
三人终于再也无法忍受杖刑之痛和这早已令人窒息的“深蓝色”,陆续的倒在了一起,倒在了血泊中,鲜血慢慢浸染了原本惨白的幕布,同时也浸润着一道道血痕,舞台被染成了一片血海,但深蓝色并未就此褪去,仍就笼罩着他们冰冷的尸身,这时开篇那哀婉凄美的京剧女声再次响起,首尾呼应直扣主题,这样的音乐色彩仿佛在以第三人称或是观众的口吻叹息着这悲惨的结局和命运。惨白的雪花在鲜红的背景中飘飘然落下,落在了她们早已僵硬的身上,给原本凄惨的气氛更增添了一丝寒意,让观众产生一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既视感,对那个时代下女性命运的扼腕、同情、悲悯一下涌上心头。然而沉重的大鼓和明快的锣鼓经再次敲响,身着蓝色旗袍手拎大红灯笼的丫鬟们缓慢冷漠的在舞台后区从台口经过三人的尸身又走下台去,她们又要匆忙的为新嫁入深宅的姨太太去掌灯了。这种表现手法的运用不仅直奔主题大红灯笼高高挂,同时进一步阐释了这一主题背后所隐含的寓意,当大红灯笼高高挂起之时,预示着在这“深蓝色”男尊女卑的深宅大院内,在这“深蓝色”封建礼教充斥下的旧时代旧社会又一个悲惨的故事悲惨的命运将再次上演,导演运用赋予京剧色彩的音乐、合幕方式及呈现方式颇具讽刺意味,当我们回过神来会发现,这何尝不就是我们在梨园舞台上看了千百遍演了千百遍的一出悲情大戏—“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