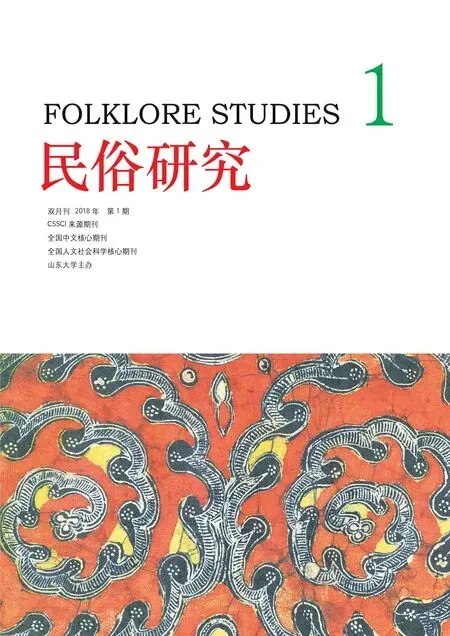谁是正统:中国古代耕织图政治象征意义探析
王加华
“正统观”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史学编纂的重要观念之一,正如朱维铮先生所说的那样:“(正统观)是困扰中国历代王朝的政府及其学者达两千年的一个核心观念。”*朱维铮:《研究历史概念史的一部力作》(代序),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中华书局,2015年,第1页。在中国古代社会,不论是偏安一隅的创业霸主,还是一统天下的开国皇帝,在开基立业的过程中,都会竭力构建其政权的正统性,以巩固与强化统治基础。作为一种政治观念,正统观在我国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先是或明或暗地存在于上古历史中,后经过《春秋》的借鉴与整理,成为正统理论,再经北宋欧阳修等史学家的发展和完善,而成为有体系的政治历史观念和史学理论。*谢贵安:《饶宗颐对史学正统论研究的学术贡献——〈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发微》,《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中国传统正统观,其理论依据主要有二,一为邹衍之五德运转说,计其年次,以定正、闰;一为依据《公羊传》加以推衍,强调“居正”“一统”之二义。其中五德运转说,主要流行于唐之前,而宋之后,则“居正”“一统”居主导地位。*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中华书局,2015年,第81页。而判断正统之标准,按梁启超(号任公)的总结,可分为六个方面,即得地之多寡、据位之久暂、是否为前代之血胤、是否为前代旧都之所在、后代之所承与所自出、是否为中国种族。*梁任公:《饮冰室文集全编》卷十一《〈历史〉(一)·论正统》,上海新民书局,1933年,第16-17页。
作为一个传统以农立国的国度,在所有那些何谓正统的标准之背后,其实都有一个隐性的基本前提,那就是必须要有发达的农业生产作为立国之基、以“重农”“劝农”为基本的治国理念。*白馥兰认为,“劝农”是中国古代“政府的哲学理念和治理技巧的核心所在”,“一直是‘经世济民’当中需要从政者主动去虑及的问题,同时关涉到仪式因素与实用因素”。[英]白馥兰:《技术、性别、历史:重新审视帝制中国的大转型》,吴秀杰、白岚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7、216页。而这一点,在以是否为“中国种族”为判断标准时体现得最为明显。是否为“中国种族”,本质上又是我国传统夷夏观的具体体现。作为一重要的政治与民族观念,夷夏观萌芽于西周时期,定型于春秋战国时期,此后一直或隐或显的代有传承。通常,民族关系紧张之时,也即是夷夏观被加以强调之时,虽然在不同的时代其说法可能有所不同。*张鸿雁、傅兆君:《论传统夷夏观的演变及其对近代社会民族观的影响》,《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夷夏观的核心思想是内华夏而外夷狄,其中华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而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华夏与夷狄的划分,表面来看是基于文化的,如服饰、饮食、居住方式等,本质上却是以“农”与“非农”为核心标准的,是“农耕为本”的话语体系所派生出的一种表述方式,代表的是农耕文明的自我天下观及与之相应的区域性政治与社会体系。因此,不论是《礼记·王制》还是《史记·匈奴列传》等,都会特别强调“农耕”这一前提。*徐新建:《牧耕交映:从文明的视野看夷夏》,《思想战线》2010第2期。所以,从更本质的角度来说,所谓“华夏”与“夷狄”的分野,也即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分野。因为“农”如此重要,故历代统治者在构建自己的正统性时(如立国号、制礼作乐、颁历等),对“农”的强调都是一个重要方面,比如行藉田礼、颁劝农文等。这其中,绘制并推广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图像——耕织图,亦是一个重要体现。
耕织图,就是以农事耕作与丝棉纺织等为题材的绘画图像。具体来说,其又有广义与侠义之分。广义的耕织图,是指所有与“耕”“织”相关的图像资料;侠义的耕织图,则仅指南宋以来呈系统化的耕织图,即通过成系列的绘画形式将耕与织的具体环节完整呈现出来。现今有确切证据并有摹本留存下来的第一部体系化耕织图,为南宋楼璹《耕织图》。楼璹之后,南宋、元、明、清时期,又先后创作绘制了至少几十套不同版本与内容的体系化耕织图。这些耕织图创作与绘制的背景、原因与目的意义,各有不同,但其最主要的目的在于教化劝农,并具有深远的象征与社会治理意义。*参阅王加华:《教化与象征:中国古代〈耕织图〉意义探释》,《文史哲》待刊稿。这其中,对“正统性”的象征性体现,就是一个重要方面。而这一点,在南宋、元与清三个朝代中又体现得最为明显:不仅创作绘制并刊刻了大量耕织图,还将其上升到皇帝与中央政府的高度加以重视。下面,本文即主要针对这一问题展开分析。
作为一个广受历代政府、学人关注的热门话题,历来关于“正统观”问题的讨论是代不乏人。而从现代学术角度展开讨论的,首推饶宗颐先生之大作《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观》,不仅对历代以来中国史学编年中的“正统观”问题做了相关梳理与论述,还对历代学者、官员等有关正统观问题的讨论文献做了搜集与整理。*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中华书局,2015年,第81页。相比于饶先生从“史学编年史”角度展开的讨论*从这一角度展开讨论的,还有很多学者,比如王晓清:《宋元史学的正统之辨》,《中州学刊》1994年第6期;张伟:《两宋正统史观的历史考察》,《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2期;魏崇武:《论蒙元初期的正统论》,《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3期,等等。,还有一些学者从“王朝政治”的角度做了相关探讨。*具体如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三联书店,2010年;刘浦江:《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7年;谢贵安:《从朱元璋的正统观看他对元蒙的政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杜洪涛:《明代的国号出典与正统意涵》,《史林》2014年第2期,等等。具体到中国古代耕织图,虽然从20世纪初期起就开始受到中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并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代表性成果,如[日]渡部武:《〈耕织图〉流传考》,曹幸穗译,《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日]中村久四郎:《耕织图所见的宋代风俗和西洋画的影响》,(日)《史学杂志》第23卷第11号,1912年;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Roslyn Lee Hammers, Pictures of Tilling and Weaving: Art, Labor, and Technology in Song and Yuan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黄瑾:《康熙年间〈御制耕织图〉研究》,浙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等等。,但综而观之,从“正统观”角度展开分析的研究却并不多,据笔者管漏所见,只著名中国艺术史大家高居翰先生有所论及。*[美]高居翰:《中国绘画中的政治主题——“中国绘画中的三种选择历史”之一》,杨振国译,《广西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不过,高先生的研究,只是对这一问题做了简单涉及,并未结合不同的时代背景展开详细讨论,因此仍有进行细致讨论的必要。有鉴于此,本文将在结合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南宋、元、清不同的朝代与时代背景,对耕织图的绘制及其背后所体现的政治“正统性”意义进行深入考察。
一、南宋:偏安一隅的自我张扬
宋代是我国“正统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正如梁启超所言:“正统之辨,昉于晋而盛于宋。”*梁任公:《饮冰室文集全编》卷十一《〈历史〉(一)·论正统》,上海新民书局,1933年,第16页。北宋初年,传统的正闰之说仍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不过此后这一观念开始遭到时人的批判与反对,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即是欧阳修,他认为“谓帝王之兴必乘五运者,谬妄之说也”,“《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一六《正统论上》,转引自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中华书局,2015年,第115、114页。,即提出了以“正”与“统”为主要标准的正统论观点。此后,以欧阳修正统观为中心,章望之、苏轼、司马光等人均提出了自己的正统观看法。其中章望之反对欧阳修的看法,更强调以“道德”(正)来评判历史;苏轼、司马光则基本认同欧阳修的观点,“凡不能壹天下者,或在中国,或在方隅,所处虽不同,要之不得为真天子”*(宋)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一《答郭纯长官书》,转引自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中华书局,2015年,第134页。。总之,北宋有关正统观的主流论述,在“正”与“统”两个方面,并相对更偏重于“统”,即更强调王朝的功业所在。
和北宋相比,南宋时的“正统论”则发生了很大改变,在“正”与“统”两个方面开始更强调“正”,即更注重“纲常名分”而非“王朝功业”。所谓“有正者其后未必有统,以正之所在,而统从之可也;有统者,其初未必有正,以统之所成,而正从之,可乎?”“有正者不必有统”,“有正者,不责其统以正之,不可废也;有统者,终于之正,是不特统与正等,为重于正矣”,“无统而存其正统,犹以正而存也;无正而与之统,正无乃以统而泯乎?”。*(宋)周密:《癸辛杂识》后集《正闰》,中华书局,1988年,第98页。而南宋时人,多主此说。如张栻认为,王道之公的关键在于“居天下之正”,赞扬以仁义得天下者。因此在三国究竟谁为正统的问题上,他赞成以蜀汉为正。“汉献之末,曹丕虽称帝,而昭烈以正义立于蜀,不改汉号,则汉统乌得为绝?”*(宋)张栻:《经世纪年序》,(宋)魏齐贤、叶棻辑:《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百二十三,(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第815页。朱熹亦持相同观点,在三国正统问题上,也持蜀汉正统观。为此,他批评司马光说:“温公谓魏为正统,使当三国时,便去仕魏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四《历代一》,中华书局,1986年,第3207页。
南宋正统观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夷夏之辨”的重提与重视。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夷夏观”,本来到唐代时已被“华夷一家”的观念所取代,北宋时期更是出现了超越“夷夏”的族群意识。*可参阅傅乐成:《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台北)《大陆杂志》第25卷第8期,1962年;邓小南:《试谈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文史哲》2005年第5期;熊鸣琴:《超越“夷夏”:北宋“中国”观初探》,《中州学刊》2013年第4期。但南宋初年,观念开始发生明显改变,“夷夏之辨”重又被当时人所关注与论述。这在胡安国于1140年编纂而成的《春秋传》中已有明确表达,“以明复仇之义,严华夷之辨,为其主旨”*牟润孙:《两宋春秋学之主流》,(台北)《大陆杂志》第5卷第4期,1951年。。对此,饶宗颐先生说:“宋代《春秋》之学,北宋重尊王,南宋重攘夷。”*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中华书局,2015年,第81页。前已述及,正是经过《春秋》的借鉴与整理,才形成了正统观理论。因此,“夷夏之辨”之说很快便影响了南宋时人的正统观念,如张栻就说:“由魏以降,南北分裂,如元魏、北齐、后周皆夷狄也,故统独系于江南。”*(宋)张栻:《经世纪年序》,(宋)魏齐贤、叶棻辑:《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百二十三,(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第815页。而南宋末年的郑思肖,更是将华裔观与正统观完全结合了起来。“君臣、华夷,古今天下之大分也”,“夷狄素无礼法,绝非人类”,“圣人也,为正统,为中国;彼夷狄,犬羊也,非人类,非正统,非中国”。*(宋)郑思肖:《郑思肖集》之《杂文·古今正统大论》、《杂文·大义略论》、《久久书·久久书正文》,陈福康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年,第132、177、103页。
南宋之所以一改北宋时所持有的正统观,是与南宋所处的社会政治形式紧密相关的。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金兵攻破北宋都城汴梁,并在第二年四月俘获徽宗、钦宗二帝北归。五月,高宗赵构于南京应天府登基,重建赵宋王朝,是为南宋。南宋建立于风雨飘摇之时,内忧外患不断,一系列政治、经济危机摆在了新登基的高宗皇帝面前。如此,国力强盛并占有中原之地的金与偏安东南一隅的南宋,究竟谁是“正统”,成为高宗皇帝乃至历代南宋皇帝、臣民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尤其是1141年,在金人的压迫之下,南宋与金签订了“皇统协议”(也称“绍兴十一年协议”)。次年,金“遣左宣徽使刘筈,以衮冕圭册,册宋康王为帝”,“俾尔越在江表”,“世服臣职,永为屏翰”*(元)脱脱:《金史》卷七十七《列传第十五·宗弼》,中华书局,1975年,第1756页。,将南宋视为臣下政权,明确以中国正统地位自居。对此,高宗的奉表之词则曰:“臣构言:‘今来画疆,以淮水中流为界……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明)冯琦原编、(明)陈邦瞻纂辑:《宋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二,中华书局,1955年,第586页。确立了南宋偏安一隅并向金称臣纳贡的事实。
在偏安一隅并向金称臣纳贡的情势下,从疆域的角度来说,南宋不仅难以与北宋相比,就是与占有中原之地的金也无法相比,如此“统”也就无从谈起。此时若仍强调“统”,反而对金以及后来的蒙元更为有利。如金海陵王完颜亮便说:“天下一家,方可以为正统。”正是以此为标准,他才发动了侵宋战争,“恃其累世强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元)脱脱:《金史》卷一百二十九《列传第六十七·佞幸·李通》,中华书局,1975年,第2783页。因此,南宋一改北宋重“统”轻“正”的看法,并转而强调蜀汉正统地位,只因他们具有相同的历史处境。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的那样:“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正史类一·三国志六十五卷》,中华书局,1965年,第403页。从称臣纳贡的角度来说,南宋也一改传统汉族政权封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做法,反而被少数民族政权所册封——这被西方学者称之为“倒过来的朝贡(逆向朝贡)”*田浩:《西方学者眼中的澶渊之盟》,张希卿主编:《澶渊之盟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3页。。在此情势之下,南宋朝廷只能强调自己“文明”“开化”的先进性面向,并重拾传统的“夷夏之辨”,将“种族”与“正统”相挂钩,以强调自己作为华夏“君子”之国的纲常名分(即“正”),从而否认金朝政权并彰显自己政权的正统性。所谓“‘夷夏之辨’在宋代兴盛,即起因于疆域狭小引起的自卑感,也与宋儒企图用文化优势弥补军事衰败的脆弱心理有关”*杨念群:《诠释“正统性”才是理解清朝历史的关键》,《读书》2015年第12期。。
前已述及,华夏与夷狄的划分,本质上是以“农”与“非农”为核心标准的。于是,是否有发达的农业生产体系及相应的重农、劝农政策,也就成为彰显王朝正统性的重要方式之一。而这正契合了南宋王朝的政治需要:虽然只能偏安一隅而没有广阔的疆域,虽然迫于野蛮的武力而不得不称臣纳贡,但由于发达农业生产及重农政策的存在,因此“我”仍旧是文明、开化之邦,因而代表着“正统”所在。这些观念与看法(如“夷狄观”),虽不是南宋初建之时就被载入典籍,但作为一种观念应该很早就出现了,并不断将其付诸行动。比如,宋高宗在甫一登基、政权尚未稳固并四处“逃窜”之时,就屡次下诏劝农、蠲免地方税收。如建炎二年春正月,“録两河流亡吏士,沿河给流民官田、牛、种”;绍兴元年春正月,“蠲两浙夏税、和买绸绢丝绵;减闽中上供银三分之一”,“诏江东西、湖北、浙西募民佃荒田,蠲三年租”。*(元)脱脱:《宋史》卷第二十四至二十八《高宗本纪》,中华书局,1977年,第498、504页。正是在此背景下,一套图绘的创作引起了高宗皇帝的高度重视,这就是楼璹的《耕织图》。对此,楼璹的侄子楼钥曾有专门记述:
高宗皇帝身济大业,绍开中兴,出入兵间,勤劳百为,栉风沐雨,备知民瘼,尤以百姓之心为心,未遑它务,下务农之诏,躬耕耤之勤。伯父时为临安於潜令,笃意民事,慨念农夫蚕妇之作苦,究访始末,为耕、织二图。耕自浸种以至入仓,凡二十一事。织自浴蚕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为之图,系以五言诗一章,章八句。农桑之务,曲尽情状。虽四方习俗间有不同,其大略不外于此,见者固已韪之。未及,朝廷遣使循行郡邑,以课最闻。寻又有近臣之荐,赐对之日,遂以进呈。即蒙玉音嘉奖,宣示后宫,书姓名屏间。初除行在审计司,后历广闽舶使,漕湖北、湖南、淮东,摄长沙,帅维扬,麾节十有余载,所至多著声绩,实基于此。*(宋)楼钥:《跋扬州伯父〈耕织图〉》,(宋)楼钥:《楼钥集》卷七十四《题跋·跋扬州伯父耕织图》,顾大朋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34页。
由此记载可知,出于对高宗皇帝“务农之诏”的响应,时为於潜县令的楼璹创作了《耕织图》四十五幅,其时间约为1133-1135年。*据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六“绍兴三年六月戊子”条“右承直郎知於潜县楼璹”、卷九十六“绍兴五年十二月乙卯”条“右通直郎楼璹与升擢差遣,遂以璹通判邵州”的记载,可知楼璹担任於潜县令的时间为绍兴三年至绍兴五年,也即1133-1135年后此图被进献给高宗,并受到皇帝的高度重视。至于进献的时间,白馥兰先说是1145年,后又据渡部武与王潮生的研究认为是1153或1154年。*[英]白馥兰:《技术、性别、历史:重新审视帝制中国的大转型》,吴秀杰、白岚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57、260页。不过,查阅王潮生之原著(1995年版《中国古代耕织图》,第33页),可发现实际上其中并未提及任何进献年份之事,不知白馥兰1153或1154年之说所由何来。不过从“未及”“寻”等词汇来看,时间应该是在图像被创作出来之后不长时间。楼璹《耕织图》后,南宋时期又至少出现了6套与耕织相关的绘画作品,如南宋名臣汪纲《耕织图》、梁凯《耕织图》、刘松年《耕织图》等。而据元代虞集所言:“前代郡县所治大门,东西壁皆画耕织图,使民得而观之。”*(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七言绝句·题楼攻媿织图》,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512页。由此可知,南宋时《耕织图》还在各地广泛传播并推向了民间。
高宗皇帝之所以如此重视楼璹《耕织图》,并在此后被多次创作、传播,只因其符合了高宗及南宋王朝的政治需要。事实上,赞助特定主题的绘画,正是高宗皇帝巩固皇权与确立正统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参见[美]孟久丽(Julia K.Murray):《作为艺术家和赞助人的宋高宗:王朝中兴》,[美]李铸晋编:《中国画家与赞助人——中国绘画中的社会及经济因素》,石莉译,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25-33页。当然,楼璹《耕织图》的创作可能具有多重目的,高宗皇帝重视此图的原因也并不单一,但彰显其相对于金王朝的“正统性”却是一个重要面向。正如高居翰所评论的那样:“对于高宗来说,这些绘画作品都是为了维护其相对于金朝而言的英明的政治统治。金人虽然采取汉人的统治方式,但仍有游牧背景,因而能否承担农民的利益颇可怀疑。高宗在用这些视觉修辞手段时就像是一个政客,农民要求遵守古老、稳定和保守的价值观,同时指控其政敌不理解农民所关心的事情。”*[美]高居翰:《中国绘画中的政治主题——“中国绘画中的三种选择历史”之一》,杨振国译,《广西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而对于建立南宋并鼓励耕织的宋高宗及南宋王朝的正统性,南宋史家则给予了高度肯定。“洪惟国家高宗寿皇,尧父舜子,雍容授受,道迈隆古,盖自揖逊以来,实有光焉。圣上丕承慈训,嗣无疆之历,正统巍然,与天地并。其视尧、舜、禹之传,三朝之盛,兼有其美,帝王之极际,莫大于此。”*(宋)廖行之:《问正统策》,《省斋集》卷九,《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
二、元朝:“内蒙外汉”的自我点缀
与南宋时期相比,元朝耕织图的创作有两个不同的特点:一是耕织图的创作主要集中于元代中期,其中又以仁宗(1312-1321)、英宗(1321-1324)两朝为最;二是出现了非以“江南”为描绘区域的耕织图。之所以如此,是与元朝的政治与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的。
前已述及,南宋正统观的一个重要转变即是开始极力强调“华夷之辨”,并以之否认金朝政权的正统性。对此,早在宋金对立时期,金人就做了极力反驳,认为夷狄也是人,夷狄有文化也一样高贵。*赵永春:《金人自称“正统”的理论诉求及其影响》,《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期。1234年,蒙古灭金,占领了广大的中原之地。当是时,北方汉地有关正统论讨论的一个重要主题即是对“夷夏之辨”“夷夏之防”的突破,并且参与讨论的并非女真、蒙古等被称为“夷狄”的人,而是绝大部分为汉族知识分子。如早在金未亡之时,赵秉文就称南宋为“岛夷”“蛮夷”,而“大金受命,传休累圣,薄海内外,罔不禀令”。*(金)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十八《祭文·宣宗哀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23页。金灭亡后,修端在有关辽、金与南宋孰为正统的讨论中,也流露出对南宋的蔑视与愤恨,并对金的灭亡充满了惋惜之情。*(金)修端:《辨辽宋金正统》,(元)苏天爵编:《元文类》卷之四十五《杂著》,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650-653页。郝经更是对夷夏之防做了彻底突破:“窃惟王者王有天下,必以天下为度,恢弘正大,不限中表而有偏驳之意也;建极垂统,不颇不挠,心乎生民,不心乎夷夏而有彼我之私也。故能奄有四海,长世隆平,包并遍覆,如天之大,使天下后世推其圣而归其仁”*(元)郝经:《上宋主请区处书》,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08-109页。;“圣人有云:‘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苟有善者,与之可也,从之可也,何有于中国、于夷?”*(元)郝经:《辨微论·时务》,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59页。作为汉人,他们之所以没有“华夷之辨”的观念并更认同金的正统地位,只因他们是金的臣民,已完全接受并认同了金的宗主国地位。因此,蒙古灭金之后,他们虽也有惋惜之情,但没有像南宋被灭后宋遗民那样持有强烈的仇恨心态,很快便接受、认同了蒙古的正统地位,如耶律楚材就从天命、威德以及政权实力的角度论证了蒙古政权的正统性。*刘晓:《耶律楚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2-219页。事实上,元世祖之所以发动灭宋战争,“正统云者,犹曰有天下云尔”*(宋)苏轼:《正统辨论·中》,苏轼撰、南宋郎晔选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第十一卷《论》,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第149页。的正统观正是一重要驱动因素:
至元四年十一月,(刘整)入朝……又曰:“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耶?”世族曰:“朕意绝矣!”*(明)宋濂:《元史》卷一百六十一《列传第四十八·刘整》,中华书局,1976年,第3786页。
作为一个兴起于蒙古草原的民族,蒙古人传统过的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并不事农耕。因此,蒙元初年的诸位统治者,从成吉思汗到蒙哥汗均不重视农业生产。相比之下,第一位真正开始关注农业生产的蒙古大汗为忽必烈。1251年,蒙哥汗即位后,派忽必烈去治理漠南地区,在此期间,在刘秉忠等儒士幕僚的帮助下,忽必烈即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参见李迪、陆思贤:《忽必烈的农业政策和农业措施》,《中国农史》1982年第2期。对忽必烈鼓励与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措施,《元史·食货一·农桑》给予了高度评价:“农桑,王政之本也。太祖起朔方,其俗不待蚕而衣,不待耕而食,初无所事焉。世祖即位之初,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于是颁《农桑辑要》之书于民,俾民崇本抑末。其睿见英识,与古先帝王无异,岂辽、金所能比哉?”不过,笔者认为,忽必烈采取农业发展的措施,可能并没有多少提高自身王朝“正统性”的考虑在内。从时间上看,忽必烈系列措施的颁布与实施,主要是在1279年彻底摧毁南宋之前,在他看来,“天下一统”才是最主要的任务及“正统性”的最主要体现,而发展农业生产则主要是为“天下一统”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
元代见于史籍记载的体系化耕织图主要有三部,即程棨《耕织图》、杨叔谦《农桑图》与忽哥赤《耕稼图》,其中程棨《耕织图》为最早的一部。据清乾隆皇帝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耕织图》刻石的题识中称:“《耕图》卷后姚氏跋云:耕织图二卷,文简程公曾孙棨仪甫绘而撰之。织图卷后赵子俊跋,亦云每节小篆,皆随斋手题。今两卷押缝均有仪甫、随斋二印,其为程棨摹楼璹图本,并书其诗无疑。”*转引自王潮生:《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第46页。程棨生平事迹不详,只知系宋人程琳(986-1054卒谥“文简”)的曾孙,字仪甫,号随斋,安徽休宁人,是当时书画家,人称“博雅君子”。程棨摹绘楼璹《耕织图》的具体年代,韩若兰认为是1275年*Roslyn Lee Hammers, Pictures of Tilling and Weaving: Art, Labor, and Technology in Song and Yuan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P.35.36.,若果如此,则此图就不能算元时所绘,应属南宋。但无论如何,此图的创作似不会晚于元代初年,又似乎完全属个人行为,并未如楼璹《耕织图》那样受到皇家与朝廷的重视与推广。因此,程棨《耕织图》的绘制,应该与“正统性”的宣扬并无什么关系。
与程棨《耕织图》相比,杨叔谦《农桑图》的绘制,则具有比较强的、宣扬王朝“正统性”的味道在里面。之所以如此,与元灭南宋后所面临的社会舆论形势及元廷自身的治国方略有直接关系。1279年,元军彻底摧毁南宋的抵抗力量,最终实现了“天下一统”。“但现在忽必烈可能面临更加难以对付的局面,因为他必须获得他征服的汉人的效忠。为赢得他们的信仰和支持,他不能仅仅表现为一位只对中国南方财富有兴趣的‘蛮人’占领者。”*[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史卫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96页。唐、五代以后,经过沙陀、北汉、辽、金等几百年的统治以后,北方民众早已习惯并接受了“异族”的统治,因此对他们来说,蒙古人的到来,更多只是换了一个统治的“异族”而已。但南方地区却截然不同,此地历史上从未“遭遇”过“异族”统治,因此民众在心理上完全无法接受蒙古这样一个“异族”征服者。尤其是经过南宋一百五十余年的统治,在与金王朝的对峙过程中,民众脑海中早已被深深植入了“夷夏之辨”的观念。因此,虽然忽必烈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但这并未消除南方汉人的“敌意”。“在忽必烈的统治结束之前,其他的起义持续不断”,“总而言之,到忽必烈统治的后期,南方并没有完全统一,而且经济问题加上政治分裂在这个地区不断干扰着元庭”。*[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史卫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20-321页。
起义之外,更多的南方汉人则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他们拒绝出仕,拒绝为蒙古人服务。大量知识分子还著书立说,攻击蒙古人的“蛮夷”身份,质疑蒙古人统治的正统性。作为忠于前朝的南宋遗民,他们的正统论更加强调“夷夏之辨”的观念意识,极力维护南宋的正统性。如林景熙就认为:“正统在宇宙间,五帝三王之禅传,八卦九章之共主,土广狭,势强弱不与焉。秦山河百二,视江左一隅之晋,广狭强弱,居然不侔,然五胡不得与晋齿,秦虽系年,卒闰也。”*(宋)林景熙:《林景熙诗集校注》卷五《季汉正义序》,陈增杰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29页。相比之下,郑思肖对“夷夏之辨”的讨论,则最具代表性。郑思肖,原名不详,宋亡后改名为“思肖”,字“所南”,号“忆翁”,皆含有忠于南宋皇室之暗示(“肖”是“趙”的一半)。宋亡后,他留居苏州,余生致力于义理和宗教的讨论,将对蒙古人的恨意埋藏在诗画作品与日常行为中。在《古今正统大论》《久久书正文》等文章中,他刻意强调了“夷夏之辨”,意在影射元朝的蛮夷身份并否认其正统性。“臣行君事,夷狄行中国事,古今天下之大不祥,莫大于是。夷狄行中国事,非夷狄之福,实夷狄之妖孽”,“君臣华裔,古今天下之大分也,宁可紊哉?”“尊天王,抑夷狄,诛乱臣贼子,素王之权,万世作史标准也”,“彼夷狄,犬羊也,非人类,非正统,非中国”。*(宋)郑思肖:《郑思肖集》之《杂文·古今正统大论》《久久书·久久书正文》,陈福康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32、134、103页。正是因为不认同元朝的正统地位,所以许多南宋遗民对元朝采取了不承认的态度,如王应麟、胡三省不用元的年号,潘荣在宋亡后则一直居于楼上,“秉节不履元地”。*王建美:《朱熹理学与元初的正统论》,《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2期。
面对南宋遗民的攻击与批评之声,除了加强行政与军事的控制之外,元朝统治者却并未采取针锋相对地“反驳”或“补救”措施,也并未如后世清朝那样对这些遗民个人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个中原因,或许元朝统治者认为自己已做得足够好,比如重用汉族儒士、实行“汉法”、发展农业生产等;或许他们认为根本就不值得,如高居翰所认为的那样:“蒙古人知道郑思肖这批人的意图,但显然认为他们成不了气候。”*[美]高居翰:《隔江山色:元代绘画》,宋伟航等译,蒋勋审阅,夏春梅修订,三联书店,2009年,第8页。忽必烈去世后,他的孙子铁穆耳即位,是为成宗。《元史·成宗本纪》称其为“守成”之君,“成宗承天下混一之后,垂拱而治,可谓善于守成者矣”。也就是说,成宗在各方面政策上均继承了忽必烈的做法。*[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史卫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38-339页。继成宗之后即位的为武宗海山。海山在位的时间虽然只有三年半,但却给元朝带来了深深的政治危机。世祖、成宗两朝,虽然在本质上奉行的是“内蒙外汉”的治国方略,即以蒙古俗为内核、以汉法为外围的方略*参见李治安:《元代“内蒙外汉”二元政策简论》,《史学集刊》2016年第3期。,但还是采取了大量的汉法措施并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效果。但海山即位后,却一反世祖、成宗两朝的做法,弃“汉法”而大力向蒙古旧俗倾斜,如滥赐、滥爵、滥官等。经济上则大量增加税收,而对农业生产却又不甚重视。如至大二年(1309)夏四月,“壬午,诏中都创皇城角楼。中书省臣言:‘今农事正殷,蝗蝝遍野,百姓艰食,乞依前旨罢其役。’帝曰:‘皇城若无角楼,何以壮观!先毕其功,余者缓之’”*(明)宋濂:《元史》卷二十二《本纪第二十二·武宗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511页。。总之,武宗海山一系列措施的实行,使元朝政治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在世祖、成宗大力实行“汉法”的前提下,都不能获得南方汉人对其“正统性”的认同,武宗复蒙古旧法的措施自更不会获得认同。
1311年1月,海山去世,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是为元仁宗。仁宗一上任,即将海山的主要大臣做了清洗,并将其大多数政策废止,与此同时开始比较全面地实行“汉法”,如恢复科举考试(1315年)等。这其中的重要的一项就是劝农,刊印了苗好谦的《栽桑图说》并将其散之民间,并颁布新令,勉励学校、劝课农桑。*柯劭忞等撰:《新元史》卷六十九《志第三十六·食货二·田制农政》,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89-1590页。一系列劝农文的发布,显示了元仁宗的重农之策。仁宗之所以能实行这些政策,与他深受儒士的影响有直接关系。十几岁起,他开始就学于儒士李孟,后来又任用了赵孟頫等诸多汉儒,还与许多艺术家有交往,因此非常熟悉儒家学说和中国古代历史,并且还能够读写汉文和鉴赏中国绘画与书法。*[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史卫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47页。正是在此大背景下,《农桑图》被绘制出来并进献给了元仁宗。对此,赵孟頫曾有记述:
延祐五年四月廿七日,上御嘉禧殿,集贤大学士臣邦宁、大司徒臣源进呈《农桑图》。上披览再三,问作诗者何人?对曰翰林承旨赵孟頫;作图者何人?对曰诸色人将提举臣杨叔谦。上嘉赏久之,人赐文绮一段,绢一段,又命臣孟頫叙其端。臣谨奉明诏……钦惟皇上以至任之资,躬无为之治,异宝珠玉锦之物,不至于前,维以贤士、丰年为上瑞,尝命作《七月图》,以赐东宫。又屡降旨设劝农之官,其于王业之艰难,盖已深知所本矣,何待远引《诗》《书》以裨圣明。此图实臣源建意令臣叔谦因大都风俗,随十有二月,分农桑为廿有四图,因其图像作廿有四诗,正《豳风》因时纪事之义,又俾翰林承旨臣阿怜帖木儿,用畏吾尔文字译于左,以便御览。*(元)赵孟頫:《〈农桑图〉叙奉敕撰》,《松雪斋诗文集外集》,上海涵芬楼影印元沈伯玉刊本。
从赵孟頫的记载可知,《农桑图》是在集贤大学士邦宁、大司徒源的主持下,由诸色匠人杨叔谦绘制的,并由翰林承旨赵孟頫进行题诗。邦宁,即李邦宁,其本为南宋宫廷的一名小太监,宋亡后随瀛国公(端宗赵昰)入元庭,后受元世祖重用,累官至集贤大学士,《元史》有传。大司徒源,不知为何人。杨叔谦,生平事迹不详,只知其为宫廷画家,潘天寿称其善画“田园风俗”*潘天寿:《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第160页。。赵孟頫,本为南宋皇室后裔,于1286年被忽必烈征召入京为官,累官至翰林院承旨,进封魏国公,《元史》亦有传。笔者推断,《农桑图》可能正是在李邦宁与赵孟頫的建议之下绘制的,二人同为南宋“遗民”,且与南宋皇家关系密切,对楼璹《耕织图》及随后据其所绘之《耕织图》应该都比较熟悉。两人之所以未在世祖、成宗朝建议绘制体系化耕织图,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当时两人地位较低,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世祖、成宗推行“汉法”的热情与力度还不够。事实上,忽必烈当政期间的政策是逐渐趋向保守的。以对儒士的态度为例,即逐渐由信任与重用转为了疏远与压制,到最后更是弃置不用。*申友良:《论忽必烈与儒士关系的转变》,《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
元仁宗推崇并奖励《农桑图》创作的目的,在于“借此证明他重视汉族的农耕生活——一种与他自己祖先截然不同的谋生方式”*Marsha Smith Weidner:《蒙元宫廷(1260-1368)之绘画与赞助研究》,[美]李铸晋编:《中国画家与赞助人——中国绘画中的社会及经济因素》,石莉译,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34页。。而其背后的根本目的,则在于扭转海山在位期间造成的不良影响,以凸显元王朝的非“蛮夷”性与正统性。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农桑图》并非如南宋诸耕织图那样是以“江南”为描绘区域的,而是描绘的“大都风俗”。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应该与元统治者对原南宋“故土”的不待见有关,四等人制就是一典型体现。尤其是东南、也即江南地区,更曾是南宋故都所在,因此当地的汉人更受歧视。正如忽必烈强迫汉人书记官用白话书写一样,他认为“采纳文言文意味着文化上对汉人的屈从”*[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史卫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13页。,元仁宗可能也有同样的心态——虽然他曾大力推行汉法。另外,从“用畏吾尔文字译于左,以便御览”来看,可能我们不能过于夸大元仁宗的汉文读写能力。但无论如何,《农桑图》的绘制还是开了一个好头。仁宗的儿子英宗硕德八剌同样对农桑题材感兴趣,他下令绘制《麦蚕图》于寺庙墙壁之上,以供人观瞻,泰定皇帝也曾命人创作了画名相同的作品。*Marsha Smith Weidner:《蒙元宫廷(1260-1368)之绘画与赞助研究》,[美]李铸晋编:《中国画家与赞助人——中国绘画中的社会及经济因素》,石莉译,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35页。在皇帝的直接与间接支持下,赵孟頫、塔失不花、陈琳等均绘制了《豳风图》,借以传达元代朝廷的重农、劝农、恤农之意。*李杰荣:《元代重农思想与〈豳风图〉的创作》,《农业考古》2015年第4期。
元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朝代,作为一个由蒙古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在其百余年的统治过程中,并未实现传统史学家们所一再强调的“汉化”或“华化”过程。之所以如此,与蒙古统治者所实行的蒙汉结合,以“蒙”为核心、以“汉”为外围的治国方略有直接关系。*李治安:《元代“内蒙外汉”二元政策简论》,《史学集刊》2016年第3期。因此,我们似乎不能过分夸大元代行“汉法”的积极效用。如以广受汉人知识分子欢迎的科举制为例,从1315年开科取士,到1366年,共进行了16次,但仅录取进士1139人,还不如宋代一科多。因此,“说句极端的话,元代的科举只是聊胜于无,或者说几等于无而已”。*王瑞来:《近世中国:从唐宋变革到宋元变革》,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305页。即使向汉法倾斜的英宗,也曾下诏“敕四宿卫、兴圣宫及诸王部勿用南人”*(明)宋濂:《元史》卷二十八《本纪第二十八·英宗二》,中华书局,1976年,第620页。。而剑桥《元史》的编纂者也提醒我们,不能只单纯站在中国的角度看元朝,还应站在欧亚“大蒙古国”的角度来看元朝。正是因为需要极力协调好中国内地与草原帝国的关系,蒙元统治者才采用了这种蒙汉结合的治国方略。这导致“元朝在中国漫长的政治史上从未成为正常的时期”,以至于“1368年蒙古人被赶出中国的时候,他们身上仍旧保留着草原民族的基本特征”。*[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史卫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21、422页。耕织图的绘制是重农的体现,重农又是汉法的重要体现,而汉法只是蒙元王朝政治统治政策的外围而已。因此,耕织图的绘制,归根到底只是元朝“内蒙外汉”政策的一个点缀。
三、清朝:积极主动的自我宣扬
清代是中国古代体系化耕织图创绘的高峰期,出现了多种形式的耕织图,既有宫廷御制的,也有地方自制的;既有描绘耕织的,也有宣扬棉业和蚕桑的;形式上,既有绘画作品,也有石刻、木刻等。*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第77页。清代之所以会出现形式多样的耕织图,是与帝王的重视及提倡分不开的,尤其是前中期的康雍乾三朝。而这三朝帝王,之所以提倡、重视耕织图的绘制与刊刻,很大程度上又是与宣扬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与正统性直接相关的,“帝国皇权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统治并使其合法化……虽然我们过去曾经是游牧民族,但是现在我们同样能够理解汉人的需求,并且已经对国家施行稳定而仁慈的管理”*[美]高居翰:《中国绘画中的政治主题——“中国绘画中的三种选择历史”之一》,杨振国译,《广西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作为又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政权,清统治者一开始就将“正统性”作为王朝建构的核心问题之一而加以重视,正如杨念群所认为的那样,“正统性”才是理解清朝历史的关键所在。*杨念群:《诠释“正统性”才是理解清朝历史的关键》,《读书》2015年第12期。因此,与元代不同的是,定鼎之初,清代统治者就开始了耕织图的绘制与刊刻。
南宋以后,“严华夷之防”成为正统论的核心思想之一。南宋、元代,由于存在比较激烈的民族矛盾与冲突,自不必说,即使明代,这一观念也仍在知识分子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如明初的方孝孺就说:“正统之名,何所本也?曰:本于《春秋》……《春秋》之旨虽微,而其大要,不过辨君臣之等,严华夷之分,扶天理,遏人欲而已。”*(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杂著·后正统论》,许光大点校,宁波出版社,2000年,第56、57页。其后如明中叶的丘浚,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仍在坚持这一思想。如王夫之说:“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明)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册《读通鉴论》,岳麓书社,1988年,第502页。黄宗羲:“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之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宋至亡于蒙古,千古之痛也”。*(清)黄宗羲:《留书·史》,《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2、11页。1640年,清军攻入北京,随后挥师南下,并于康熙元年(1662)最终消灭南明永历政权,奄有除台湾外的中国本土之地,于是由“异族”建立的政权又一次占有了中国之地。面对清军的咄咄紧逼,各地人民纷纷掀起了武装抗清斗争,但在清朝强大军队的镇压下很快便土崩瓦解。武装抗清失败后,明遗民们开始更多地拿起“文化”的武器展开了对大清王朝的攻击,而“夷夏之辨”又成为他们最主要的“武器”之一。
清初,很多人都从“夷夏之辨”的角度对大清王朝进行了批判与攻击,比较著名的如吕留良、曾静等。“中华之外,四面皆是夷狄。与中土稍近者,尚有分毫人气,转远转与禽兽无异”,“华之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为域中第一义”,“夷狄异类,詈如禽兽”,将清廷视为禽兽、夷狄,用文化上的优越感来平衡现实中的政治挫败感。在此基础上,他们又认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人与夷狄无君臣之分”,以此来否认大清王朝的正统地位。而对进犯中国的“夷狄”,必须要“杀而已矣”。“夷狄侵凌中国,在圣人所必诛而不宥者,只有杀而已矣,砍而已矣,更有何说可以宽解得?”*(清)雍正帝:《大义觉迷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六辑,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80、108、172、174、175页。正是基于对故国大明的追思及对大清王朝“夷狄”身份的鄙视与愤恨,清初大量明遗民采取了不合作、不认同的态度,一如元朝初年。如王夫之、张履祥等,在清初所著的著作中,不用清年号,而改用干支纪年法。陈确更是为不食清粟,求削儒籍、弃褚生。*孔定芳:《清初朝廷与明遗民关于“治统”与“道统”合法性的较量》,《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面对清初各地人民的武装抗清及不承认、不认同的态度,清初统治者采取了“刚”“柔”相济的统治策略。首先对各地抗清运动进行了武装镇压,很快平定了各地抗清斗争并攻灭了南明政权。抗清斗争虽被很快平定,但各地民众的拼死抵抗也让清初统治者深刻认识到,武力虽可以定天下,却不可以收服人心,尤其是那些作为汉族儒家文化代言人、社会舆论引导者的精英士大夫们。正如康熙所言:“士人之心,只能以智谋巧取,不可以用武力强夺。”*转引自孔定芳:《清初遗民社会:满汉异质文化整合视野下的历史考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6页。而不能收服人心,也就无法真正实现天下的长治久安。于是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到康熙朝,清初统治者的思想逐渐发生了改变,即由重武尚战转变为标榜理学与教化。*王俊才:《论清初统治思想的演变》,《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为收服人心、维护统治、宣扬王朝合法性与正统性,清代康雍乾三朝采取了种种相关措施。一是对汉人知识分子所秉持的“严夷夏之防”观念——这正是明遗民不认同大清王朝的最根本支持理念,进行了驳斥与破除。这在雍正六年(1728)曾静鼓动岳钟琪反叛案后,雍正帝亲自撰写的《大义觉迷录》中有深刻体现。雍正认为,“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对于明遗民斥满人喻为“禽兽”之说,雍正认为,“禽兽之名,盖以居处荒远,语言文字不与中土相通,故谓之夷狄,非生于中国为人,生于外地者不可为人也”,“《春秋》之书分华夷者,在礼义之有无,不在地之远近”,“中国之人,既有行习类乎夷狄者,然则夷狄之人,岂无行同圣人者乎?”“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而大清作为有德政、知礼义之王朝,“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清)雍正帝:《大义觉迷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六辑,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5-6、155、7、3页。总括言之,《大义觉迷录》主要包括宣德、正名、示警三个方面的内容,“但最终都归结到夷狄之争上”,“是雍正在面临中原汉族反清势力的进攻时,为维护自己统治合理性的一次全面宣传,借以消除百姓对其统治的敌意”。*陈文祥:《从〈大义觉迷录〉看雍正的华夷观》,《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乾隆则把攘夷的观念历史化,强调清人虽是金人后裔,但承袭的却是元明正统一脉,通过重构血缘与地缘关系,破除了宋代以来以种族辨夷夏的正统观。*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三联书店,2010年,第264-269页。理论上的宣传与反驳外,清初统治者还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措施,以破除民众对自己“夷狄”身份的认定,如举山林隐逸、开博学鸿儒科、开明史馆、祭祀明太祖、开经筵讲习,等等。当然,清初统治者的政策并不总是“温情脉脉”的,也有其“残酷血腥”的一面,“文字狱”就是一个典型体现。如仅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八年这六年中,就发生文字狱案41起。而文字狱的最终目的,则在于确立大清王朝的正统意识与观念。*霍存福:《从文字狱看弘历的思想统治观念》,《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6期。
农业生产是国家立足的根基,因此重农、劝农亦是清初统治者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如康熙皇帝就曾亲撰《农桑论》,希望“使天下之民咸知贵五谷,尊布帛,服勤戒奢,力田孝悌而又德以道之,教以匡之,礼以一之,乐以和之,将比户可封而跻斯世于仁寿之域”。*(清)玄烨:《康熙御制文集》卷十八,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第293页。前已述及,农业是“华夷之辨”的前提与基础所在。而在明遗民陈确看来,“农”也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根本所在,所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农焉而已矣”*(清)陈确:《陈确集·文集》卷十一《说·古农说》,中华书局,1979年,第268页。。而在明遗民心目中,满人恰是“詈如禽兽”。因此,对农业的关注亦是宣扬大清王朝正统性的重要举措之一,而这又正契合了清初明遗民的心态与观念。闯贼祸起、清兵南下,繁荣富庶、强盛一时的大明王朝转瞬土崩瓦解,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结局的呢?对此,清初遗民进行了深刻反思,如认为明代假道学、奢靡之风盛、重文而轻质等。*王汎森:《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态与消极行为——不入城、不赴讲会、不结社》,氏著:《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另外,在他们看来,对“农”的忽视亦是导致明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自古人士,未有读书而不能耕者。唐宋而降,学者崇于浮文,力田之业遂以目之农夫细民之所为,士君子罕顾而问焉。然未至以耕为耻如本朝之甚者也。”*(清)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二十《问目·题刘忠宣公遗事》,中华书局,2002年,第587页。为此,在清初明遗民中形成了一种重农、倡农的风气。如陈确说:“季俗浇伪,胥为禽兽,惟农人勤朴,未失古风,而劳苦十倍于古。”*(清)陈确:《陈确集·文集》卷十一《说·古农说》,中华书局,1979年,第268页。张履祥亦说:“稼穑之艰,学者尤不可不知。食者,生民之原,天下治乱、国家废兴存亡之本也。”*(清)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二十三《问目·书里士事》,中华书局,2002年,第659页。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耕织图得到了清初皇家的大力推崇,并被大量绘制与刊刻。
清代第一套耕织图为康熙《御制耕织图》。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南巡时有江南士人进呈宋楼璹《耕织图》残本,带回京城后,遂命宫廷画师焦秉贞依图重绘,并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刊行。*王潮生:《清代耕织图探考》,《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由于由康熙帝亲撰序文并题诗,故名《御制耕织图》。不过此图虽是据楼图而绘,但却并非完全照搬,而是分别有所增减,“村落风景,添加作苦,曲尽其致,深契圣衷,锡赉甚厚,璇镂板印赐臣工”*(清)张庚:《国朝画徵录》卷中“焦秉贞 冷枚 沈喻”条,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58页。。而对于绘制此《耕织图》的目的,康熙在序言中如是说:
朕早夜勤毖,研求治理,念生民之本,以衣食为天……爰绘耕织图各三十二幅,朕于每幅,制诗一章,以吟咏其勤苦而诗之于图。自始事迄终事,农人胼手砥足之劳,蚕女蚕丝机杼之瘁,咸备极其情状。复命镂板流传,用以示子孙臣庶,俾知粒食维艰,授衣匪易。书曰:‘惟土物爱,厥心藏。’庶于斯图有所感发焉,且欲令寰宇之内,皆敦崇本业,勤以谋之,俭以积之,衣食丰饶,以共跻于安和富寿之域,斯则朕嘉惠元元之意也夫!*转引自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第200页。
康熙《御制耕织图》后,“厥后每帝仍之拟绘,朝夕披览,借无忘古帝王重农桑之本意也”*《清雍正耕织图之一(浸种)》,《故宫周刊》第244期,1933年,第455页。,雍正朝、乾隆朝也曾分别绘制有《耕织图》。雍正朝图,由“雍正帝袭旧章命院工绘拟”*《清雍正耕织图之一(浸种)》,《故宫周刊》第244期,1933年,第455页。,画面、画目与康熙焦秉贞图基本相同,只是排列顺序稍有改动。乾隆《耕织图》是由乾隆命画院据画家蒋溥所呈元程棨《耕织图》摹本而作,不论在画幅、画目还是画面内容均与程图相一致。另外,乾隆还曾令陈枚据康熙《御制耕织图》绘《耕织图》。此外,乾隆朝还曾绘有《棉花图》,详细描绘了棉花种植的基本环节与相关技术要领,乾隆还亲为之题诗,故此图又被称为《御题棉花图》。此后,嘉庆帝也曾补刊乾隆《耕织图》。而一系列图绘的绘制与刊刻,主要目的在于彰显大清王朝的重农、劝农之意。正如乾隆在为《耕织图》刻石所做题识中说得那样:“皇考御额,所以重农桑而示后世也。昔皇祖题《耕织图》,镂板行世。今得此佳绩合并,且有关重民衣食之本,众将勒之,贞石以示。”*据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第132页所载拓片整理而成。而其背后的最终目的,则在于宣扬王朝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从而巩固自己的政权。
与元代不同的是,清代由皇家资助或受到皇帝推崇的耕织图,除《棉花图》外,全都是以“江南”为描绘区域的。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清初耕织图的绘制,基本都以南宋楼璹《耕织图》为“母本”绘制而成,而楼图的描绘区域恰是“江南”,因此这是导致清初《耕织图》以“江南”为描绘区域的原因之一。但除此之外,应该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在里面。作为宋代以后,中国经济与文化的中心,“江南”在帝制统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作为农业生产与商品经济的发达之地,早在明代,“江南”的概念就已超出纯地理的范围,而被赋予了“经济富庶区域”的含义。*周振鹤:《释江南》,钱伯诚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四十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而作为文化发达之地,“江南”更是执全国文化之牛耳,那些著书立说、对满清王朝进行猛烈抨击的明遗民们,就主要位于江南地区。正如清高宗弘历所说的那样:“此等笔墨妄议之事,大率江浙两省居多。”*《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六四《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上》,《清实录》第二十册,中华书局影印,1985年,第1084页。相比之下,华北地区的人们,基本未进行抵抗,广大知识分子与文学之士,也很快就认同并接受了大清王朝的统治。*对此,桂涛曾以被誉为清初三大儒之一的孙奇逢为例做了说明,认为经历了明季北方战乱的孙奇逢,自然倾向于将明朝的灭亡视为王朝自身衰亡所致。相反,对至迟于1644年尚处于逸乐之中的江南士人而言,清兵南下才引致了世运的转移。如此,导致了南北双方对于清朝入主的不同理解。桂涛:《“元初-清初”的历史想象与清初北方士人对清朝入主的认识——以孙奇逢为中心的考察》,《清史研究》2013年第3期。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要收服全国,必须要收服“江南”。正如钱谦益所说的那样:“夫天下要害必争之地不过数四,中原根本自在江南。长淮汴京,莫非都会,则宜移楚南诸勋重兵,全力以恢荆襄。上扼汉沔,下撼武昌。大江以南,在吾指顾之间。江南既定,财赋渐充,根本已固,然后移荆汴之锋,扫清河朔。”*(清)钱谦益:《钱牧斋致瞿稼轩书》,转引自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三联书店,2001年,第1036页。而从“正统性”的角度来说,收服江南人心更是必不可少。因此,与元代统治者对“江南”主要是压制与防范所不同的是,清初统治者对“江南”抱持的则是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即要处处设防,又要时时拉拢。对此,杨念群有非常真切地描述:
清人尤其是清初帝王对“江南”往往抱有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嫉妒的心态……可以说,凡是在满人眼里最具汉人特征的东西均与“江南”这个地区符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如何使江南士人真正从心理上臣服,绝不是简单的区域政府和制度安排的问题……过去是对中原地区的占有,具有象征的涵义,而对清朝而言,对中原土地的据有显然已不足以确立其合法性,对江南的情感征服才是真正建立合法性的基石。*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三联书店,2010年,第13-15页。
因此,以“江南”地区为耕织图的描绘区域,应该也带有收服江南人心、确定政治正统性的考虑在内。总之,经过清初诸帝的努力,大清王朝的“正统性”逐步被人们所接受与认同,“明遗民”作为一种存在也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对这一过程,可参阅孔定芳:《清初遗民社会:满汉异质文化整合视野下的历史考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三联书店,2010年。
四、讨 论
以上我们对中国古代体系化耕织图与王朝正统性构建之间的关系做了大体论述,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不论南宋、蒙元还是清代,耕织图的绘制与刊刻都得到了皇帝与朝廷的褒奖与宣扬,成为他们宣扬自身王朝正统性的一个面向。而耕织图与“正统性”之间之所以能够建立起联系,与南宋以后“华夷之辨”成为正统论建构的核心理念有直接关系,而其背后所根本体现出的又是传统中国以农为本、重农劝农的治国理念。
当然,对南宋、元、清三个王朝来说,情况又各有不同。南宋是由“华”(时人意义上的)所建立的王朝,按说本不该有正统性的忧虑,但由于军事衰败、国土促狭而偏安一隅,不论相对于金还是蒙元王朝而言,都具有多方面的正统性“劣势”,于是只能通过文化与经济上的“优势”来弥补军事与国土面积(“统”)等方面的不足与“劣势”所在。相比之下,蒙元与清朝,作为由“夷”(时人意义上的)建立的王朝,在传统儒家文化(由“华”所主导)为基本治国指导思想的情况下,他们总是多少有些文化上的“不自信”。而要想破除这种“不自信”,要想改变主流观念对他们合法性与正统性的不认同,于是他们相应采取了绘制与刊刻耕织图等在内的一系列“华”化措施。不过,仅就耕织图的绘制与刊刻所体现的情况而言,蒙元与清亦有不同:大清王朝非常地积极与主动,建国之初即在帝王的支持下进行了耕织图的绘制与刊刻;蒙元王朝则相对“消极”,一直到王朝统治的中后期才有相应的措施施行。之所以如此,应该与两个王朝不同的治国方略有直接关系:作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地域辽阔的大帝国,蒙元统治者必须要兼顾作为“本土”的蒙地与作为被征服地区汉地的实况,于是相应采取了“内蒙外汉”的政策;相比之下清就没有这方面的过多顾虑,虽然他们也采取了满汉分治的政策,但却是以“汉法”为根本核心的。
至于明代,既没有南宋偏安一隅的忧虑,亦没有蒙元、清王朝“华夷之辨”的顾虑,因此也就没有帝王、中央政府等支持耕织图绘制与刊刻的情况存在。如今已知的、绘制于明代的体系化耕织图主要有三套,即邝璠《便民图纂》耕织图、宋宗鲁《耕织图》及仇英《耕织图》。《便民图纂》本质上是一部日用类书,其编纂者邝璠虽做过吴县知县,但此书却并没有获得帝王或中央政府的崇奉与支持。宋宗鲁《耕织图》刊刻于明英宗天顺六年(1462),宋宗鲁时任江西按察佥事。关于此图,文献记载不多,因此其更详细的情况不得而知,国内至今亦未见其翻刻本*王红谊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红旗出版社,2009年,第344页。,然整体来看,此图亦没有帝王或中央政府支持的迹象存在。至于仇英《耕织图》,明显是个人兴趣之所为。仇英为明代著名的职业画家,据说为满足“市场”所需,他曾临摹过他所能接触到的所有唐宋绘画,以供创作之用。*[美]高居翰:《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杨贤宗等译,邓伟权审校,三联书店,2012年,第101-102页。因此,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这套《耕织图》,很可能就是他临摹古画的结果。总之,由于明代并没有“华夷之辨”的正统性顾虑,因此也就没有帝王或中央政府支持耕织图绘制与刊刻的情况存在。
耕织图与王朝正统性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象征性意义建构。所谓象征,就是具有意义的现象,指向的是与其自身意义完全不同的其他意义*Edward L. Bernays, “The Semantics of Symbols”, in Lyman Bryson Louis Finkelstein R. M. Maciver Richard Mckeon (eds.), Symbols and Values: An Initial Study, Literary Licensing, LLC, 2011, p.242.,它“旨在唤起或产生一种与时间、空间、逻辑或象征想象有关联的态度、系列印象或者行为模式”*Murray Edelman, The 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5, P.6.。据此,虽耕织图本意表达的是水稻种植与蚕桑、丝织生产,但其背后却能隐喻出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也即与其自身意义完全不同的另一层意义。象征有两个基本构成要素,即“载体”与“意义”。载体是象征的表现形式,在此即耕织图;意义则是载体所承载、传达出来的意义,在此即王朝正统性问题。“载体”和“意义”紧密相关、不可分离:没有“载体”,“意义”就无法存在;没有“意义”,“载体”就只是一个普通物品或行为,也就不成其为“象征”。当然,“载体”与“意义”都是具有多样性的,两者间的对应关系也并非是唯一的。也就是说,耕织图背后的象征与隐喻意义,并非只有正统性问题,还有诸如重农劝农、勤政爱民、社会教化等象征寓意;正统性也并非只有耕织图才能突显与表达,其他如国号、服色等也都是彰显正统性的重要元素与手段。另外,载体与意义之间的联系也并非是自然而然建立起来的,而是人为建构的结果。而这种联系之所以能被建构起来,又是与一个社会或群体所在的文化脉络、社会情境等紧密相关的。就耕织图与正统性言之,两者之间之所以能建立起象征性联系,本质上与以农为本的治国理念有直接关系。
中国古代耕织图与正统性间的象征性建构与联系,又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面向,即象征性特色。当然,政治象征特色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在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政治运作中都广泛存在着。从政治运作的角度来说,政治过程可大体分为两个层次,即权力体系与象征体系。权力体系由政治制度、机构、职位及由它们所决定的政治结构组成,如政府、法律、军队等,政治权力渗透其中并为其提供保障;象征体系则由政治信念、价值观和各种象征符号所组成,如国号、服色、礼仪等,并在政府获取合法性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马敏:《政治象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27页。两个层次中,权力体系是“刚性”的,往往会通过直接的权力运作或暴力执行等手段进行政治操控与运作;象征体系则是“柔性”的,主要通过“和风细雨”的手段,潜移默化地发挥影响力。就两者的关系言之,虽然它们都是政治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象征性”可能是更为根本与主要的面向。“整个帝制中国实际运作的礼乐制度、政治制度及政策过程,实际上都是(以君权为中心)统治合法性信仰的象征系统”*张星久:《象征与合法性:帝制中国的合法化途径与策略》,《学海》2011年第2期。;“中国传统政治论述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逻辑的,不如说是仪式的;其表达方式少有逻辑修辞之严谨的‘证成’,而更多地侧重于情感之调动与控制的‘表演’”*萧延中:《我们生活在一个“真正的真实”的镜像社会之中》,马敏:《政治象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序”第18页。。在这一象征体系下,统治者好比是演员,观众则是广大的民众,剧本则是经由历代积淀而成的、被人们所共同认可的政治意识、观念、仪式、符号等。“演员”表演的目的,在于努力使自己的演出被大众所接受与认可,并进而在此过程中向他们灌输自己的意识与观念。
在传统中国政治运作的过程中,象征体系可能没有权力体系的作用那样直接与明显,但却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权力体系要想真正实现自身,就必须要依赖象征体系的运作。“在所有的社会中,政治象征和符号在政府获取合法性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政治社会化不仅是公众习得政治知识和技能的过程,它更是国家对公众灌输一套既定政治价值和观念,以培养政治忠诚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实现,更多是以对政治象征的作用而达成的。”*马敏:《政治象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27页。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正如著名华裔学者陈学森(Hok-Lan Chan)所说的那样,“在中国,符号特性,包括正当性权威概念本身……以及与这些概念形影相随的仪式和象征,具有人为设计和精心修饰的倾向……统治者和其支持者通过大量的仪式操作以应对现实的政治需求……这些各种各样的象征,经常因应形势的不断变换、国家政治状况的更迭而得到加强。作为另外的政治手段,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即席表演,也为获得他们声称的合法性权威提供认可的支持”*转引自马敏:《政治象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20页。。马起华认为,“象征”对“政治”的作用机制,可概况为八个方面,即“引起知觉”“隐喻联想”“引发认同”“产生信仰”“激发情绪”“形成态度”“支配行为”“促进沟通”。*马起华:《政治行为》,(台湾)正中书局,1977年,第165-168页。也就是说,“象征”之于“政治”,主要是通过思想引致的途径发挥作用的,重在通过对集体认同的训导和教化,展现、维持并强化共同体内部的某种意识与观念。
回到南宋、蒙元、清代耕织图的绘制与刊刻上来,可以发现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象征性行为,因其并非是通过实际的官僚体系运作展开进行的,而更类似于一种褒奖性、提倡性的仪式行为。其意义的强调,更多是“说教式”的、一切尽在不言中的,而非法律、制度式的硬性话语。其意义的产生,明显是通过马起华所说的“引起知觉”“隐喻联想”“引发认同”“产生信仰”这一模式展开进行的,即通过耕织图像本身及图像绘制这一行为本身,与人们头脑中已有的意识与观念相共鸣,从而引发他们的联想与认同。而这种共鸣、联想与认同之所以能够发生,又是与上至帝王、下至普通百姓所共同持有的知识背景、价值理念等紧密相关的,如“以农为本”“华夷之辨”等。对没有这一“知识背景”的人而言,如现代人,耕织图及其创作,仅仅也就只是一种图像的绘制而已。因此,正如吉尔茨所说的那样,象征要想发挥其功用,就必须具有“公示性”(public)的特点,即必须让大家所熟悉与共知。*王海龙:《导读二:细说吉尔茨》,[美]克利福德·吉尔茨:《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导读”第39-40页。当然,前已提及,耕织图绘制与刊刻的象征性意义,并非仅仅只是为了凸显“正统性”这一个面向,而是还有多重意义与价值,如彰显最高统治者重农耕、尚蚕织的统治理念,体现帝王对农业、农民的重视与关心;鞭策、劝诫各级官员重视农业生产、永怀悯农与爱农之心;教化百姓专于本业、勤于耕织,等等。*参阅王加华:《教化与象征:中国古代〈耕织图〉意义探释》,《文史哲》待刊稿。另外,作为一种“仪式表演”,其程式与剧本也并非一成不变,而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明代之所以未有帝王或中央政府支持的耕织图绘制与刊刻,就因为没有此项“表演”的需要;蒙元与清代的不同,也是因为他们的表演舞台与面对观众有所不同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