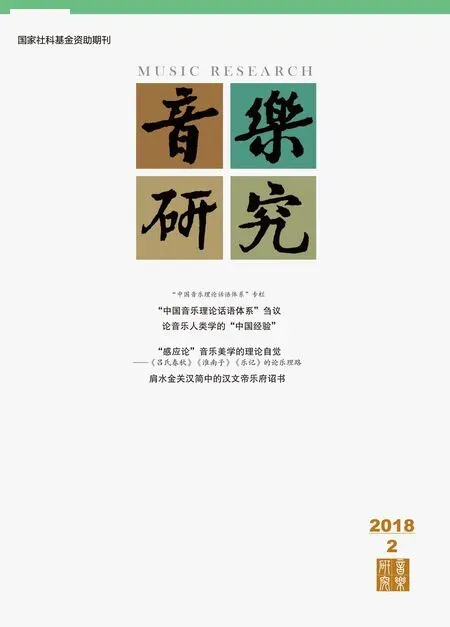“感应论”音乐美学的理论自觉
——《吕氏春秋》《淮南子》《乐记》的论乐理路
文◎刘承华
战国末至汉初的近百年间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对先秦学术的综合成为主旋律。代表作有战国末吕不韦主持编撰的《吕氏春秋》、西汉前期淮南王刘安主持编撰的《淮南鸿烈》(又称《淮南子》)以及同时期河间献王刘德主持编撰的《乐记》。这三种著作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1)都是以对先秦文献的综合为基础,又有自己独特的整合和发挥。(2)都有丰富的论乐文字,且都表现出一定的系统性或体系性。(3)都突出地体现了一种被称之为“感应论”的思维方法或思想范式。第三个特点尤为值得重视,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中的感应论倾向,虽然在之前即已存在,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他们的音乐美学其实都是建立在“感应”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作为一种较为完整的音乐感应论,系统地、自觉地运用“感应”原理来解释音乐活动中许多现象,则是在此时的这三部著作中才真正实现,并一直影响着后来音乐美学的理论思维。
一、“感应论”的基本原理及其形成
中国古代“感应”思想源于《周易》。《世说新语·文学》载,殷仲堪问释慧远:“《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殷又问:“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慧远“笑而不答”。“感”就是“感应”。在慧远看来,《易》的基本精神就是“感应”。为了解释“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余嘉锡注引《东方朔传》云:“孝武皇帝时,未央宫前殿钟无故自鸣,三日三夜不止。诏问……东方朔,朔曰:‘臣闻铜者山之子,山者铜之母,以阴阳气类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钟先鸣。《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应在后五日内。’居三日,南郡太守上书言山崩,延袤二十余里。”①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0—241页。铜出于山,两者存在着某种联系(东方朔以“母子关系”喻之),所以,山欲崩,铜钟便有感应,未击而自鸣。这个故事比较真切而又形象地反映了古人对《易》以及“感应”的理解。
1.“感应”的基本原理
考察《周易》中的“感应”,实际上存在两种类型,一是“同类相感”,一是“对立相感”。所谓“同类相感”,就是《易》中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周易·乾卦·文言》曰:“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从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②(唐)孔颖达《周易正义》,李申、卢光明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同类相感”即指具有相似性的事物易于发生感应。所谓“感应”,就是一方发生变化,与之同类的另一方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应。这里实际上还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媒介,一是“同声相应”之“声”,一是“同气相求”之“气”。“声”是指声音的频率,董仲舒解释说:“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则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③(汉)董仲舒《春秋繁露》,载《春秋繁露义证》,苏舆撰,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58页。这里的“数”就是弦振动的频率,频率相同,就会出现感应共鸣。事物的运动都有一定的节律,节律相似者,也会发生感应。在这里,节律、频率都是可以用数来表达的,都是比率问题,所以属于形式范畴。形式相似,易于发生感应。“气”则不同,它不属形式,而属质料。以“气”为媒质的感应,古人是以阴阳来解释的。董仲舒说“气同则会”,这“会”便是通过阴阳实现的:“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④同注③,第360页。阴气与阴气相应,阳气与阳气相应,不管它发生在物与物之间,还是天与人之间,原理都一样。
另一种是“对立相感”,也是在《周易》中,如“咸”卦“彖辞”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⑤同注②,第139—140页。这里讲的是阴阳二气互相感应而化生万物,阴阳二气是相互对立的两面,但也能够发生感应,而且正是因其对立,才会发生感应。先秦诸子中即有人认识到这一点。庄子说:“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欲恶去就,于是桥起。雌雄片合,于是庸有。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⑥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96页。这是说事物对立面之间的相互感应使得万物化生,大化运行。荀子也说:“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⑦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王先谦《荀子集解》(上、下),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66页。这种以阴阳相感的现象也被后人所接受,但他们称之为“异类相感”。孔颖达《周易正义》云:“其造化之性,陶甄之器,非唯同类相感,亦有异类相感者。若磁石引针,琥珀拾芥……其类繁多,难一一言也。”⑧同注②,第18页。张载《横渠易说》也指出事物间有“以异而应”者,“感之道不一:或以同而感,……或以异而应,男女是也,二女同居则无感也。或以相悦而感,或以相畏而感”⑨(宋)章锡琛点校,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25页。。不过,严格说来,“异类相感”之说并不准确,因为他们所谓能够相感的“异类”并非一般的“异类”,而是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互相对立的“异类”,阴阳二气即属此类。不在一个统一体内的异体,不相对立,故而也不会发生感应。如动物中不属一个科目的雌雄之间,不会互相吸引。不过,“对立相感”只是表面现象,其本质还是“同类相感”。既然是一事物的对立面,则对立各方均有所缺,且所缺又正好在对方,因而形成互相间的需要,需要产生吸引,吸引完成互补。物理学中有“趋于平衡态”的定律,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它一定是平衡的。但若将其划分为阴阳两面,则平衡被打破。阴的一面是阴多阳少,阳的一面是阳多阴少。按照“趋于平衡态”的原理,多的一方便自然要向少的一方流注,少的一方也需要从多的一方接纳,我多的给你,你多的给我,此即《周易》所说的“相与”。“与”就是给,就是介入对方,满足对方,就是“雌雄片合”,达成双方的平衡、协调、和谐。这里面的实质是:我所需要的正是你所拥有的,而你所需要的也正是我所拥有,一方的所“需”与另一方的所“有”是同一类事物,故此感实质上仍然是“同类相感”。也就是说,作为感应的原理和机制只有一个,就是“同类”,是彼此相同、相似、相近。
感应有简单感应和复杂感应之分,从最简单的感应到最复杂的感应之间,可以有无数个层级。感应通常由“气”“阴阳”“五行”等要素构成。“气”是物质性、质料性的媒介,“阴阳”提供“同类相感”和“对立相感”的契机,“五行”则提供一个封闭的动态平衡模式,代表着事物运动的形式规律。三者结合为一个有机系统,它可以存在于不同的事物现象之中,并由此形成多种形式的感应。
“感应论”表述了中国思想范式中在因果联系之外自然界的另一个重要联系机制,是值得重视的。
2.《吕氏春秋》《淮南子》《乐记》中的感应思想
对“感应”的理论思考在战国后期即已开始,到西汉董仲舒那里基本完成,在《吕氏春秋》《淮南子》和《乐记》等书中亦都有明显的体现。总括这三部著作的感应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万物感应系统。这在《吕氏春秋》中表现最为突出,全书的框架,即以阴阳五行的思想为纲,阴阳五行是框架,感应则是其中的黏合剂。其中一个最为直观的表征,就是它采用与四时的感应关系来安排全书的结构,这就是书的主体部分“十二纪”。它以春夏秋冬四季为序,每一季又分为孟、仲、季三月,分别对应各种自然现象、人事活动包括音乐,认为在十二纪中各类对应事物之间即存在着感应关系。《淮南子》虽然没有以十二月安排书的结构,但是在“时则篇”中也是将四时与各种自然事物社会现象相对应,阐述其间的感应关系。
其次是运用五行来建立自然与社会的对应关系。在感应论的系统中,五行是一个重要的工具。由于“金木水火土”互相之间存在着特定的相生和相克的关系,所以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解释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其中最典型、也最常见的就是中医的五脏对应五行,以五行的生克来说明五脏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解释生命体运行的状态。而用五行来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也是先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吕氏春秋》中,即以五行相胜的规则来解释和预测历史朝代的更替,所体现的是五行与自然以及政治之间的感应关系。
再次,都对感应的原则是“相类”“相同”做了自己的表述。《吕氏春秋·有始览》中专门有一章叫“应同”,是直接阐述事物间“同类相动”原理的。它说:“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这也就是《周易》中的“同类相动”,并且也是从“气”(质料)和“声”(形式)两个方面来说明的。类相“同”,才会有“感应”,所以本章名为“应同”。《淮南子》也主张“同类相动”,认为感应的机制是“相似性”。他以调弦为例:“今夫调弦者,叩宫宫应,弹角角动,此同声相和者也。”《乐记》是论乐专著,故对自然社会涉及不多,但其感应思想与前两者一脉相承。它对音乐本体论的表述就是“人心之感于物也”,也认为音乐与自然社会的联系机制是“同类相动”,即“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乐象篇》)。
“感应”,就其原初的词义来看,“感”是感,“应”是应,两者含义不同。孔颖达《周易正义》云:“感者,动也;应者,报也。皆先者为感,后者为应。”⑩同注②,第18页。就是说,“感”是先发,是主动,“应”是后发,是被动。庄子也是这样理解的:“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庄子·刻意》)这只不过是在理论上做这样的划分和界定而已,在实际的感应活动中,感应一旦发生,就很难区分是谁感谁应了,因为它是由感而应,应者又转而为感,感而又有应,形成一个持续的互相感应的过程。正如王夫之所说:“感者,交相感。阴感于阳而形乃成,阳感于阴而象乃著。”⑪(清)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页。可见,古代的“感应论”,就其实际而言,它是非线性的,是双向互动的。
3.音乐感应论的早期形态
感应思想在先秦的乐论中即有所表现,如音乐与政治、伦理、天文、地理、神灵的联系,乐器与自然、人事的对应关系,五音与五方、五味、五色、五行的对应关系;十二律与十二月的对应关系,等等。
在先秦论乐文献中,较早体现感应思想的是晋国乐师师旷。他以“歌南风”来测楚军战势,楚在南方,用的就是感应原理。吴国季札在鲁国观乐,所作评论体现的也是感应思维。齐国晏婴“济五味,和五声”,“以平其心,成其政”,遵循的也是感应原理。道家文子也是在感应基础上论乐,认为圣人治理天下,之所以要取法于天、地、人,就是因为要打通三者,建立感应关系;之所以能够调阴阳、和四时、察万物、制礼乐、行仁义、治人伦,也就因为它们之间本来就存在着相通、相同、相似之处,具有发生感应的可能。总之,在先秦,凡是在论乐时将乐与政治、伦理、天地、神灵、万物相联系,并能互相影响的,其深层意识中均为感应,只是没有在理论上自觉,没有用概念表达出来。直到《荀子·乐论》,才把这个问题明确了起来:“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乱生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应,善恶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首先,这里明确地使用了“感”“应”二字,并对它们有明确的分工:感为先,应为后。感后有应,应从感起。其次,他描述了一个完整的音乐感应过程,具备感应所需的重要环节。“奸声”和“正声”是感应源,受感者是人的听知觉。听知觉受感后分别在其主体产生“逆气”和“顺气”,这主要是在精神、人格、道德层面,故而还在人的内部。“逆气”“顺气”形成后便会通过表情、姿态、行为等外现出来,即所谓“成象”,不同的气便形成不同的象,于是有社会的“乱”和“治”。因为自然人事中存在着这种感应(“唱和有应”),而且善恶分明,各循其道(“善恶相象”),所以应该小心辨别,谨慎而行。这一段话,文字不多,但所表现出来的音乐感应思想,虽然只是一个框架,却已经是比较完整,表达也比较清晰。
但是,真正大规模运用感应论,使感应论音乐美学思想得到系统表达的,还是要到战国末的《吕氏春秋》以及西汉初的《淮南子》和《乐记》。
二、《吕氏春秋》:以作乐为中心的音乐感应论
《吕氏春秋》⑫本文所引文字均来自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为节省篇幅,所引文字只在文中夹注章节标题,不再另列注释。的音乐感应论主要是通过音乐的发明和制作体现出来的。在其《仲夏纪》中有“古乐”一章,是讲音乐的起源和创造的。它以一个个小故事构成,这些故事究竟是神话还是史实,现在已难以逐一判定。判定它们的真实程度,对于音乐形态史学的研究是至关重要,但对于音乐美学思想或思想史的研究,却无关紧要,因为即使是虚构的神话,也一样反映着当时人的音乐观念和思维方式。
1.音乐感应的本体论论证
在《吕氏春秋》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也可以说是一个矛盾,即该书的论乐竟然有两种音乐本体论:自然本体论和心本体论。在《仲夏纪·大乐》中阐述的是自然本体论:“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形体有虚,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度量”就是数,“太一”即道。他说:“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吕氏春秋》与《老子》不同,他的“道”就是“太一”,“太一”就是“一”,“一”即为“气”。“气”为一,分而为二,即为阴阳。阴阳运动变化,产生度量和秩序,音乐由此而生。这里的道、太一、两仪、阴阳、度量,都是自然,所以说这是音乐的自然本体论。另外,在《季夏纪·音初》中,又阐述了一种心本体论:“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匿。故曰:乐之为观也,深矣。”这里又认为音乐本(原)于人心,是“感于心则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这两句中,前一句是本体论,说明音乐的本原在于心,心感而后有音之运动(“荡”)。后一句是审美论、功能论,音乐形成以后,又作用于人心,影响着人心,实现感化的效应。正因为音乐源于人心,所以才能够从音乐“观其志,知其德,察其政”,明其盛衰,辨其君子小人。
如何理解这两种不同本体论的并置?一种比较简单浅显的解释是,由于该书是摘取前人文献整理改编而成,在所取文献中比较容易将不同内容甚至相矛盾的内容一起收入。但《吕氏春秋》虽然主要运用先秦文献进行著述,但并非资料汇编,而是经过编撰者的消化整合;虽然思想比较杂,但经过整合后,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整体,具有比较统一的理论主张,不至于在本体论上出现这样明显的问题。另外有一种解释是,《大乐》中的本体论只是针对作为物理现象的音声而言,《音初》中的本体论才是作为艺术的音乐的本体论。这一说法,乍听好像有道理,细思则难成立。“形体有虚,莫不有声”,确乎是指物理之音声;但“声出于和,和出于适”,特别是“先王定乐,由此而生”,则明显不止是物理音声了,而就是作为艺术的音乐,与《音初》中建立在“心”之上的音乐没什么两样。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其实,我们只要认识到《吕氏春秋》是从于感应论乐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感应论虽然也涉及客观事物之间的互相感应关系,但主要还是人与外部世界万事万物的感应。也就是说,这里的感应,一方是我们自己—人,而人的感应体又主要是“心”;另一方则是与我们相对的万事万物,包含自然和社会。而音乐,则是这感应的中介环节。这样就成为:自然←→音乐←→人心-社会。这三者具有感应关系,才能够互相影响,互相作用。而感应关系的理论论证,即是由本体论承担的。其原理是:音乐只有来自自然,才能与之发生感应,所以需要自然本体论的论证。同样,音乐要想影响人心,作用社会,也必须在两者之间存在感应关系,于是又有了心本体论。由此看来,《吕氏春秋》中的两种音乐本体论并不矛盾,也非误作,而是在“感应论”驱动下的自然结果。
正因如此,古代先王才十分重视制作音乐用来影响、调节自然和人心。《仲夏纪·古乐》中有两则记事,一则云:“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畜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另一则是:“昔阴康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这两则故事都是以音乐来影响自然,调节自然的。第一则是阳气过盛,炎帝命其大臣士达做五弦瑟,以音乐招来阴气,恢复阴阳的平衡。第二则是阴气过盛,水道不畅,河流漶漫,民之体气郁滞,筋骨僵硬。阴康氏的首领编制舞蹈以教其民,用以泄除阴气,增加阳气,使自然获得平衡,身体恢复健康。这两个故事都是从自然到音乐、再由音乐影响自然的感应过程。音乐只有源于自然阴阳,才会有影响自然、调节阴阳的能力。
2.通过仿效建立感应关系
如何才能使所作之乐对自然社会人心有更强大的影响力?根据《周易》“同类相动”的原理,就必须使音乐与自然“相类”。“相类”的方法,就是仿效。仿效才能够建立音乐与自然万物的联系通道,为感应提供契机。就这个意义上看,《仲夏纪·古乐》中的许多作乐的故事也就容易理解了。例如:“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昆仑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薄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曰‘含少’。次制十二筒,以之昆仑之下,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之本也。”又:“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乐,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乃令鱓先为乐倡。鱓乃偃寝,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又:“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作歌,乃以麋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这里,黄帝一则是制律,即为音乐制订基本的标准和制度。颛顼和尧的故事则是从自然取得音源,创作音乐。这三人的乐官——伶伦、飞龙和质的作乐,有几个共同点值得注意:其一,他们都是取自然之物的材料制作发声之器,如竹、石、兽皮。其二,都是以模仿自然界的声音为音响,如凤凰之鸣、八风之音、山林溪谷之音等。其三,也都以自然之数规范音乐形态,如十二律之于十二月,雌雄之于阴阳等。音乐本来是人类的一项发明,是纯粹的创造,但《古乐》中的几个故事却反复将其归于自然,溯源于自然,其目的就在音乐与万事万物之间建立联系的机制,从而形成感应关系。
再从另一方面看,音乐要影响社会人心,也得从模仿社会人心入手。《古乐》中的另外几则故事表达了这个思想。“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漻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于是命皋陶作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又:“殷汤即位,夏为无道,暴虐万民,侵削诸侯,不用轨度,天下患之。汤于是率六州以讨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宁。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又:“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於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作为《大武》。”禹的时代,洪水泛滥,禹率民用力治水。这个工程浩大,需要增强人民的信心,故命皋陶创作《夏籥》九章,激励民心。夏桀无道,汤除而建商;商纣无道,武王伐商而建周。这两次重大的改朝换代,使社会发生强烈震荡。为使众民尽快从内心接受并认同这一变化,商汤命伊尹创作《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武王命周公创作《大武》,都是用音乐来表现这些重大事件,其目的则是借助音乐的力量、通过感应的方式来影响人心,统一臣民的思想和意志。
在上古时期,人的生产力十分低下,生存的能力比较薄弱。为了获得生存的信心,寻求自然或神灵的帮助,往往会用到巫术,而音乐也常常作为巫术的重要工具。音乐之所以能够作为巫术的工具,就在于其积淀着浓厚的感应思想,即相信通过音乐的力量可以影响到与之相关的事物。《古乐》一则著名的乐事记载,即属此类:“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直观地看,这则故事只是描述了一次歌舞表演活动,但仍然透露出当时普遍存在的巫术思维,反映出的也仍然是感应的影响方式。“歌八阕”即唱八段歌词,每段一个主题。第一阕“载民”,是歌颂人类生活其上的大地。第二阕“玄鸟”,是歌颂葛天氏部落的图腾。第三阕“遂草木”,是希望百草树木能够生长茂盛。第四阕“奋五谷”,是祝愿庄稼长得壮,有好收成。第五阕“敬天常”,对天地永恒的规律表示敬畏和感谢。第六阕“达帝功”,表达能够获得通向天帝之功的道路。第七阕“依地德”,表示要遵循四时的规律安排生产和生活。第八阕“总万物之极”,总结自己的愿望,是要让万物都能充分发展,各得所安。这八个方面的内容,几乎包括当时生活的全部。他们一一唱来,就是相信自己的歌声能够使天地自然有所感应,从而能够满足自己的愿望。同时又能够在同伴的心中引起共鸣,从而产生共同的意念和信心。
3.从感应凸显“适音”的重要
正因为音乐有此巨大影响,故而必须重视音乐的制作。因为,不同的音乐对人发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仲夏纪》中,论乐诸篇其次序是:《大乐》《侈乐》《适音》和《古乐》。《古乐》是叙史,是述例,而前三者都是论理。《大乐》讲音乐的本原和本质,是正。《侈乐》是对大乐的违背,是反。《适音》则是对作乐标准和原则的陈述,是合。
音乐感应的标准应该在哪里?《吕氏春秋》认为应该在人之心中寻找,因为是心统领身体,支配耳目鼻口等诸种感官。他说:“耳之情欲声,心不乐,五音在前弗听;目之情欲色,心弗乐,五色在前弗视;鼻之情欲芬香,心弗乐,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乐,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乐之弗乐者,心也。”快乐源于感官的需求,但不是只要感官需求得到满足就可以产生快乐。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心”。心不乐,则尽管感官得到满足,仍然不会有快乐产生。那么,“心”如何才能快乐?答案是:“心必和平然后乐。”就是说,心过分紧张和过分松弛都不能产生快乐。心理学已经表明,人的心理若过分紧张或松弛,感官上的刺激反应就会受到抑制,变得无法感知。只有心快乐了,它通向诸感官的道路才会畅通,快乐的感觉才会涌上心头。用书中的话说就是:“心必乐,然后耳目鼻口有以欲之”(《仲夏纪·适音》)。
那么,心如何才是快乐?是平和。“故乐之务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适。夫乐有适,心亦有适。”使心平和是获得快乐的关键,而使心平和的关键又在于做事适度。快乐要适度,心的使用也要适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恶,“欲寿而恶夭,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欲逸而恶劳。四欲得,四恶除,则心适矣。”求得所欲,驱除所恶,心就会得到快乐。但这种快乐不是欲的放纵,而是通过遵循事物的规律获得,因而是合理适度的。“四欲之得也,在于胜理。胜理以治身,则生全以(矣);生全则寿长矣。胜理以治国,则法立;法立则天下服矣。故适心之务在于胜理”(《仲夏纪·适音》)。使心适中的关键在于遵循事物之理,或者说,使自己的心同事物之理相吻合。心与理相合,则会发生感应,而这就是快乐的来源。
与心的适中相呼应,在音乐上,就是对“适音”的提倡。何谓“适音”?理论上不难把握,适音就是“适中之音”。他说:“夫音亦有适:太巨则志荡,以荡听巨则耳不容,不容则横塞,横塞则振;太小则志嫌,以嫌听小则耳不充,不充则不詹,不詹则窕;太清则志危,以危听清则耳溪极,溪极则不鉴,不鉴则竭;太浊则志下,以下听浊则耳不收,不收则不抟,不抟则怒。故太巨、太小、太清、太浊,皆非适也。”“巨”和“小”是指音量,“清”和“浊”是音高,音量过大过小,音域过高过低都非“适”,故都不合要求。这是从音乐形态讲“适”。要想“音适”,就要取“衷”,即折衷。“何谓适?衷,音之适也。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小大轻重之衷也。……衷也者,适也”(《仲夏纪·适音》)。“衷”即“中”,就是适中、节制、平和。遵循“中”的原则,音乐就会“适”。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一定要是“衷”,一定要是“适音”?难道仅仅就是因为“太巨”则“耳不容”,“太小”则“耳不充”,或者“太清”则“耳溪极”,“太浊”则“耳不收”?这当然是一个方面的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与他的“感应”思想有关。前面说过,心只有在平和之时才是快乐的,只有平和才能够感受到感官所提供的快乐。心的平和状态就是“衷”和“适”的状态。听乐之心是“适”,那么,音乐要想得到听乐者心灵的感应,就必须与之相应,也是“适”的。他说:“以适听适则和矣。”这两个“适”,一个是心的,一个是音的。两者“相类”,才会发生感应,出现审美活动。
与“适音”相反的是“侈乐”。“侈乐”的特点就是不“衷”,就是“以巨为美”。“夏桀、殷纣作为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音,以巨为美,以众为观。”这种追求极端的过分行径,总是同特定的政治状态相吻合的。“宋之衰也,作为千锺;齐之衰也,作为大吕;楚之衰也,作为巫音”(《侈乐》)。《吕氏春秋》特别强调音乐与政治的紧密联系,他说“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也”(《仲夏纪·适音》)。“流辟、越、慆滥之音出,则滔荡之气、邪慢之心感矣;感则百奸众辟从此产矣”(《季夏纪·音初》)。说明这种联系不但非常紧密,而且严格地对应,其对应中的通联机制,就是“感”。《适音》说:“凡音乐,通乎政而风乎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这里的“通”,就是以感应而通,因此是双向的,音乐能够感应政治,政治也能够感应音乐,彼此是协同关系。“适音”和“侈乐”能够各自引发不同的心理感应,产生不同的社会效应,所以才引起古人的特别重视。
在《吕氏春秋》的思想体系中,“欲”是一个重要范畴,虽然不是理论的核心、思想的本原,但却是生命活动、文化创造的最原始的动力因素。他说:“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源自人的本性,故而也是自然(天)的一部分。是自然,就必须肯定。所以他说:如“耳不乐声,目不乐色,口不甘味,与死无择。”关键在于对欲的满足是否有节制:“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这里的“情”不是情感之“情”,而是情理之“情”,本性之“情”。“行其情”就是遵循其“理”,符合其法度。他说:“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仲春纪·情欲》)耳、目、口之欲,是人的本性,所有人都有,圣人、常人乃至恶人均无不同。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圣人能够“得其情”,即按照其“理”来获得满足,而其他人很难完全做到。欲的满足只要遵循其理,就会有“适”。“适”是养“欲”的过程中调理出来的。《侈乐》云:“有情性则必有性养矣。寒、温、劳、逸、饥、饱,此六者非适也。凡养也者,瞻非适而以之适者也。”养就是将非适变成适,以适驱除非适。此适,即适中,不过分,有节制。“能以久处其适,则生长矣。生也者,其身固静,感而后知,或使之也。”如果“遂而不返,制乎嗜欲;制乎嗜欲无穷,则必失其天矣。”欲之“适”与音之“适”,其理相通,其效亦相类,两者之间亦互相感应。“适音”之“适”之所以重要,于此亦可见出。
三、《淮南子》:以审美为中心的音乐感应论
《淮南子》⑬本文所引《淮南子》均见何宁《淮南子集释》(上、中、下),中华书局1998年版。为节省篇幅,所引文字只在文中夹注章节标题,不再另列注释。的音乐思想散见于各卷之中,内容丰富,有新意,有深度,其论乐文字中亦表现出浓厚的“感应”思想。如果说,《吕氏春秋》主要将“感应论”运用到作乐方面,那么《淮南子》则主要立足于音乐的审美。《淮南子》认识到音乐具有特殊的感应能力,认识到音乐对外界事物,尤其是对人的巨大影响力。“夫荣启期一弹,而孔子三日乐,感于和;邹忌一徽,而威王终夕悲,感于忧。动诸琴瑟,形诸音声,而能使人为之哀乐。县法设赏而不能移风易俗者,其诚心弗施也。”设法悬赏不能移风易俗,而音乐能。音乐之所以能,就在于它能直通人心,无法抗拒。“宁戚商歌车下,桓公喟然而寤,至精入人深矣。故曰:乐听其音,则知其俗;见其俗,则知其化”(《主术》)。通过音乐可以感知心志,察知风俗。又说:“歌哭,众人之所能为也,一发声,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缪称》)。“夫歌者,乐之征也;哭者,悲之效也。愤于中则应于外,故在所以感”(《修务》)。“夫声色五味,远国珍怪,瑰异奇物,足以变心易志,摇荡精神,感动血气者,不可胜计也”(《本经》)。这种感知、察知的渠道,就是感应。音乐审美没有物理通道传输,靠的就是“同类相动”的感应。
那么,如何才能使音乐有效地引发人的感应(即审美)活动?《淮南子》抓住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君形者”。人是有精神的,因此,要想使人产生精神的感应,音乐就必须也有相应的精神。这精神,就是“君形者”。
1.“君形者”的基本内涵
“君形者”是《淮南子》的一个独特概念,就是指“神”,与形体相对的精神。形神的区分源自庄子,他从道与器的关系把人也分为神与形,认为神贵而形轻,并将其作为养生论的基本原则,养生的核心是养神,而非养形。这个思想被《淮南子》继承下来,并加以扩展,形成艺术论意义上的形神论。而在谈论艺术中的形神问题时,他自己又新创了一个概念来表示“神”,就是“君形者”。《淮南子》以“君形者”标示艺术中的“神”,有以下三则:其一,“昔雍门子以哭见于孟尝君,已而陈辞通意,抚心发声,孟尝君为之增欷呜唈,流涕狼戾不可止。精神形于内,而外谕哀于人心,此不传之道。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为人笑”(《览冥》)。其二,“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说山》)。其三,“使但(倡)吹竽,使工厌窍,虽中节而不可听,无其君形者也。……异音者不可听以一律,异形者不可合于一体”(《说林》)。这三段话用的都是“君形者”,也都是讲艺术的,其中两条讲音乐,一条讲绘画。它们主要表达了三层意思。
第一,要有真实的情感体验,即所谓“精神形于内”,也就是要有“君形者”主宰你的精神世界。第一则是以雍门周以琴见孟尝君的故事为例的,是说音乐的接受者要想被音乐打动,就必须先有过与音乐相似的情感体验。孟尝君时值位高权重,踌躇满志,根本谈不上悲忧,故无法让他垂涕。只有当他意识到已经危机重重,朝不保夕,内心充满悲忧时,才能够以音乐使其垂泪。用《淮南子》的话说,就是“精神形于内,而外谕哀于人心”,这“精神”,就是“君形者”。它说明,无论是弹琴人,还是听琴人,都必须有此“君形者”,才能够发生真正的审美感应。第二则的“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悦),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也是因为缺了“君形者”。缺了“君形者”,剩下的就只能是空洞的、没有内涵、没有生命力的“形”。
第二,其精神要能够贯通始终。这主要在第三则中得到体现。假设让一个乐工吹竽,让另一乐工按孔(“厌窍”),“虽中节而不可听”。“中节”是指节奏一致,符合音乐的要求,也是“不可听”的。为什么?因为是两个人在操作一件乐器。两个人的“形”即操作技巧可以通过训练趋于一致,但两个人的“神”即“君形者”却无法完全相同。无法完全相同,即意味着吹奏时乐曲的“神”是分裂的,即没有一个统一的灵魂一以贯之。而没有一以贯之的灵魂,作品就不是有机的,也就不可能有生命力和感染力。其中的道理,就是所谓“异音者不可听以一律,异形者不可合于一体。”这则故事说明,音乐不仅需要“君形者”,而且要求这“君形者”必须是一个完整的、一以贯之的、生动的有机整体。⑭这个思想应该是受《韩非子》的影响,《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云:“田连、成窍,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连鼓上,成窍擫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共”即“多”“杂”“非一”,即缺乏某种一以贯之的东西。有机体中的“神”应该是“无所不充”“无所不在”,应该渗透到每一个“毫末”之端。这里强调的就是神的这种完整性、统一性和贯通性。
第三,“神”在这里所起的是“支配”的作用。这三则故事的文本中,值得注意的是,用以表示“神”的概念的都是“君形者”。在《淮南子》中,直接用“神”或“精神”来自指的地方很多。早在庄子那里,“神”和“精神”一词即已经常使用,到《淮南子》使用就更加频繁,如“保其精神,偃其智故”“形神气志,各居其宜”“志与心变,神与形化”等。但这里偏偏不用现成的“神”字,而另行杜撰出一个“君形者”来代替它。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三个字能够直接体现“神”在与“形”的关系当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独特功能——“君”,亦即统治、支配的地位与功能。而“神”与“形”相举,就其字面意思来说,它只表示两者的相对,并不自然地含有“神”对“形”的支配性。而这个支配性,才是《淮南子》所要着力强调的东西。
2.“君形者”的特点
音乐必须有“君形者”亦即“神”的统领,才能获得生命。那么,如何才能统领音乐,统领众形?《淮南子》的回答是:要统领形体就要能够超越于形体,要统领声音,就要有超越声音的东西。“君形者”即具有超越性的品格。他说:“鼓不与于五音,而为五音主;水不与于五味,而为五味调;将军不与于五官之事,而为五官督。”在中国古代乐队中,鼓是指挥。因鼓没有精确的音高,不属于五音。但也正因其与五音“不与”,所以才能统领五音。就好像水不属于五味而能调和五味,将军不属于五官而能统领五官一样。“故能调五音者,不与五音者也;能调五味者,不与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兵略》)。他还以琴和车辐为例,说的也是这个道理:“琴不鸣,而二十五弦各以其声应;轴不运,而三十辐各以其力旋。弦有缓急小大,然后成曲;车有劳逸动静,而后能致远。”这里的琴是指琴体,琴体无声,但张于其上的弦则能“缓急大小”,悠然成曲。轴心不动,但车却因此而能“劳逸动静”,悠然致远。他接着总结说:“使有声者,乃无声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动者也。故上下异道则治,同道则乱”(《泰族》)。要统领什么,你就必须有超越于它们的要素和品格。你若与其完全相同,就不能获得统领的功能,其群就会大乱。
明白这个道理,《淮南子》中下面的两段话就好理解了。这两段话都是在讲了“叩宫而宫应,弹角而角动,此同音之相应也”之类表示同类相感的意思之后出现的,《览冥》接着说:“夫有改调一弦,其于五音无所比,鼓之而二十五弦皆应,此未始异于声,而音之君已形也。”《齐俗》也说:“其于五音无所比,而二十五弦皆应,此不传之道也。”这两段话,乍一看,与我们所知的常识不相符合。音乐常识告诉我们,只有相同频率的两根弦之间才会产生感应共振,不同频率的弦间是不会共振的,而这里所强调的恰恰是不同频率的弦之间的“皆应”。瑟是五声定弦,所谓“于五音无所比”,就是指此弦与另一瑟的二十五弦频率皆不相同,但却能够使它们“皆应”。为什么?其实也就在它们之间的更深层次的相类,即在同是弦、且同是弦的振动的意义上,它们是相同的,故而仍然符合“同类相动”的基本原理。不同点只在,前者是从感性形态的层面讲其相类,而后者则是在超越感性的层面,因而也可以说是“道”的层面或接近“道”的层面上的相类,所以才说这是“不传之道”。这种超越感性形态、具有道的特点的东西,与“神”相似,它才是统领着形的“音之君”。所以,《齐俗》紧接着说:“故萧条者,形之君;而寂寞者,音之主也。”萧条、寂寞,正是“神”之所在。
“君形者”的超越性是为了获得对形的支配和统领的功能,故而它和“形”亦即器、技的关系是支配与被支配、统领与被统领的关系,在音乐上,它就是“声与所以声”“巧与所以巧”“悲与所以悲”的关系。《原道》说:“若夫规矩钩绳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无弦,虽师文不能以成曲;徒弦,则不能悲。故弦,悲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悲也”。(《齐俗》)“规矩钩绳”(即“技”)只是“巧”的形态,不是“巧”本身(即“所以巧”),“弦”只是“悲”的载体,不是“悲”本身(即“所以悲”)。“所以巧”“所以悲”是“君形者”,“技”和“弦”只是“形”。前者总是通过后者才能实现出来,但只有后者才是前者的直接支配者。
“君形者”虽然处于支配的地位,但它自身不能独立存在,而总是通过特定的“形”才得以呈现,才真正实现自己。在《淮南子》看来,音乐的本质在于它所内涵的生命感觉,在于它所特有的传神旨趣,但这种生命感觉和传神旨趣全部要通过特定的技术才能表现出来。而技术是需要日积月累的训练,即“服习积贯”,“今夫盲者目不能别昼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抚弦,参弹复徽,攫援摽拂,手若蔑蒙,不失一弦。使未尝鼓瑟者,虽有离朱之明,攫掇之捷,犹不能屈伸其指。何则?服习积贯之所致”(《修务》)。古代许多杰出的琴师都是盲人,但其弹琴却能动天地,感鬼神;而那些没有弹过琴的人,虽然他们视力超人、手指灵活,却无法成曲。不是他们没有“神”。而是此“神”没有能够在琴的技术与音响中得到展示,因而也就不存在以琴为载体的“神”,不存在支配“琴”与“音”的那个“君形者”。
“君形者”需要特定的“形”才能真正存在,但这个“形”必须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生命体。“行一棋,不足以见智;弹一弦,不足以见悲”(《说林》)。只走一步棋,只弹一个音,其形远未完成,故其神也就无法体现,所以不能见其“智”与“悲”。只有在一个相对完整的棋路上或音调中,“君形者”才会现身。不仅如此,“君形者”的呈现,还必须有较为丰富的细节来成就。《要略》说:“今《易》之《乾》《坤》,足以穷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⑮这里是以伏羲演六十四卦的,在其他文献(如《史记》)中,一般认为是伏羲作八卦,周文王将其推演为六十四卦。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测淑清之道,而捃逐万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数,不过宫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细大驾和,而后可以成曲。”传说中,伏羲作八卦,用以整理天下万事万物,文王觉其较为简单,故又推演成六十四卦,所涉方面更为丰富详尽,更能解释多样的事物现象,故而也就更为适用。同样的道理,在音乐中,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宫、商、角、徵、羽五个音,而总是要作更大幅度和更加细微的变化,并加以必要的应和(即“细大驾和”),才能将乐曲中的“神”亦即“所以悲”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缺少完整丰满细腻的“形”,“君形者”也难以丰富、生动、有力。
3.“君形者”的美学功能
《淮南子》在论及艺术、音乐时之所以特别强调“君形者”即“神”,除了它在形神关系中居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君形者”能够为艺术的审美感应提供充足的能量和应和的契机。一方面,就艺术的创造者说,只有在其创造过程中充分展示其内在精神即“君形者”,其作品才能强烈、深入、持久地打动别人,感染别人。另一方面,就艺术的接受者说,人们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也应具备与作品相通的精神底蕴亦即“君形者”,才能够完满地感知音乐的魅力,发生审美感应活动。这后一方面,前引雍门周的故事即能说明其道理,而前一方面,《淮南子》也有相关的论述。在《览冥》中记有师旷和庶女两则音乐故事:“昔者,师旷奏白雪之音,而神物为之下降,风雨暴至。平公癃病,晋国赤地。庶女叫天,雷电下击,景公台陨,支体伤折,海水大出。”这两则故事在先秦文献中多有记载,在汉代也十分流行。它们是否为历史事实,在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此所反映出来的一种观念,这个观念是历史的真实。那么,这个观念的基础是什么?就是“感应”,它是建立在感应的基础之上:人的精神可以与自然万物相通,可以互相激发,互相作用。所以他接着评论说:“夫瞽师、庶女,位贱尚葈,权轻飞羽,然而专精厉意,委务积神,上通九天,激厉至精(《览冥》)”。“专精厉意,委务积神”,就是对自己精神能量的不断积累,不断提升,使之达到某种饱和、充溢、强盛的地步,这样才能“上通九天,激厉至精”,使天地神灵产生感知而响应。没有这种至诚至强的内在精神,就不可能产生如此强烈的外部效应。这个关于音乐与天地神灵之间的关系的故事,无疑带有夸张的成分,使它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但其道理的表达则是清晰明白的。有了“君形者”,其音乐才能够“比于律而和于人心”,产生强烈的感染作用。
明乎此,则《淮南子》在论乐时之特别强调“君形者”,且特别喜欢使用“君形者”这个词,就不难理解了。
四、《乐记》:以功能为中心的音乐感应论
《乐记》⑯《乐记》文本较多,本文所据为蔡仲德校注本,载《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上、下),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版。为节省篇幅,本文所引文字只在文中夹注章标题,不再另列注释。是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篇,其作者和成书年代有不同的说法。最早记录这一信息的是《汉书·艺文志》,其中《六艺略·乐类》书目后有一段说明文字,谓“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河间献王即刘德,是汉景帝刘启次子,武帝刘彻异母兄,封河间王,后谥曰“献”。这是说,《乐记》是刘德同其门人在搜集先秦儒家论乐文献基础上撰写而成,时间是汉武帝时代。另一说法最早见于《隋书·音乐志》,认为“《乐记》取《公孙尼子》”。公孙尼子是战国初期人(一说为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如作者是公孙尼子,则该书的成书年代将提前到战国初。此后,关于《乐记》作者与成书年代的两种观点一直在争论之中,并延续到当代。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主张是公孙尼子,成书于战国初。以蔡仲德为代表的主张是刘德,成书于汉武帝时代。笔者认真阅读了两种观点的讨论文章,并结合《乐记》的文本、思想及与先秦相关文献的关系,认为“刘德说”较为合理。⑰关于“刘德说”的具体论证,参阅蔡仲德《〈乐记〉作者辨证》《〈乐记〉作者再辨证》《〈乐记〉作者再再辩证》等论文,见《音乐之道的探求——论中国音乐美学史及其他》,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年版。《乐记》成书既然也在西汉前期,与《淮南子》同时,故而也突出地体现了以“感应”论乐的基本理路。不同处只是,《吕氏春秋》是以作乐为中心运用感应原理论乐,《淮南子》是以审美为中心运用感应原理论乐,而《乐记》则是以功能为中心运用感应原理论乐。
音乐具有非凡的功能,这是先秦论乐文献中常常能够看到的一个特别现象,诸如师旷奏《清角》而令晋国大旱,匏巴鼓琴而令鸟舞鱼跃,舜歌《南风》而天下大治,等等。到《乐记》时,功能论则成为它的突出主题,其对音乐功能的论述也得到更为充分的展开。整个《乐记》,论述音乐功能的文字和段落,占了全书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乐记》中的功能论涉及的内容很多,大致可以归纳为认知功能、道德功能、政治功能、群体功能和生物功能等五大类型。但这并不意味着《乐记》全文只是单一地涉及功能问题,而不及其他。首先,我们知道,《乐记》的开篇就是阐述“人心之感于物”的音乐本体论,在其他地方还不时出现音乐创作论、音乐形态论、音乐审美论等文字和段落。但是,所有这些非功能论的论述,最后都导向功能的阐述,都是为功能论服务的。例如,《乐本篇》中对本体论的表述:“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说音乐源于人心之动,而人心之动又与行为相关,故而音乐与政治紧密关联:“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再如审美论的讨论最终也导向了功能论,《乐化篇》云:“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故人不耐无乐,乐不耐无形,形而不为道不耐无乱。”认为音乐植根于人的寻求快乐的本性,人不能没有快乐,快乐不能没有形式,形式如果不加引导,就会泛滥无序。“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先王所做的工作,就是在形式上加以规范。表现情感而不放纵(“流”),歌词合范而不死板(“息”),音乐形式的组织要能够“感动人之善心”,使放纵之心、偏邪之气不得入内。最后还是归到政治道德功能上了。由此可见,在《乐记》全部文本中,功能论是它突出的主题,其他方面的论述都是为功能论服务,在功能论的框架内得到解释的,它的“感应”思维也是在功能论的意义上展开的。
但是,《乐记》中的“感应”不仅仅是本体论或审美论中的重要连接机制,而且是音乐运行中各个环节之间普遍存在的连接机制。就是说,《乐记》的音乐美学思想,是通过“感应”才得以成为一个有机系统的。这个系统,我们可以把它粗略地划分为四个环节。
1.不同的“物感”产生不同的“心动”
乐既然由心所生,是心动的产物,那么心动是如何发生,又是如何产生差异的?在《乐记》中,这个问题是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的。一是从“感于物”的方面,一是从“感于心”的方面。
《乐记》开篇《乐本篇》开头第一段关于音乐本体论的话,就是从“感于物”的方面立论的:“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这里所讲是以人心感于物而动,然后发而为声,再由声而音、由音而乐的形成过程,突出的是由物所感而至于产生音乐的逻辑理路。这里的“物”不仅仅是指自然界的事物,同时也包括社会和精神领域的一切客观存在的现象。由于音乐产生的终极根源是“感于物”,而这样的物又是无穷无尽、多种多样的,因此,由它而引起的心动也必然是丰富多样。不同的物态会形成不同的心态,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音乐。“土敝则草木不长,水烦则鱼鳖不大,气衰则生物不遂,世乱则礼慝而乐淫”(《乐言篇》)。土有肥瘠,水有静躁,气有盛衰,它们都直接影响着生物的生存状态。同样,社会亦有治乱,也会影响到人的心理;再由不同的心理,便会产生不同的音乐。因此,以什么样的“物”相感是十分重要的,需要我们谨慎对待:“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然后发以声音,而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乐象篇》)之所以要警惕“奸声乱色”“淫乐慝礼”和“惰慢邪辟之气”,就是因为相感之“物”对于人心之动有着直接的影响。
由物之感到心之动,不仅仅在于物的方面,同时也取决于心的方面。这个意思是在《乐本篇》的第二小段得到阐述的。它在重申了“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之后,便从“心”的方面述其所感的意义,说明以不同的心感之,就会有不同的心动状态。“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乐本篇》)这里的“其声”讲的是音乐,实际上也就是人的心动状态。以哀、乐、喜、怒、敬、爱之心感之,则会分别产生“噍以杀”“啴以缓”“发以散”“粗以厉”“直以廉”“和以柔”的不同心动状态;再以此不同的心动状态,便会产生不同的音乐类型。所以它接着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智)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乐本篇》)“人之好恶”就是用以感物的“心”,这个“心”不能“无节”,“无节”,人就会被物所化(“人化物”)。只有有“节”,即有主导性的鉴别和选择,才能使所感之“心动”进入良性状态。这也就是《乐化篇》所谓“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的意思所在。
2.不同的“心动”产生不同的音乐
音乐是“心动”的产物,所以,不同的“心动”自然会产生不同的音乐。《乐本篇》云:“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这段文字中,关于“治世之音”以后的三句如何理解,是可以有不同看法的。一种理解是从音乐到现实,是讲功能的。另一种是从现实到音乐,是讲生成的。乍一看,前一种好像更顺畅;但若结合前面的“凡音者”一句,则应该是后一种意思更合理。因为这一句讲的正是音乐生成问题,是由现实到音乐的逻辑过程。实际上,这两种理解都能够成立,也都符合《乐记》的基本思想。这里我们先取后一种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治世之音安以乐”与“其政和”等句之间,应该有个省略了的“是因为”之类表示原因的词语。“政和”“政乖”“民困”是音乐形成前的现实,人们感于它,发生心动,便产生“安以乐”“怨以怒”“哀以思”的“音”。
这个思想在《乐记》中有多处表述。前文所引《乐本篇》中“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一段,也是比较典型的由心到乐的生成论文字。另如《乐象篇》中关于“德音”的论述,也体现了这样的意思:“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乐象篇》)“德音”就是德者之心所发之音。德是人的本性向音乐发生过程的开端,其中间环节,或者说,其载体就是“心”。
3.不同的音乐导致不同的心理和行为
不同的音乐导致不同的心理和行为,属于音乐功能论的范畴。这个问题是《乐记》的中心论题,其他方面的问题都是在讨论该问题的基础上展开的。因为是它的中心论题,故所论非常多。如《乐言篇》云:“是故志(纤)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不同的音乐导致不同的心理和行为,在音乐和心理、行为之间便存在着相似性。《魏文侯篇》则将各种乐器的音响特点同人的心理行为特点相联系,描述出两两的相应关系:“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鼙之声灌,灌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对每一个对应关系之间,都详细描述出两者之间的诸多环节。如钟声与“思武臣”之间,就有“铿、立号、立横、立武”四个环节;鼓鼙与“思将帅之臣”之间,则有“灌、立动、进众”三个环节。中间的几个环节都是起到从音乐到心理行为之间的过渡作用,是对其机制的描述。《乐化篇》还对《雅》《颂》的音乐形式与心理行为之间的对应关系作了具体分析:“故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伸,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雅》《颂》之声比较舒展和缓,与志意的宽广大气相通;俯仰、屈伸的操练与容貌姿态庄重典雅相通,队列行进的训练亦与众人的步调一致相通。所以它总结说:“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正是因为音乐形态与人的心理行为之间的同构,才使得古人特别重视调节心理和行为的功能。“故人不耐无乐,乐不耐无形,形而不为道不耐无乱。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乐化篇》)。人的本性需要快乐,有快乐就不能没有外部表现,外部表现如果不加引导会导致混乱。先王之所以制礼乐,目的就是制作出和谐协调的音乐形式,来对人的心理行为加以引导和调节。有了音乐的作用,人的这种良好的心理行为就会更加深入和持久。“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乐化篇》)。
4.不同的心理行为形成不同的社会状况
《乐记》认为,音乐能够影响人的心理和行为,而影响人的心理行为的直接结果,便是对社会状况、道德政治的影响。《乐本篇》云:“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这段文字前面我们取的是由现实到音乐的生成论意义上的理解,现在我们可以再从由音乐到现实的功能论意义上进行理解,即“其政和”“其政乖”“其民困”,都是前面各自音乐形态的产物,是它们作用于现实的结果。《乐化篇》还论述了音乐作用于社会的具体方法及其效果:“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音乐在国家、宗族、家庭之中,均有其协调、和谐与增强凝聚力的作用。正因为此,《乐记》才说:“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乐象篇》)又说“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乐本篇》)。“审乐”之所以能够“知政”,实施乐教之所以能够“移风易俗”,都是因为从物到心,又从心到物各个环节间的相感、相应和相通,亦即“倡和有应”“以类相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乐记》中的这种由物到心、又由心到物的过程,并非单向线性的过程,而是一个“物→心→乐”和“乐→心→物”双向互动、不断循环的过程。它是由物感使人心动,心动产生音乐,又由音乐影响心理,心理再作用于物即现实这样一个无限反复的过程。而支撑这种循环的,就是“感应”,即所谓“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乐象篇》)。它的具体机制和环节,我们可以下面的一段话为例做一分析。这段话也在《乐象篇》:“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这里的“奸声”和“正声”是指原有的音乐,“逆气”和“顺气”则是由这两种音乐分别通过“感人”而激发出来的心理、风俗、政治状况,而这两种不同的心理、风俗、政治状况又反过来通过对心的影响,强化了“淫乐”与“和乐”的再生产,形成两种不同的动态循环。其中,由“奸声”到“逆气”再到“淫乐”的循环是恶性循环,由“正声”到“顺气”再到“和乐”的循环则是良性循环。如何将恶性循环转变为良性循环,便是儒家乐教的主要课题。其方法无非有二,一是通过礼的教化调整人的行为,一是通过乐的感应协调人的心理。但实质只有一个,都是从人的方面入手,在人自身方面做工作,即“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意思就是,必须回到人性的根本,使自己的心进入平和状态。这样,就能够将负面的因素排除在外,即“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这就是儒家常说的“正心”的工作。有了这样的工作,“然后发以声音,而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乐象篇》)。这样,就摆脱了原有模式中再循环到“淫乐”的命运,转而进入“和乐”创作的轨道。“和乐”产生后,又会遵循“感应”的原理作用于人心和行为,再进而作用于风俗政治的改良。而风俗政治改良后,又会以其“正声”而引发“顺气”,再由“顺气”而创作“和乐”,从而进入儒家所理想的良性循环。
结 语
那么,如何认识并评价古代的音乐感应论?“感应”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它有什么样的现实基础,又是遵循什么样的机制?在古代的感应论中,只是讲到“以类相动”,但同类的事物是如何“相动”的?其“相动”又以何种方式进行?如此等等。这些问题在古代理论中并未得到清晰的表述,因而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好在现代科学的研究已经进入这一领域,其成果可以作为参考,全息理论就是其中的一种。⑱还有量子理论也涉及这个问题,如“量子纠缠”“超距作用”等,也与“感应”有相似之处。如何用量子理论解释“感应”现象,也是一个很有魅力的课题。
全息理论是关于事物间普遍存在的全息关系的性质和规律的学说。它认为宇宙是一个全息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各个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存在着全息对应关系。任何一个部分都浓缩着整体的信息,而任何一个整体,也只是部分信息的放大。在宇宙整体中,凡相互对应的部位较之非对应的部位在物质、结构、能量、信息、精神与功能等要素上相似程度较大,因而易于发生感应。全息理论诞生于全息照相,此后又在宇宙学和生物学中得到发展。全息有一些重要的特点:一是它发生在一个有机的整体内部。二是传播方式没有通道,是泛传播。三是传播的机制是相似性,与相似度成正比例关系。四是以识别响应的方式接受传播。中国古代感应的机理就是全息中的传播与响应。就这个意义来说,它是客观存在的事物现象,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全息理论自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它只是反映了世界事物联系的一个侧面,而非全部。其次,它的机制只是相似程度较大,故其联系不具有必然性。再次,全息、感应有一定的适用域,不在这个域内其感应就不会出现。这又提醒我们在运用时一定要谨慎,否则便会落入牵强附会,得出夸大的甚至错误的结论。古代感应论中这个问题之所以比较常见,原因即在此。⑲这方面的内容笔者已在另一篇文章中论及,请参阅《中国古代思想范式中的全息机制——罗艺峰〈中国音乐思想史五讲〉中范式研究的一种解读》,《交响》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