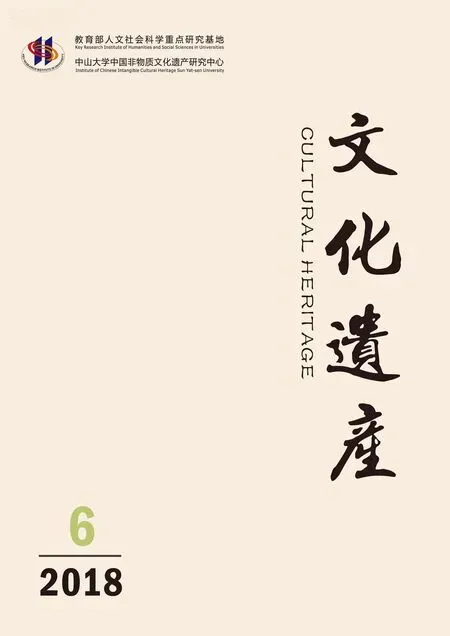行业神做为地方保护神:福建作场戏中所见“戏神群”探析
林鹤宜
前 言
自2009年福建省大田县朱坂村和永安市槐南村 “作场戏”*朱坂村的作场戏称为“丰场”,剧目抄本称《丰场总纲》。其旧抄本多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毁,现仅存民国庚午年(19年,1930)廖法昌抄本。槐南作场戏称为“人场”“着场”,其剧目抄本版本保存较多,有《人场全本》《人场总纲》《场本全部》等名称。但两地演出本中都有“作场”字眼,如《丰场总纲》《阔公请神》有“做场专是老人打闹”之语,《场本全部》《阔公口诀》有“槐林作场”之语,故学者总称之为“作场戏”。为讨论的方便,本文概以“作场戏”称之。本文讨论根据叶明生校订,《丰场总纲》廖法昌民国十九年抄本,及叶明生校订,《场本全部》黄大河民国二十五年抄本,皆收在叶明生编《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被发现以来,以福建学者群为主的研究团队已就各个面向陆续发表相当完整的研究成果。作场戏做为地方祈福消灾的社戏,包含高度信仰仪式成分,同时,在表演元素和形式各方面,保留不少宋代南方杂剧的形态,都已得到充分的论述,并获得学界的认可。
2018年2月新年期间,笔者应福建省艺术研究院、永安市政府和大田县政府之邀,参与“福建杂剧作场戏学术考察活动”。亲临朱坂村和槐南村观察记录作场戏,首先感受到的是强烈的“乡人傩”气息,即使它们被包覆在“演剧”的形式中,这样的气息仍然浓烈。与其说它是一场戏剧表演,不如说是一场科仪的执行。而更引起笔者关注的是作场戏中出现的“戏神群”。戏神做为戏剧业的“行业保护神”,如何又是地方保护神?其信仰的内在思维为何?这是张大阔公信仰产生的独特现象,又或者有其他脉络可依循?本文以既有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笔者所见、所思,首先援引地方传说和相关文献,论述宗族保护神张大阔兼具的“戏神”神格,及其可能的背景;接着论证朱坂、槐南两地作场戏中出现的“戏神群”,体现的正是在大腔戏和大腔傀儡戏流传脉络下的“子弟扮仙戏”本质;最后从张大阔公“傩神”与“戏神”交叠的身影,探究作场戏“以祭为戏/以戏为祭”、“戏”与“傩”交融的特质和渊源。
一、做为“戏神”的张大阔公
作场戏又称“阔公戏”,是一种依附于“阔公信仰”的宗族祭祀演剧。“阔公信仰”流传于福建大田县、永安市一带,“朱坂村”和“槐南村”因为保留了作场戏而受到关注。两村相距仅20公里,原本同属尤溪县,至明代景泰、嘉靖年间,才分别划归大田县和永安市。*张帆:《福建槐南村“人场”演剧与祭祀仪式研究》,《戏曲研究》第88辑,第77页。据槐南村阔公庙“大新堂”现任庙祝黄圣干表示,阔公信仰不限于本村,附近百里信众前往“大新堂”祈福者不在少数。*罗金满:《大田、永安宗族做场戏遗存探述》,《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福州: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内部资料2018年,第161页。(原收在王评章、杨榕主编《2012福建艺术研究论集》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3年)
朱坂村是一个余、廖二姓村。作场戏原本十年一祭,逢“辛”演出, 1991年改为五年一祭。*朱坂村的作场戏在1949后曾停演,1991年正式恢复演出。参见张帆,第141页。演出时间旧例从正月初一持续至清明,现于元宵结束。*王晓珊:《福建大田、永安作场戏表演形态及其艺术特征》,《戏曲研究》第88辑,第1页。演出时,采取“一出丰场一出戏”的方式,子弟演作场戏一出,接戏班演戏一出,两者交替。由余、廖二姓宗族组成理事会,负责作场之年的种种活动及普通年份的祭祀活动。*叶明生:《福建宋杂剧的发现及其戏剧形态考探》,《文化遗产》2013年第1期。张帆《福建朱坂村“作场”演剧仪式调查》,《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142、151页。演出共23个人物角色,除“巫婆”一角由村中“身分卑贱者”担任,其余22个角色皆由余、廖两姓平均分配、轮流,其中有16个角色以世袭的制度来传承,他姓或别户都不得承继。另有“啰哩队”12人,也由余、廖二姓各派出6人担任。*王晓珊:《福建大田、永安作场戏表演形态及其艺术特征》,《戏曲研究》第88辑,第2-3页。
槐南村有黄、罗、何、陈、黎等多姓。*罗金满:《大田、永安宗族做场戏遗存探述》,《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159页。自1987年建立“大新堂”后,由黄姓六房组成理事会负责作场戏的运作,并将原本连演两年歇两年,改为年年演出。演出时间在正月十五日之前,现确定为初七和十三日。本来采取“一出丰场一出戏”,后改为演出首场和终场,首、终之间请戏班演出,前后约十天。*张帆:《福建槐南村“人场”演剧与祭祀仪式研究》,《戏曲研究》第88辑,第67-68页。演出角色共24个,全数由黄姓子弟担任。*王晓珊:《福建大田、永安作场戏表演形态及其艺术特征》,《戏曲研究》第88辑,第4页。
作场戏的本质是“社祭”中的“社戏”。张大阔公做为福建大田、永安一带个别乡村的宗族保护神,如何又具备戏神神格?有关他的俗家姓名,家世、修道过程、生平事迹、神迹等,并没有较广泛的流传或文献可兹参考,但根据地方的传说、文物和文献,还是可以整理出几个线索。
(一)传说中所见的戏神张大阔公
张大阔公的地方传说不算丰富,以学者们既有的采辑成果,结合阔公庙文物和两地作场戏演出文本,可以得到以下要点。
1.张大阔公是来自江西青州的地方保护神。
根据朱坂村阔公庙香火牌位所题“祀奉青州祖殿张大阔公之神位,左边判官,右边小鬼”21字。人们认为张大阔公是来自“江西青州”*其地不详。江西查无地方名青州。从下引永安黄景山村“万福堂“大腔傀儡戏班《请师父文》和《谢愿请神文》中,“吉州王二”或作“青州王二”推断,则“青州”有可能是“吉州”之误写。吉州即今江西吉安市,在江西中部。的神祇。朱坂村《丰场总纲》第三出《阔公请神》中,阔公自言:“老人姓董名圣朝,青州人氏,表字小大伯,号为张大阔公”*叶明生校订《丰场总纲(廖法昌民国十九年抄本)》,《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399页。,重复了这个讯息。此外,朱坂村世代相沿一个传说:“宋代朝廷有个太监到此负责开采铁矿,带着从江西青州府请来的保护神阔公,从此阔公信仰便在村里流传。”*罗金满:《大田、永安宗族做场戏遗存探述》,《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158页。
青州究竟指江西何处?无从查考。可以确定的是闽中西部丘陵和赣东山区连成一片,自古就有许多江西人士迁徏移居,从而带来原地的生活文化。三明市一带流行的大腔戏和四平戏都来自江西弋阳腔,可做例证。
2.张大阔公是戏神田、窦、郭三位戏神的化身/代言人。戏神有三身,张大阔公亦有三身。
根据罗金满采辑槐南村的传说:
唐代李世民时,一个名叫何广文的太尉,有一天上山打猎,碰到一只白兔,他用箭射过去,顿时变成三人,一个红脸、一个黑脸、一个白脸。何广文问其为何会变成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是从天王界下凡而来的。问其姓什么,说是田、窦、郭三位师傅,一个做把戏,一个演傀儡戏、一个是演戏的。当时他看到三人一下子没了,就赶紧跪下说,你们没说清楚,叫我怎么找你们呢?于是教了他咒语:舍人舍人,田公舍人,啰哩嗹啰哩呤,兄弟三人个个有三身,拜请杭州铁板桥头人。……接着就消失了。他看见巨树中有一窟窿,里面有个用石头做成的四四方方的香炉,就以之供奉。而到底要称什么名字,三个回答说,称其为“张大阔公三位师傅”。*罗金满:《大田、永安宗族做场戏遗存探述》,《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159-160页。
白兔变为“田、窦、郭三位师傅”,呼应了槐南村《场本全部》“请神科仪”的《请神文》中提到:“拜请玉皇敕封九州岛风火院中田、窦、郭三位师父”。*叶明生校订《场本全部(黄大河民国二十五年抄本)》,《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429页。朱坂村《丰场全本》刊载农历十二月公告演出作场戏的《做场出票》,也有“恭维 张大阔公暨田、窦、郭三位老郎师父”的字眼,*罗金满:《大田、永安宗族做场戏遗存探述》,《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163页。三位戏神要何广文太尉叫他们“张大阔公三位师傅”,意指张大阔公是三人的化身或代言人,要找他们,找到张大阔公就对了。*传说解释参见罗旌灌,《福建永安槐南张大阔公做场戏的历史与保护》对同一传说的采辑记录,文字略有不同。见《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320页。(原收在王评章、杨榕主编《福建杂剧、南戏论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3年。)
而由“白兔”化为三位戏神,解释了槐南村《场本全部》第六出《阔公口诀》阔公自言:“我东街头姓张名大阔,号“兔老公公”*槐南村《场本全部》原不分出,为了阅读和讨论的方便,由校订者叶明生加以分出。见该本注释2。叶明生校订《场本全部(黄大河民国二十五年抄本)》,《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427、456页。三位戏神消失后,在树窟窿中出现的香炉,则解释了槐南村张大阔公原本无庙、无神像,只供奉香炉。
三位师傅中有一位是演傀儡戏的,还提到“杭州铁板桥头”,这个地名也出现在槐南《场本全部》的《请神文》中,源自南宋杭州傀儡戏班的结集地苏家巷。浙、闽两省的提线傀儡戏班供奉戏神的神龛上,都写着“杭州风火院铁板桥头”的字样*叶明生:《中国傀儡戏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7年,第163页。,而后成为指称戏曲胜地的用词。
张大阔公又有“三兄弟”的说法,老大名董圣朝,即朱坂村黑脸的张大阔公;老二是槐南白脸的张大阔公,姓名与神像均失传;老三是青州红脸的张大阔公,相关资料尚未可知。*曾宪林:《福建作场戏音乐初探》,《戏曲研究》第88辑,第22页。可以看出阔公的“三兄弟”说,呼应传说中所言田、窦、郭三位师傅“兄弟三人个个有三身”。明代增补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五“风火院田元帅”条,田公元帅亦有兄弟三人的说法。(详下)
由以上传说可知,张大阔公除了是朱坂村和槐南村的宗族守护神和地方保护神,更具备“戏剧行业神”的神格,同时也是所有戏神神帮的召集人。
此外,阔公的生日在农历六月廿四日,亦值得注意,在槐南村照例举行祭祀,并请民间戏班演戏庆贺,一般演戏五天,但没有做场。*罗金满:《大田、永安宗族做场戏遗存探述》,《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161页。六月廿四日是许多戏神的生日,早在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便有“二十四日州西灌口二郎生日”的说法。*(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卷八“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观神生日”条,台北:大立出版社1980年,第47页。永安大腔傀儡戏戏神田清源生日亦同,*刘晓迎:《永安市黄景山万福堂大腔傀儡戏与还愿仪式概述》,《民俗曲艺》第135期“福建民间傀儡戏”专辑(上),台北:施合郑基金会2002年,第115页。台湾傀儡戏神田府元帅(田都元帅)的生日亦是六月廿四日。*林茂贤、江武昌、傅正玲等记录《台湾地方戏戏神传说(六)》,《民俗曲艺》第40期,台北:施合郑1986年,第138-39页。从上文提到张大阔公相关传说所见,他身上重叠着田、窦、郭三位戏神的身影,生日同在六月廿四日,也可视为一种印证。
(二)文献中所见的戏神张大阔公
从张大阔公在作场戏中的角色造型,亦能充分印证的他的戏神特质。在作场戏中他是一个村中老人,造型却有别于一般老者。朱坂村《丰场总纲》第三出《阔公请神》,阔公自吟诗:
一个头巾三角牵。彩衣着处皆精神。
分明杂剧无双手。老人场前第一人。*叶明生校订《丰场总纲(廖法昌民国十九年抄本)》,《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400页。
“彩衣”和“杂剧”都指出阔公和演剧的关系。在槐南村《场本全部》中,阔公的戏神形象就更为清晰了。第六出《阔公口诀》,阔公未上场,先有拨文(由礼生担任)念:
忽见来有一位老公公。头戴新巾。边插桃花。脸如必粉。发似慈根。身穿蓝衣。在此大摇大摆。不知何方来的一位老公公。请到台前。愿闻胜事。
阔公上场之后,自言:
插起花。引动妙女神仙。抹起粉。惹动观音菩萨。世间多少小娘。暗想我老人去入舍。嘎嘎。*叶明生校订《场本全部(黄大河民国二十五年抄本)》,《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456页。
无论是拨文或阔公,都提到“簪花”和“敷粉”,显示阔公和演戏的关系。《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五《风火院田元帅》条用“红娘粉郎”形容戏神,可以辅证。*(明)无名氏著,(清)叶德辉校订《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43页。
此外,值得参考的是永安市黄景山村“万福堂”大腔傀儡戏的艺人学艺拜师时所念的《请师父文》,以及民众谢愿做家庭醮由戏班师公所念的《谢愿请神文》,都将阔公列入戏神行列。永安黄景山村大腔傀儡戏艺人有特定的收徒仪式,其中一个重要步骤是,为了祈求学艺顺利,由班主(师父)设神堂供祭,引领徒弟叩拜戏神,默念《请师父文》。根据刘晓迎的采辑:
《请师父文》内容繁多,面面俱到,主要有:“拜且东、南、西、北、中央,甲乙、丙丁、庚辛、壬癸、戊已值符,及上界、中界、下界天仙、地仙、水仙真符共赴花台到坐;禀明××府××县××都××坊住,奉道开学、开习子弟××,供主××合家等上香拜且,今月××日学习××曲数段;有劳五方值符使者拜请九天风火院王封田窦郭三位老郎师父、太白金星、陈平师父、李铁拐仙师、南海教主观音佛母、苏州张阔公公、杭州正生、苏州正旦、吉州王二、山东土老、泉州梅香、金花小姐、银花小娘、三百公公、四百婆婆、鸣锣打鼓仙师、招财童子、进宝七郎、顺风耳、千里眼、风火二将、梨园会上一切威灵、合台文武圣贤同降花台到坐;拜且三界神祇、本境人主、土地诸佛金仙、上至溪头下及水尾四山把界神王、扶境神将同赴花台到坐。”*刘晓迎:《永安市黄景山万福堂大腔傀儡戏与还愿仪式概述》,第116页。
所请的“梨园威灵”中,明白写着“张阔公”。此外,信众为求财、免灾、求功名等事项而许愿,若得如愿,会做家庭醮谢愿,照例演傀儡戏,由戏班师公念《谢愿请神文》。根据刘晓迎的研究:
该文内容较多,由师公在神坛前焚香祷念,需请八方值符使者到花台就座,经禀明许愿之人家后,由值符使者前往各处拜请田窦郭三大元帅、太白金仙、陈平师父、李铁拐仙师、南法教主、观音佛母、和合二仙、苏州张阔公公,杭州正生、苏州正旦、青州王二、山东兔老、泉州梅香、金花小姐、银花小娘、三百公公、四百婆婆、鸣锣打鼓仙师、招财进宝七郎、本境诸佛金仙及上至溪头、下至水口、四山把界神王、扶境神将,厅头所祀香火神明、梨园真宰和一切威灵等同时降赴花台。再祷请田窦郭三大元帅,祈保今日之搬演的金系戏文。*刘晓迎:《永安市黄景山万福堂大腔傀儡戏与还愿仪式概述》,第122页。
为谢愿演戏所请的戏神中,同样见到张阔公位列其中。从《请师父文》和《谢愿请神文》的系列戏神,可以看到永安黄景山村大腔傀儡戏有一群为数不小的“戏神群”。这一戏神群包含张阔公,且和朱坂村和槐南村作场戏所请的戏神群有诸多重叠。
二、朱板村与槐南村作场戏 中的“戏神群”主体
朱坂村作场戏共分十五出(叶明生校订本),前后上场的角色(二度出场不计)分别是:
场师、田公、阔公、判官、鬼将、金花小姐、银花小姐、正妈、副妈、招财童子、进宝郎君、王二、巫婆、道士、左右将军、左右丞相、王、太监(进宝扮)、牛将、马将、阎王、土地、回回三人。
槐南村作场戏共分十出,(叶明生校订本)依序出场的剧中角色(二度出场不计)包括:
(拨文)、太白金星、土地、田公、值符使者、伏魔关圣、驱邪赵帅、真武大帝、判官、魁星、张大阔公、郑二、左右童儿、金花小姐、银花小姐、师公,师公妻、和尚、歪嘴四嫂、童子、龙女、观音、中海龙王、东海龙王、南海龙王、西海龙王、北海龙王。
两村出场角色颇有差异,但主要角色是重叠的,包括:田公、阔公、金花小姐、银花小姐、王二(郑二)、土地、判官。而田公、阔公和金花、银花都是戏神。
田公的戏神形象在朱坂村和槐南村都很鲜明。朱坂村《丰场总纲》第二出《师父坐场》:
(场师云)忽见一位小子。头挽双髻。脸画毫光。身穿红袍。腰佩七星宝剑。不知何处小子。那处神祈(祇)。来到花棚。愿闻其说。……
(小子师父云)但小子。又小子。姓田名大熟。表字满仓。身居两召。
家住杭州。平生只好风流。雪月风花不肯休。*叶明生校订《丰场总纲(廖法昌民国十九年抄本)》,《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398页。
槐南村《场本全部》下编第二出《大熟口诀》拨文对田公的形容则是:
忽见来有一位风流子弟。头挽双髻。边插锦鸡毛。腰系黄金带。身穿红袍。手拿一把蕉芭扇。脚踹皂朝黑靴。*叶明生校订《场本全部(黄大河民国二十五年抄本)》,《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443页。
田公扮相强调“风流”二字,正是戏神本色。朱坂村田公自言“姓田名大熟,表字满仓”,凸显了“丰场”的祈福寓意;槐南村直接以“大熟口诀”标示这个段落,寓意是相同的。朱坂村由村中挑选二十岁以下,十六岁以上的余姓和廖姓的童男子轮流担任。*叶明生:《福建宋杂剧的发现及其戏剧形态考探》,《文化遗产》2013年第1期。演出当天须先至阔公庙接受场师挂讳,之后由场师前导,随阔公神舆巡村驱疫。*张帆:《福建朱坂村“作场”演剧仪式调查》,《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148页。在队伍中,田公排在场师之后,阔公之前。绕境结束回到戏棚,由场师恭请田公上台镇场,扮田公的子弟手捧木雕田公小神像,端坐戏棚正中后方,自此开始不得离座,吃饭、方便皆由专人伺候,直到演完受祭拜后退场为止。
槐南村的田公由村中九至十四岁的黄姓男孩中挑选,并增加同样由男孩扮饰的郑二*郑二为田公的兄弟,据《中国戏曲志·福建卷》,“闽北四平戏戏神”条,田公踏棚开台时,有“我的兄弟有三个,郑一郑二郑三郎”之语,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第596页。随同。演出当天需至“大新堂”装扮,之后由锣鼓前导,随同阔公神舆和四位“参神”(由礼生担任,人场戏仪式主持者)绕境,称为“迎场”。演出时由开台师迎请田公、郑二镇台,二童并坐于戏桌后,直到演出结束。*张帆:《福建槐南村“人场”演剧与祭祀仪式研究》,《戏曲研究》第88辑,第70-73页。
朱坂村田公由青少年扮演,手捧小尊田公神像,坐镇于舞台正后方,颇觉神威显赫;槐南村的田公由孩童担任,手中不捧神像,由郑二作陪,二童坐于戏桌之后,形象没有那么鲜明,但同样受到尊崇。田公在戏神中位阶高过阔公,《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五《风火院田元帅》条,田元帅有三兄弟,名田苟留、田洪义、和田智彪,因助天师逐疫,被唐明皇封侯。*(明)无名氏著,(清)叶德辉校订,《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第241-243页。康保成:《傩戏艺术源流》,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43页。田公元帅同时是傀儡戏的戏神。在福建、广东一些地方也被当作蛙神——生育之神,*康保成:《傩戏艺术源流》,第261-266页。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两村的田公都挑选童男子担任,实有祈求人丁兴旺之意。
阔公在两村作场戏中的地位则颇有落差。朱坂村的阔公除了具备戏神神格,还须为村民禳灾祈福,并出面邀请四方及本地大小神灵,连同村内余廖二姓及客居者之祖先到戏棚前看戏,可以说是田公、四方神灵及本地神鬼、信众之间的沟通者。阔公出场时,啰哩队须全体起立致敬,颇觉威仪。
槐南村作场戏先由太白金星下凡,探问槐林地方情况,再由田元帅上场,命值符使者搬请四方神灵,搬请的过程相当漫长,直到第六出《阔公口诀》,阔公才出场。他在戏中只做为一位带着戏神神格的看戏老人,并不代表田公出面邀请地方神祇,和其他角色没有太大的差别。
田公、阔公之外,还有金花和银花。她们也是戏神。金花小姐见于《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风火院田元帅》条,多做为偶戏戏神受到奉祀。有关金花、银花的戏神身分,以及戏神与生育之神的关系,康保成《傩戏艺术源流》有较详细的说明*康保成:《傩戏艺术源流》,第245-246、264-265、288-290页。朱坂村《丰场总纲》第六出《金银花小姐》:
(场师云)忽见两位神女。头带玲珑七宝。身穿羽衣霓裳。登云驾雾。舞袖蹁迁。不知何处神女。来到花棚。愿闻其说。
(金花银花答云)我来金花小姐银花小姐。闻得朱阳境内。建造丰场。
奉师父严命。下凡玩赏。果然灯火明亮。笙歌不绝。真个十年光彩。太平佳兆也。*叶明生校订《丰场总纲(廖法昌民国十九年抄本)》,《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405页。
槐南村《场本全部》下编第七出《金银花小姐》里二女神的戏神神格更加清晰:
(正旦白)奴家金花小姐。奴在斗牛宫中。听见槐林堡。高架百丈文台。搬演人场文戏。不免叫妹妹下凡。观看一番。
接着金花带着银花,还有两位童儿来到槐林村戏台,和童儿唱起【太平歌】。临下场才道出下凡的目的:
金花小姐到。银花小姐到。姐妹两人身带二仙童,场中禳灾祈福保乡中。……奴今日降下凡,保他槐里人和。雪花满地飘。……*叶明生校订《场本全部(黄大河民国二十五年抄本)》,《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461、463页。
她们下凡亲临作场演戏,目的是“禳灾祈福,保佑乡中”。然而,根据付华顺的研究,槐南村清代各本《人场全本》中均无金花、银花小娘一出。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黄大河本中,才加入了金、银花小娘。而这出与1932年黄君海所抄《金银正小旦全桥分本》内容一致,明显与当地戏剧演出有关。*付华顺:《傩之嬗变:大田县朱坂丰场戏田野考察》,《戏曲研究》第88辑,第64页。曾宪林更指出,槐南《人场全本》的金银花一出是清末民初尤溪大腔戏杰出艺人罗阿楼(傀儡罗)添加的。*曾宪林:《福建作场戏音乐初探》,《戏曲研究》第88辑,第38页。王晓珊则注意到,槐南作场戏的《金花银花全桥》出目中,已有正旦、小旦等行当名称,据说这一出的唱腔和表演曾受傀儡戏艺人萧阿罗修饰改整过。*王晓珊:《福建大田、永安作场戏表演形态及其艺术特征》,《戏曲研究》第88辑,第7页。
槐南作场戏的内容,怎么会由大腔戏或大腔傀儡戏艺人添增或修整呢?叶明生《福建傀儡戏史论》引《永安县志》卷三十二,告诉我们进一步的讯息:
木偶 清嘉庆、道光年间,槐南高腔木偶艺人萧阿楼兼学大腔戏,故木偶戏常与大腔戏交流演出。
叶明生从田调得知,萧阿楼人称“傀儡楼”,曾在大田县小廖坊村和尤溪八字桥教大腔傀儡戏,大田、尤溪一带流传大腔傀儡戏都和他有关。*叶明生:《福建傀儡戏史论》,第153页。则“罗阿楼(傀儡罗)”或“萧阿罗”可能指的都是同一人。
不仅萧阿楼兼学大腔戏,叶明生还发现,永安县青水乡丰田村的大腔戏是三百寮、青水、槐南、大田、尤溪一带大腔戏的源头,也和大腔傀儡戏有一定的关系。这一带的大腔傀儡戏和青水大腔戏风格基本一致,和南平的大腔傀儡戏在剧目方面却明显不同。*据叶明生调查,青水丰田村熊姓家族在元泰定二年因避难自江西迁徏至福建,辗转迁至该地定居,其子孙有人回江西石城祭祖,习得祖居流行的大腔戏,带回村中并办起族村的大腔戏班,原本只做为酬神和自娱,明末清初开始应邀到邻近村落演出并传授大腔戏技艺,并影响了傀儡戏。叶明生:《福建傀儡戏史论》,第154-155页。
根据曾宪林对朱坂村和槐南村作场戏的音乐分析,朱坂村的作场戏扣除第一出《场师请神挂讳》和最后第15出《师父收场》的仪式场面外,共有13出,其中,用大腔戏曲调的有7出;槐南村作场戏共计9出,用大腔戏曲调的有5出,两者都超过二分之一,是各类曲调*根据曾宪林的分析,两地的作场戏使用的的曲调包括啰哩嗹、大腔戏曲调、吟诵调、昆腔曲调、俚曲、法曲等六种,另有锣鼓经和器乐音乐。中使用最多的。*曾宪林:《福建作场戏音乐初探》,《戏曲研究》第88辑,第23-26页。罗金满的研究也补充了重要的讯息:
本村(槐南)原办有大腔戏戏班,每年与做场戏交替演出。故其唱腔音乐大体相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随着老艺人的去世,大腔戏戏班逐渐消亡,目前仅剩个别当年参与大腔戏班演出的老艺人。*罗金满:《大田、永安宗族做场戏遗存探述》,《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176页。
这条资料告诉我们,原本槐南不只是作场戏主要使用大腔戏曲调,也和大腔戏班交替演出。(后改为越剧戏班)子弟们学唱时,由村里大腔戏艺人(或傀儡戏艺人兼习大腔戏者,如萧阿楼)指导,甚至修饰、调整演出内容,是很自然的事情。槐南作场戏之称为“人场戏”,或许正取意于相对于傀儡的“非人”特质;朱坂村称“丰场”,则着眼于祈求丰年。
周治彬曾经根据对兼任道士的尤溪县大腔戏艺人的采访结果,以槐南作场戏值符表演和尤溪道坛请值符神的科仪相比较,认为两者极为相似。他首先比对槐南坐场戏开场请神仪文、尤溪道坛开场仪文,以及永安丰田大腔戏及尤溪南芹小腔戏戏班开台“通词”,认为“四者除了文辞有些不同外,所表达的请神意愿是一样的”。*周治彬:《永安槐南“作场戏”值符表演与尤溪道坛请“值符神”科仪调查》,收在《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306-317页。(原收在王评章、杨榕主编《福建杂剧、南戏论集》)以下转录永安丰田大腔戏班开台《请神通词》:
……有劳符官使者前去拜请九天风火院田窦郭三位老郎、部下千里眼、顺风耳、金花小姐、银花小娘,一生二旦三丑四净五贴六末七外八夫,千千功曹、万万师父……今据福建省**府**县**都**保**,新架戏台一所,命梨园子弟搬演戏文。子弟前来演戏,恐怕有凶神恶煞来害,未敢自专,敬请鲁班仙师、诸位神袛前来安奉,台助吾子弟前来开演……
对照见叶明生校订《场本全部》上编《请神科仪》二、《请神文》的请神内容:
先烦符使,口衔香信,直到杭州铁板桥头,拜请:玉皇敕封九州岛风火院中田窦郭三位师父、副将三位元帅杨元亨、郭元贞、金花小姐、银花小娘、三百公公、三百婆婆。梨园会上一末、二净、三生、四旦、五丑、六外、七贴、八辅。苏州兔老、吉州黄二、福州张阔……梨园会上三十六条大街。七十二条小巷。弟子知名不知名姓,知姓不知名。乃文乃武。乃圣乃贤。桃源洞里一切有感圣贤降赴戏棚到座……*叶明生校订《场本全部(黄大河民国二十五年抄本)》,《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429页。
连结本文上一节提到永安黄景山村大腔傀儡戏的戏神群,还有朱坂村、槐南村作场戏上台的神祇相对照,可以发现它们来自同一个系统,都是属于大腔戏的流传体系。
福建的尤溪、大田、永安和三明这一带,正是大腔戏和大腔傀儡戏的流行区域。清道光年间,大腔戏盛行于这一带,光是大田一地就有三十几个戏班。*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大腔戏”,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第722-723页。黄景山村的位置就在槐南村的南边,朱坂村的西南方附近;尤溪县则在朱坂的东北边,四个地点有紧密的地缘关系。
朱坂村和槐南村作场戏的主要演出内容,简单的说,即由子弟演员扮演大腔戏系统所供奉的戏神,一一上台为该村祈福。从这样的演出的结构和功能来看,它其实就是大腔戏的“子弟扮仙戏”。
“扮仙戏”是一种仪式戏剧,在每天正戏演出前,照例由演员扮演神仙上台为信众祈福。台湾北管戏的“扮仙戏”剧目相当丰富,*北管扮仙戏相当丰富,唱昆腔的有:《醉仙》《三仙白》《天官赐福》《长春》《卸甲》《封王》《金榜》《大八仙《河北封王》;唱古路唱腔的有:《新天官》《飘海》《太极图》《古挂金牌》《新挂金牌》;唱南词的有:《封相》《南词仙会》等。参见吕锺宽《北管音乐概论》,彰化:彰化县文化局2000年,第77-80页。影响台湾其他剧种甚巨。
作场戏子弟演员扮饰的神仙,是由田公和阔公领导组成的“戏神群”,搭配其他大腔戏和大腔傀儡戏艺人供奉的神明,所以说是“子弟扮仙戏”。作场扮仙戏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些专司守护演员的戏神,同时是宗族保护神和地方保护神,他们护佑的不只是代表宗族上台的子弟,更是整个宗族和地方。
三、以祭为戏、戏与傩 交融的福建作场戏
如果我们将作场戏“子弟学戏→绕境请神→登台演戏→演毕结束”四个步骤所发生的所有空间,视为一个整体的“信仰场域”,而不仅限于戏台,将会发现每一个环节都以张大阔公为核心,由紧扣“禳灾祈福”的系列仪式串连而成,兹以朱坂村和槐南村对照说明如下:
1.子弟学戏
朱坂村里的阔公庙始建年代不详。其香火牌位题“祀奉青州祖殿张大阔公之神位,左边判官,右边小鬼”21字。子弟学戏之首日,会将阔公、正妈、副妈的面具、香位、神舆及田公本像迎至祠堂供奉。学成后,会先于农历十一月和十二月在祠堂戏台各试演两场。*张帆:《福建朱坂村“作场”演剧仪式调查》,《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148页。
槐南村阔公原本无庙,也无神像或神位,只有一个香炉供奉在当地黄姓分支祠堂“后堂祠”的右厢房。在正式演出前的初三初四,会进行演场彩排,由参神向阔公陈告排演事宜。*张帆:《福建槐南村“人场”演剧与祭祀仪式研究》,《戏曲研究》第88集,第70页。2018年笔者到“大新堂”考察,已塑有神像。
朱坂村的面具有十付:分别为木雕的阔公(黑面)、正妈、副妈、判官、小鬼(现无),及纸扎的红黑白三个回回面具、牛头、马面。*叶明生:《傩近于戏:福建杂剧中的面具戏考探》,《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69页。(原收在周华斌编《舞岳傩神:中国湖南临武傩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年)。阔公、正妈、副妈等三付面具平日供奉于阔公庙,没有神像。朱坂村视面具为神,作场戏多位角色所戴的面具,若是新制,须跟民间寺庙新塑神像一样,迎送至村落最高峰开眼和开光,使新面具具备神格和神力。*张帆:《福建朱坂村“作场”演剧仪式调查》,《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未发表),第143页。
槐南村的面具有六付,皆为木雕,分别是阔公、土地、值符、魁星、小鬼和四嫂。平时不供奉于神庙或祠堂,演完后即装入箱笼,不具备神格。*叶明生:《傩近于戏:福建杂剧中的面具戏考探》,《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71页。
2. 绕境请神
正月初一为朱坂村作场戏演出首日,须将原来请到祖祠的阔公香火移到戏棚,所有演员至阔公庙装扮并接受场师挂讳护身,接着“请神起马”,即请各神灵同时降赴戏棚,并起马巡视村境各角落。接下来就是“绕境参佛”,参拜地方保护神,在固定地点挂讳、烧纸等,祭煞除秽,祈保平安。绕境由神舆先导,人员排列顺序依次为:场师、田公师父、阔公、正妈、副妈、判官、小鬼、招财、进宝、将军、演戏小生、女旦、牛头、马面、回回。《丰场秘旨》中对绕境具体情况有详细的记载。*罗金满:《大田、永安宗族做场戏遗存探述》,第164页。张帆:《福建朱坂村“作场”演剧仪式调查》,第148页,二文皆收在《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在参神、参人主、参佛时,都有不同的四句要念。做戏之前,道士要请神,变身,到戏棚封场挂讳,并为演员、器乐开喉、挂讳之后,才能正式演出。*付华顺:《傩之嬗变:大田县朱坂丰场戏田野考察》,《戏曲研究》第88辑,第47页。朱坂村阔公巡境带有鲜明的“沿村逐疫”的傩祭性质。载上面具的“扮仙”演员们,在此刻皆成为傩神的替身。
槐南村的阔公绕境前,扮演田公师父和郑二的孩童,须至大新堂进行净坛、净身、请神、装扮等仪式。接着出发巡境,称为“迎场”或“出路”。队伍次序为:锣鼓队、阔公神舆、田公和郑二在参神左右,最后为村民。沿途参拜念请神词。*张帆:《福建槐南村“人场”演剧与祭祀仪式研究》,《戏曲研究》第88集,第70-73页。驱疫色彩较淡。
3.登台演戏
朱坂村会为作场戏的正式演出塔设临时戏台,称为“场寮”或“花棚”,有关材料、过程、结构等,都有种种讲究。*张帆:《福建朱坂村“作场”演剧仪式调查》,《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143-146页。槐南村原本也一样要塔设临时戏台,1987年“大新堂”固定戏台建成启用后,便不再塔台。*张帆:《福建槐南村“人场”演剧与祭祀仪式研究》,《戏曲研究》第88辑,第69页。
就科仪来观察,朱板村作场戏第一出《田公作场》,有大段田公请天神地祇的科仪。槐南村的开场科仪更加严密,一开头由礼生(场师)表演完整的“请神科”,第二出《师父登场》值符使者再做一个“请神科”,剧中更有多次简短的科仪性质表演。*叶明生:《福建宋杂剧与道教科仪关系考》,《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57页。(原名《福建宋杂剧与道教科仪关系考——以朱坂丰场仪式的作场戏为例》,收在中国古代戏曲学会编《中国戏剧史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又,有关演员的科介动作,王晓珊指出,在作场戏中的师父、阔公、判官等神格人物的动作,多有名称和固定程序,例如啰哩舞、两步半、种豆、结手、开帐,以及道士的道坛舞蹈等,都是靠宗族世代传承,同样带有科仪的性质。*王晓珊:《福建大田、永安作场戏表演形态及其艺术特征》,《戏曲研究》第88辑,第6页。
而更引人注意的是坐在戏台左右的“啰哩队”,朱坂村保留有游场啰哩、退场啰哩、师父啰哩、阔公啰哩、判官啰哩、鬼将啰哩、金花银花啰哩、妈姆啰哩、招财进宝啰哩、回回啰哩等唱调。槐南村则保留了仙啰哩、判官啰哩、师父啰哩、魁星啰哩、阔公啰哩等唱调。罗金满在他的论文中,罗列了十四种啰哩的具体唱词。*罗金满:《大田、永安宗族做场戏遗存探述》,《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177-179页。
4.演毕结束
作场戏结束后,尚须执行相关仪式。朱坂村较为繁复,包括:退场、谢神、游场、烧寮、绕境、烧纸送神、下铁栅甲、插青、安神等,大部分由场师主导执行。
槐南村相对比较简单,由送神人员念送神口诀,即可结束。又分初夜送神和终夜送神两种。*罗金满:《大田、永安宗族做场戏遗存探述》,《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171-173页。
相较之下,朱坂村有一套规划得极为全面和细腻的仪式来操作作场戏。从一开始恭请阔公神灵督导子弟学戏、确保面具的神格和神圣性;到绕境时所有演员郑重着装接受挂讳,参与巡境禳灾祈福;到演出时身段、科仪、啰哩队等诸多讲究;再到结束后谢神、送神的谨慎和周密。朱坂村作场戏的禳灾驱邪意义被高度放大,让所有参与者感受到身处一种“非常”的时空氛际。这使得作场戏不只是一场演出,更是一整套信仰;其活动的空间,不止于戏台,而是整个村庄;参与者不止是自然空间的人们,也包括超自然空间的神灵,充分表现了信仰与生活、祭祀与戏剧融为一体的仪式特质。
特别值得一提的,如朱坂村为演出搭建的“场寮”,分为前台和后台两部分。绕境后,阔公神舆、香位、香炉都被安放在戏台后部,而非前台。*张帆:《福建朱坂村“作场”演剧仪式调查》,《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143-146页。民众经由后台入口进到阔公神案前,捐献、祈福等祭祀活动被热烈展开,使得“场寮”不仅仅是戏台,更成为充满仪式意味的祭祀空间。
整齐的啰哩队和丰富的啰哩调是作场戏演出充满仪式意味的另一个重点。“啰哩嗹”是来源自梵语的“戏神咒”*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子弟开呵一醪之,唱啰哩嗹而已。”明代宜黄县艺人开台演戏,祭戏神时,就要念戏神咒“啰哩嗹”。《汤显祖全集》,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188页。。因此田公有田公咒、阔公有阔公咒等。根据陈建华的研究,“啰哩嗹”变为“戏神咒”经由两个关键环节:巫道对僧侣咒语的借用、傀儡戏对巫道咒语的移植。后世“啰哩嗹”使用的情况复杂,但均由禳灾祈福的意义与和声的形式两方面衍生出来。*陈建华:《啰哩嗹:作为戏神咒的渊源及其意义扩散》,《文化遗产》2014年第4期。
叶明生也说,“啰哩嗹”在北宋的傀儡戏中早已滥觞,传到宋杂剧和南戏中的“啰哩嗹”,恐怕是道教所引起的作用。*叶明生:《福建宋杂剧与道教科仪关系考》,《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59-60页。朱坂村和槐南村作场戏之所以出现大量且多样的“啰哩嗹”,与流行于大田永安一带的大腔傀儡戏,以及道教科仪的植入,有绝对的关系。
事实上,朱坂村作场戏的整个仪式活动和演出,皆由该村道师掌控,其演出本、科仪资料和演出安排等均由道坛管理。叶明生指出,这是道坛替宗族发挥功能和作用。有关道坛如何成为朱坂作场戏的载体,场师如何操作整个仪式和演出的进行,以及廖法昌《丰场总纲·序》“使神道设教”,利用作场戏的“高台”达到“教化”的目的,叶明生有很完整的说明。永安槐南作场戏则由宗族主导,道教色彩较稀薄。*叶明生:《福建宋杂剧与道教科仪关系考》,《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38-61页。
前面曾提到周治彬比较永安槐南作场戏的“值符请神”表演和尤溪县道士设坛“请值符神”的科仪,*周治彬:《永安槐南“作场戏”值符表演与尤溪道坛请“值符神”科仪调查》,《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311页。以实例证明了地方道教科仪对作场戏的影响。付华顺则强调作场戏中的“面具”特征,他认为“当地(朱坂村)的阔公很有可能是傩神。*付华顺:《傩之嬗变:大田县朱坂丰场戏田野考察》,《戏曲研究》第88辑第60-61页。叶明生则举清同治六年刻本《广昌县志》“少年子弟沿门搬春戏,或朱裳鬼面以为傩”的记载和朱坂作场戏相对照,认为:“朱坂的作场戏很早就向杂剧靠拢,其傩的内涵已被淡化。仅存驱傩意识和祈禳意蕴了。”*叶明生:《傩近于戏:福建杂剧中的面具戏考探》,《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62-79页。
江西广昌县和福建省建宁县毗邻,而建宁县和大田县同属三明市,和朱坂距离不远。朱坂村作场戏虽然以戏剧的形态出现,但在上“花棚”前,村中子弟们戴着包括阔公在内多达十付面具,巡境禳灾祈福,上台后,啰哩队庄严念诵,演员依扮饰神灵的不同所做的种种科仪化的动作,傩的意味还是十分浓厚的。长年安奉阔公和二妈面具的阔公庙,实质上可以视为傩神庙,阔公实质意义上就是傩神。
阔公做为以面具为特征,禳灾驱邪的傩神,同时又是作场戏中的戏神,这之间是怎么过渡的呢?
根据康保成的研究,戏神兼为傩神颇不乏其例,例如,唐明皇、老郎神和二郎神在许多地方都是傩神。唐明皇在明末顾景星《白茅堂集》卷三十一“楚俗尚鬼,而傩尤甚”的描述中,就有“黄袍、远游冠者,曰唐明皇”被视为傩神的记载。云南昭通地区的端公庆菩萨仪式中的主神太子菩萨,便是老郎神;而二郎神更是西南地区所信奉的傩坛三圣──川主、土主、药王之一的川主。*康保成:《傩戏艺术源流》,第343-347页。
这些神祇做为傩神的记载都早于戏神。老郎神又有即是唐明皇的说法;汤显祖《庙记》也早就提到二郎神能够驱厉逐疫。陈志勇指出,傩神和戏神交融的关系,还体现在傩神二郎神、戏神老郎神、田公元帅都源于傀儡戏神。傀儡戏神可以说是后世傩神和戏神的总源头。
陈志勇的戏神研究提到“清源真君”的例子。祂原本即有傩神特质而被奉为戏神,清初,其戏神信仰逐渐消失,傩神的部分却在赣东傩戏中遗存:
清初之后戏曲行业祖师神“清源真君”信仰逐步消歇,却在赣东的宜黄、南丰等地有傩神庙、游傩神、祭祀傩神的遗存。此外,与南丰为邻的广昌县甘竹、赤溪,与宜黄为邻的乐安县东湖、罗山等村傩舞、傩戏,也都以清源为傩神。
南丰和广昌都在江西靠近福建边界,和三明市的建宁县为邻。广昌县甘坊村的清源师信仰最盛,清源师的生日,和阔公同在六月廿四日,乡民们照例要演戏十天,称为“老王会”。*陈志勇:《民间演剧与戏神信仰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69-176页。从这些线索来看,阔公做为来自江西的傩神和戏神,并非没有脉络可循。
明末顾景星《白茅堂集》除了唐明皇,还提到“高髻步摇,粉黛而丽者二,曰金花小娘、社婆。”这是金花小娘被视做傩神的记载。而田公元帅从傀儡戏神演变为民间的俗神,亦是乡民取其除疫驱祟,保境安民功能的产物。福建多种文献都保存田公元帅为当地村民除疫驱祟,保境安民的集记忆,表现在民间传说及戏神壁画等文物之中。*陈志勇:《民间演剧与戏神信仰研究》,第260-264页。朱坂村和槐南村“作场扮仙戏”中“戏神群”成员的田公元帅和金花小娘原本皆为傩神,阔公也可能先是来自江西的地方保护神的傩神,而后因为被演员奉祀,加入戏神神帮,而为之转化过渡的,可能便是流行于当地的大腔戏和大腔傀儡戏。在赋予阔公戏神神格的过程中,将不同戏神的特质,如籍贯、造型、有三身(三兄弟)、以白兔为号、生日等,加诸阔公身上,因而显现了多位戏神身影的叠合。
康保成和陈志勇都强调先有傩神后有戏神。傩神因为受到伶人尊崇,而进入戏神行列。尔后,戏神的信仰可能逐渐消失,如宜黄戏神清源真君;也可能傩神的特质被淡化,如田公元帅在许多地方都只被视为戏神来崇拜。作场戏中的戏神群,同样都先是驱疫除秽的傩神,后进入戏神行列,却仍保留他们地方保护傩神的特质。
结 语
罗金满在《大田、永安宗族做场戏遗存探述》的结论中就曾提到“阔公是戏神神帮中的一员,而且做场戏中的众多神灵也来自于戏神神帮”*罗金满:《大田、永安宗族做场戏遗存探述》,《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183页。,惜未对阔公的戏神身分和神格有所说明,或对朱坂和槐南作场戏的戏神神帮系统及脉络有所讨论。
本文就朱坂和槐南两地的传说和相关文献,包括作场戏演出本文、永安大腔傀儡戏学徒拜师所念的《请师父文》和民众请傀儡戏班演戏还愿所念的《谢愿请神文》,论述宗族保护神张大阔所兼具的“戏神”神格,及其可能的背景;接着从两地作场戏所见的“戏神群”,对照当地大腔戏、大腔傀儡戏、小腔戏等剧种戏神群的重叠,指出作场戏由村中“子弟演员扮演戏神”的“子弟扮仙戏”本质。接着,将朱坂村和槐南村从作场戏筹备到结束所含括的空间,视为一个整体的“信仰场域”,而非只限于戏台,观察两地作场戏在不同步骤中展现的以阔公为中心的鲜明仪式性。进一步论述整体历史文化中,由傩神到戏神的信仰发展脉络,以及宗教科仪和地方流行剧种对于民间信仰观念的渗透甚至活动方式的植入。
从两村作场戏的比较,我们很容易留下朱坂村的仪式较为古老,保存张大阔公信仰元素较多的印象,这也许并不尽然。因为所有民间信仰的表现方式都存在着偶然的人为变异性。付顺华指出,朱坂村廖法昌抄本《丰场总纲》系经过该村廖逢明改编,文字整齐,而且有浓厚的文人教化意味。槐南村《人场全本》则内容较为庞杂,辞多俚语、粗俗,保留了较多民间演剧的特色。在廖逢明改写以前,两村的文本内容应当是大同小异的。*付华顺:《傩之嬗变:大田县朱坂丰场戏田野考察》,《戏曲研究》第88辑,第40-65页。而如同叶明生所言,朱坂村作场戏完全由道士掌控和执行,这使得道教科仪高度渗透其中,执行上种种细腻的安排,也可以想见同样具备创设的成分。曾宪林则提到前些年朱坂村作场戏第十四代传人之一的余生旺(1935-2010)*参见福建省大田县文体局《大田杂剧作场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申报书》,《福建杂剧作场戏研究及资料汇编》,第350页。本来想将做场戏的声腔改为越剧唱腔,因为越剧唱腔流行于当地,后因生病过世而未替换。*曾宪林:《福建作场戏音乐初探》,《戏曲研究》第88辑,第38页。可以说是作场戏表演内涵之承受偶然因素影响的绝佳例证。
有关作场戏的宋杂剧遗存,已有叶明生、罗金满、刘晓珊、曾宪林等学者,就方方面面提出相当完整的阐述。作场戏珍贵之处,还在于它所提供的民间信仰发展和变化的范例,凸显朱坂和槐南做为福建中西部山区的村落,因为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历史因素所造就的样貌,无论其过程或结果,都有其独一无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