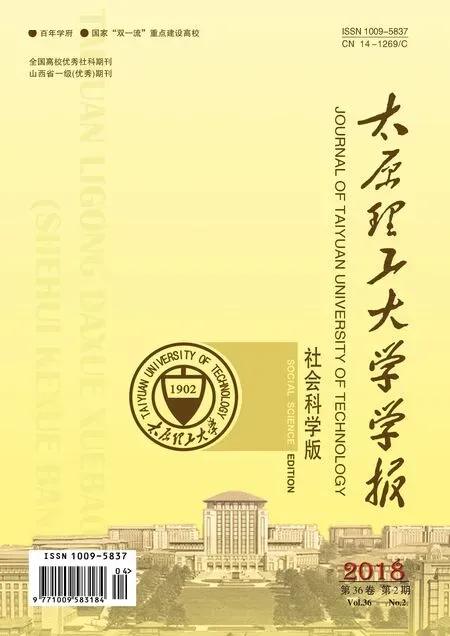论“妙悟”视域下《沧浪诗话》的运思逻辑
朱松苗
(运城学院 中文系,山西 运城 044000)
虽然“妙悟”说不是由严羽第一次提出,对于“妙悟”的重视也不始于严羽,但是在美学和艺术理论史上,却是由他第一次系统地阐释了“妙悟”,并使“妙悟”成为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理论的一个重要主题。那么,对于严羽而言,何谓“妙悟”?他又妙悟了什么?妙悟又如何成为可能?妙悟又是如何在艺术中实现的?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答形成了《沧浪诗话》的内在逻辑,并使它成为宋元诗话著作中最具有系统性的著作。王运熙、顾易生认为,《沧浪诗话》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不多见”的“具有系统的理论体系”[1]的著作;朱志荣更是认为《沧浪诗话》是一部具有“严肃性、原创性和思想性的诗话理论体系”[2]。与朱教授采用本体论、主体论等西方学术话语和理论体系来重构这部著作的思路不同,本文尝试从其核心语词“妙悟”自身的逻辑性来厘清《沧浪诗话》的内在逻辑,在其已说的基础上,补充其要说而未说的内容。基于此,本文对于“妙悟”的言说就不再集中于对妙悟的字源学、社会学的考察,也不探讨它在理论史上的流变及影响,甚至也不单纯寻求妙悟这个词的含义(如直觉说、形象思维说、灵感说等),而是结合文本自身,重点分析“妙悟”的内在结构,正是这种结构,将严羽对诗歌的理解汇集起来构成了一个整体。
一、何谓妙悟?
关于“妙”字,它在古代早期文献中是很少见的,第一次明确提出并赋予其思想意义的是老子,“故常无,欲以观其妙”。河上公注:“妙,要也。”[3]王弼注:“妙者,微之极也,万物始于微而后成,始于无而后生,故常无,欲空虚可以观其始物之妙。”[4]“其”在这里联系上下文就是指道,老子认为,道之妙就是无之妙(无生有),甚至道就是无,“它(道)自身就是虚无”[5]。这就是道之“要”,即精要、要害和重要的地方;“无”是道的本性,但这里的“无”不是指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而是说道作为万物的根源,它本身是不同于万物的,它无本、无根、无名、无极、无形,它具有无规定性、无限性和不可言说性。道始于无,然后从无到有,于是生天生地,这就是道的奥妙、精要,同时也是最精微、最深不可测的地方。“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6]所以,妙之为妙,是因为它是道的显现,表现了无的特征,并因此而通向无限和不可言说。
同样,“悟”字在古代早期文献中也是很少见的,较早提出这个字的是庄子,“客凄然变容曰:甚矣子之难悟也”(《庄子·渔父》)。《说文解字》解释为“悟,觉也,从心吾声”;《广韵·暮韵》解释为“悟,心了”;刘良在《文选·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中解释为“悟,明也”[7]。所以,悟指的就是吾心之觉解和明了。庄子之悟或道家之悟就是对自然之道的觉解和明了,这成为悟字产生之初的含义。
但“妙悟”作为一个语词的出现,却并非出自于道家学说,而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最早出现于僧肇的《般若无名论》中,后流行于禅宗诸典。这是因为在佛教中,佛即觉悟者,悟即佛,不悟即非佛,禅宗更是强化了这一点,强调即心(悟)即佛,并将悟具体化为顿悟和渐悟,由此形成北宗和南宗两派。所以“悟”在禅宗这里形成了主题。那么“妙悟”在禅宗中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它意味着悟“妙”,即悟道,由于妙体现了道的最精微、精要之义,所以它成为道的代名词。不同于道家的自然之道,禅宗所悟的是心灵之道,是人的本心、佛心,即人的自然、清净和自由之心。另一方面,它意味着这种悟是一种“妙”悟。之所以“妙”,首先,是因为它不依靠概念文字,“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坛经·机缘第七》)[8];其次,它不依靠理性和逻辑推理,“思量即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坛经·行由第一》)[8];最后,它也不单纯依靠知识和学力,“不识本心,学法无益”(《坛经·行由第一》)[8]。禅宗对妙悟的对象和妙悟的方法的理解影响了严羽对诗歌的理解。
二、妙悟什么?
“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诗辩》)[9],严羽以禅喻诗之所以成为可能,就在于两者都需要妙悟,但禅道毕竟不同于诗道,禅道悟人,诗道悟诗,禅道悟人之本性,诗道悟诗之本质。那么在严羽看来,何谓诗?或者说诗的本质是什么呢?
《诗辩》称:“诗者,吟咏情性也。”何谓情性?一般认为,情是人的情感,性是人的本性,情是已发的,性是未发的,情是显现的,性是隐藏的,所以情是性的显现,就像青色是生命的显现一样*甲骨文中没有性字,只有生字,性字本身由生字而来,而生字在甲骨文中像草从地下生长出来,引申为正在生长和生命之义;同样,青字的出现也要比情字的出现早得多,事实上,青字就是情的本字。青之本义为草之青色,即正在生长的有蓬勃生命力的草的颜色,故而青为生显,与之相应,情为性显。参见张杰.先秦儒家性情思想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03:43-56.,因此“情性”就是指符合人的本性的情感。但关于人的本性,历史上却有不同的说法,最典型的是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两种观点。与此相关,对于情,历史上也有两种相反的观点:许慎解释情为“人之阴气有欲者”,因为性善情恶,他对情持否定的态度;王圣美则解释情为“心之美者”*王圣美使用归纳法证明了“青”字的含义,即“美好”之义,如“晴,日之美者”,“请,言之美者”,“菁,草之美者”,“倩,人之美者”,“清,水之美者”等,所以将“情”字代入其中,即心之美者。,对情持肯定的态度。两种观点看似相反,实则并无冲突,因为人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人是自然性、动物性、欲望性的存在;另一方面,人又是社会性、文化性、应然性的存在。荀子从人的实然性——欲望出发,自然认为人性本恶;而孟子从应然性的角度出发,必然认为人性本善。同样的道理,许慎将情与欲相连,所以否定了情;王圣美则将情与人的应然性相连,所以认为情是美好的。
那么,严羽的“情性“指的是符合人的动物性的情感,还是指符合人的应然性的情感?“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诗辩》)。很显然,在严羽看来诗是用来抒发人的情感的,但不是抒发人的自然性(动物性)情感,即“叫噪怒张”“骂詈”等情绪,而是抒发人的应然性的情感。
然而,人的应然性情感自身也有一定的区分,它还可分为道德情感和审美情感等。前者在《毛诗序》中得以表现——“吟咏情性”作为诗的本质之说,并不是严羽第一次提出,而是首次出现在《毛诗序》中,但是《毛诗序》中的“情性”指的是一种道德情感,与道德伦理和政治教化相关,所以它的情感虽超出了人的动物性和自然性,却又受礼仪道德所限制,即“发乎情,止乎礼”的限制。
基于此,严羽对《毛诗序》的“吟咏情性”进行了重新解释,因为他的“情性”既不同于人的自然性情绪,又不同于儒家的道德情感,而只关乎人的情感自身,所以它既不受欲望的控制,也不受理性的制约,是一种自由的情感,并因此成为审美情感。这种情感就表现在严羽对情感自身的肯定上,而对情感自身的肯定又来自于对含有此类情感的诗歌的肯定:“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诗评》),“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洟满襟,然后为识离骚”(《诗评》)。严羽之所以对唐诗和《离骚》赞赏有加,就在于它们能够“感动激发人意”,让人“涕洟满襟”,而这又是因为其是出自真性情的情感——审美情感。
但是,审美情感本身还不是诗,所以接下来,严羽又用了“兴趣”一词。兴,起也,也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趣即审美情感。在审美情感和诗之间,还有一个兴的过程。也就是以物起情,以情入物,情景交融,这实际上是认为能抒发审美情感的是审美意象,只是在这里,严羽还没有明确提出,但是他对“兴趣”的描述,实则指审美意象。“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诗辩》),它虽如音、色、月、象可见可听,但我们却把握不了,原因就在于它“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立象以尽意,而象能显示无限之道,所以象能表达不可言传的审美情感,因此审美意象所传达的情感是无限的,它本身也是用逻辑语言无法表达的,所以它通往妙悟。
正是因为如此,严羽强调“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诗辩》),诗的材料不是来自于书本知识,而是来自于生活世界的象;诗的趣味不在于道理和理性,而在于审美情感。诗就在于生活世界的象与审美情感的合一。这种合一之所以成为可能,就在于审美情感就源于生活世界,而生活世界之所以具有意义,又是因为人的审美情感。
除了将诗的本质归于表达人的审美情感之外,严羽还强调了诗的表达方式也应该具有审美性——吟咏。何谓吟咏?孔颖达解释为:“动声曰吟,长言曰咏。作诗必歌,故言吟咏情性也。”[10]诗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又可分为语音和文字。从上古歌谣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情况来看,诗最早只是语音的艺术,只是这种语音不是一般的发音,而是有节奏、有韵律的声音,即审美之音,也正是这种审美之音,使诗具有了音乐性,从而诗与歌相连,诗便成为诗歌。同时,由于音乐与情感的相连性,诗歌也就成为古人抒情的工具。但随着文字的出现和发展,诗逐渐脱离了音乐性而与文字相连,虽然文字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审美性,但它更多的是与意义相连,其结果便是诗更强调诗意,而不再是诗情,更强调的是诗的文字性,而不是诗的音乐性。所以严羽对“吟咏”的强调实际上是对诗的本性,即诗的音乐性和情感性的回归,正是基于此,他强调对楚辞要朝夕“风咏”(《诗辩》),“读骚……须歌之”(《诗评》),诗歌要有“一唱三叹之音”(《诗辩》),并对时人所抨击的叠字、叠韵之诗加以肯定,这是因为这些诗符合了诗的节奏性和音乐性,即诗的吟咏本性。
正是在此基础上,严羽对江西诗派展开了激烈的批判,“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在”(《诗辩》)。不管是禅道还是诗道,都强调通向道之路,即对本心和审美意象(包括审美情感)的把握,不是靠日常语言(文字)、理性思维(议论)和知识的积累(才学)就可以完成的,因为本心、审美意象从本质上讲是通往无限的,并因此也是不可言说的,所以我们只能通过非理性、非学识、非语言的妙悟,才能把握其本性和本质,因此“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诗辩》)。
而妙悟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妙悟者和妙悟对象在一起,或者说他们是合一的。对于禅宗而言,作为妙悟者的人和作为妙悟对象的本心是合一的,因为人原本就具有本心,所以在人的本心被遮蔽之后,人才能妙悟本心;同理,严羽对诗的本质,即“吟咏情性”的妙悟也因为他们是合一的,一方面,人应该具有审美情感,另一方面,审美情感使人成为人,而对这种审美情感的吟咏就成为诗歌。
三、如何妙悟?
(一)识
严羽在《诗法》中有对学诗的三层境界的描述,“学诗有三节:其初不识好恶,连篇累牍,肆笔而成;既识羞愧,始生畏缩,成之极难;及其透彻,则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矣”(《诗法》)。从“不识”到“既识”再到“透彻”,实际上是三个阶段,我们要想到达最高阶段——“透彻”即妙悟,实际上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识”。正是因为如此,《诗辩》开门见山就强调“夫学诗者以识为主”。
识就是认识、了解,识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只有对诗有所认识和了解,“其(诗)真是非自有不能隐者”(《诗辩》),相反,如果“见诗之不广,参诗之不熟”(《诗辩》),则容易导致“野狐外道,蒙蔽其真识,不可救药,终不悟也”(《诗辩》),所以严羽强调“辨家数如辨苍白,方可言诗”(《诗法》)。
那么具体而言,从前人、今人诗中我们应该识什么呢?
一方面是诗体。“作诗正须辨尽诸家体制,然后不为旁门所惑”(《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所以在《诗体》中,严羽分别从时代、作者、选体、流派、语言韵律和杂体等诸多方面对诗歌的流变和体式做详尽的划分,正是因为有此功夫,严羽才会对自己有如下评价:“仆于作诗,不敢自负,至识则自谓有一日之长,于古今体制,若辨苍素”(《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
另一方面是诗法,即诗的技巧和方法。“世之技艺,犹各有家数。市缣帛者,必分道地,然后知优劣”(《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不同的诗体有不同的技巧和方法,所用技巧和方法是否合适,这需要我们进行辨别,那么我们依据什么进行辨别呢?博取,也就是博观,“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文心雕龙·知音》),正是因为如此,严羽虽然反对以学识为诗,强调“诗有别材,非关书也”,但又认为“然非多读书,则不能及其至”。诗材虽不取决于书和识,但是它也不是空穴来风,所以它又要以书和识为基础。
(二)学
在识诗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学诗,不仅要认识诗,还要学习诗。严羽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禅宗虽然强调心灵的觉悟,但是并没有像印度佛教一样将其神秘化,而是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通向觉悟的道路——学习。《坛经》虽然主张“顿悟成佛”,并因此与主张渐悟的神秀北宗形成区别,但是它并不反对学习,“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须假大善知识示导见性”(《般若第二》)。这在于心迷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佛心被“浮云盖覆”,要去掉“浮云”,是可以借助外力即风的,“风吹云散,上下俱明,万象皆现”(《忏悔第六》),具体而言,就是学习佛法僧“三宝”。,“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诗评》),宋诗之所以不及唐诗,在严羽看来就是因为学习之故。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学习呢?“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诗辩》)。
1.以识为主。学诗要以识诗为基础。识的对象可以是正诗,也可以是邪诗,可以是汉魏晋盛唐诗,也可以是“大历以还”、晚唐甚至是“本朝苏黄以下诸家之诗”,但是学的对象则要有所辨析、有所取舍。
2.入门须正。学习的对象必须是正诗,而非邪诗,因为“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相反,学习正诗,“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诗辩》),学习就如走路,学习正诗就如走正路,反之就会走火入魔。那么对于严羽而言,何为正,何为邪?“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诗辩》),学习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为正,因为这些诗为第一义之悟,学习“大历以还”及晚唐诗者为不正,因为这些诗本身是“一知半解之悟”和“分限之悟”,至于学习苏黄诗者,更是不正,因为这些诗一如“野狐外道”。严羽以孟郊为例,论述了“入门之不正”,“诗道本正大,孟郊自为之艰阻耳”(《诗评》),这是因为“孟郊之诗刻苦,读之使人不欢”(《诗评》),孟郊的诗雕刻过甚,有理性思维的痕迹。
3.立志须高。这是因为严羽将诗道妙悟进行了区分,由高到低分别是不假悟、透彻之悟、一知半解之悟、分限之悟和终不悟。所谓“立志须高”就是要立志于不假悟和透彻之悟,因为“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诗辩》),所以严羽强调学诗要“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诗辩》)。具体而言,“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诗辩》)。
4.学须刻苦。学诗不仅要读书,而且要熟读。从时间上来讲,要朝夕风咏,学习不是心血来潮的冲动,而是天长地久的积累;从空间上来讲,要“枕藉观之”,学习不仅要发生在书房中,甚至要延伸到卧室里。总之,学习不是一时一地,而是时时处处;读诗不是一般的看,而是“咏”和“观”。如果把读理解为诵读的话,那么严羽所强调的就不是一般的诵读,而是有节奏感、有音乐性、有情感性的“咏”;如果把读理解为看的话,那么严羽所强调的就不是一般的看,不是目看,而是心观,也就是带着情感的观照和体味。
(三)酝酿胸中
不管是识,还是学,它们虽是通达妙悟的基础和途径,但它们本身还不是悟,相反,它们只是悟的外在条件。与之相对,悟更强调的是人的内在条件,即心灵的觉悟。所以在识和学之后,还有一个在胸中酝酿的过程。
酝酿的本义是指造酒发酵的过程,引申为事情逐渐达到成熟的准备过程,也就是涵育、熏陶之意。之所以要以前人的诗为“本”,熟读前人之诗要“如今人之治经”,就是因为这是一个逐渐陶冶、发酵的过程。诗人对于诗的本质和规律的领悟与把握不是朝夕就能完成的,它是在对前人优秀诗歌的不断吟咏的基础上,耳濡目染的结果,这样才能“久之自然悟入”。
四、妙悟的实现
禅悟与诗悟虽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重要之处在于禅宗特别强调悟,因为悟即成佛,一悟百悟,于是觉悟成了禅宗的最终目的。但是对于诗歌而言,它不仅强调觉悟,而且强调了悟的实现,即显现,就是说诗歌还需要运用艺术技巧和手法来显现这种觉悟。所以在《诗法》中,严羽详细地规定了显现的方式。显现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有遮蔽的存在,所以显现首先表现为去蔽。
首先,这在《诗法》中表现为去“五俗”。“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诗法》)。之所以要去俗,这是由诗的本质——吟咏情性所决定的,诗要显现的是人的审美情感而不是人的世俗情感,这种独特的情感就需要独特的情感形式来加以表现,所以对于诗而言,我们一方面要去俗意,以保藏我们的审美情感;另一方面,要去俗体、俗句、俗字、俗韵,以保藏独特的情感形式。
其次,去蔽还表现为五忌:“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音韵忌散缓,亦忌迫促”(《诗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诗从本质上讲并不是通过概念语言来直抒胸臆的,它通过“兴趣”——审美意象来显现审美情感,以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以语要曲——含蓄蕴藉,而不能直;意要深——情深意切,而不能浅;文脉要隐——前后相随,悄无痕迹,而不能露;味要长——耐人咀嚼,回味无穷,而不能短;音韵要适合吟咏而不宜太急和太缓。除了这五忌之外,严羽还强调了两个“最忌”:“最忌骨董,最忌趁贴”(《诗法》)。所谓骨董就是以古为尚,不加选择,甚至采用古词古字,以致诗歌斑驳陆离,艰深晦涩;趁贴则指诗文在形式技巧上过度雕刻以求贴切。所以无论是表现方法上以古为尚,还是形式技巧上的刻意求工,都是诗人凭借理性的雕钻结果,其后果是对诗人情性的压抑,甚至是对诗情的破坏。
最后,去蔽还表现为四个“不必”:“不必太着题,不必多使事。押韵不必有出处,用事不必拘来历”(《诗法》)。对于诗中的“着题”“使事”“押韵”“用字”,严羽并没有完全否定,因为它们也是诗的组成部分,他所否定的是将它们极端化,即“太”“多”“有”“拘”,使诗拘泥于这些因素。对于严羽而言,诗的本质在于吟咏情性,如果我们拘泥于这些因素,势必也会使我们的精神受到束缚,情性不能畅达。
经过一系列的去蔽和否定,严羽又从正面进行了揭示和肯定。
一方面,其认为应表现为“四贵”:“下字贵响,造语贵圆。意贵透彻,不可隔靴搔痒;语贵脱洒,不可拖泥带水”(《诗法》)。“下字贵响”意味着文字要有哀怨清澈之声,慷慨高歌之意,缠绵悱恻之情,这样的诗才适合吟咏;“造字贵圆”意味着文字要避免僻涩,既可娱心,又可感人,这样的诗才适合表现情性;而“意不透彻”,是因为情意混沌不解,语不洒脱是因为情意为功利所困。所以为诗之道,重在审美情感的获得,得之自然透彻、洒脱。
另一方面,其认为应表现为“三须”:“须参活句,勿参死句。须是本色,须是当行” (《诗法》)。“活句”“死句”之说指的是诗句不要拘泥于文词等外在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审美情感,只有文词者便是死句,有了审美情感,诗句便成了活句。“本色”即自然之色,诗歌要抒发的是人的最本质的情感(本性),所以它要用最本色的形式,只有这样,才能保全天趣,情感才能保全纯净。“当行”即恰如其分,诗歌形式不仅要自然,而且要恰如其分,因为自然地就应该是恰如其分的,不自然(即人为的雕刻)就会使事情失去平衡,从而事情就不再是事情本身,所以最自然的音韵就是吟咏——恰如其分的音韵,否则音韵要么散缓,要么急促,这就不是音韵了。
所以在妙悟诗的本质——审美情感的同时,严羽对审美情感在诗中的位置也要进行恰如其分的定位——否则诗便不再是诗了。
五、诗的有机整体观
“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诗评》)。如果意兴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审美情感,即情趣的话,理在这里就可以理解为理趣,词则是显现情趣、理趣的形式。在严羽看来,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失去了任何一方,诗都不再完美而入于病,南朝诗歌如此,本朝诗歌更是如此,唐诗则将三者融为一体以求平衡,汉魏之诗则无须追求,浑然天成,所以无迹可求。因此,严羽虽然反对以理为诗,但并没有否定理本身;虽然反对以文字为师,但并不否定文字;虽然反对以才学为师,但并不否定才学。他要做的是让理、文字、才学在诗中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这当然也包括审美情感。
这种恰如其分的位置感,其实显示了严羽关于诗歌的一种有机整体观,这种有机整体观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他强调的是五俗、五忌、四不必、四贵和三须,而不是更多或更少,为什么他强调性情的同时又强调词理,为什么强调别材、别趣的同时又强调多读书、多穷理……这些都在于他所面对的诗歌状态是一种失衡的状态,无论是去蔽也好,还是显现也好,他的目的就是让诗歌从失衡重新走向平衡,让诗歌的每一个部分都能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这集中地表现在他对文章结构的看法上,“对句好可得,结句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诗法》)。他的感慨不是空穴来风,他的诗歌理想也由此可见端倪。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具有强烈现实指向性的观点确实削弱了其理论内容的纯粹性和理论形式的体系化,但是这并不代表严羽对诗歌的思考完全是“想当然的”[11]和“列单子的”[11]。
综上所述,《沧浪诗话》从诗歌的本性出发,针对诗歌的现实病症,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观点,它虽然不是为了体系而著,与德国古典思想相比也不够体系化,但是它却有着与体系类似的或相得益彰的内在逻辑。
参考文献:
[1] 王运熙,顾易生,袁震宇,等.明代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之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412.
[2] 朱志荣.论《沧浪诗话》的理论体系[J].学术月刊,2009(2):88-94.
[3] 王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M].北京:中华书局,1993:2.
[4] 王弼.老子[M].北京:中华书局,1998:82.
[5] 彭富春.论中国的智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56.
[6] 朱谦之.老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3:36.
[7] 宗福邦.故訓汇纂[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793.
[8] 郭朋勘.《坛经》对勘[M].济南:齐鲁书社,1981:106,8,20.
[9]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10] 孔颖达.毛诗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57:48.
[11] 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 [M].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434,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