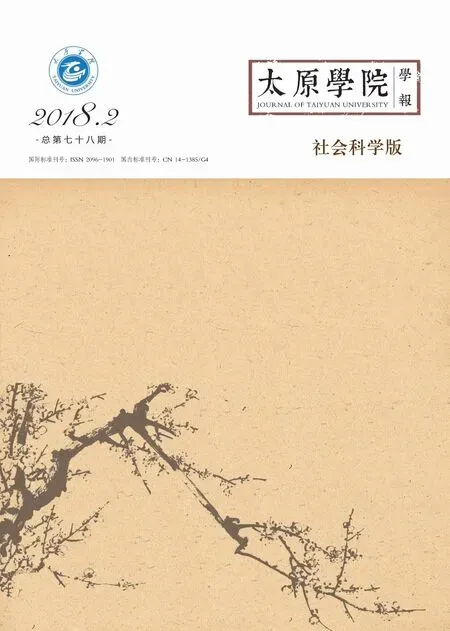当代戏曲文学的“文学性”的回归
——以莫言《锦衣》为例——以莫言《锦衣》为例
赵 璐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自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几乎每一次露面,这个讲故事的高手都会被问及新作的情况。终于,我们在2017年《人民文学》第九期上见到了翘首以盼的新作——戏曲文学剧本《锦衣》。《锦衣》的发表,不仅彰显了莫言“想成为一个剧作家的野心”,也让我们将目光移至这个一直游荡于研究者视野之外的文学体裁——当代戏曲文学。
中国的戏曲艺术灿若星河,宋元时期是古代戏曲的完全成熟阶段,成为中国戏曲史的“黄金时代”。由于当时诞生了大量的专业剧本作家,他们致力于戏曲剧本的创作,从而大大加强了戏曲文学的文学性。“自从中国戏曲有了文学这个基础之后,才出现了宋元南戏、元杂剧和昆山腔传奇等几次艺术高峰时期。可以说,没有戏曲文学这个基础,就没有中国戏曲的真正繁荣。”[1]44所以说,戏曲文学的文学性对古代戏曲艺术的推动与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代戏曲文学的文学性在某种意义上更体现为一种审美品格,这也是中国戏曲文学本身的肌理,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戏曲文学才能呈现出自身的情感和美感。王露霞指出:“戏曲作品中的文学性就是那种能够打动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的东西,是能够让我们怦然心动,引起我们不断惊叹和深刻反思的那种审美力量……使其艺术作品充溢着丰厚的人性魅力和审美价值。”[2]6戏曲文学的题材、主题、人物、结构、语言等要素统一在戏曲文学的内部,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闭合的文学系统,从而完成戏曲文学的文学性的自我指涉。《锦衣》之所以引起当代文坛广泛关注,正是在于剧本中展现的独特的审美品格。莫言在戏曲艺术中重新复活了他的动物王国,借“公鸡变人”的故事塑造了具有人性化特征的“神鸡”形象,并在颇具魔幻性的现代意识的指导下对“才子佳人”的模式进行了重塑。另外,莫言通过女主人公春莲的生命状态解码了晚清女性身上的女性意识,打破长期以来女性“失语”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莫言从戏剧内容、主题和人物三方面开拓了戏曲文学创作的能动性,从而实现了对当代戏曲文学的文学性的回归。
一、民间想象力传统的复苏
莫言一直强调自己“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创作立场,这种书写姿态是以“民间”的审美价值为取向,在民间视域下重新考察历史与历史洪流中人的生命图景。陈思和认为民间是个藏污纳垢的存在,它有着超越阶级的包容性。民间不仅作为莫言的创作立场,更是他作品中独特想象力的来源。当代戏曲文学的想象方式表现为以现实主义意识为主导,在日常逻辑的支配下对历史和当代生活秩序进行重构。但从想象力表现得充分与否来看,民间想象力的部分多被遮蔽。那么具体来说何为民间想象力呢?王光东总结出民间想象力的特点主要有二:其一人、兽、鬼、神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其二是动物、鬼神的形象具有人性化的特点;并认为“这样的民间想象一方面与民间底层的生活相连,另一方面又对抗现实中的不幸,依靠想象完成有希望的人生,浸透着浓郁的审美化人生精神。”[3]113
从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开始,莫言不断扩展民间想象力的部分,从故乡大地上流传的传说、故事中攫取超越现实空间的内容。莫言的故乡高密东北乡在古代隶属齐国,自古以来,齐人好谈怪力乱神,齐文化中有着浓厚的生命崇敬意识。在民间,很多动植物常被人们视为灵异之物。恩斯特·卡西尔指出“人在这个社会中并没有被赋予突出的地位。他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但他在任何方面都不比任何其他成员更高。生命在其最低级的形式和最高级的形式中都具有同样的宗教尊严。人与动物,动物与植物全部处在同一层次上。”[4]130在莫言小说中,有很多关于动物的想象性描述,动物的形象不比人类低贱,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动物的生存智慧、个性品格有着难以言说的神秘性和高明性。如《白狗秋千架》中的那只白狗,它有着非比寻常的感受力并极其通晓人性,是主人公真诚的守护者也是维系二人感情的红线。而《生死疲劳》中“众牲”狂欢的世界更诠释了人与动物之间相互转化的关系,西门闹转生后的动物均以人的视角观察和体验世界。在这里,人与动物的界限被打破,动物有着人的直觉和判断力,其行为所遵循的也是人类的日常逻辑。
在《锦衣》中,莫言将民间传奇与想象合体,在戏剧中将历史与民间传说并置于同一文本中。《锦衣》的故事原型为莫言小时候听母亲讲述的“公鸡变人”的故事:地主家小姐与一位身着锦衣的公子经常在房中幽会,不料被小姐的母亲觉察到。在母亲的再三逼问下,小姐不得不道出实情。母亲怀疑这身穿锦衣的公子为妖所变,于是给女儿设了一计:夜里公子来房里时,趁其不备偷偷将公子的锦衣锁入衣柜。小姐依照母亲所说锁了公子的锦衣,第二天天明时分公子欲离开,却找不到锦衣,只好无奈离去。等公子走后,母女俩打开衣柜一看,大惊,锦衣不在,衣柜里只剩一堆鸡毛。莫言十分喜爱这个诙谐诡异的故事,利用民间鬼怪文化的传统语境,以“公鸡变人”的故事为原型与辛亥革命的背景结合起来。这样极具创造性的艺术想象力在当代戏曲文学中颇为少见,更重要的在于它复苏了民间传说和故事的想象方式。莫言将神鸡与人并置于历史中,欲表达一种“今不如昔,人不如畜”的寓言性的历史慨叹,体现出莫言“万物通灵”的朴素理念。《锦衣》中的神鸡有着人性化的特点,它懂得主人的情绪变化,并像丈夫一般守护着女主人,它的行为方式均受人的生活经验所支配。如第八场【挑盐路上】的场景中,莫言用“神鸡救人”的人性化描写拉近了动物与人类的距离,神鸡在春莲遭人调戏之时奋勇救主,啄退了一群身强力壮的男性,庄雄才等一众小人最终落荒而逃。神鸡的“神”不仅仅体现在对人类的情义,更体现在能辨清这世上的善恶。神鸡身上的“善”反衬出作恶小人人性中的“恶”,从而体现出人世的荒诞与混乱。莫言选择众生平等的视域,把人与神鸡视为同等的生命体来观照。《锦衣》一改当代戏曲文学缺乏创造性的弊病,极尽想象之能事,发掘民间文化资源参与到文学创作中的价值。由此可以看出,民间想象力对于保全民族文学的文学性有着重要意义。尤其在我们的审美经验被日益西化的时候,当代戏曲文学的创作更应该汲取民间传说、民间资源、民间想象的内容。《锦衣》正是基于这种文学自觉的艺术追求,以民间立场对于历史和民间传说重构,在自由自在的民间表达中复苏了民间想象力的传统。
二、对“才子佳人”模式的消解与重构
自元明清以降,“自是佳人,合配才子”的爱情模式一直是古代文学中典型的爱情模式,在明清传奇和小说、戏剧中屡见不鲜。以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与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两部伟大的戏剧为例,在主题思想上都寄寓了作家“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理想。在封建社会中,“才子佳人”为自由的爱情而与封建势力斗争可以看作是一场爱情革命了,才子与佳人的结合也就表达着古代文人对反叛封建的社会价值和追求自由的人生理想的肯定。明末清初,出现了一大批以描写社会上青年男女爱情为主题的才子佳人小说,如《玉娇梨》《平山冷燕》《春柳莺》等。对于如何界定“才子佳人小说”,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才子佳人小说,至所叙述,则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故当时或亦称为‘佳话’。”[5]189纵观元明清的小说戏曲,“才子佳人”的模式大同小异,主要是:男女一见钟情,小人拨乱离散以及才子及第大团圆。莫言的《锦衣》袭用了才子佳人戏的框架,同时与广阔的社会生活紧密结合。《锦衣》的背景是辛亥革命时期,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季星官与好友秦兴邦巧妙化妆回乡策划暴动,路遇大烟鬼宋老三插草卖女,季星官心生爱慕之情。村中保媒拉纤者王婆与在县衙当差的侄儿王豹联手上演了一场好戏,巧舌如簧的两人骗得季星官之母季王氏娶宋老三之女春莲为儿媳。而春莲在经历了婆婆的责备、庄雄才的骚扰等一系列阻难后与季星官相恋,最终两人有了大团圆的结局。莫言无意于塑造传统类型的“公子”形象,也没有将“才子佳人”的结合局限在冲破封建藩篱的意义上,而是赋予人物形象复杂多义的内涵,并通过男女主人公美妙的结合来确认生命个体的存在价值。《锦衣》中对“才子佳人”模式的消解与重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才子”的形象内涵上。何为才子?据《汉语大词典》解释:“才子”多指有才有德的人,大都是风流倜傥、器宇不凡的形象,总体来说就是集才、情、貌、德于一身,是天才与情种共存的理想人格的化身,也因此受到“佳人”的青睐。《锦衣》在戏曲文本表层显像相似的模式里,摒弃了传统“才子”类型化的形象,而具有多义的形象内涵。男主人公季星官是在逃的革命者,是落难公子的形象。季星官半夜潜回家中,为了取得春莲的认可,用红布盖住鸡笼,自己假扮成鸡精,这才让春莲接受了他。“才子佳人”模式中,女性往往是男性受难者的避风港,然而春莲接受的“才子”并非是直观意义上的“才子”,在春莲看来,季星官实际上是公鸡的化身。洞房花烛夜时是公鸡相伴,遇到危险时也是公鸡三番五次相救,春莲与公鸡互怜互爱的行为在精神层面上达到了完美的耦合。公鸡与春莲相伴相依,公鸡处处履行男性对妻子保护的责任,所以当春莲与季星官两情缱绻之时,“佳人”春莲在精神上所青睐的并非是季星官而是公鸡,春莲实际上是将公鸡的情感转移季星官身上。此时季星官的身份是自己本身与公鸡双重身份的叠加。因而,季星官的“才子”形象所展示的多义内涵表现为革命者的“才、德”和公鸡的“真善美”的交织。
其次表现在对“才子佳人”结局的处理上。古代的“才子佳人”戏中男女主人公的结局多为大团圆的喜剧结局,基本是才子科举及第,借助仕途的顺利来扭转自己的处境,才得以与佳丽结下美好姻缘,这寄寓了封建时代读书人对于功名和美好姻缘的期待。如果说才子及第奉旨成婚带有某种封建性的意义的话,《锦衣》则试图通过革命的胜利消解大团圆结局的封建性。当刘四喊出:“他不是鸡精!他是季王氏的儿子季星官!”[6]38戏剧冲突达到顶峰,此时峰回路转,革命党们攻入县城,旧制度下的受益者此时不再专享权威,刚刚到达的矛盾临界点通过革命成功被巧妙化解了,革命的胜利也是才子佳人斗争的结果,用斗争的胜利消解了传统戏曲中借助“他力”的封建性意义。同时,《锦衣》中的尾声处理极富艺术性,春莲与公鸡在舞台上共舞,颇具优美抒情和魔幻色彩。季星官追逐春莲,春莲巧妙躲闪,季星官像盲人一样,扑了一个又一个的空,最终舞台上的鸡形与披着锦衣的季星官合二为一。张清华认为“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才子’与‘佳人’已不仅仅是个性意义上的完美,两者的结合也不仅仅是感性生命意义上的人格实现,而是一个既符合理性又符合道德、既具有个体意义又具有社会价值的独特而丰富的文化观念,它几乎体现了中华民族全部的历史的人生理想。”[7]11此时春莲与季星官的结合并不是借助功成名就实现的,“才子佳人”的结合不是冲破封建藩篱的封建性意义,而是寄寓着作家人性诉求的精神向度,体现着个体意义与社会价值的人生理想。当古怪的表演直接作用于读者的感官,简单的情境能够奇妙地跃升到形而上的超验境界,这种颇具魔幻色彩的情境能极大程度地唤醒读者的情绪体验,从而对读者产生更为持久的、更具震撼力的戏剧效果,让“才子佳人”的主题原型在颇具魔幻的艺术直觉中呼应了戏曲文学的文学性的回归。
三、打破女性“失语”状态
在中国几千年来的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社会里,男性话语成了中心话语。女性在男性本位文化中被雕塑成文静柔弱、逆来顺受的形象,被铸造成弱势话语的群体。女性被压抑、遮蔽、扭曲,变成男性麾下患有“失语症”的“他者”。在这样的语境中,女性要想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必须打破父权制加在她们身上的枷锁,通过语言的重新编码与整合,冲破原有制约女性“发声”的话语系统。而书写女性真实的生命体验,让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对于男性作家来说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莫言在创作《锦衣》时,将叙述的权力放归到剧中人物的身上,每个角色都在对话中自我揭示、自我阐发,此时的创作主体隐退到剧中人物身后,最大限度发挥戏剧人物的主体意识。莫言将女主人公春莲置于戏剧冲突中,春莲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恢复女性意识,从而完成自我构建。《锦衣》在很大程度上承继了《西厢记》《牡丹亭》那种对女性话语内在性的深入体察与探究,并试图以男性作家的身份打破长期以来女性“失语”的命题。在这个意义上,剧中的主要人物,王婆、王豹、季王氏、知县、庄雄才、宋老三等,都与春莲发生过冲突和斗争。被置于冲突中心的春莲,其勇于反抗、视死如归的性格渐趋明朗化。春莲从一开始的逆来顺受到最终的殊死反抗,其形象变化背后的内涵是莫言对被遮蔽了的女性生命存在的深刻挖掘与揭示。
春莲生活在宗法制男权社会的清朝末年,农村“男性中心”的观念依旧根深蒂固,施加给女性的道德指令是“三纲五常”里对男性权力的顺从。第一场【桥头卖莲】中,春莲出场时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柔弱女子,当宋老三为换银钱“插草卖女”,她试图扭转自己的境遇,但在“男性中心”的父权社会,她的命运遭遇了深刻的困境,她的女性意识处于压抑与沉寂的状态,只能发出“我的命好苦哇”的感慨。当春莲被王婆和王豹骗去季家与公鸡同入洞房,春莲的女性意识依旧处于压抑状态。这是因为在宗法制家族中,婆婆季王氏充当着权力的象征,女性在与封建家长的对话中处于“失语”状态,春莲对于婆婆的要求只能言听计从,否则,接踵而来的便是季王氏的厉声呵斥,但春莲被压抑的女性意识却在悄悄成熟。春莲此时正处于寻找自我的过程中,她不是没有“自我”,而是“自我”暂时被压抑,这种压抑不必通过他人来解除,而是可以通过纯自然的更替就能解除。
发展到第十一场【撞墙救鸡】时,春莲的女性意识开始复苏并释放。面对知县公子庄雄才威逼利诱,此时的春莲如待宰的羔羊无路可逃,无奈成为被男性“凝视”的客体。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将“凝视”纳入权力运作的系统中,并指出“这种凝视具备一种持久的、洞察一切的、无所不在的监视手段,能使一切隐而不现的事物变得昭然若揭,把整个社会机体变成一个可感知的、可控制的领域”。[8]240当女性被迫面对男性社会中无从逃避的“男性的凝视”后,她就被降格为男性的猎物,也会失去自我应有的活力。而春莲面对庄雄才的“凝视”,其作为女性的活力非但没有失去,反而激起了自身女性意识的觉醒。春莲不屈不挠、大张挞伐,大骂庄雄才:“我火烧胸膛咬碎银牙。难道这大清朝没了王法?难道这玉帝爷爷双眼瞎?难道如来佛把六道轮回、因果报应全废啦。任凭恶棍横行天下?快快放开我的鸡,要不然,我撞死在你面前。化作厉鬼将你拿。”[6]32-33此时婆婆的畏缩与她的勇敢形成反差,春莲纤弱的体质与她视死如归的精神亦形成巨大反差,春莲选择撞墙自杀这一自我身心粉碎的方式与命运作抗争。
伍尔夫指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在男人脑子里男性胜过女性,在女人脑子里女性胜过男性”。[9]120《锦衣》中春莲仿佛是男性霸权社会中的独行者,她为救鸡撞墙,用破坏自己的身体来表达对于霸权的不屈从,她对男性霸权话语的大胆挑战和对女性权力的捍卫,打破了男性将其变为股掌的玩物的“白日梦”,从而冲破了男性话语系统下女性长久被压抑的状态。春莲的心理变化和激烈的行为更像是一个女性剧作家面对屈辱时愤怒的表达,这种宣泄解构了传统社会的性别不对等的秩序,也打破了女性长久被压抑的“失语”状态。
四、结语
戏曲文学的各要素,不论是结构、主题、人物、情节、戏剧冲突上都需要不断创新。戏曲文学的文学性也是因时而变,不论是元杂剧还是明代传奇、小说,都具有本时代文学性特征,因而当代戏曲也有自身的文学性。当代戏曲文学发展之路举步维艰,作家要想凸显自己与众不同的声音,在叙事策略上必定要在传统戏曲的基础上继承与创新,这种转变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观念的更新,更重要的是关涉到当代具有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锦衣》中的“锦衣”不仅仅是季星官的隐身衣,也是莫言穿梭于传统与当代的暗道。莫言自觉承担了转变这种艺术观念的追求,以探索的方式继承了传统戏曲文学的文学性的内蕴,加之剧作家创作经验中独特的艺术手法,从而实现了当代戏曲文学的文学性的回归。
参考文献:
[1]王振伟.戏曲文学剧本的文学性[J].当代戏剧,1989(6):44-47.
[2]王露露.当代戏曲:呼唤文学性的回归[J].大舞台,2010(10):6-7.
[3]王光东.“民间想象原型”与近三十年小说创作[J].当代作家评论,2010(1):108-115.
[4]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130.
[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莫言.锦衣[J].人民文学,2017(9):4-39.
[7]张清华.论中国文学中的才子佳人模式[J].齐鲁学刊,1990(4):9-14.
[8]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240.
[9]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王还,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