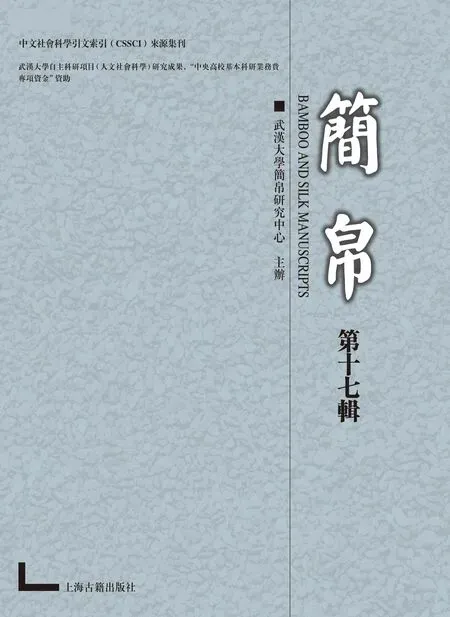禮樂概念的形成
——以楚簡爲中心
[韓] 李晟遠
關鍵詞: 樂邑 用樂 喜樂 禮樂 社會合并
《論語》中孔子對詩和禮樂業已有所論述,司馬遷也曾對此評論道“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然禮樂之所以並稱,禮樂論之所以盛行,則應是始於《禮記》。《禮記》中强調禮和樂彼此相對,卻也似陰陽一般相互作用、相互補完。然而孔子的禮樂論並未系統地流傳下來,《禮記》成書年代亦未成定論,是以禮樂的概念具體何時形成依然模糊不清。究其原因乃是和“禮”相比,“樂”的概念和文字用例並不清晰。漢字文化圈中,“樂”字有“音樂,樂器,演奏”之意的“樂(yuè)”,“歡喜、快樂”之意的“樂(lè)”,以及“喜好、欣賞”之意的“樂(yào)”等多重的解釋和使用方法。音樂之意大抵就是從這種樂器演奏所伴隨而來的一系列活動中派生出來的。《禮記》中“樂”含有歌詩、奏演、踊舞的綜合性的樂舞概念,這和今天的“樂”字中包含着音樂(music)的概念是類似的。而我們若想確認初期文字的例證,則不能止步於此。
1. 甲骨文中的“樂邑”
從文字學的角度來看,可確認的最早的“樂”字來自甲骨文。目前爲止,殷墟卜辭中可以在8個骨片中確認有9個關於“樂”字的用例。下面就是其中的幾個用例:
(1)-① 丙午卜,在商,貞,今日步于樂無災。
(《合集》36501∶5)
(1)-② 己酉卜,在樂,貞,今日王步于噩無災。
(《合集》36501∶5)
(2) 癸亥王卜,在樂,貞,旬無禍,王卜曰吉。
(《合集》36556∶5)
(3) 癸亥卜,在樂,貞,王旬無禍。
(《合集》36904∶5)(1)姚孝遂、肖丁: 《殷墟甲骨刻辭纂》,中華書局1989年,第1228—1229頁。
首先,(1)是商紂王帝辛初期“人方遠征”後,歸王都殷墟途中占卜的甲骨片。(2)嚴一萍: 《帝辛日譜》,《殷商史記》卷38,(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年,第1366頁。即,(1)-①是丙午日在商邑卜問今日去樂邑的途中可有災禍;同一個甲骨片所記録的(1)-②的内容,是在此三日後到達樂邑後卜問商王去噩邑的途中可有災禍的内容。“步于某”形式的甲骨用例約有400餘片,是典型的商王、諸侯外出、出行時貞人卜問的記録。此中關於樂的用例都是“-在樂”或“-于樂”的形式,這裏的“樂”應該是占卜時的場所或者出行的目的地,也就是樂邑。
雖然商代甲骨卜辭中所記録的“樂”字用例是與音樂無關的商國地名,但是我們卻無法斷言“樂”字本來就與音樂無關。但是卜辭的内容卻也僅僅展現了商代社會的一部分而已。甲骨卜辭是商王和少數卜官、史官所進行的特别的宫中儀式的産物,是以其内容也不可避免地局限在這些範圍之内。(3)張光直: 《商文明》,尹乃鉉譯,民音社1988年,第69頁。因此,即使某些漢字的原型來自於甲骨卜辭中的地名、人名、氏族名,也不能由此來斷定甲骨卜辭用例中所見的這些古文字的原意就當是如此。(4)饒宗頤: 《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香港大學出版社1959年。張秉權: 《甲骨文中所見人地同名考》,《清華學報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下册,1967年。丁山: 《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中華書局1988年。關於商代樂邑所具有的意義筆者日後將會有專文論述,而本文中筆者所想要著眼的則是和音樂關聯的“樂”的用例究竟始於何時。
2. 金文中的“用樂”
西周春秋時期的金文是商代卜辭之後的重要文字資料。包含戰國時代的青銅器金文資料,目前可以確認的關於樂的用例有68個。將其中重複的用例加以排除,羅列如下。
①樂乍(作)旅鼎。(4.1969 樂作旅鼎,西周中期)
②召樂父乍(作)婦妃寶也(匜),永寶用。(16.10216 召樂父匜,西周晩期)
③ 唯正月初吉丁亥,樂子嚷豧擇其吉金,自乍(作)飤簠,其眉壽,萬年無諆(期),子子孫孫,永保用之。(9.4618 樂子簠,春秋晩期)
④ 井叔叔采乍(作)朕文祖穆公大鐘,用喜(饎)樂文神、人,用祈福、多壽、誨魯,其子子孫孫永日鼓樂兹鐘,其永寶用。(2.357 井叔采鐘,西周中期)
⑦ 余武于戎攻(功),霝(靈)聞,用樂嘉賓、父兄、大夫、倗友。(1.51 嘉賓鐘,春秋晩期)
⑧ 唯王正月初吉庚申,自乍(作)永(咏)命(鈴),其眉壽無疆,敬事天王,至于父兄,以樂君子,江漢之陰陽,百歲之外,以之大行。(1.73-74敬事天王鐘,春秋晩期)
⑨ 唯王正月初吉,辰才乙亥,鼄(邾)公牼擇厥吉金,玄鏐膚吕,自作龢鍾(鐘),曰,余畢龏威(畏)忌,鑄辝(台)龢鍾(鐘)二鍺(堵),台(以)樂其身,台(以)匽(宴)大夫,台(以)喜(饎)者(諸)士,至于萬年,分器是寺(持)。(1.150 邾公牼鐘,春秋晩期)
⑩ 唯王正月,初吉乙亥,鼀(邾)公華擇厥吉金,玄鏐赤鋁,用鑄厥龢鐘,台(以)乍(祚)其皇祖皇考……台(以)樂大夫,台(以)宴士庶子,慎爲之名(銘),元器其舊,哉(載)公眉壽,鼄(邾)邦是保,其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1.245 邾公華鐘,春秋晩期)
①中的“樂”,②中的“召樂父”,以及③中的“樂子”都是各青銅器作器者的名字。典型的青銅器銘文開頭的格式首先是作器日的干支,接着是以“某乍(作)某器”的樣式來記録周王、諸侯、大夫等作器者的名稱和銅器的名稱。(6)松丸道雄: 《西周青銅器製作の背景》,同氏編: 《西周青銅器とその國家》,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年,第15頁。①中的“樂乍(作)旅鼎”和1978年河北省元氏縣出土的西周中期前段邢國的銅鼎上“攸乍(作)旅鼎”四字銘文的形式幾乎完全一致,可見此種刻鑄作器者和器名的形式當爲西周初期的銘文樣本之一。上海博物館所藏的青銅器③中所見的“樂子”很可能就是春秋中期宋大夫宋載公的後人“樂懼”,(7)馬承源: 《記上海博物館新收集的青銅器》,《文物》1964年第7期,第11頁。因此此處“樂”的用例也應當是指代作器者。(8)《左傳》成公十六年:“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于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衆所周知,古代中國的姓、氏、族(9)《左傳》隱公八年:“公問族于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大多使用動物圖騰、自然界的山川、樹木等物名和邑名相混用。(10)丁山: 《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張光直: 《商文明》第213—216頁。從前述的甲骨卜辭中指代邑名的樂,以及先秦文獻中指代人名的樂來看,(11)〔晉〕 杜預: 《春秋經傳集解》附《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大抵①、②、③中也是類似的用法。只是這些用例中的人名和“音樂”相關,還是作器者和甲骨文中的樂邑相關還不明確。包含①、②、③在内的“樂字金文”的銅器大多屬於較早時期的銅器,其種類也趨於多樣性,包含了鼎、匜、簠等器型。
⑦、⑧中雖然只是單獨出現了“用(以)樂某某”的辭例,但大部分卻是與“用(以)樂某某”和“用喜(饎)某某”“用祈某某”“台(以)匽(宴)某某”“台(以)喜(饎)某某”等一起出現的。即,這種表現通常是祈禱長壽多福,或祈禱“大夫、神人、諸士”能够愉悦地參與宴會和享用酒食。其中④中的“永日鼓樂兹鐘”和⑤中的“永寶日鼓”正是暗示了能够使其愉悦開心的招待方法。④—包含了從西周中期到春秋後期的銅鐘表面刻鑄的金文,是迄今爲止所見最早的“樂”字與音樂這個所指直接相關的文字。爲了避免重複,這裏只選擇了一部分用例,但是金文中關於樂的68個用例中就有56個是“用(以)樂某某”爲模本的青銅樂器金文,想來也絶非偶然。
3. 鼓、喜、樂
從金文中“喜樂”的用例可以看出,“樂”不僅從一般名詞發展成動詞,且“樂”字從原意中又擴展出了新的意義。其中從喜樂的概念升華爲禮樂的過程,則可以透過對楚簡的梳理加以觀察。前述金文用例中可以發現和“樂”一起刻鑄的“喜”字。“喜”有高興、快樂之意,也有愛好之意,常與怒、哀、樂一起並稱,是人類最爲原始的性情;(13)《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偶爾也與懼、憂等相對,古人常用其來表達自己的志向等積極正面的感情。(14)《論語·里仁》:“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左傳》宣公十二年:“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左傳》宣公九年:“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於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其中“怒”字最常與“喜”相對,所謂“喜怒不形於色”就是説君子不應將喜怒外露;(15)《左傳》宣公十七年:“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道家認爲喜怒乃是感情的過剩,會擾亂陰陽,是以將其稱爲道之過、道之邪;(16)《莊子·刻意》:“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淮南子·原道》:“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吕氏春秋·季春紀·盡數》:“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而所謂“桑中之喜”也常常成爲淫亂的代名詞。(17)《詩經·鄘風·桑中》:“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毛傳》:“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左傳》成公二年:“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正如《説文解字》中對“喜”的定義一樣,(18)《説文解字》:“喜,樂也。从壴,从口。凡喜之屬皆從喜”,段玉裁注:“古音樂與喜樂無二者,亦無二音。壴,象陳樂立而上見。从口者,笑下曰:‘喜也。’聞樂則笑,故从壴从口,會意。”“樂”作爲“喜”的同義字常常被混用、並稱。然而在大部分的文化中,其原型卻出乎意料地是從形而下學中發展出來的。
商代甲骨文的“喜”字是由鼓字的象形字“壴”和“口”字結合而成的。甲骨文中的“口”字表現爲口、皿二意。(19)唐蘭: 《釋壴》,《殷墟文字記》,中華書局1981年,第68頁。與“口”字結合表達“感歎、快樂、歌曲或咒術”之意;(20)白川静: 《漢字百話》,中央公論社1978年,第28—30頁。與“皿”字結合則表達“祭器、器物或盛在器物中的酒食”。(21)唐蘭: 《釋壴》第68頁。金文學者認爲“用喜某某”中的“喜”字通“饎”字,(22)白川静: 《金文通釋》卷4,白鶴美術館1973年,第316頁。張亞初: 《殷周金文集成引得》。這裏“喜”的“口”旁當理解爲“盛在器物中的飲食”。而金文⑨號用例中的“台(以)匽(宴)大夫”即是酒宴嘉賓之意。如此,“宴”句已經充分地表達了酒食招待之意,那麽“壴”旁與“皿”字結合之意就有重複,而與“口”字結合則表達“高興、快樂、喜悦”之意,也並不顯得違和。戰國時代出土的竹簡材料爲解釋“禮”的本質“快樂”和音樂之間的重要性,喜和音樂本質間的密切性,以及真正關於喜悦的表現究竟是始於何處提供了可能性。
① 笑,禮之淺澤也。樂,禮之深澤也。凡聲其出於情也信,然後其入撥人之心也够。聞笑聲,則鮮如也斯喜。聞歌謡,則陶如也斯奮。聽琴瑟之聲,則悸如也斯歎。
(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簡22~25)(23)李零: 《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② 笑,喜之薄澤也。樂,喜之[深澤也]。[凡]聲,其出於情也信,然後其入撥人之心也够。聞笑聲,則馨如也斯喜。聞歌謡,[則陶如也斯]奮。聽琴瑟之聲,則悸如也斯歎。
(上博楚簡《性情論》,簡13~15)(24)濮茅左: 《性情論》,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38—242頁。李零: 《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56頁。
郭店楚簡性情論的代表《性自命出》篇的簡文①和上博楚簡《性情論》的簡文②之間的内容相當相似,因此這可能是戰國時代最有代表性的性情論的論述。禮與喜雖不相同,但都是始於“笑”“樂”,通過音樂得以升華,因此真正的喜悦也當是始於“笑”“樂”。即,上述性情論是以“笑→喜→樂(歌謡→鼓樂器)→禮”爲過程展開的。是以,金文的“用喜”不論是表達“笑”“樂”之意,亦或是“酒食”之意,其本質當是與“喜悦”之意相通的。
4. 喜和樂
上述對鼓樂的起源、喜的起源及其與鼓的關係進行了考察,接下來將探討樂的意義,以及和喜、鼓之間的關係。《禮記》云:“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25)《禮記·樂記》:“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又云:“樂者,樂也”。(26)《禮記·樂記》:“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荀子·樂論》:“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這些經典中的“樂”字與金文用例中所確認的喜樂之義相互呼應。《吕氏春秋》中齊國的東郭牙答管仲云:“顯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27)《吕氏春秋·審應覽·重言》:“少頃,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叁色,顯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湫然清静者,衰絰之色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淮南子》云:“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筦絃之音”,(28)《淮南子·泰族》:“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鍾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絰哭踴之節。”可見喜樂的根源乃始於以鐘鼓爲代表的音樂;而《詩經》中的“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也表達了喜宴的喜樂。(29)《詩經·唐風·山有樞》:“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内,弗洒弗埽。子有锺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然而演奏樂器和唱歌跳舞並不是單單爲了“快樂”的喜事。音樂始於感情,是以“喜怒哀樂”都可以用音樂來表現。(30)《禮記·樂記》:“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綏。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鐘鼓不僅也運用在生死攸關的戰争之中,就連一般生活中的悲傷之事,(31)《詩經·小雅·鼓鍾》:“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鼓鍾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鍾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特别是喪禮、葬禮等喪事中也常常需要用到鐘鼓。(32)《周禮·地官·鼓人》:“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鼓。”《周禮·春官·小師》:“小師,掌教鼓、鞀、柷、敔、塤、簫、管、弦、歌。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飨亦如之。大喪,與廞。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朄。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周禮·夏官·太僕》:“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贊王牲事。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大喪,始崩,戒鼓傳達於四方。窆亦如之。”音樂活動和交織着喜怒哀樂的人類活動緊密相關。因此,不同的情況,音樂的情調、形式、内容也有所不同。喪事時需要“敬謹”“悲哀”,(33)《禮記·曲禮上》:“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此時“喜樂”之情需要絶對的禁止,(34)《禮記·曲禮下》:“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禮記·檀弓下》:“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論語·述而》:“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論語·陽貨》:“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没,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論語·子張》:“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若是不能慎重地區分哀和樂,則會招來災禍。(35)《左傳》莊公二十年:“冬,王子頽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頽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二十五年春……宋公享昭子,賦《新宫》。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兹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儘管如此,通過文字、圖像、考古材料所窺見的古代中國的“樂”爲何唯獨被“喜樂”之意牢牢占據?
周敬王的大夫趙簡子在論述治民論和性情論時,認爲好、惡、喜、怒、哀、樂是人類最原始的感情。這其中爲我們理解喜樂和音樂的關係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視角。
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此性情論中所提及的要素明確地分爲“好-喜-樂-陽-福-賞-生”和“惡-怒-哀-陰-禍-罰-死”兩個好、惡的範疇。以生存和喜樂、幸福和贊賞爲志向,以死亡和悲傷、災殃和刑罰爲忌諱,此爲人類的本能;與哭泣和戰鬭相比,選擇歌舞和喜樂,亦是人類的本心。是以,《禮記》有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荆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相反,“樂有歌舞”中的喜樂則包含了全部的歌舞活動,而這裏喜樂被等同於音樂。“喜有施舍”所表達的則是喜宴中的樂舞、祭禮儀式,治者和主君的恩德和其施與百姓賓客的救恤、鄉飲酒禮、以及各種免除令和政治後援保障時的喜悦之情。
“學而時習之不亦説(悦)乎”的悦,是個人主觀上、精神上的喜樂,而“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樂,則是與朋友共賞樂舞和分享酒宴(36)《詩經·小雅·鹿鳴》:“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的互惠的、集體的喜樂,(37)《論語·學而》:“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因此以食客三千聞名的春秋四君子之一的平原君,其“喜賓客”的喜,應當就是“喜施”之意。(38)《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項羽雖成就滅秦霸業,卻僅僅五年就因劉邦而卒亡,司馬遷評價他“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而司馬遷在《高祖本紀》中雖對漢興大義加以評判,卻未對高祖劉邦個人作出評論。但是《高祖本紀》開篇的人物評價中卻暗示了劉邦的特長。即,司馬遷認爲劉邦“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史記》中將高祖描述成爲一位對人傑和任俠包容施舍,撫慰秦漢之際疲敝的人民,建立新的統治秩序基礎的形象,就如高祖入關後舉辦喜宴的故事中也可以看出其寬容喜施的一面(從某個角度來看,高祖劉邦正好可以和漢武帝相互對照),這或許就是司馬遷心目中理想的皇帝形象。而這在某種程度上不就是再現了“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賢良,順民所喜”的商湯王嗎?
是以,喜樂從個人的性情論擴展成團體、社會的範圍時就上升爲公共的喜樂,超越了本能的維度成爲了社會共有的意識目標和理想。對於在惡劣的外在條件下生存的古人來,比起喜樂,憂懼才是他們常常所面對的。史前遺物中人物相幾乎都是無表情,或是因苦痛而扭曲,(39)金秉駿: 《神之笑,聖人之樂——中國古代神聖概念再檢討》,《東洋史學研究》2004年86期,第15—16頁。這正是對充滿憂懼的古代社會自然的反應。因此,古人迫切地追求喜樂,正是因爲現實中的遥不可及,喜樂或許是只有神和聖人才能實現的世界。(40)金秉駿: 《神之笑,聖人之樂——中國古代神聖概念再檢討》,《東洋史學研究》2004年86期,第15—16頁。
然而公共喜樂的原型卻始於質樸。能够緩解自身的饑渴,向神奉獻簡單的飲食,用質樸的樂器傳達祈福,這就是公共喜樂的開始。在這樣的條件下禮開始萌生了,這就是所謂的“夫禮之初,始諸飲食”。(41)《禮記·禮運》:“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男女、老少、職分有别,相互扶助、信賴的“天下爲公”的世界,孔子冀望的“大同世界”,從某種程度上來看也是公共的喜樂。新石器時代以後,政治、經濟、社會、身份分化快速發展,原始共同體的理想不過是一個烏托邦式的幻想,(42)陳正炎、林其錟: 《中國大同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民衆所傳唱的歌謡或許也只是對公共喜樂的憧憬而已。
5. 從喜樂到禮樂
目前爲止,我們討論了“樂”所具有的地名、樂器、喜樂的意義及其演變的過程。準確的時間點雖然還不明確,但從春秋戰國時代到漢代之間所編著整理的先秦、秦漢時期的樂論中,“樂”已經是“音樂”之意了。從最近出土的戰國時代簡牘材料中喜樂和音樂的綜合用例中,或許可以讓我們對現存的先秦時代的樂論有一些新的理解。
(1)
① 聞道而悦者,好仁者也。聞道而畏者,好義者也。聞道而恭者,好禮者也。聞道而樂者,好德者也。
(郭店楚簡《五行》簡50)
② 善其節,好其容,樂其道,悦其教,是以敬焉。
(郭店楚簡《性自出命》簡21)
③ 凡憂思而后悲,凡樂思而后忻,凡思之用心爲甚。
(同上,簡31,32)
④ 凡至樂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哀樂其性相近也,是故其心不遠。
(同上,簡29,30)
⑤ 喜斯陶,陶斯奮,奮斯詠,詠斯猶,猶斯舞。舞,喜之終也。愠斯憂,憂斯慼,慼斯歎,歎斯辟,辟斯踴。踴,愠之終也。
(同上,簡34,35)
(2)
① 凡古樂龍心,益樂容指,皆教其人者也。
(同上,簡28)
② 聞君子道,聰也。聞而知之,聖也。聖人知天道也。知而行之,義也。行之而時,德也。見賢人,明也。見而知之,智也。知而安之,仁也。安而敬之,禮也。聖,知禮樂之所由生也。五[行之所和]也。和則樂,樂則有德,有德則邦可興。
(郭店楚簡《五行》簡26~29)
③ 仁,内也。義,外也。禮樂,共也。
(郭店楚簡《六德》簡26)
④ [性生仁 仁生忠 忠生信 信]生德,德生禮,禮生樂,由樂知刑。
(郭店楚簡《語叢一》簡25)(43)李零: 《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
(3)
① 笑,喜之薄澤也。樂,喜之[深澤也]。[凡]聲其出於情也信,然後其入撥人之心也够。聞笑聲,則馨如也斯喜。聞歌謡,則陶如也斯奮。聽琴瑟之聲,則悸如也斯歎。
(上博楚簡《性情論》簡13~15)
② 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五至乎?物之所至者,志亦至焉。志之所之者,禮亦至焉。禮之所至者,樂亦至焉。樂之所至者,哀亦至焉,哀樂相生。君子以正,此之謂五至。”
(上博楚簡《民之父母》簡3~5)
③ 昔堯處於丹府與雚陵之閒。堯賤施而時時,不勸而民力,不刑殺而無盜賊,甚緩而民服。於是乎方百里之中,率天下之人就,奉而立之,以爲天下。於是乎方圓千里,於是於持板正位,四向,和懷以徠天下之民。於是乎始於堯天地人民之道。與之言政,悦簡以行。與之言樂,悦和以長。與之言禮,悦薄以不逆。堯乃悦。
(上博楚簡《容成氏》簡6~8)(44)(3)-①,濮茅左: 《性情論》,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第238—242頁;(3)-②,濮茅左: 《民之父母》,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8—162頁;(3)-④,李零: 《容成氏》,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第254—256頁。
戰國時代的郭店楚簡(1)中“樂”的用例與西周時代以來的金文材料中的喜樂是相同的。(1)-①、②所揭示的“樂”的意義和既有的儒家經學中的道德論觀點一致,(45)《禮記·樂記》:“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1)-③、④、⑤則是典型的性情論觀點,喜怒哀樂都是從基本的人類性情中發端,强調至樂就是至悲的終極一致的性情普遍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前面所引用的(3)-①的性情論也是如此。特别是(1)-⑤中對“哀、樂”的論述與《禮記》中的一段故事緊密相關。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
(《禮記·檀弓下》)
這個故事中,喪禮所使用的“踊”展現了送别死者的家屬們的極度悲傷的表情,而以孔子爲代表的儒家一向對過度的性情表達有所警戒,因此提出了警惕“喪之踊”的主張。(46)《禮記·檀弓上》:“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踴有節。’”《禮記·檀弓下》:“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辟踴,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愠,哀之變也。”子游的性情論也不亞於這段禮道論。子游認爲人類喜樂的性情是以“喜-陶-詠-猶-舞”來遞增的,也就是(1)-⑤所謂的“舞,喜之終也”。然而,如(1)-④所説的至樂必悲,可見喜樂的極致是悲哀,而悲哀以“愠-戚-歎-辟-踊”來遞進,悲哀的極致就是踊。這正是孔子所謂的“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喜樂和悲哀就像陰陽一樣相生、相通,循環不止。因此,“舞踊”取自於極致的喜樂和悲哀,既相克,又相通。上述故事中,承認了人類的性情變化,對極端的性情予以警戒,這其中有悲哀與喜樂可以互相轉换的生活智慧,也强調了節制性情的禮道的重要性。若是將性情漸變過程加以分離,則可以成爲像(1)-⑤一樣的獨立的性情論。前述《左傳》中春秋時人的性情論雖也可見端倪,但若以系統化的禮樂論的發展和樂論的成熟爲整理樂論的着眼點的話,那麽最近以郭店楚簡的樂的用例中,喜樂和音樂的複合使用爲主要立足點的樂論研究則與此一脈相通。(47)李天虹: 《〈性自命出〉中的樂論》,《郭店竹簡〈性自命出〉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3頁。
郭店楚簡(2)的用例是典型的儒家禮樂論。和禮制典章儀式的一環相比,樂通常被認爲是禮制的附屬或是下層概念,(48)栗塬圭介: 《中國古代樂論の研究》,大同文化大學東洋研究所1978年。音樂的現時性所不能局限的絶對道德律内化在了音樂和樂律中,(49)崔振黙: 《中國古代樂律的運用和禮制》,《東洋史學研究》2004年第89期。然而這種樂論觀點都是集中於樂的“音樂性”方面。但是,(2)-②中的“聖,知禮樂之所由生也”,由此乃得出“五行之所和也。和則樂,樂則有德,有德則邦可興”的結論相接,由此可以瞭解到作爲禮樂論的基礎的樂的“喜樂、和樂”之意是多麽重要。這就和我們目前爲止所探討的樂的社會性是一脈相承的,也就是説,與堅持從社會性層面理解與禮、樂的先行或並行概念相比,此種觀點更有説服力。而(2)-④中所揭示的以“性→仁→忠→信→德→禮→樂→刑”爲立論基礎的話,派生出禮樂的德也是始於人類的性情,其結果禮、樂、刑亦起源於性情之中。
戰國時代的上博楚簡則對性情和禮樂的關係有更具體的暗示。(3)-①整理出的“笑→喜→樂→禮”也可以進一步解釋爲“喜-樂、樂-禮”,可以看作是“樂”從性情論中的喜樂向禮樂過度的過程。(3)-②中也可以看到喜樂和禮樂的混用。(3)-②可以看作是現存的《禮記·孔子閒居》《禮記·大學》《孔子家語·論禮》等記載的所謂“民之父母—五至—三無”論的一部分。“民之父母”的真諦是“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五至爲“至志—至詩—至禮—至樂—至哀”,三無是“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而貫通“民之父母—五至—三無”論的核心正是禮樂。上博楚簡中“五至”的“禮—樂—哀”的關係中,樂實際上是禮樂和喜樂的混用,也就是説其證實了“禮—樂、樂—哀”的關係。(3)-③中使人民自覺地服從並確立統治權的堯帝,則正是施展了“政—禮—樂”的統治手段,這正好再次印證了我們前面提到的以禮樂作爲統治基礎的觀點。和直面春秋戰國的變革,通過真摯地探索、省察人類和自然發展而出現的諸子學一樣,(50)李成珪: 《諸子之學和思想的理解》,《講座中國史》Ⅰ,知識産業社1989年。這些經文和簡文不僅比較系統地反映了古代中國“樂”的概念的發展過程,同時也反映了性情論和禮樂論從混用到分化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