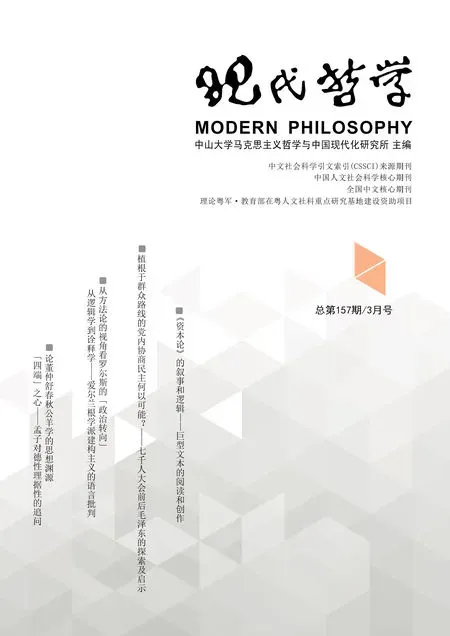“见证”的双重意义
——论海德格尔的“见证”之思
汪隐峰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赋予“见证”(Bezeugung)一个枢纽性的地位。在他看来,此在的本真生存是正确地理解此在这一存在者,因而理解存在本身的唯一途径;唯有依赖某种现象的见证,此在的本真性才是实际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一种理论的构想)*[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69页。。据此,Antonio Cimino认为,见证“是整个《存在和时间》的方法论和主题框架的一个决定性的组成部分”*Antonio Cimino, “Attestation and Facticity: On Heidegger’s Conception of Attestation in Being and Time”, in Journal of the British Society for Phenomenology, 44:2, p. 181.,甚至可以说是“哲学的终极基础”*Ibid., p. 190.,如果《存在与时间》缺乏这一见证的维度,其整个生存论分析就失去了现象上的基础而沦为理论的玄思。海德格尔之后(或者说在奥斯维辛的灾难之后),“见证”成为欧陆思想界的重要话题,列维纳斯、纳贝尔德(Jean Nabert)、保罗·利科、德里达、阿甘本都从各自的视角思及见证。
但在《存在与时间》中,“见证”概念又是一个极度缺乏澄清的概念。这首先可以归咎于海德格尔“并未对‘见证’给予特别的关注,也没有明确和扩展的论述来界定他自己对这个概念的使用”*Ibid., p. 181.。其次,应归咎于“见证”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前-概念”特征:海德格尔引入见证概念的初衷本就是为“理论层面上的生存论分析”寻找“现象上的根基”,这一现象本身很难被概念、语词所把捉。上述双重原因使得见证概念在《存在与时间》阐释中备受忽略,总是被当成几乎自明的东西一带而过。
鉴于《存在与时间》中“见证”概念的枢纽性与模糊性,本文将直面这一概念本身。作为下述分析之引导线索的是“见证”一词本身所蕴含的双重语义。“Bezeugung”的动词形式“bezeugen”来自动词“zeugen”,在日常使用中,它既意味着“证实”,又意味着“生产”。以之为线索,本文将揭示出海德格尔见证之思所蕴含的双重理解可能性,即“作为本真性之证实的见证”与“作为本真性之生产的见证”,并强调后一意义的基础性。
一、作为证实的见证
在日常语境中,“zeugen”首先意味着“证实”“作证”,例如“空无一人的街市证实了经济危机的严峻”、“证人的作证向法官、观众揭示出了罪犯的残忍”等。事实上,从该语义来理解海德格尔的“见证”是最常见的阐释方式,这种观点实际上或隐或现地蕴含了如下三个有争议性的主张。
1.在“证实”意义上的见证是指:通过一个可通达的现象“A”而指示出另一个难以通达的现象“B”,“A”就是证实“B”之可能的“证据”“标志”“症候”,就像我们可以通过对某人“犯罪证据”的寻找而证实其犯罪事实。依此来理解《存在与时间》中所谓的“本真能在的见证”(Bezeugung eines eigentlichen Seinkönnens),意味着一种抽象的理论结构,即此在在生存论层面上的(existenzial)本真能在之可能性,需要一种此在生存活动层面上的(existenziell)实际经验来对它进行证实。对该见证的寻求似乎就是对某一种现成证据的寻找。若这一证据被寻获,就意味着此在在实际的生存活动层面也具备本真能在的可能性,本真性概念本身得以证成。*Cf. Carol J. White, Time and Death: Heidegger’s Analysis of Finitude, ed. Mark Ralkowski, Aldershot: Ashgate, 2005, p. 107; Jan Aler, “Heidegger’s Conception of Language in Being and Time”, in Martin Heidegger: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 3,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21; Christopher Macann, “Who is Dasein? Towards an Ethics of Authenticity”, in Martin Heidegger: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 4,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230.
2.在许多论者看来,“此在本真能在之见证”这一事实恰恰意味着“常人自身并未具有这样的支配性,以至于此在向自身的回返以及此在对自身存在的本真可能性的把握是不可能的”*Richard Sembera, Rephrasing Heidegger: A Companion to “Being and Time”,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2007, p. 163; Cf. Michael Watts, The Philosophy of Heidegger, Durham: Acumen, 2011, p. 82.。也就是说,日常沉沦着的此在之所以能够证实“自身本真生存的可能性”,得益于“此在之沉沦的不彻底性”。只有主张此在的沉沦是不彻底的,在日常此在的生存(它首先和通常便是非本真的)中才可能有某种本真生存的指引、迹象、征兆。进而言之,此在沉沦的不彻底性恰恰体现在日常此在对自身本真能在的逃避之中,因为“回避”内在地包含“回顾”:对某物的回避,已经蕴含了对那回避之物的某种前反思的理解和唤起。例如,某人对某件不堪回首的往事讳莫如深,但他的这种决绝的回避态度,恰恰意味着即使事到如今,这件事对他而言仍然不是“无所谓”,而是仍旧深深地镌刻在其内心深处,以至于他的每次刻意回避,同时就是旧事的涌上心头。这意味着他尽管在日常生活中压制着这件往事,但这种压制从来都没做到彻底忘怀的地步。对于日常此在之生存处境而言,亦是如此:日常此在的“逃避”,恰恰意味着日常此在总以某种方式对其所避之物即本真生存有所理解(尽管这种理解是非反思的、非专题性的)。海德格尔说:“从存在论上说,唯由于此在在本质上已经被属于此在的那种展开状态带到此在本身面前,此在才可能在它面前逃避。”*[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前揭书,第259页。以沉沦为其基本动向的日常此在,即使它总已陷入常人自身的支配中,但它仍然已经以某种方式知晓了其自身(实际上是陷于常人统治下的自身)与本真自身的区别,它的逃避与沉陷恰恰是这种知晓的“见证”。这种对自身本真能在之可能性的见证经验,可以被刻画为一种“在作为常人自身的非本真之生存中的持续的‘自我察觉’现象。”*Richard Sembera, Rephrasing Heidegger: A Companion to “Being and Time”,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2007, p. 163.
3.这种证实现象的存在揭示了日常此在与其本真状态之间的某种连续性。John Macquarrie在论及此在之生存转变时认为,从一种生存状态到另一种生存状态之“转变”有三种可能性:一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B取代了A;二是不变因而也就不会转变,A与B都各自持自身;三是A转变为B,作为真正意义上的转变,它是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第三种情况正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之生存转变:一方面“在转变过程中得到维持的是……他作为‘在世存在’的基础存在论结构,但在存在者层次上来说,他的存在完全被重新定向了;因此,存在着一个与过往的真实断裂,他既是同一个人,同时也是一个不同的人”*John Macquarrie, An Existentialist Theology: A Comparison of Heidegger and Bultmann,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73, p. 132.;另一方面,如果从非本真状态到本真状态的转变是可能的话(John Macquarrie认为海德格尔与基督教思想都承认这一可能性),那么,两种生存状态之间必然存在着“连续性”。我们正在寻找的此在本真能在可能性的见证,其实质正是这一连续性的证实,若无此证实现象,此在的日常状态与本真状态之间便如隔天渊,此在的生存转化也将不可能。
综上所述,“作为证实的见证”实质是此在在实际生存活动层面上所经验到的、一种能够证实此在本真生存可能性的现象;这一经验之所以可能,是缘于日常沉沦的不彻底性;凭借这一实际经验的证实,此在的本真性便不再是一种理论思辨的结果,而是具有现象基础的、绝非任意的生存论概念,此在之生存转变也得以可能。尽管不少《存在与时间》的阐释者都持此种解释并停留于这种解释,但这种解释实际上不是一个充分的解释。若仅只固执“作为本真性之证实的见证”这一种阐释路向,它将不得不面临着一些解释上的困难。
1.上述证实观念仿佛认为对此在之本真能在的见证,可以一劳永逸地被证讫,就像日常语境中,当我一旦找到了某人的犯罪证据,那么对他作为罪犯的指证便已经完成,在后续各种审判中,无需再行寻找便可以不断地援引既有的证据链。但这仍然是一种“非此在式”的理解方式。首先,“见证者”及“其所见证者”之间的关系,绝非两个现成实体之间的关系(例如“结冰的湖边证实了寒潮的来临”)。一方面,就“其所见证者”而言,有待见证的此在之本真状态不是某种隐藏着的、有待实现的理想人格。另一方面,那可以充当证据的现象即良知*依据Kasowski的考察,在德语中,“Gewissen”最初是对拉丁语中“testmonium”的翻译,后来才被转为对拉丁语“conscientia”的翻译,因此,“Gewissen”一词的源始含义本就是“见证”。Cf. Gregor Bartolomeus Kasowski, Conscience and Attestation: The Methodological Role of the “Call of Conscience” (Gewissensruf) in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é de Montréal, 2011, pp. 255ff.不“只是纯然经验性的事实或某种人类的举止”,也不是“现象学为了确证其分析而能够识别出来的人类的可被观察之特征”*Antonio Cimino, “Attestation and Facticity: On Heidegger’s Conception of Attestation in Being and Time”, in Journal of the British Society for Phenomenology, 44:2, p. 188.。作为此在本真能在之见证的良知本身尚待“倾听”才能成为实际的。由此,见证活动的“意向性”结构之两极都是未来的,而非现成的。基于日常的存在观念,甚至可以说见证这一意向活动的两极都“不存在”,都是“无”。其次,此在之本真性与非本真性之间的关系,并非是两个现成的、静止的端点。本真性只是非本真性的变式,此在的本真生存构成了对此在日常沉沦趋向的逆行、反运动(Gegenbewegung),它需要被持续地施加力量才能被保持,而不是某种可以被一劳永逸地跨越过去的彼岸理想世界。因此,此在对自身本真能在的见证,不是在某一个时刻可以被一劳永逸地证讫,而是要时刻地保持在这种见证活动中。
2.表面看来,对证实的要求正是现象学的本性(若非如此,便沦为思辨哲学的纯粹体系建构)。然而,只停留在这种证实的观念,仍是将海德格尔所理解的现象学过分简单化了。上述证实观念预设了一种定见:此在生存论分析必须基于某种实际的、现成可得的经验,生存论分析所要做的只不过是反思这种经验,并将其中“普遍必然的超越论结构”即此在的“生存论建构”给抽象出来。但上述方法对于海德格尔的此在分析工作来说是难以奏效的。海德格尔不断强调,对此在源始真理的把握只有基于一种本真的此在才是可能的,而此在的本真性对于日常此在而言无论如何都不是现成可得的。现象学描述之现成基础的“缺失”,在海德格尔的“死亡现象学”中达到了顶峰,其所要求的源始死亡之经验恰恰是不可通达的*Iain Thomson, “Death and Demise in Being and Time”,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ed. Mark A. Wrathal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261-262.。考虑到日常此在首先和通常是非本真的,现象学分析的基础对于日常此在而言不是现成可得的经验,而毋宁是其生存的转变。
3.如果坚持“日常无差别状态”与“非本真状态”之间存在着区别的话,那么,上述证实观念与海德格尔对此在日常状态的刻画相冲突。首先,无论是从义理还是文本上看,海德格尔都明显地区分出了“日常无差别状态”与“非本真状态”。在海德格尔那里,本真的此在“选择去选择自身存在”(Wählen der Wahl eines Selbstseins)。对此,可以援引Béatrice Han-Pile的做法*Béatrice Han-Pile, “Freedom and the ‘Choice to Choose Oneself’ in Being and Time”,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ed. Mark A. Wrathal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97.,将其中的两个“选择”分别命名为C1与C2:C2是“对自身存在的选择”,C1是“对上述选择的选择”。就我们是否做出“对自身存在选择”而言有三种可能性,同样是对此在在生存活动层面上的三种可能的生存样式形式化表达:一是本真状态[C1(C2)],亦即对“对自身存在的选择”的“选择”;二是非本真状态[C1~(C2)],亦即明确地选择了“不选择自身存在”,它在其本己自身面前逃离;三是无差别状态{~[C1(C2 ⊕ ~C2)]},这是日常此在首先和通常所处的那种悬而未决的、无所差别的浮游状态。在此,可以明显看到“非本真状态”与“无差别状态”并不是同一种状态,这种区分也可以在海德格尔的相关文本中找到证据*[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前揭书,第66、79、98页。。其次,如果坚持认为日常此在中有着某种现成可得的、对其本真能在之可能性的见证,那无异于断言日常此在并非首先处在一种漠然的、未作出抉择的状态,而是首先和通常便已经处在了“明知故犯”的境地:虽然它能够见证自身本真能在,但仍然在本己自身面前决绝地逃离。这明显地与海德格尔对此在日常状态之刻画不符。
二、作为生产的见证
由上节可知,仅仅基于作为“证实”的见证观念,尚无法充分理解海德格尔所说的“本真能在之见证”。为此,需要再引入见证一词所蕴含的另一重含义来深化对此概念的理解。在日常语境中,zeugen也意味着“生产”“产生”,例如“她生了一个孩子”、“这件事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这个国家产生了许多伟大的艺术家”等。这一含义对于理解海德格尔的“见证”概念至关重要。Richard Sembera说:“我们所要寻求的实际本真性之Bezeugung是一种行为举止,藉此此在既‘生产’又‘证实’了其本真性之本己可能性。”*Richard Sembera, Rephrasing Heidegger: A Companion to “Being and Time”,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2007, pp. 163-164.Daniela Vallega-Neu也敏锐地洞察到:“见证不是单纯的被动性;‘见证’的德文词是‘Zeuge’,它衍生自‘zeugen’,后者不仅表示‘见证’,‘作证’,而且也有‘生育’的意思。”*[美]瓦莱加-诺伊:《海德格尔〈哲学献文〉导论》,李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5—126页。这实际上也为海德格尔自己所指出,在1936年的讲演“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中,海德格尔对见证问题作出重要评论:“‘见证’(Zeugen)一方面意味着一种证明;但同时也意味着:为证明过程中的被证明者担保。人之成为他之所是,恰恰在于他对本己此在的见证(Bezeugung)。在这里,这种见证的意思并不是一种事后追加的无关痛痒的对人之存在的表达,它本就参与构成人之此在……人之存在的见证以及人之存在的本真实行(Vollzug),乃是由于决断的自由。”*[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8页。本节即以此段落为阐释基础,并不断返照《存在与时间》中的相关论述,来阐释作为本真性之生产的见证。
1.见证不是对早已存在着的某物即本真能在之可能性的一种“事后的表达”(例如,在我掌握某种证明手段之前,该定理的真理性已经是现成的、确凿无疑的,我的证明活动不过是一种“事后的表达”)。即使认为日常此在之生存总已经有了本真生存之“证据”(亦即总已经为良知所唤及),但这一“证据”却只有对那些实行着见证活动的此在而言,才能成为本真生存的“证实”。对于那些未实行此种见证活动而言,这种证据是无意义的,与之相应的见证关系也无从说起。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举过一个例子:在农耕时代,刮起南风预示着即将下雨,南风是下雨的标志;但这种标志的功能并不是被农民人为地安设在、附属在一个现成的气流现象上面的;毋宁说,正是农作活动本身所牵连出的意义总体,才使南风作为南风被揭示出来;甚至可以说,唯有基于活生生的农作之操劳,南风才“存在”。 “南风却绝不是首先作为仅只现成的东西存在,而后才偶尔承担起预兆的功能。毋宁说,恰恰是农耕的寻视以有所计较的方式才刚揭示出南风的存在。”*[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前揭书,第118页。
因此,不是日常此在通过某种现成经验而被动地证实了本真能在之可能,而毋宁是下了决心的此在,主动地“生产”了本真能在之可能。那充当本真能在之见证的不是某一现成现象,而恰是本真生存的实行,见证活动中的“那一有待见证者”自身就在这种见证活动中被“生产”出来。这正是见证一词的实行意义(Vollzugssinn):日常的此在如果要将某一证据(畏之经验、良知)作为“本真能在之可能性的见证”来把握,需要植根于特定的操劳即对自身的本真操劳之中,若根本上缺乏这一操劳(这一操劳的实质恰恰就是本真生存的实行),那么这一“证据”将无法被把握为见证,它对于未实行此种生产义之见证的此在即日常此在而言是锁闭的。
2.按照常理,我们必定是基于已观察到的事实进行合理地推论,以之作为我们下一步行动的根据。但这并不适用于此在对其本真能在的见证活动,因为日常此在对事实的理解与推论都完全地持留于常人所开放出来的可能性之中,都在一个不断修补圆融的“世界观”体系中得到解释。一种对常人统治之倾听的瓦解,对于日常此在而言,必定显示自身为无可理喻的断裂。因此,日常此在对自身本真能在之“生产”,绝不是合理的、有据的,而毋宁是“决断的自由”之展开,是以深渊为根据的起跳与决断,是一种确信(überzeugung)。
这种确信是全然任意、独断的吗?并非如此,这种确信有其自身的确定性。“确知的一种样式是确信。在确信中,此在唯通过对被揭示的(真的)事情本身的见证(Zeugnis)来规定它向这一事情的有所理解的存在。”*[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前揭书,第354页,译文有改动。在此,首先值得留意的是“确知(Gewissheit)与确信(überzeugung)”与海德格尔后来所说的“良知(Gewissen)与见证(Bezeugung)”在构词法上的亲缘性,这种亲缘性绝非偶然。海德格尔的上述说法“似乎乍看起来令人讶异,因为在日常用法中,‘确信’这个词通常仅仅意味着强烈地持有一个个人意见,但海德格尔却用相反的方式来解释‘确信’:当我通过对‘被揭开的事物自身’的见证而让自己完全被压倒、征服之际,并且,让它完全决定了我与其揭示之联系,我便处于对它的确信之中”*Magda King, A Guide to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p. 156.。也就是说,确信所具有的确定性意味着此在在确信状态中,使自己处在与“其所确信者”的确信关系中,此在完全让自己的生存方向被它规定、谐调,这种确信能够赋予那以深渊为根据的本真此在一种特有的坚住性,因而赢获其自身持驻性。*保罗·利科说:“证实(l’attestation)首先表现为一种信念。但是,这不是一种意见式的信念,因为‘意见’——信念——比起‘épistèmè’(科学,或者说是知识)更少确定性。既然意见式的信念包含在‘我相信……’的语法中,那么证实就术语‘我信仰……’的语法。因此,它是与见证(témoignage)相关的。”这揭示出了确信状态与信仰状态之间的关联。事实上,这一关联也为海德格尔所认可:“信仰乃是人类此在的一种生存方式,根据其本己的——本质上归属于这种生存方式的——见证(Zeugnis)。”但确信状态与信仰状态之间仍然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信仰“这种生存方式并非从此在中而且并非通过此在而自发地产生的,而是从那个在这种生存方式中并随着这种生存方式而启示出来的东西而来,也即从信仰所信的东西而来产生的。”与之相反,对于本真能在的见证而言,“如果这种见证可以‘让’此在在其可能的本真生存中理解自己本身,那它就会在此在的存在中有其根苗。从而,对这样一种见证的现象学展示就包含着对它源出于此在的存在建构的证明。”([法]保罗·利科:《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佘碧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3页;[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59页,译文有改动;[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前揭书,第369页,译文有改动。)
3.这种作为决心状态之实行的见证,对于日常此在而言,绝不是Antonio Cimino所说的一种人类生存的“事实”*Antonio Cimino, “Attestation and Facticity: On Heidegger’s Conception of Attestation in Being and Time”, in Journal of the British Society for Phenomenology, 44:2, p. 187, 189.,而毋宁是未来的、有待奋力争取的。在《存在与时间》的语境中,这最鲜明地体现在“良知呼唤”(Gewissensruf)与“愿有良知”(Gewissen-haben-wollen)的对比上。表面看来,日常此在总已经置身于良知呼唤之中,总已经以某种方式对其自身本真能在有所见证。因此,担负起对此在本真能在之见证使命的乃是良知呼唤。但是,在海德格尔看来,即使始终“有”良知呼唤,但日常此在对其充耳不闻,因为良知呼唤“这东西并非每次都被理解”*[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前揭书,第385页,译文有改动。,唯有那想要回返、归属这一呼声者才能与这一呼声遭遇。因此,完整的良知经验作为见证活动之发生,不是来自对良知的被动经验,而是首先来自一种主动的“意愿”(Wollen)活动之实行,“对良知的回应是一种意愿……从根本上来说,生存就是意愿”*Michael Lewis, Heidegger and the Place of Ethics: Being-with in the Crossing of Heidegger’s Thought, London: Continuum, 2005, p. 45.。其次,来自于坚住其中的“拥有”与保持:“拥有意味着把持、保持;对良知的本真理解,不会放过良知的呼唤(好像它只是一个事件),而是将其自身保持在一个持续的准备之中。”*Magda King, A Guide to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p. 195.因此,最终担负此在本真能在之见证的不是被动的“良知呼唤”,而是主动的“愿有良知”。本真此在不是偶然地、被动地观察到了某种被称为“良知呼唤”、“畏”的此在,而是那下了决心的愿有良知、为畏之到来准备着的此在。唯有“本真的此在在以下了决心的方式愿有良知之际,为我们提供了揭示此在存在意义的恰当的现象基础”*Mark A. Wrathall and Max Murphey, “An Overview of Being and Time”,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ed. Mark A. Wrathal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30-31.。这对于日常此在而言绝非现成的,而毋宁是有待争取的未来事件。
对此说法最直观的证据是,在1925年夏季学期的马堡讲座《时间概念史导论》(这也是《存在与时间》撰成之前最后的一个稿本)中,在从日常此在向着本真此在的转变之关键点上,海德格尔依赖的仅仅是“愿有良知”概念,而绝无提及“良知呼唤”*Martin Heidegger,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 1979, pp. 440-441.。事实上,“良知呼唤”概念不像“愿有良知”概念那样是从海德格尔漫长的讲课稿、手稿撰写中生发出来的概念。按照G. B. Kasowski的说法,在《存在与时间》成书前夕,海德格尔在读到舍勒的学生Hendrik Gerhardus Stoker的著作DasGewissen(1925)之后,才将此书中的核心概念“良知呼唤”引入自己的著作。*Gregor Bartolomeus Kasowski, Conscience and Attestation: The Methodological Role of the “Call of Conscience” (Gewissensruf) in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é de Montréal, 2011, pp. 64ff.
三、结 语
综上所述,此在本真能在之可能的见证,不是基于现成之物的对证据的观察和演绎的证明,而是一种对自身本真生存之意愿的实行,唯有“愿有良知者”才能成为“见证者”,日常此在不可能被动地由一些外在经验而被推入本真生存中。因为见证不是对“久以揣度者”即此在的本真能在的证实,而是一种以全然被“其所见证者”即此在的本真能在决定的方式向之生存的实行。不是日常此在证实到、观察到了本真能在之可能,而是下了决心的此在“生产”了自身的本真能在。唯有基于一种“生产”意义上的见证观念,一种作为“证实”意义的见证观念才是可行的。
见证概念的上述双重理解可能性,在《存在与时间》之后更彻底地偏向于第二种理解。例如,在《哲学论稿》中,海德格尔说:“死亡〈乃是〉最高的和极端的存有之见证。但这一点只能为那种人所知晓,他能够在自身存在的本真性中经验此-在,并且共同为此-在建基。”*[德]海德格尔:《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37页。在此,见证一词似乎同时蕴含了上述两重理解。一方面,“死亡〈乃是〉存有的最高见证”*[德]海德格尔:《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前揭书,第270页。说的是此在的最终极的有限性即死亡瓦解了日常此在的自足状态(日常此在总以各种方式抵御着死亡带来的冲力,而在一种自以为的“根基稳固”中浮游、攀援),为这无急难之时代(这种无急难之急难乃是最为深重的急难)赋予了急难(Not),因而使历史性的此在进入到与自身存在意义之开端的对峙,而使对另一开端之期备成为可能。在此,此在对自身有死性的经验就成为存有之本质现身的决定性瞬间(Augenblick),死亡不是此在的终结,而是此在之在“此”的敞开。在这里,似乎是将死亡这一现象视为存有之本质现身的证据、证实,因而此处的见证可以视为一种“证实”。另一方面,对此在有死性的本真经验,恰恰依赖于此在能够在自身存在的本真性中经验“此-在”。也就是说,作为存有之最高见证的死亡并不是日常此在随处可见的、现成可得的现象,毋宁说其本身就是有待赢获的:对死亡的本真理解本身就依赖于此在自身的决断与本真生存的实行。因此,“死亡〈乃是〉最高的和极端的存有之见证”,不是说此在通过对日常死亡现象的经验而证实存有之本质现身,而是唯有当此在被其自身的终极有限性所调定、谐调,因而是本真生存之实行,此在成为此-在,那“终有一死者”才有可能成为存有之真理本质现身的处所。在此,见证不是对日常中某一现成现象的拎出以为证明,而是要求日常此在实行一种本真生存的转变。因此,“见证是最难之事”*[德]海德格尔:《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前揭书,第101页,译文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