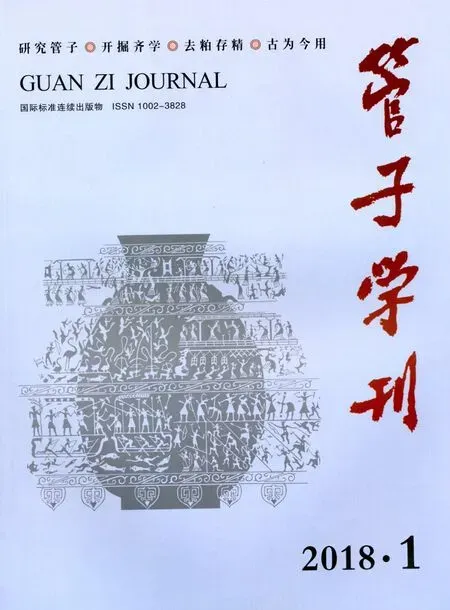试论《诗》与传统中国人的家教
王伟萍
(广西财经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3)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诗》是中国诗歌也是中国文学的源头,这已是人所共知的定论。自孔子以来直至近现代,中国人的家教始终离不开《诗》与诗。尽管在当代中国社会,很多人已不再读《诗》诵《诗》赋《诗》,也不再写诗,也很少读诗,但我们依然还可以在众多中国人的家教中寻到《诗》与诗教的痕迹。本篇试以讨论《诗》与传统中国人家教的几个问题,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孔子确立了《诗》作为传统中国人家教的基本教材
《诗》也称《诗三百》,编者为孔子,这是学术界的一般定论。其实,在孔子之前,诗已存在且作为皇家或世胄贵家教育弟子的基本内容,《尚书·舜典·虞书》载,舜帝命乐师夔典乐教胄子,其中就把诗当作乐教的一个内容:“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礼记·王制》也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国语·楚语》载楚庄王使士亹傅太子葴,士亹辞教不成,向申叔时讨教如何教太子,申叔时给的建议中就有“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诵诗以辅相之”。但彼时的诗只是教育的一项基本内容,尚未以成书的格局固定下来。在孔子编定《诗》之前,有各种各样的歌谣和乐歌传唱于民间百姓、朝廷乐师口中,那些歌谣和乐歌最早大约成于西周初年,最晚成于春秋中叶,辞曲固定者有三千余篇,时间跨度约500年。孔子自卫返鲁,对三千余篇歌诗进行了择选,选定其中的305篇成册,并依琴瑟而歌咏。孔子周游列国无果,晚年回到鲁国,杏坛设教,收弟子三千,授六艺之学,在教授弟子的基本教材中就有其选编的《诗》。他要求弟子的学习都要从学《诗》开始,《论语·泰伯》篇弟子录孔子言:“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嫡孙子思说:“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孔丛子·杂训》)
教授弟子从诗始,以《诗》为据,教授自家孩子亦是如此做法。《论语·季氏》载孔子弟子陈亢问其子伯鱼:“子亦有异闻乎?”伯鱼回答说:“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时至汉代,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言,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诗》《书》《礼》《易》《春秋》等五部儒家经典成为教授皇室弟子的教材,且均以“经”冠名,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后汉书·儒林列传》),五经中以《诗》最易读,加之历代当权者的提倡,世家大族的影响,民间亦多好者,故《诗》成为五经中传习最多、最广的一本家庭教育教科书。
二、《诗》在传统中国人家教中的地位
孔子定下的《诗》教基调,经汉代的发扬,使得“诗礼传家”“诗书济世”成为传统中国社会所有家庭教育子女的共识和基本要求。读《诗》,以《诗》为教成为传统中国人家教的基本方式和内容。
(一)《诗》为必读书目
学自《诗》始,不学《诗》,无以言;学《诗》,可以知鸟兽草木之名,诵《诗》三百,可“授之以政”“使于四方”(《论语·子路》)。无论世胄贵族之子还是寻常百姓之子,只要向学、问学,有从政的热望,《诗》必定是必读之书目。又,《诗》承载了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思想与价值理念,因此,凡服膺儒学之人,《诗》也必定是其阅读书目。加之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沿袭汉制,儒术治国,儒学成为传统中国人立身行事的依凭,儒家之五经六艺之学成为家庭教子的基本内容。因为《诗》为学人必读书目,传习的人多,所以刊版也最夥、辗转传讹也最甚①《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十五·诗类一·诗集传八卷(通行本)》:“盖《五经》之中,惟《诗》易读,习者十恒七八。故书坊刊版亦最夥,其辗转传譌亦为最甚。”(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版,第123页)。因此,针对《诗》的阅读问题而展开的相关研究著述也颇丰,据《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五、十六、十七、十八的记载,与《诗》相关的著述就有62部941卷,附录1部10卷;《诗》类著述存目83部913卷。翻阅史籍,你会发现,从汉到清两千三百余年,在传统中国人的家教中,《诗》及与《诗》相关著述是父母要求孩子阅读的基本书目。三国曹丕于其《典论·自叙》中称“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1]1097西晋钟会母亲张氏,“(钟会)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诵成侯《易记》。”[2]785明仁孝文皇后徐氏于《内训·御制序》中说:“吾幼承父母之教,诵《诗》《书》之典,职谨女事。”[3]23-25清世武进杨含辉,幼承父训,通《毛诗》《文选》,工诗[4]1396。蒋士铨《鸣机夜课图记》记母亲教儿子读书的情况:“铨九龄,母授以《礼记》《周易》《毛诗》,皆成诵。”清世才女顾慈,七岁受《毛诗》《女戒》诸书,即能识大意,旁及汉魏六朝三唐诸家,靡不贯通[5]卷五十二。长乐梁钜章叔母许鸾案,生长名家,擩染庭训,敦《诗》悦《礼》;夫人郑齐卿,名父之子,幼通《诗》《礼》;九妹蓉函子妇赵玉钗,初入门即课读《四子书》及《毛诗》,年余尽通其义[6]225、250。毕沅在《自题(慈闱授诗图)四首》序言中回忆母亲张藻“口授《毛诗》,为讲声韵之学”[7]卷一。在《再题一首并序》中又忆“行年十五,先太夫人教之学诗,云:‘诗之为道,体接风骚,义通经史,非冥心孤诣,憔悴专一数十年,不能工也。”[7]卷三十九青浦曹谔廷记其继室陆凤池少时教育状况:“余妇少时从族叔祖受四子书、《毛诗》,皆读《集注》。”[8]1134阳湖完颜恽珠在《国朝闺秀正始集》序有记其幼时授业情状:“先大人以为当读书明理,遂命与二兄同学家塾,受四子书、《孝经》《毛诗》《尔雅》诸书。”[9]择举如上,余不一一。
(二)《诗》乃教育之根基
1.情感的教育
《论语·阳货》载,孔子要求学生学《诗》,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即学习者在吟咏和诵读《诗》的过程中,美好情感得以熏陶,不良情绪得以过滤,从而使得强制的社会伦理规范转化为个体自觉的心理欲求,达到个体自我与社会群体的和谐统一。
诗可以化解、过滤人的不良情感和情绪,孔子并不是第一个提出此观点的人。早生孔子一百六十余年的管子早就指出:“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是故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管子·内业》)管子认为,诗歌和音乐是人平息愤怒、去除忧愁获得内心宁静从而归返人生平正之性的途径。这一观点深得孔子之心,从而服膺,当其与弟子周游列国的途中,每于厄难绝境,忧愁困苦之时,“弦歌不辍”。曾与弟子厄于陈蔡之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弟子子路带着怨怒之情前来相问:“君子亦有穷乎?”孔子平静答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孔子知道弟子心中有怨怒,于是召来子路、子贡、颜回三弟子论《小雅·何草不黄》中“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句(《史记·孔子世家》)。后来,孔子派子贡出使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陈蔡之厄于是结束。孔子深知歌诗和音乐的力量,故其自卫返鲁,对上古流传下来的三千余篇诗进行了选编,并将选定的305篇“皆弦歌之”,用于教授弟子和儿子。在平常里居中,孔子要求儿子鲤与弟子一样,学《诗》诵《诗》,通过学《诗》,管理好自己的情感与情绪,学会好好说话,在与人的交往中能够和谐相处。孔子这一教育理念在传统中国社会得到了很好地贯彻。历代中国尤其是明清家庭中的母氏普遍认为:诗可以治性情、和心志、尽性生,故诗(指包括《诗》在内的所有的诗)往往是她们训诲子女的重要内容。明末清初的才母顾若璞,丈夫早世后于课子之余息游于骚雅词赋中,度过了62年漫漫守志的岁月。后来又为其家女孩聘请塾师进行诗教,一位老妇批评她妇道无成,她以诗反驳:“二仪始分,肇经人伦。夫子制义,家人女贞。不事诗书,岂尽性生?”[10]卷二福建晋安邓兰水在教孙女邓秋英学《诗》时,郑重其事地说:“此可理性情者也,尔试读而思之,虽女子不为无益。”[11]15929武进杨含辉曾命其子煜廷学诗,说:“诗以治性情,和心志,不可少也。”杨氏本人即通《毛诗》《文选》,工诗。晚喜《白乐天集》,暇辄携一编,挑灯默坐,或为子妇、诸孙讽诵解说以自娱[4]1396。名家女骆绮兰,自幼从父学诗,丈夫早世后收养螟蛉义女并教以诗律,涵养其气性,希望她无论于母家为女还是于夫家为妇,于女工妇职余闲能够在“流览坟素,讽习篇章”中“多识故典,大启性灵”[19]卷七。
人生在世,不如意者常八九,困厄之境常遇,钟嵘认为:“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诗品·序》)《诗》(后泛指所有的诗),可以“群”可以“怨”,它能够化解、疏通内心的情感郁结,从而获得内心的和谐。点检史籍,我们不难发现,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士人,每每处于困厄之中,情绪处于低潮期,他们往往选择与诗为伴,渡过人生的一个个难关,如苏武、李陵、陶渊明、李白、苏东坡、辛弃疾等,余不一一。因为不良情感、情绪疏泄有渠道,所以不会轻易选择自杀或杀人等极端的情绪发泄途径。反观当代中国社会,诗歌衰落,绝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不读诗、也不能诗(作诗),志无以申,情感郁结心中,往往容易致病,给自己与他人的生命乃至给社会造成极大的伤害,这在当今中国社会已是不争的事实。
2.人伦之道的教育
中国先民认为,人之所以别于禽兽者,在于知人伦。故圣人设教,欲使人明于人伦,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若人伦不明,则治家无法;家不治,则国不治,国不治则天下不平,故人伦于身尤切。因此,在传统中国,人伦教化是一件非常切要的事情。作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老师,孔子非常看重人伦教化这件事情,曾说:“大罪有五,而杀人为下……逆人伦者,罪及三世。”(《孔子家语·五刑解》)在回答哀公问政时,他将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等五伦视作天下五达道(《孔子家语·哀公问政》)。
天下至治是孔子毕生追求的理想,而欲天下治,当首正人伦;欲正人伦,当首正夫妇;欲正夫妇,当首正男女。《礼记·中庸》中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礼记·昏义》也说:“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因此,如何处理男女、夫妇关系与情感是先民进行人伦教化的重点,也是孔子教子的中心。《论语·阳货》前一章载孔子要求弟子“何莫学夫诗”,紧接的后一章即载孔子问其子伯鱼:“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周南》《召南》是十五国风的首二章,《周南》选诗十一篇,《召南》选诗十四篇。孔子为什么要求儿子伯鲤去研读这两章?此两章与其他十三章内容有何特别之处?朱熹《论语集注》说此二章“所言皆修身齐家之事”[13]178。郑浩说:“《周南》十一篇,言夫妇男女者九。《召南》十五篇(笔者按:实十四篇),言夫妇男女者十一,皆无淫荡狎亵之私,而有肃穆庄敬之德;无乖离伤义之苦,而有敦笃深挚之情,夫妇道德之盛极矣。匡氏衡曰:‘夫妇者,人伦之始,万福之源。’《中庸》亦曰:‘君子之道,肇端乎夫妇。’此处一失其道,即无以为推行一切之本。”[14]1214孔子之所以看重《周南》《召南》二章缘于二章所言关涉修身齐家之事,主题以夫妇男女关系为主。考察国风中其他十三章述男女婚姻、爱情之事的篇章如《邶风》中《静女》《二子乘舟》,《卫风》中《氓》《木瓜》,《郑风》中《狡童》《褰裳》《子衿》《野有蔓草》《溱洧》诸篇,其情感的表达较为肆意、张扬且多怨,不如《周南》《召南》二章内敛而温柔敦厚。故孔子将“二南”作为儿子人伦之教的立足点,让他去仔细研读,并说人若不读“二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孔子此语何意?朱熹说:“《周南》《召南》,所言修身齐家之事。”“修身齐家,自家最近的事,不待出门,便有这事,去这个上理会不得,便似那当墙立时,眼既无所见,要动也行不去。”[15]1186孔子当年选编此书时,即围绕“明人伦”选篇择章,除二南集中言男女夫妇之事外,其他诸章亦不出男女爱情、婚姻之事,其他还有述事君、事父母的篇章,凡305篇,篇篇皆欲使人明人伦,故朱熹有言:“人伦之道,《诗》无不备。”[13]178此乃孔子编《诗》教化弟子与儿子之良苦用心,从其谆谆的叮嘱可见。孔子以《诗》明人伦的良苦用心在后世得以承续。汉代以来,传统中国人家庭训子诲女不离《诗》,在父母的课读中,孩子诵《关雎》而知淑女君子之道;诵《桃夭》而知女子于归,宜其室家;诵《氓》《谷风》而知夫妇离绝,国俗伤败;诵《棠棣》而明兄弟当友爱互助;诵《伐木》而知友贤不弃,不遗故旧;诵《凯风》《蓼莪》而知父母生我劬劳,当知孝敬,诸如此类,余不一一。
3.为政的教育
《论语·子路》载孔子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诵《诗》三百何可以“授之以政”“使于四方”?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解决政者何谓的问题。《尚书·虞书·大禹谟》载上古圣王大禹关于“政”与“为政”的观点:“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周书·洪范》又载,周武访箕子,问彝伦攸叙即治国常道,箕子对以“洪范”九畴,其三曰“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日宾,八曰师。”“八政”涵括了老百姓寻常里居中的吃穿住行人情往来等大事小情,正是对大禹王“政在养民”的具体阐释。既然“政在养民”,那么国家如何“立政”,职官如何“为政”方能“养民”?《尚书·周书·周官》载周成王建百官以理内外之政,并提出这样的“立政”观点:“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官不必备,惟其人。”置官理政不在设官的多少与全备与否,而在用人得当,人尽其才。
那么官又当如何为政?《礼记》中《哀公问》和《中庸》两章有载孔子答哀公问政。孔子认为,为政的根本是爱人与敬人,无爱不亲,无敬不正。爱与敬又以礼立,故为政又先礼,礼,是为政根本的根本。三代明王之政,均从敬妻敬亲敬身做起,敬身又从谨言慎行做起。总之,为政在人,为政者要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亲亲为仁,知人知天,以明人伦。
在《论语》《为政》《颜渊》《子路》诸篇中,弟子也记录了孔子的为政观:孝顺父母,友于兄弟,是亦为政;为政的根本是人,政在养人(足兵、足食、孝、信、忠);为政者要明于人伦、礼乐;为政以德,要身先士卒,要正身。
既然政在养民,那么民风民情民意不可不观、不解,风衰俗怨不可不知;既然立政惟人,为政在人,那么执政者、为政者的德行是政之善恶的关键,因此,为政之教亦是为人之教,培养人温厚的德行是教育的重心。孔子自卫返鲁杏坛设教,其意在培养学生成为为政者,到各诸侯国推行其为政理念,冉有、季路是七十二弟子中政事方面的优异者。《诗》里的篇章不仅书王道之迹且本乎人情,穷究物理,可以观验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且其言又温厚和平,怨而不怒,可为垂轨教之典,故诵之,必达于政而能言。故孔子将《诗》作为弟子“授之以政”“使于四方”的教材,日夜诵读。当然,孔子以《诗》为弟子为政之教也是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使然。其时无论是寻常里居中的人际交往还是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使节往来,开口即称《诗》诵《诗》赋《诗》,以谕其志,以观人之贤不肖。若不读《诗》,不解诗,则不能言。且其时的执政者,亦信奉“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史记·秦本纪》),故欲为政,不能不学《诗》、不诵《诗》。为政者通《诗》即通人情物理,能胜任所职之事。且《诗》里也有一些关于为政的感想和感悟、警戒,诸如《邶风·北门》篇,这是一位位卑多劳的下层小官吏吟诵的怨诗,他苦于王事又窘于政事。繁重的公役与劳务弄得他疲于奔命,又被贫困的生活弄得满腹忧思,身心憔悴,苦不堪言;《小雅·节南山》篇是对旷废职司的官员的批判,试图劝诫君王改弦更张,以延续政治;《大雅·抑》篇,写的是一老臣对执政同僚晚辈的谆谆告诫,告诫他们要遵行先王法度,要言出谨慎,敬慎威仪,恭敬神明,不欺暗室,重视民生疾苦等。有意为政者在诵读这些诗篇时,那些来自先辈的关于为政的直接经验与感悟、体悟对他们来说会是一个有益的提醒和教训。
汉以后,中国人服膺儒术,儒家以《诗》教为政的传统也承袭下来,讲《诗》学《诗》成为执政集团政治生活中的常态①汉以后的史籍多有皇室讲《诗》的记载,如《汉书·楚元王传》载: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宋书·志·礼四》载:咸宁三年,讲《诗》通;成帝咸康元年,帝讲《诗》通。诸如此类,余不一一。。上行下效,在传统的中国人家庭中,若欲子弟为政,则《诗》必为家庭施教的主要内容。父母以《诗》训子,奠定子今后入仕为政的基础是传统中国家庭教育的基本理念。在史籍的记载中,我们发现历代很多官员在他们成长的历程中,都有自小接受家庭《诗》教的经历,如后汉马援兄子严子续,七岁能通《论语》,十三明《尚书》,十六治《诗》。朱勃十二能诵《诗》《书》(《后汉书·马援传》)。伏湛父为当世名儒,以《诗》授成帝,为高密太傅,别自名学。湛性孝友,少传父业,教授数百人(《后汉书·伏湛传》)。冯衍幼有奇才年九岁,能诵《诗》。冯衍子豹好儒学,以《诗》《春秋》教丽山下(《后汉书·冯衍传》)。郑兴执义坚固,敦悦《诗》《书》;其子众,年十二,从父受《左氏春秋》,精力于学,明《三统历》,作《春秋难记条例》,通《易》《诗》(《后汉书·郑兴传》)。翟酺家四世传《诗》(《后汉书·翟酺传》)。崔骃年十三能通《诗》《易》《春秋》(《后汉书·崔骃列传》)。周燮十岁就学,能通《诗》《论》(《后汉书·周燮》)。皇甫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诗》《书》(《后汉书·皇甫嵩》)。晋孔衍少好学,年十二,能通《诗》《书》。范宣年十岁,能诵《诗》《书》(《晋书·儒林》)。夏侯湛在其《昆弟诰》中载,母亲羊姬,教子书学,敦《诗》《书》《礼》《乐》(《晋书·夏侯湛传》)。魏祖莹年八岁,能诵《诗》《书》(《魏书·祖莹》)。择举如上,余不一一。故隋代牛弘有言:“握符御历,有国有家者,曷尝不以《诗》《书》而为教,因《礼》《乐》而成功也。”(《隋书·牛弘》)
(三)《诗》教与《礼》《乐》《书》《易》《春秋》之教的配合
《诗》在传统中国人家教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但《诗》只是学习的开始,教育的初始阶段,《诗》教须有《礼》《乐》《书》《易》《春秋》的配合才能最终完成。
先民认为“礼节民心,乐和民声”,《礼记·乐记》里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诗》里的篇章是本乎性情而发的,如果没有礼乐的约束(礼以节制,乐以和合),情感的抒发就会泛滥过度或呆笨愚顽,惟有《诗》教《礼》教《乐》教三教合一,方能“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16]1537故孔子以《诗》《礼》《乐》教育弟子和儿子时,从《诗》教起,配以《礼》《乐》。他说:“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礼记·仲尼燕居》)故《诗》教须与《礼》《乐》二教相互配合,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
但是,《诗》《礼》《乐》三教还得《书》《易》《春秋》之教的配合。因为《诗》《礼》《乐》三教均有其缺憾所在:“《诗》之失愚”“《礼》之失烦”“《乐》之失奢”。因此,需以《书》教之“疏通知远”,《易》教之“絜静精微”,《春秋》教之“属辞比事”来补其缺憾。当然,《书》《易》《春秋》之教也都有其缺憾所在:《书》之失诬,《易》之失贼,《春秋》之失乱。惟有《诗》《礼》《乐》《书》《易》《春秋》六教即“六艺”齐备、完整,学养才算最终完成,其为人就可做到“温柔敦厚而不愚”“疏通知远而不诬”“广博易良而不奢”“絜静精微而不贼”“恭俭庄敬而不烦”“属辞比事而不乱”(《礼记·经解》)。今后无论是入仕为官长,还是以处乡里、室家,为人父子,均能行止有方,知敬让之道,内心安和。治人治心之理相通,能和心者自能和人,心不和,则人不和,世亦不和。
六艺之教以《诗》《礼》《乐》三教为本,其他诸教配合。三教中又以《诗》为始为本,其次《礼》教,其次《乐》教。之所以如此安排,按朱熹的理解:“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礼以恭敬辞逊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可以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故学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为事物之所摇夺者,必于此而得之。乐有五声十二律,更唱迭和,以为歌舞八音之节,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查滓。故学者之终,所以至于义精仁熟,而自和顺于道德者,必于此而得之,是学之成也。按《内则》,十年学幼仪,十三学《乐》诵《诗》,二十而后学《礼》。”[13]104-105《诗》既是三教之始,也是六艺之本,所以无论三代以前还是三代以后,“其教为至广”且文章之用“莫盛于《诗》”[17]78。
三、家庭《诗》教的意义
《诗》所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集文学、社会学、语言学、伦理学、历史学、植物学、动物学于一体,因此,自春秋以来《诗》一直被当权者当作垂轨教之典,作为化民之道而推广,延续了两千三百余年之久。或有人质疑,世易时移,世代陵替,《诗》所言之自然、社会、人生实际情状与基本价值理念已与今日大异,若仍以《诗》之所言教之,不亦迂乎?当然,《诗》教的内容与形式,会随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侧重,汉代确立了“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强调“劝谏”的功能和“修身”的功效,后世在此基础上有所变通。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教不特指三百篇,其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广泛,包括所有“诗”在内的“诗教”。宋代《诗》教坚持伦理本位,道德中心的原则,重视《诗》中关涉天理人伦,“合于道”的内容。明清《诗》教依然坚持儒学传统,且自上而下,诗教风气浓厚,能诗者越来越多,流风波及女性群体。相当多的女性于家庭《诗》教中成长,成为人母后又以《诗》与诗训子诲女,形成《诗》教的良性循环,两千余年的《诗》教根脉得以承续,文化的正统得以世代承续。中国历代社会,治乱相替,且乱多于治。但无论处于治世还是乱世的中国家庭,母亲始终坚持以《诗》训子诲女,治性情、和心志、明人伦、知为政,坚守“诗书济世”的信念,所以尽管社会板荡,风衰俗怨,但始终有一基本价值理念贯穿于其中,《诗》教之道统不失,文化根脉不断,正统得以保持。且《诗》教中成长的孩子无论治乱始终不失生活的乐趣。反观今日中国,很多家庭子女性情暴慢,家庭伦常失序、人际相处困难,这与家庭忽略甚至没有对子女进行诗教有很大关系。缺乏诗教的孩子,也缺乏基本价值观念的持守,面对外在的诱惑,内心容易摇摆。而当其心有不良情绪、对他人对社会有积怨无法通过合理有效的途径进行疏解,以致于对他人、社会包括自己造成很大的伤害。我们梳理《诗》与传统中国人的家教之关系,审视承续了两千三百余年之久的《诗》教观,是为了能得到一些智慧的启迪,以为今日家庭教育之福祉。
[1]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严可均,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58.
[2]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
[3]女四书女孝经[M].王相,笺注.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4]江南女性别集三编[M].王冉冉,杨焘,主编.合肥:时代出版传媒集团,黄山书社,2012.
[5]两浙輶轩续录[M]∥续修四库全书.潘衍桐,编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6]清代闺秀诗话丛刊(一)[M].王英志,主编.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10.
[7]毕沅.灵岩山人诗集[M].嘉庆四年,经训堂刻本.
[8]江南女性别集二编[M].查正贤,赵厚均,主编.合肥:时代出版传媒集团,黄山书社,2010.
[9]国朝闺秀正始集[M].完颜恽珠,辑.道光辛卯镌,红香馆藏版.
[10]顾若璞.卧月轩稿[M].光绪嘉惠堂丁氏刻本.
[11]清诗纪事:第 22册[M].钱仲联,主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12]陈兆伦.紫竹山房诗文集[M].乾隆陈桂生刻本.
[13]四书章句集注[M].朱熹,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14]论语集释[M].程树德,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
[15]朱子语类[M].黎靖德,编.王星贤,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
[16]十三经注巯[M].阮元,校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7]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