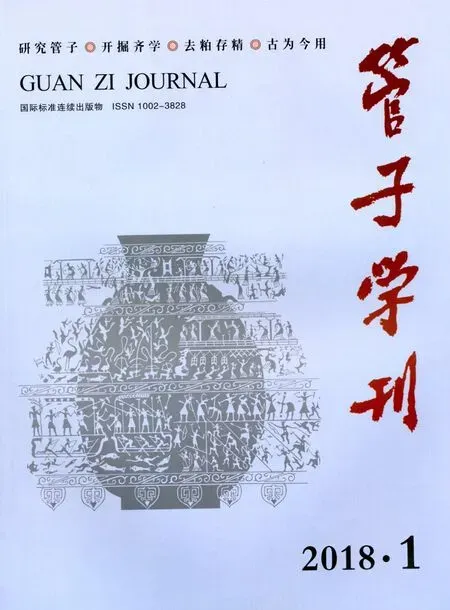庄子哲学实则气学
——兼论其理论盲点与理论困境
尹江铖
(南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0)
庄周已于两千多年前“化蝶”去了,留给我们的是一部汪洋恣肆的《庄子》。其文气纵横四海,遨游九霄,与其说是出自一位思想家,不如说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化身而成的诗。“哲学”一词是后人给诗性的《庄子》贴上的一个不十分恰当的标签,但后人要对《庄子》进行理解又不得不借助哲学概念。面对具有丰富内涵的《庄子》,首先要恰当地把握其最核心的概念和哲学特质,由此才能提纲挈领,阐述其内涵,分析其不足。
然而《庄子》毕竟难解,后来人由于自身所处学术背景、自己学术兴趣等等的不同,对《庄子》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历史上出现的多种解释,大体可分为三类,首先是将《庄子》作美学的解释,其次是将《庄子》作道学的解释,最后是将《庄子》作心学的解释。《庄子》无疑是可以作美学的解释的,《庄子》所蕴含的美学思想也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各个方面,但任何一种美学都有其哲学根源,因此若搞不清楚这个根源,仅将《庄子》解释为一种美学不足以给庄子作思想上的定性。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讲,前辈学者都从哲学的角度将《庄子》解释为一种承袭老子而来的道学,因此其中蕴含的美学思想也就是根植于道学,直到现代才有学者从心学的角度去诠释庄子,开出了新的视域。这种解释上的不统一则说明《庄子》本身具有丰富的内涵,可以多样的诠释,二来也呼唤新的声音来剖析《庄子》,丰富和深化对庄子的理解。到底应该将《庄子》作怎样的学理定性呢?本文立足《庄子》文本,试作一番新的解释。
一、应该将庄子定性为一种气学
(一)对以往解释的重新思考
如何定性《庄子》,是一个解释学的问题。解释行为本身有两个大的特征,首先是解释行为囿于解释背景,以往前辈学者解庄,无不囿于自身主客观环境;其次是解释行为的无限性,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解释背景在变化,解释行为当然也会跟着变化。因此,面对前辈学者的解释,仍然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首先,不能仅将《庄子》哲学把握为一种美学。《庄子》中确有很多命题,如“逍遥”“坐忘”、“心斋”“神”“复根”“道通为一”等等都能用美学的眼光看待,进行美学的解释。然而这些命题之所以能作为美学命题被得到认可,是有其哲学根底的。仅将《庄子》把握为一种美学,无疑会使其美学命题背后的哲学根底隐退难见。何以能“逍遥”?通向“逍遥”之路的哲学保证是什么?“坐忘”“心斋”想达到什么?这其中有什么机理?“神”何以“神”?为什么强调“复根”?其哲学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厉与西施”“道通为一”?这些问题就得不到解答,甚至连问题都会隐而不见。因此,若将《庄子》仅把握为一种美学,就会使得这些丰满的,有其内在学理和生命力的命题降格为一种主张,沦为一种意见。当这些命题沦为一种产物,就不再具有生发命题的哲学学理;而对产物进行的任何诠释,都不能代替对其根本学理的发掘。
其次,不能将《庄子》把握为一种创生论意义上的道学。《庄子》思想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老子,其本人也属于道家学派,但以“道学”来定位他的学说则是错误的。
第一,所谓“道学”,旨在学“道”,意即探究这个客观的“道”。老子、管子的“道”都有创生性质,也有万物本质的意思,能生发规制万事万物。“道”在他们的学说里是一个核心概念,根本性命题,能作为因此以“道学”来定位他们的思想是可以的。但《庄子》并无这种创生论。虽然“道”这个字在《庄子》中出现了380多次,但在历来被认为是庄子本人所作的内七篇中仅有46处,且通观内、外、杂篇,未见有如《老子》第四十二章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样的肯定“道”的创生性的文字。《庄子》文本中只有一处论“道”的文字,似乎是在讲“道”的创生性,即“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庄子·大宗师》)。但我们看到,且不论这里的“道”指的是什么,文本传达的意思主要有三层:首先是“道”的难以领会,不可把握的性质;其次是强调“道”自本自根的性质;第三是“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对于这段文句的理解,关键点就在如何理解“自本自根”和“神鬼神帝,生天生地”。郭象将“自本自根”进一步确立为其“独化论”哲学,在此基础上,他这样解释“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斯乃不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斯乃不生之生也”[1]137,明确说明天地神鬼非道所生,而是自生。后来的气学家王夫之继承了这一解释,他在对这段文句的评论中说:“天地、日星、山川、神人,皆所寓之庸,自为本根,无有更为其根者。若有真宰,而岂能得其朕乎。”[2]137“道”非创生万物之真宰的意思也很明确。笔者认为,这是对这段文句的忠实解释,是符合庄子原意的。
第二,《庄子》文本中“道”的内涵,主要包含三个意思:其一是理或真理的意思,如“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谦,大勇不忮”(《庄子·齐物论》);其二是境界的意思,如“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庄子·大宗师》);其三是观察对待万事万物的方法、标准的意思,如“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这第三个意思是《庄子》中“道”的核心意思,更是其与老子之“道”有效地区分开来的意思。因为在老子那里,“道”有着客观唯心主义的意味,也有着创生性意义,所以是老子学说的核心概念;而在《庄子》中,“道”则是从主观认识上来讲的,并非是其学说中具有奠基性的核心概念。综上两个原因,笔者认为将《庄子》把握为道学是不妥的。
最后,不能将《庄子》把握为一种心学。陈鼓应先生曾作题为《庄子内篇的心学开放的心灵与审美的境界》的文章,以“心学”把握庄子。陈先生将《庄子》中的“气”视为“道”的具象化,同时以心解气,将“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中的“气”解释为“空明的心境或清虚的精神境界”[3]54。笔者认为,陈先生这种以心解气的理解,与庄子原意不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中的“气”,实际上是“而听之以气”的缩略语。关于这一点,成玄英说的很明白:“如气柔弱,虚空其心,寂泊忘怀,方能应物。此解‘而听之以气’也”[1]81,意即“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是对“而听之以气”的解释。而且,郭象说:“遣耳目,去心意,而符气性之自得,此虚以待物也”[1]81,这就是说,“虚而待物”的目的在“气性之自得”,落脚点并非在“心”上。笔者认为,这才是正确的理解。另外,《庄子》中出现的“心”虽有182处之多。但其含义一是指个体意义上的认知之心,二是指大众舆论意义上的“人之心”,均不具有本体论意味,都是从人体器官之心出发而讲的心的各种功能。由此也可反证出《庄子》确是一种自然气论哲学,而非心学。
(二)气是《庄子》的思想基石
以上是从否定的方面来说《庄子》哲学不是什么,那么从肯定的方面来讲又当如何呢?要恰当地把握《庄子》哲学,就要找到那个能保证《庄子》美学得以成立的思想核心、思想基石,就要找到那作为理的“道”寓于其中的东西,找到那作为境界的“道”在哲学学理上得以成立的东西,找到那作为方法和标准的“道”得以可能的东西。
笔者认为,这一思想基石,这一核心的概念就是“气”。“气”在《庄子》中具有本根论的意义。就人来讲,“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知北游》);就万事万物来讲,“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这已经很能说明“气”较之于“道”更有本根论意义了。“气”还与《庄子》美学各命题有着学理关联。对“心斋”这个美学命题,《庄子》中借孔子与颜回的问答这样描述:“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 ,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这就明明白白点出“听之以气”就是“心斋”的办法和诀窍。为什么呢?成玄英疏曰:“心有知觉,犹起攀缘;气无情虑,虚柔万物。”[1]80而“坐忘”则是“心斋”的一种形式。就“神”这个美学命题,集中体现在《庄子》所载异人或称神人、圣人、至人的“神乎其技”上。《庄子·达生》篇中,列子问关尹为什么至人“潜行不窒”“蹈火不热”,关尹答道:“是纯气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梓庆为鐻,见者“惊犹鬼神”,鲁侯问其中玄妙,梓庆答道:“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必齐以静心”,诸如佝偻承蜩、津人操舟都是如此。若总其原因,“壹其性,养其气,合其德,以通乎造物之所造。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隙”,然后才能“神凝”而“神乎其技”。就“逍遥”这个《庄子》所宣扬的最高美学命题,文本中有这样的论述:“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呜呼待哉”(《庄子·逍遥游》)。郭象注曰:“御六气之辩者,即是游变化之涂也。”[1]11成玄英疏曰:“言无待圣人,虚怀体道,故能乘两仪之正理,顺万物之自然,御六气以逍遥,混群灵以变化。”[1]11能御六气,即是游于自然无穷之大化,即是逍遥。“气”就为“逍遥”提供了前提和保证。又,“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齐物论》),郭象注曰:“寄物而行,非我动也”[1]52,人以物为我,化寄气中,任随根本之气自然而动,即是遨游四海。可见“气”确实是《庄子》美学命题的根基,若缺了这个根基,一切二级命题都“恍惚窈冥”,失去了意义根据。
继承老子而来的“道”,在《庄子》文本中出现的次数为“气”的九倍不止,但在很大意义上只是用其名而不用其实。另外,《庄子》不仅继承了老子的道论,还继承了先秦气论,尤其是管子的“精气”学说,李道湘先生就曾指出:“以《管子》的精气论到《庄子》的气论是先秦气论发展最重要的阶段,也是先秦气论发展的最高阶段,它以《庄子》气论的建立为最高成就。”[4]1庄子将老子的“道”创造性地转化为观念论层面的范畴,失去了奠基性意义的“道”就需要“气”来为之作学理上的奠基和保证。以最具特征的“道通为一”和“以道观之”为例,这两个命题在学理上是如何可能的呢?若不是“通天下一气”,“道通为一”就成了所谓的绝对的相对论,就失去了其合理合法性;“以道观之”若合理可行,则必须奠基于“通天下一气”的基础上,进行“坐忘”“心斋”,通过“听之以气”来达到。
综上而论,笔者认为,《庄子》哲学,必须把握为一种气论哲学才是合理的。尽管按照庄子本人,未必有给自己学说定位的主观愿望和学理冲动;尽管用“气学”来把握庄子哲学有损其诗性魅力,但从学理上来讲,这确是一条明确的通达《庄子》的哲学道路。而且若要使其思想通达无碍,也应当会“逼迫”出一条“气论”线索来。
二、《庄子》哲学中的气论分析
前文已经将《庄子》哲学把握为一种气学,则必然要对其气论进行深入分析。《庄子》文本中出现的“气”的次数,有说40次的,有说43处的,准确的来讲,应该是46处。面对这46处“气”,结合《庄子》全文,既要揭示“气”在《庄子》中的不同含义,也要理出以“气”贯之的哲学理论。
(一)《庄子》中“气”的涵义
关于《庄子》中“气”的含义,前人也有所论。据笔者所见,主要有两篇:黄柏青、朱登吾的《庄子的气论及其哲学和美学意义》和王洪泉、王赠怡的《庄子论“气”》。在上所录第一篇中,作者将《庄子》中的“气”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构成万物始基的气;另一类是作为人的生命本源的气。作者又将第二类细分为生理之气和心理之气两类[5]48。在第二篇中,作者认为可对《庄子》中的气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道”的性质的气;另一类是构成宇宙生命具体介质的气[6]129-130。两文的划分似都较为简单,不能囊括《庄子》中“气”的含义之全貌,也不能从划分中看到“气”的隐藏之意或具有引发再阐释意义的意思。另外,有些说法也似乎欠妥。比如,《庄子论“气”》中认为《庄子》之气是道通向天地万物的中介,认为庄子修正了老子有关道生万物的神秘性和形而上性,将老子的“道万物”的形而上生成演化模式和“气万物”的形而下生成演化模式结合起来,形成了“道气万物”演化模式[6]130。因此按照这个模式,《庄子》中的“气”就既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基本质料,又成为了道通向天地万物的拱顶石。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违背庄子原意的。首先,虽然《庄子》中的“道”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继承老子而来,但实际上是只用其名而不用其实。“道”在“庄子”那里并不具有创生、演化万物的意义,而只具有主观上的方法论意义。其次,所谓演化模式,与“自本自根”原则相违背。这样,就有必要重新对《庄子》中“气”的涵义重新进行梳理。
笔者认为,《庄子》中“气”的涵义大致可分为五种。
第一,专指“云气”的“气”。如:“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庄子·逍遥游》)、“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庄子·在宥》)中云、气并用的“气”就是专指水蒸气一样的“云气”。《说文解字》中也将这个意思视为气的本义。
第二,生理之“气”和心理之“气”。如:“愁其五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庄子·在宥》)、“兽死不择音,气息茀然”(《庄子·人间世》)都是指生理之气;“方虚骄而恃气”(《庄子·达生》)、“犹疾视而盛气”(《庄子·达生》)、“溺于冯气”(《庄子·盗跖》)都是指心理之气。
第三,万物各自的“气”。如:“天气不合,地气郁结,六气不调,四时不节。今我愿合六气之精以育群生,为之奈何”(《庄子·在宥》)、“四时殊气,天不赐,故岁成”(《庄子·则阳》)、“阴阳者,气之大者也”(《庄子·则阳》)等都显示出天、地、四时、阴阳等万物各有其气。这也从一方面佐证了所谓的“自本自根”,要不是各有其气,如何而能“自本自根”呢?这同样也说明郭象以“独化”来解庄的正确性。
第四,本根论意义上的“气”。如:“通天下一气”“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庄子·大宗师》)、“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庄子·秋水》)都是阐发万物混同一气的道理。但需要注意的这里的“气”虽有本根论意味,却无气生万物的创生演化之意。
第五,以气言心,以道言气意义上的“气”。如:“汝方将忘汝神气,堕汝形骸,而庶几乎!”(《庄子·天地》)此处神气与形骸对用,神气用来指心的意思是很明确的,成玄英亦疏曰:“身心既忘,而后庶近于道。”[1]235如:“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中“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是说“二仪万物,无是无非者也”[1]37,道与物对用,显然是实指。前文已述,“道”在《庄子》中只具有主观层面的意义,那么“道行之而成”就是指“气行之而成”。结合“通天下一气”来看意思更明显,只有“通天下一气”,万物由“气”行之而成,才能“道通为一”。所以“道行之而成”中的“道”是以“道”言“气”。另外,“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庄子·大宗师》)的“道”按庄子义不可能是实指。结合以上所论,也应理解为以“道”指代“气化自然”。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笔者认为这里有一个关键点应该注意:《庄子》文本,有以气言心者,也有以道言气者,却似未有以心言道,以心言气者。若笔者所说确然,若不甚恰当地以唯心唯物论之,则《庄子》唯物论意义上的哲学品格更为突出,其气论哲学的面貌更为清晰。
以上将《庄子》中“气”的涵义析为五种,可以看到“气”的全貌,也能看到在《庄子》中“气”与“心”、与“道”的暧昧处、模糊交涉处。这些暧昧和模糊交涉处恰是《庄子》薄弱处,也恰是作为庄子以后的哲学家所继续思考的理论生长点而存在的。
(二)《庄子》气论的逻辑理路
作为一种气论哲学,自然有其内在理路,虽然这在《庄子》中并未明显地诉诸文字。后世哲学家均认为这一理路就暗含在《庄子》内七篇的排序中。如成玄英在《南华真经疏序》中,王夫之在《庄子解》中均是这样看待。后世哲学家除了都认为《庄子》内七篇是按照所要表达的思想理路特意安排的以外,还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都以首篇《逍遥游》为逻辑起点,认为以后各篇皆因此篇而依次展开,如王夫之所论:“逍者,响于消也,过而忘也。遥者,引而远也,不局于心知之灵也。故物论可齐,生主可养,形可忘而德充,世可入而远害,帝王可应而天下治”[2]75。
分析《庄子》内七篇可知:《逍遥游》主要为庄子心目中的至高境界,或者说是一种圣人气象;《齐物论》齐“物论”或“齐物”论,表达“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道理;《养生主》表达“缘督以为经”,不以形累,不以知累,一任自然的道理;《人间世》讲真人不能离开人而超世独立,而能够通过“心斋”而随缘应世;《德充符》描述内虚而无所执,外忘其形骸而一任自然的真人形象,与儒家注重威仪容貌、文辞礼乐的圣人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大宗师》表达“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富,其所宗而师者,无心也”[1]124的思想宗旨;《应帝王》表达无心而应物,一任物之自然自化,“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的道理。笔者认为,内七篇可分为三部分。《逍遥游》《人间世》《应帝王》为一部分,“逍遥”一词总括真人境界,《人间世》讲处世,《应帝王》讲任物。这三篇合为《庄子》之“用”,是从境界、发用上来讲。《德充符》独为一部分,描述真人形象,也为《庄子》全书之“相”。《大宗师》《齐物论》《养生主》发明达“相”致“用”的道理,为《庄子》全书之“理”。以“理”“相”“用”来概括《庄子》内七篇,那么其逻辑就应该是“通理达相致用”。这样,代表《庄子》至高境界的《逍遥游》就应该是逻辑的终点,而非起点。
以上用“通理达相致用”来把握《庄子》全文的线索只能观其大概。还需要学理上的逻辑线索才能对它进行支撑。而这个线索的核心就是“气”。首先是“通天下一气”,确立自本自根的自然观本体论;进而才能“齐物”,并通过“心斋”“坐忘”而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进而才能树立“德充于内,物应于外”[1]103、内则虚而待物,外则遗其形骸的真人形象;最后才能“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大治”(《庄子·应帝王》),才能“乘物以游心”(《庄子·人间世》),才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
三、《庄子》气论哲学的得与失
(一)《庄子》气论哲学是自然美的哲学基础
《庄子》哲学凭借“气化自然”的思想超越有、无,玄同是、非,又凭借“通天下一气”不流于唯心空无,确实是对《老子》哲学的修正和超越。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对“气化自然”的承认和尊重,由是才能作为中国美学的主要根基而在艺术中得到生命的延续和绽放。提出“通天下一气”,又拈出“自本自根”,则万物在其自己,而不像佛教哲学那样对万物进行“缘起性空”的分解,这固然是对气化自然的尊重,更是对气化之物的尊重。万物在其自己,而人只应该“心斋”“坐忘”“听之以气”,让气化之物在如镜之心中自然呈现,让通天下之一气自然流行,才能确立“气论美学”或者“物论美学”的根基。若没有对这“气化自然”的肯定与尊重,若没有对“自本自根”的气化之物持“听之以气”的态度,就只能将美诉诸于心了,自然与物之美安在?
(二)《庄子》哲学的理论盲点与理论困境
作为原创哲学家,庄子或《庄子》的编撰者并未能在学理上扫清一切障碍,而有其理论盲点。这种理论盲点集中体现其未对“心”“气”关系作自觉、恰当的阐述。
《庄子》否定心知而一任自然之气,但“心”的概念在其哲学中却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庄子》论“心”多是从功夫论层面上来论述的,若没有从“心”上成办的功夫论,则《庄子》气论无以达成。所以论《庄子》之“气”,必须论《庄子》之“心”。但《庄子》中的“心”“气”关系却暧昧不明。
笔者认为《庄子》中有三处文句对理解《庄子》“心”“气”关系至为重要。第一,《天地》篇“汝方将忘汝神气,堕汝形骸,而庶几乎”中的“神气”显然指的是“心”。但这里是否意味着“心”即“气”之神呢?从《庄子》全文来看,此义不明显,但这里确有“心即气”的萌芽。第二,《德充符》篇“常季曰:‘彼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为最之哉?’”中提出了“常心”的概念。郭象注:“得其常心,平往者也。”成玄英疏:“得真常之心者,固当和光匿耀,不殊于俗。”[1]106这里的“常心”,是褒义的,是从正面来讲的,显然异于《庄子》中出现的其他认知意义上的“心”,而具有形而上的普遍意义。《庄子》也只有此处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心”。第三,《天地》篇“其心之出,有物采之”一句,是说真人的“心”并不是时常在场的,“非先物而唱”,而是“物采之而后出耳”[1]223。成玄英疏曰:“采,求也。夫至圣虚怀,而物我斯应。自非物求圣德,无由显出圣心。圣心之出,良由物采。欲和而不唱,不为物先。”[1]223这里面有几层意思值得注意:首先是真人并非无心,而只是说真心应物而起。其次是物求圣德,可以显出圣心。可见心有独立于气化之物的特殊意义,同时气化之物也有引发圣心得以开显的作用。最后是说真心与气化之物“和而不唱”,可见《庄子》不仅有气化流行,一任自然之意,也有心物和谐之意。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庄子》中的“心”对于“气”而言的重要作用,亦可见《庄子》中“心”之涵义的复杂性以及心气、心物关系的复杂与暧昧。第一,《庄子》中“心”“气”并提,虽然说“通天下一气”,但并没有处理好“心”和“气”的关系。若说“通天下一气”,那“心”是不是“气”呢?虽然有一处以“神气”言心,但仅此一件并不能解决问题。第二,人本来处于“气化自然”之中,应当本来就如山野草木鸟兽一样无心而处世,又为何不能逍遥呢?此“不能逍遥”的状态是因何而起又如何能起的呢?这个问题犹如佛教《首楞严经》中富楼那尊者问释迦牟尼的:“清净本然,如何忽生山河大地?”《庄子》并未加以注意,只从不能逍遥而求逍遥入手,而未关注逍遥如何又不能逍遥。实际上 也是“心”“气”关系的问题,即一任自然之气,而使人不得逍遥的心知又从何而来。第三,荀子批评庄子说“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确有道理。所谓“蔽于天而不知人”,实际上可以理解为“蔽于气而不知心”。若一任自然气化,那么一切人为施设就只能是负面意义的了,仅以美学而言,则所谓“艺术创作”就不可能而且不应该了。这足可表明“心”“气”关系问题是《庄子》哲学的盲点。
盲点造成困境。“心”“气”关系的模糊不清,导致“听之以气”缺乏切实可行的逻辑通路。“听之以气”如果可能,那么其运作机理是怎么样的呢?“听之以气”状态下的审美经验究竟是不是一种心知呢?如果不是心知,那么“气化自然”如何能自见“气化”呢?
引申
面对《庄子》气论哲学的理论盲点和理论困境,我们将之理解为“理论生长点”更公允、恰当一些。《庄子》之后,宋明儒对气论有所发明,更对“心”“气”关系有深入论述。到刘宗周、黄宗羲师徒更畅言“心即气”,或可在其美学意义上予以重视。另外,佛教中圭峰宗密在《原人论》中也以唯识学中心识的“相分”论气,而以“见分”论认知之心;藏传佛教中即心即气,心气不二的观点虽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和宗教意味,但也值得借鉴。
仅就美学而言,“气论”奠定了中国自然美学的根基,但若“心”“气”关系得不到圆满解决,中国自然美学就得不到确立。因此,“心”与“气”的关系,不仅是一部《庄子》的薄弱处,更是自然美学的核心问题。
[1]成玄英.庄子注疏[M].郭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2]王夫之.老子衍·庄子通·庄子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陈鼓应.《庄子》内篇的心学(下)——开放的心灵与审美的境界[J].哲学研究,2009,(3).
[4]李道湘.从《管子》的精气论到《庄子》气论的形成[J].管子学刊,1994,(1).
[5]黄柏青,朱登吾.庄子的气论及其哲学、美学意义[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04,(6).
[6]王洪泉,王赠怡.庄子论“气”[J].中华文化论坛,20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