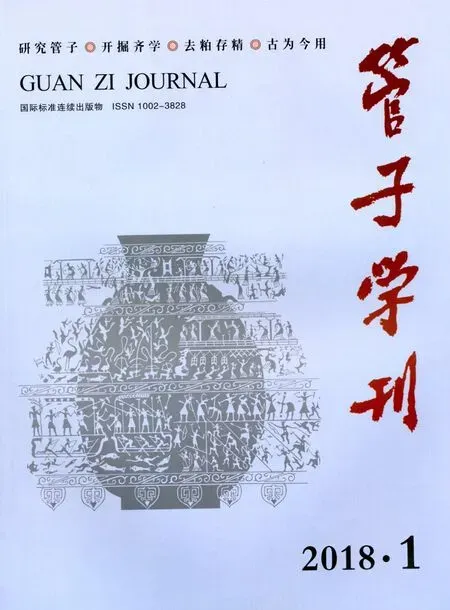“兼别之辨”与先秦儒墨论战的几个诠释维度
田宝祥
(首都师范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048)
一、逻辑意义上的“兼别之辨”
“兼以易别”四字出自《墨子·兼爱下》,简言之,即以“兼”之道取代“别”之道。“兼”有两个层面的解释:一是整体性、包容性,在逻辑上取全集;二是同一性、共通性,在逻辑上取交集。在逻辑上,“兼”与“别”对立;在价值判断上,“兼”与“别”却以某种相对的方式共存。在墨家的思想系统中,“兼以易别”也被处理为“同”与“异”的关系。同的状态维持一段时间,在逻辑上必然会导向异,由于同比异的属性更稳定,所以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意义系统下,异必然又要归于同,这时的同已是“大同”,比起初始状态时的“小同”,显然要更充分,也更兼容。
“爱”的对象有二:“他者”和自己。儒家认为,“他者”乃由亲人、陌生人以及人以外的其他生命体构成,即孟子所谓“亲亲而仁民,任民而爱物”的等差结构。《墨子·大取》则说:“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己在所爱,爱加于己。论列之爱己,爱人也。”墨家认为,爱人就是爱一切人,陌生人、亲友、父母乃至自己,皆在所爱的范围之内,并无厚薄之分。如果说儒家之“爱”强调的是现实状态下的有限可分,那么墨家之“爱”则强调理想状态下的无限可分。有限可分的必要条件是“别”,即有层次、有亲疏地分配“爱”;无限可分的必要条件则是“兼”,乃无差别、公平正义地分享“爱”。“爱”,既可以是具有实效性的切实行动,也可以是自主、自觉、自发的心理活动。当然,意念的生发是一步,行为的落实又是一步,二者皆备,即表明“爱”的动机与结果在逻辑上达到了统一。在这个意义上,便可说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是一种不分彼此、不分你我的无血缘差别、互惠互利之爱,更是一种具有人本性、平等性、超越性、理智性、兼容性、开放性、实践性的人道主义[1]。在墨家看来,良好生活的实现,受两大因素的制约:第一,社会正义的长存;第二,能力价值的开发。“‘兼爱’意味着对每一个主体的独立主体的平等地位与权利的承认。‘兼相爱’与‘交相利’之‘相’与‘互主体性’是相通的,即相互承认对方是独立的主体。而‘互主体性’是确立现代社会道德的前提,因为现代公民道德理念的形成正是在承认‘互主体性’前提的基础上,通过个人与个人之间,主体之间的平等交谈、真诚对话,而实现共同诉诸理性,以达到道德共识的达成。”[2]一个个体,若无法在社会共同体当中获得价值上的认同,其德性便永不能自足,而“兼以易别”的本质要求即在于,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被这个社会平等地接纳,并被充分地纳入“价值理性”的考量之中。
有学者认为:“泾渭分明的主观动机和理论初衷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儒家与墨家之爱的思想内涵和心理机制之别。如果说孔孟之仁的精神实质是别的话,那么,墨子兼爱的原初含义则是兼;如果说仁的心理机制是由己及人的层层推进的话,那么,兼爱的心理机制则是放射性的释放和平铺。”[3]这种说法在固化“兼”这一理念时,也无形中遮蔽了“爱”作为道德本原的价值属性。从本质上看,墨家之“爱”呈散点状,无边界但有分疏。“兼爱”作为一种伦理原则,是无等差、无亲疏的;作为一种伦理模式,则是可操作的、可实践的,这一点恰好回应了儒家在亲疏问题上的非难。儒家认为,人的爱心善行,受制于时间、空间的限制,不可能无节制地施予,因而当自己的父母和陌生人处于同等危难的状况时,必然要遵循“亲亲”之伦理次序,先救父母于危难之中,而不是违背孝义之道、第一时间向陌生人伸出援手。问题在于,这样的例子在逻辑上并不周全。首先,一亲一疏两个人在同一空间下陷入同一种的危险,这只能是一种假设,也没有生活中加以还原的可能。其次,如果可以假设遇险的一方有亲疏两人,那么是否也可以假设施救的一方也有两人、甚至是亲亲关系一一对应的两人?退一步讲,即便儒家举出“亲人和陌生人同时落水该先救谁”这样一个颇具现代性伦理意味的例子来论证“亲亲相隐”或“亲疏有别”,也并无多大说服力。第一,就时间的绵延这一意义上讲,一人总是先于另一人而落水,不存在绝对同时落水的可能;第二,即便两人落水的时间相差无几,其落水的远近程度、危急状况必有不同。这就说明:第一,情感的侧重与行动的实现,很多时候并不一致;第二,儒家所谓的“有等差之爱”,在伦理道德的超越与永恒意义上存在太大的局限性,对于现实的考量也似乎不完备。
二、“兼别之辨”在伦理意义上的展开
先秦时期,仅有儒、墨两家从公共伦理的角度探讨了“爱”的话题。在胡适看来,“墨家的爱,是‘无差等’的爱,孔门的爱,是‘有差等’的爱”。“墨家重在‘兼而爱之’的兼字,儒家重在‘推恩足以保四海’的推字,故同说爱人,而性质截然不同。”[4]144在“兼爱”“别爱”的看法上,冯友兰与胡适并无不同。冯友兰也认为:“墨家主张爱无差等,而儒家主张爱有差等。换句话说,在爱人的问题上,墨家强调同等,儒家强调差等。”[5]82胡适、冯友兰作中国哲学史,皆侧重儒、墨两家思想的差异性,而较少从源流上讨论二者的互补关系。
《墨子·兼爱下》说:“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又说:“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也。”故曰:“兼以易别。”为什么要“兼爱”呢?兼则利,不兼则不利。“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不周爱,因为不爱人矣。”(《墨子·小取》)在墨子看来,如果“天下人皆相爱”,则“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
《墨子·大取》:“智亲之一利,未为孝也,亦不至于智不为己之利于亲也。”墨家认为,“亲”与“孝”内在地包含于“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准则之中。“亲其亲”“孝所孝”作为“兼爱”结构中的一环,并不具有多么突出的地位。在墨家看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对待普通人、陌生人尚且如此真诚、无私,对待自己的父母又岂有不周全之理?一个心地善良的年轻人,同时将仅有的两块干粮,分别给了自己的父亲以及路边的一个旅人。在这个事情上,年轻人即很好地践行了墨家的“兼爱之道”,“孝”和“爱”的伦理原则都得到了体现。事实也证明,对自己父母的孝与对他人的爱,在动作发出者那里可以兼顾,也可以有效地分配好。父亲觉得自己没吃饱、抱怨儿子不孝,那是父亲个人道德估量的问题,儿子并没有做错。可以说,儒家的“推而广之”,乃人的情感关怀依循一定的内在结构而展开,是有条件、有限度的。而墨家的“兼而爱之”,“一方面,可以说把仁的群体性内涵发挥到了极致;另一方面,又不像孔子那样以孝悌为本推出仁爱,而是主张以兼爱为本推出孝慈”[6]。由此可见,“墨氏兼爱,是无父也”之类的论断,更似情绪化的言语攻击,而非事理层面的反驳。
“兼”作为墨家思想体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既有历史维度下的确定性,又有信仰意义上的抽象性。其确定性体现为对实在物的基本属性的规定;其抽象性则体现为“天”“圣王”“民”三者之间隐秘的“尚同”关系。在墨家那里,“节用”“节葬”“非乐”所体现出的,大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价值观;但同时墨家也讲超验的“天”和“鬼”,这就避免不了要披上神道设教的外衣。所以,理解墨家的另一关键在于,借助“天”“君”“民”三种视角来把握其内在价值与精神实质。墨家显然认为,个体是否具有强烈的公共道德和仁义观念以及国家能否形成平等、兼爱、互利、包容的生存格局,其实取决于“兼以易别”这一伦理原则能否得以确立。
三、从文本角度看儒、墨思想之关系
(一)“心”“礼”问题
儒学在宋明那里有“人心”“道心”两种说法。具体而言,“从人的人所有之性发出者,谓之人心。从人的人之性发出者,谓之道心”[7]40。所谓“理一分殊”,亦是由这个意义出发而言的。可以说,这一系列涉及主体道德问题的讨论,乃始于孟子。相较而言,孟子更侧重儒学之内在建设,即仁人之“心”的生成与扩充,而荀子更侧重儒学之外在建设,即仁人之“礼”的开显与普及。众知周知,先秦诸子中,墨子反礼最甚,故而荀子在总结诸子学说时,对墨家的批判也最重。荀子指出:
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荀子·天论》)
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悬君臣。(《荀子·非十二子》)
先王之道,礼乐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于道也,犹瞽之于白墨也,犹聋之于清浊也,犹欲之楚而北求之也。(《荀子·乐论》)
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非将堕之也,说不免焉。(《荀子·富国》)
蔽于用而不知文,……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荀子·解蔽》)
由上可见,在“礼”的问题上,儒、墨是坚决对立的,儒家隆礼,而墨子反礼。儒家以“礼”为价值范式,来疏导人趋于“仁”。子曰:“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所谓“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荀子·议兵》)。儒家以“礼”定“名分”,所谓“名分正”则“仁”,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乃是“君子”人格的基本要求。墨家则把“把道德问题视为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及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而他所主张的‘兼爱’,也就成为一种不分亲疏、不论贵贱、爱人如己、一视同仁的无差别之爱”[8]。
(二)“追古”“立圣”问题
儒、墨两家思想立场之分明,在“追古”“立圣”方面亦有体现。儒家法周,孔子之前,有尧、舜、禹、汤、文、武以及周公七位圣人;荀子时,有“法先王”与“法后王”之分;韩愈时,“道统”之名既正;宋明时,道统之路方才开出。墨家法夏,立圣首推大禹,对于“圣人”之道的推崇,并不亚于儒家。在传世本《墨子》的53篇文字当中,“圣人”一词出现了45次,与圣人有关的“圣”“圣王”“元圣”“先圣”等语词加起来,更是超过了160次[9]80。而在《论语》文本中,“君子”二字达106次之多,“圣人”二字却只出现了4次。
就墨家“十论”的思想体系而言,“追古”“立圣”的意义十分显著。首先,圣人、圣王作为天之意志、民之德性的代表,合天人之意、行“兼王之道”,在任何一种历史境遇下,都是“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万民衣食之所以足”(《墨子·兼爱中》)的有力保证。其次,从思想启蒙的意义上讲,圣人、圣王作为“兼爱”“非攻”“尚贤”等“十论”的先觉者、先行者,既是诸理念在公共视域内得以确立的第一因,又是民众在现实生活中得以效仿的范例。
(三)“性”“命”问题
儒家论“性”,首推孟、荀。孟子言“性善”,荀子则言“性伪合”。《荀子·礼论》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在荀子看来,“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唯有“性”与“伪”相合,方能“成圣人之名,就天下之功”。墨子论“性”,立场近于荀子,所谓“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墨子·所染》),更强调外在之熏染对于“性”的影响,以及后天之“命”对于人的改造。
荀子言“性”,不为究本,重在论“礼”,这也是荀、孟在人性问题上的一大差别。这一问题延伸下去,便是“内在之仁”与“外在之礼”的结构问题。以蒋庆为代表的政治儒学家认为,“内圣”与“外王”作为儒家两条重要的理路,结构上并无先后,逻辑上也非前者导向后者。以牟宗三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儒家则秉持“内圣开外王”的理念,并从这个意义出发,将“为己”“修身”推向“亲亲”“仁民”“爱物”的层次,从而建立起了一套“天道性命相贯通”的道德形上学架构。然而这套看似丰满、严密的精神大厦,却因为过分强调德性的自足以及对传统的忠实,而丧失了对于新意义与新价值的追寻,致使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在现实的生存困境里面,再难有磨砺自我的激情和动力。由于缺少了墨学“兼以易别”“兼爱非命”思想的内在张力以及诸子学说的制衡、牵扯,中国文化从此便飘荡于儒家“德性”“克己”与道家“逍遥”、佛家“解脱”这几艘意义孤立或断裂的小舟上,再难显现鲜活、迸发的生命力和与宇宙、自然相契合的超越人格。而墨学的中绝,也使得中国文化在理性、逻辑性、创造性和自由意志等诸多层面皆受到严重的损害。
四、从“兼”与“力”的角度看墨学精神之本质
墨子言“兼”,旨在促成“智”与“力”合、“志”与“功”合。从动机上讲,墨子是十足的道德论者;而在结果上,却部分地导向了功利主义。墨家主张义利统一、既“尚利”又“贵义”,其本质是一种集体本位的功利主义,既不同于边沁的个人功利主义,更有别于法家的极端功利主义。足见,“孔子与墨子在‘爱人’的抽象道德原则及其履行角色道德义务的基本道德要求上,其实有着共同或基本相同之处”[10]。
墨家尚“力”,高扬理性与实践,节制情感与快乐。《墨子·经上》说:“力,刑之所以奋也。”《墨子·非乐上》说:“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兼爱中》说:“夫挈太山而越河济,可谓毕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墨子认为,“力行”是一个社会由衰败向兴盛转化的根本手段。“力”的丧失,意味着人的退化,也预示着人对于自我价值的放弃。而在应对“乐”“葬”“命”等问题时,墨家也显然站在一个更为理智、公共的层面。在墨家看来,无论谁,都有机会通过知识和劳动改变自身的命运,桀、纣的时代再缪乱,也阻挡不了个体生命蓬勃发展的趋势与人类历史向前演进的浪潮。
近些年,以黄蕉风、顾如、南方在野为代表的新墨家,正通过自身的努力,使墨学的复兴由愿景变为现实。在2015年的国际新子学研讨会上,黄蕉风发表了《告别路径依赖,建构大乘墨学》的会议论文,创造性地提出了“大乘墨学”的理论建构,表现出与传统墨学划清界限的决心。同年底,饶宗颐国学院发起了“普适价值再思”之主题论坛,作为新墨家代表人物、论坛召集人的黄蕉风,再一次成为论战的焦点。他认为,墨家的“兼爱、非攻、交利”思想,可以成为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与“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别人”(基督教)之后的第三种全球伦理“黄金律”。黄蕉风的另一思想创造,乃是围绕“墨耶对话”所展开的一系列讨论。他认为,墨家所明之“鬼”,已然超越了“人文”层面的意义而具备了“人格”意义;所推之“天”,比之儒家“推恩”式的泛爱,更接近基督教的博爱。尽管马来西亚学者姚育松在《中国新墨家的出现》一文中批评墨家是绝对的极权主义,但不可否认,在应对现代性的问题上,墨学完全有资格站出来,在中国文化与普适价值之间确立一种全新的范式。
总体而言,儒家隆“礼”,其根本目的在于体达人的情感,消解个体生命中的负面因素。换言之,乃是为安置道德、为内心的“乐感”寻找一个合理的外在依据。而墨家言“兼”与“力”,本质上是为启蒙,它重在激发人的价值与能力,使每一个个体都能与现实世界有效互动甚至参与历史进程。客观来看,这当然是一种理想模态,但不可否认,这亦是墨学十论的要义所在。
[1]张斌峰.张晓芒.新墨学如何可能[J].哲学动态,1997,(12).
[2]张斌峰.墨子“兼爱”学说的新透视[J].中国哲学史,1998,(1).
[3]魏义霞.“兼以易别”——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比较[J].江淮论坛,2012,(2).
[4]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6]刘清平.论墨家兼爱观的正当内涵及其现代意义[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
[7]冯友兰.新原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8]黄勃.论墨子的“兼爱”[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4).
[9]孙君恒.墨子伦理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10]孙理兴.论孔墨“爱人”伦理思想之异同——兼谈现代伦理建设[J].道德与文明,19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