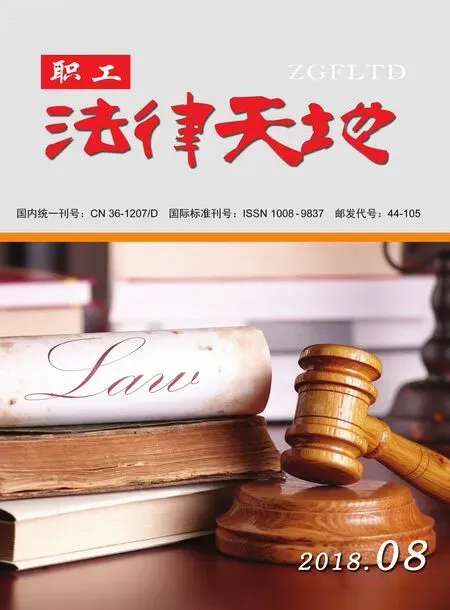大数据时代下电子取证的程序规制
——以个人信息保护为视角
郭凯文
(730070 甘肃政法学院 甘肃 兰州)
一、大数据时代电子取证的变迁
在计算机技术刚兴起之时,网络的发展还不够成熟,因此早期的电子取证大都在单机体系中进行,其既包括单机系统自身产生的数据,也包括在网络空间产生并留存在单机系统中的数据。但伴随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传统的计算机技术已经不能涵盖呈指数增长的海量数据,电子取证也进入了“大数据时代”。
1.取证范围扩大化
(1)电子介质种类繁多。在智能化的快速发展下,除了传统的计算机外,大量的电子介质涌现。这些扩大了“单机”体系的物理范围,成为电子取证的新的对象。
(2)互联网的全覆盖。在移动通信技术以及无线网络的发展,互联网渗入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行为轨迹通过各种智能设备被记录于网络中,其结合起来形成个人的巨大信息库。
2.数据挖掘复杂化
大数据取证需要从海量的数据源中挖掘有关证据,分析其价值和关联性,并进行电子数据展示。而伴随着数据爆发而来的是电子取证难度的增大。基于上文所提及的,大数据强调的是数据的混杂而非精确,大数据所追求的是数据的相关性。
二、大数据时代电子取证的法律困境
1.侵犯隐私风险
大数据一方面将大量计算资源、存储资源与软件资源连接在一起,形成巨大规模的共享虚拟IT资源池。用户之间的网络交互活动的数据皆自动上传存储其中,在进行取证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另一主体的隐私数据。
另一方面,大数据所使用的云计算是将数据存储在云端,其是属于相对开放的存储环境,所有的用户的数据信息皆存储其中,随时面临着泄漏的风险。
2.主体权限不明
在我国对电子取证的主体主要是公权力机关,其既包括司法机关还包括行政机关与权力机关。对于不同的权力主体,其对数据的调取权限应当根据其职权性质加以区分。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除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
3.主观推测倾向
基于上文所提及的大数据的相关关系是一种弱关联关系。实际上,大数据的相关性是基于机器逻辑的相关关系 。大数据的关联性与品格证据的关联性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一般来说,品格证据并不具有当然的可采性,其适用是 “间接性的”。在我国证据的认定必须具有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而大数据取证虽然具有一定的弱相关关系,但就其真实性或是客观性而言,确实有待商榷。虽然其数据来源基本真实,但其所整合和分析的方法确实主观选择的结果。
四、电子取证程序的规制路径
1.建立层级化个人信息保护体系
在对个人信息进行层级化保护前,应当对个人信息进行基本的私密程度排序。即请求个人信息控制者对已经发布在网上不恰当的、过时的、会导致其社会评价降低的信息进行删除的权利。个人可以决定向谁告知哪些与其本人相关的信息,哪些可以隐瞒。
虽然其对大数据的数据库无任何影响,但是其对于个人信息的层级化分类具有重要意义。针对一些数据进行一定的层级化保护,由低至高,对有删改的完整原始数据予以最高层次的保护。
2.细化电子取证主体权限
在对个人信息进行层级保护的基础上,对公权力机关调取个人数据的权限进行细化,以达到与个人信息层级保护的平衡。公权力的拥有者在利用大数据取证打击犯罪的同时,还应当保留一定的底线。人享有对自身信息处理和支配的权利,国家公权力必须予以尊重并受到限制。
对于上文中所提及的有删改的完整原始数据作为最高层级的保护,只能由侦查机关基于司法职权的行使予以调取或是人民法院根据审判的需要予以调取,除此之外,其他公权力主体在调取此类信息数据前需告知数据所指向的人员。
3.完善电子取证的特殊证据规则
一方面,对大数据取证的过程实行全程公证、全程记录的方式,客观的记录大数据取证的客观性,将取证过程予以透明化,既能保证并坚定证据的真实性,又能有效对取证活动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对其证明力必须加强对补强证据的适用。当以大数据取证的数据作为事实认定的主要证据时,还需要其他的法定证据类型予以补强认定的事实,以形成能够尽可能还原事实的证据链。
五、结语
在面对大数据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冲击时,侦查机关在侦查技术的极大革新、侦查手段极大丰富时,应当在“人性尊严”前予以克制,保持对个人信息的尊重的基础上,建立层级化个人信息保护体系,完善电子取证程序,从而实现更好的保护个人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