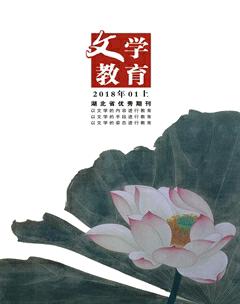论传统隐喻修辞观的现代困境
王飞
内容摘要:中国固有的传统隐喻修辞观念,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与西方话语体系孕育的隐喻观念存在交错共存的现状,造成研究及理解上不必要的障碍,其表现是多方面的,但究其实际,隐喻使用范围广泛,而其概念也应依据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区分。
关键词:隐喻 修辞 现代
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转型,国内的学术发展与国际融合日趋活跃,在七十年代欧美语言学界“隐喻热”的波及下,国内学者对隐喻的关注度逐渐增加,乃至在九十年代形成一个隐喻研究的高潮,至今仍然风起云涌,不但研究水平不断提升,而且研究内容日趋深入,从本体研究到应用型研究都有相当可观的、有份量的成果出现,为国际隐喻研究贡献了中国学者应有的学术智慧和学术力量。由于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学术发展迥异于以往,带有明显的现代学术特色,无论是学术研究的规模还是质量都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而本文所探究的也正是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在对隐喻这一概念的探究上所体现出来的学术创新,因此,在学界还没有对这一历史时期赋予它以新的称谓之前,本文还是参照一些学者的说法,姑且以“新时期”标目。
对于“隐喻”一词,中国的研究者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它是我国固有的文学表达方式。在上古时期的《诗经》之中已经使用了“比”的艺术手法;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大量使用比喻手法,如《孟子》、《荀子》、《墨子》等;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全面论述了隐喻的定义、特征、分类和功能[1];南宋陈骙的我国首部修辞学专著《文则》中,把“取喻之法”总结为十种,其中即明确标有“隐喻”一种。宋元以降,文学作品中的比喻就更司空见惯了。在一般的修辞学著作中,“隐喻”也往往被看作是“比喻”手法的一种,等同于“暗喻”。但是,随着人们对隐喻研究的深入,隐喻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修辞,而是与语言学、认知科学、文化哲学甚至心理学等学科相融合的一种表达方式、思维习惯,或艺术风格。对它的理解,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
二
“隐喻”作为一种文学表达方式,最主要的使用领域在文学文本,因此传统观念中,隐喻一直被视为一种文学修辞手法。这种观点长期以来并没有表现出与时俱进的发展态势,而是作为一种静态知识被人们传播和接收,呈现出一定的封闭性,相对于迅猛发展的现代“隐喻学”研究明显表现出知识的固化,而没有任何与其它学科或知识领域交轨的迹象。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在谈到一般修辞学著作时这样描述说,“一些讲修辞的书……在近于敷衍似的稍微讲讲修辞原理之后,就把几十个修辞格一字摆开,作为读者学习的对象”[2]。吕叔湘先生所说的是当时比较普遍的情况,一般的修辞书主要是介绍修辞学习的相关知识,尤其是注重对辞格的介绍,总结归纳出比喻的各种修辞格式,形成固定搭配,甚至对常见喻词也予以罗列囊括。这一时期比喻的概念可以比较典型的概括为:“比喻,又叫譬喻,俗称打比方,就是根据联想,抓住不同事物的相似之点,用另一个事物来描绘所要表现的事物。”[3]而暗喻的概念则是“字面上不说是在打比方,而是当作实有其事来表现。常用‘是、‘变为、‘变成一类比喻词来联系本体和喻体”[4]。大多数的修辞学著作或语言学著作对比喻及其分类的描述,与此大同小异。
出现这样大面积雷同的原因所来有自。早在1932年,著名的修辞学家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所列38种辞格中区分了“譬喻”所包含的类型,即是明喻、隐喻、借喻三类[5]。但这一说法也并非没有不同声音。如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即指出譬喻包括明喻、暗喻、借喻和象征[6]。
对于当时的修辞著作的这一现状,有研究者指出“從严格意义上讲,我们国内以系统的认知语言学为视角研究隐喻的历史是非常短暂的,因为国内关于隐喻的研究始终是与‘比喻的研究结合在一起的。”[7]国外的认知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起步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认知体验为其哲学基础,它的研究领域已经触及到了思维层面,这与单纯的语言修辞自然有着明显的不同。
但是传统修辞学所解释的比喻规律却与认知语言学所提出的“隐喻”概念有密切联系。在传统修辞学视角下,隐喻是与“明喻”、“借喻”并举的喻格,其构成包括本体、喻体与喻词[8]。这与西方的隐喻研究不谋而合。
三
在现阶段,对隐喻的研究视角是多维的,而影响最大的是认知语言学视角。随着认知领域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从认知的角度对“隐喻”的理解又有所不同。并且,由于认知学科的巨大影响,隐喻的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比较典型地体现在类型上,隐喻的范围扩大了。戴卫平《词汇隐喻研究》中认为,隐喻包括了“提喻、明喻、讽喻、引喻、换喻、拟人或称为活喻、夸张或称为夸喻、拟声或称为声喻”,“借代也称为换喻”、“移就也称为转喻”、“曲言也称谦喻”,并认为委婉、迂回、换称、通感、仿拟、拈连这五种修辞格“如作深入考虑,也与隐喻有关”[9]。这样,纳入隐喻系统的辞格竟达17种之多,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像这样名目繁复的喻格,并非这本书所独有,还有一些命名奇特的喻格,如赵毅《缩喻探微》(修辞学习,1994.3)、田国华《较喻及其分类》(盐城教育学院学报,1995.2)、寿咏逊《顶喻的特征分析》(语文应用与研究,1997.2)等,基本也都属于隐喻的范畴。对于这一现象,有研究者指出:“隐喻同其他修辞格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修辞家族,各成员之间具有一定的‘家族相似,即‘隐喻性。[10]”
传统修辞观念在新时期形成了概念混乱的情况。比如“转喻”,在戴卫平的《词汇隐喻研究》中,认为“移就也称转喻。把形容甲事物的修饰语(本体)移动来修饰乙事物(喻体),通常把形容人的修饰语移用于物。移就就是把属于甲范畴的修饰语移来修饰属于乙范畴的事物。这是认知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中关系隐喻的典型特征,把一个词从一个认知域投射到另一个认知域,因此被称为‘转喻。”[11]而张光明的《认知隐喻翻译研究》则认为:“转喻重在取代,用一事物的名称取代另一事物,其构成的基础在于这两个事物之间存在常规共存的关系。无论是局部与整体、特定与普通,还是具体与抽象、原因与结果以及工具与工具使用者,等等,两者之间都存在着一种相互联系,不管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都会给人的心理造成空间上或时间上的一种“邻近”感,从而引起联想思维活动。所以说,转喻基于常规共存的由此及彼的邻接联想,喻类辞格基于相似联想。”[12]这里,从张光明介绍的特征来看,说的显然是借代,他把借代称为转喻,这和戴卫平称“移就”为转喻大不相同。endprint
再如隐喻与转喻的关系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转喻是隐喻的一种,如王寅认为:“当今广义的隐喻范围十分宽泛,包括明喻、转喻、提喻、引喻等。”[13]而上文中戴卫平的著作则是纳入隐喻之下的,谢之君也认为“从基本概念隐喻的角度分析,拟人、换喻等辞格不过是概念隐喻的不同类型”[14],同样把换喻归属于隐喻之下。此类的看法还有不少,这给隐喻和转喻概念的理解造成了混乱。究其原因,恐怕与中西方对“metap-hor”的理解不同以及汉语对译的差异所致。胡亚敏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与当代中国》一书中说,随着西方的隐喻概念译介到中国,“现代汉语修辞意义上的隐喻自此涵盖了原本与之并列的明喻、暗喻、奇喻、转喻、通感乃至象征等概念。”[15]这似乎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解释两者之间不同的原因在于,隐喻概念在传入中国的环节中出了问题。事实上普遍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在诸多受西方认知语言学影响的论著仍并举“隐喻”与“转喻”,把两者视同平级关系。如高原的《古典诗歌中隐喻与转喻的互动》在《绪论》中分别论述了两者认知特点的不同,甚至说“转喻甚至比隐喻更普遍”[16],似乎是要把两者之间的包含关系倒过来了。这种混乱局面,给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造成了不小的困难。
这样的混乱在隐喻与暗喻的关系上也有体现。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两者含义相同。有的研究者认为二者涵义相同,“暗喻也叫隐喻,是各种语言普遍采用的一种修辞手段。暗喻是根据事物或现象在某些方面的类似性、共同性,用表达另外事物的词语来表达该事物或现象,通过这些词语反映出两事物相似之处”[17]。即是从修辞学的角度,把两者等同于同一事物。此类修辞学视野下的隐喻观念是一大类型,如仲掌生认为“隐喻是形象化的语言,是比喻中最普通的一种”[18]。与之对举的有“明喻”,两者的区别是两者使用的比喻词不同,明喻一般使用“好像”、“如同”;隐喻则使用“是”、“成了”等。二是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差异。如何晓琪指出:“较准确的说法应是,隐喻是一种把某一名称或属性赋予另一事物的辞格,其含义不能照字面解释。”[19]三是认为隐喻的含义大于明喻,如张利生指出:“metaphor一词在汉语中译作‘暗喻或‘隐喻,事实上,它比汉语辞格‘暗喻的范围要广得多,涉及汉语中‘暗喻、‘借喻、‘比拟、‘转类、‘移就等修辞方式。……将暗喻分为述谓性和修饰性两大类型。述谓性暗喻包括‘主-系-表和‘主-谓-宾两种结构;修饰性暗喻包括‘喻体-本体修饰和‘转移修饰型两种结构。”[20]
出现以上对概念的探究,体现了可贵的学术努力,表明研究者对隐喻深入拓展的学术兴趣。
在众多隐喻概念中,郭琳则给了我们一个更为全面的定义,他说:“最后,或许可以试着对隐喻概念作一种多维的界说,尽管这种界说仍然需要有所限制。首先,文学批评意义上的隐喻是一种基于关联性想象的思维方式;其次,在文学和话语的意义上,隐喻是一种修辞方式;最后,隐喻是我们与客观世界产生关联的途径,是一种对人类思维之本质的表述形态。隐喻使我们认识到思维是一种从已知向未知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对意义的探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以隐喻的方式把握人类在文学艺术中所创造出的审美层次的意义,而且以隐喻的方式去把握自身的思维与语言”。[21]
如此纷杂的隐喻概念,对研究者来说,去取成了一个大问题。关于“隐喻”概念界定,可以预见的是仍将继续下去,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在没有得出那个我们期待的完美结论之前,我们的一切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可能都是在做某种准备。也许我们可以参照戴维·E·库珀的建议:“如果一个预备性的讨论都必须等待这些争论的判决,那么我们的讨论将难以为继。因此,我将暂时采取一种自由主义的策略:在必要的情况下,我将自由地谈论隐喻句子及其使用、隐喻词语及其使用,以及隐喻概念、思想、图像等内容。”[22]这种开放的视野,对隐喻概念摆脱现代困境不失为一方有效的解决办法。
参考文献
[1]张沛《隐喻的生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2]吕叔湘:《汉语修辞学·序》,载王希杰《汉语修辞学》卷首,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3][4][8]王希杰:《汉语修辞学》,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282页、第283页、第282页.
[5]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69页.
[6]朱自清:《诗言志辨》,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83页.
[7]王文斌:《隐喻的认知构建与解读》,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9][11]戴卫平:《词汇隐喻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2页、第2页.
[10]张沛:《隐喻的生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
[12]张光明:《认知隐喻翻译研究》,国防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196页.
[13]王寅:《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2页.
[14]谢之君编著:《隐喻认知功能探索》,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
[15][21]胡亚敏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与当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69页、第323页.
[16]高原:《古典诗歌中隐喻与转喻的互动》,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参见第8页.
[17]孙淑惠:《俄语隐喻浅谈》,《外语学刊》1980年第3期,第15-53页。
[18]仲掌生:《英语隐喻探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第1-8页.
[19]何曉琪:《隐喻隐喻同明喻的区别》,《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1年第6期,第13-16页.
[20]张利生:《浅谈metaphor的结构》,《外语与外语教学》1991年第6期,第15-16页.
[22][英]戴维·E·库珀(David E. Cooper):《隐喻》,郭贵春,安军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作者单位: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