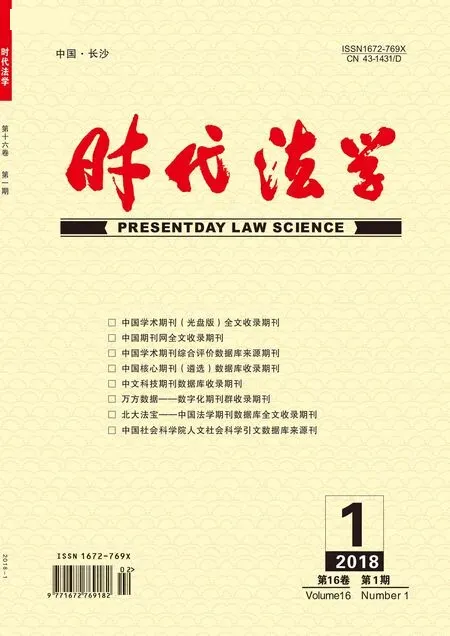浅析灭绝种族罪中的“受保护团体”*
黄志雄,应瑶慧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一、灭绝种族罪的历史沿革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血腥地消灭整个团体人民的场面时有发生。这种犯罪的表现各异,就像引发它的动机和实施这种犯罪的时间一样具有多样性。灭绝种族现象在20世纪表现得特别突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居住在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就是一场种族清洗运动的受害者,死亡人数达到50~100万人*Frank Chalk and Kurt Jonassohn, The History and Sociology of Genocid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39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超过600万犹太人沦为希特勒发起的第三帝国灭绝种族政策的牺牲品*Raul Hilber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3rd Edi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3.。
在纽伦堡审判中,对主要战犯的审判集中在纳粹进行的侵略战争和他们对战争的法律和习惯的违反方面*R Lemkin, Axis rule in Occupied Europe,1973, p.79.。纳粹的种族灭绝行为本身并没有包括在内,而是作为一项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尤其是“灭绝”和“迫害”加以涵盖了*IMT, Judgment of 1 October 1946, in the Trail of German Major War Criminal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Sitting at Nuremberg; Germany, Part 22, pp.463 et seq.。在1946年12月11日的决议*UN Doc. A/RES/1/96(1996).中,联合国大会第一次对“灭绝种族罪”下了定义,并且决定这是一种国际法项下的犯罪。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获得授权起草了一份《灭种公约》的草案。在经过修改与润饰后,这份草案被提交给了法律委员会*这些草案重印于William. A. Schabas, Genocide in International Law: the Crime of Cr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553 et seq.。1948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在第260A(III)号决议中一致通过了该公约*RES 3/260, UNGA(1948).。
《灭种公约》的第2条规定:灭绝种族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个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团体,犯有下列行为之一:(1)杀害该团体的成员;(2)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3)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声明;(4)强制实行办法,意图防止该团体内的生育;(5)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这一规定,标志着这项罪行第一次在国际法律文件中得到了阐述,也是直到此时,“灭绝种族”才有了一个详细而相当技术性的作为国际法上罪行的定义*William. A. Schabas, Genocide in International Law: the Crime of Cr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4.。
但是,灭绝种族的行为并没有因为《灭种公约》的通过而就此消除。二战后,地区性武装冲突不断,70年代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的大屠杀,90年代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大屠杀,包括在孟加拉、布隆迪和埃塞俄比亚等地,都发生过这种可怕的罪行*Frank Chalk and Kurt Jonassohn, eds., The History and Sociology of Genocid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258-384。在《灭种公约》签署整整半个世纪以后,卢旺达国际刑庭宣布了对卢旺达塔巴市市长阿卡耶苏(Akayesu)的判决,才第一次为《灭种公约》的理想“带来了生命”*Payam Akvahan, The Crime of Genocide of ICTR Jurisprud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3(2005), p.989.。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设立的前南刑庭、卢旺达国际刑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 以下简称“卢旺达刑庭”)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等国际刑事司法机构,都将灭绝种族罪作为最严重的国际犯罪加以惩治。《前南斯拉夫国际刑庭规约》第4条第2款和《卢旺达国际刑庭规约》第2条第2款原封不动地采纳了《灭种公约》第2条关于灭绝种族罪的规定。在之后《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下简称《罗马规约》)的谈判中,曾经有代表意图把政治团体和社会团体包括在这个定义之中,然而,大多数代表倾向于不修改习惯国际法已经承认的这个定义,因而拒绝了扩大这个列表范围的提议*Otto Triffterer, Commentary on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Observers’ Notes, Article by Article. C. H. Beck, 2008, Article 6, marginal no. 16.。鉴于此,《罗马规约》第6条也一字不变地重复了《灭种公约》第2条的内容。

二、关于“受保护团体”的争议
《灭种公约》的第2条规定:“灭绝种族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个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团体,……而在相关研究中,此罪的犯罪对象被统一称为“受保护团体”。”
从1948年《灭种公约》签订开始,关于受保护团体的范畴,即民族团体(national group)、族裔团体(ethnical group)、种族团体(racial group)和宗教团体(religious group),就一直是灭绝种族罪的一个核心争议点。由于公约条款的规定,一些特定暴行的受害者的类别并不能明确符合公约所要求的这四类团体,这常常造成这些受害者由于无法将行为人以灭绝种族罪定罪而失望。
不同的情形下受保护团体的适用也截然不同。在纳粹对于犹太人的暴行中,纳粹曾根据客观方面的标准,建立了明细的规则,来判断谁是犹太人而谁不是,这使得判断犹太人属于受保护的团体的逻辑非常清晰。而适用这四种团体的艰难,在卢旺达的案例中就能明显体现。阿卡耶苏审判庭遇到的第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便是按照对族裔和人种团体的分类,很难判定胡图族和图西族分属不同的族裔或人种。卢旺达的图西族,被广泛认为是尼罗河牧民的后裔,而卢旺达的胡图族被认为是来自起源于中部和南部非洲的班图人。历史上看,他们的生产方式是不同的,图西族养牛放牧而胡图族耕田种地。他们在基因上也有区别,一个典型的图西族人高而瘦,有细而尖的鼻子;而一个典型的胡图族人则更矮,鼻子也更扁平。这种区别在一些人里是可以看出来的,但不是所有图西族人和胡图族人都能被明显区分。卢旺达的图西族人和胡图族人说一样的语言,信仰同样的宗教,并且有着在本质上共同的文化。两族人之间的通婚也是很普遍的。区分他们变得很困难,以至于比利时殖民者建立了一个身份证明的系统,并且决定用一个家庭所拥有的牛的数量来区分卢旺达法律中的“血统”*G. Prunier, The Rwanda Crisis, 1959—1994, History of a Genocide, Kampala: Fountain Publishers, 1995.。
确实在乍看之下,不能认定图西族是与胡图族完全区分开的团体,而在1994年被仇恨点燃和驱使的种族灭绝是毫无疑问地针对“一个民族、族裔、人种或宗教团体”的。如果卢旺达的图西族,不是一个这样的团体,那他们是什么呢*William A. Schabas,Genocide in International Law: The Crimes of Cr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0, p.109.?
对于“受保护团体”的理解众说纷纭,但总结而言,不外乎就是两个问题:第一,对于公约所列举的民族、族裔、种族和宗教团体,应当作出怎样的解释;第二,公约所保护的团体是否应该严格限制在《灭种公约》第2条列举的四种有名团体之中。下文将会对这两个问题一一阐明。
三、 《灭种公约》所列举四种团体的解释
《灭种公约》仅仅列出了受公约保护的四种团体,即民族团体、族裔团体、种族团体或宗教团体。这四种团体目前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多年来,许多学者和法官曾尝试为这些术语提供一些明晰的概念,但这些努力仍然不能让人完全信服。明晰这四种团体的定义却又是如此的重要,这是因为,“团体”一词不仅在《灭种公约》第2条的开头被提及,牵涉到了该罪行的心理因素(mens rea),也在接下来所列举的五种犯罪行为(actus reus)中被一一重复。
在沙巴斯(Schabas)看来,这四种团体不仅有所重叠,而且可以相互加以界定,就像四个支柱一样,共同明确并限定了公约所涵盖的多个团体能够获得保护的范围。在各团体之间作出清楚的区分是不太可能的,因为社会意识在构成这些团体中具有最终的决定意义;一个受到攻击的团体可能会具有许多团体的特征*William A. Schabas,Genocide in International Law: The Crimes of Cr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0, p.111.。在实践中,前南和卢旺达刑庭则都倾向于将受害者团体确定地归为列举的四种团体中。
(一)民族团体(national group)
常设国际法院在解释欧洲有关保护少数民族的条约时,曾对民族作出了定义:“就传统而言,‘民族’就是居住在某一国家或某一地点的人的群体,具有自己的种族、宗教、语言和传统,以种族、宗教、语言和传统团结在一起,形成凝聚力,保持自己崇拜的形式、遵守信条,根据本民族的传统和精神教育下一代并且相互予以协助*“对格利科——保加利亚团体所作出的咨询意见”1930年7月31日,《常设国际法院案例集》第17卷,第19页。转引自李世光,刘大群,凌岩.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评释(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60.。”在英文中,民族和国民是同一个词,但这两者并不是同一个意思,诚如《奥本海国际法》所述:作为一国国民的人的概念,不能与作为由种族组成的民族的成员的概念相混淆*Oppenheim International Law, Volume 2, 9th edition, London, New York Press, 1996, p.857.。
阿卡耶苏案的审判分庭根据国际法院在“诺特鲍姆案”*See Nottebohm case (Liechtenstein v. Guatemala), Judgement of April 6th 1955, pp.1-10.(Nottebohm)中的陈述,将“民族团体”定义为基于共同的公民身份、相互享有权利并互担义务而被认为具有共同法律纽带的人类群体*See Prosecutor v. Akayesu (Judgement) (1998 Trail Chamber), Case No. ICTR-96-4-T, para.512. A national group is defined as a collection of people who are perceived to share a legal bond based on common citizenship, coupled with reciprocity of rights and duties.。但是在“诺特鲍姆案”中,国际法院的重点是建立“国籍(nationality)”,而不是“民族团体”的成员资格。这个区分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国际法院聚焦于一种对应关系,即正式授予“国籍”和联系个人与其民族的国家的现实纽带之间的对应关系。“诺特鲍姆案”并没有成功解决与给定国家有共同的文化与其他纽带的少数民族,可能实际上有着另一个国家的国籍,或者甚至是一个无国籍人的情形。所以,“阿卡耶苏案”关于诺特鲍姆案的引用对于“民族团体”这一定义而言是不完整的。
与一个民族团体相联系的因素,首先是共同的国籍。在国籍的基础上,可以视情况考量共同的历史、习惯等因素,所谓的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团体,大抵可以涵盖进这一定义中。
(二)族裔团体(ethnical group)
“族裔团体”被阿卡耶苏案审判分庭定义为成员共享共同的语言或者文化的团体*See Prosecutor v. Akayesu (Judgement) (1998 Trail Chamber), Case No. ICTR-96-4-T, para.513. An ethnic group is generally defined as a group whose members share a common language or culture.,然而这一定义纯粹从客观性特征来判断,似乎过于狭窄,在随后的“卡伊西玛案”(Kayishema)中,审判分庭没有遵循“阿卡耶苏案”客观性判断的先例,而是给出了一个更宽的概念,不仅考虑客观性特征,也表明社会性归类的过程在决定什么是人种团体的概念中具有重要关系,即一个人种团体是一个其成员共同使用一种语言和文化的团体;或者,一个使自己具有特色的团体,作为自己本身(自我识别的身份);或者,一个由他人,包括由这种犯罪的行为人识别身份的团体(他人识别的身份)*See Prosecutor v. Kayishema and Ruzindana (Judgement) (1999 Trail Chamber), Case No. ICTR-95-1-T, para.98.。
在之后的判例中,主观性因素也得到了考虑。在“鲁塔甘达案”*See Prosecutor v. Rutaganda (Judgement) (1998 Trail Chamber), Case No. ICTR-96-3-T, para.56.(Rutaganda)与“巴基里西玛案”*See Prosecutor v. Bagilishema (Judgement) (2001 Trail Chamber), Case No. ICTR-95-1-T, para.65.(Bagilishema)中,审判庭指出:由于缺乏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因此对于这个团体的判断必须根据各种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背景来理解。由此可看出,在该团体的身份认定问题上,已经体现出了主观的维度。
笔者认为将主观性因素纳入考量的进步是很值得肯定的。因为“团体”这一称呼,是一种社会性的构造,由此,它必定会根据各种社会历史背景来决定,并且团体也是在发展变化的,所以单用客观科学的量度来限定,很难在案件里直接适用。2003年的“舍曼扎案”(Semanza)判决中,卢旺达刑庭采纳了一种客观性标准和主观性标准为基础的方法*See Prosecutor v. Semanza (Judgement) (2003 Trail Chamber), Case No. ICTR-97-20-T, para.317.,而这种方法后来也得到了国际法院的肯定*Case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Bosnia and Herzegovina v. Serbia and Montenegro), ICJ Judgment, 26 February 2007, para.191.。
(三)种族团体(racial group)
阿卡耶苏案的审判分庭认为,公约对“种族团体”的定义基于与特定的地理区域相关的、遗传的外貌特征,而不考虑语言、文化、民族或宗教的因素*See Prosecutor v. Akayesu (Judgement) (1998 Trail Chamber), Case No. ICTR-96-4-T, para.514; also see Prosecutor v. Kayishema and Ruzindana (Judgement) (1999 Trail Chamber), Case No. ICTR-95-1-T, para.98.。美国的种族灭绝立法采取了类似的观点,将“种族团体”定义为“在身体特征或生物血统方面具有独特性的一群个体”*Genocide Convention Implemention Act of 1987, (Proxmire Act), s. 1093.。卢旺达国际刑庭在判断种族团体时,首先考虑的是外貌上的遗传特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种族团体的概念在研究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等问题的时候确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种族团体与人种团体常常很难区分。总结而言,人种团体和种族团体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更看重语言文化上的差异,而后者则更强调遗传外貌的特征,比如肤色或身材。许多学者认为,要区分族裔与种族并不容易,最好是对有关的时间同时适用这两个概念,而不去试图区分两者之间的差异*马尔科姆·肖.灭绝种族罪与国际法[M].德国尼赫夫出版社,798.转引自自李世光,刘大群,凌岩.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评释(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60.。
(四)宗教团体(religious group)
实际上,宗教团体是一个相当不稳定的概念。与人种团体和种族团体这些很大程度上靠遗传等先天因素决定的团体相比较,宗教团体是一个流动并且完全靠后天选择的团体。在第六届联合国大会委员会上,英国代表就曾经质疑过该不该将“宗教团体”纳入受保护团体的范围,理由是:人们有自由随时加入或离开一个宗教*UN Doc.A/C. 6/SR.69 (Shawcross, United Kingdom).,这使得这个团体既不永久,也不稳定。
“卡伊西玛案”的审判分庭指出,宗教团体是指那些其成员有着共同的宗教、教派或信奉方式的团体*See Prosecutor v. Kayishema and Ruzindana (Judgement) (1999 Trail Chamber), Case No. ICTR-95-1-T, para.98.。“阿卡耶苏案”审判分庭则认为宗教团体是包括教派、信奉方式或具有共同信仰的团体*See Prosecutor v. Akayesu (Judgement) (1998 Trail Chamber), Case No. ICTR-96-4-T, para.514.。美国国内法对“宗教团体”定义,即因为相同的宗教信条、信仰、教义、实践和仪式而身份独特的群体*Genocide Convention Implementation Act of 1987(Proxmire Act), s. 1093(7).。根据Matthew Lippman的看法,宗教团体既包括神学的,又包括非神学的,甚至包括被同一精神理想统一无神论的群体*Matthew Lippman, ‘The 1948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Forty—Five Years Later’, (1994) 8 Templ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Journal, p.1 at p.29.。无论如何,政治上的确信是不能等同于宗教信念的,否则,政治团体就会从这个渠道进入受保护团体的范畴了。
四、“受保护团体”分类的标准
除了“受保护团体”的定义外,在事实上鉴别他们的标准也是一个争议很大并且正在逐渐演进的问题。在这方面, 卢旺达刑庭在“阿卡耶苏案”的审判判决也确立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先例。在这一判决中,分庭承认,尽管图西族人没有自己的语言或独特的文化——从其对族裔群体的定义中产生的两个显著特征——从卢旺达其他人口中, 一些诸如身份证等客观指标以及《卢旺达宪法》和1994年生效的《民法典》表明了独特的身份*〔42〕See Prosecutor v. Akayesu (Judgement) (1998 Trail Chamber), Case No. ICTR-96-4-T, para.170. para.171.。此外, 分庭注意到:
“在分庭作证的卢旺达证人是由族裔团体确定的, 他们一般都知道他们的朋友和邻居所属的族群。此外, 图西人被那些将他们作为杀戮目标的人认为是一个族裔团体。”〔42〕
在阿卡耶苏案确立的客观标准后,“卡伊西玛案”中,审判分庭没有遵循这个先例,而是指出判断团体的方法是选择性的而不是累积性的,即采用了主客观综合的方法。尽管在审查基布耶的图西族人口是否构成一个族裔群体时, 分庭确实考虑了客观因素*〔44〕〔49〕See Prosecutor v. Kayishema and Ruzindana (Judgement) (1999 Trail Chamber), Case No. ICTR-95-1-T, para.535-525. para.98.。分庭认为:
“族裔团体是其成员共享一种语言和文化的团体;或者,一个使自己具有特色的团体,作为自己本身(自我识别的身份);或者,一个由他人,包括由这种犯罪的行为人识别身份的团体(他人识别的身份)。”〔44〕

目前还没有对此问题的定论,在国际刑事法院审理的苏丹总统巴希尔案(Al Bashir)中,预审分庭也宣布正在忖度到底是采用“绝对主观,绝对客观或主客观相结合的分类标准”*See Prosecutor v. Omar Hassan Ahmad Al Bashir, ICC-02/05-01/09, Decision on the Prosecution’s Application for a Warrant of Arrest, 4 March 2009, footnote 152.。
五、“受保护团体”的范围问题
《灭种公约》第2条规定的“受保护团体”,是否应该严格限制在《灭种公约》列举的四种团体内?换言之,《灭种公约》中对团体的列举是穷尽的,或者只是举了几个典型的例子?这是个争议了很长时间却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结论的问题,对于该问题的争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意见。
(一)肯定意见

根据《罗马规约》第22条第2款“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规定,犯罪定义应予以严格解释,不得类推延伸。涵义不明时,对定义作出的解释应有利于被调查、被起诉或被定罪的人*Rome Statute, Article 22.。并且,《灭种公约》的起草者有意地排除了一些团体,比如:政治团体*UN Doc.A/C.6/SR.75 (Petren, Sweden).、思想团体*UN Doc.E/623/Add.4.、语言团体*UN Doc.A/AC.10/41; UN Doc.A/362.、经济团体*UN Doc.A/C.6/214.等。在《罗马规约》的内容谈判期间,有许多代表团提出应该扩大公约受保护团体的范围,把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包括在内,以填补定义的任何空白,但是这种建议遭到了反对,认为会削弱权威定义,因为公约的定义已经被各国广为接受,最终这一建议并未被采纳*Payam Akhavan, The Crime of Genocide in the ICTR Jurisprud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3 (2005), pp.989-1006, p.999.。
(二)否定意见
根据Frank Chalk和Kurt Jonassohn的观点,“公约的措辞致使受保护团体的范围是如此狭窄,以至于若是严格采纳公约的意见,则并没有任何一起犯下的杀戮能够被称为种族灭绝……潜在的行为人甚至可能会只针对那些并没有被公约的定义所覆盖的团体犯下罪行。”*Kurt Jonassohn,‘What is Genocide?’, in Helen Fein, ed.,Genocide Watch,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7-26.正是由于公约定义限定的范围,许多学者与人权积极分子频繁地尝试扩张和延伸公约所给出的定义,甚至有学者认为:种族灭绝的“团体”应该包括任何团体,限制国际法对一些团体的保护是毫无意义的*Pieter Nicolaas Drost, The Crime of State, Vol.2, Genocide, Leyden: A.W.Sijthoff, 1959, pp.122-123.。
最出名的否定意见,应该要属作为灭绝种族实践的代表案例——“阿卡耶苏案”审判分庭的判决,其指出:在制定《灭种公约》时,该罪名只针对“稳定”的构成团体,其成员是由出生决定的。这就排除了个人能够通过自愿行为参加的那些“流动的(mobile)”团体,例如政治团体和经济团体。因此《灭种公约》保护的四种团体的共同准则是由于其出生而自动取得成员资格,一旦成为该团体成员就一直继续下去,一般是不能够改变的*〔59〕See Prosecutor v. Akayesu (Judgement) (1998 Trail Chamber), Case No. ICTR-96-4-T, para.511. para.516.。……在法庭的意见看来,尊重《灭种公约》的起草者的目的是相当重要的,根据该公约的补充资料(travaux préparatoires),显然是确保对于任何稳定且永久的团体(any stable and permanent group)的保护〔59〕。
(三)笔者观点
笔者不同意 “阿卡耶苏案”中确立的“任何永久且稳定的团体”的看法,理由如下:第一,这一说法明显违反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nullum crimen sine lege)的原则;其次,这一解释在随后的判例中,也完全没有得到沿用;第三,如果公约只保护任何永久且稳定的团体,那么公约的起草者就应该在公约中明示这种意图,但公约里却没有任何关于此问题的规定,反而是在制定过程中有意排除了一些团体;第四,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2条的规定,补充资料(travaux préparatoires)在条约意义不明或难解、或所获结果显属荒谬或不合理时,为确定其意义起见,得使用解释之补充资料,包括条约之准备工作及缔约之情况在内,而不是去添加其他的元素。最后,即使是公约中列举的“宗教团体”,也不是永久且稳定的团体。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的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由此可以得出,改变宗教是生而为人的一项基本权利。鉴于此,“任何永久且稳定的团体”连公约明文列举的“宗教团体”都不能包括进去,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根据前述各执一词的观点,不难看出,不论是支持严格解释的观点,还是对其进行稍微的扩大解释的观点(不包括以“阿卡耶苏案”为例的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笔者更倾向于“受保护团体”应该严格限制在《灭种公约》所列举的四种团体内。
首先,出于对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nullum crimen sine lege)的原则的尊重和落实。根据《罗马规约》第22条第2款法无明文不为罪的规定,犯罪定义应予以严格解释,不得类推延伸。涵义不明时,对定义作出的解释应有利于被调查、被起诉或被定罪的人*Rome Statute, Article 22.。
其次,《灭种公约》《罗马规约》等的起草者并不是没有注意到有其他团体的可能,而是有意地排除了一些团体,比如:政治团体*UN Doc.A/C.6/SR.75 (Petren, Sweden). See also N. Robinson,The Genocide Convention: A Commentary, World Jewish Congress, 1960, p.59.、思想团体*UN Doc.E/623/Add.4.、语言团体*UN Doc.A/AC.10/41; UN Doc.A/362.、经济团体*UN Doc.A/C.6/214.等,这说明了制定者本身对受保护团体的范围就持一种谨慎的态度。
再次,从种族灭绝罪所保护的法益入手,种族灭绝罪是对团体存在权(right to exist)的践踏和否认。两个关键词,“团体”和“存在权”。种族灭绝罪所要求的“特别意图(dolus specialis)”是要毁灭一个团体,而不是针对个人。如果是缺少了这个要件,那么不管一个行为的罪恶程度有多令人发指,不论这个行为与公约的描述有多么贴切,该行为都不能被称为“种族灭绝”*Prosecutor v. Akayesu (Judgement) (1998 Trail Chamber), Case No. ICTR-96-4-T, para.519. also see Summary Records of the meetings of the Sixth Committee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21,September-10 December 1994, op.cit., p.109.。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会议第96号决议明确指出,种族灭绝罪是“对全部人类团体生存权利的否认”*UN Doc. A/RES/96(I) (1946).。对于灭绝种族的犯罪化,是为了寻求保护特定团体的存在权*ICJ Advisory Opinion of 28 May 1951(Reservation to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Genocide), ICJ Rep.1951, p.15.。
复次,种族灭绝罪被称为“罪中之罪”*See Prosecutor v. Kambanda (Judgement and Sentence) (1998 Trail Chamber), Case No. ICTR-97-23-S, para.16; Prosecutor v. Serashugo (Sentence) (1999 Trail Chamber), Case No. ICTR-98-39-S, para.15.(Crime of the Crimes),即使是在只管辖四个十恶不赦的罪行的《罗马规约》里,种族灭绝罪也占有一席之地,其恶劣程度不言而喻。对于这种罪行进行定罪,就意味着更应该谨慎,举证的标准更应该体现排除合理怀疑的理念。

只要对比一下《罗马规约》的第6条和第7条,就可以发现种族灭绝罪和危害人类罪有明显的重叠的部分。在大多数时候(但不是所有情况下),二者可以看成是一种阶梯式的关系。换言之,种族灭绝罪基本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更为严重的危害人类罪。在卡伊西玛案中,审判庭直言,种族灭绝罪的定义是基于危害人类罪的,即 “灭绝”和“迫害”政治、种族和宗教团体等的结合,并特别涵盖“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的意图。种族灭绝罪就是一种危害人类罪*See Prosecutor v. Kayishema and Ruzindana (Judgement) (1999 Trail Chamber), Case No. ICTR-95-1-T, para.89.。 笔者确实认为虽然绝大多数情况下,灭绝种族的行为是完全满足危害人类罪的要求的,但必须承认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毕竟危害人类罪要求“对平民人口大规模而系统的攻击”,而灭绝种族罪要求“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受保护团体”。即使确实难以将受害人所处的团体归入规约所列举的四种团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可以将行为人以危害人类罪定罪的,所以不至于出现“有罪不罚”的情况。
综上,笔者认为将“受保护团体”严格限制在《灭种公约》所列举的四种团体内的做法更为稳妥。
六、结论
灭绝种族罪被称为“罪中之罪(Crime of the Crimes)”, 是现今世界上最严重的罪行之一。《罗马规约》一字不落地重复了《灭种公约》第2条的规定,即“灭绝种族罪是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团体而实施的下列任何一种行为:……”。从《灭种公约》筹备工作的早期阶段到现在, “受保护团体”的法律概念就几乎是由两种紧张关系形成的, 一种是包容性或排他性的“受保护团体”的范围, 一个是客观或主观的“受保护团体”分类标准。这样的紧张关系也让该条中“受保护团体”的内涵与外延至今仍众说纷纭。民族团体为基于共同的国籍而共享同一法律纽带,从而在权利和义务上互惠的人类群体的总和。族裔团体被定义为成员共享共同的语言或者文化的团体。种族团体定义基于与特定的地理区域相关的、遗传的外貌特征,而不考虑语言,文化,民族或宗教的因素。族裔团体和种族团体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更看重语言文化上的差异,而后者则更强调遗传外貌的特征。宗教团体包括崇拜的教派或方式或具有共同信仰的群体。
除了四种列举的团体外,各种其他团体都不受国际条约法或习惯国际法的保护。灭绝种族罪对民族、族裔、种族和宗教团体的限制,有相当的合理性:这些团体的成员最需要得到保护。至少在民族、族裔或民族团体方面,个人不能仅仅通过使自己离开团体的方法使自己与这个团体分离,这个个人的命运与这个团体的命运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另外,这些稳定的团体比较容易识别,而政治、社会、经济和其他团体却在不断改变自己的成分,因此其本身是不受保护的。
对于“受保护团体”的分类标准问题,目前有三种,即客观分类、主观分类或主客观相结合的分类标准,前南刑庭、卢旺达刑庭的不同判例曾采纳过不同的分类,目前对此问题并无定论。
笔者首先不同意“阿卡耶苏案”认为该保护“任何稳定且永久的团体”的观点;其次,笔者更倾向于公约所保护的团体应该严格限制在第2条列举的四种有名团体之内,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对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的尊重和落实;《灭种公约》《罗马规约》等的制定过程;该罪名所保护的法益;该罪行的严重性以及该罪名与危害人类罪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