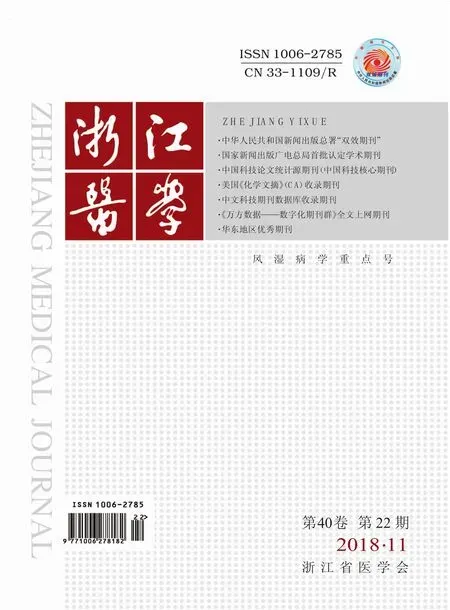嗜酸性粒细胞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李慧莹 戴元荣 林洁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obstructivepulmonarydiseases,COPD)是一种常见的可以预防和治疗的疾病,其特征是持续存在的呼吸道症状和气流受限,通常是由于暴露于毒性颗粒或气体引起的气道和/或肺泡异常所导致。COPD是全球范围内疾病致残率和死亡率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全球疾病死亡原因中占第4位。据估计,到2020年,COPD将成为全球第三大死因[1]。COPD通常与辅助性T细胞1(Th1)介导的中性粒细胞免疫反应相关,但在10%~40%的COPD患者中可以观察到嗜酸性粒细胞性气道炎症[2]。Gao等[3]根据痰标本中嗜中性粒细胞(>61%)和嗜酸性粒细胞(>2.5%)的数量分别对83例急性加重期COPD(AECOPD)患者进行分层分析,将AECOPD患者分为嗜酸性粒细胞表型(EOS)组、嗜中性粒细胞表型(NEU)组、少细胞表型(PAU)组和混合型粒细胞表型(MC)组4个亚组,其中EOS组中痰嗜酸性粒细胞>2.5%,NEU组中痰嗜中性粒细胞>61%,PAU组中痰嗜酸性粒细胞≤2.5%和嗜中性粒细胞≤61%,MC组中痰嗜酸性粒细胞>2.5%和中性粒细胞>0.61%。他们发现10例以嗜酸性粒细胞为主,36例以嗜中性粒细胞为主,5例以混合粒细胞为主,32例以少粒细胞为主。由此可见,COPD是一种复杂的异质性疾病,识别EOS COPD,并予以相应的治疗可以使临床获益,本文对EOS COPD生物标志物作一综述。
1 痰嗜酸性粒细胞
诱导痰检测作为气道炎症的非侵入性检查方法用来定义患者气道炎症表型,在临床上应用广泛,哮喘和COPD患者痰嗜酸性粒细胞数≥3%时都表现出对糖皮质激素治疗反应好[4-5]。大多数研究将COPD患者中痰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的临界值定义为痰嗜酸性粒细胞≥3%,并将痰嗜酸性粒细胞作为预测COPD吸入或口服糖皮质激素治疗效果的生物标志物[6]。Siva等[7]发现减少痰嗜酸性粒细胞数目可有效降低COPD急性加重风险。
一项评估痰液或血液中高嗜酸性粒细胞是否与严重COPD表型相关的多中心观察性研究[8]将痰嗜酸性粒细胞1.25%用作分析的临界值,其中痰嗜酸性粒细胞≥1.25%为高痰嗜酸性粒细胞组(171例),痰嗜酸性粒细胞<1.25%为低痰嗜酸性粒细胞组(656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种族、BMI、吸烟史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高痰嗜酸性粒细胞组患者应用吸入糖皮质激素的比例和吸入或雾化支气管扩张剂的比例、肺气肿指数、空气滞留量(残余体积)均明显高于低痰嗜酸性粒细胞组,肺功能明显低于低痰嗜酸性粒细胞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按2%痰嗜酸性粒细胞分界值分层的亚组之间也观察到类似的结果。高痰嗜酸性粒细胞组患者需要糖皮质激素的比例高于低痰嗜酸性粒细胞组(19%vs 10%),并且需要急诊科就诊的严重急性发作多于低痰嗜酸性粒细胞组(13%vs 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综上所述,痰嗜酸性粒细胞增多与COPD急性加重有相关性,减少痰嗜酸性粒细胞数目可以有效降低COPD急性加重风险。痰嗜酸性粒细胞作为EOS COPD的生物标志物有参考价值,痰诱导作为气道炎症的非侵入性检查方法,可以用来定义患者气道炎症表型,但也具有一定局限性,它需要专业人员操作及患者的配合,失败率约30%[9-10],不利于及时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
2 血嗜酸性粒细胞
Bafadhel等[11]研究发现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和痰嗜酸性粒细胞计数之间存在相关性,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2%)可作为替代COPD痰嗜酸性粒细胞的敏感生物标志物,用于确定COPD气道嗜酸性粒细胞增多(≥3%)(AUC=0.85,灵敏度为90%,特异度为60%)。而且另有研究表明间隔28d两次测量的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稳定性好[6]。因此将血嗜酸性粒细胞≥2%作为COPD气道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的生物学特征之一。研究证实血嗜酸性粒细胞在急性加重期[12]和稳定期[13-14]的COPD患者中有作为对糖皮质激素治疗反应良好标志物的潜在能力。
研究发现当血嗜酸性粒细胞≥1.7%时,随着嗜酸性细胞水平的增加,COPD中重度急性加重风险逐渐增加[13]。高水平的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可以预测COPD急性加重风险。然而在SPIROMICS研究中发现血嗜酸性粒细胞<1%的COPD患者气道阻塞更严重,6分钟步行距离更短,恶化加重次数更多[15]。同样有研究发现血嗜酸性粒细胞≤2%的COPD患者发生肺炎的概率更高[16]。嗜酸性粒细胞有杀伤微生物的作用,可以将抗原递呈给T细胞并促进Th2细胞分化成熟[17],是先天免疫防御的主要成分。当嗜酸性粒细胞减少时,COPD患者免疫防御功能减弱,容易导致细菌、病毒等微生物的定殖,从而导致发生肺炎的概率增高。
目前对于血嗜酸性粒细胞绝对值的临界值尚无定论。Vedel-Krogh等[18]研究表明,当患者血嗜酸性粒细胞>0.34×109cell/L时,COPD重度加重风险将会增加1.76倍。亦有研究将血嗜酸性粒细胞≥0.2×109cell/L定义为COPD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其在0.2×109cell/L的临界值处的灵敏度为91.1%[19]。血嗜酸性粒细胞在临床上较易获得,但是对于其绝对值的临界值,需要更大样本进行研究,至少笔者认识到血嗜酸性粒细胞在一定程度上可用以识别EOS COPD。嗜酸性粒细胞增多与COPD急性加重风险增加有关,并且EOS COPD急性加重期对于糖皮质激素有较好的反应[10],长期吸入糖皮质激素治疗也能有效缓解急性加重风险[11,13],Barnes等[20]发现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2%的COPD患者在吸入糖皮质激素治疗后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的下降速率较慢。对于嗜酸性粒细胞≥2%的COPD患者,长期联合使用吸入糖皮质激素+长效β受体激动剂(LABA)效果优于单用LABA药物[13]。另有荟萃分析研究了100mg美泊利单抗与安慰剂在不同嗜酸性粒细胞水平的COPD患者中的获益情况,结果发现血嗜酸性粒细胞在300~500个/ml的COPD患者使用美泊利单抗后在减少急性加重方面获益最大[21]。这些发现为特异性抑制嗜酸性粒细胞炎症的治疗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嗜酸性粒细胞性气道炎症在COPD急性加重过程中起作用,且靶向阻断IL-5来减少血液和组织中的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在COPD患者中同样有效,血嗜酸性粒细胞可以预测抗IL-5单抗预防COPD急性加重治疗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相对值偏低的COPD患者容易发生肺部感染。同时需要注意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升高的COPD患者,目前多以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2%确定为EOS COPD,随着嗜酸性细胞水平的增加,中重度急性加重风险逐渐增加,并且其相对值可以预测COPD患者对糖皮质激素治疗的反应性,也为特异性抑制嗜酸性粒细胞炎症的治疗提供了证据。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在临床上容易获得,测定方法简单,其作为EOS COPD的生物标志物值得推广和进一步深入研究,但痰嗜酸性粒细胞较血嗜酸性粒细胞更能反映EOS COPD,建议客观看待血嗜酸性粒细胞指标。
3 嗜酸性粒细胞颗粒蛋白
嗜酸性粒细胞阳离子蛋白(ECP)是嗜酸性粒细胞的特异性标志物,是嗜酸粒细胞活化后释放出的强碱性颗粒蛋白,可以刺激肥大细胞释放组胺,导致黏液分泌增加,进而导致气道高反应[22]。同时ECP是哮喘气道炎症严重程度的标志之一。研究发现COPD患者ECP也有所增加,急性加重期COPD患者痰和血清ECP水平高于稳定期COPD患者[23-24],并且ECP随COPD严重程度增加而增高[25]。Paplinska-Goryca等[26]研究发现ECP在诱导痰中的较高表达与COPD症状评估测试评估的COPD控制情况较好相关。虽然ECP是嗜酸性粒细胞活化的标志物,但在嗜酸性粒细胞型和非嗜酸粒细胞型COPD患者间,痰ECP水平并无明显差异(P>0.05)[27]。COPD患者表现出ECP增加,这提示嗜中性粒细胞是ECP的另外来源[28]或者说嗜酸性粒细胞脱粒程度在患者中有较高的可变性,有些患者尽管细胞计数不大,但仍有大量的脱粒。基于上述研究,ECP可以评估COPD的严重程度,但因ECP在中性粒细胞中同样能检测到,因此,并不适用于区别EOS COPD[29]。同样,主要碱性蛋白(MBP)在其他细胞如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中也观察到了显著的表达[30-31],故MBP同样不适于用来区别EOS COPD。
综上所述,由于缺乏特异性和众多的干扰因素,目前还没有一种合适的嗜酸性粒细胞颗粒蛋白来识别EOS COPD。如果将来能特异性检测出嗜酸性粒细胞来源的颗粒蛋白,也许能作为其生物标志物。
4 呼出气一氧化氮(FeN O)
一氧化氮(NO)是各种细胞中精氨酸在一氧化氮合酶(NOS)的作用下合成的,同时产生瓜氨酸。人体内的NOS大致分为神经型一氧化氮合酶(nNOS)、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eNOS)和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3类。nNOS和eNOS统称为固有型一氧化氮合酶(cNOS),cNOS的活性依赖于钙离子和钙调蛋白,在正常生理条件下催化合成少量NO[32]。iNOS的活性不依赖于钙离子和钙调蛋白,生理状态下不表达,在特殊条件下经诱导才会产生,一旦被激活,将会大量持续合成NO。哮喘患者气道上皮中iNOS表达增高,应用吸入糖皮质激素治疗后,iNOS表达减少[33]。哮喘患者呼出NO主要是由i-NOS产生,糖皮质激素可以选择性抑制iNOS表达而降低FeNO水平,但是对cNOS表达无明显影响[34],糖皮质激素治疗对COPD患者疗效不显著[35],笔者推测iNOS可能不是COPD患者气道NOS的主要成分。有研究表明COPD患者cNOS表达增高[36],COPD患者气道NOS的优势类型可能与哮喘患者不同。
在过去10年里,FeNO作为哮喘标志物的研究较多,FeNO水平可以反映气道嗜酸性粒细胞性气道炎症的程度,在哮喘患者中广泛应用,在大多数轻度哮喘患者中,FeNO升高表明对糖皮质激素治疗反应好[37-38],同时FeNO可以检测哮喘控制程度以及预测未来急性发作。有研究发现COPD患者FeNO水平与痰嗜酸性粒细胞也具有相关性[23,39]。一项研究收集了49例戒烟的急性加重期COPD患者入院和出院前的痰液及FeNO数据,发现FeNO是急性加重COPD患者痰嗜酸性细胞的良好代用标记,切点值为19ppb(灵敏度为90%,特异度为74%)[40]。然而FeNO与血嗜酸性粒细胞之间并无相关性[41],FeNO在COPD中的作用机制尚未明了,吸烟与否以及中性粒细胞性气道炎症对FeNO都有影响[42],仍需进一步研究FeNO在EOS COPD中的意义。不过,有研究提示COPD患者进行性升高的FeNO预示ICS治疗效果好[10],FeNO对EOS COPD的应用价值需要更多的研究进行验证。
综上所述,FeNO水平反映了气道嗜酸性粒细胞性炎症程度,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COPD的嗜酸性粒细胞水平。由于吸烟(多数COPD患者的危险因素)等因素可使FeNO值下降,限制了其应用价值。对于FeNO值较高的COPD患者,还应注意合并哮喘的可能。目前FeNO在临床上应用逐渐广泛,其测定方法简单,迅速得到结果,值得更多的研究探讨其价值。
5 骨膜素
骨膜素是由气道上皮细胞和肺成纤维细胞分泌,是Th2型炎症以及支气管重构的标志物[43]。Jia等[44]发现伴有嗜酸粒细胞性气道炎症反应的哮喘患者,骨膜素水平明显升高,说明骨膜素是气道嗜酸性粒细胞炎症的优越预测因子。而最近的一个横断面研究显示痰嗜酸性粒细胞与血液嗜酸性粒细胞有很强的相关性,但未能证明血清骨膜素和痰嗜酸性粒细胞之间的关系[45]。这表明血清骨膜素可能提供作为Th2炎症的生物标志物的额外价值,但不能直接与血液或痰嗜酸粒细胞增多相媲美。骨膜素可能用作评估特异性IL-13活性和对抗IL-13治疗的反应的标志物[46]。骨膜素在哮喘患者中研究较多,由于吸烟可以抑制骨膜素基因表达[47],故而骨膜素在COPD患者中的表达水平较哮喘患者低。Konstantelou等[48]研究表明,虽然COPD急性加重期患者入院时骨膜素水平比出院时高,但骨膜素水平升高与其预后及死亡率等并无明显相关性。然而,在另一项研究中,骨膜素可以预测嗜酸性粒细胞性气道炎症,在对稳定期COPD患者吸入糖皮质激素/LABA治疗3个月后,骨膜素与改善的FEV1呈正相关[49]。IL-13可以直接诱导上皮衍生的骨膜素,与上调的FENO表达相关,而气道嗜酸性炎症与IL-13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例如通过上皮衍生的化学引诱物的上调,各种研究中生物标志物测量的这些变化进一步突出了气道炎症的异质性和复杂性。目前骨膜素在EOS COPD中的应用价值尚无明确研究来验证。
6 总结和期望
COPD是一种异质性疾病,多种生物机制参与其发生、发展,至今还没有一种生物标志物可以简单地预测急性加重风险,联合多种生物标志物和临床指标对COPD进行综合评判,临床意义比较大。COPD患者对糖皮质激素总体治疗效果不如哮喘患者好,而EOS COPD患者对糖皮质激素治疗表现出较好的疗效。目前研究EOS COPD的生物标志物是一大热点,本文就痰嗜酸性粒细胞、血嗜酸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颗粒蛋白、FENO和骨膜素等生物标志物进行探讨。痰嗜酸性粒细胞增多与COPD加重有相关性,减少痰嗜酸性粒细胞数目可以有效降低COPD急性加重风险。痰嗜酸性粒细胞作为EOS COPD的生物标志物参考意义较大。血嗜酸性粒细胞与痰嗜酸性粒细胞具有相关性,其在EOS COPD患者中有作为对糖皮质激素治疗反应良好标志物的潜在能力。嗜酸性粒细胞颗粒蛋白ECP、MBP在EOS COPD患者中不具有特异性,目前其在临床无实际应用价值。FeNO是急性加重COPD患者嗜酸细胞性炎症的良好代用标志物,与痰嗜酸性粒细胞具有相关性,但其与血嗜酸性粒细胞之间尚未发现明显相关性,这值得进一步研究。骨膜素是由气道上皮细胞和肺成纤维细胞分泌,是Th2型炎症以及支气管重构的标志物,其在EOS COPD患者中的研究存在矛盾,目前尚无明确的研究来表明其能预测EOS COPD。以上生物标志物对于区别EOS COPD患者的应用价值,仍需更深入的研究,建议临床应用时,综合多个指标指导个体化COPD治疗,研究EOS COPD标志物具有广阔的前景,同时将为诊治COPD提供更为详实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