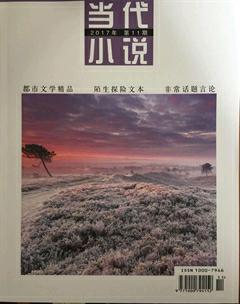惊瓷儿(短篇小说)
娄光
马强进来的时候,鹤云正在摆棋式,手里拿着棋谱,书名奇巧,《鬼手 妖刀 仙路》,真是,三个词儿摆在一起,别说还全是围棋的门道。
“来财叔,摆棋呀?”马强笑,眼四巡着。屋里静得很,地扫得也干净,来财锔盆锔碗的工具早就规规矩矩地收拾起来,且落了薄薄的灰尘。怕是多日未曾有生意了。
“又叫来财叔!”鹤云从棋谱上挪开眼,埋怨道。马强在桑梓路上开了个高档的茶馆,为的是以棋会友。此刻正在装修,小伙子岁数不大,为人灵精,关键是也懂得围棋,偶尔过来手谈几盘。鹤云很喜欢这小伙子,“不是说了嘛,见我下棋不能叫来财叔。”
马强夸张地打了一下自己的嘴,故作郑重地说:“鹤云叔,我找点儿铁丝。”“角落里,自己拿。”坐在那里动也不动,用嘴巴稍一示意,又专心摆起他的棋式来。
马强拿了铁丝,走时又说:“等茶馆开张了,过来下,我敬茶。”
来财讨厌自己的名字,是因为他迷上了围棋。在桑梓路上作锔匠来财能迷上围棋?人们真的觉着有些不可思议,整天和盆盆罐罐、碎碗乱壶打交道,那营生虽能挣钱养活生计,毕竟是些粗活,粗手粗脚的人却能与围棋挂上钩,且迷得如痴如醉?这事儿连在扎啤摊上说起来也颇不可思议的。可这来财就是迷上了,自从迷上了围棋,就想改掉自己的名字。随着锔锅锔盆的生意越来越淡,迷得越来越深,整日在他的“破盆破碗”铺子里摆式手谈呢!来财讨厌自己的名字,是呀,在桑梓路,在这三教九流聚集的地方,你喊一声“来财,来财,下一盘!”也太难听了。桑梓路本来就是一条极特色的路,是宠物市场,狗,猫,花鸟,鱼虫,一喊起“来财”,直叫人想起动物来,大不吉利。而迷棋,迷的是境界,是风光无限,况且围棋乃古朴之物,看上去就非常“儒雅”,凭吊怀古,很雅意,叫“来财”太俗气了吧!决心一下,名字改成“鹤云”。
来财的名字改成鹤云的时候,也正是他在桑梓路上的“破盆破碗”店关门的时候,女儿抚筝从艺术学院毕业了,随着时光一日日地过来,锔匠这活儿越来越少,如今塑料、不锈钢、搪瓷的东西塞满了市场,谁还会用过去旧瓷的东西呢? 抚筝还是有头脑的,她在艺术学校学的就是琵琶弹奏,毕业后,工作难找,又见来财整日在门头上摆弄棋子,已没有什么生意,就对她爸说:“爸,以后你这活就别干了,安心下棋呗。”
来财一怔:“什么意思?”他有些惊疑不解地望着女儿。“爸,你这生意又不好,这房子就腾出来开个古琴行吧,以后你就安心下棋。”来财双眼突然迷茫起来。他木然地望着远方,浑浊的泪水沿着苍老的脸颊缓缓流下来。
抚筝的古琴行开张的那天,来财正式宣布他把名字改为“鹤云”了 。
“破盆破碗”的匾额撤下来,抚筝新漆的“古琴行”的牌匾在绣红花绸的包裹装饰下缓缓地升了起来,鞭炮声响成一片,花花绿绿的鞭炮碎屑中,人们纷纷前来祝贺。抚筝和她妈妈满面笑意地迎接着来贺的朋友,而前场单单不见了刚改过名字的鹤云先生。马强从外面进来,双手朝抚筝打拱,“来……不,鹤云叔哪?”抚筝惊异地扭头四面寻找,呀!真的就不见了爸爸:“刚刚还在这宣布改名字呢!我去找找。”马强摆摆手:“不用,我去找吧。不会又摆棋谱去了吧。”
马强的茶馆和抚筝的店正好装修,马强一直过来,和抚筝也熟悉了,所以有些事就随意了。马强四下寻找,还是找到了鹤云叔,此时此刻的他,正坐在角落里,表情木然,脚下放着他锔盆锔碗的工具,手拉钻,胶油,灰膏,手套……在他前面还有一只大大的黄布包。他认真地摆弄着里面的东西,是什么东西,马强看不清楚,因为他根本就没拿出来。他一边认真地摆弄一边低声自言自语:往后就只下棋了呀,就只下棋了呀。名字都改了,也只能下棋了……
“来……鹤云叔,客人都在外面,你躲在这里干啥呀?”马强一时改不过来,面色涨得通红。
“女儿的店,我去干啥?”鹤云认真地把帆布包收拾好,斜背在肩上,把地上的那些工具锁进仓库,没有再理马强,独自一声不响地从后门走了,任凭前面开业多么热闹,他头也没回。
名字改成“鹤云”,云来云去的,似有些古意,禅意,很符合棋的原旨。在桑梓路上走来,像云般飘拂。路边把棋一摆,也是迷棋的状态。可是,生活并不能给鹤云充足的下棋时间,店面没有,只好和老婆在老“破盆破碗”的店面前摆了个杂货摊。
抚筝可是个出色的姑娘,艺术学院毕业,琵琶弹得好,而且身材高挑秀气,开古琴店,穿上传统的旗袍,在店里古曲的悠扬回声里,走起路来款款的,为桑梓路新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与父亲鹤云的名字挺配,可与他的工作真不怎么搭界。鹤云的杂货摊无非是些日常用品,没什么好东西,与女儿的古琴行真不相配,一些来买琴的顾客走过来免不了要斜上几个白眼,这让抚筝的心里很难受,但是又不能说,生怕伤了爸爸的自尊心。
鹤云唯一兴奋的事儿就是还能在摊前摆棋局,读棋谱,这时马强和秋林肯定会来。秋林是书法家,在报社里是个闲差,多年的老邻居,他对那时的来财爱棋也有些不理解,没想到的是来财变成鹤云了,棋也精到了许多。
秋林在鹤云的摊位前坐下来,鹤云脸上露出了喜色:“你怎么才来,不知道我正寂寞着嘛。”“你正做生意哪!我来给你耽误了生意,你老婆要骂我呢!”秋林笑笑。“什么呀!”鹤云一撇嘴,把棋盘的子儿收起来,把棋盂递过去,两人就在棋盘上下起来。两人正进入状态,马强在对面看到了,跑过来看个热闹:“两位叔,下着哪?”
两人抬头看他一眼,便把注意力又集中在棋盘上。人都熟了,没必要有什么客套话。马强便站在一旁看俩人下棋,一副观棋不语的君子样儿。路过的人来买点东西,马强应招呼过去帮他打理,又回过头来问:“鹤云叔,这卫生面纸多少钱一包?”鹤云抬头茫然地问:“什么?”“面纸,一包多少钱?”马强问。“两块。”鹤云说完再专心到棋上。马强一会儿捏着两块钱回来,放在鹤云面前。只听到抚筝喊:“马强,过来帮个忙!”
“哎!”馬强脆快地应着,起身奔抚筝而去。
听到这声,鹤云的心感觉有点儿异样,忍不住去看马强的背影,谁知扭头却看到抚筝看着马强笑,笑得挺甜,还别有些意味儿。“这家伙……”他嘴里咕哝着回头,又与秋林的目光相遇,秋林的笑也颇有些味道。
“这些年轻人。”鹤云又说。秋林却呵呵地笑起来。
两人继续摆着棋。马强过去真帮忙,一会儿帮着抚筝搬琴,一会儿帮着客户装车,被抚筝指挥得屁颠儿乱转。鹤云心里说,也真是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
马强忙活完后,笑嘻嘻地回来了,鹤云和秋林的棋刚过半。马强在两人面前感叹:“抚筝的生意真好啊,一架琴卖了三万多。鹤云叔这摊摆的可真没意义,抚筝一单生意就能挣鹤云叔半年的。”鹤云一听,脸一下子涨红了,瞪了马强一眼。马强意识到自己走了嘴,急忙把话咽了回去。茶馆前台服务员探出头来喊马强,马强留恋地看了一下棋盘,起身向茶馆走去,又回过头来说:“再下棋来茶馆里吧,别在这大街上。”两人不理。
鹤云和秋林继续下棋。两人是铁杆的棋友,每天——也不是这么绝对,只要是有时间吧,两人就在露天地里手谈比棋,滋味无穷,乐在其中。鹤云才不会去管他的小摊收入几钱。其实,抚筝对父亲在这里摆摊早就心有芥蒂了,在这格调高雅、古琴悠扬的店门前,摆这么一个小摊确实不雅,这极不相称的混搭让人看上去很不舒服,抚筝一直感觉影响她的生意。
抚筝为这事儿已多次找过鹤云了,一听女儿的话,鹤云双眼一瞪,看看女儿,火没有发出来,脸上露出不屑的神情:“你现在这样子,当年你爸的生意比这火多了。”鹤云说的并不是虚话,当年,鹤云还叫来财的时候,他不过是个“锔匠”,其实“锔匠”也是很文雅的叫法,用鹤云自己的说法是也只有他才可以叫“锔匠”,而那些走街串巷的只能叫“箍漏子”的,肩上挑满了工具,扯着嗓子喊:“锔锅锔盆锔大缸 ——”有的尖细悠长,有的浑厚深沉。而来财却不喊,他的嗓音不行,喊不出腔调,其实他也不用喊,因为他开店,他开的“破盆破碗”是这个城市里唯一一家锔锅锔盆的店,生意出奇的好,整个城市好像都要到他这里来修补锅碗瓢盆。每天清晨开了门,面對着眼前堆满的这些盆盆罐罐,脸上总是一副满足惬意的神色,眼睛迷离起来,把盆的外形、豁口认真地瞅一遍,瞅得极其仔细,轮廓和豁口看清了,看明白了,再用舌头舔了舔破盆的豁口,吧唧几下嘴,仿佛要尝出瓷器的味道,然后拿起工具,选好钻头和箍子,根据瓷的特性合好密封的灰浆,在他那纤细的手指的摆弄下,就把那些破盆破碗恢复得完好如初了。
每箍好一件东西,他就像完成了一件作品,总会背过身去,喝上几口早已泡好的茶,再用眼睛欣赏一下自己刚箍好的物件,似是在挑自己的瑕疵和漏洞。其实是没有什么可挑的,自己的手艺心里还不明白吗?他从来不干返工的活儿!
就这样安安稳稳地干了几十年,他觉得他的手艺不是在养家糊口,而是在置办家业。可真干到今天,这祖传的手艺倒也失了业,只能在女儿的琴行前摆地摊了。
天已交傍晚,秋林输给了鹤云两盘,鹤云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怎么样,这些日子我的棋式没有白摆吧?”秋林面色涨得通红:“再来一盘!”“不摆了,帮我收摊吧。”鹤云说。把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件件地往袋子里装。
鹤云杂货摊的物品都收拾起来,都放到抚筝的古琴行里,本来整洁高雅的琴行里放进这些东西很扫抚筝的面子,她很厌恶,心里不高兴,又不能表现在脸上,过来说:“爸,今天收获怎么样?”“赶不上你。”鹤云搪塞。“不能和我比,价值不同。”抚筝说着,从钱包里掏出一百元塞给他,“要不,这摊就别摆了,安安心心和秋林叔去马强哥茶馆里下棋得了。”
鹤云要去接钱,手都伸出来了,一听女儿的话,猛地把手缩了回去:“我不要!我一身的手艺还用你的钱?!”“爸,拿着吧,不然回家怎么向我妈交账?”抚筝一笑,碎步跟上来把钱塞进鹤云的口袋里,又低声说:“爸,告诉我妈,晚上不回家吃了。”鹤云警觉了:“又去哪?和谁?”抚筝撒娇地拍打着鹤云的肩膀,挤眉弄眼地说:“女孩子家的事儿,少管吧。”鹤云掏出口袋里的一百元,故意在抚筝面前捻了捻,抚筝会意地笑了,又从钱包里抽出一张。“别,给零的,我这小地摊哪有这么多百元大钞向你妈交账。”鹤云说。“我没零钱,去小商店破吧!”抚筝说。“去吧,早些回家,别耽误了正事儿。”鹤云叮嘱女儿。抚筝笑着点头应是。鹤云放心地走出女儿的琴行,手里捏着两张百元,嘴里却叹气:“我一个摆地摊的,还要到小商店去破零钱。”独自咕哝着,破完零钱兀自转路回家了。
其实,鹤云早就不愿意摆这小摊了,可不摆摊干啥?总不能光下围棋吧!再说老待在家里也不行呀,老婆能看上?摆小摊只是挡眼的。每天回来交上几个小钱,老婆心里也舒服。晚上做几个小菜,几杯扎啤下去,小日子倒也挺滋润的。可是,女儿抚筝一不在家,鹤云就有些心神不宁。吃过晚饭后,鹤云坐在沙发上,双眼盯着电视屏幕,心思却不在那些男欢女爱的电视剧上。平日他不看电视,一有空就看棋谱。此时手里没棋谱,眼神儿就无法安定,一会儿电视,一会儿斜瞄墙上的石英钟。八点钟刚过,就让老婆给抚筝打电话,“女儿都大了,出去吃个饭,你催她干啥?”老婆被鹤云说的烦了,对他没好气。“不管多大也得回家呀!”鹤云也没好气,“一个女孩子晚上在外面疯什么!”
老婆不再接鹤云的话,她心里明白鹤云为什么着急,看看他放到地上的那些破瓷破瓦,怕是又要让抚筝回来给锔起来。“快给抚筝打电话,让她回来。”鹤云黑着脸说,老婆不吭声,电话也不打,兀自看着她的情感剧。
“快打电话。”鹤云又催,“也不知道和谁出去鬼混?”
“要打你打。有你这样说话的吗?”老婆也没好气了,“你为什么非要她学你那破行当,她一个女孩子家你为什么逼她?”
“不学行吗!”鹤云一听老婆这唠叨,猛地一拍桌子发起火来,“她是我来财的闺女,不学不行!”
老婆猛然被吓了一惊,她惊异地盯着丈夫,惊异他竟把“来财”两个字叫的那么狠!她在丈夫的目光下让步了,没吱声,默默地给抚筝拨手机。拨了几遍,通了,可是抚筝没接。鹤云焦急地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一个女孩子在外面疯到这么晚。”
“好了,好了,别转了,她一个女孩子谁干你这行。你们家的规矩传男不传女,你逼她干什么?”老婆说。
“我倒是想传男,我有吗?”鹤云喊。
老婆一下子被憋了回去,坐在一旁不敢做声了。
抚筝回到家时已经是午夜,她蹑手蹑脚地进门,生怕惊动了爸妈,轻手轻脚脱掉高跟鞋,打开灯。昏黄的灯影中,鹤云正坐在沙发上,一双眼睛紧紧地盯住抚筝。
“爸,你怎么还没睡?”抚筝惊得张大了嘴。
鹤云在沙发上呆坐着,一声不吭。抚筝望着他那严肃的面孔,久久不敢往屋里迈步,看上去爸爸真的生气了。
“明天早上把那些破碗锔好了再去开琴行的门。”鹤云扔下一句,低头进卧室了。
“爸……你为什么非要我学呢?我是弹琵琶搞艺术的。”抚筝委屈地喊。
“弹琵琶也是种手艺,手艺做精了就是艺术。”鹤云头也不回,声音很低,但语调严肃得不容反抗。
第二天,抚筝的琴行中午才开门。马强就在茶馆门口直勾勾地盯着。抚筝一时不出来心里就一时不得安宁。抚筝从胡同口走出来,马强一溜烟地跑过去:“抚筝,怎么啦?怎么才来?昨晚喝多了吗?”“没呢,还不是我爸在家押着我箍了一上午的破瓷碗。”抚筝委屈地说。“鹤云叔真是,非逼你干什么。”马强抓住抚筝的手,无限怜爱地吹了吹:“这双弹琵琶的玉手,能干那些粗活吗!”“去!”抚筝脸一红,急忙把手抽出来,“也不怕人看到。”“怕什么,早晚的事儿。”马强嬉皮笑脸地笑,抚筝嘴唇歪了歪,从嘴皮儿中间“切”了一声。“我不是担心你嘛!”马强又追上来说。抚筝一下子站住,用手指着马强的鼻子尖上:“真担心我,就想法把我爸弄走,别让他这么盯着我。”“可你爸爸要摆摊呀!”马强迷茫地说。“他摆什么摊啊!是在摆棋,昨天就你给他卖了那两块钱,给我妈的钱是我给他的。”抚筝揭了鹤云的老底。
“那怎么办?”马强困惑了。
“想办法找他去下棋呀!他现在不是迷棋吗?”抚筝说。马强眼珠儿一转,似乎领悟明白了抚筝的意思。
马强又献媚地跟上抚筝,笑着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离我远点呀,别让他看到了说我们预谋。”抚筝跺了一下脚,挤着眼示意说。马强急忙走开了,然后就站在茶馆门口,双眼盯着鹤云每日来回走的胡同,单等他的出现。
鹤云今日出门也是很晚,但是脸上却洋溢着喜色。怎么说呢?女儿还是听他的话的,尽管心里不乐意,还是锔完了他制定的那些物件才去开门,这样他的心里就有股满足感,心情不自觉地平添了喜气,嘴里哼起了小曲儿。他刚一出胡同口,马强就笑着迎上来:“叔,今天怎么才出来?”
鹤云看看马强,没吱声,继续往前走。“叔,我在等您哪!”马强迎上前来,压低了声音。“叔,今天一帮棋友约着在茶馆比棋呢!”“什么人?新的?”鹤云的眼光突然间就亮了,扭头望着马强。
“不是,昨天那帮人下棋顶起角来啦,今天各自请的高手。”马强神秘地说。“假话,又是那帮赌棋的吧?”鹤云摇摇头说。
“我还敢和您说假话?反正是高手要来,您爱信不信。”马强说的模样依旧神秘,用话吊着他的胃口。
“我去了,你秋林叔怎么办?”鹤云对马强找借口。
“叔,秋林叔的棋已经不能和您比了。”马强说,“现在,秋林叔在您面前只能算是臭棋了。”
鹤云的脸上挂了笑意,这夸赞虽有拍马屁的成分,他还是很受用的。他看了看马强,兀自往前走。
对于茶馆里的摆棋者,鹤云是知道的,也是他没有想到的。年代骤然就变了,当他把名字从“来财”改为“鹤云”后,下棋的人又都讲究求财发财了,原本儒雅的爱好与营生也都往钱财上靠了。相比之下,古意又算什么呢?禅意又何其遥遥无期!连最接近古意的围棋也都变味道了。黑白二子拈于指间,好似酸不叽、粘不沓的,心理不再那么愉悦。原先下棋,大家只图个清乐,乐而忘事,乐而忘忧。现在呢,棋人纷纷不肯白白磨手指头了,就是“开赌了”,这很令鹤云气愤,气愤而无奈。
如此,他和秋林宁肯在路边手谈,有时宁肯观光,也坚决不进茶馆去赌。可是,秋林已远远不是他的对手,和臭棋篓子下棋,怕是要越下越臭。
鶴云内心其实已经孤独一阵子了。他缓缓走到桑梓路的十字路口,冷不丁回头望着马强:“那高手什么时候到?”“过一会儿吧。”马强说。鹤云悠悠地回过头去,慢慢向抚筝的琴行走去。对着他的背影,马强琢磨不出所以然来。
鹤云走到琴行里,却没有急着要出摊,而是斜睨着马强茶馆的大门,装作无意地注视着茶馆里进出的人,他越是注视就越没法探求到心里想要的答案,心就越吊吊的。还是忍不住了,对抚筝说:“今天晚了,我就不出摊了。”“行,爸。你去哪?”抚筝求之不得呢。“不过,今天不出摊是因为你耽误了我的时间,晚上交给你妈妈的钱还得你出。”鹤云又不冷不热地对抚筝说。抚筝一怔,接着咯咯地笑起来:“爸,下棋下刁了啊,再说哪天的钱不是我出的?以后不让我学你的手艺了,我多出!”“嗯——”鹤云猛地黑下脸,望着抚筝。抚筝暗吐舌头,没想到就说漏了嘴,急忙扭头走开。
鹤云挪步向马强的茶馆走去,头也没回地嘱咐抚筝:“秋林叔来找我,就说我去茶馆了。”说着走过去,步子还是犹犹豫豫的,指定要去又有些拿捏。还没到茶馆的门口,马强便从里面迎出来:“叔,你到底还是来了。欢迎,欢迎!”马强的热情让鹤云有些不大适应,问:“你怎么知道我要来?”马强一惊,忙说:“抚筝……我在里面看见了嘛!”鹤云会意,心里说这小子反应还快着呐!
茶馆里还是桑梓路上那些下棋的人,他们无所事事,便聚在马强的茶馆里下棋赌钱。其实,凡开赌,就没有对弈的“平常心”,皆大开杀戒,两军相逢勇者胜,谁力量大就占便宜,而且输赢要论子计价,比方说,输一子十元,一目翻四倍,或者五元,累积起来,一次进出几十元,成百元,数目可就大了。倘若只赢四分之一或四分之三,微胜,白扯淡,等于没玩儿。俗态毕现,雅意也就没了。众人见鹤云来了,皆往前让,鹤云不语,微笑观看,先摸底细,见几位的棋路皆不上道,观战长了,不住叹气,终于忍不住,上了场。对手弱就狂炸滥砍,业余名手见鹤云气势,也不免惴惴,加上心理素质不见得怎么好,竟然也败于鹤云之手,于是鹤云洋洋自得。
下到傍晚,口袋里鼓鼓的,有四五百元的收入,比他摆地摊强很多。直到马强送他出门时,也没见到所谓的高手来临。但是,鹤云的心思和表情都是自得的,用手点马强的鼻尖说:“你小子,敢糊弄你叔,高手哪!”
马强贼贼地笑了:“说来没来,明天我再打电话确定一下。不过,您今天也没白来,岂不比您摆摊强吗?”鹤云得意地用手拍了拍装钱的口袋,却说出一句:“小子,你叔我下棋是雅士,说到钱可就俗了。”往前走几步,只见秋林正站在茶馆门前怒目而视:“你雅个屁!”
“你怎么不进去,在这里站着哪?”鹤云上前怯怯地问。
“沾到钱我是死活不干的!”秋林怒怒地扔下一句,扭头而去,给鹤云留下一个迷茫的背影。鹤云呆呆地站住了,突然又回头对马强说:“都是你这小子给闹的。”
鹤云仿佛心中的火气没撒完,直直地走进抚筝的琴行。琴行里只有抚筝一个人,一见女儿,鹤云脸上露出笑意:“走,回家了。”抚筝笑迎上来,手却早早拉开了钱包:“爸,我再过一会儿。”鹤云急忙挡住抚筝拉钱包的手,顺便拍了拍口袋:“不用了,今天我自己交。走吧别靠了,不会有人来了。”
“爸,您先回吧。我怕有同学约我。”抚筝在父亲面前讨好地挤眉弄眼。
“不行!别想逃过去,今天早上的活锔得太粗了,今晚上得回去下细功夫。”鹤云黑着脸说。“爸,我是个弹琵琶的,却让我锔盆锔碗?”抚筝噘起了嘴,是一副欲哭无泪的表情。
“抚筝,弹琵琶是一门手艺,锔盆锔碗是我们家传的手艺,你得学呀!逃不了的。”鹤云语重心长地说。
“爸,你也不看看,这都什么年代了,我学这手艺干什么?有用吗?”抚筝争辩道。
“压着你了没有?”鹤云提高了语气,“再说你学弹琵琶现在用着了吗?还不是在卖琴。艺多不压身。走吧。”鹤云的话已经说到了底,不让再有所反抗。抚筝无话可说了,只好关门,默默地跟在鹤云的身后回家。她注意到了,马强正站在茶馆的门前,眼睛直勾勾地,怅然若失。
抚筝往前走去,把握着手机的手举起来摇了摇,马强会意,兀自忙不迭地点着头。
自打进了马强的茶馆后,鹤云的心就不平静了,时常不住地探头递耳地去打听消息。实战总比在小摊前摆棋式等秋林强,但再想到秋林那愤怒的目光又不敢轻易前去,他害怕因为铜臭失去朋友。日子在这心情的纠结中过得两难了。而那帮输了钱的棋友,自然也不肯罢休,时常过来挑衅他,他心里蠢蠢欲动,但还是咬牙忍住了。正纠结的时候,马强跑过来,说:“叔,他们请的高手来了。”
“怎么样?”鹤云问。“我看着棋路还行。”马强说。“走,和高手过过招,你秋林叔就不责怪我了。”说完,摊也不顾得收拾就往茶馆里跑,回头对马强说:“让抚筝把摊收起来。”
鹤云跑进茶馆,高手正站在对面等着他。高手真有高手的风范,岁数看上去比鹤云年长,但身材笔挺,腰板笔直,头顶已半秃,胸前却飘着几绺长髯 ,身着白色中式丝绸短褂,灯笼裤,纳底皮鞋,一只手背于身后,另一只胸前端着,掌中一盏古旧的小泥茶壶。介绍相见过后,鹤云盯着高手手中的小泥茶壶直了眼。那可真是一只旧茶壶,外皮已斑驳得不成样子,并且茶壶上有一道长长的裂纹,上面斑斑驳驳地箍着铜锔子。
众人落了座。鹤云心里稍有点虚,毕竟是高手,又没试过水,不敢妄断。而鹤云的棋力,是个悲剧的“半吊子”,自称0.9段,太弱的不敢靠前向鹤云请战,太强的,鹤云总吃亏。与高手定下价码,几局下来,虽然各有胜负,总帐一算,还是鹤云稍亏本。但鹤云的心里却有了底。第二天,高手又来,讲规矩时,鹤云突然对高手说:“我输你,你算钱,如果我能赢你十局,你把这把壶送给我如何?”
高手一怔,他没想到鹤云看中的竟是他的这把壶,他明白手里的壶看似古朴,其实并不值钱,本身就是一把破壶,上面有条长长的纹,锔满了铜锔子。
鹤云定下的条件对高手是非常优越的,他自然高兴,但是面色却严肃:“鹤云兄,我这把壶虽破旧,也有些年岁了,你说话算数?”鹤云笑笑:“我在桑梓路过大半辈子了,何时有过戏言?”双方盟约既成,双方开始对战,两天下来,鹤云却仅仅赢了三局,而口袋里三千多元的私房钱却打了水漂。
“鹤云先生,还来吗?你若赢够十局,得多少钱往上赔呀。”高手面带冷笑挑衅地说。
“放心,我还输得起。”鹤云也笑笑说。
第三天又如约而至。鹤云和高手正对战着,抚筝找上门来。马强一见,喜上眉梢,“你怎么肯过来了?”“你这是干的什么破勾当,我爸今天又向我要了两千元,是在赌棋吗?”抚筝面带怒气。
什么?鹤云输了这么多?马强是个血性汉子,是因为迷棋才开了这个茶馆,本来是为了以棋会友,稍加理财滋润,却弄成了这个样子。他安慰了抚筝,独自在旁边观棋。俗话说,外行看热闹,行家看门道,一会儿便了解了事情的原委,高手的棋力细究起来并不优于鹤云,而是这一帮人在对付鹤云呢!马强嘴上不语,心里却较了劲儿,当看到鹤云局势不妙,抓耳挠腮时,便替鹤云着急,忍不住,就替鹤云来个一招两招,形势片刻间对鹤云有利,鹤云凭空增加了许多力气,好像援兵突降一般,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竟然在无人支招的情况下,也连下三城,可见人的力量也是三分體力,七分精气神啊!
高手和身后的那帮泼皮便对马强白眼相加,口出怨言,马强不做声。高手一帮以为马强羞愧了,又要声讨鹤云,谁知马强回身拿起一把精致的紫砂壶,往高手面前一拍,说:“是什么局势明眼人心里明白,鹤云叔钱也输你不少,你把这壶拿去喝茶,你那把旧壶给鹤云叔留下。”
因为气大力猛,马强拿过来的壶却被拍坏,碎成了八块!
“我没输,为什么要留下我的壶?”高手口里争辩道,不肯把壶放下。马强一瞪眼珠子,也不言语,死死地盯住高手的眼睛……高手胆怯了,颤抖着把壶放在鹤云面前,悻悻地要率那帮泼皮离去。“你自己去架子上再挑一把壶吧,碎的我留下。”马强说。高手也没客气,走时顺了一把紫砂壶。高手刚出门,鹤云便宝贝似的把那旧茶壶捧在手里。
“叔,你要这把破壶干啥?”马强问。鹤云抬头木然地笑笑,又低头细数着那旧壶上的锔子,低声感叹:“这活,做得精致呀。”
马强坐在鹤云的对面,叫服务员特意泡了两杯明前西湖龙井,两人对饮叙话。马强说:“叔,你看不出来吗,他们在合伙算计你哩。”鹤云沉默了一会儿叹气说:“大家活得都不容易,就将就过去吧!再说,我真的想赢这把壶。”
“就这把破壶?”马强一脸不屑。
“可别小看了这把壶,你看把紫砂壶锔成这样,做得多么精致,真是头一次见啊!”鹤云说,“值得学呀!”
“店都关了,还学这些干什么?”马强说。
鹤云脸上露出一丝儿苦笑:“是种手艺,总是学精致了好。”说完,又把马强拍成八瓣的紫砂壶收起来,用舌头微微舔了舔破壶的茬口,又认真地舔了舔,低声说:“放心,这把壶,我也给你锔起来。”“算了,都破成这样了,”马强说。“相信叔的手艺。”鹤云笑着,小心地把碎壶捧在手里,回家去了。
半夜时分,马强被电话铃声惊醒,一看是抚筝的。他有些惊异,抚筝在电话里撒娇似的骂他:“你从哪里弄这么个破壶,害得我和我爸给你干到现在!你不打算让小娘子活啦?”马强急忙嬉皮笑脸地说:“我错了,我错了!害你受累。我还以为你这时来查我的岗呢!”“滚!我哪有那闲工夫。你一个破壶累得我腰酸背疼的。”抚筝语气里故作生气。“待我抽空给你揉揉算作补偿。”马强急忙讨好说,一番柔情蜜意的悄悄话。
清晨,马强刚一开茶馆的门,鹤云早就捧着昨夜锔好的茶壶站在门前,见到马强把壶递上,“锔好了,把壶还你。”“鹤云叔。”马强接过茶壶不禁呆了,昨天一把拍成八瓣的壶竟然完好如初,修补锔钉做得精致极了,锔子都是红铜的,细小精巧,镶嵌得恰到好处,不深不浅,都是量物而做,不差分毫,掩缝的灰膏单做的颜色,与茶壶无异,不但有原壶的圆润,而且像是给原壶刻意增加了装饰,反而增色。
“叔,你收我做徒弟吧,我跟你学锔壶。”马强手捧茶壶,脱口说道。鹤云没有接话,而是说:“你别看外观,还没试漏不漏呢。”“做得这么精美,我都不舍得用了。”马强说。“别……”鹤云从马强手里接过壶来,把沸腾的水倒进去,然后用细绳打了托扣,用手提了提稳实了,才对他说:“你把它吊起来,把壶下面铺上宣纸,如果宣纸湿了一滴,就不是我来财的手艺。”鹤云颇有些得意地说。
“不用吊。叔,我信,真的。我太崇拜您了,就连用细绳打的托扣都没人会了。您收我做徒弟吧,什么条件,孝敬你多少钱我都答应。”
马强诚恳地说。“照我说的做吧!”鹤云微微一笑,转身而去。
马强按照鹤云的吩咐,把壶悬在了横梁上,底下铺上白色的宣纸。明眼人都知道宣纸是很薄的,只要有一滴水从壶中漏下来,就会把宣纸洇湿。可是,过了多日,那宣纸安然无恙。
这些日子,鹤云既没出摊也没有出来下棋,而是在家里研究那把刚赢来的壶。抚筝下班回来,对鹤云说:“爸,马强要请你吃饭。”“吃什么饭?”鹤云眼盯在壶上,头也不抬。“请你吃大餐,说要摆个拜师宴。”抚筝凑到鹤云跟前,撒娇地试探着问:“爸,马强这徒弟你收不收?”
“我都不干了,还收什么徒弟。”鹤云说。“你不是要传你的手艺吗?”抚筝噘着嘴说,“有马强这个徒弟,手艺不就传下去了吗?”
鹤云把眼一瞪:“那你干什么?”“我弹琴呀!”抚筝说。“马强愿意学,就传给他吧,再说你们家的手艺不是传男不传女吗?”老婆在一旁打着帮腔。
“胡说!什么传男不传女?再说马强是我什么人?”鹤云说。“你这榆木疙瘩,不知道马强和咱家抚筝……”老婆上前点了一把鹤云的脑袋,“马强都快成你的女婿了。”
鹤云一怔,疑惑地看着抚筝,抚筝捂着嘴笑。鹤云猛然咬牙:“马强这小子,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呀!竟敢勾引我的女儿。”“怎么?爸,你不满意?”抚筝一惊。鹤云沉默了,在屋里默不作声地踱步,步子又稳又慢,却把抚筝弄得心惊肉跳,一双杏眼儿盯着爸爸,期待着那严肃的面孔渐渐地溢出笑意。“满意是满意,但传他这手艺也得订了婚再说。”鹤云说。“行,爸,你没意见,我们就订婚。”抚筝喜上眉梢,上前亲昵地挽住鹤云的胳膊。
马强和抚筝的订婚仪式和拜师酒宴是一起办的。酒宴上主要演绎了马强拜师的场面,马强向鹤云献了花,敬了酒,也鞠过了躬。参加酒宴的人都很高兴。秋林老师主持的仪式,秋林从心里感到高兴,拍着鹤云的肩膀说:“这下好了,你的手艺也失传不了啦。”“马强这小子还和抚筝好上了。”鹤云咂着嘴儿,“抚筝可是个搞艺术的。”“行啊,马强也不错。”秋林说。两个老朋友,心里高兴话就多,说到兴致,就想再去来上几杯扎啤。岛城人就这样,扎啤摊上一坐,来上一碟蛤蜊,所有的兴奋就溢在脸上了。
鹤云和秋林刚转出胡同,黑影里马强正和抚筝拥抱着,说着悄悄话。鹤云扭头要走,秋林一把拽住了他,酒精的兴奋勾起了两人年轻的心。
只听到马强甜蜜地说:“小娘子,这回大爷可算是给你赎身了,你以后真是大爷的人了。”抚筝问:“什么意思?”
马强说:“以前是你爸你妈的人,现在转给我了,以后你爸的手艺传给我,把你解脱了,让你真正地当老板,弹琵琶,这不权当给你赎了身么?”
抚筝转过脸:“我呸!你小子赚了便宜还卖乖。和你说以后要对我更好,不然本姑娘就重操旧业。”
“那可更好了,大爷赎个色艺双绝的小娘子岂不是天大的美事!”马强得意洋洋地飘了。
“本姑娘可是只賣身不卖艺。”抚筝说。
……
秋林捂着嘴忍不住都要笑出声来了。鹤云却虎下脸来:“抚筝,早些回去,这会儿有马强陪着,活再学起来就不孤单了。”说完,拉着秋林,胸有成竹地向扎啤摊走去,留下抚筝和马强一脸的无奈。
马强拜师以后,鹤云就不再摆摊了,被马强邀请到茶馆里,留意着茶馆的生意,也摆着棋式,对弈手谈两不误。鹤云这师父和准岳父的双重身份也合适,不会被人说三道四。每天,鹤云走进茶馆,抬头看到悬挂在横梁上的茶壶,心情极是愉悦,下棋摆式也极有兴致。每当客人走尽,要给马强示范教授锔工的技艺时,他总是对马强说:“去把抚筝叫来,让她跟你做个伴儿。”马强就去叫抚筝。抚筝来时虽噘着嘴,不过有马强陪着,心情总要好些。她对马强说:“小女子可真是算错了这一步呀。”
马强对锔功的确很用心,小伙子机灵,肯钻研,技艺进步很快。鹤云心里很满意这个徒弟,在茶馆里的日子过得舒畅滋润。
一日,鹤云又在独自摆着棋式,马强带着几个人走进来,“爸,有客人来了!”鹤云点点头,礼貌地打着招呼,又独自研究着棋谱。“爸,重要客人哪!”马强又说。“哦,我摆完这几步就来。”鹤云头也没抬,对棋迷得极其专注。
一位领导模样的人制止了马强,站在旁边,真是等鹤云摆完棋式才过来说话,来的是市博物馆的馆长和陶瓷协会的教授。鹤云有些手足无措。馆长很客气,对鹤云很是尊敬:“鹤云先生,我们来请您来了。”鹤云紧张地搓着双手,却不敢上前:“我一个小箍漏子,真是见笑了……”“您的杰作挂在大厅里哪,我们可都见识了。”馆长赞叹着。
馆长和几位教授的确是慕名而来,市博物馆有一批珍贵的古旧瓷器需要修复,因为没有找到好的锔工,一些老的修复技术近乎失传,一直没敢动。最近这批古瓷器去各地展出,非修不可了,博物馆听说了马强茶馆悬着壶的事儿,市里已派专家暗访了多次,今日终于上门来请高明了。
“我不去,我已经洗手不干了,这事儿还是让马强去吧。”鹤云说话的时候很紧张。结结巴巴的,“我——现在只——迷围棋了。”鹤云只是个桑梓路的锔匠,或许真的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在这些人面前搓着手,不一会儿就拘谨得满头大汗。
馆长见鹤云说这些话,面色有些失望,扭头疑惑地望着马强。
“他是我女婿,又是我徒弟,他肯定能做好。”鹤云说着,把马强练习时锔的瓷片递过去,馆长挑了几块瓷片,有些失望地回去了。
“爸,是您大显身手的时候,您怎么又退缩了?”送走了客人,马强疑惑地问。
“现在有你,还用得着我吗?”鹤云一转窘态,口气得意起来,“传统技艺得让年轻人发扬光大,还要让他们知道,这箍漏子也有传人。”
博物馆的一行人根据带回去的瓷片,经有关部门专家鉴定和研究,还是高薪聘请马强去修复古陶瓷。马强很高兴,鹤云也很高兴,他对抚筝说:“教你还不愿意学,这下有用了吧?马强,给师父争脸。”
“爸,我有眼无珠哪!”抚筝夸张地拱手作揖,“师父,你也收了小女子吧!”
马强去博物馆了,茶馆交给抚筝管理,一边琴行,一边茶馆,忙得不可开交。可鹤云并不在意这些,依然迷他的棋,对另外的事问都不问。在棋盘上打谱读式,一手捻起来尚未放下,眼前却放上了一块包着东西的白手帕,鹤云抬头,见是马强。马强不做声,默默地把手帕打开,里面包着几块小茶壶的碎瓷片,这瓷是难得一见的好瓷,而这瓷碎得也是难得一见,瓷片都弯弯曲曲的,九曲回肠一般,要想把这个茶壶准确拼凑起来都难,更别说锔起来了。
“爸,馆里还有这么把壶,能锔起来吗?”马强试探着问,“博物馆珍藏着这些瓷片已经多年了,一直散着。”
鹤云的双眼微微有些迷离,默默地抓起一块碎瓷片,用舌头舔了舔,他不做声,想起了师父曾对他说过的一件事:江湖上有一种“撑壶法”,就是用小锤子轻轻敲打茶壶,既不能敲坏,又不能留下疤痕。被敲打的茶壶表面上完好,其实已经有了暗璺,已经是一把残壶了,然后再在壶里面装上大豆或高粱粒子,用热水一泡,闷在壶里,等不长时间,大豆或高粱粒子一膨胀,就听得茶壶在“咔咔”地响,过不了半天,茶壶就碎成这样了。能做出这手段的,在瓷界也不是泛泛之辈。以前鹤云也只是听说,没想到现在也着实开了眼界。
“爸,能锔吗?”马强又试探着问。
鹤云把用舌头舔过的瓷片轻轻放在棋盘里,嘴唇吧嗒了几下,像是在回味瓷片的滋味。他的眼睛里突然划过了一丝儿光亮,低声说:“去叫上抚筝一起回家吧,这手艺师父传给我,一直没有机会试过,今天遇上,是有幸,也是你们的造化啊!”
马强和抚筝回家,鹤云已经从他的工具箱里拿出了工具,并且还请出了师父的遗像。他对两人说:“是有造化啊!你们看,这也是锔行中的难活啦!锔起来有些麻烦,这是景德镇的细瓷,要用金刚钻,金锔子才行。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就是对这种瓷说的。过去用寻常的铁锔子见水生锈。”
“爸,那还能锔吗?”两人异口同声。
“當然。”鹤云说着,把碎壶放在师父的遗像前,恭恭敬敬地拜了拜,又把壶拿下来,在香炉里上了香,低声说:“你们看好了,在烧完这炷香之前,我就要把这活干好。如果烧完香这壶就锔不起来了,你们仔细看着,注意我的手法。”说完,鹤云坐下来,拿出金刚钻和金锔子。只见鹤云把茶壶的碎片放在手里,另一只手快速地晃了晃,碎片就拼成了一个完整的茶壶,还原得丝毫不差,然后把茶壶固定好,施展开了绝技,那动作快得让人眼花缭乱,连抚筝和马强的眼睛都看花了。但是,在他们面前,鹤云一直让自己的动作清晰完整,让俩人看清他的手法。只听得一些细碎清脆的声音,不多时,一只完整的茶壶就捧在鹤云的手里了。锔好的壶身完美光滑,茬口之间合得一丝不差,一点也找不出破碎过的痕迹,金锔子摆得也工整,从外面看金光闪闪,煞是好看,直把马强和抚筝看得嘴都合不上了,而师父像前的那炷香只燃到半截。
鹤云又叮嘱道:“记住了,锔这样的碎壶,讲究一个快字。”“爸爸,你真是神了!”抚筝过去扶着鹤云说,“要是这种手艺不传下来,太可惜了!”
“我所以硬要把这手艺传给你们,就是怕有遗憾。其实,有很多高超精绝的手法都快失传了。”鹤云叹了口气说,“幸亏有了马强这个女婿,还有了两个传人。”
“爸,您说有些绝技失传了,还有比您这手法更绝妙的吗?”马强问。
“有啊!”鹤云说,“还有种手法叫隔空锔物。”鹤云接着给两个孩子讲了一个他师祖的故事:早年,师祖下东北闯关东,因为有这锔锅锔盆锔大缸的手艺,就没有去深山老林挖金子、伐木头,而是凭着他的手艺走街串巷。一日走到一家大镇上,被一户富贵人家请了进去,进门时,少东家还亲自出门迎接,师祖有些受宠若惊,正想着,管家牵了一条大狼狗进来,那狗一呲牙,师祖吓得不由得倒退了几步。
少东家急忙上去说:“师傅不要惊慌,这是我的爱犬。你别看它外表凶狠,其实十分听话,没有主人的话,你就是踩在它身上,它也会一动不动。这次请师傅来,就是为了这条狗。”说着,少东家拿出一小块东西来,细一看,竟是半颗狗牙,少东家说:“这条不知好歹的狗竟然把石头当成了骨头,一颗牙啃成了两半。师傅能不能把它给锔起来,让 这狗有颗完整的牙?”
什么?!给狗锔牙?真是闻所未闻。但师祖并未惊慌,细细观察后,他要求少东家用小铁架子把狗的嘴支开,再把狗的四肢捆起来,让它不得动弹。在少东家的调教下,那条狗比绵羊还老实,任由少东家把铁架子塞进嘴里,把缺了牙的地方显露出来。狗嘴支起来后,师祖却不急着下手,反而跟少东家聊了些无关紧要的事儿,等人们都不把注意力放在狗嘴上时,他突然大叫一声,谁也没见师祖做了些什么动作,只见金光一闪,狗“嗷”地叫了一声……大家再一看,师祖还是纹丝不动地坐在原地,那半颗狗牙已经牢牢地安在了狗嘴里,在那颗狗牙上还有一个细如蚕丝的锔子……
“爸,这绝技是怎么练成的?”抚筝惊叹着。鹤云微微笑了笑,别有意味地说:“手艺和艺术一样,有时也要看天分悟性的。”
因为修复这把破壶,马强受到了全市的嘉奖,不但挽救了这把珍贵的瓷壶,同时还展现了锔壶的绝妙工艺,并被破格提拔为博物馆的副馆长,并任市古瓷修复小组的组长。一不小心还获得了机会走上了仕途。
茶馆和琴行都彻底交给了抚筝打理。鹤云此刻可真正成为悠闲的棋人了,平日没事时和秋林喝扎啤,聊围棋,日子过得挺清闲。
“如果你年轻时遇到这机会,说不定不差于马强。”秋林说。“我只耍手艺,上门来行,不会去。有马强这徒弟,我也知足了。”鹤云说。
马强确实挺争气的,和抚筝结婚后,运势很好,步步上升,现在已经是全国知名的古瓷修复专家了,有很多外地单位和个人慕名而来,一时红火得很。马强的棋扔到一边去了,主业反倒成了副业,而副业却成就了他的事业。
市博物馆接受了一批珍贵陶瓷的修复任务,有一部分需要破碎后再修复。马强故意在鹤云面前提过几次,而鹤云只顾研究他的棋谱,对马强的话充耳不闻,只做没听见。马强再也忍不住了,拿出一只瓷碗放在鹤云面前:“爸,您帮我敲碎这只碗?”
其实,把瓷碗敲碎谁不会?关键是怎么个敲法,如果要把碗敲成两半,从中间分开,两边一样大小,差一点儿都不行,这难度就可想而知了。谁能把碗敲成一模一样的两半?马强要的是根据要求把瓷器敲碎。
“我是锔瓷的,哪会破碎?”鹤云对马强的话不屑一顾,“再说了,这是犯忌的事儿。”一甩手,不再理那碗。马强很失望,晚上要出去应酬时还不住地唉声叹气,看来真的遇到难题了。
马强刚走,鹤云就让老伴儿打电话给抚筝,叫抚筝回来,说有急事。抚筝一听家里有急事儿,自然在店里坐不住,急匆匆地回到家里。进门后,发现和平时一样,只是爸爸坐在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块垫布,垫布上放着几只瓷碗。抚筝一见笑了,开玩笑说:“爸,你不摆棋,怎么又玩起戏法来了?”
“过来,坐下。”鹤云却没笑,而是一脸严肃。抚筝急忙过来在鹤云面前坐下来,鹤云把小铜锤拿在手里,低聲说:“面前说的那种破瓷的方法,叫惊瓷儿,我现在教你怎么敲。”
“你直接教马强行了,怎么还教给我?”抚筝不解地说,“两个店都把我忙坏了。”
“坐好了!”鹤云严肃地说,“你是女儿,他是女婿,我教谁?”
抚筝不敢再言语了,坐下来,静着心跟爸爸学会了“惊瓷儿”的绝技。
“明天你去帮马强他们吧,要稳住了,不要轻易让他们看出你的手法。别人都会,你还有意义吗?记住,一招鲜,吃遍天!”
抚筝走的时候,鹤云千叮咛万嘱咐。抚筝频频点着头,心里却满是迷茫。
抚筝“惊瓷儿”的绝技在博物馆里发挥得淋漓尽致,惊到了众人。当她满面春风地回家时,鹤云脸上挂着会心的笑意,“怎么样?闺女。”
“谢谢爸,不!谢谢师父的真传!”抚筝双手抱拳,对爸爸撒着娇。鹤云用满意怜爱的眼光望着女儿,开心地笑出声来,心里说,抚筝也行了,成手了,往后真可以安心地下棋了。想到这儿,禁不住转过身来,微笑着欲出门去茶馆,再喊上秋林对弈几盘,然后惬意地喝上几杯扎啤。
“爸,你不会真的让隔空锔物的绝技失传吧?”抚筝在他身后低声问道。
鹤云猛地站住了,身体冷冷地一抖,刚安下的心瞬间吊了起来。棋怕是没心思再去下了。
责任编辑:刘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