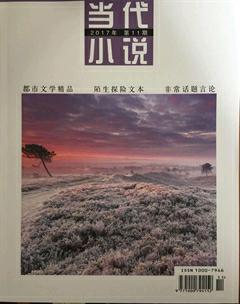老狼来了(短篇小说)
孙鹏飞
我趴在床上,等待着盲人给我按摩颈椎。我这几天颈椎疼得要命。盲人是个中年汉子,在我租房子的小区里开了家按摩店,很小的门店。店里生着炉子,我脱了大衣,老老实实趴着。他冲着我的脖子,一把捏了下来,我的脚抖了一下。他说,脖子太僵硬了。我忍着疼哼哼两声。他又捏了几下说,你的颈椎不好,一捏就知道。我说我是个小说家。颈椎是平时写小说累的,不光颈椎疼,腰也疼。他劝我好好调养身体,他自己年轻时候干苦工,不注意身体,人到中年留了一身病。我写小说不是不知道休息,经常是盯着电脑敲打一阵,恍惚一阵,一天差不多过去了。
墙上挂着盲人年轻时候的照片,模样颇像我爸爸。盲人做过木匠,做过铁匠,我单从几张照片无法判断他做工的先后顺序,但是能判断他真的很有劲。跟我爸爸一样有劲。
我成长中最大的敌人是我爸爸,我少年时候他的火气很大,后来随着我长大成人,火气倒在慢慢变小。每次碰见他要发火又忍着,我都不遗余力把他的火气逼出来。他打我最狠的一次我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去。我一度怀疑我有病,症状表现在我从来不知道示弱。这么说好像往自己脸上贴金,说我是缺心眼儿错不了。
这是十二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就过元旦了。很显然,除了疼痛,一整年我一无所有。我出了一身汗,按完,我在他小店里坐了会儿,汗消下去,我拿钱给他才知道犯了错误。带的现金并不够。现在出门带的现金少,多数时候用支付宝。我问他支付宝可以吗,很抱歉,他用的老年机。
“我回去取你放心吗?”
“你还有事,先去忙吧。忙完回来再给钱。”
我有些犹豫,鉴于每个周末都找盲人按一次,月底结账,这笔钱已经不是个小数目了。可我确实有事,西海岸电影学院的编剧系的大四学生李桢约了我。我兜里可怜的几十块钱不能给他,得留着坐公交车。李桢这次约我是因为老狼来了,也不光老狼,来的还有张驰、周大年、狗子,他们今天下午两点在岛城一家独立书店签名售书。虽然我是写小说的,可这些人里,我只知道老狼。虽然老狼不是写小说的。
我跟盲人道了谢,出了门到马路对面等公交车。岛城现在开发地铁,只开发了几条线,我住的地方尚未普及。上了公交车,售票员问我去哪,我没敢说到火车站,因为到火车站有近一个小时的路程。我报了最近的站牌。买了票,我扔到了车厢,混进一堆五颜六色的票里。
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售票员多数情况下不会记得你在哪一站下车,也不会再检查你的票。我这样投机取巧,有失一个小说家的尊严。可是,我租的房子是女朋友交的押金,交了半年的,过完元旦就到期了。我最近的一篇小说是明年二月初发表,远水可救不了近火。此外还有一家省级刊物的稿费没领到手,编辑说杂志社经营不太好,他也是写作的,知道写作不易,但更清楚办刊物的艰难,望理解。
我怎么理解?
李桢发短信说坐上了公交车,进了海底隧道。问我到哪里了。我没好意思说刚出门,只说在路上堵了。
也真的在路上堵了。车窗外的喇叭声此起彼伏,我伸着脖子看扭七拐八的车龙,在岛城二中的减速地带堵上了。我对二中实在情有独钟,这地方离我租的房子最近,经常散步过来买两本杂志。这边的报摊效益很好。因为消费者都是些上课憋屈,下课又无所事事的小学生。
小手里握着书本的小学生,从一辆辆堵着路的或新或旧的私家车里往外钻,奔跑起来活像传送带上的炮仗。小学生在二中大门口的一张书桌前聚集成堆,已经有稍见成熟的初中生等在这里了,书桌后面站着和蔼可亲的校长。
校长写了新书,《管理学生的一百零二条建议》,身后是硕大的红色横幅,“一校之长爱生如子,情系教育又作新书”。跟前小学生排了四条队伍。我跟我旁边的大姐说,给小学生建议不是应该老师买来读的?大姐肥头圆脸,冷漠地白了我一眼,并不搭腔。
这个大姐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大姐。
高中时候我还给一家灵异小说刊物供过稿子,一月印三期,稿费一期一结算。如果手机的娱乐功能再少一点,我想这家灵异刊物不会这么早倒闭。印象最深的是一直在开视频谩骂我的东北大姐。大姐对我要求很苛刻,其实也不怨大姐,他们的杂志发稿子没什么逻辑,只要出现一只很吓人的鬼,题材不触及军、警、政、婚姻,就可以发表。
我写稿子讲究,凡事探讨个因果,她极不喜欢因果,每次看见我写因果都要毙,从她那里领到稿费我都诅咒一次他们杂志。
公交车慢悠悠碾压过减速带,脱离了校门口“减速慢行”的路牌,四条队伍慢悠悠消失在车子后面的玻璃窗。岛城的文化风气好,每一个站点,都有在呼啸的北风中摆报摊的男女。只是等车的乘客很少光顾。大姐跟我说话是在市政府这一站,当时车上拥挤,车门开着。站牌下面摆着几把塑料凳子,供乘客坐。大姐已经从不同乘客手里要到了钱,当然钱不是大姐私吞,用她的话说,是在募集冬天的正能量。让小小的爱心涟漪,在居民和游客中扩散。大姐指给我看站牌处的爱心凳子。我说我没有钱,惹得大姐不快。用大姐的话说不是找我要钱,是找我要爱心,给市民添置一份陌生的温暖。在大姐的带动下,好事的人七嘴八舌议论起了我,我冲着他们骂了一句。站点的报摊,忽而整沓报纸从压住的石头下飞了出去。摊主袖着手从马路牙子上站起来,用脚踩住风中舞蹈的报纸。
迟到了近一个小时,老远看见李桢点上了一支烟,吸了几口,烟在大风中自己灭了。他刚烫了头发,边吸烟边用手捋着头发别提多洋气,我下意识压了压自己的一头枯草,急着蹭他的烟抽,车没停稳我差点出溜下去。
我们是在省级刊物办的九零后文学笔会上认识的,聚餐时他喝多了,几天的采风他都苦着一张脸。原本也不会熟,虽然都在岛城,可是这之前从未见过。直到最后一天下午,几个德高望重的文学评委给我们开会,批评了我们年幼、低龄的作品,问我们还有什么说的吗。李桢苦着脸挠挠头皮说,肚子餓了,开饭吧。
我坐在李桢对面,大笑着从椅子上出溜了下去。几个老师脸上有些挂不住,倒不全是因为李桢,也因为我,他们相互瞅了会儿,也就散了会。
回到岛城我和李桢几乎每两个周来往一次。他虽还在上大学,可是比我混得要好。经济来源一方面依靠家长,另一方面李桢写小说,也写剧本。他写小说是拿稿费的,写剧本只是帮忙,帮系主任的忙,帮北漂朋友的忙,帮几个自创刊物的老作家的忙。
我和李桢抽完了烟又上了公交车,去大集附近的独立书店见老狼。时间是上午十点半,比较尴尬的点。路上和李桢谈起了最近读的书,李桢说中断阅读了,最近只看电影。问及看什么电影,李桢说,昨晚还在看北野武的《座头市》。我说这个片子我知道,讲的是日本的盲侠。
我说我羡慕盲人,李桢问我,看不见有什么好。我说看不见才更专一。我脑子里回荡着早晨给我按摩的盲人形象,自从全职写作,我的注意力并不集中。到了临近的站牌已经十一点钟,李桢说,下个周要去内蒙古拍一部故事片,申请到经费了。我也想跟着去,但是我没钱。上次见面李桢请我吃的饭,在一家萧索、破败的烧烤店,我们点了四条烤鱼,一盘烤肠,二十根羊肉串,两瓶啤酒。想吃个腰子补补身子,发现除了我们点的这几样,其余一概没有。我举着脖子灌酒时,一只硕大的老鼠从我桌面一跃而过,吓得李桢一口酒喷到了我身上。
上次他请我,这次理该我请他。我在书店附近的银行取了卡里所有钱。不到二百。钱是我女朋友离开我的时候留下的。留的是现金,我又排了半天队存进银行的。现在取钱,银行里坐满了退休后的老头老太太。独立书店旁边有个大集,老头老太太赶集,取的是现钱。要花十块钱,取二十。赶集回来,把剩下的再存回去。
他们有时间,又有耐心,而我只有时间。把钱取出来的那一刹那我哭了。身后的大妈吓坏了,还上来摸摸我的头。我紧握着手里的钱啜泣着说,大妈,我没事。
我哭是因为我差一点过上憧憬已久的诗意的生活,真的是差一点。我女朋友给我买了一台德国产的咖啡机。我理想的生活就是每个早晨眯着睡眼给自己冲一杯咖啡,吞一杯咖啡再醒过来。
咖啡机来时是个清晨,阳光踩在厚厚的窗帘上,室内天昏地暗。女朋友下了夜班推门才带进来一束光,她怀抱着一只小花猫。
“你买的吗?”我赤身裸体把咖啡机摆到厨房,从已经断了电的冰箱里拿冻鱼。
“不是买的难不成路上捡的。”
“不是咖啡机,我说猫。”
“路上捡的。”
我把鱼的内脏掏出来,给猫吃。
女朋友皱着眉躲开我,“好恶心,不给它吃。”
我最后煎了鱼尾巴给猫,小花猫低着头吃的时候我跟女朋友说,我们不适合养猫。
“先不养,过一阵子,我买只好的给你。”
“不。”
“没东西喂它。”
“那我去买。”
不怕人笑话,我在家写作,钱都是花女朋友的。当然我自己偶尔有了钱也不吝啬,也带女朋友上街吃喝。我刷信用卡给女朋友买过一件一万多的皮草。这也导致了我严重怀疑自己有病。不管手里有多少钱,我都要短时间内花出去。不然我没办法集中精力写作。
女朋友上班之后我抱着猫站到阳台,一边佯装往楼下扔猫一边说,“你敢再来,我就从这里扔你下去。”小花猫喵喵叫个不停。我把它放到楼下草坪上,摸了它好长时间,松手后它没回头看我,走了。
女朋友只给我买了咖啡机,并没有买咖啡豆。
我看着手里仅有的一百七十块钱说,“我把猫送走,我就知道,咖啡豆她永远都不会再给我买了。”
但是这些话我没办法跟大妈说,我不知道说的顺序是,先说自己有病,还是先说女朋友给我买了咖啡机,没买咖啡豆。
我擦干净眼泪和李桢并肩出了银行大厅,李桢也问我哭啥。
“我哭我理想的生活。”
“理想的生活就是作协把我们养起来。”李桢在一家烧烤店门前停步。
“我不指望哪个机构养我,我希望能有自己的读者。”
“没人看文学书。”
大概我脸色很难看,李桢忙说,时代的大钟来回摆,有一天人们会回来的。
“我们能赶上那天吗?”
“你一直写下去,说不准。”
我点了几样烤肉,要了啤酒。点菜时也是好面子,往多了点。李桢一个劲阻拦我说,犯不上犯不上,等咱们挣了大钱再好好吃一顿。
我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挣到大钱,以及挣到大钱之后干嘛,禁不住悲从中来。我和女朋友就是吃烤肉认识的。我坐在她旁边,她低着头刷微博,我在思考我是不是有病。烤肉上来了,她刷着微博一串串吃了起来。啤酒上来了,她跟服务员说我不喝酒。服务员说这些是你旁边的先生的。
她的嘴张成了圆形,我以为她要说抱歉,谁知道她问我是不是有病,吃你的烤肉也不说。我带着哭腔说我就是有病啊。本来不确定,你一说,我真觉得我有病了。逗得她哈哈大笑。
我们去领证的那天,我给她买了一万多的皮草,她挎着我的胳膊也是这样哈哈大笑。当我发现带的钱不够领证时,她抽出手,扇了我一耳光。
“你根本不想领证。”
“我以为你带着钱呢。”
女朋友的原则是无条件给我花钱,但是领证的钱必须我出。
“我哪知道你的原则这么奇怪。”
“我就是干这个的,你早知道。”
“不是因为这些,我带的钱不够。”
“那你来干嘛的?”
她又要抽我,我躲开说,注意点影响,人家以为咱俩诈婚呢。
她瞅着工作人员说,那明天我们再过来。
服务员过来问我们要冰冻的还是常温的,我说你傻吗,这个季节喝什么冰冻的。服务员气冲冲从门口的白菜堆里抽了两瓶埋在积雪里的常温啤酒,我忙制止了她,跟她要冰冻啤酒。
等菜時我连了店里的网刷微博,发现老狼的签售会需要提前订座位,问李桢现在订座位还来得及吗。李桢说来得及。
李桢笑着问我,除了咱俩,谁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