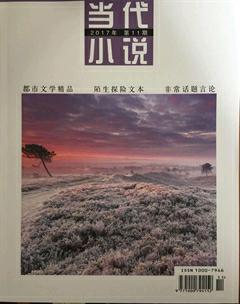弑父(短篇小说)
田友国
1
有一个女人的子宫很贫穷。没有男人来播种,当然穷。刘玉玉有丈夫,可她丈夫汪表表干那事不行,一直没用刘玉玉。刘玉玉是一堆干柴,要汪表表点燃。汪表表的火是熄的。这样维持了七八年。七八年来,汪表表都是把自己的眼光压在刘玉玉白花花的大腿上,对刘玉玉重复着这样一句话:“没有孩子咱们也要过下去。”刘玉玉叹息一声,把她的目光浸泡在汪表表的泪水深处。汪表表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一副可怜的苦相。刘玉玉把大腿动弹了一下,又动弹了一下,迷茫地对夜说:“睡觉吧睡觉吧。”汪表表就很自觉地睡到了刘玉玉的脚那头。七八年的汪表表都这个样式。
后来,刘玉玉怀了身孕,那是偷来的。子宫穷慌了,穷急了,不这样不行。刘玉玉舔了舔火焰般的嘴唇,说,他像一只老虎。夏句句说,他要是想偷工减料的话,就对不起她了。还接着说,她就不会呻吟了。就这么一回,刘玉玉有了。
刘玉玉把自己身体上发生的情况告诉给夏句句。夏句句坐在汉水河边的晴月里,听后,很不正经,说他射击得真准。刘玉玉没有他那样的闲情逸致,急急地问:“怎么办?”这一问,夏句句才知道了问题的严重。
刘玉玉的肚子看来是掩蔽不住了,越来越大。她不想瞒汪表表,要瞒也瞒不了。这不比其它的事。汪表表也不是傻瓜,大腿根的那条命根子不来事,但老婆的肚子大起来了,也还是可以看出她怀孕的迹象的。他没声张。汪表表心想,老婆把裤腰带勒得再紧,那是给外人看的。像江汉平原,看上去是一块平地,可土地肥沃。而且,地下的石油矿藏丰富。汪表表与她困在一张床上,手一摸索,就明白刘玉玉被人开采过了。汪表表一直没挺进“江汉平原”。他对自己的历史黯然伤神。
荒了一个女人。
刘玉玉说:“表表,你摸我的肚子干啥嘛。”汪表表就啥也不说,还是拿手去摸她的肚子,暖和了一个冬季。刘玉玉猜想,汪表表会打她,并把她的耳朵拧下来,搬到另一个地方,至少也会骂她的娘。她并不了解汪表表。汪表表没有像她想象的那個样子,夜夜还是自觉地睡他的那一头。一切太平。这个世上不止他一个男人知道他的老婆有孕了,汪表表也没有去追究那个男人是谁。夏句句很长时间害怕汪表表来找他算账,总是躲藏在家中。后来没事,夏句句倒觉得自己多虑了,把汪表表的“阶级觉悟”低估了。刘玉玉说,表表是个难得的好人。夏句句就笑。刘玉玉骂了一声:“笑,笑,笑个屁!”
刘玉玉生下了一个男孩儿。她以为女人有了小孩,就是一大荣耀。她把头举得很高,她自己也不明白,生下婴儿把她的母体都撕裂了,却从心底有种自豪感:她是一个完整无缺的女人了。然而,正当她高兴时,汪表表对那个粉嘟嘟的男婴望了望,隔了一定的距离。他一直对这个男婴保持着这样的距离。后来,床上就多了一个人。刘玉玉说:“表表呀,给孩子取个名吧。”汪表表想了想,说:“就叫子富吧。”信口一说,却合了刘玉玉的意。刘玉玉点点头,认为这个名字不错,就对汪表表说:“到我这头来睡。”汪表表睡惯了刘玉玉的脚那头。
睡到半夜,汪表表一脚把汪子富铲下了床,汪子富像受了莫大的委屈,振奋声带大哭起来。刘玉玉从地上急忙地捡起汪子富,把奶子塞进子富的嘴里。夜空中就不止一种声音了,还有吮奶的声音。汪子富一下就安静了。
刘玉玉说:“表表呀,心里窝着火,也不能拿孩子出气嘛。”汪表表闷着头,睡。
窗外,有一双如船的大脚走去走来。夏句句听到子富的哭泣,心就裂了一个长长的口子,渗出了血。夏句句几次把手伸向了汪表表的大门,又缩回来了。这门不是他的。是汪表表的。可惜,汪表表用不上刘玉玉。
2
汪子富长大了。汪子富当然像夏句句。汪表表对汪子富不冷也不热。汪子富觉得自己受了侮辱,说汪表表像仇人一样对他。刘玉玉就说:“你爸就是这样的人,你要顺着他才对。”汪子富更不明白:夏句句为什么背了人对他亲切,总是摸他的屁股?刘玉玉说:“子富呀,听妈的话……”话没说完,泪却淌了下来。
3
汪子富当然跟汪表表一个姓。汪子富长大到七八岁的时候,村上的人就喜欢逗他。汪子富长得让人疼,小小年纪就露出了峥嵘:很帅气的样子。大概与他的母亲和夏句句的野合有关系。汪表表不服气还真不行,这狗日的杂交品种就是比真正的夫妻干出的东西漂亮。村子上的人说,子富呀,你长得太像你妈了。一般情况下,村子上的人会省略他的姓。都知道,他的姓有点“张冠李戴”的意味。别看村子上的人没多少文化,但说话还是讲含蓄美的。说子富长得像他妈,是给他,还有他的名誉爸爸,以及他的妈妈一点面子。好听。为什么不说子富长得像汪表表呢?这半截话没人说,但比挖他家的祖坟还要恶毒。其实,汪子富长得太像夏句句。夏句句躲在自家的堂屋里,短浅的目光沿了门缝向外跑,也就不那么短路了。夏句句听别人说说笑笑,就想起与刘玉玉那夜纠缠不清的气息。
汪子富问刘玉玉:“妈,我是谁生的?”刘玉玉稍稍地惊了一下,马上就恢复了常态。对这一个问题,刘玉玉在怀上子富的时候,她就开始考虑未来如何回答。所以,刘玉玉摸着子富的头,说:“当然是妈生的啰!”刘玉玉绕了一个弯。汪子富对她的回答并不满意,他的肚子里存放着一个重大的疑惑:与自己不相干的人对他那么疼,疼得让他犯糊涂,而自己的爸爸对他却横竖看不顺眼。
这朵开在天边的云压在他的头上。汪子富一边问他的母亲,一边长大。到了十二三岁,汪子富在一个雨季的长夜,把夏句句堵在了村东头的河边。河边有一座小茅屋。小茅屋的面前有很多的鱼在河水中弄得响。夏句句见了人影在雨的夜里一路滑过来,以为有人来偷地下网。这季节,正逢春,鱼们就像城市的男男女女跳那种搂得喘不过气来的舞。而且,鱼也在搞妻妾成群。一网下去,不得了!所以,夏句句的眼睛警卫着鱼池。
可迎面来的是汪子富。夏句句一把抱住汪子富,亲了几口,说了一句:“想死老子了!”这话不着边际。夏句句把汪子富拉进小茅屋。雨水还在头发上滚动。一条狗从床底下悠扬地爬出来,把汪子富的背脊吓了一大串的冷汗。夏句句说:“子富,别怕别怕,它不会伤害你的。”狗就紧挨在汪子富的脚跟前,匍匐出很安静的姿态。
汪子富突然说:“你就是我的亲爸爸!”这句话,汪子富酝酿了几年,也反反复复地判断了几年。终于,他豹着胆喊了出来。夏句句既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他想从汪子富的眼睛里把自己搬出来,便掏出一支烟。空气发潮,手也有点打颤,但还是很艰难地点燃了。点燃后,就不说什么。汪子富很生气,质问夏句句:“你聋了还是哑了?”夏句句叹息了一声:“子富呀,不该你知道的你都知道了。还要我说什么?”
那个雨季说结束的,可仍然没有一个完。房子里生了霉,几条蚯蚓爬在刘玉玉的眼睛里。汪子富沉闷了几天,想从母亲的口里得到证实。他一直在寻找机会,与母亲面对面地说说。可是,刘玉玉却一直在回避儿子。那天,汪表表正好不在家,他是亲眼看着汪表表端了一杯茶,出去了。汪表表逢雨的时候,就泡那种叶子很阔的茶,嘶了嗓,咳几声,去看别人抹牌。刘玉玉更是知道他的这个习惯。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她的肚子里才有了汪子富的。当时,汪表表是在喝茶还是在咳嗽?刘玉玉想象不到,反正她在這个时候的那段事与他没有关联。
汪子富向母亲走过来。刘玉玉正要从他的目光中撤离,汪子富叫了一声:“妈。”刘玉玉觉得儿子的眼睛长大了,可以透视她的心。她有点怕儿子的一双眼睛。汪子富说:“妈,你别走。”刘玉玉尽力把自己的心调整到平静状态。汪子富和母亲互相看了一下,都转眼瞄别的地方。沉闷了好久,汪子富说:“我不是我爸爸生的。”刘玉玉装着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怎么会呢?”汪子富说:“我是另一个男人生的。”看来再瞒儿子是瞒不了了。在瞒儿子的长时间里,她的心就像腌在腌菜缸里。刘玉玉沉重地背负着时光。当儿子把这事亲口说出来后,她反而有了那么一点轻松感。刘玉玉说:“我想你会有一天知道你的身世的,但我没有想到你知道得这么早。子富,你长大了。”
汪子富没有任何反应,木在那里。屋檐下的雨水散发出一股隔夜的菜味。刘玉玉说:“真是有鬼,怎么和他呢?其实,说句真心话,你爸是好男人。我怎么就背叛了一个好男人呢?”刘玉玉好像有点自责。汪子富说:“你不承认多好。我想你会不承认的。你给了我一个意外。”刘玉玉说:“何必欺骗你呢!”汪子富说:“爸爸他知道么?”刘玉玉说:“他早就晓得。你爸活得比谁都要痛苦。但他可以忍受。”
汪表表回来了。汪表表把一杯茶喝光了。回来续水。汪子富说:“爸爸,能坐一下么?”汪表表听了一声“爸爸”,脚窝里也暖和。汪子富说:“今晚,我陪你睡。”汪表表说:“那你妈呢?我一直在陪你妈睡。不然,她会冷得睡不着的。你妈下半夜脚才会热。多少年了,我知道。”汪子富就不再勉强。汪子富说:“妈,你和爸去睡吧。”
刘玉玉和汪表表进了房。刘玉玉把房门关出一声响,轻柔,像树枝摇晃着身体再去擦月色。那一声响从新婚之夜的遥远心跳里重续过来。汪表表说:“关不关门没多大意思。”刘玉玉说:“表表呀,今夜你就睡我这头。”汪表表说:“这多年了,我习惯给你暖脚。”刘玉玉把灯拉熄了,睡到了汪表表的那头。汪表表说:“子富都知道了。”刘玉玉说:“他什么都知道了。”汪表表说:“这样就省心了。我一直怕他知道。他的眼睛真毒!”刘玉玉说:“这下我才把自己彻底清算了。”汪表表说:“你没有。你还欠我的。”刘玉玉说:“那是那是。总有那么一天,我会还清的。”汪表表说:“算了,眼睛里流什么尿!”刘玉玉就越发抽泣了。
4
汪子富不想再在这个地方呆下去。他要逃避这个地方。他做了一系列的准备,把一张发黄的地图翻烂了。汪子富想到新疆,那里有大草原,有骏马,也有美丽的姑娘。当然,他也想到南方。南方有钱可以赚,南方的姑娘把胸挺得老高老高,暗示着她的想法。这些信息是他在上茅厕时从一张报纸上获取的。原准备用这张报纸为这次大便画上句号的。那一刻,舍不得了。
可是,正要走的时候,发生了意外。
汪子富觉得,他的爸爸仍然是汪表表。原计划明天就悄悄离开的。刘玉玉和汪表表都没有发现任何动静,都认为他还是一个小孩。所以,汪表表像以前一样,泡了满满的一杯茶,又去看别人打麻将。汪表表不会玩,可看别人玩却上劲。汪子富望了望渐行渐远的那个背景,默了又默。汪子富想,自己的爸爸长得像一头牛,看上去真壮。可就是活得窝囊。他同时认为自己来到这个世上有点不明不白。所以,看样子,汪表表是不会走出他的眼睛的。只有他走出汪表表的目光了。
汪子富到了母亲的房子。他没有一点离别的样子。刘玉玉说:“去睡吧。”汪子富随即就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说:“马上就去睡。的确也困了。”也的确没有什么异样。汪子富说:“妈,你的背上有一只蚊子。”刘玉玉说:“妈的皮厚,蚊子咬不进去。”汪子富一巴掌,拍死了那只蚊子。刘玉玉说:“去,把手洗了去睡。”汪子富就给妈熄了灯。
刚刚睡下,屋外就有一阵脚步声,紊乱了还没来得及合眼的夜。汪表表被人抬了回来。门是刘玉玉打开的。一打开,惊了。说是汪表表被毒蛇亲了一猛口。刘玉玉朗声大哭。汪子富知道了,磕头请大家把他的爸爸送到医院。浩浩荡荡的脚步就走向深夜。说汪表表呆在家里就没有这次大灾了。说汪表表哪能在家里呆得下去。说汪表表心里烦着呢,少说几句行不行!汪表表的脸苍白,失血太多了。汪表表对任何人没有侵略的样子,可就是把自己送进了蛇的口里。真有点狼狈。
医院的灯光泛出纸币的颜色。汪表表疼痛得大叫。但医院把汪表表平静地摆在病床上,说是要见了钱才治疗。刘玉玉跪下了,说救死扶伤等于积德。医院临危不乱。见医院没有动静,汪表表在病床上发出一声声穿透骨头的疼痛,刘玉玉没有办法了,转身去找大队长。汪表表说:“你不要离开我,也不要去找他。”刘玉玉把手从丈夫的手中挣脱出来,扯了个由头,说是去找村子里的人借钱。
大队长夏句句有钱。夏句句把鱼塘霸了。霸得很有理:他是大队长,他不霸谁霸?村民也习惯了,觉得他是天经地义的。其他人去占鱼塘反而不符合情理。刘玉玉不想借他私人的钱,大队长掌握着全队的财经大权,可以签批借条。也可以大笔一挥,把借条上写得一清二楚的钱抹掉。你一年到头干死干活,值多少钱?夏句句说给你抹掉就抹掉,一点痕也不会有。谁都服他手里的那管笔。
刘玉玉找夏句句的路很泥泞,也很滑。她是抄近路走的。她要节省时间。近路像河里的泥鳅。黑灯瞎火的,摔了好多跤。她想她摔跤比汪表表要好受多了。于是,她爬起来,再走。眼睛遥遥地望向夏句句的方向。
夏句句在那茅棚里。他几年前就丧了妻,一直没续弦。很多女人想把自己嫁给他,他也知道自己对女人来说是一座大山。可他不想娶,娶了麻烦,会把他套住。与别的女人再干那事,碍手碍脚。他要感受更多女人的滋味。女人也盼望把自己给他,进了他的被窝,把肚子伸向他,就像傍到了一棵大树。但过细一想,又有点怯,怕他“克”了自己。那回,刘玉玉没这多顾虑,可能是荒得太久了,就进了那个茅棚。夏句句也就深入到了她的夜里,隔了半夜,她才从他那里把自己搬出来。
对刘玉玉的到来,夏句句并不吃惊。他淡淡地说:“来了。”刘玉玉的目光在跳动的灯火中淌出泪水,说:“找你借钱。”夏句句以为,她要递交一个夜,但不是。他多么失望。他冷了一句:“我不能开这个口子。我手中有多少户人家,开了口子,岂不摆不平了?每家各有各的难处。”刘玉玉说:“你已经把我的口子开了。那时,我还是一个处女。如果你给我钱,我再给你。”夏句句说:“你去叫儿子来。”刘玉玉把衣服脱了,说:“时间不能再等了,表表的生命还要钱来救呢。”夏句句说:“你去,叫儿子来。”刘玉玉打了一个很响的喷嚏。
5
汪子富来了。汪子富没给夏句句好脸色看,硬了一句:“你到底给不给钱?我爸等着钱救命。”夏句句说:“我是你爸。你要叫我爸爸,我才给钱。”汪子富说:“我肯定不会叫你,但我非要你给钱。”口气像一堵墙。于是夏句句软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夏句句心想,一个大队那多人,就汪子富能治他。夏句句说:“你什么时候喊我一声爸?”见子富把脸又垮下来了,连忙说:“好好好,我这就给你签。”夏句句的名字值钱,签了,说:“你去找大队会计。”汪子富白了一眼夏句句。沿了河边,去敲大队会计的那两扇门。
钱到医院的时候,已是第二天的八九点钟。汪表表最后没喊“疼”了,可能是没气力了,也可能是疼到这时已经麻木了。等汪子富把钱送到医院,气喘吁吁的他听到了一个可怕的消息:他爸爸汪表表的腿保不住了。钱迟到了。汪表表的右腿被锯了。刘玉玉就伏在汪表表的脚前号啕大哭起来:“当初嫁给你时,你曾对我承诺过,会让我一生过上好日子的。你怎么就不守信了呢?表表呀,为什么老天不让我去替你承受灾难呀!”
汪子富没哭泣,愣了一会儿,打死他他也不会相信爸爸的右腿就这样废了。爸爸的右腿真的没了,汪子富的眼睛突然辣了,像长出了蛇信子。就是那个姓夏的迟迟不给钱,才耽搁了爸爸的治疗。汪子富从医院跑到夏句句的鱼塘边,本来是要找他算账的,可夏句句不在,气没地方出。夏句句喜欢喝冷茶,小茅屋里放了一个很大的茶壶。汪子富眼睛突然一亮,揭开壶盖子,从胯裆里掏出那玩艺儿,对准茶壶,尿了长长的一泡。他想:尿和茶的颜色相同,让姓夏的喝吧。
过了一会儿,夏句句回来了。舌干口渴的,他便端起那个大茶壶,仰了脖,喝起了茶。解了渴,舌尖伸出来,舔了舔嘴唇,才发觉不对,茶里有尿,“誰尿到了老子的茶壶里?”便用眼睛四处搜索。汪子富躲在一棵树下,捂着嘴笑。没笑出声,但很解恨。
汪子富回到家中,刘玉玉正挨着长吁短叹的汪表表,说:“以后怎么过下去呀?”
汪表表说:“你嫁给那个姓夏的吧。”汪表表的眼睛里有两滴清泪在滚滚下流。刘玉玉说:“我并没有这个意思呀。你犯什么傻?”汪表表说:“我早就晓得了。”泪水就开始了汹涌,泪水酿了好多年了,像苦大仇深的样子。刘玉玉想,这日子只有依靠夏句句才能过下去了,但她下不了狠心搁下汪表表不管,再说,村子上的人长了舌头,什么话就由别人去说了。她想村子上的人吃腌菜萝卜,除了下饭充饥,还诱发了好多好久的口水。她怕口水把自己淹死。刘玉玉思前想后,觉得不能丢下汪表表嫁给夏句句。汪表表说:“我是一个包袱,背过去会压弯你的腰。”
刘玉玉找到夏句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刘玉玉长得可心,她坐在鱼塘边的傍晚里,把夏句句的目光全占去了。夏句句说,他想娶她的念头已很长了,早就巴不得呢。刘玉玉说,以后有两件事要答应她。夏句句猴急了,手就伸进了刘玉玉的丰臀上。刘玉玉说:“第一,你要对表表好,不能把气给表表怄。第二,从今往后,你不能再去引蝶招蜂。”夏句句满口应承下来,说:“听你的,听你的。”刘玉玉没有理会夏句句的调情,她要把这事与儿子商量一下。儿子已经二十岁了。她很在乎儿子的反应。
妈妈做这样的选择,也是不得已了。但他对这样的家庭格局,想象得很可怕。如果妈妈来问他,他肯定会一口否了。汪子富最看不得夏句句,一看见,就眼睛充血。还有,自己那可怜的爸爸,怎么能和夏句句在一个屋檐下吃一口锅的饭!那是要爸爸的命呀!
怪就怪那个姓夏的。汪子富想阻止妈妈嫁给姓夏的,就得把姓夏的杀了。他知道,自己的身上流着夏句句的血,生命是夏句句给的。正因为这样,他身上的血很脏。这需要与夏句句了断。也好让妈妈与夏句句有一个了断。
到了深夜,汪子富怀里藏了一把菜刀,往那个鱼塘边跑去。夏句句已睡了,还打着如雷的鼾声。正是下手的时候。汪子富猫一样地靠近小茅屋,轻推门,仄了身,闪了进去。夏句句的脸看不清,但鼾声响。于是,他循着鼾声,贴近床边。手颤抖地摸到了那把菜刀,便一下抽出来,砍下去。偏了,没砍到夏句句的头,只剁了夏句句左手的一根手指头。此时,狗惊醒了,一声狂叫。夏句句早已翻身下来,“谁?”一把抓住了汪子富。汪子富没有急忙逃跑,愣在那里。夏句句还没看清是谁,提起床边的一根木棍,一出手就把汪子富扫倒在地上了……
汪子富没吭一声,也没走,躲在地上。凑近了,夏句句才看清是汪子富,大惑不解:“怎么是你?我是你爸,你杀亲爸?”汪子富说:“我杀的就是你!”夏句句问:“为什么?”汪子富答:“你清楚。”
“杀人是要抵命的。”
“我巴不得。”
“我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杀的。”
“你等着,总有这一天的。”
夏句句开始寻找那枚断指。摸索了一会儿,不知断指的下落。汪子富眼尖手快,一下就发现了地上血淋淋的手指,马上捡到了自己手里。夏句句要汪子富给他,汪子富就是不给,“我要带回家给我爸,让他高兴高兴。”夏句句说:“狗日的,汪表表用什么把你喂大的?”便去抢。俩人你争我夺,扭在一起。汪子富怕斗不过他,急了,生出一智,连忙说“我给我给”,等夏句句停止了争夺,汪子富飞身把那枚断指投进了鱼塘。夜,水面轻起一圈涟漪。
6
夏句句断了一根手指。他想去想来就是想不通:创造了一条生命,却让亲子把自己的手指砍断了。换了别人,他是不会就此罢了的。他是谁?堂堂的人。他不是没有考虑把汪子富告了。那条线他有很多的熟人,可让自己的儿子坐几年牢,心那个地方就有点堵塞。所以,他叫汪子富滚,滚得远远的,滚得让他忘了这件事。
汪子富说:“我可以滚,也滚不到哪里去。”夏句句说:“我是看你是我的儿子,我才放你一马的。”汪子富不服气,呛了一句:“那你把我送到派出所嘛。你没这个胆。我有的是胆,我要杀你。”
事态的发展,汪表表最揪心。弄下去,让夏句句怒了,汪子富坐几年的牢,就是夏句句一句话了。汪表表把儿子叫到身边,也马了脸,要他滚,越远越好。汪子富说:“那个姓夏的也是这句话,你也是这句话?”汪表表说:“你也替我想一个办法,如何解决这事。”汪子富说:“你是我爸,我滚。我也是一个男人了,你就咽得下这口气?”汪表表说:“儿子,活着出去,活着回来呀。”见状,顿了顿,汪子富退了一步,表示“滚”。
这事就这样平息了。
夏句句来接刘玉玉和汪表表。汪表表还睡在床上,把背给夏句句看。刘玉玉劝他,一起去吧,也好有个照料。汪表表说:“我不去,你去,我死不了的。”刘玉玉说:“你不去,我就不去了,一直陪同你过下去。”夏句句也走近他,劝他跟玉玉一起去,说:“你要是不去,谁会放心呢?”刘玉玉看汪表表没反应,就叫夏句句回去,别烦表表了。夏句句说:“表表,你不去,我也不要玉玉了,留给你,让她跟你过。”汪表表忽然翻了一个身,说:“你要对玉玉好。”于是,夏句句一把抱起汪表表,就朝自家走。刘玉玉跟在后面,一条狗跟在刘玉玉的后面。那狗是夏句句的狗。
7
汪子富进了城,他的运气好,遇到了一个好人。那天,他在一家酒店门前晃来晃去,一双眼睛到处看,像贼。好就好在这时有一辆小车刚停泊到他的脚跟前。从车上下来一个香女,迷了汪子富。他搞不明白,这女人的身上怎么香得这样,淡淡的,却往骨肉里跑。香女是这家酒店的老板,叫丁玉莲。丁玉莲收留了他,安排他去帮厨。
汪子富长得人高马大,夏天在厨房里做事,热,汗湿了,骨骼就从衣衫里凸了出来。丁玉莲见了,呼吸一停一顿的。丁玉莲就把他安排到大厅当保安。这活轻,用不了体力。从农村来,哪受到过这种厚待!汪子富就一声一个“姐”,喊得丁玉莲的心起了涟漪。丁玉莲很喜欢,把他带到自己的家里。丁玉莲的家在丁香花园,复式结构。汪子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房子,两颊生出许多的新奇。丁玉莲带他在房子里转,最后就转到了她的卧室。卧室的情调让汪子富联想到很多事,问丁玉莲:“你老公呢?”丁玉莲往口里丢了一枚口香糖,漫不经心地说:“早离了,他在别的女人肚子上。”汪子富不便多嘴,就坐到一只沙发里。丁玉莲在床边也坐下来,用发潮的目光去浸湿汪子富。汪子富经不起这样的目光,也拿眼去盯她薄薄的圆领衫内的两座山峰。丁玉莲幽幽地说:“坐过来。”那口吻既有哀求又有命令,而且如丝的细。汪子富知道他听了她的这句话后,就会再也走不出丁玉莲的眼睛。丁玉莲仍然坐着,可目光却在幽怨地牵引着汪子富。她问:“卧室是干什么的?”并把两瓣唇递向汪子富。汪子富就知道她要什么了。
事情进行得淋漓尽致。完了,丁玉莲给了一沓钱。汪子富没敢接,也不想接。丁玉莲说:“拿着,你的家里人很需要钱。”汪子富说:“是的,你说对了,可我不能这样赚钱。”一脸的认真。丁玉莲怕再伤害他,说:“那就算是我给你加的薪。”汪子富忽然间产生了一个计划,很宏伟,说:“我要娶你。”丁玉莲说:“别犯傻了,我大你七八岁。又结过婚的。”汪子富说:“你在找托词,我配不上你?”丁玉莲说:“见到你的第一天,我就喜欢上了你。但你家的人会不会同意?”
汪子富给妈妈去了信,说了这事。但他没说丁玉莲是二婚,他必须这样做。不然,妈妈是不会让他娶“二锅头”的。妈妈以为他还是过去的他。他不是他了。汪子富还说,没多久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了。
说到结婚,汪子富比丁玉莲还要急。丁玉莲说:“我曾被男人甩过,你可别把我再抛弃了。”说这话时,丁玉莲一点也不像老板,脆弱,倒像一个爱情的乞求者。汪子富想起刚来到城里的样子,也是这般的姿态。于是,他说他永远不会。丁玉莲还是有点疑,说咱们同居一段时间再说。汪子富搞不懂,城里的男女可以这样过。但也只好依她。在那张床上睡了几夜,汪子富才终于理解了自己的妈妈。所以从内心里默认了家庭的奇怪现象。妈妈在无性的婚姻里度过了那么长的日子,也亏了她。
8
听妈妈在电话中说,爸爸病了,病得不轻,是那种要人性命的病。汪子富问是谁病了。刘玉玉說:“是你爸。”汪子富明白,是汪表表病了。汪子富说,他攒了钱,可以给爸治病,还可以把妈赎回来。妈妈说:“你爸都快没了,还说什么赎不赎的。本来就是我自愿的。”汪子富看在妈妈的份上,给家里寄了钱。钱是丁玉莲给他的,丁玉莲说:“你回家吧。”汪子富说:“我要留在这陪你。”一下就感动了丁玉莲。她给汪子富追加了两千块钱。
后来,妈妈在电话里要他一定回去,说爸爸没多少日子了。妈妈的哭泣隔山隔水地流过来,动了汪子富的心。他说他马上就回去。汪子富收了线,转过身找到丁玉莲,说家中有事,要回去一趟。丁玉莲见他一脸的忧郁,问他家发生了什么。汪子富说:“你不是要嫁给我嘛,跟我回家,一切就依你的。”
汪表表躺在病床上,还有一口气在细细地悠,两眼沉沉地锁着。似乎感应到了儿子的脚步向他响过来,汪表表把眼睛睁开了,见儿子真的进来了,笑了一下,空虚地说:“儿子,叫我一声爸爸……”汪子富舔了一下舌头,“爸爸”的叫声却始终在口中打转,可就是没喊出口。妈妈在一旁,催促道:“快叫他,快喊他,不然就没时间了。”汪子富这才喊出了口:“爸爸……”听了,汪表表突然灿烂一笑,只一瞬,就断气了。
汪表表出殡的那天,空气潮乎乎的,弥漫着一股悲痛的雾。有一辆小车为他送葬,也算是排场了,汪表表没有想到,儿子会带小车给自己送葬。他不明白,儿子在城里干什么,混得这般阔气。村子上的人怎么也没想到,汪表表的死会让汪子富这么悲痛欲绝。
夏句句说,他要去送汪表表一程。汪子富双眼迷茫,说你用不着这个样子。夏句句坚持要去。汪子富奈何不了,就把他塞进了小车。夏句句说:“他真的死了吗?是真的吗?”没有人应他,都不知道他此时的肚子里藏了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刘玉玉的脸上像一张白纸,看不出她在想什么,也许什么也没想,也许什么都不值得她去想了。
9
汪子富对丁玉莲说:“再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同居了。咱们结婚。”丁玉莲想,有这样的心态,或者说这句话,应是她说才合适。从汪子富的口中说出来,她认为滑稽,顿时又觉得汪子富的可爱。汪子富诚恳地把自己放进丁玉莲的目光里,等着她说话。丁玉莲吻了吻他,说:“你的话把我的心给暖了。”其实,她也着急了,肚子里有了汪子富的种,她还怕他从自己的身边跑了。这是她第一次怀孕。
丁玉莲的肚子越来越鼓,一天一个样,汪子富乐得直亲她的肚子,听胎声。丁玉莲说:“别别别,弄不得了。”汪子富说,他又没想干她,看把她吓得像只小兔。丁玉莲就幸福了一脸,说:“酒店的事就给你去打理了。”汪子富抓到了时机,说:“你放心,我会干好的。但一定要把我妈接来。”丁玉莲说:“男人像你这样细心体贴,不多。你是珍稀动物。”汪子富学会了讨丁玉莲欢心,把胸贡献出来,让丁玉莲的头躺进去。汪子富顺水推舟地说:“还有我爸。”丁玉莲疑惑地说:“你爸不是走了么?怎么又出现了一个?”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汪子富也不想再骗她了,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你可要听下去呀——”
……
“这是真的么?”丁玉莲问。汪子富说:“一点不假。”丁玉莲说:“你妈是一位值得尊重的女人。但你不应该这样牵挂夏句句呀。”汪子富顿了一下,说:“再怎么说,他也是我的爸呀。”丁玉莲说:“我去接他们。”汪子富的脸上掠过一丝窃喜,内心酝酿着杀气。
丁玉莲随了汪子富回家的时候,夏句句正在和刘玉玉晒着太阳。刘玉玉说:“过得挺好的,哪里也不去了。太阳落下来,月亮会出来。”夏句句已不当官了,刘玉玉老了,他也老了,闲了,还真想到城里去看看。可一想到汪子富曾杀过自己,没杀死,至今还后怕。不过,老子哪有记儿子的仇的道理?当老子的就要不计儿子的前嫌。不然,就枉了老子的身份。汪子富容不得夏句句左思右想,端出臭脾气,说:“把你当爸爸,你就端架子了。”夏句句说:“给我一丝阳光,我就会灿烂的。搞惯了。我去还不行么?”
惟恐儿子和夏句句搞僵,刘玉玉叹息了一声,说:“去吧。”
一晃,丁玉莲就临盆了。刘玉玉和汪子富轮流到医院护理丁玉莲。正午的时候,丁玉莲产了一个男婴。汪子富喜得鼻涕眼泪一把甩,对丁玉莲说:“这小子姓汪吧?”丁玉莲弄不懂,感到奇怪,“你说什么呀?”汪子富说:“我……怕是野种……”丁玉莲觉得他在开玩笑,也笑了,“你应该知道他是不是野种。”
这天,汪子富回到家里,做了饭,叫夏句句吃。有孙子了,夏句句好高興。汪子富说:“爸爸,今天高兴,我陪你喝酒。”一听儿子叫自己“爸爸”,夏句句眉毛飞扬起来。知道夏句句爱酒,汪子富平时就给他备了酒,还泡了枸杞。汪子富在厨房里给夏句句倒酒的时候,又往杯子里放了早就备好的老鼠药。老鼠药和酒在体内此起彼伏,夏句句问:“这是什么酒?真厉害……”
终于杀了夏句句。汪子富咧着嘴,跑到街上,乐颠颠地高喊:“我杀了我爸……”
责任编辑:刘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