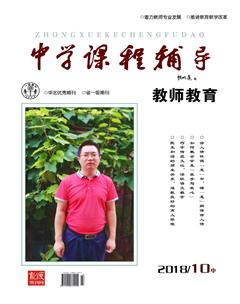都市人的乡村情
姚首仓
【摘要】 《祝福》以祥林嫂的悲惨一生为线索,把鲁镇上形形色色的民众串连起来。祥林嫂在鲁四老爷等富人们一片祝福声中寂然死去,她的死和鲁镇上的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祥林嫂人生悲剧之所以产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周围民众的冷漠、无情,甚至残忍。鲁四老爷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他迂腐、保守、顽固尊崇理学和孔孟之道,自觉维护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正因为他对祥林嫂的这种歧视,才彻底毁灭了她生存的信心。
【关键词】 祝福 边城 比较阅读
【中图分类号】 G6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992-7711(2018)10-015-010
就是位于和祥林嫂的同一阶层的人,也在一步步蚕食祥林嫂的生命。柳妈还算是同情祥林嫂的一个,可同情祥林嫂的人,也同样把祥林嫂推向深渊,更显示出悲剧之可悲。鲁镇上的人们对祥林嫂的遭遇没有任何同情,他们一开始只是用祥林嫂的悲剧满足一下自己的猎奇心理,等到厌倦了,便对之嘲笑唾弃,表现出一种冷漠厌烦的态度,这种态度,也增加了祥林嫂精神上的痛苦,他们和鲁四老爷一起,把祥林嫂逼上了死路。丁玲曾说过:“祥林嫂是非死不可,同情她的人和冷酷的人,自私的人,是一样把地往死地里赶,是一样使她增加痛苦。”作品中“我”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虽然“我”反感鲁四老爷,厌恶封建礼俗,同情祥林嫂,但又是软弱无能的,无力给她帮助。
中国人的奴性也是鲁迅先生所深深憎恶的。祥林境是个善良、朴实、纯厚的贫苦农村妇女,她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用自己诚实、勤恳的劳动,换取一种最起码的“人”的生活。然而,诚如鲁迅先生在杂文《灯下漫笔》中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民在历史上从来只有两种命运: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祥林嫂的一生,便始终在这两者之间浮沉。鲁迅先生深深地憎恶国民地奴性性格,真诚地期盼中国能有所革新,进入一个新时代,普通民众真正争取到做人的资格和权利。
《祝福》中人物大多或卑怯,或残忍。鲁迅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中,对国民性的卑怯是深恶痛绝的,他一再针砭在中国传统文化浸淫下国民性的卑怯。他说:“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该敢说、敢笑,敢哭,放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鲁迅先生对于卑怯者的恃强凌弱的残忍更为痛恨,他曾愤愤地指出: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祝福》中鲁迅先生描写的鲁镇人对祥林嫂悲剧故事的学舌、对祥林嫂额头伤疤的嘲笑,无疑是对卑怯者凌弱的针砭和揭示,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乡村社会卑怯者恃强凌弱的深恶痛绝。
沈从文先生也在营造自己的人性世界。通过《边城》他无限深情地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原始自然的风俗画。大自然的美令人陶醉,大自然养育出的子民更令人赞叹。生活在那里的是一群未曾被现代文明污染的善良人。
在这山水画一般的山城里,在如此纯朴的民风的孕育下,作者塑造了翠翠这一女主人公形象。湘西的清风、丽日给了她一个健壮的躯体;茶铜的青山、绿水给了她一双碧玉般清澈透明的眸子;碧溪咀的竹篁、白塔又给了她一颗决不世故的赤心;酉水、小船载满了她那少女的悠悠岁月。在爱情挫折中翠翠的性格因此展现着柔中有刚的美。而爷爷呢,则是“善”的化身。作者同样是把他放在“爱”与“美”的人性天国里来进行刻画的。老船夫的“善”,主要是通过对孙女翠翠的呵护、关爱充分体现出来。特意“放大”了去表现一位平凡老人充满人情美、伦理美的宽广浩大的胸襟,即是一个纯真、至善、完美的人性的生命个体。
虽然翠翠和傩送之间发生的是一场以悲剧结束的爱情故事,但这丝毫不影响沈从文先生对人性善与美的颂扬。他追求爱与美,是个热情的理想主义者。《边城》,是沈从文先生桃源重构时期的作品,在文中,他充满深情地唱出一曲生命的理想之歌。小说中,主人公对爱情的自由追求过程中,始终存在“走马路”与“走车路”,“渡船”与“碾坊”的对立冲突,即保留在湘西世界里的原始文化和封建文化,以人性为核心的原始价值观与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价值观的对立和冲突,这些冲突使主人公翠翠和傩送的爱情之路变得坎坎坷坷。主人公翠翠和傩送在追求自由爱情的过程中,他们漠视封建宗法制度和金钱势力,越过了现实的障碍,虽然他们的爱情最终以悲剧结束,但他们追求自由爱情的精神却在不断进步、不断超越。在这一过程中,从他们身上体现了边城原始自在状态下的人性的金子、人性的闪光点。
在边城,以金钱为本位的价值观凭借其物质优势向古老纯朴的人生价值观渗透,悄悄地改变着边城人本来的信守,在这两种文化价值观的冲撞过程中,原始自在状态下的人性受到考验和锤炼。翠翠和傩送面对两种价值观的选择,都忠于自己内心的真实感情,选择了一种属人的爱,人性的光辉得以弘扬。作者在表现边城人们人性善和美的同时,也深谙边城人们的人性具有的缺陷。
鲁迅先生的《祝福》在编织故事,描绘人物,抒发对故乡的无限怀念的同时,更多的是以觉醒着的现代知识者的眼光,去冷静地审视他们曾经生活其中得到乡村,描绘现实农村的衰败,封建宗法勢力的强大和农民在思想束缚、生活压迫下的愚昧麻木。而沈从文先生则流露出更多的温情和依恋。他用迷醉的歌喉,对那个“充满原始神秘的恐怖,交织着野蛮与优美,浪漫与严肃”的湘西社会的风情人物,深情地唱出一曲心灵的恋歌,表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的“理想情感”。显然,在沈从文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丝抹不掉的乡愁记忆,这使他一直不曾被城市文明完全同化,并最终在对故乡的记忆、幻想中获得某种精神上的满足和平衡,实现其独特的美学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