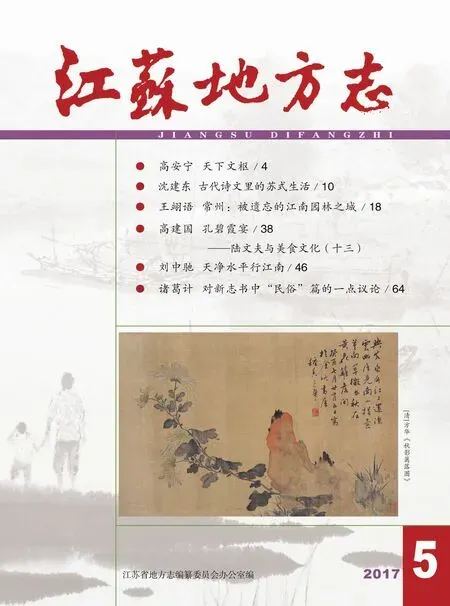鸳鸯蝴蝶派电影文献研究的新突破
——《江苏艺术家与早期中国电影文化产业发展研究》评介
◎ 曹燕宁
鸳鸯蝴蝶派电影文献研究的新突破
——《江苏艺术家与早期中国电影文化产业发展研究》评介
◎ 曹燕宁
电影史研究早就关注到鸳鸯蝴蝶派在早期中国电影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如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文化产业发展史》(电影出版社1980年版)、许道明和沙似鹏的《中国电影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等。20世纪末出版的上海通史系列研究也提及了鸳鸯蝴蝶派对电影的贡献,如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民国文化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苏州科技大学李斌副教授新著《江苏艺术家与早期中国电影文化产业发展研究》得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的2014年度艺术学后期资助学项目支持,批准号为14FYS003,2017年7月由高教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上世纪30年代前的报刊文献为“起搏器”,尝试着复苏早期中国电影影像的文字记忆。在作者的努力下,铺盖在早年中国电影身上的历史尘埃被吹散,艺术细节被点亮,显现出鸳鸯蝴蝶派电影的明丽景象,重构出早期中国电影史上鸳鸯蝴蝶派的新印象。
一、用历史新视角阐释了早期中国电影史上的“江苏力量”
早期中国电影史研究的薄弱之处在于区域研究的空白。存在着资料缺乏、结论泛化的问题。专门以“江苏”为主题的电影研究有待系统化。《江苏艺术家与早期中国电影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一书强调,江苏(以苏州为主)文学艺术是中国电影艺术的母源之一,揭示出了电影史上的“江苏力量”。通过对中国电影艺术的“江苏之源”的追溯,一张以浙江、上海、江苏为犄角的早期中国电影发展的“金三角”版图渐渐浮现,早期中国电影取得巨大成就的文化地理奥秘露出真容。
范伯群指出:“中国早期的电影工作者就觉得出路是在于和通俗作家合作,拍出符合市民兴趣的影片来,扩大受众面,降低经营风险,才不致使新生儿因断奶而饿死。”(《朱瘦菊论》,《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1期)他说的这批通俗作家被称为鸳鸯蝴蝶派,正是江苏艺术家的主体人群。主要包括来自苏、扬的通俗文学作家,以包天笑、周瘦鹃、程瞻庐、徐卓呆、程小青、范烟桥、李涵秋、贡少芹、毕倚虹、张丹斧、张碧梧、张秋虫等为代表。同时包括了其它艺术领域的艺术家们,如拍摄了《冯大少爷》《早生贵子》《四月里底蔷薇处处开》《爱情与黄金》的洪深、导演了《战功》《小厂主》《透明的上海》的陆洁、导演了《阎瑞生》《人心》《公平之门》《可怜天下父母心》的顾肯夫、演出《谁是母亲》《地狱天堂》《逃婚》《失意的英雄》《韩湘子》等片的陈秋风,出演《孤儿救祖记》《玉梨魂》《苦儿弱女》《弃妇》《摘星之女》《春闺梦里人》等片的王汉伦,出演《海誓》的殷明珠等。他们共同构成了早期中国影史上的“江苏力量”。
鸳鸯蝴蝶派的通俗文学作品中呈现出的丰富故事资源不仅解决了早期中国电影文化产业的剧本荒问题,而且贡献了可资借鉴的叙事技巧,向中国电影输入创作套路,奠定了中国电影讲故事的模式,揭示出简单却有效的创作逻辑:中国通俗文学创作的传统符合民族的阅读欣赏习惯,选用这种小说传统、开展结构情节设计的电影作品也自然能够实现娱乐性和消遣功能。这也正是当时电影文化产业需要接受的一种观念,电影艺术应当吸收鸳鸯蝴蝶派善于刻画人物形象的优点,用对情感的细致描绘打动当代的受众。
鸳鸯蝴蝶派亲身参与了早期中国电影艺术形态的革新,他们致力于艺术传统内容与新的媒体形式的结合,在他们的推动下,具有小说特点的早期电影的字幕与镜头、画面互为解释、补充而又成为其不可分割的整体,形成了独特的“文学化影像”,成为艺术传统与新的媒体技术融合相生的典范,是早期中国电影文化产业的亲和舆论的建构者。不同艺术类型在市场化过程中存在着互动效应,传媒为其它艺术类型的发展架构出所需的文化生态环境。艺术家们以主编的报刊为平台发表、撰写了各种影评、文章为中国电影文化产业营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和受众基础,帮助电影人提高了编剧、拍摄、表演的技能,为电影艺术提供了自省、自审与自改的渠道,培育了早期中国电影人才。
鸳鸯蝴蝶派进入上海之后,身份出现了重大改变(或者说升华)。完成了从小说作者到电影作者的创作身份转型,塑造出了早期中国电影的新形态和新状貌,形成中国电影史的独特作者格局,成为早期中国第一代电影人。该书第一次将鸳鸯蝴蝶派标识上“电影先驱”的身份,在中国电影的起点之处为鸳鸯蝴蝶派留下重要位置。这些新认识、新结论无疑让读者重新认识了江苏在影史上的区域价值,对拓展中国电影研究领域和加强江苏文化软实力建设,都有着重要意义。
二、用新的资料文献打开了洞悉鸳鸯蝴蝶派电影的视窗
该书通过整理民国一手报刊文献中关于鸳鸯蝴蝶派、电影人、电影文本、电影文化现象等资料,展示出了回归历史现场的新观念。新发现的文献和观察旧文献的新视角,共同培育出了该书具有理论意义的崭新结论。纵观之,该书文献具有三大意义。
(一)还原了隐没于历史暗角中的鸳鸯蝴蝶派电影的艺术状貌
鸳鸯蝴蝶派电影研究到了最后,学者们都遭遇了公认的瓶颈,就是20世纪30年代前的电影影像的集体缺失。1905年至1930年间,国内大小制片公司摄制750部以上的影片,被中国电影资料馆收藏的只有区区22部,其中还有11部是残本,这使得鸳鸯蝴蝶派电影研究缺乏基本的影像参考,难以生长延续。如何迎难而上?该书直抵历史现场,披览《良友画报》《上海画报》《电影月报》《电影杂志》《影戏杂志》《大中华百合特刊》《开心特刊》《明星特刊》《天一特刊》等一手报刊文献,从影评、报道中间接探看早期中国电影的字幕、表演、光线、镜头、特技等景象,让读者看到了徐卓呆导演的《济公活佛》一片的“忽隐忽现,令人如真着妖魔”的特技效果;电影《玉梨魂》的光线,“多浓美的软光,令人悦目外,还增加美点不少”(冰心:《如此离婚》,《申报》1929年1月4日);《春闺梦里人》中陈时英远征他乡,受伤客死,为亲人思念的近景影像;朱瘦菊导演的《就是我》中的逼真景,“吻合剧情”“与真者初无二致”。作者还在《电影月报》中发现,徐碧波是战争片《战海精魂》的编剧。当时战乱频仍,电影并非只关注男女情爱,也关注时局、战争。这部影片在人员调度、布景安排、资金投入上都比一般影片复杂,“军衣军用品及帐篷等,皆由自备,费用竟达十万,演员万余人,战马四千余匹,复有飞机及种种费用,共需十五万元之巨”(《友联影片公司摄制新片战海精魂》,《申报》1928年5月8日)。
该书对已无影像留存的鸳鸯蝴蝶派电影艺术的形态还原证明了自身的价值。这些被挖掘出来的珍贵镜头证明了鸳鸯蝴蝶派对电影艺术的探索,显现出艺术与技术正在初步融合的早期中国电影的影像生命力。
(二)揭示出鸳鸯蝴蝶派在早期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多维角色
鸳鸯蝴蝶派对早期中国电影的贡献不止于编撰剧本,而是包括了电影编剧创作、电影市场开拓、电影报刊编撰、电影艺术探索等多类工种。囿于文献资料所限,多数研究还是集中在对小说原本与改编剧本的分析上。该书从文化产业的视角出发,充分肯定了他们在电影编剧创作、电影市场开拓、电影舆论构建、电影艺术建构、电影人才培育等领域的突出贡献,展现出他们更加多元的职业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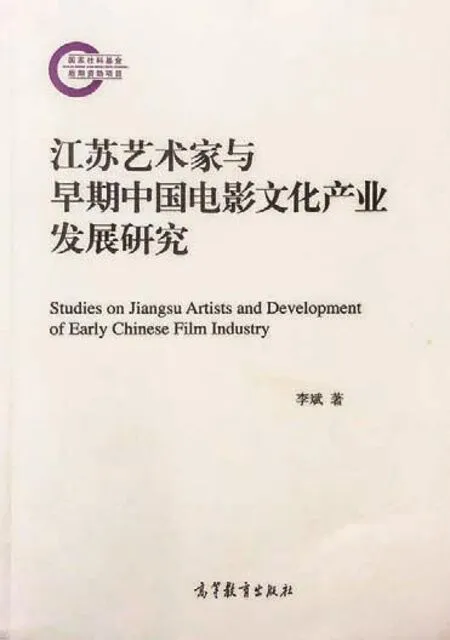

包天笑编剧的《挂名的夫妻》剧照
为了确认鸳鸯蝴蝶派在电影史上扮演的多元角色,该书采用了总分式逻辑,先从宏观的层面评析他们的电影角色,然后选择重点和典型来切入详谈,让读者对他们的职业角色有一深刻印象。在论述鸳鸯蝴蝶派对电影舆论的推动作用时,该书分析了鸳鸯蝴蝶派发表在各大报刊的大部分电影评论,其中对周瘦鹃发表在《申报》上的《影戏话》文献的整理最有价值。《影戏话》是香港科技大学陈建华教授在《文人从影——周瘦鹃与中国早期电影》(《电影艺术》2012年第1期)一文中较早“发现”的,但陈建华提到的《影戏话》的篇数为14篇,该书作者逐一翻阅《申报》后认定有16篇《影戏话》,足见文献查找之细。该书顺势提出的结论尤为可贵:《影戏话》是以周瘦鹃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正式走向电影的起点之作,是鸳鸯蝴蝶派与电影发生整体性关联的思想入口,更是鸳鸯蝴蝶派推动民族电影文化传播的舆论武器。源于这些扎实文献提供的细节支撑,一个在电影行业众多领域大有作为的鸳鸯蝴蝶派的立体多维形象才得以站立,且让读者信服。
(三)展示了鸳鸯蝴蝶派参与早期中国电影产业实践的动态细节
从整体框架来看,该书遵循了从面到点的研究思路。在上编中,将电影文化产业发展分为电影编剧创作、电影舆论构建、电影市场开拓、电影人才培育、电影艺术建构等几大类,据此梳理鸳鸯蝴蝶派对中国电影文化产业的推动作用,包括江苏艺术家进入早期中国电影文化产业、江苏艺术家与电影编剧创作、江苏艺术家与电影市场开拓、江苏艺术家与电影报刊编撰、江苏艺术家与电影艺术探索、江苏艺术家与创意阶层成型、江苏艺术家电影实践的当代启示。下编选取典型个案来说明他们的广泛活动对早期中国电影文化产业的生产、消费与传播过程的整体影响,包括周瘦鹃与早期中国电影文化产业、包天笑与早期中国电影文化产业、徐卓呆与早期中国电影文化产业、范烟桥与早期中国电影文化产业、徐碧波与早期中国电影文化产业,让读者看到了鸳鸯蝴蝶派在早期中国电影史中具体生动的活动,有助于读者重新理解鸳鸯蝴蝶派的电影史地位。

周瘦鹃编剧的《水大鸳鸯》剧照
在谈及鸳鸯蝴蝶派的电影活动时,以往的著作大都语焉不详,泛泛而论说他们编了多少剧本,导了多少影片等,但读者更感兴趣的是“鸳鸯蝴蝶派究竟在早期中国电影圈里做了什么”。该书就以详实文献为窗,让读者得窥鸳鸯蝴蝶派在电影圈内的活动状貌,如周瘦鹃与制片方发生冲突、包天笑与剧组泛舟湖上、徐卓呆依靠电影收入在上海买房等生活景观呈现于读者眼前。又如,旧址难觅的苏州公园电影院是徐碧波、程小青在苏州从事户外电影放映产业的重要成果,该书作者从浩如烟海的民国报刊中,还原出了一座园中“有竹篱”“栽以花木”“再数年者,必有扶疏可观之致矣”的清晰的“公园电影院”形象。这种抵达历史现场的分析廓清了人们对鸳鸯蝴蝶派电影活动的认识,为作者提出的“鸳鸯蝴蝶派不仅是文学艺术流派,而且是文化创意阶层”的结论提供了坚实论据。
朱栋霖认为:“什么是贯穿于推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是20世纪对人的发现:人对自我的认识、发展与描写,人对自我发现的对象化。”(《人的发现与文学史构成》,《学术月刊》2008年第3期)还原历史现场,本来就是还原人的生活和生存的状态。该书凸显文献史料特色,依靠文献史料开展层级剖析,重新发现鸳鸯蝴蝶派作为中国电影“局中人”的职业角色,确定了鸳鸯蝴蝶派及其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值得学术界给予充分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