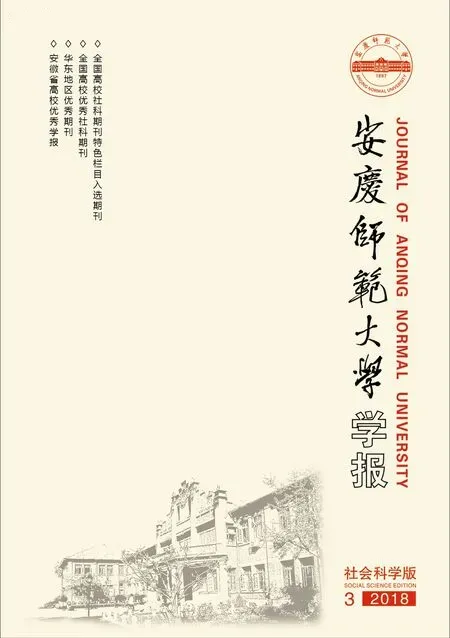1946年“制宪国大”期间《大公报》的民主诉求
张维达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89)
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举行的旧政协会议通过《宪法草案案》,决定成立宪草审议委员会,根据政协原则修改国民党1936年公布的《五五宪草》,制定体现英美宪政精神的民主宪法。然而,由于国共两党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宪草审议活动无果而终。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单方面在1946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举行“制宪国民大会”(“制宪国大”),并以宪草审议委员会持保留态度的《政协宪草》为蓝本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制宪国大”因为违反政协决议,又为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召开,遭到中共与民盟的共同抵制,只有中间党派中的青年党与民社党以及少数“社会贤达”参加了国大。
《大公报》对“制宪国大”予以高度关注。事实上,《大公报》一开始反对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大。在1946年11月5日的社评《国民大会是否就开?》一文中,《大公报》认为:“政府召开国大的目标是正确的,……但若不待其他党派的代表参加,即行开会,那自然也开得成,并且会中也可争论甚少,但却缺乏了民主统一的规模,甚且形成分裂。……我们一定要少意气,多理智;一定要使这个国民大会是民主统一性的,而制订的是一部民主统一的宪法。”[1]但在国大召开后,《大公报》并未抵制,而是在此期间连续发表多篇社评,就制宪相关问题进言献策。通过这些社评,可了解《大公报》对“制宪国大”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所持的政治主张与态度。
一、反对以主义冠国体
《五五宪草》第一章《总纲》第一条为“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共和国”[2]242。这个带有国民党一党专政色彩的条文自公布起即遭到各方人士的反对。张君劢认为:“假定以三民主义四字当形容词写下去,则如将来发生有关各人思想,各党主义的诉讼问题时,岂不可以根据宪法判罪吗?而合于三民主义与不合于三民主义,又成为思想上顺逆之标准,……以三民主义作为国体的形容词,不但不能息争,而且引起纷争,至于永无穷尽之境。”[3]《政协宪草》将其修改为:“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2]282而后立法院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加以沿用。“制宪国大”召开后,宪草进入分组审查讨论阶段时,围绕国体条文,国民党与青年党、民社党展开激烈争论。青年党与民社党主张将国体条文修改为“中华民国为民主共和国”,反对以主义冠国体;而国民党则坚持在国体条文中突出三民主义。由于国民党代表占多数,当时的宪草审查会先后做出修改国体条文为“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民主共和国”[4]和“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主共和国”[5]两项决议,均遭到青、民二党抵制,两党代表甚至以退席向国民党抗议。
早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1946年11月22日刚由立法院通过公布时,《大公报》就认为“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的表述“啰嗦”,主张修改国体为“中华民国为民主共和国”[6]。在随后的国体之争中,《大公报》坚定站在青年党与民社党一方,反对以三民主义冠国体。1946年12月18日《大公报》发表社评《关于宪草第一条》,表示无论《五五宪草》“三民主义共和国”,还是《政协宪草》“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以及宪草审查会做出的两项修改,均不如“民主共和国”来得“瞭朗”[7]。社评认为,国民党当前既“尚未真正统一全国”,也“不希望永久实施一党制”,中国的现状是“多党并存,贫富悬殊,人民的利害及意见分歧不一”。因此,“以一党主义冠诸国体,是不切实的。强制人民接受这个国体,不仅欺人自欺,或且将贻纷扰于无穷。”[7]社评指出:“根据孙中山先生遗教,宪政时期即还政于民。‘还政于民’四字不论作何解释,总不能再还政于国民党一党。若宪法规定中华民国是三民主义国家,则国家已不啻为国民党所有,将置四亿人民于何地?若然,政权还来还去都是给国民党了。‘还政于民’,将何以自圆其说?”社评还指出,《建国大纲》并未规定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国家,《训政约法》第一条也没有以主义冠国体,而是规定“中华民国永为统一共和国”[7]。社评认为,宪法需要明确具体,能“以依据为准绳”。三民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概念,“内容浩繁”,至今无人能给其“下个定义”,以此冠国体,“如何责人民以遵守。以此主义冠诸国体,可以被人利用任何一语一义,歪曲内容,而思想自由也将成为具文了。”社评最后明确表示:“中华民国上不必挂主义的招牌。”[7]
后来,在青、民二党施压下,国民党方面做出让步,同意恢复《政协宪草》原条文,青年党与民社党则放弃原主张,各方对此问题达成妥协[8]。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最终规定国体为“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2]553时任“制宪国大”副秘书长的雷震认为:“如此,这个所谓三民主义,就不是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而是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了。”[9]152
二、反对扩大国民大会职权,建议实行责任内阁制
在“制宪国大”召开期间,除国体外,争论最激烈的是国民大会职权问题。孙中山将政治权力分为人民行使的政权和政府行使的治权。他认为欧美代议制民主属于间接民主,不充分。为此,他主张人民直接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民权,每县由人民直接选举国民代表组成国民大会,代表人民行使政权。同时,由政府按照“五权分立”思想建立“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行使治权,如此可实现“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孙中山的设想,大多在其生前未能实践,而且其思想也有不完善之处,因此给后面中国的制宪者带来了困扰。《五五宪草》规定国民大会有极大的职权,但是每三年才能由总统召集开一次会,且会期只有一个月,这使得国民大会“大而无用”,而且国民大会的职权同立法院存在冲突[2]245。政协《宪法草案案》提出“无形国大”的主张,即“全国选民行使四权名之曰国民大会”,这样,通过取消国民大会,真正由全国人民行使民权来防止国民党借国民大会来操纵政权。后来,鉴于国民党方面一再发难,《政协宪草》中恢复了国民大会的设置,但是职权基本仅限于选举总统副总统,类似美国总统选举的选举人团。
“制宪国大”召开后,国民党代表坚持要求扩大国民大会职权,主张“限制立法院权力”,恢复《五五宪草》中规定的国民大会职权。对此,青年党与民社党坚决予以反对。《大公报》在这个问题上,支持青、民二党的主张,主张制宪按照政协原则,反对赋予国民大会较大的权力,甚至提出取消国民大会。在1946年12月6日《辨清一个问题:国民大会并不等于人民》一文中,《大公报》强调:“直接民权一定要由人民自己来行使,国民大会只是人民的代表,不是人民的本身;其权力来自人民的委托,不是人民政权的本身。”“国民大会并不等于人民,国民大会的权力也并不等于人民的权力。要尊重人民的政权,唯有将四权归于人民自己行使;如果只争国民大会的权力,实与人民的政权不相干。”[9]宪草修正案中,规定立法院为民选,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模仿英国实行责任内阁制。《大公报》认为,据此“国民大会可以不设”。由立法院和监察院共同组成国会,“政府机构便可简单灵活了”[10]。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沿用了宪草修正案的设计,虽然在法理上将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共同视为欧美民主国家的国会,但在条文上没有赋予国民大会太大的职权,只将其作为一个选举总统副总统的机关。
《大公报》同时还支持政协《宪法草案案》中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实行责任内阁制的原则,反对总统权力过大。在《论宪草中的政府责任》一文中,《大公报》认为宪草修正案有关《总统》一章的规定不够明晰。如第三十七条“总统统率全国陆海空军”并未详细规定总统如何行使统帅权,在《大公报》看来,“这是个很大的漏洞”。第四十四条规定“总统得依行政院决议发布紧急命令”,《大公报》主张立法院常年开会,以防总统借发布紧急命令之际扩大职权[11]。宪草修正案虽然规定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但《大公报》认为相关规定仍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如第五十七条规定“行政院各部会首长,及不管部会的政务委员,由行政院院长提请总统任命之”[2]304。《大公报》建议将这条中“总统”改为“立法院”[11]。
此外,关于宪草修正案中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的具体规定,《大公报》也认为可以改进。第五十八条规定:“行政院对于立法院通过之法律案、预算案、条约案,如认为该案窒碍难行时,得经总统之核可,于该案送达行政院十日内,移请立法院覆议,覆议时如经出席立法委员三分之二维持原案,该案行政院院长应予执行或辞职。”[2]304《大公报》认为此项规定“可能使立法院的决议及法案都须经三分之二通过才能发生效力。这不但贻误事机,而且大大削弱了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的原则。”主张为慎重计,“预算案及条约案可移请立法院复议,其他一般法案经立法院通过即可,不应再移请复议。”《大公报》在社评结尾指出:“民主国的政府应对人民或人民的代表机关负责,并在宪法上明白规定如何负责,否则‘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只是一句空话。我国革命以来,政象纷纷,从不曾建立负责的政府。现在制宪开始,请大家注意这个根本问题。”[11]表达了希望在中国建立责任政府的美好愿望。
三、拥护地方自治,反对中央集权,呼吁民族自治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是宪法中另一个重要问题,《大公报》在1946年11月28日《集权与均权:宪草修正案中地方制度》一文中认为《五五宪草》中相关规定使省的地位附属中央、县的自治权受束缚、县长人选受中央操控,会导致“地方全无独立自由的权限”[12]。政协决议《宪法草案案》规定:“1.确定省为地方自治之最高单位。2.省与中央权限之划分,依照均权主义规定。3.省长民选。4.省得制定省宪,但不得与国宪抵触。”[13]《大公报》赞成政协关于宪法中地方制度规定的四项原则,指出四项原则“一反五五宪草精神,而确立均权制度”[12]。政协结束后,由于国民党方面不满政协决议,因此《政协宪草》相关规定一定程度上偏向于中央集权,《大公报》对此提出批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省得召集省民代表大会,依据省县自治通则制定省自治法,但不得与宪法抵触。”[2]312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省法规与国家法律抵触者无效”[2]312。《大公报》认为,省县自治通则既然由中央制定,那么“中央要制定何种自治通则,则不得而知”。省宪只需“不抵触国宪”,而省自治法要受“宪法”“自治通则”“国家法律”三重束缚[12]。针对宪草第一百一十六条“省自治法制定后,须即送司法院,如司法院认为有违宪之处,应将违宪条文宣布无效。”和第一百一十七条“省自治法施行后,如因某项发生重大障碍时,由司法院召集有关方面陈述意见后,由立法院院长监察院院长与司法院院长组织委员会,以司法院院长为主席,提出方案解决之。”两项,《大公报》认为这更是对地方自治的束缚,“在实质上,仍是中央集权。”[13]《大公报》在社评结尾中指出:“今日中国需要民主与建设,地方非有权不可。要解决实际政治纠纷,中央尤应多放权限出去,让地方享受更大的自由。”[12]由于国民党方面始终认为地方自治尤其省自治会对保障中共解放区民主政权有利,故在这个方面不愿让步,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仅将宪草修正案第十一章《省县制度》改名为《地方制度》,未对条文文字做较大的调整。
此外,《大公报》还支持少数民族代表呼吁在宪法中加入保障民族自治条文的要求。政协《宪法草案案》曾规定:“聚居于一定地方之少数民族,应保障其自治权。”[13]《政协宪草》虽然规定民族平等,但是对民族自治却并无具体规定。《大公报》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漏”[14]。后来在“制宪国大”分组讨论宪草时,内蒙古代表主张在宪法中保障民族自治。《大公报》1946年12月5日发表社评《内蒙自治问题》,在开篇援引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说:“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是包括外求国家民族之平等及国内一切民族之平等的主义。我们不愿受异民族统治,不愿受外国的不平等待遇。自然不应该以统治民族的姿态,君临国内的少数民族。”[15]《大公报》反对“大汉族主义”,指出“否认民族问题,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统一的基础,应该放在地方均权——少数民族有自治权之上。”“没有一个大国不是许多民族的混合以至混血的。大汉族的偏见是应让它过去的。”[15]进而主张在宪法中保障民族自治,促进民族团结,“我们不但同情内蒙代表,赞成上宪法上规定其应有的自治要求;即对边疆及散居内地各省的少数民族,也应开明的让他们自治,俾各民族团结一致,造福国家。”[15]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在第一百一十九条和第一百二十条分别规定:“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制度,以法律定之。”“西藏自治制度,应予以保障。”[2]568相比中国以前的宪法文本而言是一个进步。
四、呼吁宪法保障人民的权利与自由
关于宪法中人民权利与自由的相关规定,《大公报》也给出了许多建议。《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尚未公布时,《大公报》于1946年11月21日发表《减少宣传,多给自由》一文,明确提出:“宪政即将开始,言论首先应该绝对自由。”[16]在《大公报》看来,言论自由是宪法上重要的自由权之一。“人之为人,实在应有自由说话的权利。自由说话,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是不可抗的时代潮流,顺之者,为进步,光明;逆之者,为反动,黑暗。”[16]《大公报》认为,在“制宪国大”召开之际,国民政府正宜广开言路,通过言论自由博采众议,团结人心。“国大在开会,此时应有宪政气象,使民间充分呼吸自由空气。……通过自由言论,多多听取人民对宪法及对政治的种种意见。这时正宜广开言路,让全国人民及不同党派或团体说话绝对自由,而不可出现有干涉言论的事。”[16]
《五五宪草》有关人民自由的相关规定,大多在后面有“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这样就给政府干涉人民自由提供了借口[2]243。《政协宪草》与《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则采取直接尊重制,删去了“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大公报》认为这样“进步多了”。但是,《大公报》认为宪法关于人民自由的规定还有可改进之处。宪草修正案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2]300。《大公报》认为这条可改为“人民有信仰之自由”,因为“信仰自由,不仅为宗教,还包括更广泛的思想自由”[6]。宪草修正案第二十四条规定:“关于以上所列之自由权利,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2]301《大公报》认为应删去此条,否则“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可能日后会成为政府“另定法律限制人民自由权利的借口”[6]。
在人民权利方面,《大公报》从全面内战的现状出发,主张制宪要特别重视人民的生存权与受教育权。在1946年12月7日《人民有生存权与受教育权》一文中,《大公报》开篇先描述内战下国内的惨状:“双方在比战略,竞争战果,成千累万的士兵死亡枕藉,流血盈野。在炮火下的人民,朝不保夕,田地荒芜,庐舍为墟。战火烧不到的地方,也征兵征粮,急如星火,壮丁流离转徙,失业恐慌日益深刻化,老弱妇孺与饿寒疾病相挣扎。……大多数人民在工商不景气下,走投无路,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全国任何事业,均无发展的些微希望,以勉渡难关万幸。……人人不得其所,民气消沉,人心陷溺”[17],进而指出人民当下最需要的是生存权。《大公报》告诫国大代表:“如果这点要求不能兑现,他们对于什么宪政都不会感觉兴趣。”在《大公报》看来,生存权是人民“最基本的权利”,《大公报》向国大代表们呼吁:“一部国家的根本大法,对于人民的权利必须有周到的规定。……我们要求全部宪法的精神应以这种权利做基础。……一切讨论与规定,应以是否尊重人民的生存以及生存得合理为衡量判断的尺度。”[17]
在《大公报》看来,人民的受教育权与生存权同等重要。“为求人民生存的合理,教育一点,特别值得强调。”[17]《大公报》认为,“一部良好宪法的执行成功,也有赖于全国人民知识与能力的增强,否则国家搞到怎样地步,人民也没有力量出来作主的。”[17]宪草修正案第二十二条规定“人民有受国民教育之权利与义务。”[2]300《大公报》认为,这种规定“实在太空洞”,主张在宪法中应对教育有几条较明确的规定,如:“一,每个未达成年的国民,应有免费受幼稚园、小学、中学(可能时连大学在内)教育的机会。……二,教育的目的在启发培养人民健全的身心,重科学,求真理。依照资质的高低,施以不同的培育方法……三,……学校行政不宜受政治影响。校内学术思想绝对自由,一切党派党团的活动都应退出学校。”[17]后来,胡适、朱经农等人在“国大”中提出十条促进教育发展的条文,要求在宪法第十三章《基本国策》中设立教育专章,得到大会的采纳[2]1109-1110。《大公报》在制宪国大将要结束的1946年12月24日发表《制宪中谈教育问题》一文,指出在宪法中详细规定教育问题固然好,但是“宪法贵能实行,而无取乎空洞理想。”[18]《大公报》接着介绍内战下中国教育界的危机情形:“唐山工学院罢教,因为教育部每月仅拨经费四百万,与实际开支相差三千五百余万,校务无法推进;教授待遇,最低的只十一万元,最高也不过三十五万。平津各大学教授也因天寒无法举火,联名宣言要求改善待遇。……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因教育厅两月不发薪被迫全体停教”,发出“这是何等的悲惨!”的控诉,进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重视教育。“请将军费政费裁减一点,内战可以不打,教育不可不办。”[18]《大公报》在社评后半部分再次强调教育超出于政治之外,呼吁教育自由。“教育超于党派以外,一切党派要确实退出学校,勿以学生为政争的工具。政府在观念上尤其要改正两点,各级教师都是为国家为社会作育人才,而不是为一党培养党员,过去公立学校教员必须入党的办法不应再有。其次,学生的思想不必干涉,法律只问行为,而不能管人思想。”[18]《大公报》这些言论表达了对国民党党化教育政策的反对和对中国教育自由发展的美好展望。
五、一厢情愿的幻想
从社评内容来看,《大公报》的政治主张与以中间党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类似。《大公报》推崇英美的自由与民主,在制宪方面就国体、中央政制、地方制度、人民权利与自由等方面畅所欲言,希望国大根据政协原则制定一部民主宪法。《大公报》的呼吁与建议,部分得到了大会的采纳,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从条文上看是“一部典型的美式宪法”[19]。在国大结束次日,《大公报》发表社评《国民大会闭幕了》,认为这部宪法“实是比较进步的。较之《训政时期约法》及《五五宪草》,尤其进步。……就这部宪法的本身而论,虽有不少可议,而大致是可取的。”[20]
由于“制宪国大”系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单方面召开,中共与民盟共同抵制,《大公报》也承认这一点,在社评中指出:“这部宪法的最大缺点,还不在它的本身,而是这次的制宪国大缺少了一个和平团结的规模。一个主要的党派未参加,而半个中国还在打着内战,因此大大减损了这部宪法的尊严性。”[20]《大公报》希望以制宪为契机,促进国内和平,为此呼吁:“现在国大闭幕,宪法完卷,继此而后的国家问题,还更应该要力求和平团结的实现;尤其政府要努力根据这部宪法中的进步精神,去谋求中共民盟在参加行宪。这一点,极关重要。”[20]
然而,在中共和民盟看来,宪政要在国内和平的环境下得到国内各政治势力一致同意才能实行,国民党片面召开的“制宪国大”并不能广泛反映民意,《中华民国宪法》也不具有合法性。中共驻沪代表华岗在1946年12月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按照政协决议程序,必须改组政府后始能召集国大,制定宪法,如此,才能包含政协精神。除此,闭门造车,乱抄一阵外国宪法,毫不顾及现实,我们根本否认它。……国大就是按照政协协议全部通过,中共以国大是非法组织的,也不予承认。”[21]民盟在1946年12月31日也发表声明:“制宪的国民大会必须为全国人民代表所愿共同参加的一种会议。人民对宪法有共议共制的权利,而后人民才有共遵共守的义务。只有用民主统一方式产生的宪法,而后宪法才有真正民主的内容,而后宪法才能发生真正的效力。……中国民主同盟站在维护政协的立场,拒绝了参加此次国大,因此,本同盟对今天公布的宪法愿保留其接受的权利。”[22]
对蒋介石与国民党而言,他们并无真正实施宪政的诚意,宪政在他们眼中主要为赋予统治合法性和“剿共”的工具。蒋介石在1946年11月25日演讲时表示:“任何宪法都有修改的规定的,这次宪法草案通过之后,如果将来发现有不妥的地方,我们在下届国民大会,仍旧可以提出修改,使之符合我们的理想。我们现在所要采取的步骤,是如何在这恶劣的环境下,打破共产党中伤本党的阴谋。”[23]国民党于1948年举行“行宪国大”,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总统凌驾于宪法之上的特权。《中华民国宪法》并没有给中国人民真正带来民主和自由。
在当时内战的环境下,和平是民心所向,民主要在和平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施。《大公报》在呼吁民主的同时,也不忘呼吁和平,在1946年11月30日的社评《议宪与打仗不能并行》一文中明确指出:“宪法草案已上议程,而半个国家还在伏尸盈万,流血千里。这太不可想象了!……人民是最能理解现实的。现实的苦痛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他们时时刻刻辗转呻吟于战祸之下,而偏说就要民主了,一切为民所有,一切为民所治,一切为民所享。这与冬烘书呆子的讲仁义说道德有何两样?人民是憧憬未来的,他们尤其渴望目前的安定,大家过个太平日子。使民休息,使民安定,在目前比什么都重要。”[24]但是,《大公报》在“制宪国大”期间,始终对执政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抱有希望,希望在国民党的“宪政”框架下通过渐进式改良,来解决国家和社会的各种问题,而不赞成中共的武装革命,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历史证明,《大公报》呼吁的西式民主并不符合中国国情需要,只有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真正通过推翻国民党专制统治实现了主权在民。